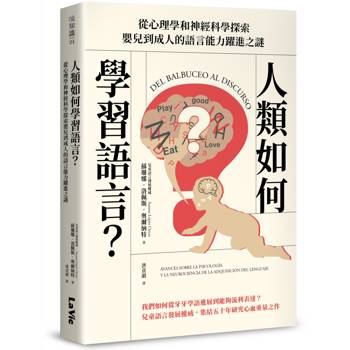〈在聽與說之際,大腦會選擇要注意哪些語言細節:競爭與協商〉
語言並不是孩子周遭環境中唯一令他感興趣的事情。還有許多其他事情也會激發他們的好奇心、吸引其注意力並促進能力發展。儘管本書將重點放在語言上,但事實上,在所有書中論及的現象發生的同時,其他認知、社會和生理的變化也會出現。儘管本書以語言為焦點,但學習者也必須做出選擇。他們的注意力必須處理語言經驗中種種面向,而忽略其他部分,這是他們必須要做的事情,從幾十個語言細節中擇一全神貫注。
舉個例子好了。洗澡時,爸爸對十二個月大的小孩說:「現在我們要幫腳腳搓肥皂了。」小孩可能會將注意力集中在「現在」或「腳」上,因為他還太小,所以無法明確察覺句子當中的每個元素。如果他將注意力放在「現在」上,他可能從那時候就會開始理解「現在」這個字,並在每次聽到同一個字時,覺察力會越來越強,可能兩、三個月後,他就能說「先哉」來表示「現在」。如果孩子歲數再稍微大一點,比如二十二個月大,那他就不用像小孩子一樣全神貫注地把焦點放在爸爸這句話中的某個片段,因為他會自動迅速理解整個句子。真可謂天壤之別!因此,在那個階段,他反而會把注意力轉向其他語言面向。比如將心思放在造句,好跟爸爸開玩笑,像是說:「不是這個腳,不對,是這個腳,這個腳!」邊把腳藏起來。
孩子在努力學習某個語言細節時,會出現所謂的「FIS 現象」,這種現象只會出現在這個時候,以前不會出現,以後也不會有。FIS 現象之名是源自說英語的孩子因為還說不出「魚(fish)」,因而用「予咦(fis)」來指稱充氣塑膠魚。如果大人問他:「這是你的予咦嗎?」,孩子會拒絕對話。但如果問他:「這是你的魚嗎?」,孩子就會回答:「對,這是我的予咦」。在這種時刻,面對他自己發錯音的「予咦(fis)」和正確發音的「魚(fish)」,孩子能夠察覺到兩者發音之間的差異,因此對大人所使用的「予咦(fis)」,他不予以回應,但卻會對「魚(fish)」做出回應。他能感知的東西比他能說出來還要多。在習得語言的過程中,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很多不同的案例中也都有過相關報告。重點在於,孩子當時正努力將心力集中在發不出的那個小小的語音上(即 -ish),而且他看起來並不想錯過能夠好好學會的機會。
關於語言注意力,有人提出競爭與協商一說,意指大腦每次在面對外界刺激時,會選擇要注意什麼以及不注意什麼。注意力會傾向聚焦於語言中的某個細節(聽到的或說出來的),這種有所偏好的選擇是種必然,畢竟資源有限。每次資源都只能用在單一焦點上。只要是人都會這麼做,這並非小孩獨有的行為。舉例來說,學西班牙語的孩子幾乎都會用「他哉(tá)」來表示「他在(está)」,而且這種講法會用上很長一段時間。有時大人講太快也會這樣說。大人如果想要,幾乎不用花什麼力氣就能正確發音。而孩子在語言發展到某個階段時,會說成「他栽(tá)」,是因為儘管能察覺到「他栽(tá)」和大人所說的「他在(está)」之間有差距,此刻他就是沒辦法說得更準確。
這段對話來自「瑪麗亞語料庫」第 299 段,這是從十九個月到四歲之間紀錄語言習得的縱向語料庫。在這段對話中,瑪麗亞和她舅舅正在翻閱一本雜誌。瑪麗亞當時二十四個月大:
舅舅:「你看,我們來這裡找安東尼奧,看在這本雜誌裡找(開始翻雜誌)。」
瑪麗亞:「他在那裡嗎?」
舅舅:「應該在。」
瑪麗亞:「他栽(在)…去糟(找)安東尼奧」
舅舅:「我們去找安東尼奧好嗎?」
瑪麗亞:「好,他栽(在)…去糟(找)安東尼奧」
瑪麗亞在同一個場景中說了「他栽(ta)」和「他在(está)」。說「他栽(ta)」的時候,並不是因為她聽不出「他在(está)」的發音,也不是因為她不會這個字的發音。她其實已經會說「他在(está)」了。但大腦在同時面對多個注意力焦點時,語言處理系統會超載,這時就必須協調分配資源,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好好發出完整的「他在(está)」上,就是放棄將注意力放在這個字,所以無法做到完整或準確的發音,但以此換來的好處是可以造出更長而且難度更高的句子,即:「企遭(去找)安東尼奧(Ta a buscá a Antonio)」。因為大腦資源有限,語言處理系統必須做出取捨。在初期發言中,她已能說出完整的「他在(está)」,那是她已經說了很多遍而且長度很短的短語。但當她把注意力放在比較長的句子時,她的發音就不行了,沒辦法準確說出「他在(está)」,但換來的是她能夠造出複雜的句子。就像幾乎所有二十四個月大的孩子一樣,瑪麗亞還在學習母語的語音系統,學習如何正確發音。但要做到能說出口、足以產出語言,光是將心力放在發音上是不夠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句法、語義,甚至語用層面的訊息。想當然爾,這項任務肯定很艱難,而且全都得同時處理。在前述語境中,遇到困難的情況,也就是必須同時說出「他在(está)」並造長句表達「正在找安東尼奧」的意思時,她已經學會說「他在(está)」的能力幾乎消失殆盡。
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隨便一個小孩子(大人也是)的模仿能力都比產出能力更厲害。前提是不要因為害羞或顧慮而不敢開口——而這種情況在大人身上卻非常常見。模仿會比較容易,因為不需要靠自己組織句法、語義或語用的內容,別人已經幫我們把這些東西都準備好了。我們只需要組織語音和發音,所以自然更容易能夠成功仿說。跟大家分享一個老掉牙的笑話:有個大人喜歡喝咖啡,但他不會說「咖啡(Café)」這個詞,只會在酒吧裡點「苦艾酒(Vermut)」。後來他喝膩了苦艾酒,好不容易才學會說「咖啡(Café)」。於是他走進酒吧說:「咖啡。」,而服務生問他:「要純咖啡(solo)、加奶(con leche)、加少量牛奶(cortado)、還是要無咖啡因(descafeinado)?」他一聽,腦子全亂了,最後只好說:「那……還是苦艾酒吧(Vermut)。」這種退回舊有用法的情況,看起來像是退步,但其實並不是。他並沒有忘記「咖啡」這個詞,甚至也聽懂了服務生的話。只是要同時處理、發出那些新詞仍然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必須將心力放在同時協調大量的全新語音發音才可能做到。
〈語言感知不只用到聽覺:一個人說話時,我們會看他的嘴和頭,並共享溝通情境〉
前面提到了,寶寶需要更多線索來克服實際辨識單字的難點,那就是從聲學上來說,單字的語音在每次發音時其實都會有所變化。我們還需要找出更多變因,才能解釋為什麼到了二十四個月大時,嬰兒的語言感知能力能取得初期成果,也就是父母會說出:「說話要小心,他都聽得懂。」的時候。語言雖是用耳朵聽的,但聽的同時會看見語言使用者的臉部,也會留意其嘴部、頭部動作和眼神注視的方向。孩子們也會觀察語言使用者在說話時同時做出的手勢,某種程度上,他們是跟著說者的眼神與肢體動作來推斷他們所說的內容。人類在理解語言時會出現多模態的狀態,聆聽語言語音的同時也會接收非聽覺的感官訊息。
大人通常和嬰兒面對面說話,這樣他們會更容易理解對話的內容。目前確知的是,能看到說話者的臉會更容易理解語言的語音。關於這個部分有個實驗為例,研究人員找來兩組九個月大的嬰兒進行實驗。兩組都聽了第二語言的同一組新音素,在這個實驗中所使用的第二語言為中文,但兩組在實驗室中接觸的情境不同。在社交情境中,一位母語中文的女性和嬰兒說故事,並與他玩耍。而另一組嬰兒的狀況則是聽到完全相同的語音,也看到一樣的畫面,但是從電視螢幕中接觸到的,沒有社交互動。而在社交情境中的嬰兒明顯學得更好,更能區分新語音的差別,應該是因為他們在這種情境下專注力更高,而十二天後,研究人員透過行為表現及腦部影像也證實了這一點,反倒是處於非社交情境中的嬰兒什麼也沒有學到。研究人員在九個月大的嬰兒身上也觀察到了微妙的個體差異。在其他實驗中,研究人員透過腦部造影測出,會將視線從對話的大人轉移到大人所談論物體的嬰兒,更能夠辨識新單字的語音,相較之下,只會看著物體或只看著大人的嬰兒,辨識能力就比較低落。
與他人溝通、與對話者處於相同的溝通情境,對於孩子們語言感知能力的成長可謂關鍵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大人所使用的單字,會對應情境當中實際存在的物體或動作,談論的是存在於此時此地的事物。因此,嬰兒才能夠將成人使用的單字發音,與存在於當下情境的指涉對象搭配起來。比如玩球的同時提到「球」,孩子就能將「球」這個字的發音和物體連結起來。與嬰兒之間的交流,會讓他們更容易發現單字與句子的形式和功能之間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語音與意義之間的關聯。這個階段的語言習得重點在於理解語音背後的意義,這一點有助他們更留心發音的細節,並聚焦於處理這個單字的形式。
社交互動幫助嬰兒更加專心,也能更加注意對話情境中出現的語音,同時也提供他們一種連結的經驗,也就是活化大腦機能,結合感官與行動,即知即行,聽到什麼就嘗試去模仿。嬰兒聽到真人說話時,比起非生命體所發出的語音,他們對語言的注意力向來明顯更高。舉例來說,嬰兒看來並無法從電視中聽到的語言得到語音感知能力的成長效果。如果只聽語音而沒有畫面,也就是只有純粹聽到語言發音,則是幾乎沒有學習效果可言。不過在孩子年紀較大的情況,因為學習方式變了,學習語言的面向也有所不同,就必須另當別論。
有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可以說明幼童無法有效利用源自無生命體的語言,比如說有個兩歲半的孩子在講電話,雖然他們已經能說一些話,在家裡大人也聽得懂,而且「什麼都聽得懂」,卻還是聽不懂電話中說的內容,除非對方使用的是慣用語句。電話是只能傳遞聲音的媒介,無法提供額外的語言情報,小孩講電話時既看不到語言使用者說話時的表情、看不到對方說話時的目光所向,更不要說透過用詞遣字共享指稱的語境,他只能聽到聲音。這個例子同樣適用於那些還未掌握第二語言的成人,萬一非得打電話給該語言的母語人士,那對他來說可是很頭大的問題,肯定能免則免。
語言並不是孩子周遭環境中唯一令他感興趣的事情。還有許多其他事情也會激發他們的好奇心、吸引其注意力並促進能力發展。儘管本書將重點放在語言上,但事實上,在所有書中論及的現象發生的同時,其他認知、社會和生理的變化也會出現。儘管本書以語言為焦點,但學習者也必須做出選擇。他們的注意力必須處理語言經驗中種種面向,而忽略其他部分,這是他們必須要做的事情,從幾十個語言細節中擇一全神貫注。
舉個例子好了。洗澡時,爸爸對十二個月大的小孩說:「現在我們要幫腳腳搓肥皂了。」小孩可能會將注意力集中在「現在」或「腳」上,因為他還太小,所以無法明確察覺句子當中的每個元素。如果他將注意力放在「現在」上,他可能從那時候就會開始理解「現在」這個字,並在每次聽到同一個字時,覺察力會越來越強,可能兩、三個月後,他就能說「先哉」來表示「現在」。如果孩子歲數再稍微大一點,比如二十二個月大,那他就不用像小孩子一樣全神貫注地把焦點放在爸爸這句話中的某個片段,因為他會自動迅速理解整個句子。真可謂天壤之別!因此,在那個階段,他反而會把注意力轉向其他語言面向。比如將心思放在造句,好跟爸爸開玩笑,像是說:「不是這個腳,不對,是這個腳,這個腳!」邊把腳藏起來。
孩子在努力學習某個語言細節時,會出現所謂的「FIS 現象」,這種現象只會出現在這個時候,以前不會出現,以後也不會有。FIS 現象之名是源自說英語的孩子因為還說不出「魚(fish)」,因而用「予咦(fis)」來指稱充氣塑膠魚。如果大人問他:「這是你的予咦嗎?」,孩子會拒絕對話。但如果問他:「這是你的魚嗎?」,孩子就會回答:「對,這是我的予咦」。在這種時刻,面對他自己發錯音的「予咦(fis)」和正確發音的「魚(fish)」,孩子能夠察覺到兩者發音之間的差異,因此對大人所使用的「予咦(fis)」,他不予以回應,但卻會對「魚(fish)」做出回應。他能感知的東西比他能說出來還要多。在習得語言的過程中,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很多不同的案例中也都有過相關報告。重點在於,孩子當時正努力將心力集中在發不出的那個小小的語音上(即 -ish),而且他看起來並不想錯過能夠好好學會的機會。
關於語言注意力,有人提出競爭與協商一說,意指大腦每次在面對外界刺激時,會選擇要注意什麼以及不注意什麼。注意力會傾向聚焦於語言中的某個細節(聽到的或說出來的),這種有所偏好的選擇是種必然,畢竟資源有限。每次資源都只能用在單一焦點上。只要是人都會這麼做,這並非小孩獨有的行為。舉例來說,學西班牙語的孩子幾乎都會用「他哉(tá)」來表示「他在(está)」,而且這種講法會用上很長一段時間。有時大人講太快也會這樣說。大人如果想要,幾乎不用花什麼力氣就能正確發音。而孩子在語言發展到某個階段時,會說成「他栽(tá)」,是因為儘管能察覺到「他栽(tá)」和大人所說的「他在(está)」之間有差距,此刻他就是沒辦法說得更準確。
這段對話來自「瑪麗亞語料庫」第 299 段,這是從十九個月到四歲之間紀錄語言習得的縱向語料庫。在這段對話中,瑪麗亞和她舅舅正在翻閱一本雜誌。瑪麗亞當時二十四個月大:
舅舅:「你看,我們來這裡找安東尼奧,看在這本雜誌裡找(開始翻雜誌)。」
瑪麗亞:「他在那裡嗎?」
舅舅:「應該在。」
瑪麗亞:「他栽(在)…去糟(找)安東尼奧」
舅舅:「我們去找安東尼奧好嗎?」
瑪麗亞:「好,他栽(在)…去糟(找)安東尼奧」
瑪麗亞在同一個場景中說了「他栽(ta)」和「他在(está)」。說「他栽(ta)」的時候,並不是因為她聽不出「他在(está)」的發音,也不是因為她不會這個字的發音。她其實已經會說「他在(está)」了。但大腦在同時面對多個注意力焦點時,語言處理系統會超載,這時就必須協調分配資源,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好好發出完整的「他在(está)」上,就是放棄將注意力放在這個字,所以無法做到完整或準確的發音,但以此換來的好處是可以造出更長而且難度更高的句子,即:「企遭(去找)安東尼奧(Ta a buscá a Antonio)」。因為大腦資源有限,語言處理系統必須做出取捨。在初期發言中,她已能說出完整的「他在(está)」,那是她已經說了很多遍而且長度很短的短語。但當她把注意力放在比較長的句子時,她的發音就不行了,沒辦法準確說出「他在(está)」,但換來的是她能夠造出複雜的句子。就像幾乎所有二十四個月大的孩子一樣,瑪麗亞還在學習母語的語音系統,學習如何正確發音。但要做到能說出口、足以產出語言,光是將心力放在發音上是不夠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句法、語義,甚至語用層面的訊息。想當然爾,這項任務肯定很艱難,而且全都得同時處理。在前述語境中,遇到困難的情況,也就是必須同時說出「他在(está)」並造長句表達「正在找安東尼奧」的意思時,她已經學會說「他在(está)」的能力幾乎消失殆盡。
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隨便一個小孩子(大人也是)的模仿能力都比產出能力更厲害。前提是不要因為害羞或顧慮而不敢開口——而這種情況在大人身上卻非常常見。模仿會比較容易,因為不需要靠自己組織句法、語義或語用的內容,別人已經幫我們把這些東西都準備好了。我們只需要組織語音和發音,所以自然更容易能夠成功仿說。跟大家分享一個老掉牙的笑話:有個大人喜歡喝咖啡,但他不會說「咖啡(Café)」這個詞,只會在酒吧裡點「苦艾酒(Vermut)」。後來他喝膩了苦艾酒,好不容易才學會說「咖啡(Café)」。於是他走進酒吧說:「咖啡。」,而服務生問他:「要純咖啡(solo)、加奶(con leche)、加少量牛奶(cortado)、還是要無咖啡因(descafeinado)?」他一聽,腦子全亂了,最後只好說:「那……還是苦艾酒吧(Vermut)。」這種退回舊有用法的情況,看起來像是退步,但其實並不是。他並沒有忘記「咖啡」這個詞,甚至也聽懂了服務生的話。只是要同時處理、發出那些新詞仍然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必須將心力放在同時協調大量的全新語音發音才可能做到。
〈語言感知不只用到聽覺:一個人說話時,我們會看他的嘴和頭,並共享溝通情境〉
前面提到了,寶寶需要更多線索來克服實際辨識單字的難點,那就是從聲學上來說,單字的語音在每次發音時其實都會有所變化。我們還需要找出更多變因,才能解釋為什麼到了二十四個月大時,嬰兒的語言感知能力能取得初期成果,也就是父母會說出:「說話要小心,他都聽得懂。」的時候。語言雖是用耳朵聽的,但聽的同時會看見語言使用者的臉部,也會留意其嘴部、頭部動作和眼神注視的方向。孩子們也會觀察語言使用者在說話時同時做出的手勢,某種程度上,他們是跟著說者的眼神與肢體動作來推斷他們所說的內容。人類在理解語言時會出現多模態的狀態,聆聽語言語音的同時也會接收非聽覺的感官訊息。
大人通常和嬰兒面對面說話,這樣他們會更容易理解對話的內容。目前確知的是,能看到說話者的臉會更容易理解語言的語音。關於這個部分有個實驗為例,研究人員找來兩組九個月大的嬰兒進行實驗。兩組都聽了第二語言的同一組新音素,在這個實驗中所使用的第二語言為中文,但兩組在實驗室中接觸的情境不同。在社交情境中,一位母語中文的女性和嬰兒說故事,並與他玩耍。而另一組嬰兒的狀況則是聽到完全相同的語音,也看到一樣的畫面,但是從電視螢幕中接觸到的,沒有社交互動。而在社交情境中的嬰兒明顯學得更好,更能區分新語音的差別,應該是因為他們在這種情境下專注力更高,而十二天後,研究人員透過行為表現及腦部影像也證實了這一點,反倒是處於非社交情境中的嬰兒什麼也沒有學到。研究人員在九個月大的嬰兒身上也觀察到了微妙的個體差異。在其他實驗中,研究人員透過腦部造影測出,會將視線從對話的大人轉移到大人所談論物體的嬰兒,更能夠辨識新單字的語音,相較之下,只會看著物體或只看著大人的嬰兒,辨識能力就比較低落。
與他人溝通、與對話者處於相同的溝通情境,對於孩子們語言感知能力的成長可謂關鍵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大人所使用的單字,會對應情境當中實際存在的物體或動作,談論的是存在於此時此地的事物。因此,嬰兒才能夠將成人使用的單字發音,與存在於當下情境的指涉對象搭配起來。比如玩球的同時提到「球」,孩子就能將「球」這個字的發音和物體連結起來。與嬰兒之間的交流,會讓他們更容易發現單字與句子的形式和功能之間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語音與意義之間的關聯。這個階段的語言習得重點在於理解語音背後的意義,這一點有助他們更留心發音的細節,並聚焦於處理這個單字的形式。
社交互動幫助嬰兒更加專心,也能更加注意對話情境中出現的語音,同時也提供他們一種連結的經驗,也就是活化大腦機能,結合感官與行動,即知即行,聽到什麼就嘗試去模仿。嬰兒聽到真人說話時,比起非生命體所發出的語音,他們對語言的注意力向來明顯更高。舉例來說,嬰兒看來並無法從電視中聽到的語言得到語音感知能力的成長效果。如果只聽語音而沒有畫面,也就是只有純粹聽到語言發音,則是幾乎沒有學習效果可言。不過在孩子年紀較大的情況,因為學習方式變了,學習語言的面向也有所不同,就必須另當別論。
有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可以說明幼童無法有效利用源自無生命體的語言,比如說有個兩歲半的孩子在講電話,雖然他們已經能說一些話,在家裡大人也聽得懂,而且「什麼都聽得懂」,卻還是聽不懂電話中說的內容,除非對方使用的是慣用語句。電話是只能傳遞聲音的媒介,無法提供額外的語言情報,小孩講電話時既看不到語言使用者說話時的表情、看不到對方說話時的目光所向,更不要說透過用詞遣字共享指稱的語境,他只能聽到聲音。這個例子同樣適用於那些還未掌握第二語言的成人,萬一非得打電話給該語言的母語人士,那對他來說可是很頭大的問題,肯定能免則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