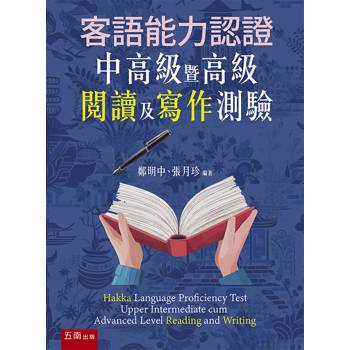緒言
臺灣於2019年01月09日公布施行《國家語言發展法》,第1條立法目的即開宗明義指出,「為尊重國家多元文化之精神,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復振及發展,特制定本法。」《國家語言發展法》讓臺灣固有族群的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均獲「國家語言」的法律位階,國家語言地位一律平等,國家語言使用不受歧視與限制(第3、4條)。第5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召開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研議、協調及推展國家語言發展事務。第2條及第6條則明確規定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並得指派中央及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推動各個國家語言的相關事務(第7-15條)。《國家語言發展法》第15條也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各國
家語言能力認證。」例如,閩南語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文化部,客家語為客家委員會,原住民語為原住民族委員會。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之甄選得視業務需要,附加國家語言能力證明作為資格條件(第16條)。這部語言專法讓各級政府的施政得以傳承、振興與發展各個國家語言,實際落實國家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由於這部語言專法的實施,客語能力認證考試的舉辦獲得更多法律的保障。1因此,每年均有大批客籍或非客籍人士報考各級客語能力認證考試。由此可見,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對於客家語言的保存、復振及發展之重要性不可言喻。
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一般包含「聽、說、讀、寫」這四項語言技能(four skills),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聽、說、讀、寫」也代表人類習得母語的先後順序。由於文字的逐步產生與廣泛運用是近幾千年的事,因此人類的語言最初是以「口說耳聽」的形式出現,而「聽」又是習得「說」的最佳媒介,先「聽」而後「說」是人類掌握母語的最主要途徑(聾啞人士例外)。例如,嬰兒在學會發出母語語音之前會歷經一段靜默期(silent period),此時的嬰兒看似對於母語習得毫無作為,但卻暗地裡透過「聽」而接收母語中的言語輸入,培養音韻知覺的能力,在短短一年內就能聽辨哪些語音屬於母語,哪些不是(Long, 1981)。培養聽的能力的同時,「說」的能力也慢慢突飛猛進,從嬰兒時期僅能發出簡單語音的「啞啞學語」(babble)階段,再到由實詞2構成為主的「獨詞句」(holophrase)及「電報句」(telegraphic speech)階段,最後到「簡單句」進而至「複雜句」的句子階段(李宇明,2004)。以上種種均發生在嬰兒出生後的短短幾年之間。例如,一位五歲的兒童,在不涉及複雜的社會文化概念的情況下,對於日常生活的議題幾乎已可與成人暢談無阻,無怪乎兒童被稱為是「小語言學家」(Little Linguist)。對於此種現象,當代語言學之父喬姆斯基(Noam A.Chomsky)主張,人腦與生俱來即具有一個「語言習得機制」,只要在
自然的母語使用環境中給予兒童適當且足夠的言語輸入,他/她就能夠自然地習得(acquire)母語的聽說能力,無須父母親或照護者特別教導(Chomsky, 1965, 1981)。
臺灣於2019年01月09日公布施行《國家語言發展法》,第1條立法目的即開宗明義指出,「為尊重國家多元文化之精神,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復振及發展,特制定本法。」《國家語言發展法》讓臺灣固有族群的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均獲「國家語言」的法律位階,國家語言地位一律平等,國家語言使用不受歧視與限制(第3、4條)。第5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召開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研議、協調及推展國家語言發展事務。第2條及第6條則明確規定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並得指派中央及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推動各個國家語言的相關事務(第7-15條)。《國家語言發展法》第15條也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各國
家語言能力認證。」例如,閩南語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文化部,客家語為客家委員會,原住民語為原住民族委員會。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之甄選得視業務需要,附加國家語言能力證明作為資格條件(第16條)。這部語言專法讓各級政府的施政得以傳承、振興與發展各個國家語言,實際落實國家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由於這部語言專法的實施,客語能力認證考試的舉辦獲得更多法律的保障。1因此,每年均有大批客籍或非客籍人士報考各級客語能力認證考試。由此可見,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對於客家語言的保存、復振及發展之重要性不可言喻。
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一般包含「聽、說、讀、寫」這四項語言技能(four skills),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聽、說、讀、寫」也代表人類習得母語的先後順序。由於文字的逐步產生與廣泛運用是近幾千年的事,因此人類的語言最初是以「口說耳聽」的形式出現,而「聽」又是習得「說」的最佳媒介,先「聽」而後「說」是人類掌握母語的最主要途徑(聾啞人士例外)。例如,嬰兒在學會發出母語語音之前會歷經一段靜默期(silent period),此時的嬰兒看似對於母語習得毫無作為,但卻暗地裡透過「聽」而接收母語中的言語輸入,培養音韻知覺的能力,在短短一年內就能聽辨哪些語音屬於母語,哪些不是(Long, 1981)。培養聽的能力的同時,「說」的能力也慢慢突飛猛進,從嬰兒時期僅能發出簡單語音的「啞啞學語」(babble)階段,再到由實詞2構成為主的「獨詞句」(holophrase)及「電報句」(telegraphic speech)階段,最後到「簡單句」進而至「複雜句」的句子階段(李宇明,2004)。以上種種均發生在嬰兒出生後的短短幾年之間。例如,一位五歲的兒童,在不涉及複雜的社會文化概念的情況下,對於日常生活的議題幾乎已可與成人暢談無阻,無怪乎兒童被稱為是「小語言學家」(Little Linguist)。對於此種現象,當代語言學之父喬姆斯基(Noam A.Chomsky)主張,人腦與生俱來即具有一個「語言習得機制」,只要在
自然的母語使用環境中給予兒童適當且足夠的言語輸入,他/她就能夠自然地習得(acquire)母語的聽說能力,無須父母親或照護者特別教導(Chomsky, 1965,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