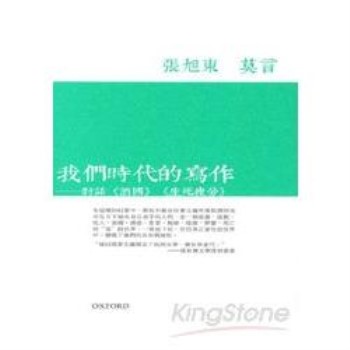「妖精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敘事可能性
──《酒國》中的語言遊戲、自然史與社會寓言
對於那些努力為市場經濟時代的中國尋求定義,或是尋求某種具有一致性描述的人來說,莫言的《酒國》提供了一種想像中的解決方案,一種審美快感,甚至一種道德淨化。這當然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從莫言的小說中看到關於中國的清晰圖畫,而是說,在《酒國》中,所有與當代中國聯繫在一起的幽暗、矛盾、混沌,儘管在分析理性看來,非常令人費解,但在一種敘事藝術品的界定中,則變為一種「詩學規範」( poetic norm),並由此達到了在「可能」的世界中(與「現實」世界相對立),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更具哲學性」。這部奇異、滑稽、令人反胃但又極具誘惑力的小說,是「文學粗糙性」( literary coarseness)與「風格無邊性」(stylistic boundlessness)的實驗。在這一實驗中,寫作的「絕對能量」(sheer energy)、多樣性、遊戲性,在不斷將敘事的特定形式推向崩塌邊緣的同時,為「再現」提供了各種新的可能性。在這一坐落於幻想
與紀實之間的虛構空間之中,總有一些令人激動的「現實主義」的東西,既因為它對我們來說是熟悉的、可辨識的,也因為它觸及「歷史真理」與「價值判斷」這些更重要的層面。所有這些,使得讀者不得不產生疑慮,《酒國》中高強度的語言與形式遊戲,是否僅被用來提供一種「審美庇護所」,並在此之中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景象發動一場最無情、最輕蔑的進攻——既在社會諷刺的意義上,也在「道德—寓言」的意義上。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現代主義者,莫言從一開始就沒有對社會分析、道德批評、政治介入表現出明顯的現實主義傾向,對於中國文學生產領域令人眼花繚亂的多樣風格,他也並未表現出任何固定立場,儘管莫言的文學生產具備明顯的風格延續性,這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中期,當他被命名為「魔幻現實主義 」時。人們看到的莫言更像是一個帶著農民的智慧與詭計的遊擊隊戰士,始終對中國日常生活的快速都市化與商品化投以厭煩的目光,而他在社會政治領域的規避( evasiveness)與看似超然的態度,則與其在形式與寓言層面的「強度」、「激進」與「大膽」相匹配。在莫言的世界中,現象世界很少得到再現,而是被「形式–敘述」空間所吞沒,並由一種無情的虛構邏輯轉化為寓言性形象。在這個意義上,顛倒的反而成為真實的。莫言小說的「敘事」,顯然並非作為反映「真實」( the real)的管道,但也正是在其作品的「敘事構造」(narrative enterprise)中,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諸種碎片化現實,找到了自身形式與道德的確定性,甚或意義性——常常棲身於「眼花繚亂的曖昧性」、過剩、褻瀆、「無意義」的形式中。對於一個缺乏「社會–歷史構架」和「道德–政治構成」的時代來說,這是一九九○年代中國諸種失了根的、無家的、彷徨的經驗、意象、記憶與幽靈的「象徵性落座」symbolic dwelling) ——這種「象徵性落座」即便不是註定的,也是一種優先之物。從這點看來,《酒國》中的「酒國市」恰恰象徵醉漢眼中呈現出的中國:模糊但依舊鮮明;奇異、荒誕、但仍具有一種獨特的邏輯性;令人發狂的不一致,但又具有令人驚異、不知羞恥的清晰感。一方面,這裏有一種「自然史」的陷落,伴隨著所有或陳舊過時,或剛被創造出來的表達、姿態、理念的混亂的咕噥。在另一方面,借用拉康( Jacques Lacan)對「無意識」的觀察,「酒國」也是像「語言」一樣被組織起來的。倘要用一種超越犬儒主義的態度閱讀《酒國》,並抵制從最負面的態度,最具「顛覆性」的眼光去看待今日中國的誘惑,就要抓住《酒國》中處於活動狀態的語言,去辨識出這一語言的語法,一種與旨在交際、再現、編碼的傳統理性的語言相對抗的語法。《酒國》中所截取的世界,是與清醒意識相對立的夢的世界。這也是一種被挫敗的心靈狀態、一種方向錯亂的、精神分裂的心靈狀態,被投射到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客觀世界。在這樣一座鏡子屋( mirror house)裏,內在領域與外在領域都被消解為屬於「震驚」經驗的各種破碎的「身體部分」,在社會–文化的幻景( phantasmagoria)中無助地飄浮。在這樣的幻景中,那些不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光天化日下說出自己名字的人們,在一個放蕩、狂飲、吃人、諂媚、誘惑、欲望、賄賂、陰謀、野蠻、死亡的「夜」的世界,一個地下的、但仍具正當性的世界中,發現了他們的自由與迷狂。
敘事的劃分
《酒國》包含了三段並置又相互聯繫的敘事,這些分化而又統一的敘事處於這個小說結構設計的中心位置,反過來加強了小說辯證的張力,而這一張力有助於凸顯小說寓言性上的「尖銳」和再現層面上的生產性。
處在最前面的是小說文本主要部分,也就是,特級偵察員丁鉤兒對「酒國」所謂「吃人案件」的調查。為了便於區分,我們可以將這一敘述稱之為「敘事1」:「全然虛構」(the properly fictional)。
第二種敘事則由「莫言」與業餘寫作者「李一斗」(或酒博士,酒國市釀造學院勾兌專業博士研究生)的通信構成。他們來回信件的主要內容大多是李一斗要求「莫言」幫助他在《國民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這個敘事最終結束於小說結「莫言」的酒國之行,他在那裏與人的會晤及其他活動。像大多數私人通信一樣,這些信件談到了範圍相當廣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並對當代中國社會進行了指涉與議論。在這些各種各樣的話題所觸及的眾多事情之中,有兩條脈絡的持續發展值得注意:一是「莫言」對李一斗從事文學職業的鼓勵意見,這些鼓勵意見,在「真實」與雙重虛構的層面上,都不僅具有社會批判性,而且也是自我指涉、甚至是自傳性的。另一條脈絡是李一斗彷彿永不衰竭的「語言性」特質與語言過剩:大量的奇聞異事、流言、抱怨、小報告,來自於自封為政府線人的這樣一個愛出風頭的、諂媚的、竭力要討得一個大作家的欣賞與幫助的鄉下業餘作者之筆。這裏我們看到作者在小說中以真名與他的一個書迷交流,這個書迷不只是普遍意義上虛構的產物,而是一個在「敘事1」所虛構出的地點——「酒國」中生活、工作、並不斷打小報告的「真實人物」。我們可以稱這個敘事為 「敘事2」:『虛構性的「非虛構」』(the fictional nonfiction)。
第三個層面或維度則由一個迷你系列構成,它包含了「敘事2」所設定的「真實人物」或是 「非虛構人物」李一斗所寫的九部帶有半關聯性的短篇小說。這些故事當然很「糟糕」(但也正是作家本人極具創造性地,故意將它們寫得如此之糟糕):沒有任何虛構作品的一致性,缺乏基本的恰當的形式,更不用說(審美)自律性,但與此同時,這些失敗之處也恰恰反映出在這三種敘事中貫穿這一個重疊、平行、空白、省略的網絡。在這個意義上,由「小說」的傳統概念所界定的「糟糕」或「低於標準」,在「寓言」的領域,轉化為一種非常歡鬧的、具有生產性的、引人入勝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短篇小說序列構成了對現代中國文學史主要範式的半系統化的戲仿( parody),摹仿其主流寫作風格以及涉及到的話題,其中最明顯的是李一斗用《肉孩》戲仿魯迅的《藥》。但在更直接的意義上,這些作品似乎更是在氣喘吁吁地追趕改革開放年代,以 「創新」或「現代化」的名義橫掃中國的世界文學潮流。這些故事,可以視為結合了兩種對立的性質,即對「酒國」中現實與超現實之物最「現實主義」的描繪,與一種最具幻想性、無形式感的、反傳統的「說故事」形式,結合在了一起。這一結合使這些故事構成了一本記錄種種笨拙手法的「文學寫作」手冊,以及對各種風格嘗試「實驗」與多變的標籤的誇張鋪陳:它們被「作者」李一斗一一命名,諸如「嚴酷現實主義」「妖精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等等。我們可以將此稱為「敘事3」:「虛構性的虛構」(the fictitious fiction)。
敘事的分化,以及這三個被區分的、半自律的敘事領域的互相重疊和滲透,對於這部小說的組織性結構與 「再現–寓言」野心來說,是非常關鍵的。首先,它通過敘事的分化,擴大、深化了小說的形式空間,同時也回應了「社會–經驗」總體的複雜性與多樣性——而這種總體「社會–經驗」同時也指向一種「象徵–寓言」層面的總體性。相對於單一敘述聲音或敘述視角,小說的多重敘述聲音與敘述視角——莫言、莫言–李一斗、李一斗——創造了一個高度柔軟,具有生產性的「流動視角」,這一「流動視角」帶來對同一個寓言空間反復進入(從不同的角度,帶著不同的道德和再現訴求) ——這樣的敘述設計也從一種貌似「現代主義」或「實驗性」、實際卻深陷於自身諸種「形式–風格」界線內的傳統「虛構寫作」之中,發動並誕生出一種「前虛構」與「元虛構」。「前虛構」包括「虛構的非虛構」,信件體等等;「元虛構」則呈現為莫言這篇小說在虛構性上的悖論,或者敘述者對小說整個生產過程的揭露、展示、示範——在此之中有著作為生產者之作者的活動。有意思的是,對「前虛構」與「元虛構」的發明,並未破壞小說最根本的現實主義本質——「摹仿」與「再現」,而是,通過將「全然虛構」重新配置並重新建構為「全然現實主義」(這一「現實主義」既與「敘述2 」中通信體的、記錄體的敘述相對,也與「敘述3」中 「幻想的」、「寓言」的敘述相對),最終加強了小說的現實主義本質。如果莫言在九十年代最具野心的風格實驗,可以視為對現代主義的追求,那麼它也是一種期望實現,同時也有能力實現與現實主義聯盟的一種「晚期現代主義」——這一對現實主義聯盟的期待,具有一種歷史性與政治性上的必然。在莫言九十年代的作品中,「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這兩個傳統似乎在一個更嚴酷、更「妖魔」的寓言的領地,實現了一種結合,這樣一種寓言化的寫作,既是遙遠的、古代的,也至少潛在地在後現代的意義上,是更加 「現代」的。
這可以從《酒國》對後社會主義現實性的多層面展現中看出:首先是它驚人的再現能力:通過「敘事」的內在分裂、碎片化,以及向某個 「寓言」領地的邁進與拓展(這一「寓言」領地,正坐落於形式本身的坍塌與彌散之上),達到一種敘事的擴散,借此來容納並覆蓋一種斷裂的(令人迷亂的斷裂)、精神分裂的、但又極具生產性與能量的現實。審美探險(或冒險)似乎已經以「主體位置」或「自我意識」為代價,還清了債務——這一代價表現為:由「世界的異化」帶來的「主體位置」或「自我意識」的崩潰、中斷、分解、挪用。比如:通過自身內質與對立面的交換「主體位置」或「自我意識」變為「動物」「物」、「他者」,變為「反自我」——這些都作為「敘述」的有效、積極的元素(anti-self),「動員」起來,以此呈現一個脫節了的時代——這個時代在「思想」中被把握,或者更準確地說,在一種寓言「沉思」中被把握。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種「再現性」上的總體性的實現,並沒有掉入一個固定的道德、意識形態或審美的位置與「一致性」( uniformity),而是通過與一個活生生的世界的共存,或者就活在其中來獲得,這個活生生的世界既包括商品經濟的新的惡魔,也包括多重傳統的舊的幽靈——舊朝代的與革命的、毛主義與後毛主義甚至反毛主義的、以都市為中心的與以鄉土為基礎的、世界主義的與地方的。所有這些都證明莫言的作品對今日中國的社會與日常生活有所訴求,邀請它們進入其作品中的寓言化狂歡,儘管這一狂歡帶有某種寓言式的詭詐、諷刺和疏離,卻仍然全心全意地歡迎現實中的一切事物。
──《酒國》中的語言遊戲、自然史與社會寓言
對於那些努力為市場經濟時代的中國尋求定義,或是尋求某種具有一致性描述的人來說,莫言的《酒國》提供了一種想像中的解決方案,一種審美快感,甚至一種道德淨化。這當然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從莫言的小說中看到關於中國的清晰圖畫,而是說,在《酒國》中,所有與當代中國聯繫在一起的幽暗、矛盾、混沌,儘管在分析理性看來,非常令人費解,但在一種敘事藝術品的界定中,則變為一種「詩學規範」( poetic norm),並由此達到了在「可能」的世界中(與「現實」世界相對立),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更具哲學性」。這部奇異、滑稽、令人反胃但又極具誘惑力的小說,是「文學粗糙性」( literary coarseness)與「風格無邊性」(stylistic boundlessness)的實驗。在這一實驗中,寫作的「絕對能量」(sheer energy)、多樣性、遊戲性,在不斷將敘事的特定形式推向崩塌邊緣的同時,為「再現」提供了各種新的可能性。在這一坐落於幻想
與紀實之間的虛構空間之中,總有一些令人激動的「現實主義」的東西,既因為它對我們來說是熟悉的、可辨識的,也因為它觸及「歷史真理」與「價值判斷」這些更重要的層面。所有這些,使得讀者不得不產生疑慮,《酒國》中高強度的語言與形式遊戲,是否僅被用來提供一種「審美庇護所」,並在此之中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景象發動一場最無情、最輕蔑的進攻——既在社會諷刺的意義上,也在「道德—寓言」的意義上。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現代主義者,莫言從一開始就沒有對社會分析、道德批評、政治介入表現出明顯的現實主義傾向,對於中國文學生產領域令人眼花繚亂的多樣風格,他也並未表現出任何固定立場,儘管莫言的文學生產具備明顯的風格延續性,這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中期,當他被命名為「魔幻現實主義 」時。人們看到的莫言更像是一個帶著農民的智慧與詭計的遊擊隊戰士,始終對中國日常生活的快速都市化與商品化投以厭煩的目光,而他在社會政治領域的規避( evasiveness)與看似超然的態度,則與其在形式與寓言層面的「強度」、「激進」與「大膽」相匹配。在莫言的世界中,現象世界很少得到再現,而是被「形式–敘述」空間所吞沒,並由一種無情的虛構邏輯轉化為寓言性形象。在這個意義上,顛倒的反而成為真實的。莫言小說的「敘事」,顯然並非作為反映「真實」( the real)的管道,但也正是在其作品的「敘事構造」(narrative enterprise)中,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諸種碎片化現實,找到了自身形式與道德的確定性,甚或意義性——常常棲身於「眼花繚亂的曖昧性」、過剩、褻瀆、「無意義」的形式中。對於一個缺乏「社會–歷史構架」和「道德–政治構成」的時代來說,這是一九九○年代中國諸種失了根的、無家的、彷徨的經驗、意象、記憶與幽靈的「象徵性落座」symbolic dwelling) ——這種「象徵性落座」即便不是註定的,也是一種優先之物。從這點看來,《酒國》中的「酒國市」恰恰象徵醉漢眼中呈現出的中國:模糊但依舊鮮明;奇異、荒誕、但仍具有一種獨特的邏輯性;令人發狂的不一致,但又具有令人驚異、不知羞恥的清晰感。一方面,這裏有一種「自然史」的陷落,伴隨著所有或陳舊過時,或剛被創造出來的表達、姿態、理念的混亂的咕噥。在另一方面,借用拉康( Jacques Lacan)對「無意識」的觀察,「酒國」也是像「語言」一樣被組織起來的。倘要用一種超越犬儒主義的態度閱讀《酒國》,並抵制從最負面的態度,最具「顛覆性」的眼光去看待今日中國的誘惑,就要抓住《酒國》中處於活動狀態的語言,去辨識出這一語言的語法,一種與旨在交際、再現、編碼的傳統理性的語言相對抗的語法。《酒國》中所截取的世界,是與清醒意識相對立的夢的世界。這也是一種被挫敗的心靈狀態、一種方向錯亂的、精神分裂的心靈狀態,被投射到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客觀世界。在這樣一座鏡子屋( mirror house)裏,內在領域與外在領域都被消解為屬於「震驚」經驗的各種破碎的「身體部分」,在社會–文化的幻景( phantasmagoria)中無助地飄浮。在這樣的幻景中,那些不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光天化日下說出自己名字的人們,在一個放蕩、狂飲、吃人、諂媚、誘惑、欲望、賄賂、陰謀、野蠻、死亡的「夜」的世界,一個地下的、但仍具正當性的世界中,發現了他們的自由與迷狂。
敘事的劃分
《酒國》包含了三段並置又相互聯繫的敘事,這些分化而又統一的敘事處於這個小說結構設計的中心位置,反過來加強了小說辯證的張力,而這一張力有助於凸顯小說寓言性上的「尖銳」和再現層面上的生產性。
處在最前面的是小說文本主要部分,也就是,特級偵察員丁鉤兒對「酒國」所謂「吃人案件」的調查。為了便於區分,我們可以將這一敘述稱之為「敘事1」:「全然虛構」(the properly fictional)。
第二種敘事則由「莫言」與業餘寫作者「李一斗」(或酒博士,酒國市釀造學院勾兌專業博士研究生)的通信構成。他們來回信件的主要內容大多是李一斗要求「莫言」幫助他在《國民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這個敘事最終結束於小說結「莫言」的酒國之行,他在那裏與人的會晤及其他活動。像大多數私人通信一樣,這些信件談到了範圍相當廣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並對當代中國社會進行了指涉與議論。在這些各種各樣的話題所觸及的眾多事情之中,有兩條脈絡的持續發展值得注意:一是「莫言」對李一斗從事文學職業的鼓勵意見,這些鼓勵意見,在「真實」與雙重虛構的層面上,都不僅具有社會批判性,而且也是自我指涉、甚至是自傳性的。另一條脈絡是李一斗彷彿永不衰竭的「語言性」特質與語言過剩:大量的奇聞異事、流言、抱怨、小報告,來自於自封為政府線人的這樣一個愛出風頭的、諂媚的、竭力要討得一個大作家的欣賞與幫助的鄉下業餘作者之筆。這裏我們看到作者在小說中以真名與他的一個書迷交流,這個書迷不只是普遍意義上虛構的產物,而是一個在「敘事1」所虛構出的地點——「酒國」中生活、工作、並不斷打小報告的「真實人物」。我們可以稱這個敘事為 「敘事2」:『虛構性的「非虛構」』(the fictional nonfiction)。
第三個層面或維度則由一個迷你系列構成,它包含了「敘事2」所設定的「真實人物」或是 「非虛構人物」李一斗所寫的九部帶有半關聯性的短篇小說。這些故事當然很「糟糕」(但也正是作家本人極具創造性地,故意將它們寫得如此之糟糕):沒有任何虛構作品的一致性,缺乏基本的恰當的形式,更不用說(審美)自律性,但與此同時,這些失敗之處也恰恰反映出在這三種敘事中貫穿這一個重疊、平行、空白、省略的網絡。在這個意義上,由「小說」的傳統概念所界定的「糟糕」或「低於標準」,在「寓言」的領域,轉化為一種非常歡鬧的、具有生產性的、引人入勝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短篇小說序列構成了對現代中國文學史主要範式的半系統化的戲仿( parody),摹仿其主流寫作風格以及涉及到的話題,其中最明顯的是李一斗用《肉孩》戲仿魯迅的《藥》。但在更直接的意義上,這些作品似乎更是在氣喘吁吁地追趕改革開放年代,以 「創新」或「現代化」的名義橫掃中國的世界文學潮流。這些故事,可以視為結合了兩種對立的性質,即對「酒國」中現實與超現實之物最「現實主義」的描繪,與一種最具幻想性、無形式感的、反傳統的「說故事」形式,結合在了一起。這一結合使這些故事構成了一本記錄種種笨拙手法的「文學寫作」手冊,以及對各種風格嘗試「實驗」與多變的標籤的誇張鋪陳:它們被「作者」李一斗一一命名,諸如「嚴酷現實主義」「妖精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等等。我們可以將此稱為「敘事3」:「虛構性的虛構」(the fictitious fiction)。
敘事的分化,以及這三個被區分的、半自律的敘事領域的互相重疊和滲透,對於這部小說的組織性結構與 「再現–寓言」野心來說,是非常關鍵的。首先,它通過敘事的分化,擴大、深化了小說的形式空間,同時也回應了「社會–經驗」總體的複雜性與多樣性——而這種總體「社會–經驗」同時也指向一種「象徵–寓言」層面的總體性。相對於單一敘述聲音或敘述視角,小說的多重敘述聲音與敘述視角——莫言、莫言–李一斗、李一斗——創造了一個高度柔軟,具有生產性的「流動視角」,這一「流動視角」帶來對同一個寓言空間反復進入(從不同的角度,帶著不同的道德和再現訴求) ——這樣的敘述設計也從一種貌似「現代主義」或「實驗性」、實際卻深陷於自身諸種「形式–風格」界線內的傳統「虛構寫作」之中,發動並誕生出一種「前虛構」與「元虛構」。「前虛構」包括「虛構的非虛構」,信件體等等;「元虛構」則呈現為莫言這篇小說在虛構性上的悖論,或者敘述者對小說整個生產過程的揭露、展示、示範——在此之中有著作為生產者之作者的活動。有意思的是,對「前虛構」與「元虛構」的發明,並未破壞小說最根本的現實主義本質——「摹仿」與「再現」,而是,通過將「全然虛構」重新配置並重新建構為「全然現實主義」(這一「現實主義」既與「敘述2 」中通信體的、記錄體的敘述相對,也與「敘述3」中 「幻想的」、「寓言」的敘述相對),最終加強了小說的現實主義本質。如果莫言在九十年代最具野心的風格實驗,可以視為對現代主義的追求,那麼它也是一種期望實現,同時也有能力實現與現實主義聯盟的一種「晚期現代主義」——這一對現實主義聯盟的期待,具有一種歷史性與政治性上的必然。在莫言九十年代的作品中,「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這兩個傳統似乎在一個更嚴酷、更「妖魔」的寓言的領地,實現了一種結合,這樣一種寓言化的寫作,既是遙遠的、古代的,也至少潛在地在後現代的意義上,是更加 「現代」的。
這可以從《酒國》對後社會主義現實性的多層面展現中看出:首先是它驚人的再現能力:通過「敘事」的內在分裂、碎片化,以及向某個 「寓言」領地的邁進與拓展(這一「寓言」領地,正坐落於形式本身的坍塌與彌散之上),達到一種敘事的擴散,借此來容納並覆蓋一種斷裂的(令人迷亂的斷裂)、精神分裂的、但又極具生產性與能量的現實。審美探險(或冒險)似乎已經以「主體位置」或「自我意識」為代價,還清了債務——這一代價表現為:由「世界的異化」帶來的「主體位置」或「自我意識」的崩潰、中斷、分解、挪用。比如:通過自身內質與對立面的交換「主體位置」或「自我意識」變為「動物」「物」、「他者」,變為「反自我」——這些都作為「敘述」的有效、積極的元素(anti-self),「動員」起來,以此呈現一個脫節了的時代——這個時代在「思想」中被把握,或者更準確地說,在一種寓言「沉思」中被把握。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種「再現性」上的總體性的實現,並沒有掉入一個固定的道德、意識形態或審美的位置與「一致性」( uniformity),而是通過與一個活生生的世界的共存,或者就活在其中來獲得,這個活生生的世界既包括商品經濟的新的惡魔,也包括多重傳統的舊的幽靈——舊朝代的與革命的、毛主義與後毛主義甚至反毛主義的、以都市為中心的與以鄉土為基礎的、世界主義的與地方的。所有這些都證明莫言的作品對今日中國的社會與日常生活有所訴求,邀請它們進入其作品中的寓言化狂歡,儘管這一狂歡帶有某種寓言式的詭詐、諷刺和疏離,卻仍然全心全意地歡迎現實中的一切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