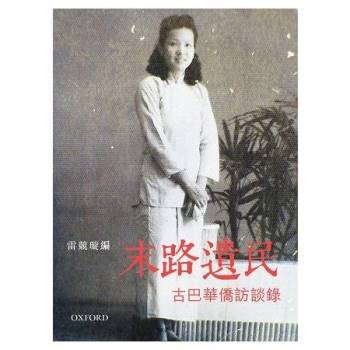海隅秀才 曾經造反
趙肇商 Guillermo Chiu
在古巴,我最早認識的華僑是趙肇商和蔣祖廉兩位先生,2010年年底我和家人去古巴,希望尋找一下祖父、父親的痕跡,按父親從前來信上的地址,抵埗哈瓦那就馬上到華區,結果發現那地址竟是《光華報》所在,但重門深鎖,無法入內,再經打聽,找到了趙、蔣兩位先生,交換名片後,得知趙先生是《光華報》的總編輯,蔣先生是翻譯員,兩位都友善熱心,開了報館的大門,引領我們進入參觀,向我們介紹《光華報》的歷史和古巴華人的情況。當時和我一起的有我三弟,是香港《大公報》的執行總編輯,趙先生看到他的名片,露出敬慕之情,和我三弟交換了一點報人的經驗和感受。然後,我2013年1月再到古巴,進行訪談老華僑的工作,首先找趙先生,他一口答應,讓我完成了第一個訪談,令我對這項嘗試的信心大為增加,我很感謝他。至於蔣祖廉先生,也作了訪談,可惜他的堂兄弟蔣祖樂先生在2012年逝世,沒法再會面。我第一次到古巴時和他們堂兄弟倆吃了一頓飯,從他們口中瞭解了很多從前華僑社會的情況,祖樂先生很儒雅,文墨水平比較高,我本來期望和他再次細談,結果無法如願,真是遺憾。
雖然離鄉數十年,趙先生到現在還鄉音無改,說的應是古舊的新會話,我聽起來有點困難。現時還在古巴的華僑,在家鄉上過學的為數不多,像趙先生這樣讀過中學的更如鳳毛麟角,於是,華區凡涉及翰墨和搖筆桿的事,多由趙先生操辦,他可說是古巴華人社群的秀才。我一再對他說,要爭取時間,趁記憶尚完好,將古巴革命前後他自己和其他華僑的政治經歷寫下來,以供後人作參考,他也同意。趙先生今( 2016 ) 年八十三歲了。
訪談在2013年1月8日下午進行,在哈瓦那中華總會館內,是年12月我再到古巴時又見到趙先生,談話中他補充了一些情況,見本文之末的後記。
我名叫趙文立,正式名字是趙肇商,文立是我讀書時取的名字。家鄉是新會古井霞露鄉,1933年在鄉下出生。
我父親名趙厚和,屬於我家庭「和」字輩,母親名黃月桂,長樂村人氏。我父親讀書很少,可能只讀過一、兩年。我大伯即我父親的哥哥先來古巴,他有些少生意做(按:廣東話「些少」即「一點」之意),在1922年辦手續讓我父親來古巴,將生意交托給他,自己回去鄉下,之後再沒有回到古巴。
我父親是1904年出生的,來古巴時約十八歲,已經結婚,我是在他第一次從古巴回到鄉下,停留一年多兩年期間出生的。我還有兩個弟弟,但二弟出生三個月便病死了,三弟沒有來古巴,一直在中國,三弟出生時父親已經離開鄉下回去了古巴,所以他小時沒有見過父親。我父親回到古巴不足一年,我母親就在鄉下病死,我當時十一、十二歲,我弟弟由婆婆照顧,我婆婆是紮腳的。我和弟弟相差十一歲。後來我父親年老了,1989年11月從古巴回去中國三弟處生活,住在江門市,直至1990年9月逝世,他逝世後三弟來信告訴我,我才知道*。我三弟現在還在江門市,做些出口買賣生意,常常到外地辦採購。
打仗時( 按:指抗戰)鄉下常被賊劫,我母親和我去了香港避難,不久父親從古巴到香港和我們聚合,然後一起回鄉。當時我大約六歲,父親將金錢塞在我衣袋中,路上遇到一夥賊人,我走在前面,因為是小孩子,沒有受到注意,沒有搜我身,賊人只是搜我父母親,沒有搜到錢。後來我父親在鄉下用這些錢買了點田地,等到我弟弟出生,父親就回來古巴了( 按:約在1944年) 。我母親去世後,我父親沒有再娶。我小時候因為有父親從外面匯錢回來,生活比一般人稍好。當時一般人生活極之困難,很多人要吃番薯葉、龍眼核,吃得腳也腫了,錢常常貶值,又換來換去(按:指貨幣轉換),做小買賣的很困難。
我在鄉下讀完小學,考上了在江門市的新會一中。我父親在古巴買了紙張(按:即「證件」),寄回來給我辦手續來古巴,即是用假紙張辦理,紙張上的人已經死去,是一個姓黃( 音,或為「王」) 的。我1952年來古巴,當時十七、八歲,假名叫「供邦」,沒有「黃」( 音) 字。當時用假紙張來古巴很普遍,曾經有三個人共用一張姓李的假紙張一起來古巴的情況,古巴政府對此也是知道的,但貪污厲害,有錢就可以辦到,當時買假紙張要花800〔古巴〕元,我父親因為有生意,可以負擔。我是在古巴革命勝利後,大約在1961年才恢復原來的姓名趙肇商,是得到古巴革命政府支持才改名的,沒有付錢,請兩個人作為見證,買了士擔(按:即印花),辦理改名手續。我抵達古巴時,父親有兩間雜貨店,我就在雜貨店工作。
趙肇商 Guillermo Chiu
在古巴,我最早認識的華僑是趙肇商和蔣祖廉兩位先生,2010年年底我和家人去古巴,希望尋找一下祖父、父親的痕跡,按父親從前來信上的地址,抵埗哈瓦那就馬上到華區,結果發現那地址竟是《光華報》所在,但重門深鎖,無法入內,再經打聽,找到了趙、蔣兩位先生,交換名片後,得知趙先生是《光華報》的總編輯,蔣先生是翻譯員,兩位都友善熱心,開了報館的大門,引領我們進入參觀,向我們介紹《光華報》的歷史和古巴華人的情況。當時和我一起的有我三弟,是香港《大公報》的執行總編輯,趙先生看到他的名片,露出敬慕之情,和我三弟交換了一點報人的經驗和感受。然後,我2013年1月再到古巴,進行訪談老華僑的工作,首先找趙先生,他一口答應,讓我完成了第一個訪談,令我對這項嘗試的信心大為增加,我很感謝他。至於蔣祖廉先生,也作了訪談,可惜他的堂兄弟蔣祖樂先生在2012年逝世,沒法再會面。我第一次到古巴時和他們堂兄弟倆吃了一頓飯,從他們口中瞭解了很多從前華僑社會的情況,祖樂先生很儒雅,文墨水平比較高,我本來期望和他再次細談,結果無法如願,真是遺憾。
雖然離鄉數十年,趙先生到現在還鄉音無改,說的應是古舊的新會話,我聽起來有點困難。現時還在古巴的華僑,在家鄉上過學的為數不多,像趙先生這樣讀過中學的更如鳳毛麟角,於是,華區凡涉及翰墨和搖筆桿的事,多由趙先生操辦,他可說是古巴華人社群的秀才。我一再對他說,要爭取時間,趁記憶尚完好,將古巴革命前後他自己和其他華僑的政治經歷寫下來,以供後人作參考,他也同意。趙先生今( 2016 ) 年八十三歲了。
訪談在2013年1月8日下午進行,在哈瓦那中華總會館內,是年12月我再到古巴時又見到趙先生,談話中他補充了一些情況,見本文之末的後記。
我名叫趙文立,正式名字是趙肇商,文立是我讀書時取的名字。家鄉是新會古井霞露鄉,1933年在鄉下出生。
我父親名趙厚和,屬於我家庭「和」字輩,母親名黃月桂,長樂村人氏。我父親讀書很少,可能只讀過一、兩年。我大伯即我父親的哥哥先來古巴,他有些少生意做(按:廣東話「些少」即「一點」之意),在1922年辦手續讓我父親來古巴,將生意交托給他,自己回去鄉下,之後再沒有回到古巴。
我父親是1904年出生的,來古巴時約十八歲,已經結婚,我是在他第一次從古巴回到鄉下,停留一年多兩年期間出生的。我還有兩個弟弟,但二弟出生三個月便病死了,三弟沒有來古巴,一直在中國,三弟出生時父親已經離開鄉下回去了古巴,所以他小時沒有見過父親。我父親回到古巴不足一年,我母親就在鄉下病死,我當時十一、十二歲,我弟弟由婆婆照顧,我婆婆是紮腳的。我和弟弟相差十一歲。後來我父親年老了,1989年11月從古巴回去中國三弟處生活,住在江門市,直至1990年9月逝世,他逝世後三弟來信告訴我,我才知道*。我三弟現在還在江門市,做些出口買賣生意,常常到外地辦採購。
打仗時( 按:指抗戰)鄉下常被賊劫,我母親和我去了香港避難,不久父親從古巴到香港和我們聚合,然後一起回鄉。當時我大約六歲,父親將金錢塞在我衣袋中,路上遇到一夥賊人,我走在前面,因為是小孩子,沒有受到注意,沒有搜我身,賊人只是搜我父母親,沒有搜到錢。後來我父親在鄉下用這些錢買了點田地,等到我弟弟出生,父親就回來古巴了( 按:約在1944年) 。我母親去世後,我父親沒有再娶。我小時候因為有父親從外面匯錢回來,生活比一般人稍好。當時一般人生活極之困難,很多人要吃番薯葉、龍眼核,吃得腳也腫了,錢常常貶值,又換來換去(按:指貨幣轉換),做小買賣的很困難。
我在鄉下讀完小學,考上了在江門市的新會一中。我父親在古巴買了紙張(按:即「證件」),寄回來給我辦手續來古巴,即是用假紙張辦理,紙張上的人已經死去,是一個姓黃( 音,或為「王」) 的。我1952年來古巴,當時十七、八歲,假名叫「供邦」,沒有「黃」( 音) 字。當時用假紙張來古巴很普遍,曾經有三個人共用一張姓李的假紙張一起來古巴的情況,古巴政府對此也是知道的,但貪污厲害,有錢就可以辦到,當時買假紙張要花800〔古巴〕元,我父親因為有生意,可以負擔。我是在古巴革命勝利後,大約在1961年才恢復原來的姓名趙肇商,是得到古巴革命政府支持才改名的,沒有付錢,請兩個人作為見證,買了士擔(按:即印花),辦理改名手續。我抵達古巴時,父親有兩間雜貨店,我就在雜貨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