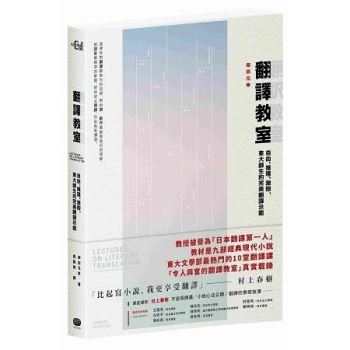【前言】柴田元幸/文
這本書是將2004 年10 月到2005 年1 月為止,在東大文學系的課程「西洋近代語學近代文學演習第1 部 翻譯演習」的內容直接化為文字的結果。課堂中的口誤和矛盾等都經過修正,特別是教師的一連串不合理、不明所以的發言,也做了某些程度的合理化修飾,不過基本進行方式都跟實際課堂相同。
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到實際課堂上哪些問題會讓教師和學生特別熱辯得欲罷不能,若是對翻譯或者文字技巧等並不特別感興趣的人,或許會認為那大多是微不足道的爭論。但是也有人認為,一個地方能熱切討論社會上多數人覺得無關緊要的事,才夠格稱為大學。再說,這世上本來就沒有什麼問題能讓萬人同聲認同是全天下最重要的大事。任何事都可能對某人來說無關緊要、對某人來說至關重要。在這2004 年的課堂中,不知為何聚集了不少認為翻譯這個問題至關重要的人,是個相當幸運的場域。我也由衷希望整理內容成書後,能讓更多有同樣想法的朋友模擬參與討論。
課堂的進行方式大致如下:首先我會事先發下習題,請所有學生翻譯、繳交譯文。這些譯文由教師和幾個研究生(該學期有三個)分工修改,寫上評語後在上課時發還。上課時學生手邊會有領回的譯文。課堂上會使用懸吊式攝影機,簡稱OHC,又稱俯視攝影機,或是教材提示裝置,這種工具始終沒有固定名稱,總之就是一部簡單的放映攝影機,可以把事先列印出來的學生譯文映在畫面上提示,一邊跟學生討論,教師當場批改。課堂結束時學生繳交下次上課的習題譯文……這樣的過程重複了一個學期。學生幾乎每星期都得交出翻譯,是挺吃力的一門課。
從1993 年到2001 年,我在教養學系開這門課的時候,授課對象是所有學系的學生,選修人數多達100 ∼ 400 人,授課方式多半是教師一個人講課、對著畫面上的譯文批改(很少有學生能在200 人面前自在發言),2002 年以後我開始在文學系開這門課,授課對象基本上都是文學系學生(也有少部分其他系感興趣的人聞風而來),選修人數大約40 ∼ 60 人左右,教師和學生得以在課堂上做各種討論。其中,2004 年的課堂討論氣氛莫名熱烈。有人常喜歡強調名師、劣師的差異,其實我覺得,一堂課的好壞主要還是掌握在參與的學生手中。要怎麼讀這本書,當然是讀者的自由。這本書沒必要從第一章開始依序閱讀(其實前兩章的內容最細雜,可能從第三章開始看比較容易進入狀況)。不過,若試著用參加虛擬課堂的觀點來思考如何利用本書,最理想的方式還是像課堂上的學生那樣,先親自面對原文,就算不親自試譯,至少也在腦中想想「這裡該怎麼譯?」,把原文讀透一遍。還有,很遺憾讀者的譯文無法由教師或院生團隊來批改,但各位可以把存在自己腦中或者已確實寫在紙上的譯文,與各章末尾收錄的教師譯文範例作比較,自行批改,再開始「上課」。
為了讓讀者能更輕鬆地閱讀原文,我也想過要不要加上注釋,但是這種一個英文單字對應一個譯詞的注釋,對翻譯有百害而無一利。儘管比較費事,但長遠看來我還是認為利用字典「閱讀」每個生字的定義和例句,由此掌握詞語整體的「面貌」,才是有益的做法。如同我對待學生的方式,我也同樣將習題原封不動地丟給各位讀者。像這樣親自讀過、譯過,然後發現「這裡該怎麼處理才好?」、「這個地方就是看不懂」,在腦中帶著幾個問號來「上課」,就是最棒的過程。
該感謝的人很多。首先是渡邊利雄老師和島田太郎老師,這兩位在筆者的學生時代灌輸筆者正確閱讀英語的重要性,還有每次上課都踴躍發言的學生,以及曾經應邀來授課的傑・魯賓(Jay Rubin)和村上春樹先生。有兩位蒞臨的課堂,學生的表情真的都容光煥發,我在一旁看了也很高興。還要感謝每次提供課堂協助的小野進老師等視聽覺教育中心的各位,以及文學系教務課的各位。雖然基於公司方針不便在此公布名字,但我也要特別謝謝每次到教室來錄製上課過程、將錄音文字化的責任編輯。每週跟我一起批改學生提交譯文的研究生,新井景子小姐、小澤英實小姐、小路恭子小姐,謝謝妳們。以前不管100 份或200 份,我都得獨自看完批改,但是現在能挪來閱讀報告的時間減少、體力衰退,再加上大腦的轉數(rpm)也大幅降低,研究生助教(TA)已經是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另外小澤小姐在本書原稿的階段已經先行讀過,並給了無數建設性意見。多虧了她的幫忙,全書的明瞭度提升了20%。在此一併致謝。【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 ▎家庭力學Popular Mechanics】
【B】 這裡的getting dark 可能也有「氣氛慢慢變糟」的感覺,我覺得用「而」不太適合。
【柴田】 原來如此。你認為除了字面上的天色變暗,還帶有象徵的意涵是嗎?另外,屋外雖然泥水四濺,算不上賞心悅目,但是不斷有車輛往來。雖然不能說開闊,但至少可以感覺到空間的開放,跟屋裡封閉的感覺剛好形成對比,用順接的「而」來連接,好像把外面的開放感也帶進了屋裡。可能還是用「但」比較安全一點。
這麼一來,要不要用現在進行式來處理「正要變暗」這一句,又很讓人猶豫。先描述了外面窗上的水流、車輛經過等背景確實不錯,以電影手法來說,就像鏡頭穿過窗戶進入屋裡,可以很明顯知道故事正要開始。這時如果用「正要XX」的現在進行式,就能夠感受到逐漸接近、進入,乃至於置身房間裡的感覺。如此雖然非常貼切地展現這種感覺,但是,故事中運用的是冷酷的攝影機,即使面對這對男女,都絲毫不帶同情或共鳴,甚至也不透露憤懣、憎恨或怒氣。這是一架與人保持距離的攝影機,因此在這裡使用「正要⋯⋯」或許太過貼近人物,這當中的拿捏確實不容易。
這種問題不能光看一個句子來決定,是整體風格的問題。這整篇作品都用過去式,但這個譯本卻刻意使用許多現在式,我覺得運用得挺不錯。
***
【特別講座 村上春樹】
音樂最明顯了。每個人的喜好都不同,有人愛聽史克里亞賓(Julian Alexandrovich Scriabin, 1872 - 1915)的鋼琴奏鳴曲,也有人愛聽南方之星。本來就因人而異,每個出場人物的角色都會影響到他們說的話。不過以前我可能不會寫這些,所以或許真的有些改變吧。
【K】所以您並不是有意圖地做出這些改變。
【村上】不是呢。只要塑造好出場人物的角色特性,這個人會說的話就會自然而然地定下來。反過來說,這可能表示我開始能塑造各種類型的出場人物了吧。我果然也慢慢在改變。這點我也有自覺。
【柴田】在《海邊的卡夫卡》裡,約翰走路和桑德斯上校也具有某種象徵意義或者功能不是嗎?那麼這次在《黑夜之後》之中, Denny’s除了代表現實生活中的Denny’s之外,好像也帶有其他衍伸的意義呢。如果是大江健三郎的話,這裡應該會出現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或者聖經吧……【村上】因為修養不同(笑)。
【柴田】不,這其實也代表村上先生能夠把流行文化運用自如啊。
【村上】你還真會說話。不過如果說到把流行文化運用自如,許多年輕作家比我擅長多了。對這些東西我有我的用法,比我更年輕的作家應該也能比我更自然、自由地運用。我覺得本來就可以有許多用法,但並不是刻意為了討好年輕讀者而寫這些,只是故事自然而然地要求這些東西,我才寫出來。
【L】村上先生的小說有時候看起來舞台不像是現實的日本,而是一個捉摸不定的地方。不過我自己反而覺得其中包含著現實感。您在以日本為舞台的小說中作這樣的設定,是有特別的企圖嗎?
【村上】我基本上對寫實主義沒興趣,從來沒想過要寫出具有寫實性的小說。只有一次寫了《挪威的森林》這部小說,完全是寫實主義。當初為什麼要寫這部小說,只是為了向自己證明,如果我想寫寫實的東西,一樣寫得出來。嘗試一次之後認為自己也辦得到,就安心了,然後又往不同方向走了(笑)。你說得沒錯,撰寫一個不存在這裡的世界確實是我的興趣。不對,不像是興趣,應該說是中心思想。所以,《黑夜之後》的姊姊被帶到一個莫名其妙的房間,然後主角這個女孩也身處於黑暗中,進入某種異界當中。那裡雖然是都會裡某條具體的深夜街道,但也是一種異界。那種不同的世界、異界,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其實翻譯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異界體驗。
【柴田】喔,翻譯也是?
【村上】翻譯也是。經由翻譯,可以迅速進入一個跟日常生活不同的地方,這讓我覺得很愉快。我從小就是書蟲,很愛看書,像是翻譯這種事,就算沒人拜託也會做。像這樣逃到一個跟現實不同的世界中是我很喜歡的事情,長大之後也沒改變,動不動就想逃到那邊去。想到報稅、家庭生活,我就馬上想逃(笑)。逃了之後發現還可以賴此維生,簡直太棒了啊。
【柴田】寫小說也是一種逃避嗎?
【村上】就算不是逃避,也等於到了一個不同的世界。來到這間翻譯教室的各位,我想都對翻譯很感興趣,翻譯的好處就是在翻譯的當下你可以「逃避」。還有比這更愉快的事嗎?即使這樣,如果還能靠這個來維生,實在是至高無上的幸福,對吧?(看著柴田)
【柴田】呃……對對對,沒錯沒錯。(眾人爆笑)【村上】我每天早上四點就起來了,四點起來先打開擴大機的開關,放上CD 或者黑膠唱片,用小音量一邊聽音樂一邊翻譯,這就是我最幸福的時光了。
【W】村上先生會看自己作品的評價或者書評嗎?
【村上】不會,至少跟小說有關的評論我都不看,跟翻譯有關的評論我可能會主動去看。但是不看自己小說的評論、批評其實非常不容易,總是會忍不住。年輕時雖然告訴自己不要看,還是會忍不住,接著後悔,現在就完全不看了。別人怎麼寫都無所謂,就算眼前有刊載書評的書或者報紙的書評專欄,我也不看,沒什麼興趣。
【柴田】會看讀者迴響嗎?
【村上】之前有自己的網站時我全部都看。當時我的感想是,這些個別意見或許有的並不正確,有的充滿偏見,但是若統整在一起或許就是正確的聲音。我不看書評家的評論也是因為這樣。當我看過一千則、兩千則讀者意見後,大概就知道了。儘管裡面有正面也有負面,但我可以感受到有一股空氣形成,那股空氣中的人在讀我的作品。就算意見當中有誤解,讓我想要反駁,也沒有辦法。我覺得所謂正確的理解就是誤解的總合。只要聚集大量的誤解,就可以從中建立起正確的理解。假如全都是正確的理解,就無法建立起正確的理解,我覺得必須建立在誤解之上。
【柴田】這麼一來,你覺得評論家的聲音跟讀者的聲音是一樣的嗎?還是不一樣?
【村上】假如有評論家寄了郵件到網站,在網站上的二千多封信裡,他只是2000 分之1。那可能是寫得很精闢的評論,但也只是2000 分之1。對我來說,分量也是一樣的。
【柴田】但如果那是刊登在新聞的書評,就會自以為是百分之百。你指的是這個吧?
【村上】沒有錯。所以我認為,網際網路真的是一種直接民主。雖然會帶有危險性,可是對我們來說幫助很大。在這種直接民主當中交出作品、收到回饋,我覺得很高興,所以網路世界很適合我。遇到像今天這種機會,我也會像這樣跟大家面對面說話,但並不是天天有機會,通信又太沉重,這樣看來網路可以馬上更新、馬上回應,真的很有趣。不過投入網路時就沒辦法做其他事了。對了,前不久我三個月內回了一千六百封信呢 。
【柴田】《海邊的卡夫卡》那時候?
【村上】對。真的很有趣。
這本書是將2004 年10 月到2005 年1 月為止,在東大文學系的課程「西洋近代語學近代文學演習第1 部 翻譯演習」的內容直接化為文字的結果。課堂中的口誤和矛盾等都經過修正,特別是教師的一連串不合理、不明所以的發言,也做了某些程度的合理化修飾,不過基本進行方式都跟實際課堂相同。
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到實際課堂上哪些問題會讓教師和學生特別熱辯得欲罷不能,若是對翻譯或者文字技巧等並不特別感興趣的人,或許會認為那大多是微不足道的爭論。但是也有人認為,一個地方能熱切討論社會上多數人覺得無關緊要的事,才夠格稱為大學。再說,這世上本來就沒有什麼問題能讓萬人同聲認同是全天下最重要的大事。任何事都可能對某人來說無關緊要、對某人來說至關重要。在這2004 年的課堂中,不知為何聚集了不少認為翻譯這個問題至關重要的人,是個相當幸運的場域。我也由衷希望整理內容成書後,能讓更多有同樣想法的朋友模擬參與討論。
課堂的進行方式大致如下:首先我會事先發下習題,請所有學生翻譯、繳交譯文。這些譯文由教師和幾個研究生(該學期有三個)分工修改,寫上評語後在上課時發還。上課時學生手邊會有領回的譯文。課堂上會使用懸吊式攝影機,簡稱OHC,又稱俯視攝影機,或是教材提示裝置,這種工具始終沒有固定名稱,總之就是一部簡單的放映攝影機,可以把事先列印出來的學生譯文映在畫面上提示,一邊跟學生討論,教師當場批改。課堂結束時學生繳交下次上課的習題譯文……這樣的過程重複了一個學期。學生幾乎每星期都得交出翻譯,是挺吃力的一門課。
從1993 年到2001 年,我在教養學系開這門課的時候,授課對象是所有學系的學生,選修人數多達100 ∼ 400 人,授課方式多半是教師一個人講課、對著畫面上的譯文批改(很少有學生能在200 人面前自在發言),2002 年以後我開始在文學系開這門課,授課對象基本上都是文學系學生(也有少部分其他系感興趣的人聞風而來),選修人數大約40 ∼ 60 人左右,教師和學生得以在課堂上做各種討論。其中,2004 年的課堂討論氣氛莫名熱烈。有人常喜歡強調名師、劣師的差異,其實我覺得,一堂課的好壞主要還是掌握在參與的學生手中。要怎麼讀這本書,當然是讀者的自由。這本書沒必要從第一章開始依序閱讀(其實前兩章的內容最細雜,可能從第三章開始看比較容易進入狀況)。不過,若試著用參加虛擬課堂的觀點來思考如何利用本書,最理想的方式還是像課堂上的學生那樣,先親自面對原文,就算不親自試譯,至少也在腦中想想「這裡該怎麼譯?」,把原文讀透一遍。還有,很遺憾讀者的譯文無法由教師或院生團隊來批改,但各位可以把存在自己腦中或者已確實寫在紙上的譯文,與各章末尾收錄的教師譯文範例作比較,自行批改,再開始「上課」。
為了讓讀者能更輕鬆地閱讀原文,我也想過要不要加上注釋,但是這種一個英文單字對應一個譯詞的注釋,對翻譯有百害而無一利。儘管比較費事,但長遠看來我還是認為利用字典「閱讀」每個生字的定義和例句,由此掌握詞語整體的「面貌」,才是有益的做法。如同我對待學生的方式,我也同樣將習題原封不動地丟給各位讀者。像這樣親自讀過、譯過,然後發現「這裡該怎麼處理才好?」、「這個地方就是看不懂」,在腦中帶著幾個問號來「上課」,就是最棒的過程。
該感謝的人很多。首先是渡邊利雄老師和島田太郎老師,這兩位在筆者的學生時代灌輸筆者正確閱讀英語的重要性,還有每次上課都踴躍發言的學生,以及曾經應邀來授課的傑・魯賓(Jay Rubin)和村上春樹先生。有兩位蒞臨的課堂,學生的表情真的都容光煥發,我在一旁看了也很高興。還要感謝每次提供課堂協助的小野進老師等視聽覺教育中心的各位,以及文學系教務課的各位。雖然基於公司方針不便在此公布名字,但我也要特別謝謝每次到教室來錄製上課過程、將錄音文字化的責任編輯。每週跟我一起批改學生提交譯文的研究生,新井景子小姐、小澤英實小姐、小路恭子小姐,謝謝妳們。以前不管100 份或200 份,我都得獨自看完批改,但是現在能挪來閱讀報告的時間減少、體力衰退,再加上大腦的轉數(rpm)也大幅降低,研究生助教(TA)已經是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另外小澤小姐在本書原稿的階段已經先行讀過,並給了無數建設性意見。多虧了她的幫忙,全書的明瞭度提升了20%。在此一併致謝。【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 ▎家庭力學Popular Mechanics】
【B】 這裡的getting dark 可能也有「氣氛慢慢變糟」的感覺,我覺得用「而」不太適合。
【柴田】 原來如此。你認為除了字面上的天色變暗,還帶有象徵的意涵是嗎?另外,屋外雖然泥水四濺,算不上賞心悅目,但是不斷有車輛往來。雖然不能說開闊,但至少可以感覺到空間的開放,跟屋裡封閉的感覺剛好形成對比,用順接的「而」來連接,好像把外面的開放感也帶進了屋裡。可能還是用「但」比較安全一點。
這麼一來,要不要用現在進行式來處理「正要變暗」這一句,又很讓人猶豫。先描述了外面窗上的水流、車輛經過等背景確實不錯,以電影手法來說,就像鏡頭穿過窗戶進入屋裡,可以很明顯知道故事正要開始。這時如果用「正要XX」的現在進行式,就能夠感受到逐漸接近、進入,乃至於置身房間裡的感覺。如此雖然非常貼切地展現這種感覺,但是,故事中運用的是冷酷的攝影機,即使面對這對男女,都絲毫不帶同情或共鳴,甚至也不透露憤懣、憎恨或怒氣。這是一架與人保持距離的攝影機,因此在這裡使用「正要⋯⋯」或許太過貼近人物,這當中的拿捏確實不容易。
這種問題不能光看一個句子來決定,是整體風格的問題。這整篇作品都用過去式,但這個譯本卻刻意使用許多現在式,我覺得運用得挺不錯。
***
【特別講座 村上春樹】
音樂最明顯了。每個人的喜好都不同,有人愛聽史克里亞賓(Julian Alexandrovich Scriabin, 1872 - 1915)的鋼琴奏鳴曲,也有人愛聽南方之星。本來就因人而異,每個出場人物的角色都會影響到他們說的話。不過以前我可能不會寫這些,所以或許真的有些改變吧。
【K】所以您並不是有意圖地做出這些改變。
【村上】不是呢。只要塑造好出場人物的角色特性,這個人會說的話就會自然而然地定下來。反過來說,這可能表示我開始能塑造各種類型的出場人物了吧。我果然也慢慢在改變。這點我也有自覺。
【柴田】在《海邊的卡夫卡》裡,約翰走路和桑德斯上校也具有某種象徵意義或者功能不是嗎?那麼這次在《黑夜之後》之中, Denny’s除了代表現實生活中的Denny’s之外,好像也帶有其他衍伸的意義呢。如果是大江健三郎的話,這裡應該會出現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或者聖經吧……【村上】因為修養不同(笑)。
【柴田】不,這其實也代表村上先生能夠把流行文化運用自如啊。
【村上】你還真會說話。不過如果說到把流行文化運用自如,許多年輕作家比我擅長多了。對這些東西我有我的用法,比我更年輕的作家應該也能比我更自然、自由地運用。我覺得本來就可以有許多用法,但並不是刻意為了討好年輕讀者而寫這些,只是故事自然而然地要求這些東西,我才寫出來。
【L】村上先生的小說有時候看起來舞台不像是現實的日本,而是一個捉摸不定的地方。不過我自己反而覺得其中包含著現實感。您在以日本為舞台的小說中作這樣的設定,是有特別的企圖嗎?
【村上】我基本上對寫實主義沒興趣,從來沒想過要寫出具有寫實性的小說。只有一次寫了《挪威的森林》這部小說,完全是寫實主義。當初為什麼要寫這部小說,只是為了向自己證明,如果我想寫寫實的東西,一樣寫得出來。嘗試一次之後認為自己也辦得到,就安心了,然後又往不同方向走了(笑)。你說得沒錯,撰寫一個不存在這裡的世界確實是我的興趣。不對,不像是興趣,應該說是中心思想。所以,《黑夜之後》的姊姊被帶到一個莫名其妙的房間,然後主角這個女孩也身處於黑暗中,進入某種異界當中。那裡雖然是都會裡某條具體的深夜街道,但也是一種異界。那種不同的世界、異界,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其實翻譯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異界體驗。
【柴田】喔,翻譯也是?
【村上】翻譯也是。經由翻譯,可以迅速進入一個跟日常生活不同的地方,這讓我覺得很愉快。我從小就是書蟲,很愛看書,像是翻譯這種事,就算沒人拜託也會做。像這樣逃到一個跟現實不同的世界中是我很喜歡的事情,長大之後也沒改變,動不動就想逃到那邊去。想到報稅、家庭生活,我就馬上想逃(笑)。逃了之後發現還可以賴此維生,簡直太棒了啊。
【柴田】寫小說也是一種逃避嗎?
【村上】就算不是逃避,也等於到了一個不同的世界。來到這間翻譯教室的各位,我想都對翻譯很感興趣,翻譯的好處就是在翻譯的當下你可以「逃避」。還有比這更愉快的事嗎?即使這樣,如果還能靠這個來維生,實在是至高無上的幸福,對吧?(看著柴田)
【柴田】呃……對對對,沒錯沒錯。(眾人爆笑)【村上】我每天早上四點就起來了,四點起來先打開擴大機的開關,放上CD 或者黑膠唱片,用小音量一邊聽音樂一邊翻譯,這就是我最幸福的時光了。
【W】村上先生會看自己作品的評價或者書評嗎?
【村上】不會,至少跟小說有關的評論我都不看,跟翻譯有關的評論我可能會主動去看。但是不看自己小說的評論、批評其實非常不容易,總是會忍不住。年輕時雖然告訴自己不要看,還是會忍不住,接著後悔,現在就完全不看了。別人怎麼寫都無所謂,就算眼前有刊載書評的書或者報紙的書評專欄,我也不看,沒什麼興趣。
【柴田】會看讀者迴響嗎?
【村上】之前有自己的網站時我全部都看。當時我的感想是,這些個別意見或許有的並不正確,有的充滿偏見,但是若統整在一起或許就是正確的聲音。我不看書評家的評論也是因為這樣。當我看過一千則、兩千則讀者意見後,大概就知道了。儘管裡面有正面也有負面,但我可以感受到有一股空氣形成,那股空氣中的人在讀我的作品。就算意見當中有誤解,讓我想要反駁,也沒有辦法。我覺得所謂正確的理解就是誤解的總合。只要聚集大量的誤解,就可以從中建立起正確的理解。假如全都是正確的理解,就無法建立起正確的理解,我覺得必須建立在誤解之上。
【柴田】這麼一來,你覺得評論家的聲音跟讀者的聲音是一樣的嗎?還是不一樣?
【村上】假如有評論家寄了郵件到網站,在網站上的二千多封信裡,他只是2000 分之1。那可能是寫得很精闢的評論,但也只是2000 分之1。對我來說,分量也是一樣的。
【柴田】但如果那是刊登在新聞的書評,就會自以為是百分之百。你指的是這個吧?
【村上】沒有錯。所以我認為,網際網路真的是一種直接民主。雖然會帶有危險性,可是對我們來說幫助很大。在這種直接民主當中交出作品、收到回饋,我覺得很高興,所以網路世界很適合我。遇到像今天這種機會,我也會像這樣跟大家面對面說話,但並不是天天有機會,通信又太沉重,這樣看來網路可以馬上更新、馬上回應,真的很有趣。不過投入網路時就沒辦法做其他事了。對了,前不久我三個月內回了一千六百封信呢 。
【柴田】《海邊的卡夫卡》那時候?
【村上】對。真的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