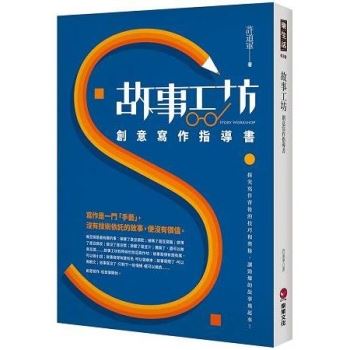故事動力設置
找到自己的A點
創作一個故事,或重新講述一個故事,都是這樣一種創造行為:設置一個生活世界和一些生活人物,透過人物合乎生活邏輯的或改變世界或改變自己的行動,去虛擬地探討、解答與解決作者自己設置的問題,包括關於自己的問題,表達自己對現實世界的態度、理念與情感。這種創造性表達,對作者而言,是直接的而非間接的,是他的世界觀、價值觀,是他對這個世界的發言與宣言。
它不僅關乎「寫什麼」、「怎麼寫」,而且關乎「為什麼要寫」。「如是我聞」或「姑妄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寫」。「下筆前一定問自己:這個劇本你非寫不可嗎?什麼讓你如鯁在喉?也許是一個憤怒、一段思念、一個畫面、一場高潮戲、一個流淚片段,甚至可能是一次委屈。總之,找到這個動力源,把它做為A點確定下來。有了A,才能推演出B,由B再推演C和D。也許往下推演不順而回過頭來調整A,但是,寫劇本必須找到A。」(註83)
陳秋平談的是劇本創作,故事創作也是這樣。寫故事就是寫作者自己,解決作者自己的問題。
將寫作轉化為談話
找到傾訴對象
汪曾祺說:「作者在敘述時隨時不忘記對面有個讀者,隨時要觀察讀者的反應,他是不是感興趣,有沒有厭煩?……寫小說,是個人聊天……寫小說的要誠懇、謙虛、不矜持、不賣弄,對讀者十分地尊重。否則,讀者會覺得你侮辱了他!」(註84)這句話其實透露了兩個資訊:第一個資訊是著名作家的告誡,寫作要尊重讀者;第二層資訊是成功作家的經驗之談,寫作其實就是與讀者對話、聊天。
如果作家、敘述者、人物高度合一的話,這樣的故事最能感動作家自己,但也最容易讓讀者討嫌(新手不知道為什麼,自戀的作家控制不住),因為只要讀者不喜歡上述敘述結構中的任何一項,他都會抵觸你的故事。但你還是有話要說,不可遏制,怎麼辦?不管他!你可以把聽故事的人想像成你無話不說的朋友,他喜歡聽你的嘮叨,那麼你就心無障礙了。實際說來,認真是我的朋友的,我恐怕一個也沒有吧!我把我的內心生活赤裸裸地寫出來時,我恐怕一切的朋友們都要當面唾罵我、不屑我;我恐怕你也是會這樣的吧?我現在寫這封信來要使你不得不飽嚐著幻滅的悲哀,我是誠然心痛;但是我們相交一場,我們只是在面具上彼此親吻,這又是多麼心痛的事實喲!
——郭沫若《喀美蘿姑娘》
創意寫作是一種交流、溝通和說服的活動,透過故事對現實發言或發布宣言,又為了什麼?「要他用你的眼睛看世界,要他同意你的看法,同意這是激動人心的情景,同意這個情景本質上是悲劇,或者另一個故事具有深刻的幽默感。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小說都是說服性的。作者的使命就是,強調所有的對這個世界富於想像力的表現,無論在何種程度上。」(註85)讀者或者聽眾既是故事的接受者,同時也是故事的假想敵,因為想要讀者同情、接受、認同,最後被改變,這就是故事的任務。
談話,而不是寫作,可以激發你創作的熱情,也可以激發你的想像力。因為你知道讀者就在你面前,等著聽你的故事,或者你的介紹,或者你乾脆就跟他們談情說愛、吵架。這個時候你也會熱情洋溢、興致勃勃。在這種狀態下,連最枯燥的解說也生動活潑:
你說你不能直直地把飛盤扔出去?你是不是想對這個人扔,可是卻飛到別的方向去了呢?你說你把它扔了出去——它飛了起來,停在半空中,卻又直接向你飛回來,並打中了你的頭?這個問題同時也困擾著你的兒子嗎?其實,問題在於拿飛盤的手法:你們拿的姿勢錯了。
讓我解釋一下:
你現在的姿勢是把四個手指放在凹槽裡,大拇指放在飛盤的邊緣。錯!你應該把三個手指放在凹槽裡,一個手指放在飛盤的圓邊上,大拇指放在飛盤的上面。當你在扔飛盤的時候,你是不是就是閉上眼睛,朝著你的拍檔的方向一扔,然後就默默地祈禱呢?這樣不好,查理!睜大你的雙眼,盯著你的拍檔,請確保你的手臂是直直地對著他(她),接下來輕輕地扔出去。
現在扔飛盤還難嗎?(註86)
——艾倫.詹森《教你把飛盤扔得最遠》
假想敵
罵人也會罵得活靈活現、慷慨激昂(興高采烈)。
下面是詩人在罵一條河:
鬆軟泥濘的河岸上長滿蘆葦的河流啊!我這麼匆忙地趕路,是要去會見我的情婦哩!
請你將水流停一停吧!因為你既沒有橋樑,又沒有擺渡。如果我沒有記錯,不久之前,你還只是一條小小的水溝,我可以毫不畏懼地涉水而過,因為你的最深處,也不過打濕我的腳踝。然而,遠山上的融雪使你的水流暴漲,沿著你的泥濘河道,大水挾帶著泡沫,狂野地向下奔湧。
你知道我為什麼快馬加鞭、日夜兼程嗎?如果找不到渡河的工具,難道你要我在這裡停下嗎?為什麼我沒有長出達娜厄的英雄兒子所擁有的翅膀呢?如果沒有這雙翅膀,祂怎能砍下梅杜莎那長滿毒蛇頭髮的腦袋呢?
此刻,我多麼渴望眼前能夠出現一輛穀神的戰車,它可將萬穀的種子,撒進無論多麼堅硬的土壤。
噢,所有這些奇蹟,僅僅是詩人的夢想。他們在過去從未為人所見,在將來也不會來到人的身旁。
然而,溢出寬闊河岸的河流啊!不管是昨天,還是在明日,都將活生生地在屬於你自己的疆界裡流淌。萬一你阻止情人會見情婦的事情為人知曉,你的老臉怎能承受公眾的羞辱?
唉,算了,這些煩心的事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自己的不幸已夠我承受的了!
看我,真是一個蠢蛋,居然對這條小溪大談河流的愛情故事,在如此可憐的一條小溪面前提到如此偉大的河流的名字,唉,我是羞愧難當啊!我這是做什麼白日夢呢?居然對它大談阿克洛奧斯河、伊納科斯和寬闊的尼羅河!
滾開吧!你這條醜陋、泥濘的溪流,永遠灼熱的夏天和無雨的冬天就是等待你的命運!(註87)
「謹以此文獻給某某」的故事講述方式太多了,「某某」可以是一個人、一個地方、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者是更大的單位,比如地球。「某某」可以是你認識的人(因此要特別善待你的戲水夥伴和工作坊老師,他們是你的第一讀者),也可以是你不認識的人,比如這樣:
讀者,我不知道你是誰,也不知道你在哪年哪月翻開這一頁歷史的殘篇。但是,如果你懷念那些在這裡遇害的冤魂,你還想伸張人間的正義,那麼,請涉過這條坑坑窪窪、野草覆蓋的小徑,到我的身邊來,把手放在我衰弱的身軀上,我會慢慢向你訴說我所看到的一切……(註88)
——竹林《女巫》
找到自己的A點
創作一個故事,或重新講述一個故事,都是這樣一種創造行為:設置一個生活世界和一些生活人物,透過人物合乎生活邏輯的或改變世界或改變自己的行動,去虛擬地探討、解答與解決作者自己設置的問題,包括關於自己的問題,表達自己對現實世界的態度、理念與情感。這種創造性表達,對作者而言,是直接的而非間接的,是他的世界觀、價值觀,是他對這個世界的發言與宣言。
它不僅關乎「寫什麼」、「怎麼寫」,而且關乎「為什麼要寫」。「如是我聞」或「姑妄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寫」。「下筆前一定問自己:這個劇本你非寫不可嗎?什麼讓你如鯁在喉?也許是一個憤怒、一段思念、一個畫面、一場高潮戲、一個流淚片段,甚至可能是一次委屈。總之,找到這個動力源,把它做為A點確定下來。有了A,才能推演出B,由B再推演C和D。也許往下推演不順而回過頭來調整A,但是,寫劇本必須找到A。」(註83)
陳秋平談的是劇本創作,故事創作也是這樣。寫故事就是寫作者自己,解決作者自己的問題。
將寫作轉化為談話
找到傾訴對象
汪曾祺說:「作者在敘述時隨時不忘記對面有個讀者,隨時要觀察讀者的反應,他是不是感興趣,有沒有厭煩?……寫小說,是個人聊天……寫小說的要誠懇、謙虛、不矜持、不賣弄,對讀者十分地尊重。否則,讀者會覺得你侮辱了他!」(註84)這句話其實透露了兩個資訊:第一個資訊是著名作家的告誡,寫作要尊重讀者;第二層資訊是成功作家的經驗之談,寫作其實就是與讀者對話、聊天。
如果作家、敘述者、人物高度合一的話,這樣的故事最能感動作家自己,但也最容易讓讀者討嫌(新手不知道為什麼,自戀的作家控制不住),因為只要讀者不喜歡上述敘述結構中的任何一項,他都會抵觸你的故事。但你還是有話要說,不可遏制,怎麼辦?不管他!你可以把聽故事的人想像成你無話不說的朋友,他喜歡聽你的嘮叨,那麼你就心無障礙了。實際說來,認真是我的朋友的,我恐怕一個也沒有吧!我把我的內心生活赤裸裸地寫出來時,我恐怕一切的朋友們都要當面唾罵我、不屑我;我恐怕你也是會這樣的吧?我現在寫這封信來要使你不得不飽嚐著幻滅的悲哀,我是誠然心痛;但是我們相交一場,我們只是在面具上彼此親吻,這又是多麼心痛的事實喲!
——郭沫若《喀美蘿姑娘》
創意寫作是一種交流、溝通和說服的活動,透過故事對現實發言或發布宣言,又為了什麼?「要他用你的眼睛看世界,要他同意你的看法,同意這是激動人心的情景,同意這個情景本質上是悲劇,或者另一個故事具有深刻的幽默感。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小說都是說服性的。作者的使命就是,強調所有的對這個世界富於想像力的表現,無論在何種程度上。」(註85)讀者或者聽眾既是故事的接受者,同時也是故事的假想敵,因為想要讀者同情、接受、認同,最後被改變,這就是故事的任務。
談話,而不是寫作,可以激發你創作的熱情,也可以激發你的想像力。因為你知道讀者就在你面前,等著聽你的故事,或者你的介紹,或者你乾脆就跟他們談情說愛、吵架。這個時候你也會熱情洋溢、興致勃勃。在這種狀態下,連最枯燥的解說也生動活潑:
你說你不能直直地把飛盤扔出去?你是不是想對這個人扔,可是卻飛到別的方向去了呢?你說你把它扔了出去——它飛了起來,停在半空中,卻又直接向你飛回來,並打中了你的頭?這個問題同時也困擾著你的兒子嗎?其實,問題在於拿飛盤的手法:你們拿的姿勢錯了。
讓我解釋一下:
你現在的姿勢是把四個手指放在凹槽裡,大拇指放在飛盤的邊緣。錯!你應該把三個手指放在凹槽裡,一個手指放在飛盤的圓邊上,大拇指放在飛盤的上面。當你在扔飛盤的時候,你是不是就是閉上眼睛,朝著你的拍檔的方向一扔,然後就默默地祈禱呢?這樣不好,查理!睜大你的雙眼,盯著你的拍檔,請確保你的手臂是直直地對著他(她),接下來輕輕地扔出去。
現在扔飛盤還難嗎?(註86)
——艾倫.詹森《教你把飛盤扔得最遠》
假想敵
罵人也會罵得活靈活現、慷慨激昂(興高采烈)。
下面是詩人在罵一條河:
鬆軟泥濘的河岸上長滿蘆葦的河流啊!我這麼匆忙地趕路,是要去會見我的情婦哩!
請你將水流停一停吧!因為你既沒有橋樑,又沒有擺渡。如果我沒有記錯,不久之前,你還只是一條小小的水溝,我可以毫不畏懼地涉水而過,因為你的最深處,也不過打濕我的腳踝。然而,遠山上的融雪使你的水流暴漲,沿著你的泥濘河道,大水挾帶著泡沫,狂野地向下奔湧。
你知道我為什麼快馬加鞭、日夜兼程嗎?如果找不到渡河的工具,難道你要我在這裡停下嗎?為什麼我沒有長出達娜厄的英雄兒子所擁有的翅膀呢?如果沒有這雙翅膀,祂怎能砍下梅杜莎那長滿毒蛇頭髮的腦袋呢?
此刻,我多麼渴望眼前能夠出現一輛穀神的戰車,它可將萬穀的種子,撒進無論多麼堅硬的土壤。
噢,所有這些奇蹟,僅僅是詩人的夢想。他們在過去從未為人所見,在將來也不會來到人的身旁。
然而,溢出寬闊河岸的河流啊!不管是昨天,還是在明日,都將活生生地在屬於你自己的疆界裡流淌。萬一你阻止情人會見情婦的事情為人知曉,你的老臉怎能承受公眾的羞辱?
唉,算了,這些煩心的事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自己的不幸已夠我承受的了!
看我,真是一個蠢蛋,居然對這條小溪大談河流的愛情故事,在如此可憐的一條小溪面前提到如此偉大的河流的名字,唉,我是羞愧難當啊!我這是做什麼白日夢呢?居然對它大談阿克洛奧斯河、伊納科斯和寬闊的尼羅河!
滾開吧!你這條醜陋、泥濘的溪流,永遠灼熱的夏天和無雨的冬天就是等待你的命運!(註87)
「謹以此文獻給某某」的故事講述方式太多了,「某某」可以是一個人、一個地方、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者是更大的單位,比如地球。「某某」可以是你認識的人(因此要特別善待你的戲水夥伴和工作坊老師,他們是你的第一讀者),也可以是你不認識的人,比如這樣:
讀者,我不知道你是誰,也不知道你在哪年哪月翻開這一頁歷史的殘篇。但是,如果你懷念那些在這裡遇害的冤魂,你還想伸張人間的正義,那麼,請涉過這條坑坑窪窪、野草覆蓋的小徑,到我的身邊來,把手放在我衰弱的身軀上,我會慢慢向你訴說我所看到的一切……(註88)
——竹林《女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