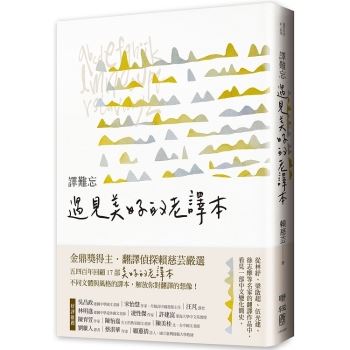斷盡支那蕩子腸:林紓、王壽昌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一八九九)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這兩句嚴復的詩,說明了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 1848)在中國翻譯史上難以取代的地位。林紓一八九九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是近代第一部暢銷西洋翻譯小說。至於為何名滿天下的Dumas父子不叫「杜馬」而叫「仲馬」,則跟林紓和王壽昌都是福州人有關:這在聲韻學上叫做「端知不分」,也就是說現在國語中的「ㄓ」聲母字,在中古音系與「ㄉ」聲母不分(如臺語的「豬」、「箸」就是明顯的例子),所以用臺語念「仲馬」會比國語更接近法文發音。畢竟林紓的年代還沒有所謂的國語,當時所翻譯的人名地名,不少都有方言影響;另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Holmes譯為福爾摩斯(請以臺語念「福氣啦」就知道福與H的關係了)。林紓影響力太大,小仲馬大概很難翻案成為小杜馬了,福爾摩斯也很難翻譯成為霍姆斯了。
林紓(一八五二—一九二四)是福州人,父親曾到臺灣淡水經商。他三十歲才中舉,一直考不上進士,與官場無緣。他人生的轉捩點就是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他不會外文,這本影響中國翻譯史的作品是他的同鄉王壽昌口譯的。王壽昌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留法六年。一八九七年,林紓喪偶,心緒不佳,遇到回母校船政學堂教法文的王壽昌。王壽昌跟他說了小仲馬的茶花女故事,林紓便以文言文翻譯了出來,一八九九年自刻出版,首版只印了一百本,分贈親友留念而已。沒想到一砲而紅,兩人都因此在翻譯史上留名。根據王壽昌的孫子王文興教授說法,他比對王壽昌本人的筆記,認為《巴黎茶花女遺事》或許是王壽昌的作品多些,只是由林紓潤筆。但無論如何,林紓從此老運大開,一連翻譯了兩百多本作品,都是由合作者口述,林紓筆述,林紓的翻譯才具無庸置疑。他翻譯的長篇名作不少,短篇也很好,像是《羅剎因果錄》(托爾斯泰故事集)就有幾篇很棒的小品。
現代讀者一聽說林紓本人不會外語,竟然能成為翻譯大師,往往嘖嘖稱奇;其實中國翻譯史上這種合作模式本來就是常態,從佛經翻譯開始就是由西僧口述,中國弟子筆受;明朝利瑪竇和徐光啟也是合作翻譯,「平行線」、「鈍角三角形」這些詞彙都是合作翻譯出來的;一直到清朝的聖經翻譯還是如此,由歐洲傳教士口述,中國教徒筆受。與林紓同時代的清末民初譯者,合作模式也很常見,像是《婀娜小史》(安娜‧卡列妮娜)、《十之九》(安徒生童話)都是合作的,由讀過洋學堂的陳家麟口述,晚清舉人陳大鐙筆述。後來有些讀洋學堂的文人,也開始自己翻譯,像是林紓的長期合作者魏易(張艾嘉的外曾祖父),是上海梵王渡學院(後來的聖約翰大學)畢業的,與林紓合譯了四十多本書之後,開始自己獨立翻譯。嚴復、伍光建、周作人這些譯者也都是洋學堂出身,留學外國者也越來越多,翻譯才漸漸由兩人合作模式轉變為通外語者獨立作業。
林紓晚年與五四文人打筆仗,說不過進步青年,十分落寞,在一九一九年四月間寫下:「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但在過世之後,五四文人紛紛懷念小時候看林譯小說的快樂。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就稱讚林紓:
林紓譯小仲馬的「茶花女」,用古文敘事寫情,也可以算是一種嘗試。自有古文以來,從來不曾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闢了一個新殖民地。
只是白話文運動一舉成功,林紓的譯筆再好也失去舞臺了。雖然現在課本中還是會提到林紓的名字和他翻譯的幾本名作,但真正看過林譯小說的恐怕寥寥無幾。因此本書的第一篇,還是來看看林紓的文筆吧。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這兩句嚴復的詩,說明了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 1848)在中國翻譯史上難以取代的地位。林紓一八九九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是近代第一部暢銷西洋翻譯小說。至於為何名滿天下的Dumas父子不叫「杜馬」而叫「仲馬」,則跟林紓和王壽昌都是福州人有關:這在聲韻學上叫做「端知不分」,也就是說現在國語中的「ㄓ」聲母字,在中古音系與「ㄉ」聲母不分(如臺語的「豬」、「箸」就是明顯的例子),所以用臺語念「仲馬」會比國語更接近法文發音。畢竟林紓的年代還沒有所謂的國語,當時所翻譯的人名地名,不少都有方言影響;另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Holmes譯為福爾摩斯(請以臺語念「福氣啦」就知道福與H的關係了)。林紓影響力太大,小仲馬大概很難翻案成為小杜馬了,福爾摩斯也很難翻譯成為霍姆斯了。
林紓(一八五二—一九二四)是福州人,父親曾到臺灣淡水經商。他三十歲才中舉,一直考不上進士,與官場無緣。他人生的轉捩點就是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他不會外文,這本影響中國翻譯史的作品是他的同鄉王壽昌口譯的。王壽昌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留法六年。一八九七年,林紓喪偶,心緒不佳,遇到回母校船政學堂教法文的王壽昌。王壽昌跟他說了小仲馬的茶花女故事,林紓便以文言文翻譯了出來,一八九九年自刻出版,首版只印了一百本,分贈親友留念而已。沒想到一砲而紅,兩人都因此在翻譯史上留名。根據王壽昌的孫子王文興教授說法,他比對王壽昌本人的筆記,認為《巴黎茶花女遺事》或許是王壽昌的作品多些,只是由林紓潤筆。但無論如何,林紓從此老運大開,一連翻譯了兩百多本作品,都是由合作者口述,林紓筆述,林紓的翻譯才具無庸置疑。他翻譯的長篇名作不少,短篇也很好,像是《羅剎因果錄》(托爾斯泰故事集)就有幾篇很棒的小品。
現代讀者一聽說林紓本人不會外語,竟然能成為翻譯大師,往往嘖嘖稱奇;其實中國翻譯史上這種合作模式本來就是常態,從佛經翻譯開始就是由西僧口述,中國弟子筆受;明朝利瑪竇和徐光啟也是合作翻譯,「平行線」、「鈍角三角形」這些詞彙都是合作翻譯出來的;一直到清朝的聖經翻譯還是如此,由歐洲傳教士口述,中國教徒筆受。與林紓同時代的清末民初譯者,合作模式也很常見,像是《婀娜小史》(安娜‧卡列妮娜)、《十之九》(安徒生童話)都是合作的,由讀過洋學堂的陳家麟口述,晚清舉人陳大鐙筆述。後來有些讀洋學堂的文人,也開始自己翻譯,像是林紓的長期合作者魏易(張艾嘉的外曾祖父),是上海梵王渡學院(後來的聖約翰大學)畢業的,與林紓合譯了四十多本書之後,開始自己獨立翻譯。嚴復、伍光建、周作人這些譯者也都是洋學堂出身,留學外國者也越來越多,翻譯才漸漸由兩人合作模式轉變為通外語者獨立作業。
林紓晚年與五四文人打筆仗,說不過進步青年,十分落寞,在一九一九年四月間寫下:「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但在過世之後,五四文人紛紛懷念小時候看林譯小說的快樂。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就稱讚林紓:
林紓譯小仲馬的「茶花女」,用古文敘事寫情,也可以算是一種嘗試。自有古文以來,從來不曾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闢了一個新殖民地。
只是白話文運動一舉成功,林紓的譯筆再好也失去舞臺了。雖然現在課本中還是會提到林紓的名字和他翻譯的幾本名作,但真正看過林譯小說的恐怕寥寥無幾。因此本書的第一篇,還是來看看林紓的文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