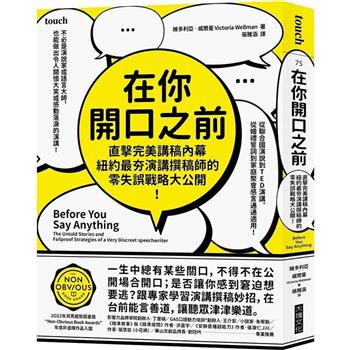4.盤問(節選)
挖掘你還沒意識到的素材
你有思想、有經驗,還有想法與知識,腦中已坐擁大量演講題材(有些素材可能在助理幫你整理的電子郵件和文檔裡),就這麼挺身接下講者這份任務。你可能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素材,但反正你手上有題材就是了。我懷疑,許多人之所以害怕寫講稿,有個原因就是他們擔心動筆寫稿後會發生什麼事。確切來說,他們怕的是:要是什麼都沒發生怎麼辦?但有時候,你就是得趕快將腦袋裡那些模糊的初步概念寫下來,先別去擔憂口才和影響力的問題。我敢保證,要是你寫稿時放手讓自己隨心所欲、反覆無常,甚至自由發揮,沒頭沒腦地把事物串聯起來,那麼你的筆記裡就有七成的演講內容了。讓大腦洩洪(brain dump)令人自由自在,但你得容忍自己笨手笨腳、自然而然把話講得語無倫次──反正你現在只是在卸貨啊。我準備講稿初期的筆記根本就像天書,讓人連看都看不懂,更遑論要理解了:東缺一字西少一字,句子都沒寫完,點列式記下一大堆東西,還有稍晚要再回頭看的問題。
你或許會拿著筆和筆記本,兩腳盤在沙發上就開始寫。或許你會更想找個安靜的房間,對著螢幕上一片發光的空白開始打字。不過我為自己的演講和別人的演講打初稿時,發現拿筆寫字才能打造出那些隨機的連結。我感覺要是自己在打字,就很容易因為自我挫敗心態或自我意識,把「不正確」的想法都刪除掉。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在電腦和螢幕周圍的桌上放了幾本大大的可撕式筆記本,桌面也散著一頁又一頁的筆記;這麼一來,我梳理各章初步構想時,就能撕下筆記,把他們搬來又移去。我桌上沒剩多少空間能擺東西,所以大部分的筆記都沾了早餐的杏仁醬、咖啡和獨門「速成沙拉醬」(每次都做得太酸),斑斑點點髒成一片。看頁面沾到哪種食物的污漬,搞不好就能看出是我什麼時候寫的筆記。嗯,或許我該把這段細節刪掉才對。
說到讓大腦洩洪,我跟講者合作時,會在創意啟動會後半段開始做類似的活動,之後我會再用「二十個問題」(The 20 Questions)跟進,使概念更為凝聚。二十個問題是我創作法的基石。你或許聽過小朋友玩的「二十個問題」遊戲:主持人得想著某種動物、某行職業或某個國家,其他玩家得透過是非題向主持人確認謎底特質,設法在二十個問題內推斷出答案──演講實驗室的「二十個問題」可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這些問題的意圖很明確,是要引出深思熟慮、詳盡仔細、清晰無比的答案。我把「二十個問題」當成慣用的訪問技巧,持續頻繁使用,要說我對它的忠誠度到近乎信仰的地步也不為過。(納森和我是猶太人沒錯,但納森發表的逾越節哈加達〔Passover Haggadah〕擁戴外星人入侵論,讚揚歌手吐派克〔Tupac〕,還說希伯來先知以利亞〔Elijah〕是重金屬之神,嗯,總之故事就是這樣啦。)
每位客戶都會收到我寄的「二十個問題」。在我歸檔的成千上百份「二十個問題」裡,雖然從沒哪兩份長得一模一樣,但我精心寫下這些問題的目的卻都相同:我要跟深入鑽研創意啟動會時浮現的那些主題和概念,揭示出人意料的細節、不為人知的故事、未能盡善盡美的意見、罕為聽聞的事實──就我的創意簡報來看,我知道這些內容能為敘事增添質感、原創性、真實感與人性。你問為什麼是二十個問題?因為有了二十這個數字,目標就很明確,一切都有了目的,這讓我不得不小心謹慎地列出每一道問題,把題目寫得精精確確。我們演講實驗室不問浪費人生的問題,也不問打混偷懶的問題。而且,要是有份問卷的問題少於二十個,要怎麼稱呼它才好?「問題」?「一些問題」?「你的專屬問題」? 我覺得這樣未免太籠統了吧!哪算得上什麼問卷標題?
每位講者來到演講實驗室時,對演講的準備程度都不同──而程度的差異通常(雖然也未必)取決於他們對登台演講的渴望。有的人可能是受邀去講講話,便覺得自己有義務演講,有的人可能是在積極尋找登台機會;他們對演講的感受也都不相同,從不安全感(我到底要說什麼?)到過度自信(我完全清楚自己要說什麼)都有。講者對演講的感受不一,未必對自己想分享的觀點有把握,但有件事我倒是有十足把握:講者來找我的時候,沒有誰完完全全清楚自己要怎麼把一個概念(或不只一個概念)轉化成五分鐘、十分鐘或四十分鐘的演講。而「二十個問題」能為我們好好梳理這道難題。啟動會聊到的大部分內容,會成為建構二十個問題的基礎,也是我以問題深入探究的對象;不過,這二十個問題的實際功用與演講類型息息相關,要看這次打磨的是哪種演講而定。
若檢視演講實驗室的內部工作安排,就會發現我們從頭到尾、方方面面都把「關於人的演講」和「關於事物的演講」分很開。我很少讓同一位撰稿師跨足兩種不同類型的稿子,這兩種講稿的寫作訓練也大不相同。而且我還堅持:撰稿師負責的如果是「關於人」的演講,就要穿紅色,象徵愛與溫暖;要是負責「關於事物」的演講,那就要穿藍色,代表藍天般的創意思維──剛剛講的這段當然是開玩笑啦,完全瞎扯淡。不過,這種分工方式裡有個重點,就是擬定二十個問題的視角,會依據演講類型有所不同。一個視角要求講者內省,向內觀望,眼界深遠,無窮無盡。另一個視角則要求講者抽絲剝繭,細細拆解分析,鉅細靡遺。
正如前一章說明的,如果你的演講主題是人,光把對方變成敘事裡的主要角色還不夠。你講的內容要非常具體。聽眾會期待,在婚喪場合的致詞裡聽聽至親好友的行止軼聞, 痛痛快快笑一回或哭一場──講的是他們早知道的事也好,是他們從未聽聞的事也罷。但這不表示他們想聽你說新娘熱愛瑜伽、是《鑽石求千金》(The Bachelor)的狂粉。我們把話講明了吧:一畢業就找到工作的千禧世代都會女性,幾乎沒幾個不是這樣。聽眾會想知道新娘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興趣,想明白這些事又如何展現她的性格特質。她練瑜伽的方式和別人有什麼不同嗎?有沒有什麼趣聞軼事?例如,她會不會練完瑜珈又不洗澡?她做戰士二式(Warrior Two)的時候,是不是跟我一樣頭老是轉錯邊?還有,她為什麼不看《與卡戴珊一家同行》(Kardashians)或《酷男的異想世界》(Queer Eye),或另外那個叫什麼的……那個所有參加者得穿泳裝和比基尼又要努力戒色禁欲的實境節目?這類小觀察會揭露新娘獨一無二的特質,而大家可能還不知道這些事。婚禮、成人禮和其他代表人生里程碑的儀式,大家三不五時就要跑個幾場;有鑑於此,講者的首要目標,應該是為主角打磨出專屬致詞,獨特到下周末在同一場地結婚的新娘親友絕對無法照抄。
培訓新手撰稿師時,我們常討論問題要怎麼問才高明,才有助打造獨樹一幟的演講──討論關於人的演講時尤其如此。我們這些訪談者問得愈具體,就愈能把客戶往成功的路上推進。要是我們能為講者描繪出某個場景,或讓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某個時刻,講者回答起問題就更容易。我們都是按初次接洽客戶時的創意電訪(Creative Call)談話內容客製二十個問題。不過我畢竟也創業十二年了,明白哪些問題最能引人說出最合適的背景資訊,所以我們也有個題庫,會從那些長青題目裡挑問題來問。例如,要講婚禮致詞、成人禮敬酒詞或喪禮悼詞,可能就會收到以下問題:
回想一下……你女兒十五歲時,臥室牆上掛著什麼?
你兒子的學校成績單上,有沒有哪則評語會反覆出現,讓你每次看到都超級詫異?
你女兒十三歲前做過最有趣的是什麼事?
假設現在是星期六中午,你急著要找你母親──那會先去哪裡找?
臥室牆壁那則問題,引發我客戶華特一段特別的回憶:他女兒在床頭牆上貼了一張瑪丹娜海報,父女倆為此大吵一架。吵到氣頭上,華特就衝進臥室把海報扯下來。華特被尚.保羅.高堤耶(Jean Paul Gaultier)設計的胸罩激怒了(簡直離經叛道!),覺得那張海報很不得體。他女兒則認為那是她的個人空間,可以隨她裝飾。她有好幾個禮拜都不和爸爸說話。華特說女兒至今一如往昔,是位性格剛烈、擇善固執、獨立自主的年輕女性──這段故事恰好能映襯這番特質。如果我們只問華特記不記得女兒十幾歲的樣子,他可能根本就不會想起那張海報,那麼他對女兒的描述,聽起來八成和其他十幾歲的女孩差不多。
關於事物的演講,聽眾通常是同業和其他專業人士而非親友,那麼我們的二十個問題就會因講者與題目制宜,較為多變。我前一章已談過:若要將個人經驗融入演講,撰稿時一定要維持一定程度的客觀,才能決定要講多少、什麼時候講──在這章裡,這種客觀視角可是必要條件了。就算我的合作對象是口腔外科醫師,再假設他的聽眾是滿屋醫療從業人員,人人都對溫度與連結這些事不怎麼感興趣,反倒殷殷期盼要聽到某台醫療儀器的最新發展,那機器的名字裡還有一大堆連字符和數字──我仍會試著在講稿裡營造一點人性化的橋段(雖然要辦到這點可能跟拔牙一樣痛苦艱難)。
你還記得讓我落淚的比基尼太空人雪麗嗎?我們第一次合作那場天文館演講時,雪麗完全不曉得自己想談什麼。要是你受邀演講,不管是商務研討會、募款活動、開幕式或年會,通常都是因為你知道某件事、經歷某件事、做過某件事或準備要做某件事,而人們對你的評價很高。但就雪麗的案子來看,她是因為「一整段」人生經歷才登上那座頒獎台──包含她擔任工程師達致的成就,包括她培訓太空人的貢獻,也涵蓋她對規畫民間太空體驗的投入。
我當時正好在培訓一位撰稿師,於是就建議由那位新同事負責創意電訪,再讓她針對二十個問題的內容向我提案。我們初步探索、梳理創意簡報的過程中,明白聽眾會期待雪麗多多少少分享一點職涯故事,而且她領的還是女性科學家獎,大家可能想聽聽她身為女性航太工程師的經歷。我們也假設聽眾渴望聽她談自己對太空旅行的見解。所以我們問了一大堆問題,想了解她的所知所聞、認識她的專業領域,因為「成為專家」也是我們職責的一部分。不過,替我們挖出演講主題的問題跟工作無關,我們問她,在職涯以外,她人生中有沒有什事件特別令人難忘?問問題的時候,我們也提了她近期在民營太空旅行領域的工作:
對你服務的這群人而言,你帶給他們的體驗肯定是他們人生中數一數二難以忘懷的經歷。對你而言,有沒有哪件事在你人生中是特別關鍵呢?初吻?生小孩?畢業?出車禍?還是看到外星人?
她答道:
有幾件事對我來說特別有意義:我的婚禮、我女兒她們出生,還有第一次參觀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天文台背後的深刻意涵讓我震懾不已。我解釋一下格林威治的事好了──你想想,世界上有多少事情能讓全世界「同意達成共識」?我們沒有一致的語言,沒有一致的曆法,也沒有一致的精神信仰,大家意見不同的事數也數不清。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卻定義出同一套座標系來描述地球:赤道、兩極和本初子午線。因此伊萊子午儀(Airy telescope/Airy Transit Circle)的十字準線對我來說簡直有魔法,能為全人類定義座標系的魔法──畢竟所有工程問題都要先從定義座標系開始。格林威治之行讓我體驗了一種純粹的魔法──從定義全世界的共同座標系這件基本的事情裡,我感受到自己和人類的力量與未來願景,有著確確實實的聯繫。
中了!她的回答讓我們明白,這場演講要談的不是女科學家,也不是太空人。雪麗要談的是,遙遠的星系裡是否存在著和諧一致,以及這件事對於地球上的和諧一致又有何影響。我們詢問她人生是否有什麼關鍵事件時,本來也不確定雪麗會不會列舉到婚禮就沒下文。幸好──對於她的演講和本書的開場白來說都是萬幸──雪麗沒有停在婚禮而已。
我們也不是刻意要讓她講去天文台的事,而是想以她的方式去認識、理解世界;要想辦到這點,唯一的方法就是拋給她一連串問題,問一大堆看似稀鬆平常的事。我說深入內省總能發掘最真最有趣的素材,就是這個意思,這些素材會成為堆疊敘事的積木。
如果將問題剝去皮肉形體,展露骨幹精髓,就能看出:我們其實是透過點出雪麗職涯中情感層面的真相(規畫民間太空旅程的乘客體驗,能夠改變他人人生),讓她發掘自己生命中有什麼事件能呼應這種轉折。本來我們也不知道,雪麗分享的難忘時刻會如此巧妙地與她的工作、她受邀演講的原因相互聯繫。如果雪麗跟我們講另一個完全不相干的故事(例如:她跑去參加禪修,從此決定不再殺蜘蛛),那我們就會用這個故事來打造不同的演講效果,或者就直接把它放一邊不管。我們問下個問題時,本來預設雪麗分享的內容可能會是一段波瀾壯闊的故事。結果她的答案很逗趣,正好拿來當引子為演講破冰。
你記不記得,是誰或哪件事讓你迷上太空?她回答:
我媽媽很愛話當年:我還是小嬰兒的時候,她看到一則談太空任務的新聞提要,心裡默默想著,「喔,希望她這輩子都不會去做那種事」。
前幾天,有位花旗銀行的重要利害關係人告訴我,回答我的問題,感覺就像是坐在心理分析師診療室的椅子上。我從很早以前就說我的訪談過程是在模仿心理治療,雖然那時我根本也不曉得真正的心理治療長怎樣。我現在曉得了,謝天謝地,我說的沒錯,太好了!(不過我現在還多了治療師的帳單要付,這就不怎麼好了。)訪談過程涉及諸多隱私,而且可能讓人坐立難安,但就像心理治療一樣,要是你不克服心中不適就不會進步。要是你有空間能傾訴心聲,能表達自己最情緒滿溢的想法和感受,要是你被誘導著往更深處去,那自然而然就能發掘出更有趣又有幫助的事物。前幾天我聽了一個podcast,製作人告訴來賓:「來聊聊這件事吧,你一路講我會一路逼問到底。」我心裡想:就是要這樣! 重點就是把受訪者往正確的方向逼。我們懷著記憶、理論、智慧、經驗、軼事、信念和觀點行走人世,但卻認為這些東西不重要,暗自封藏心底,某天有人問了對的問題,這些事物才終於流瀉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