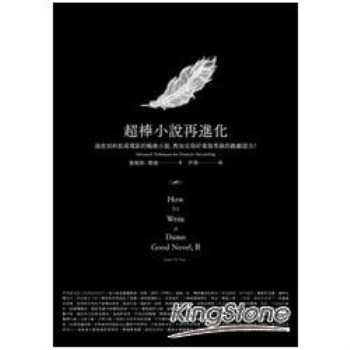帶領讀者進入你創造的時空
寫小說是種服務業
假如你想在服務業打天下,你得知道客戶為何上門,而你該如何滿足他們的需求。
比方說,如果你經營一間清潔公司,你該知道顧客期待看到光可鑑人的地板,以及閃閃發亮的浴室;如果你是個離婚律師,你得瞭解客戶不只想獲得一大筆贍養費,還會想要讓前妻或前夫嘗到苦頭。小說寫作是一種服務業,在你坐下來寫一本超棒小說之前,得先知道讀者要的是什麼。
如果你寫的是非小說,讀者要什麼,端看你寫的是什麼書。教人致富的勵志書,會有不少章節告訴讀者,要對自己保持信心,堅持奮鬥,準時交稅以避免國稅局找碴等等。性愛指導手冊裡應該要放大量圖片,並且誇稱練習書中扭來扭去的姿勢,將有助心靈成長。而獨裁者穆加比的傳記裡,應該收集且詳述這壞蛋做過的所有醜事,不管重不重要。
就非小說的書籍寫作而言,作者的主要目的在於提供資訊給讀者,你要陳述事實,且針對這些事實,提出見解。
小說不一樣。一般而言,小說作者所陳述的並非事實,當然也談不上針對事實,提出見解。讀者很難從小說裡獲得所謂系統性的知識,因為小說是虛構的、完全出於想像,書中所陳述的事件從來不曾發生,所描寫的人物也從不存在。那麼,稍微有一點腦袋的人為什麼要買這種騙人的東西?
部分原因頗明顯。推理小說的讀者期待在書的開頭陷入迷霧,而在書的結尾對偵探的聰慧感到歎服;歷史小說的讀者期待品嘗曾經有過的輝煌年代京華煙雲;而愛情小說的讀者則想看到大膽的女主角與英俊的男主角,以及很多令人心神蕩漾的戀情場景。
狄佛托(Bernard DeVoto)在《小說世界》(The World of Fiction)中說,人看書是為了「樂趣。……除了專業與半專業人士之外,沒有人會為了其他理由看小說。」
確實,事情就這麼簡單,一般讀者就只為了樂趣而看小說。但為了達到娛樂讀者的效果,作者要做的事卻絕不簡單,因為,你要帶領讀者進入另一個時空。當讀者看書時,如果覺得像是真的活在小說世界裡,真實世界反而消失無蹤,那麼他們就是被帶進另一個時空了。
來到另一個時空的讀者,像是在作著「虛構的夢」。賈德納(John Gardner)在所著《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Fiction)中說:「不管是哪種類型的小說,『虛構的夢』就是小說讓人著迷之處。」
虛構的夢是靠暗示的力量所建構。廣告人、騙子、宣傳家、教士、催眠師,都是用暗示的力量當成主要操作手法,小說家也是。不過,廣告人、騙子、宣傳家和教士,是用暗示的力量來說服別人,而催眠師和小說家則是用它來引導,讓人進入另一個意識狀態。
你會說,哇,這聽起來好神祕!從某個角度來看,確實如此。
催眠師使用暗示的力量,引導被催眠者進入恍惚的情境。催眠師教你坐在椅子上,看著一個發亮的東西,比方一個吊飾,催眠師輕輕晃動那吊飾,抑揚頓挫地說:「你的眼皮很沉重,你覺得愈來愈放鬆,聽著我的聲音,愈來愈放鬆……你的眼睛開始閉起來了,你發現自己在心中的一座樓梯上,你往下走,往下,往下,下到黑暗又安靜的地方,黑暗又安靜……」妙哉,你真的覺得愈來愈放鬆。
催眠師又說:「你看到自己在一座美麗的花園裡,站在步道上,這裡好安靜、好祥和。是慵懶的夏日,太陽出來了,溫暖的微風吹拂,木蘭花盛開……」
催眠師說出的這些詞句,提到的這些東西──花園、步道、木蘭花──會在你的意識裡出現,你感覺到微風吹拂、陽光和煦、花朵芬芳,你進入了恍惚的心境。
小說作者使用同樣的手法,將讀者帶入虛構的夢。他用文字描繪出明確的圖像,在讀者的意識裡形成故事的一幕。在催眠過程中,催眠師敘述的小小故事主角是「你」,你就是主角。小說作者可能也用「你」,但更常見的作法是用「我」、「他」或「她」,效果相同。
大部分的小說寫作書會建議作者「展現給讀者看」,而不要「敘述給讀者聽」。以下是「敘述」的例子:「他走進花園,看見庭園美好。」作者在「告訴」你某個情況,而沒有「展現」給你看。「展現」的例子是這樣:「日落時分,他走進寂靜的花園,感覺微風吹拂過冬青樹叢,空氣中有濃郁的茉莉香。」
就如賈德納在《小說的藝術》中說的:「生動的細節是小說的生命之血……。透過細密觀察所做的細節描述,會持續提供讀者憑據……。具體的細節,把我們帶進故事裡,讓我們信以為真。」當作者「展現」給讀者看時,他是在提供感官知覺的細節,藉此把讀者帶入虛構的夢境。相反的,用「敘述」的方式會把讀者推出虛構之夢,因為這種方式會讓讀者有意識地去分析敘述的內容,讀者於是清醒了過來。在這種情況下,讀者是去思考,而不是去體驗。
因此,閱讀小說是在潛意識的層次裡體驗一個夢境,這就是為什麼愛讀小說的人,討厭學者理性地分析文學。本來是要讓你作夢的境地,學者偏要在裡面尋找理性與邏輯。讀《白鯨記》而去分析其意象,就是在清醒的狀態閱讀。但作者要你受到吸引,進入小說的世界,要你搭上漁船,周遊半個世界去尋找大鯨魚,而不是要你困坐斗室,研究他是怎麼寫,或者搜索隱藏的象徵意義,彷彿這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捉迷藏似的。
作者一旦用文字為讀者創造出圖像,下一步就是讓讀者的情緒融入其中。這靠的是取得讀者的同情。
同情
教人寫小說的書,對於同情這件事往往只是一筆帶過。但是,要引領讀者進入你所創造的時空,關鍵就是讓他們對你的筆下人物產生同情。如果你不能引導讀者進入故事裡的時空,你就沒有寫出超棒小說。
「同情心」這個概念常被誤解。有些小說寫作老師立下偽規,說要讓讀者對書中人產生同情,這人必須要令人敬佩。這絕非事實。像是笛福(Defoe)筆下的茉莉.法蘭德絲、狄更斯《孤雛淚》裡的賊窩首領費金、史蒂文生《金銀島》裡的獨腳海盜,大部分讀者都很同情他們,卻絕不敬佩這些傢伙。茉莉說謊、偷竊、浪蕩;費金指使流浪兒童當小偷;獨腳海盜則是個惡棍、騙子兼海盜。
有一部老電影叫做《蠻牛》,講的是中量級拳王拉莫塔的故事。在電影裡這個角色會打老婆,在拳壇嶄露頭角後便與妻離婚。他勾引未成年少女,因偏執妄想而脾氣暴烈,說話還含糊不清。他在擂台場與街頭同樣野蠻殘忍,然而,由勞勃狄尼洛飾演的這個角色,卻贏得觀眾相當多的同情。
這是怎麼做到的?
在電影開始的時候,拉莫塔受盡冷落忽視,生活貧困,觀眾覺得他可憐。關鍵在這裡:要贏得讀者的同情,就要讓讀者覺得這角色可憐。比方說,在雨果所著《悲慘世界》中,尚萬強出場的時候,他風塵僕僕抵達一個小鎮,想進旅店吃飯。他明明有錢,旅店卻拒絕招待,把他餓得頭昏眼花。不管尚萬強是否曾犯下滔天大罪,在那一刻,讀者同情他。
還有一些別的情況,都會自然而然贏得讀者的同情,像是寂寞、無愛、羞辱、窮困、壓抑、尷尬、危險這種種狀況。幾乎所有會帶來主角身體、心理或精神上痛苦的狀態,都能夠贏得讀者的同情。
同情是個門檻,過了這門檻,讀者的情緒就進入故事。沒有同情,讀者對這故事就沒有投入情緒。然而贏得了同情之後,你若要進一步引領讀者進入故事裡的世界,就得讓他認同書中人。
認同
常有人把認同與同情混為一談。同情是讀者覺得角色受苦,讓人不忍。但即使是一個討厭的壞蛋,在臨上絞刑台的那一刻,讀者也會同情他,雖然並不認同他。認同,是讀者不僅同情這角色的苦難,而且還支持他的目標與志向,希望這人能夠如願以償。
以下是是「認同」的範例:
? 在《大白鯊》裡,讀者支持布洛第殺死大白鯊這個目標。
? 在《魔女嘉莉》裡,讀者支持嘉莉參加舞會的渴望,與她反抗暴君母親的意願。
? 在《傲慢與偏見》中,讀者支持伊麗莎白找到愛情與結婚的渴望。
? 在《審判》中,讀者支持K的決心,要掙脫法律的桎梏,獲得自由。
? 在《罪與罰》中,讀者支持拉斯柯尼柯夫脫離貧困的需求。
? 在《亂世佳人》中,讀者支持郝思嘉重整被北軍燒毀的莊園。
你會說,好嘛,可是如果你寫的是一個討厭的惡棍怎麼辦?要怎樣讓讀者認同呢?很簡單。
比方說,你有一個角色關在牢裡。他受到嚴重虐待,獄卒毆打他,別的囚犯痛扁他,他的家人也拋棄他。在這種情況下,就算他像(聖經裡謀殺親兄弟的)該隱一樣有罪,讀者也會憐憫他,所以你贏得了讀者的同情。但是讀者會認同他嗎?
假設他的目標是越獄,但如果他是個冷血殺人犯,讀者不見得會認同這個目標。讀者會希望他關在牢裡,而認同讓他下監服刑的檢察官、法官、陪審團以及獄卒。不過,如果這犯人的目標是改過自新,那讀者就很有可能會認同他。給你的人物一個高貴的目標,讀者就會站在他那邊,不管過去他犯下怎樣的惡行都無妨。
普佐在寫《教父》時遇到的困難是,男主角柯里昂靠放高利貸、收保護費以及賄賂工會維生。他不是那種你會請到家裡喝茶玩牌的人;為了做生意,他還賄賂政客、收買新聞記者、恐嚇義大利裔的小店主,叫他們只准賣他進口的橄欖油。他給的好處讓人難以拒絕,但事實擺在眼前,柯里昂是個一等一的大壞蛋,讀者不可能認同這樣的人。但是普佐要讀者同情並且認同,他還真做到了。幾百萬人讀了他的書,更多的人看了這書改編的電影,他們同情並且認同柯里昂。
普佐是怎麼做到的?他很天才,他讓柯里昂這角色曾遭受不公平對待,而且擁有一個高貴的目標。
普佐在故事開始的時候,並不講柯里昂怎樣欺壓弱勢,那樣的話讀者會討厭他。恰恰相反,他一開始講一個辛苦幹活的殯葬業者,波納賽拉,站在美國法庭上「等待司法正義,讓殘暴侵犯他女兒的兩個人得到報應」。但是法官判這兩個年輕人緩刑,釋放了他們。普佐的敘述者告訴我們:
來美國這麼多年,波納賽拉一直信賴法律與秩序,生意也依法做了起來。而現在他滿懷怨恨,恨不得買槍把這兩個年輕人給斃了。他轉身面對仍然不瞭解怎會如此的老妻,向她解釋說:「他們根本沒把我們放在眼裡。」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下定決心,不再擔心要付出怎樣的代價:「為了討回公道,我們只好跪著去見柯里昂大人。」
很顯然,讀者會同情要為女兒討回公道的波納賽拉。而既然他非得去找柯里昂才能伸張正義,我們的同情就轉移到柯里昂這個能主持公道的人身上。就這樣,普佐在讀者與柯里昂之間牽繫上正面情緒的紐帶,他創造出的情況是,柯里昂要為不幸的波納賽拉父女伸張正義,這目標是讀者可以認同的。
接下來,普佐加強讀者對柯里昂本人的認同。他安排一個外號「土耳其人」的傢伙,來向柯里昂接洽販賣毒品的事。柯里昂基於道德原則拒絕了,讀者於是更加認同柯里昂。普佐賦予柯里昂一種個人的道德標準,促使讀者拋棄原本對這黑社會頭子的厭惡,讀者於是不但不討厭他,反而充分同情,與他站在同一邊,為他的目標吶喊助威。
同理心
讀者雖然會同情一個深感寂寞的人,卻不見得會對他的寂寞感同身受。但是產生同理心之後,讀者會與這個人有相同的感覺。同理心是比同情心強烈得多的情緒。
妻子分娩的時候,有的丈夫也會發生陣痛,這是同理心的一個例子。做丈夫的不僅是同情,他的感受深刻到身體真的產生痛楚。
假設你去參加喪禮,你並不認識死者魏德比,他是你的朋友愛妮的哥哥。你的朋友很悲痛,而你是局外人,只是因為愛妮傷心,你也替她難過。
喪禮還沒開始,你陪愛妮到教堂庭園中走走,她邊走邊告訴你關於她哥哥的事。魏德比本來正在攻讀物理治療的學位,希望將來能幫助殘障兒童走路。他為人幽默,常在朋友聚會時模仿尼克森講話,學得唯妙唯肖。念大學時,有一次有個教授給了他六十分,他氣得把一個派丟在教授臉上。聽起來這傢伙挺有趣的。
隨著愛妮的講述,魏德比好像活生生就在眼前,你漸漸滋生比同情更深的感覺。你漸漸覺得這樣一個聰明、有創意、愛搞怪的人走了,是世界的損失。你開始對你的朋友產生同理心,感受到她的悲痛,這就是同理心的力量。
好,那小說作者要怎樣讓讀者產生同理心呢?
假設你在寫牙醫山姆的故事。山姆好賭,輸給一個幫會老大兩百萬元,這輩子毀了,他一家人都毀了。你要如何才能讓讀者對山姆感同身受?最有可能的情況是讀者覺得他的家人好可憐,而他本人根本該去死一死。
的確不容易,但你還是可以爭取。
方法是利用暗示的力量,使用觸動五官感知的文字、激發情緒的細節,向讀者暗示處在山姆的境地、承受那樣的苦是怎樣的感覺。換言之,你創造出故事的世界,讓讀者可以身歷其境:
一陣冷風吹下大街,潮溼的雪已經開始落下。山姆的腳趾在鞋子裡麻木了,飢餓的感覺又開始啃噬著他。鼻水流出,他用袖子抹掉,管不了好不好看了。
用訴諸感官與觸動情緒的細節,你把讀者帶進山姆的世界,體驗他的處境。你詳細描述環境中的感官細節──景象、聲音、痛苦、氣味等觸發讀者情緒的感覺:
第三天早上,山姆醒來,四下望望。房間四面白牆,窗上掛著白色的窗簾,一台大螢幕電視高高掛在牆上,床單聞起來挺乾淨的,床邊小几上放著花。他摸摸自己的身體。不太有感覺,因為並不冷也不痛,就連肚子,原本痛了很久的,現在也不痛……
這樣訴諸感官、能觸發情緒的細節,透過暗示的力量,會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同理心。
以下是史蒂芬﹒金在《魔女嘉莉》中,一段訴諸感官與觸動情緒的細節描述:
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她〔嘉莉〕在房間裡首次穿上那件禮服。她還買了一件魔術胸罩穿在裡面,把她的胸部托高……。穿上這衣服,她有一種奇怪的、作夢的感覺,半是羞慚,半是頑抗的興奮。
注意看細節(胸罩、托高)與情緒(一種怪怪的、作夢的感覺,半是羞慚,半是頑抗的興奮)牽繫在一起。幾段以後,嘉莉古板的母親打開了房門:
她們互相注視。
下意識裡,嘉莉覺得她的背挺直了,終於直挺挺地站在從窗子透進來的那一塊早春的陽光裡。
背挺直,是頑抗的象徵,是強大的情緒;站在一片陽光裡,是訴諸感官的細節。兩者緊密連繫。
讀者因為嘉莉的母親指控她而感到同情,也認同她去參加舞會的目標;又因為作者用觸動情緒的感官細節創造出真實的感覺,讀者產生了同理心。
以下是取自《大白鯊》的一個例子:
布洛第坐在甲板上固定著的戰鬥椅上,努力保持清醒。他身上又熱又黏,坐著等了六個鐘頭,一直都沒有風。他的頸子後面已經曬傷得很厲害,頭一動,制服襯衫的領子就刮得皮痛。身上的體味蒸騰到臉上,與船上魚內臟和魚血的腐臭氣味攪和在一起,令他頭暈。他覺得被煮熟了。
讀這段文字時,讀者也被穩穩地安在那張戰鬥椅上,感覺到領子刮得脖子痛,陽光灼燙,頭暈想吐,跟布洛第一起處在很不舒服的靜候狀態,等待鯊魚。
卡夫卡也描寫K在類似的處境,等候審判:
一個冬天的早晨,窗外降著雪,天空霧濛灰暗,K坐在辦公室裡,一大早就累極了。為了讓他自己至少不要在屬下面前丟臉,他命令職員不要讓任何人進他辦公室,說是他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但他非但沒忙工作,反而在椅子上歪來扭去,把辦公桌上的各種東西擺擺弄弄,然後,不知不覺地,伸直手臂安放在桌面上,低頭坐著一動也不動。
再一次,重要的是細節:霧濛灰暗的天、在椅子上歪來扭去、伸直手臂安放在桌面上等等。
同情、認同與同理心都會讓讀者與角色之間產生情緒連結。這時候,你就要帶領讀者進入你所創造的時空了。
最後一步:轉移讀者的時空
被順利轉移之後,讀者面臨到的情況就像是一腳跨進書中,真實的世界反而暫時消失無蹤。這是小說作者的目標:把讀者帶到小說的世界,完全被書中人所吸引。
在催眠術裡,這叫做「絕對狀態」。催眠師完全掌控,他要催眠對象學鴨叫,那人就馬上呱呱呱。小說作者把讀者引進絕對狀態時,讀者一會兒哭一會兒笑,感受著書中人物的痛苦,滿腦子書中人的想法,並且參與他的決定。
進入這種狀態的讀者,會深陷其中,你想要引他分神,往往必須搖晃他,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嘿,查理!把書放下!吃晚飯了!喂!你聾了嗎?」
那麼你要怎樣讓讀者從同情、認同與同理心,進展到完全沉浸其中?答案是:內心掙扎。
內心掙扎是人物心中的風暴:懷疑、憂慮、內疚、悔恨、左右為難。讀者一旦對人物抱持同情心,認同並產生同理心,就容易與書中人物感受到同樣的悔恨與內疚,體驗到他們的懷疑與憂慮,而且最重要的是,對於人物不得不作的決定,產生自己的看法。
就是這個參與決定的過程,讓讀者完全沉浸在小說情境中。讀者感受到角色的內疚、懷疑、憂慮和悔恨,想要勸說角色應該這麼做而不要那麼做……
寫小說是種服務業
假如你想在服務業打天下,你得知道客戶為何上門,而你該如何滿足他們的需求。
比方說,如果你經營一間清潔公司,你該知道顧客期待看到光可鑑人的地板,以及閃閃發亮的浴室;如果你是個離婚律師,你得瞭解客戶不只想獲得一大筆贍養費,還會想要讓前妻或前夫嘗到苦頭。小說寫作是一種服務業,在你坐下來寫一本超棒小說之前,得先知道讀者要的是什麼。
如果你寫的是非小說,讀者要什麼,端看你寫的是什麼書。教人致富的勵志書,會有不少章節告訴讀者,要對自己保持信心,堅持奮鬥,準時交稅以避免國稅局找碴等等。性愛指導手冊裡應該要放大量圖片,並且誇稱練習書中扭來扭去的姿勢,將有助心靈成長。而獨裁者穆加比的傳記裡,應該收集且詳述這壞蛋做過的所有醜事,不管重不重要。
就非小說的書籍寫作而言,作者的主要目的在於提供資訊給讀者,你要陳述事實,且針對這些事實,提出見解。
小說不一樣。一般而言,小說作者所陳述的並非事實,當然也談不上針對事實,提出見解。讀者很難從小說裡獲得所謂系統性的知識,因為小說是虛構的、完全出於想像,書中所陳述的事件從來不曾發生,所描寫的人物也從不存在。那麼,稍微有一點腦袋的人為什麼要買這種騙人的東西?
部分原因頗明顯。推理小說的讀者期待在書的開頭陷入迷霧,而在書的結尾對偵探的聰慧感到歎服;歷史小說的讀者期待品嘗曾經有過的輝煌年代京華煙雲;而愛情小說的讀者則想看到大膽的女主角與英俊的男主角,以及很多令人心神蕩漾的戀情場景。
狄佛托(Bernard DeVoto)在《小說世界》(The World of Fiction)中說,人看書是為了「樂趣。……除了專業與半專業人士之外,沒有人會為了其他理由看小說。」
確實,事情就這麼簡單,一般讀者就只為了樂趣而看小說。但為了達到娛樂讀者的效果,作者要做的事卻絕不簡單,因為,你要帶領讀者進入另一個時空。當讀者看書時,如果覺得像是真的活在小說世界裡,真實世界反而消失無蹤,那麼他們就是被帶進另一個時空了。
來到另一個時空的讀者,像是在作著「虛構的夢」。賈德納(John Gardner)在所著《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Fiction)中說:「不管是哪種類型的小說,『虛構的夢』就是小說讓人著迷之處。」
虛構的夢是靠暗示的力量所建構。廣告人、騙子、宣傳家、教士、催眠師,都是用暗示的力量當成主要操作手法,小說家也是。不過,廣告人、騙子、宣傳家和教士,是用暗示的力量來說服別人,而催眠師和小說家則是用它來引導,讓人進入另一個意識狀態。
你會說,哇,這聽起來好神祕!從某個角度來看,確實如此。
催眠師使用暗示的力量,引導被催眠者進入恍惚的情境。催眠師教你坐在椅子上,看著一個發亮的東西,比方一個吊飾,催眠師輕輕晃動那吊飾,抑揚頓挫地說:「你的眼皮很沉重,你覺得愈來愈放鬆,聽著我的聲音,愈來愈放鬆……你的眼睛開始閉起來了,你發現自己在心中的一座樓梯上,你往下走,往下,往下,下到黑暗又安靜的地方,黑暗又安靜……」妙哉,你真的覺得愈來愈放鬆。
催眠師又說:「你看到自己在一座美麗的花園裡,站在步道上,這裡好安靜、好祥和。是慵懶的夏日,太陽出來了,溫暖的微風吹拂,木蘭花盛開……」
催眠師說出的這些詞句,提到的這些東西──花園、步道、木蘭花──會在你的意識裡出現,你感覺到微風吹拂、陽光和煦、花朵芬芳,你進入了恍惚的心境。
小說作者使用同樣的手法,將讀者帶入虛構的夢。他用文字描繪出明確的圖像,在讀者的意識裡形成故事的一幕。在催眠過程中,催眠師敘述的小小故事主角是「你」,你就是主角。小說作者可能也用「你」,但更常見的作法是用「我」、「他」或「她」,效果相同。
大部分的小說寫作書會建議作者「展現給讀者看」,而不要「敘述給讀者聽」。以下是「敘述」的例子:「他走進花園,看見庭園美好。」作者在「告訴」你某個情況,而沒有「展現」給你看。「展現」的例子是這樣:「日落時分,他走進寂靜的花園,感覺微風吹拂過冬青樹叢,空氣中有濃郁的茉莉香。」
就如賈德納在《小說的藝術》中說的:「生動的細節是小說的生命之血……。透過細密觀察所做的細節描述,會持續提供讀者憑據……。具體的細節,把我們帶進故事裡,讓我們信以為真。」當作者「展現」給讀者看時,他是在提供感官知覺的細節,藉此把讀者帶入虛構的夢境。相反的,用「敘述」的方式會把讀者推出虛構之夢,因為這種方式會讓讀者有意識地去分析敘述的內容,讀者於是清醒了過來。在這種情況下,讀者是去思考,而不是去體驗。
因此,閱讀小說是在潛意識的層次裡體驗一個夢境,這就是為什麼愛讀小說的人,討厭學者理性地分析文學。本來是要讓你作夢的境地,學者偏要在裡面尋找理性與邏輯。讀《白鯨記》而去分析其意象,就是在清醒的狀態閱讀。但作者要你受到吸引,進入小說的世界,要你搭上漁船,周遊半個世界去尋找大鯨魚,而不是要你困坐斗室,研究他是怎麼寫,或者搜索隱藏的象徵意義,彷彿這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捉迷藏似的。
作者一旦用文字為讀者創造出圖像,下一步就是讓讀者的情緒融入其中。這靠的是取得讀者的同情。
同情
教人寫小說的書,對於同情這件事往往只是一筆帶過。但是,要引領讀者進入你所創造的時空,關鍵就是讓他們對你的筆下人物產生同情。如果你不能引導讀者進入故事裡的時空,你就沒有寫出超棒小說。
「同情心」這個概念常被誤解。有些小說寫作老師立下偽規,說要讓讀者對書中人產生同情,這人必須要令人敬佩。這絕非事實。像是笛福(Defoe)筆下的茉莉.法蘭德絲、狄更斯《孤雛淚》裡的賊窩首領費金、史蒂文生《金銀島》裡的獨腳海盜,大部分讀者都很同情他們,卻絕不敬佩這些傢伙。茉莉說謊、偷竊、浪蕩;費金指使流浪兒童當小偷;獨腳海盜則是個惡棍、騙子兼海盜。
有一部老電影叫做《蠻牛》,講的是中量級拳王拉莫塔的故事。在電影裡這個角色會打老婆,在拳壇嶄露頭角後便與妻離婚。他勾引未成年少女,因偏執妄想而脾氣暴烈,說話還含糊不清。他在擂台場與街頭同樣野蠻殘忍,然而,由勞勃狄尼洛飾演的這個角色,卻贏得觀眾相當多的同情。
這是怎麼做到的?
在電影開始的時候,拉莫塔受盡冷落忽視,生活貧困,觀眾覺得他可憐。關鍵在這裡:要贏得讀者的同情,就要讓讀者覺得這角色可憐。比方說,在雨果所著《悲慘世界》中,尚萬強出場的時候,他風塵僕僕抵達一個小鎮,想進旅店吃飯。他明明有錢,旅店卻拒絕招待,把他餓得頭昏眼花。不管尚萬強是否曾犯下滔天大罪,在那一刻,讀者同情他。
還有一些別的情況,都會自然而然贏得讀者的同情,像是寂寞、無愛、羞辱、窮困、壓抑、尷尬、危險這種種狀況。幾乎所有會帶來主角身體、心理或精神上痛苦的狀態,都能夠贏得讀者的同情。
同情是個門檻,過了這門檻,讀者的情緒就進入故事。沒有同情,讀者對這故事就沒有投入情緒。然而贏得了同情之後,你若要進一步引領讀者進入故事裡的世界,就得讓他認同書中人。
認同
常有人把認同與同情混為一談。同情是讀者覺得角色受苦,讓人不忍。但即使是一個討厭的壞蛋,在臨上絞刑台的那一刻,讀者也會同情他,雖然並不認同他。認同,是讀者不僅同情這角色的苦難,而且還支持他的目標與志向,希望這人能夠如願以償。
以下是是「認同」的範例:
? 在《大白鯊》裡,讀者支持布洛第殺死大白鯊這個目標。
? 在《魔女嘉莉》裡,讀者支持嘉莉參加舞會的渴望,與她反抗暴君母親的意願。
? 在《傲慢與偏見》中,讀者支持伊麗莎白找到愛情與結婚的渴望。
? 在《審判》中,讀者支持K的決心,要掙脫法律的桎梏,獲得自由。
? 在《罪與罰》中,讀者支持拉斯柯尼柯夫脫離貧困的需求。
? 在《亂世佳人》中,讀者支持郝思嘉重整被北軍燒毀的莊園。
你會說,好嘛,可是如果你寫的是一個討厭的惡棍怎麼辦?要怎樣讓讀者認同呢?很簡單。
比方說,你有一個角色關在牢裡。他受到嚴重虐待,獄卒毆打他,別的囚犯痛扁他,他的家人也拋棄他。在這種情況下,就算他像(聖經裡謀殺親兄弟的)該隱一樣有罪,讀者也會憐憫他,所以你贏得了讀者的同情。但是讀者會認同他嗎?
假設他的目標是越獄,但如果他是個冷血殺人犯,讀者不見得會認同這個目標。讀者會希望他關在牢裡,而認同讓他下監服刑的檢察官、法官、陪審團以及獄卒。不過,如果這犯人的目標是改過自新,那讀者就很有可能會認同他。給你的人物一個高貴的目標,讀者就會站在他那邊,不管過去他犯下怎樣的惡行都無妨。
普佐在寫《教父》時遇到的困難是,男主角柯里昂靠放高利貸、收保護費以及賄賂工會維生。他不是那種你會請到家裡喝茶玩牌的人;為了做生意,他還賄賂政客、收買新聞記者、恐嚇義大利裔的小店主,叫他們只准賣他進口的橄欖油。他給的好處讓人難以拒絕,但事實擺在眼前,柯里昂是個一等一的大壞蛋,讀者不可能認同這樣的人。但是普佐要讀者同情並且認同,他還真做到了。幾百萬人讀了他的書,更多的人看了這書改編的電影,他們同情並且認同柯里昂。
普佐是怎麼做到的?他很天才,他讓柯里昂這角色曾遭受不公平對待,而且擁有一個高貴的目標。
普佐在故事開始的時候,並不講柯里昂怎樣欺壓弱勢,那樣的話讀者會討厭他。恰恰相反,他一開始講一個辛苦幹活的殯葬業者,波納賽拉,站在美國法庭上「等待司法正義,讓殘暴侵犯他女兒的兩個人得到報應」。但是法官判這兩個年輕人緩刑,釋放了他們。普佐的敘述者告訴我們:
來美國這麼多年,波納賽拉一直信賴法律與秩序,生意也依法做了起來。而現在他滿懷怨恨,恨不得買槍把這兩個年輕人給斃了。他轉身面對仍然不瞭解怎會如此的老妻,向她解釋說:「他們根本沒把我們放在眼裡。」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下定決心,不再擔心要付出怎樣的代價:「為了討回公道,我們只好跪著去見柯里昂大人。」
很顯然,讀者會同情要為女兒討回公道的波納賽拉。而既然他非得去找柯里昂才能伸張正義,我們的同情就轉移到柯里昂這個能主持公道的人身上。就這樣,普佐在讀者與柯里昂之間牽繫上正面情緒的紐帶,他創造出的情況是,柯里昂要為不幸的波納賽拉父女伸張正義,這目標是讀者可以認同的。
接下來,普佐加強讀者對柯里昂本人的認同。他安排一個外號「土耳其人」的傢伙,來向柯里昂接洽販賣毒品的事。柯里昂基於道德原則拒絕了,讀者於是更加認同柯里昂。普佐賦予柯里昂一種個人的道德標準,促使讀者拋棄原本對這黑社會頭子的厭惡,讀者於是不但不討厭他,反而充分同情,與他站在同一邊,為他的目標吶喊助威。
同理心
讀者雖然會同情一個深感寂寞的人,卻不見得會對他的寂寞感同身受。但是產生同理心之後,讀者會與這個人有相同的感覺。同理心是比同情心強烈得多的情緒。
妻子分娩的時候,有的丈夫也會發生陣痛,這是同理心的一個例子。做丈夫的不僅是同情,他的感受深刻到身體真的產生痛楚。
假設你去參加喪禮,你並不認識死者魏德比,他是你的朋友愛妮的哥哥。你的朋友很悲痛,而你是局外人,只是因為愛妮傷心,你也替她難過。
喪禮還沒開始,你陪愛妮到教堂庭園中走走,她邊走邊告訴你關於她哥哥的事。魏德比本來正在攻讀物理治療的學位,希望將來能幫助殘障兒童走路。他為人幽默,常在朋友聚會時模仿尼克森講話,學得唯妙唯肖。念大學時,有一次有個教授給了他六十分,他氣得把一個派丟在教授臉上。聽起來這傢伙挺有趣的。
隨著愛妮的講述,魏德比好像活生生就在眼前,你漸漸滋生比同情更深的感覺。你漸漸覺得這樣一個聰明、有創意、愛搞怪的人走了,是世界的損失。你開始對你的朋友產生同理心,感受到她的悲痛,這就是同理心的力量。
好,那小說作者要怎樣讓讀者產生同理心呢?
假設你在寫牙醫山姆的故事。山姆好賭,輸給一個幫會老大兩百萬元,這輩子毀了,他一家人都毀了。你要如何才能讓讀者對山姆感同身受?最有可能的情況是讀者覺得他的家人好可憐,而他本人根本該去死一死。
的確不容易,但你還是可以爭取。
方法是利用暗示的力量,使用觸動五官感知的文字、激發情緒的細節,向讀者暗示處在山姆的境地、承受那樣的苦是怎樣的感覺。換言之,你創造出故事的世界,讓讀者可以身歷其境:
一陣冷風吹下大街,潮溼的雪已經開始落下。山姆的腳趾在鞋子裡麻木了,飢餓的感覺又開始啃噬著他。鼻水流出,他用袖子抹掉,管不了好不好看了。
用訴諸感官與觸動情緒的細節,你把讀者帶進山姆的世界,體驗他的處境。你詳細描述環境中的感官細節──景象、聲音、痛苦、氣味等觸發讀者情緒的感覺:
第三天早上,山姆醒來,四下望望。房間四面白牆,窗上掛著白色的窗簾,一台大螢幕電視高高掛在牆上,床單聞起來挺乾淨的,床邊小几上放著花。他摸摸自己的身體。不太有感覺,因為並不冷也不痛,就連肚子,原本痛了很久的,現在也不痛……
這樣訴諸感官、能觸發情緒的細節,透過暗示的力量,會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同理心。
以下是史蒂芬﹒金在《魔女嘉莉》中,一段訴諸感官與觸動情緒的細節描述:
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她〔嘉莉〕在房間裡首次穿上那件禮服。她還買了一件魔術胸罩穿在裡面,把她的胸部托高……。穿上這衣服,她有一種奇怪的、作夢的感覺,半是羞慚,半是頑抗的興奮。
注意看細節(胸罩、托高)與情緒(一種怪怪的、作夢的感覺,半是羞慚,半是頑抗的興奮)牽繫在一起。幾段以後,嘉莉古板的母親打開了房門:
她們互相注視。
下意識裡,嘉莉覺得她的背挺直了,終於直挺挺地站在從窗子透進來的那一塊早春的陽光裡。
背挺直,是頑抗的象徵,是強大的情緒;站在一片陽光裡,是訴諸感官的細節。兩者緊密連繫。
讀者因為嘉莉的母親指控她而感到同情,也認同她去參加舞會的目標;又因為作者用觸動情緒的感官細節創造出真實的感覺,讀者產生了同理心。
以下是取自《大白鯊》的一個例子:
布洛第坐在甲板上固定著的戰鬥椅上,努力保持清醒。他身上又熱又黏,坐著等了六個鐘頭,一直都沒有風。他的頸子後面已經曬傷得很厲害,頭一動,制服襯衫的領子就刮得皮痛。身上的體味蒸騰到臉上,與船上魚內臟和魚血的腐臭氣味攪和在一起,令他頭暈。他覺得被煮熟了。
讀這段文字時,讀者也被穩穩地安在那張戰鬥椅上,感覺到領子刮得脖子痛,陽光灼燙,頭暈想吐,跟布洛第一起處在很不舒服的靜候狀態,等待鯊魚。
卡夫卡也描寫K在類似的處境,等候審判:
一個冬天的早晨,窗外降著雪,天空霧濛灰暗,K坐在辦公室裡,一大早就累極了。為了讓他自己至少不要在屬下面前丟臉,他命令職員不要讓任何人進他辦公室,說是他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但他非但沒忙工作,反而在椅子上歪來扭去,把辦公桌上的各種東西擺擺弄弄,然後,不知不覺地,伸直手臂安放在桌面上,低頭坐著一動也不動。
再一次,重要的是細節:霧濛灰暗的天、在椅子上歪來扭去、伸直手臂安放在桌面上等等。
同情、認同與同理心都會讓讀者與角色之間產生情緒連結。這時候,你就要帶領讀者進入你所創造的時空了。
最後一步:轉移讀者的時空
被順利轉移之後,讀者面臨到的情況就像是一腳跨進書中,真實的世界反而暫時消失無蹤。這是小說作者的目標:把讀者帶到小說的世界,完全被書中人所吸引。
在催眠術裡,這叫做「絕對狀態」。催眠師完全掌控,他要催眠對象學鴨叫,那人就馬上呱呱呱。小說作者把讀者引進絕對狀態時,讀者一會兒哭一會兒笑,感受著書中人物的痛苦,滿腦子書中人的想法,並且參與他的決定。
進入這種狀態的讀者,會深陷其中,你想要引他分神,往往必須搖晃他,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嘿,查理!把書放下!吃晚飯了!喂!你聾了嗎?」
那麼你要怎樣讓讀者從同情、認同與同理心,進展到完全沉浸其中?答案是:內心掙扎。
內心掙扎是人物心中的風暴:懷疑、憂慮、內疚、悔恨、左右為難。讀者一旦對人物抱持同情心,認同並產生同理心,就容易與書中人物感受到同樣的悔恨與內疚,體驗到他們的懷疑與憂慮,而且最重要的是,對於人物不得不作的決定,產生自己的看法。
就是這個參與決定的過程,讓讀者完全沉浸在小說情境中。讀者感受到角色的內疚、懷疑、憂慮和悔恨,想要勸說角色應該這麼做而不要那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