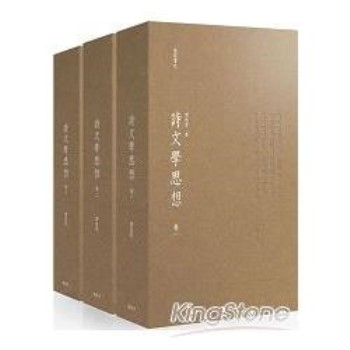論詩學
本章為對詩學總體論述嘗試。我們先從西方詩學說起。
一、西方詩學回顧一:古典詩學
在美學與詩學兩者間,西方始於詩學而非美學,原因有二:一、自然界之美因順承人本性而明顯,幾近無可討論或解釋。相反,作品之美並不顯然,有待探討與解釋,此美學始於詩學之原因。二、美學作為感性之學,必須有待主體性甚至感性有被建立後始能深入;西方早期多為客體存有論,非主體哲學,故鮮有對美學作為門類討論。
作品問題主要有兩類:一為其構造、構成問題,二更基本,為作品之價值問題。作品之價值與意義問題至為基本,亦一切詩學及美學之根本。我們的討論即參照這一問題進行。
首先仍需從柏拉圖開始。柏拉圖著名詩學論,為對一切詩作品劃分為形式(lexis)與內容(logos)兩方面。因一切詩作品對柏拉圖甚至希臘言均為敘述(récit),為一種表象模式,故其形式主要有三種可能:或為直述(純敘述diègèsis)、或為摹倣(mimèsis)、或為兩者之混合。柏拉圖只肯定直述一模式,而否定另外兩者。在這表象模式三分中,柏拉圖舉以下文體(genre)為例:直述式如酒神頌(dithyrambe)、摹倣式如悲劇及喜劇,而混合式如荷馬史詩。酒神頌今已不存在,內容無從考究,從記錄觀應為對酒神之歌頌。
柏拉圖詩論引發出大問題,是因後來亞里士多德著名《詩學》沒有跟隨這劃分法,而柏拉圖這一劃分法其真正意義亦不為人所知;西方詩學史之後只單純跟隨亞里士多德,沒有再理會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詩學之修改或改變,正在把三種表象模式全收攝在「摹倣」一模式下,因而使一切詩敘述性表象直等同摹倣。無論此時敘述是虛構抑真實,一切作品對亞里士多德言均為摹倣(=表象),這是作品唯一之方式。亞里士多德把柏拉圖三分完全內化於摹倣(表象)一模式下表示:一切作品只從其表象性界定,直述抑戲劇只其模式而已。這一轉變結果嚴重。
首先,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最大差異在是否接納敘述為根本獨立模式,抑只從屬摹倣下。柏拉圖之視敘述為獨立,正因對柏拉圖言唯敘述一模式為真實,摹倣非是。亞里士多德之做法,明顯為反對柏拉圖如此詩學。但若撇開反對不談,柏拉圖劃分法之所以能為亞里士多德所取代,確因在敘述一模式下,柏拉圖所舉例子為酒神頌,而酒神頌因其對象性,縱然非如戲劇般摹倣,然始終仍是表象;因而當亞里士多德把摹倣意思擴大等同表象時,自然可把敘述亦收攝於摹倣下,一切形式始終只是對象性而已,因而為表象,亦為摹倣。
柏拉圖以敘述而不以摹倣為詩文學之本,其洞見本深刻,唯錯誤以酒神頌為例而已。讓我們先從結論說起:
敘述這一模式,實等同「詩言志」中「言」一模態,而這是一切詩學甚至作品創制應視為根本的。柏拉圖之錯誤只因不從「志」言,而舉酒神頌為例。本來舉酒神頌為例仍可,因假若把酒神頌對等《詩》之「頌」,這仍是「言志」;唯若被歌頌者本身為神人二分下之神靈,始使「言志」成份不見,故為亞里士多德視同「表象」:一種基於對象而有之作品,與「志」無關,因而亦無須保留敘述或「言」為獨立模式,致使詩學及一切作品創制均為表象或摹倣,表象亦為詩唯一模式。若明白這點,我們便可看到,中西方詩學之全部差異與關鍵,就源於此而已:中國以「言志」為詩之本,而自亞里士多德詩學,詩全為摹倣或表象。
若我們跳躍至西方浪漫主義詩學,浪漫主義詩學把詩文體三分為悲劇、史詩與歌詩(lyrique)。當代詩學家Gérard Genette指出,無論是柏拉圖抑亞里士多德,從沒有提及歌詩,更沒有把歌詩視為文體模式。希臘時期詩學如柏、亞二人那樣,從不以歌詩為真正作品,不以歌詩為詩,因而從不對歌詩予以討論。亞里士多德《詩學》(或詩)所排掉的,除沒有節奏、旋律、語句構造之散文外,即為歌詩。原因明顯在:歌詩非表象或摹倣故。如是我們可清楚看到,西方在浪漫主義出現前之古典詩學,在亞里士多德影響下,對表象作為詩或作品之根本模式,多麼地看重。
如Genette指出,歌詩之被接受為詩學文體,歷史漫長。在十六、十七世紀前,歌詩都被混同種種非表象性形式;而構成大文體,只有悲劇、史詩甚至喜劇,無歌詩在內。直至1559年意大利Minturno於其De Poeta中,始有把詩分為場景、歌詩及史詩三者。Cervantes後來分為四:史詩、歌詩、悲劇、喜劇。至英國Milton(1644)始有史詩、戲劇、歌詩三分。又如Baumgarten(1735)在其Esthétique有曾提及歌詩、史詩、戲劇及其細分這樣分類,但因從無理論基礎與說明,故這樣劃分法始終無代表性,歌詩始終被視為只是對想法之虛構(fabula構造)。至1746年Batteux始試圖對亞里士多德摹倣論與歌詩兩者在理論上作協調:一如戲劇與史詩中人物均有其感情甚至激情,詩人若有對自身感情之抒發,也應視作對情感之摹倣;在情節進行或行動中即為戲劇與史詩,而在行動中止後,單純對心靈感受之描繪則為歌詩;歌詩因而並沒有違背摹倣這一原則。 如是而歌詩一文體只作為對情感感受之摹倣而呈現或被接納,只是對象內容不同,非形式或手法不同。
於此我們始明白,之所以柏拉圖必須區分敘述與摹倣,及二人之忽略歌詩,其關鍵在詩人是否能直述自身這一事情上:柏拉圖以直述為對神靈讚美故以直述模式為至真,摹倣因非以神靈為對象故必然偽;亞里士多德則以摹倣為表象客觀對象時唯一之方式,縱使虛構仍有其對象真實性在,非如直述自身情感之歌詩,其內容因只為人主觀感受故無真理性;二人始終以對象之客觀真實性甚至真理性為詩唯一可有之依據。
西方這古典詩學既對人心志所有之人性與真實完全否認,始有以詩為外在真實或事實之摹倣。因而全部西方古典詩學之所由起,正為對「詩言志」之否定與對立;其關鍵全在人心是否能有真實,或人自身是否能有真實性而已。
當亞里士多德以摹倣為對「在行動中人」之摹倣,我們不應誤會以為此已涉及人而再非是神靈,並非如此。所謂「在行動中之人」,其關鍵在行動而非人,因而為戲劇(drama)。這行動所對反的,實為「志」或「心」;而其背後所關涉的,只為人之欲望及其想法、智力等之錯誤,始終非人性或其心志之真實。在對人行動作表象時,所表象者均為人之錯誤與過失,只如此錯誤有大小之分而已,一為悲劇,另一為喜劇。正因是對如此重大至為悲劇錯誤之表象,故其中所言之人,乃顯要個體;其作為個體,又為自身性格(èthè)與想法(dianoia)所左右,行動之全部錯誤由此而生。詩學所對之對象,如是由向內而言之人心轉移至向外有所欲求而行動時之個體,以此個體之事實為真實。作為行動,其情節或故事(mythos)必須虛構或構造;正是如此虛構或構造,構成亞里士多德《詩學》之本。於此我們始明白西方詩學其源起之究竟。
本章為對詩學總體論述嘗試。我們先從西方詩學說起。
一、西方詩學回顧一:古典詩學
在美學與詩學兩者間,西方始於詩學而非美學,原因有二:一、自然界之美因順承人本性而明顯,幾近無可討論或解釋。相反,作品之美並不顯然,有待探討與解釋,此美學始於詩學之原因。二、美學作為感性之學,必須有待主體性甚至感性有被建立後始能深入;西方早期多為客體存有論,非主體哲學,故鮮有對美學作為門類討論。
作品問題主要有兩類:一為其構造、構成問題,二更基本,為作品之價值問題。作品之價值與意義問題至為基本,亦一切詩學及美學之根本。我們的討論即參照這一問題進行。
首先仍需從柏拉圖開始。柏拉圖著名詩學論,為對一切詩作品劃分為形式(lexis)與內容(logos)兩方面。因一切詩作品對柏拉圖甚至希臘言均為敘述(récit),為一種表象模式,故其形式主要有三種可能:或為直述(純敘述diègèsis)、或為摹倣(mimèsis)、或為兩者之混合。柏拉圖只肯定直述一模式,而否定另外兩者。在這表象模式三分中,柏拉圖舉以下文體(genre)為例:直述式如酒神頌(dithyrambe)、摹倣式如悲劇及喜劇,而混合式如荷馬史詩。酒神頌今已不存在,內容無從考究,從記錄觀應為對酒神之歌頌。
柏拉圖詩論引發出大問題,是因後來亞里士多德著名《詩學》沒有跟隨這劃分法,而柏拉圖這一劃分法其真正意義亦不為人所知;西方詩學史之後只單純跟隨亞里士多德,沒有再理會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詩學之修改或改變,正在把三種表象模式全收攝在「摹倣」一模式下,因而使一切詩敘述性表象直等同摹倣。無論此時敘述是虛構抑真實,一切作品對亞里士多德言均為摹倣(=表象),這是作品唯一之方式。亞里士多德把柏拉圖三分完全內化於摹倣(表象)一模式下表示:一切作品只從其表象性界定,直述抑戲劇只其模式而已。這一轉變結果嚴重。
首先,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最大差異在是否接納敘述為根本獨立模式,抑只從屬摹倣下。柏拉圖之視敘述為獨立,正因對柏拉圖言唯敘述一模式為真實,摹倣非是。亞里士多德之做法,明顯為反對柏拉圖如此詩學。但若撇開反對不談,柏拉圖劃分法之所以能為亞里士多德所取代,確因在敘述一模式下,柏拉圖所舉例子為酒神頌,而酒神頌因其對象性,縱然非如戲劇般摹倣,然始終仍是表象;因而當亞里士多德把摹倣意思擴大等同表象時,自然可把敘述亦收攝於摹倣下,一切形式始終只是對象性而已,因而為表象,亦為摹倣。
柏拉圖以敘述而不以摹倣為詩文學之本,其洞見本深刻,唯錯誤以酒神頌為例而已。讓我們先從結論說起:
敘述這一模式,實等同「詩言志」中「言」一模態,而這是一切詩學甚至作品創制應視為根本的。柏拉圖之錯誤只因不從「志」言,而舉酒神頌為例。本來舉酒神頌為例仍可,因假若把酒神頌對等《詩》之「頌」,這仍是「言志」;唯若被歌頌者本身為神人二分下之神靈,始使「言志」成份不見,故為亞里士多德視同「表象」:一種基於對象而有之作品,與「志」無關,因而亦無須保留敘述或「言」為獨立模式,致使詩學及一切作品創制均為表象或摹倣,表象亦為詩唯一模式。若明白這點,我們便可看到,中西方詩學之全部差異與關鍵,就源於此而已:中國以「言志」為詩之本,而自亞里士多德詩學,詩全為摹倣或表象。
若我們跳躍至西方浪漫主義詩學,浪漫主義詩學把詩文體三分為悲劇、史詩與歌詩(lyrique)。當代詩學家Gérard Genette指出,無論是柏拉圖抑亞里士多德,從沒有提及歌詩,更沒有把歌詩視為文體模式。希臘時期詩學如柏、亞二人那樣,從不以歌詩為真正作品,不以歌詩為詩,因而從不對歌詩予以討論。亞里士多德《詩學》(或詩)所排掉的,除沒有節奏、旋律、語句構造之散文外,即為歌詩。原因明顯在:歌詩非表象或摹倣故。如是我們可清楚看到,西方在浪漫主義出現前之古典詩學,在亞里士多德影響下,對表象作為詩或作品之根本模式,多麼地看重。
如Genette指出,歌詩之被接受為詩學文體,歷史漫長。在十六、十七世紀前,歌詩都被混同種種非表象性形式;而構成大文體,只有悲劇、史詩甚至喜劇,無歌詩在內。直至1559年意大利Minturno於其De Poeta中,始有把詩分為場景、歌詩及史詩三者。Cervantes後來分為四:史詩、歌詩、悲劇、喜劇。至英國Milton(1644)始有史詩、戲劇、歌詩三分。又如Baumgarten(1735)在其Esthétique有曾提及歌詩、史詩、戲劇及其細分這樣分類,但因從無理論基礎與說明,故這樣劃分法始終無代表性,歌詩始終被視為只是對想法之虛構(fabula構造)。至1746年Batteux始試圖對亞里士多德摹倣論與歌詩兩者在理論上作協調:一如戲劇與史詩中人物均有其感情甚至激情,詩人若有對自身感情之抒發,也應視作對情感之摹倣;在情節進行或行動中即為戲劇與史詩,而在行動中止後,單純對心靈感受之描繪則為歌詩;歌詩因而並沒有違背摹倣這一原則。 如是而歌詩一文體只作為對情感感受之摹倣而呈現或被接納,只是對象內容不同,非形式或手法不同。
於此我們始明白,之所以柏拉圖必須區分敘述與摹倣,及二人之忽略歌詩,其關鍵在詩人是否能直述自身這一事情上:柏拉圖以直述為對神靈讚美故以直述模式為至真,摹倣因非以神靈為對象故必然偽;亞里士多德則以摹倣為表象客觀對象時唯一之方式,縱使虛構仍有其對象真實性在,非如直述自身情感之歌詩,其內容因只為人主觀感受故無真理性;二人始終以對象之客觀真實性甚至真理性為詩唯一可有之依據。
西方這古典詩學既對人心志所有之人性與真實完全否認,始有以詩為外在真實或事實之摹倣。因而全部西方古典詩學之所由起,正為對「詩言志」之否定與對立;其關鍵全在人心是否能有真實,或人自身是否能有真實性而已。
當亞里士多德以摹倣為對「在行動中人」之摹倣,我們不應誤會以為此已涉及人而再非是神靈,並非如此。所謂「在行動中之人」,其關鍵在行動而非人,因而為戲劇(drama)。這行動所對反的,實為「志」或「心」;而其背後所關涉的,只為人之欲望及其想法、智力等之錯誤,始終非人性或其心志之真實。在對人行動作表象時,所表象者均為人之錯誤與過失,只如此錯誤有大小之分而已,一為悲劇,另一為喜劇。正因是對如此重大至為悲劇錯誤之表象,故其中所言之人,乃顯要個體;其作為個體,又為自身性格(èthè)與想法(dianoia)所左右,行動之全部錯誤由此而生。詩學所對之對象,如是由向內而言之人心轉移至向外有所欲求而行動時之個體,以此個體之事實為真實。作為行動,其情節或故事(mythos)必須虛構或構造;正是如此虛構或構造,構成亞里士多德《詩學》之本。於此我們始明白西方詩學其源起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