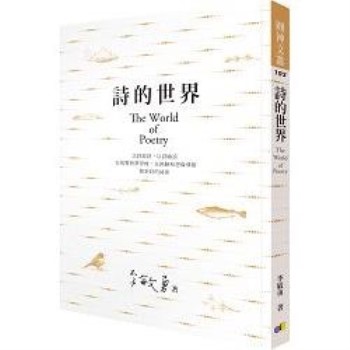第一堂課
使思想像薔薇一樣芬芳
薔薇的世界,是詩的國度。
英語詩人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有一句話形容詩,說「詩是使思想像薔薇一樣芬芳的事物」。這句話,恰當精要地描述了詩的質地和形貌。思想,或說精神、意涵是詩的核心,而薔薇的形式和香味是詩的形貌。既說了精神,也說了造型。 詩是一種語言的藝術形式。語言的藝術,可以用文學來概括。在文體上,詩在韻文的時代和散文相區分;但在文類上,詩,與小說、散文、評論、戲劇等有所差別。面對文本時,詩儘管已脫離韻文的形態,仍然可以和其他文類區別出來。因為詩,常以分行形式斷句。雖然,也有所謂的散文詩,但篇幅較小。它和散文、小說的分別,在形式上仍可捉摸。 但是,詩脫離韻文的規範之後,受限於文化保守主義的禁錮和限制,許多國度的閱讀者仍然無法接受,或以輕忽輕鄙的態度面對。這或許是某種面對自由的不知適從的文化惰性。 如果,喜歡文學,但又無法進入已經自由化的詩,就如同喜歡科學而不知數學一樣。因為詩之於文學,就像數學之於科學。
詩是什麼?T.S.艾略特這位原為美國籍,後來歸化為英國籍,留下許多經典作品,並於一九四八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以一句話留下詩意的答覆。這樣的答覆,應該留在許多愛詩人的腦海。 詩人以詩喻詩,有許多例子。
〈薔薇〉李敏勇 作
薔薇的世界
是詩的國度
薔薇有女神的面頰
女神的思想
我把薔薇獻給你
黑暗的世界
爆開一朵花的光輝
我把薔薇枯萎
愛的生命
熄滅成一堆灰燼的陰暗
沒有薔薇的世界
是生活的國度
以薔薇的國度和生活的國度相對比,意味著詩的國度和生活的國度對比。藝術性和日常性,或說非日常性與日常性,在這首〈薔薇〉的行句,用了「女神的面頰」和「女神的思想」來形容詩。這裡的面頰,就像T.S.艾略特的描述,是使思想芬芳出來的薔薇。
詩人擁有在行句裡的某種話語權。「把薔薇獻給你╲黑暗的世界╲爆開一朵花的光輝」和「我把薔薇枯萎╲愛的生命╲熄滅成一堆灰燼的陰暗」,讓人想起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Mishima Yukio, 1925-1970)一個自敘短篇,說他小時候瘦弱、耽讀童話,把精裝本童話堆疊成城堡,拉下燈泡;打開燈光時像太陽光亮起,捻熄燈光,像關上太陽光,有某種宰制的力量。這樣的觀念論,也是語言的一種力量。〈薔薇〉是在描繪詩。
〈詩〉李敏勇 作
世界的峰頂
飄揚著我的憧憬
世界的窪地
埋設著我的鄉愁
遼敻的空間
張架著我的語言
綿遠的時間
流動著我的思想
腐敗的土壤
孕育著我的生
燦爛的花容
潛伏著我的死
發表了〈薔薇〉這首詩,是一九七一年的事,那時候,我也發表了〈詩〉。這兩首詩都是以詩喻詩,是我的告白。在〈詩〉的行句,我用「峰頂」相對「窪地」,「空間」相對「時間」,「土壤」相對「花容」;並以「憧憬」和「鄉愁」,「語言」和「思想」,「生」和「死」呼應,可以說是對詩之為詩,做了較為深沉的探視。這是我在自己詩人之途對詩是什麼的鏡照。那時候,我已讀到日本詩人田村隆一(Tamura Ryūichi,1923-1998)所說的「如果你成了醫生、軍人、詩人這三種人之一,就會體認到人類悲慘的根源。」他是經歷太平洋戰爭,面對戰敗廢墟的日本詩人。 「生命的感覺和涵養是詩人的條件。」這句話是英語詩人W.H.奧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在他未完成的「詩人學校」夢想裡提到的。詩是從生命的感覺和涵養孕育出來的。W.H.奧登原為英國人,後來歸化美國籍,恰與T.S.艾略特相反。無論是哪一種語言,詩的形式論和內容(精神)論,都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形塑。詩是什麼?詩人們常常以詩自況,以詩回答探詢。
來看看保羅.克利(Paul Klee, 1879-1940),他是一位著名的畫家,也是個詩人。因為畫名遠比詩名為人所知,常常只被認為是一位畫家。
〈詩〉(瑞士)保羅.克利 作李敏勇 譯
我全身甲冑站著
我不在這兒
我站在深處
我站在遠方
站在非常遠的遠方……
我放出死亡的光輝
保羅.克利的這首詩,以「深處」「遠方」「非常遠的遠方」來描述詩的存在。「全身甲冑」一如武士的裝備,是說自己詩的本質在行句形式緊緊保護之中,「不在這兒」又喻示著非日常、反日常。他用了深,以及遠的語字,來表述自己探觸之境。而末尾的「我放出死亡的光輝」有讓人寒顫的感覺。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藝術的現代主義發展中的時代,保羅.克利的詩是他的畫的另一種語言形式。
再來看看一位出身德國,於二戰後到美國留學,並留在美國的大學教授德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詩人艾斯納(Richard Exner, 1929-2008)的詩。
〈詩〉(德國╲美國)艾斯納 作杜國清 譯
字句
襲擊你如群狼
因此你伸出雙手作為犧牲
以保全身體。
詩行
像你脖子上的繩索
像你鼠蹊間的拳頭。
停頓 窒息你。
艾斯納像保羅.克利一樣,使用德語。二戰時期的納粹時代,對這位詩人有相當的影響。他的許多詩,探討並反省了納粹德國的罪行。並曾獲奧地利柯寧格詩獎—紀念一九四二年在維也納被納粹迫害而下落不明的詩人Koenig,每五年頒給一位以德語寫詩的詩人。 艾斯納這首〈詩〉強調了詩精鍊字句的力量。他的詩觀,對於語言形式有深刻的體認,對行句有著詩性的堅持。像群狼襲擊,是何等力量!面對等待,閱讀以雙手作為犧牲,又何等慎重!詩的行句力量能重擊一個人的身體,應該是說心!在他的描繪中,詩的行句像繩索套在閱讀者脖子,像拳頭在閱讀者鼠蹊部。畢竟是一位對納粹暴行有深刻經歷的詩人,證之他的詩,也確實如此!面對這樣強而有力的詩,讓人不得不停頓下來。詩的力量彷彿能夠窒息一個人。
二戰時,東歐諸國大多淪陷在納粹德國的占領下,詩人常常是抵抗運動分子、共產黨人。但二戰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化並未帶來自由化,許多知識分子文化人出走、流亡。留在自己國度的詩人,也經歷另一種紅色極權的宰制,他們在詩裡抵抗。巴茲謝克(Atoinin Bartusek, 1921-1974)的詩留下許多沉默抵抗的證言。
〈詩〉(捷克)巴茲謝克 作李敏勇 譯
告知我,昨夜到今晨
在這個海灘上
直以滲透了睡眠的全透明水液
拖曳我到底部的是什麼?
語言的魚群懶洋洋地漂游過我身
尋覓一處水面以便躍出 吐一吐空氣,
偽裝成像是為了一個小蠕動
以便能夠飛躍。
皮膚的表層下是黑暗的,
生命在那兒腐朽;
其上,規列的銀鱗之光半是美麗草地,半是緘默的魚。
巴茲謝克的〈詩〉以魚群比喻詩的語言,「尋覓著一處水面以便躍出╲吐一吐空氣╲偽裝成像是為了一個小躍動╲以便能夠飛躍」,描述詩人如何在不自由的國度,以語言的各種隱喻條件,去完成見證的使命。巴茲謝克像許多捷克的詩人,或波蘭的詩人、匈牙利、羅馬尼亞、前南斯拉夫的詩人、波羅的海三小國的詩人一樣,利用詩能夠藏有祕密的特性,為東歐留下詩的光榮。
詩能極大,也能至小;詩能深刻,也能天真。
〈詩是什麼?〉(日本)大岡信 作李敏勇 譯
詩不是
孩子的遊戲
但詩人
是孩子
「詩不是╲孩子的遊戲╲但詩人╲是孩子」日本詩人大岡信(Ōoka Makoto, 1931-)的悖論與反差,讓人莞薾。詩不是童騃的產品,但詩人是有孩童赤子之心的人。
〈詩〉(美國)瑪麗安.摩爾 作李敏勇 譯 我,也,不喜歡它。 讀著它,無論如何,帶著對它的完全輕蔑, 但畢竟,有人在詩裡 發現,那是一個存有真摰之所。 瑪麗安.摩爾(Marianne Moore, 1887-1972)用反面手法指出,詩存有真摰。儘管「我」也不喜歡它。這個詩裡面的「我」是詩人對詩不見得都受人喜歡的一種巧妙辯證。就像大岡信的四行短詩一樣,會讓人眼睛一亮。 我對於詩是什麼,寫了許多詩,進行我的辯證。 …… 詩 其實是 自己面對自己的備忘錄 每一本詩集 都是自白書 向歷史告解 …… ─〈自白書〉 一首詩應該是: 一個許諾 黑暗中晃動的燈光 寒風裡 霧夜中 航行船隻的汽笛聲 為相遇的旅人響起 …… ─〈備忘錄〉 在我的詩人之路,我逡巡意義的視野,探觸並見證時代光影。我也觀照世界其他國度的詩人,看世界的詩人怎樣以詩探觸,並為他的時代作見證。詩,使思想像薔薇一樣芬芳。它不只是思想,它要能夠發出芬芳。
使思想像薔薇一樣芬芳
薔薇的世界,是詩的國度。
英語詩人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有一句話形容詩,說「詩是使思想像薔薇一樣芬芳的事物」。這句話,恰當精要地描述了詩的質地和形貌。思想,或說精神、意涵是詩的核心,而薔薇的形式和香味是詩的形貌。既說了精神,也說了造型。 詩是一種語言的藝術形式。語言的藝術,可以用文學來概括。在文體上,詩在韻文的時代和散文相區分;但在文類上,詩,與小說、散文、評論、戲劇等有所差別。面對文本時,詩儘管已脫離韻文的形態,仍然可以和其他文類區別出來。因為詩,常以分行形式斷句。雖然,也有所謂的散文詩,但篇幅較小。它和散文、小說的分別,在形式上仍可捉摸。 但是,詩脫離韻文的規範之後,受限於文化保守主義的禁錮和限制,許多國度的閱讀者仍然無法接受,或以輕忽輕鄙的態度面對。這或許是某種面對自由的不知適從的文化惰性。 如果,喜歡文學,但又無法進入已經自由化的詩,就如同喜歡科學而不知數學一樣。因為詩之於文學,就像數學之於科學。
詩是什麼?T.S.艾略特這位原為美國籍,後來歸化為英國籍,留下許多經典作品,並於一九四八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以一句話留下詩意的答覆。這樣的答覆,應該留在許多愛詩人的腦海。 詩人以詩喻詩,有許多例子。
〈薔薇〉李敏勇 作
薔薇的世界
是詩的國度
薔薇有女神的面頰
女神的思想
我把薔薇獻給你
黑暗的世界
爆開一朵花的光輝
我把薔薇枯萎
愛的生命
熄滅成一堆灰燼的陰暗
沒有薔薇的世界
是生活的國度
以薔薇的國度和生活的國度相對比,意味著詩的國度和生活的國度對比。藝術性和日常性,或說非日常性與日常性,在這首〈薔薇〉的行句,用了「女神的面頰」和「女神的思想」來形容詩。這裡的面頰,就像T.S.艾略特的描述,是使思想芬芳出來的薔薇。
詩人擁有在行句裡的某種話語權。「把薔薇獻給你╲黑暗的世界╲爆開一朵花的光輝」和「我把薔薇枯萎╲愛的生命╲熄滅成一堆灰燼的陰暗」,讓人想起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Mishima Yukio, 1925-1970)一個自敘短篇,說他小時候瘦弱、耽讀童話,把精裝本童話堆疊成城堡,拉下燈泡;打開燈光時像太陽光亮起,捻熄燈光,像關上太陽光,有某種宰制的力量。這樣的觀念論,也是語言的一種力量。〈薔薇〉是在描繪詩。
〈詩〉李敏勇 作
世界的峰頂
飄揚著我的憧憬
世界的窪地
埋設著我的鄉愁
遼敻的空間
張架著我的語言
綿遠的時間
流動著我的思想
腐敗的土壤
孕育著我的生
燦爛的花容
潛伏著我的死
發表了〈薔薇〉這首詩,是一九七一年的事,那時候,我也發表了〈詩〉。這兩首詩都是以詩喻詩,是我的告白。在〈詩〉的行句,我用「峰頂」相對「窪地」,「空間」相對「時間」,「土壤」相對「花容」;並以「憧憬」和「鄉愁」,「語言」和「思想」,「生」和「死」呼應,可以說是對詩之為詩,做了較為深沉的探視。這是我在自己詩人之途對詩是什麼的鏡照。那時候,我已讀到日本詩人田村隆一(Tamura Ryūichi,1923-1998)所說的「如果你成了醫生、軍人、詩人這三種人之一,就會體認到人類悲慘的根源。」他是經歷太平洋戰爭,面對戰敗廢墟的日本詩人。 「生命的感覺和涵養是詩人的條件。」這句話是英語詩人W.H.奧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在他未完成的「詩人學校」夢想裡提到的。詩是從生命的感覺和涵養孕育出來的。W.H.奧登原為英國人,後來歸化美國籍,恰與T.S.艾略特相反。無論是哪一種語言,詩的形式論和內容(精神)論,都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形塑。詩是什麼?詩人們常常以詩自況,以詩回答探詢。
來看看保羅.克利(Paul Klee, 1879-1940),他是一位著名的畫家,也是個詩人。因為畫名遠比詩名為人所知,常常只被認為是一位畫家。
〈詩〉(瑞士)保羅.克利 作李敏勇 譯
我全身甲冑站著
我不在這兒
我站在深處
我站在遠方
站在非常遠的遠方……
我放出死亡的光輝
保羅.克利的這首詩,以「深處」「遠方」「非常遠的遠方」來描述詩的存在。「全身甲冑」一如武士的裝備,是說自己詩的本質在行句形式緊緊保護之中,「不在這兒」又喻示著非日常、反日常。他用了深,以及遠的語字,來表述自己探觸之境。而末尾的「我放出死亡的光輝」有讓人寒顫的感覺。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藝術的現代主義發展中的時代,保羅.克利的詩是他的畫的另一種語言形式。
再來看看一位出身德國,於二戰後到美國留學,並留在美國的大學教授德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詩人艾斯納(Richard Exner, 1929-2008)的詩。
〈詩〉(德國╲美國)艾斯納 作杜國清 譯
字句
襲擊你如群狼
因此你伸出雙手作為犧牲
以保全身體。
詩行
像你脖子上的繩索
像你鼠蹊間的拳頭。
停頓 窒息你。
艾斯納像保羅.克利一樣,使用德語。二戰時期的納粹時代,對這位詩人有相當的影響。他的許多詩,探討並反省了納粹德國的罪行。並曾獲奧地利柯寧格詩獎—紀念一九四二年在維也納被納粹迫害而下落不明的詩人Koenig,每五年頒給一位以德語寫詩的詩人。 艾斯納這首〈詩〉強調了詩精鍊字句的力量。他的詩觀,對於語言形式有深刻的體認,對行句有著詩性的堅持。像群狼襲擊,是何等力量!面對等待,閱讀以雙手作為犧牲,又何等慎重!詩的行句力量能重擊一個人的身體,應該是說心!在他的描繪中,詩的行句像繩索套在閱讀者脖子,像拳頭在閱讀者鼠蹊部。畢竟是一位對納粹暴行有深刻經歷的詩人,證之他的詩,也確實如此!面對這樣強而有力的詩,讓人不得不停頓下來。詩的力量彷彿能夠窒息一個人。
二戰時,東歐諸國大多淪陷在納粹德國的占領下,詩人常常是抵抗運動分子、共產黨人。但二戰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化並未帶來自由化,許多知識分子文化人出走、流亡。留在自己國度的詩人,也經歷另一種紅色極權的宰制,他們在詩裡抵抗。巴茲謝克(Atoinin Bartusek, 1921-1974)的詩留下許多沉默抵抗的證言。
〈詩〉(捷克)巴茲謝克 作李敏勇 譯
告知我,昨夜到今晨
在這個海灘上
直以滲透了睡眠的全透明水液
拖曳我到底部的是什麼?
語言的魚群懶洋洋地漂游過我身
尋覓一處水面以便躍出 吐一吐空氣,
偽裝成像是為了一個小蠕動
以便能夠飛躍。
皮膚的表層下是黑暗的,
生命在那兒腐朽;
其上,規列的銀鱗之光半是美麗草地,半是緘默的魚。
巴茲謝克的〈詩〉以魚群比喻詩的語言,「尋覓著一處水面以便躍出╲吐一吐空氣╲偽裝成像是為了一個小躍動╲以便能夠飛躍」,描述詩人如何在不自由的國度,以語言的各種隱喻條件,去完成見證的使命。巴茲謝克像許多捷克的詩人,或波蘭的詩人、匈牙利、羅馬尼亞、前南斯拉夫的詩人、波羅的海三小國的詩人一樣,利用詩能夠藏有祕密的特性,為東歐留下詩的光榮。
詩能極大,也能至小;詩能深刻,也能天真。
〈詩是什麼?〉(日本)大岡信 作李敏勇 譯
詩不是
孩子的遊戲
但詩人
是孩子
「詩不是╲孩子的遊戲╲但詩人╲是孩子」日本詩人大岡信(Ōoka Makoto, 1931-)的悖論與反差,讓人莞薾。詩不是童騃的產品,但詩人是有孩童赤子之心的人。
〈詩〉(美國)瑪麗安.摩爾 作李敏勇 譯 我,也,不喜歡它。 讀著它,無論如何,帶著對它的完全輕蔑, 但畢竟,有人在詩裡 發現,那是一個存有真摰之所。 瑪麗安.摩爾(Marianne Moore, 1887-1972)用反面手法指出,詩存有真摰。儘管「我」也不喜歡它。這個詩裡面的「我」是詩人對詩不見得都受人喜歡的一種巧妙辯證。就像大岡信的四行短詩一樣,會讓人眼睛一亮。 我對於詩是什麼,寫了許多詩,進行我的辯證。 …… 詩 其實是 自己面對自己的備忘錄 每一本詩集 都是自白書 向歷史告解 …… ─〈自白書〉 一首詩應該是: 一個許諾 黑暗中晃動的燈光 寒風裡 霧夜中 航行船隻的汽笛聲 為相遇的旅人響起 …… ─〈備忘錄〉 在我的詩人之路,我逡巡意義的視野,探觸並見證時代光影。我也觀照世界其他國度的詩人,看世界的詩人怎樣以詩探觸,並為他的時代作見證。詩,使思想像薔薇一樣芬芳。它不只是思想,它要能夠發出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