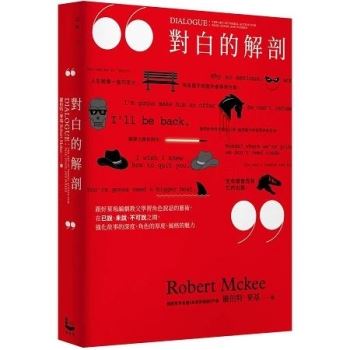表達(三):技巧
語言比喻
文學可用的比喻手法,例如隱喻(metaphor)、直喻(simile)、借代(synecdoche)、轉喻(metonymy),再到頭韻(alliteration)、諧音(assonance)、逆喻(oxymoron)、擬人(personification)等等,名目繁多。語言能耍的手法、能玩的花樣真要細數道來,可以有好幾百種。這些遣辭用字的法門,不僅為說出來的話語增添華采,也帶出引申義,和話語之下沒說出來、不能說出來的潛文本共鳴共振。
舉例來看,田納西.威廉斯寫的舞台劇《慾望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白蘭琪.杜布瓦(Blanche DuBois)這位美國南方的遲暮佳麗,脆弱到一摧即折,正處於精神、情感崩潰的邊緣。她在第六景見到了米契(Mitch)。他是個寂寞、敏感的勞工階級單身漢,還必須照顧病重垂死的母親。一天晚上,兩人約會過後,相互傾訴各自過往的人生際遇;他們的運途南轅北轍,卻同樣寫滿了痛苦。兩人相互傾心,終於帶出下面這一刻:
米契:(慢慢把白蘭琪擁進懷裡)妳的人生需要有個伴。我的人生也需要有個伴。我的伴會不會是妳呢,白蘭琪?
白蘭琪瞅著他看了好一會兒,眼神一片空白,然後鳴咽一聲,依偎在他的懷裡。她輕聲啜泣,想擠出話來。米契吻上她的額頭,然後是她的眼睛,最後是她的唇。波卡舞曲飄得愈來愈遠。白蘭琪深吸一口氣,送出長長的一聲聲啜泣,透著感激。
白蘭琪:有時——真的有神啊——這麼快呢。45
最後一句只用了五個英文字,就匯聚出澎湃洶湧的意義和感情。「真的有神啊」幾個字,不是拿米契去比擬神祇,而是在說白蘭琪有如得救上天堂一般喜難自勝。不過,我們也猜想這應該不是她第一次領受這樣的神恩。
「有時」、「這麼快」幾個字則暗示白蘭琪以前便曾多次蒙男士拯救,只是那些突如其來拯救了她的男士,想必也突如其來拋棄了她,否則她不會還耗在這裡,不會依然被孤單逼得飛蛾撲火,再次緊緊攀附著陌生人不放。不過寥寥幾個字,觀眾馬上就看出當中隱含的行為模式:白蘭琪在男性面前始終以受害者的姿態去激發他們內心的白馬王子現身。他們拯救了她,但之後又拋棄了她,原因就有待我們去挖掘了。而這一次,她遇到的米契,可會不同於以往?
田納西.威廉斯祭出比喻,勾得人耳朵一豎,就把白蘭琪人生的悲涼調性提點出來,同時在觀眾腦中勾起疑問,心頭不禁一震。
作者遣辭用字寫出來的對白,光譜的一頭是傳達心靈、精神性意義,另一頭則是情慾經驗的描寫,形色不一而足。例如角色說起歌手的嗓音如何,可以拿「lousy」(長蟲)或是「sour」(臭酸)來形容。這兩個詞都說得通,但「長蟲」算是「死比喻」(dead metaphor)46了,原先的意思是「爬滿臭蟲」。「臭酸」倒還有生趣,觀眾一聽到,嘴角大概就翹起來了。下面兩句台詞,以哪一句更能撩撥觀者的感覺?「她走路像模特兒在走台步」,還是「她走起路來像一曲輕緩、挑情的歌」?同樣的意思,寫成對白可以有千萬種花樣,不過,大體上是以愈偏向感官知覺的修辭,效果愈見深刻,愈發教人難忘。【 】
修辭只在用上的那一句裡發揮作用,但由於對白能將一段又一段充斥衝突的話語帶出戲劇效果,時機和時間差的技巧也就可以加進來施展手腳:連珠砲的快節奏對上沉默無聲的停頓,一洩千里的連綴句對上斷斷續續的零碎字,妙答對上強辯,文謅謅的陽春白雪對上沒文法的下里巴人,單音節對上多音節,斯文有禮對上汙言穢語,逼真對上詩意,輕描淡寫對上誇大其詞,這類文體學和文字遊戲的例子多到不可勝數。不論人生唱得出來多少支曲子,對白一概有能耐跟著起舞。
我已經強調過好幾次,作者創作的天地無限寬廣,這裡也還要再重提一次。我再三重複這點,是希望作者可以確實明瞭:形式不會限制表達力,反而會激發表達力。這本書談的是撐起對白的形式,但絕對不會歸納寫對白的公式。有選擇才有創造。周邊語言
演員一出現在觀眾面前,全身上下無不透著形形色色的周邊語言,但凡與字詞無關的細微聲調變化和肢體動作,都會強化字詞傳達出來的意義和感覺——例如臉部表情、手勢、姿態、語速、音高、音量、節奏、音調、重音,甚至人際距離,也就是角色之間的站位,也是有作用的。演員傳遞的周邊語言,講的是「姿態對白」(gesticulate dialogue)。觀眾的眼睛抓到這些微表情(microexpression),頂多只需要四分之一秒。【 】但是在書頁上,周邊語言就需要借助語言比喻來加強描寫了。
下述例子摘錄自〈一九九五年八月的鐵路事故〉(Railroad Incident, August 1995)。這是大衛.閔茲所寫的短篇小說,描寫四個流浪漢晚上圍坐在篝火旁,忽然看到一個半裸男子從暗處冒了出來。
他們看出原來是個男子,一身步入中年的鬆軟,走路微瘸,但還是透著些許尊貴、拘謹的痕跡,抬腳的樣子好像高價鞋還穿在腳上,仍帶著份量;不過,說不定他們根本沒看出這些事,一直到他走到他們身邊、開口講話;他張開嘴說話,輕輕一聲你們好,母音拉得比較開,嘴型像是珍貴的貝殼……【 】
(大衛.閔茲喜歡寫短篇小說,我猜正是因為他舞文弄墨的絕招路數太多,要講上好幾百篇故事才有辦法盡數施展。)
混搭手法
小說能用的手法可以擇一施展,也可以混合並用。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在《一場美國夢》(An American Dream)下面這一段對話中,就把直接對白、第一人稱直接敘述、周邊語言,不論直義或是比喻,直接綰合為一:
「妳想離婚。」我說。
「是吧我看。」
「就這樣要離?」
「不是就這樣,親愛的,而是這麼多這樣。」她打了個呵欠,姿勢很漂亮,一時間看來有點像個十五歲的愛爾蘭小女僕。「你今天沒來跟狄兒黛樂說再見……」
「我又不知道她要走了。」
「你當然不知道。你怎麼會知道?你有兩個禮拜沒打電話過來了。成天只知道找你那些小姑娘又親又咬的。」她不知道那時候我一個小姑娘也沒有。
「她們現在沒那麼小了。」怒火開始在我身上延燒,這時候已經燒到心窩,燒得我覺得肺好像乾得像枯葉,心臟蓄積的壓力大概都要爆炸了。
「妳那蘭姆酒給我一口。」我說。47【 】
這裡簡單提一下不同媒介的改編問題:若是想把文學作品改編為電影,要注意長、短篇小說家多半把最高妙的語言留給主述去講,而不是戲劇場景中的對白——正如上述梅勒的手法。
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會遇上不小的扞格,原因在哪裡一目瞭然:攝影機拍不出心思。文思細密的敘述性故事,其內心對白沒辦法往旁邊橫移一步,就從書頁搬上銀幕。所以,改編一定要再作改寫,一定要從裡到外把故事重新再想像過一遍,將小說的敘事對白改頭換面為影視的戲劇對白才行。這絕非易事。台詞句式
台詞句式是以關鍵字為樞紐,因此必須找出對一句台詞意思最要緊的那一個字或詞。作者可以把關鍵字放在句頭、句尾或是句中,依據其選擇寫出下述三種基本的對白句式:懸疑、累進、平衡。
懸疑句(The Suspense Sentence)
勾起好奇心就會驅動求知欲——這是我們拆解謎團、尋找答案的知性需求。帶起同理心就會牽動連繫感——這是我們將心比心、求他人福祉的感性需求。生命的理智面和情緒面兩方合一,就會產生懸疑。而懸疑也可以歸納為一句話,那就是:好奇心被注入同理心。
懸疑之所以抓得住讀者/觀眾,在於下述這些帶著情感的疑問有如排山倒海灌進讀者/觀眾的腦中,勾住他們的注意力不放:「接下來會出什麼狀況?」「這樣子之後會怎樣?」「那主角會怎麼做?他有什麼感覺?」因而有所謂的「劇情重大疑點」(major dramatic question, MDQ)懸浮在上空,牢牢將故事從頭到尾罩在下方:「後來會怎樣?」這些疑問緊緊揪住人心,教人渾然忘了時間。隨著劇情推向高潮,懸疑愈來愈濃,最終會來到此去無回的轉捩當口,重大疑點跟著水落石出,接著就是劇終。
好奇加上關心,推送出貫串故事的懸疑弧線,但若是我們深入放大去看,會看出探究的心思其實瀰漫在故事的每一環節當中,不論輕重。每一景/場(scene)都找得到它飽含懸疑的轉捩點,當中的每一段話從第一句到最後一句,都要抓得住觀眾的注意力;連最小的單位,對白裡的一句台詞,都不脫小小的懸疑。故事要講得精采絕倫,就要一景接著一景、一段對話接著一段對話、一句台詞接著一句台詞,無不在將觀眾的理性、感性牢牢抓住入戲,片刻不會鬆脫。讀者一刻也不會停下,觀眾一刻也不會分心。
而要讓大家的眼睛定在書頁上、將大家的耳朵定在舞台和銀幕上,最重要的法寶就是掉尾句。所謂「掉尾句」,是把核心意思壓到句子的尾巴才說出來。把修飾語或次要的意思往前挪,主要的意思壓到最後,這樣的掉尾句便能拖住人的興趣不放。
舉例來看:「既然不讓我做,幹嘛又給我那個________ ?」這樣一句台詞填入下面哪一個字詞,可以帶出明確的意思?「眼色」?「槍」?「吻」?「點頭」?「相片」?「錢」?「報告」?「微笑」?「電子郵件」?「聖代」?只要是名詞,幾乎全都可以帶出明確的意思。掉尾句的句式不開門見山就把意思講得清楚明白,而是吊著讀者/觀眾的胃口,非得要從第一個字聽到最後一個字才能搞清楚,這樣就能帶起疑竇。
換句話說,掉尾句就是懸疑句。
例如下述雅思敏娜.黑薩寫的舞台劇《都是Art惹的禍》(Art, 1994)的開場;英譯出自克里斯多福.漢普頓(Christopher Hampton, 1946~)。我在每一句意思裡的關鍵字上頭加黑點標示出來。
馬克(Marc),一個人在台上。
馬克:我朋友塞哲(Serge)買了幅畫。油畫,五呎乘四呎大小;白色的。背景全白。你要是瞇起眼用力看,大概就看得出上面有幾條細細的白色斜線。
塞哲是我老朋友裡的老朋友,奮鬥有成,在當皮膚科醫生,十分醉心於藝術。
我禮拜一時去看了這幅畫。其實塞哲禮拜六才剛拿到手。但他垂涎很久了,有好幾個月吧,這幅白底上有白線的畫。
塞哲的家。
白底的油畫上有細細的白色斜痕,用畫架擺立在地板上。塞哲盯著他的畫,十分興奮。馬克細心端詳畫作。塞哲轉向馬克看著他看畫。
長長一陣靜默。兩人都沒出聲,無聲的情緒暗潮洶湧。
馬克:很貴?
塞哲:二十萬。
馬克:二十萬?
塞哲:尚.德洛尼(Jean Delauney)願意出二十二萬從我手裡搶過去。
馬克:那是誰?
塞哲:你是指德洛尼?
馬克:從沒聽過。
塞哲:德洛尼欸!德洛尼藝廊啊!
馬克:那個德洛尼藝廊願意出二十二萬來跟你搶?
塞哲:不是,不是藝廊,是他。德洛尼本人。他自己要收藏。
馬克:那為什麼德洛尼沒買?
塞哲:賣給私人客戶更重要啊。這叫市場流通。
馬克:嗯,嗯……
塞哲:怎樣?(馬克沒吭聲)你沒站對地方。要從這角度看。看到那些線條沒有?
馬克:這人……叫什麼……?
塞哲:畫家啊?安屈奧(Antrios)。
馬克:很出名?
塞哲:非常、非常出名。
(停頓)
馬克:塞哲,你該不會真的拿二十萬法郎買了這幅畫吧?
塞哲:欸,你不懂,就是這價碼。安屈奧嘛。
馬克:你真的拿二十萬法郎買這幅畫?
塞哲:早該想到你會抓錯重點。
馬克:你花二十萬法郎買這鬼東西?
塞哲,像是單獨一人在場。
塞哲:我這朋友馬克人是相當聰明的,我一直很珍惜兩人的友誼,他的工作不錯,在當航空工程師,但他是那種所謂「新式」的知識份子,不光是現代主義的天敵,好像還拿糟蹋現代主義來自鳴得意,真搞不懂……48【 】
這兩段自言自語的敘述對白,以及夾在中間的戲劇對白場景,總計表達出四十五點意思,當中有四十點是以懸疑句的構造出現。即使有地方簡單提了一下周邊語言(馬克和塞哲非語言的面部表情),還是一樣是把重點壓到末尾「無聲的情緒」這裡。
懸疑句不僅是戲劇力最強的句式,喜劇效果也最大。口頭講的笑話幾乎全都是拿懸疑句收尾打出笑點,驀然斬斷堆疊的張力、帶出笑聲。
黑薩和漢普頓都把關鍵字壓到最後,既帶得句子活潑生動,也牢牢抓住了觀眾的注意力,將衝擊的火力集中在最後一句爆發,而且往往還是喜趣的一擊。累進句
累進這手法的歷史有多悠久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早在兩千三百年前就在提倡這樣的手法。在他的《修辭學》(On Rhetoric)第三卷第九章中,便針對組織緊密的掉尾懸疑句,相較於組織鬆散、自由推進的累進句,二者有何差別進行探討。這兩種句式正好相反,互成鏡像:懸疑式組織把次要的字詞往前放,把核心的字詞往後推;累進式構造則把核心的字詞往前放,再依序排放次要的字詞來推展或修飾句義的重點。
這裡就來看看某乙對白的台詞句式:
某甲:還記得傑克嗎?
某乙:(點頭)那時候,白煙在他頭頂上繚繞,像怒氣的光暈,菸屁股掛在嘴邊都要燒到嘴唇了,除了使勁地在拖備胎,嘴裡還要罵千斤頂,手忙腳亂在換爆掉的輪胎……
(神情有一點落寞)
某乙:……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
我們若是把句式反過來,將上述懸疑句變成累進句:
某甲:還記得傑克嗎?
某乙:(神情有一點落寞)上次就是最後一次,他手忙腳亂在換輪胎,嘴裡要罵千斤頂,手上還要拖備胎,菸屁股叨在嘴邊都要燒到嘴唇了,白煙繚繞在他頭頂上,像怒氣的光暈。
雖然隨意推展的累進句式,戲劇力比起懸疑句可能較為薄弱,卻不算草率隨便。只要技巧高明,累進句勾畫出來的是漸次疊加、愈趨細膩的主題圖像,像滾雪球一樣,賦予對白像口語對話一樣的順勢自然,由字詞推展出宜人的節奏。
懸疑的句式是有不少優點,但也不乏缺點。首先,由於意思的重點一直往後推,要壓到結尾,可能給人矯揉造作的感覺。再者,懸疑要是拖得長一點,讀者/觀眾可能要被迫記住許多句義的枝節,捱到最後才有辦法把複雜的句義完全統合起來。若不懂得拿捏分寸、適可而止,懸疑句也會和寫得不好的累進句一樣累贅鬆垮。
懸疑句式和累進句式分別落在相對的兩端:一邊是把核心字句放在開頭,另一邊是拉到結尾,二者之間還有形形色色的無數變體。
例如「排比句式」(Parallel design)就是把長度、意思、句式差不多的句子連結起來,製造對比和強調,例如:
當我踏入那間教會,也踏入新的人生。平衡句式
把核心字詞放在句子中間,次要句子分別夾在頭尾兩端,就叫做平衡句式(Balanced Sentence):
傑克的性愛、賭博成癮的問題已經夠危險了,我覺得這傢伙絕對有刺激上癮症,要是再把他玩攀岩、高空跳傘算進來的話,
懸疑句不論是串接或排比,都是對白當中驅迫力、戲劇力最強大的句式。所以,想要製造緊張、強調、繁縟、笑聲的時候,就可以把核心字詞壓後。但反過來,累進句式和平衡句式便是最貼近言談、最自然流暢的句式。不過,過猶不及,任何技巧用得太多都會變得像壁紙圖案一樣單調,像機器人一樣僵硬。所以,對白在傳達角色確實活在這一刻、說了什麼之餘,要再推動觀眾入戲、蓄積張力,就必須結合幾種句式並用才行。
混合句式(Mixed Designs)
《無間警探》(True Detective)第一季第三集,主人翁之一,羅斯汀.柯爾(Rustin Cohle),對另兩位警探吉爾博(Gilbough)和帕帕尼亞(Papania)講述他的世界觀。我同樣在句子裡的核心字詞上頭加黑點標示出來。請注意,這裡的核心字詞都放在句子中段的位置。(DB是警方用語,意指死屍〔dead body〕)
羅斯汀.柯爾
這個……這個就是我在說的。我說的就是這個,當我在說時間、死亡,還有轉眼成空的時候。好吧,這裡面是有更大的概念在攪和,主要是我們這整個社會是造了什麼孽,搞得我們都有一樣的幻覺。整整十四小時盯著DB看,就會讓你開始想這些事。你們這樣子做過沒?你盯著他們的眼睛看,就算是照片也一樣,是死是活都不重要,這樣你就看得出來他們的心思。你們知道你會看到什麼嗎?他們樂得這樣子就好……當然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可是……到了最後一刻,就是這樣。絕對是解脫,不會錯。懂嗎?因為他們原本都很害怕,但到了這時候,他們終於明白原來是這麼簡單,只要……撒手就好。對,他們看清楚了,到了最後那十億分之一秒的那一刻,他們看清楚了……自己到底是什麼。你,你自己,人生這一整場大戲,從頭到尾不過是一堆自以為是、愚蠢的意志什麼的,東拼西湊出來的東西,扔了也罷。到最後終於搞懂,你根本就不用抓得這麼緊。終於搞清楚你這一生,你愛的那些,恨的那些,記得的那些,痛苦的那些,全都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全都不過是同樣的一場夢,你在一間上鎖的房間裡作的一場夢,你以為自己身而為人的一場夢。而且就跟許多的夢一樣,到最後都會出現一個惡魔。49
羅斯汀這一段總共表達了二十多點意思,其中有十二點用的是懸疑句,剩下的就是平衡、排比、累進的句式混合著用。結果就是這麼長的一段話,既吊住觀眾的興趣、堆疊起觀眾的興趣,也酬答了觀眾的興趣,同時有如自然流露的心聲,近乎恍惚神遊。請注意這一部影集的主創(creator)兼編劇尼克.皮佐拉圖(Nic Pizzolatto, 1975~),還為羅斯汀這段長長的話加上一個隱喻作壓軸:人生如夢。就像樂曲的裝飾音為樂段添加華采,修辭的手法一樣能為懸疑句添加撥動心弦的裝飾。精簡
意味深長的對白,最後一個重要條件便是精簡——意思是言簡意賅,用最少的字講出最豐富的意思。但凡寫得好的作品,尤其是對白,都符合小威廉.史壯克(William Strunk Jr, 1869~1946)和E. B.懷特(E. B. White, 1899~1985)兩人在《文體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當中提出來的「精簡」原則:「鏗鏘有力的文筆率皆簡潔精鍊。句子不應該有非必要的字詞,段落不應該有非必要的句子,這道理一如繪畫不應該有非必要的線條,機器不應該有非必要的零件。這不是要求句句簡短,也不是要求細節一概刪除只描述梗概,而是要求作者字字句句一定要言之有物。」【 】
不是空洞,而是精簡。
「非屬必要就刪」,就成了史壯克和懷特兩人論寫作的金科玉律。各位就為自己行行好,把這幾個字貼在電腦螢幕上面,乖乖照做。全天下沒有什麼話,不管多長多短,值得讀者/觀眾多費力氣去吸收一個不必要的字。廢話只會惹人討厭。刪!
(蘇菲亞.柯波拉執導的《愛情,不用翻譯》,對白就將精簡原則發揮得盡善盡美。參見第十八章的討論)
停頓
停頓放在你來我往的對話當中,用途不少。已經走到轉捩點卻遲疑一下不講話,會拉高讀者/觀眾心頭的緊張,一個個屏氣凝神等著看接下來的發展,也強調出事態有多嚴峻。但要是過了轉捩點才停頓,則能夠讓讀者/觀眾稍稍緩一口氣,消化一下陡然一變的狀況,領會一下變化後的情勢。
停頓出現在危機之前,會卡住情緒的流洩。寫得好的場景會帶動讀者/觀眾的好奇和關心往天翻地覆的那一刻流過去。讀者/觀眾會問自己:「接下來會怎樣?變成那樣的話,女主角該怎麼辦?情況又會變成怎樣?」如此的推動力蓄積得愈來愈高,驟然被停頓壓住,會將力量壓縮起來,等到轉捩點一轉過去,備受壓制的能量就會一口氣爆發,帶動場景衝到高潮的那一拍。
然而,若是濫用停頓——和對話一樣——原本近悅遠來,也會磨損成令大家退避三舍。其他技巧都要運用的精簡原則,在停頓這個技巧一樣重要。對白要是一停、再停、又停,以示強調、強調、再強調,到後來等於什麼都沒強調了。就像「狼來了」一樣,手法玩得愈浮濫,效果就愈少。等到作者寫到某一場景真的需要把手法的效力發揮到淋漓盡致時,就會發覺先前用得太多,把機鋒都磨鈍了。
所以,停頓要安排在哪裡才好,也要小心拿捏。情節推展的節奏不該磨蹭就要勇往直前,這樣一來,真的到了踩煞車時,定住不動的那一刻才抓得到注意力。愛停就停,不是白吃的午餐;只要一停,都要付出代價。沉默
文字簡約、步調敏捷,意義內隱多於外顯——這樣的對白會吊得讀者/觀眾迫不及待往下看;但若是文字冗贅,步調拖沓,意義外顯多於內隱,可就在對讀者/觀眾大澆冷水了。囉囉囌囌的對白,宛如老牛拖破車,只會逼得讀的人以走馬看花為宜,看的人以充耳不聞為要。所以,一如悲哀的場景常常需要喜趣來作調劑,話太多的時候就要懂得閉嘴。
不過,怎樣叫做「太多」,倒是每一則故事、每一幕場景都有不同,斷難定於一尊,端視個人的品味和判斷來作決定。要是覺得你寫的話比演的戲還多,那就換檔,改以眼睛為寫作的目標而非耳朵,以畫面取代言語。
各位不妨拿以下的問題來考自己:這一幕要是我全以影像來寫,將角色該做的事、故事該有的情節,一概寫成用畫面表現而不加一句對白,那麼應該怎麼做?下面這兩種做法可以擇一用來發揮畫面的威力:
一,周邊語言。姿態和臉部表情,嚴格來說不算語言,卻可以將字詞的言外之意和言下之意說得淋漓盡致。所以,與其要角色張嘴說「對/不對」、「我同意/我不同意」、「我覺得你是對的/我覺得你錯了」這樣的肯定句、否定句來打亂場景,還不如用點頭示意、眼神一掃、伸手比劃來把戲撐起來。
這一點對於寫電視、電影劇本尤其重要。只要做得到,就要在字裡行間留下餘地讓演員去發揮創意。由於攝影機可以把人臉放大好幾倍,心思和情緒會像在眼睛深處、在皮膚底下湧動如海面的波濤。角色不發一語,就是在邀請攝影機靠近深入。好好運用它。
二,肢體動作。只要有機會就問自己以下的問題:我這個角色在這裡的行動和反應,若不用口語,是否有肢體動作可以表達?發揮想像力去勾畫文字畫面,不要「光說不練」。
例如英格瑪.柏格曼某部電影裡的一幕場景。它的片名取得也很巧,就叫做《沉默》(The Silence, 1963)。片中有一名女子在旅館的餐廳裡任由自己讓侍者勾引。這樣的戲該怎麼寫呢?
侍者是不是遞菜單給女子,一一唸出當日的特餐?他會向女子推薦自己最喜歡的菜色嗎?或是讚美女子的衣著品味?他有沒有問女子是否在旅館過夜?是遠行嗎?是否問女子對該地熟不熟悉?隨口提起他再過一小時就下班了,可以當嚮導帶女子四處看看?唉,都是在講話、講話、講話!
柏格曼的處理手法如下:侍者不管有心還是無意,掉了一條餐巾在女子座椅旁邊的地板上。他慢慢彎下腰去撿餐巾,順便一路又吸又聞,從女子的頭頂往下到腿間再到腳邊。女子作出反應,深吸一口氣,帶著喜悅長歎一聲。之後,柏格曼把鏡頭切換到旅館房間,女子和侍者在床上激情交纏。侍者和女子兩人在餐廳那一場勾引戲,散發強烈的情慾,純屬影像,只用肢體,不發一語,再由女子發出那一聲吸氣與長歎,帶到轉捩點。
沉默無語是精簡到極致的語言。
語言比喻
文學可用的比喻手法,例如隱喻(metaphor)、直喻(simile)、借代(synecdoche)、轉喻(metonymy),再到頭韻(alliteration)、諧音(assonance)、逆喻(oxymoron)、擬人(personification)等等,名目繁多。語言能耍的手法、能玩的花樣真要細數道來,可以有好幾百種。這些遣辭用字的法門,不僅為說出來的話語增添華采,也帶出引申義,和話語之下沒說出來、不能說出來的潛文本共鳴共振。
舉例來看,田納西.威廉斯寫的舞台劇《慾望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白蘭琪.杜布瓦(Blanche DuBois)這位美國南方的遲暮佳麗,脆弱到一摧即折,正處於精神、情感崩潰的邊緣。她在第六景見到了米契(Mitch)。他是個寂寞、敏感的勞工階級單身漢,還必須照顧病重垂死的母親。一天晚上,兩人約會過後,相互傾訴各自過往的人生際遇;他們的運途南轅北轍,卻同樣寫滿了痛苦。兩人相互傾心,終於帶出下面這一刻:
米契:(慢慢把白蘭琪擁進懷裡)妳的人生需要有個伴。我的人生也需要有個伴。我的伴會不會是妳呢,白蘭琪?
白蘭琪瞅著他看了好一會兒,眼神一片空白,然後鳴咽一聲,依偎在他的懷裡。她輕聲啜泣,想擠出話來。米契吻上她的額頭,然後是她的眼睛,最後是她的唇。波卡舞曲飄得愈來愈遠。白蘭琪深吸一口氣,送出長長的一聲聲啜泣,透著感激。
白蘭琪:有時——真的有神啊——這麼快呢。45
最後一句只用了五個英文字,就匯聚出澎湃洶湧的意義和感情。「真的有神啊」幾個字,不是拿米契去比擬神祇,而是在說白蘭琪有如得救上天堂一般喜難自勝。不過,我們也猜想這應該不是她第一次領受這樣的神恩。
「有時」、「這麼快」幾個字則暗示白蘭琪以前便曾多次蒙男士拯救,只是那些突如其來拯救了她的男士,想必也突如其來拋棄了她,否則她不會還耗在這裡,不會依然被孤單逼得飛蛾撲火,再次緊緊攀附著陌生人不放。不過寥寥幾個字,觀眾馬上就看出當中隱含的行為模式:白蘭琪在男性面前始終以受害者的姿態去激發他們內心的白馬王子現身。他們拯救了她,但之後又拋棄了她,原因就有待我們去挖掘了。而這一次,她遇到的米契,可會不同於以往?
田納西.威廉斯祭出比喻,勾得人耳朵一豎,就把白蘭琪人生的悲涼調性提點出來,同時在觀眾腦中勾起疑問,心頭不禁一震。
作者遣辭用字寫出來的對白,光譜的一頭是傳達心靈、精神性意義,另一頭則是情慾經驗的描寫,形色不一而足。例如角色說起歌手的嗓音如何,可以拿「lousy」(長蟲)或是「sour」(臭酸)來形容。這兩個詞都說得通,但「長蟲」算是「死比喻」(dead metaphor)46了,原先的意思是「爬滿臭蟲」。「臭酸」倒還有生趣,觀眾一聽到,嘴角大概就翹起來了。下面兩句台詞,以哪一句更能撩撥觀者的感覺?「她走路像模特兒在走台步」,還是「她走起路來像一曲輕緩、挑情的歌」?同樣的意思,寫成對白可以有千萬種花樣,不過,大體上是以愈偏向感官知覺的修辭,效果愈見深刻,愈發教人難忘。【 】
修辭只在用上的那一句裡發揮作用,但由於對白能將一段又一段充斥衝突的話語帶出戲劇效果,時機和時間差的技巧也就可以加進來施展手腳:連珠砲的快節奏對上沉默無聲的停頓,一洩千里的連綴句對上斷斷續續的零碎字,妙答對上強辯,文謅謅的陽春白雪對上沒文法的下里巴人,單音節對上多音節,斯文有禮對上汙言穢語,逼真對上詩意,輕描淡寫對上誇大其詞,這類文體學和文字遊戲的例子多到不可勝數。不論人生唱得出來多少支曲子,對白一概有能耐跟著起舞。
我已經強調過好幾次,作者創作的天地無限寬廣,這裡也還要再重提一次。我再三重複這點,是希望作者可以確實明瞭:形式不會限制表達力,反而會激發表達力。這本書談的是撐起對白的形式,但絕對不會歸納寫對白的公式。有選擇才有創造。周邊語言
演員一出現在觀眾面前,全身上下無不透著形形色色的周邊語言,但凡與字詞無關的細微聲調變化和肢體動作,都會強化字詞傳達出來的意義和感覺——例如臉部表情、手勢、姿態、語速、音高、音量、節奏、音調、重音,甚至人際距離,也就是角色之間的站位,也是有作用的。演員傳遞的周邊語言,講的是「姿態對白」(gesticulate dialogue)。觀眾的眼睛抓到這些微表情(microexpression),頂多只需要四分之一秒。【 】但是在書頁上,周邊語言就需要借助語言比喻來加強描寫了。
下述例子摘錄自〈一九九五年八月的鐵路事故〉(Railroad Incident, August 1995)。這是大衛.閔茲所寫的短篇小說,描寫四個流浪漢晚上圍坐在篝火旁,忽然看到一個半裸男子從暗處冒了出來。
他們看出原來是個男子,一身步入中年的鬆軟,走路微瘸,但還是透著些許尊貴、拘謹的痕跡,抬腳的樣子好像高價鞋還穿在腳上,仍帶著份量;不過,說不定他們根本沒看出這些事,一直到他走到他們身邊、開口講話;他張開嘴說話,輕輕一聲你們好,母音拉得比較開,嘴型像是珍貴的貝殼……【 】
(大衛.閔茲喜歡寫短篇小說,我猜正是因為他舞文弄墨的絕招路數太多,要講上好幾百篇故事才有辦法盡數施展。)
混搭手法
小說能用的手法可以擇一施展,也可以混合並用。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在《一場美國夢》(An American Dream)下面這一段對話中,就把直接對白、第一人稱直接敘述、周邊語言,不論直義或是比喻,直接綰合為一:
「妳想離婚。」我說。
「是吧我看。」
「就這樣要離?」
「不是就這樣,親愛的,而是這麼多這樣。」她打了個呵欠,姿勢很漂亮,一時間看來有點像個十五歲的愛爾蘭小女僕。「你今天沒來跟狄兒黛樂說再見……」
「我又不知道她要走了。」
「你當然不知道。你怎麼會知道?你有兩個禮拜沒打電話過來了。成天只知道找你那些小姑娘又親又咬的。」她不知道那時候我一個小姑娘也沒有。
「她們現在沒那麼小了。」怒火開始在我身上延燒,這時候已經燒到心窩,燒得我覺得肺好像乾得像枯葉,心臟蓄積的壓力大概都要爆炸了。
「妳那蘭姆酒給我一口。」我說。47【 】
這裡簡單提一下不同媒介的改編問題:若是想把文學作品改編為電影,要注意長、短篇小說家多半把最高妙的語言留給主述去講,而不是戲劇場景中的對白——正如上述梅勒的手法。
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會遇上不小的扞格,原因在哪裡一目瞭然:攝影機拍不出心思。文思細密的敘述性故事,其內心對白沒辦法往旁邊橫移一步,就從書頁搬上銀幕。所以,改編一定要再作改寫,一定要從裡到外把故事重新再想像過一遍,將小說的敘事對白改頭換面為影視的戲劇對白才行。這絕非易事。台詞句式
台詞句式是以關鍵字為樞紐,因此必須找出對一句台詞意思最要緊的那一個字或詞。作者可以把關鍵字放在句頭、句尾或是句中,依據其選擇寫出下述三種基本的對白句式:懸疑、累進、平衡。
懸疑句(The Suspense Sentence)
勾起好奇心就會驅動求知欲——這是我們拆解謎團、尋找答案的知性需求。帶起同理心就會牽動連繫感——這是我們將心比心、求他人福祉的感性需求。生命的理智面和情緒面兩方合一,就會產生懸疑。而懸疑也可以歸納為一句話,那就是:好奇心被注入同理心。
懸疑之所以抓得住讀者/觀眾,在於下述這些帶著情感的疑問有如排山倒海灌進讀者/觀眾的腦中,勾住他們的注意力不放:「接下來會出什麼狀況?」「這樣子之後會怎樣?」「那主角會怎麼做?他有什麼感覺?」因而有所謂的「劇情重大疑點」(major dramatic question, MDQ)懸浮在上空,牢牢將故事從頭到尾罩在下方:「後來會怎樣?」這些疑問緊緊揪住人心,教人渾然忘了時間。隨著劇情推向高潮,懸疑愈來愈濃,最終會來到此去無回的轉捩當口,重大疑點跟著水落石出,接著就是劇終。
好奇加上關心,推送出貫串故事的懸疑弧線,但若是我們深入放大去看,會看出探究的心思其實瀰漫在故事的每一環節當中,不論輕重。每一景/場(scene)都找得到它飽含懸疑的轉捩點,當中的每一段話從第一句到最後一句,都要抓得住觀眾的注意力;連最小的單位,對白裡的一句台詞,都不脫小小的懸疑。故事要講得精采絕倫,就要一景接著一景、一段對話接著一段對話、一句台詞接著一句台詞,無不在將觀眾的理性、感性牢牢抓住入戲,片刻不會鬆脫。讀者一刻也不會停下,觀眾一刻也不會分心。
而要讓大家的眼睛定在書頁上、將大家的耳朵定在舞台和銀幕上,最重要的法寶就是掉尾句。所謂「掉尾句」,是把核心意思壓到句子的尾巴才說出來。把修飾語或次要的意思往前挪,主要的意思壓到最後,這樣的掉尾句便能拖住人的興趣不放。
舉例來看:「既然不讓我做,幹嘛又給我那個________ ?」這樣一句台詞填入下面哪一個字詞,可以帶出明確的意思?「眼色」?「槍」?「吻」?「點頭」?「相片」?「錢」?「報告」?「微笑」?「電子郵件」?「聖代」?只要是名詞,幾乎全都可以帶出明確的意思。掉尾句的句式不開門見山就把意思講得清楚明白,而是吊著讀者/觀眾的胃口,非得要從第一個字聽到最後一個字才能搞清楚,這樣就能帶起疑竇。
換句話說,掉尾句就是懸疑句。
例如下述雅思敏娜.黑薩寫的舞台劇《都是Art惹的禍》(Art, 1994)的開場;英譯出自克里斯多福.漢普頓(Christopher Hampton, 1946~)。我在每一句意思裡的關鍵字上頭加黑點標示出來。
馬克(Marc),一個人在台上。
馬克:我朋友塞哲(Serge)買了幅畫。油畫,五呎乘四呎大小;白色的。背景全白。你要是瞇起眼用力看,大概就看得出上面有幾條細細的白色斜線。
塞哲是我老朋友裡的老朋友,奮鬥有成,在當皮膚科醫生,十分醉心於藝術。
我禮拜一時去看了這幅畫。其實塞哲禮拜六才剛拿到手。但他垂涎很久了,有好幾個月吧,這幅白底上有白線的畫。
塞哲的家。
白底的油畫上有細細的白色斜痕,用畫架擺立在地板上。塞哲盯著他的畫,十分興奮。馬克細心端詳畫作。塞哲轉向馬克看著他看畫。
長長一陣靜默。兩人都沒出聲,無聲的情緒暗潮洶湧。
馬克:很貴?
塞哲:二十萬。
馬克:二十萬?
塞哲:尚.德洛尼(Jean Delauney)願意出二十二萬從我手裡搶過去。
馬克:那是誰?
塞哲:你是指德洛尼?
馬克:從沒聽過。
塞哲:德洛尼欸!德洛尼藝廊啊!
馬克:那個德洛尼藝廊願意出二十二萬來跟你搶?
塞哲:不是,不是藝廊,是他。德洛尼本人。他自己要收藏。
馬克:那為什麼德洛尼沒買?
塞哲:賣給私人客戶更重要啊。這叫市場流通。
馬克:嗯,嗯……
塞哲:怎樣?(馬克沒吭聲)你沒站對地方。要從這角度看。看到那些線條沒有?
馬克:這人……叫什麼……?
塞哲:畫家啊?安屈奧(Antrios)。
馬克:很出名?
塞哲:非常、非常出名。
(停頓)
馬克:塞哲,你該不會真的拿二十萬法郎買了這幅畫吧?
塞哲:欸,你不懂,就是這價碼。安屈奧嘛。
馬克:你真的拿二十萬法郎買這幅畫?
塞哲:早該想到你會抓錯重點。
馬克:你花二十萬法郎買這鬼東西?
塞哲,像是單獨一人在場。
塞哲:我這朋友馬克人是相當聰明的,我一直很珍惜兩人的友誼,他的工作不錯,在當航空工程師,但他是那種所謂「新式」的知識份子,不光是現代主義的天敵,好像還拿糟蹋現代主義來自鳴得意,真搞不懂……48【 】
這兩段自言自語的敘述對白,以及夾在中間的戲劇對白場景,總計表達出四十五點意思,當中有四十點是以懸疑句的構造出現。即使有地方簡單提了一下周邊語言(馬克和塞哲非語言的面部表情),還是一樣是把重點壓到末尾「無聲的情緒」這裡。
懸疑句不僅是戲劇力最強的句式,喜劇效果也最大。口頭講的笑話幾乎全都是拿懸疑句收尾打出笑點,驀然斬斷堆疊的張力、帶出笑聲。
黑薩和漢普頓都把關鍵字壓到最後,既帶得句子活潑生動,也牢牢抓住了觀眾的注意力,將衝擊的火力集中在最後一句爆發,而且往往還是喜趣的一擊。累進句
累進這手法的歷史有多悠久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早在兩千三百年前就在提倡這樣的手法。在他的《修辭學》(On Rhetoric)第三卷第九章中,便針對組織緊密的掉尾懸疑句,相較於組織鬆散、自由推進的累進句,二者有何差別進行探討。這兩種句式正好相反,互成鏡像:懸疑式組織把次要的字詞往前放,把核心的字詞往後推;累進式構造則把核心的字詞往前放,再依序排放次要的字詞來推展或修飾句義的重點。
這裡就來看看某乙對白的台詞句式:
某甲:還記得傑克嗎?
某乙:(點頭)那時候,白煙在他頭頂上繚繞,像怒氣的光暈,菸屁股掛在嘴邊都要燒到嘴唇了,除了使勁地在拖備胎,嘴裡還要罵千斤頂,手忙腳亂在換爆掉的輪胎……
(神情有一點落寞)
某乙:……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
我們若是把句式反過來,將上述懸疑句變成累進句:
某甲:還記得傑克嗎?
某乙:(神情有一點落寞)上次就是最後一次,他手忙腳亂在換輪胎,嘴裡要罵千斤頂,手上還要拖備胎,菸屁股叨在嘴邊都要燒到嘴唇了,白煙繚繞在他頭頂上,像怒氣的光暈。
雖然隨意推展的累進句式,戲劇力比起懸疑句可能較為薄弱,卻不算草率隨便。只要技巧高明,累進句勾畫出來的是漸次疊加、愈趨細膩的主題圖像,像滾雪球一樣,賦予對白像口語對話一樣的順勢自然,由字詞推展出宜人的節奏。
懸疑的句式是有不少優點,但也不乏缺點。首先,由於意思的重點一直往後推,要壓到結尾,可能給人矯揉造作的感覺。再者,懸疑要是拖得長一點,讀者/觀眾可能要被迫記住許多句義的枝節,捱到最後才有辦法把複雜的句義完全統合起來。若不懂得拿捏分寸、適可而止,懸疑句也會和寫得不好的累進句一樣累贅鬆垮。
懸疑句式和累進句式分別落在相對的兩端:一邊是把核心字句放在開頭,另一邊是拉到結尾,二者之間還有形形色色的無數變體。
例如「排比句式」(Parallel design)就是把長度、意思、句式差不多的句子連結起來,製造對比和強調,例如:
當我踏入那間教會,也踏入新的人生。平衡句式
把核心字詞放在句子中間,次要句子分別夾在頭尾兩端,就叫做平衡句式(Balanced Sentence):
傑克的性愛、賭博成癮的問題已經夠危險了,我覺得這傢伙絕對有刺激上癮症,要是再把他玩攀岩、高空跳傘算進來的話,
懸疑句不論是串接或排比,都是對白當中驅迫力、戲劇力最強大的句式。所以,想要製造緊張、強調、繁縟、笑聲的時候,就可以把核心字詞壓後。但反過來,累進句式和平衡句式便是最貼近言談、最自然流暢的句式。不過,過猶不及,任何技巧用得太多都會變得像壁紙圖案一樣單調,像機器人一樣僵硬。所以,對白在傳達角色確實活在這一刻、說了什麼之餘,要再推動觀眾入戲、蓄積張力,就必須結合幾種句式並用才行。
混合句式(Mixed Designs)
《無間警探》(True Detective)第一季第三集,主人翁之一,羅斯汀.柯爾(Rustin Cohle),對另兩位警探吉爾博(Gilbough)和帕帕尼亞(Papania)講述他的世界觀。我同樣在句子裡的核心字詞上頭加黑點標示出來。請注意,這裡的核心字詞都放在句子中段的位置。(DB是警方用語,意指死屍〔dead body〕)
羅斯汀.柯爾
這個……這個就是我在說的。我說的就是這個,當我在說時間、死亡,還有轉眼成空的時候。好吧,這裡面是有更大的概念在攪和,主要是我們這整個社會是造了什麼孽,搞得我們都有一樣的幻覺。整整十四小時盯著DB看,就會讓你開始想這些事。你們這樣子做過沒?你盯著他們的眼睛看,就算是照片也一樣,是死是活都不重要,這樣你就看得出來他們的心思。你們知道你會看到什麼嗎?他們樂得這樣子就好……當然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可是……到了最後一刻,就是這樣。絕對是解脫,不會錯。懂嗎?因為他們原本都很害怕,但到了這時候,他們終於明白原來是這麼簡單,只要……撒手就好。對,他們看清楚了,到了最後那十億分之一秒的那一刻,他們看清楚了……自己到底是什麼。你,你自己,人生這一整場大戲,從頭到尾不過是一堆自以為是、愚蠢的意志什麼的,東拼西湊出來的東西,扔了也罷。到最後終於搞懂,你根本就不用抓得這麼緊。終於搞清楚你這一生,你愛的那些,恨的那些,記得的那些,痛苦的那些,全都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全都不過是同樣的一場夢,你在一間上鎖的房間裡作的一場夢,你以為自己身而為人的一場夢。而且就跟許多的夢一樣,到最後都會出現一個惡魔。49
羅斯汀這一段總共表達了二十多點意思,其中有十二點用的是懸疑句,剩下的就是平衡、排比、累進的句式混合著用。結果就是這麼長的一段話,既吊住觀眾的興趣、堆疊起觀眾的興趣,也酬答了觀眾的興趣,同時有如自然流露的心聲,近乎恍惚神遊。請注意這一部影集的主創(creator)兼編劇尼克.皮佐拉圖(Nic Pizzolatto, 1975~),還為羅斯汀這段長長的話加上一個隱喻作壓軸:人生如夢。就像樂曲的裝飾音為樂段添加華采,修辭的手法一樣能為懸疑句添加撥動心弦的裝飾。精簡
意味深長的對白,最後一個重要條件便是精簡——意思是言簡意賅,用最少的字講出最豐富的意思。但凡寫得好的作品,尤其是對白,都符合小威廉.史壯克(William Strunk Jr, 1869~1946)和E. B.懷特(E. B. White, 1899~1985)兩人在《文體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當中提出來的「精簡」原則:「鏗鏘有力的文筆率皆簡潔精鍊。句子不應該有非必要的字詞,段落不應該有非必要的句子,這道理一如繪畫不應該有非必要的線條,機器不應該有非必要的零件。這不是要求句句簡短,也不是要求細節一概刪除只描述梗概,而是要求作者字字句句一定要言之有物。」【 】
不是空洞,而是精簡。
「非屬必要就刪」,就成了史壯克和懷特兩人論寫作的金科玉律。各位就為自己行行好,把這幾個字貼在電腦螢幕上面,乖乖照做。全天下沒有什麼話,不管多長多短,值得讀者/觀眾多費力氣去吸收一個不必要的字。廢話只會惹人討厭。刪!
(蘇菲亞.柯波拉執導的《愛情,不用翻譯》,對白就將精簡原則發揮得盡善盡美。參見第十八章的討論)
停頓
停頓放在你來我往的對話當中,用途不少。已經走到轉捩點卻遲疑一下不講話,會拉高讀者/觀眾心頭的緊張,一個個屏氣凝神等著看接下來的發展,也強調出事態有多嚴峻。但要是過了轉捩點才停頓,則能夠讓讀者/觀眾稍稍緩一口氣,消化一下陡然一變的狀況,領會一下變化後的情勢。
停頓出現在危機之前,會卡住情緒的流洩。寫得好的場景會帶動讀者/觀眾的好奇和關心往天翻地覆的那一刻流過去。讀者/觀眾會問自己:「接下來會怎樣?變成那樣的話,女主角該怎麼辦?情況又會變成怎樣?」如此的推動力蓄積得愈來愈高,驟然被停頓壓住,會將力量壓縮起來,等到轉捩點一轉過去,備受壓制的能量就會一口氣爆發,帶動場景衝到高潮的那一拍。
然而,若是濫用停頓——和對話一樣——原本近悅遠來,也會磨損成令大家退避三舍。其他技巧都要運用的精簡原則,在停頓這個技巧一樣重要。對白要是一停、再停、又停,以示強調、強調、再強調,到後來等於什麼都沒強調了。就像「狼來了」一樣,手法玩得愈浮濫,效果就愈少。等到作者寫到某一場景真的需要把手法的效力發揮到淋漓盡致時,就會發覺先前用得太多,把機鋒都磨鈍了。
所以,停頓要安排在哪裡才好,也要小心拿捏。情節推展的節奏不該磨蹭就要勇往直前,這樣一來,真的到了踩煞車時,定住不動的那一刻才抓得到注意力。愛停就停,不是白吃的午餐;只要一停,都要付出代價。沉默
文字簡約、步調敏捷,意義內隱多於外顯——這樣的對白會吊得讀者/觀眾迫不及待往下看;但若是文字冗贅,步調拖沓,意義外顯多於內隱,可就在對讀者/觀眾大澆冷水了。囉囉囌囌的對白,宛如老牛拖破車,只會逼得讀的人以走馬看花為宜,看的人以充耳不聞為要。所以,一如悲哀的場景常常需要喜趣來作調劑,話太多的時候就要懂得閉嘴。
不過,怎樣叫做「太多」,倒是每一則故事、每一幕場景都有不同,斷難定於一尊,端視個人的品味和判斷來作決定。要是覺得你寫的話比演的戲還多,那就換檔,改以眼睛為寫作的目標而非耳朵,以畫面取代言語。
各位不妨拿以下的問題來考自己:這一幕要是我全以影像來寫,將角色該做的事、故事該有的情節,一概寫成用畫面表現而不加一句對白,那麼應該怎麼做?下面這兩種做法可以擇一用來發揮畫面的威力:
一,周邊語言。姿態和臉部表情,嚴格來說不算語言,卻可以將字詞的言外之意和言下之意說得淋漓盡致。所以,與其要角色張嘴說「對/不對」、「我同意/我不同意」、「我覺得你是對的/我覺得你錯了」這樣的肯定句、否定句來打亂場景,還不如用點頭示意、眼神一掃、伸手比劃來把戲撐起來。
這一點對於寫電視、電影劇本尤其重要。只要做得到,就要在字裡行間留下餘地讓演員去發揮創意。由於攝影機可以把人臉放大好幾倍,心思和情緒會像在眼睛深處、在皮膚底下湧動如海面的波濤。角色不發一語,就是在邀請攝影機靠近深入。好好運用它。
二,肢體動作。只要有機會就問自己以下的問題:我這個角色在這裡的行動和反應,若不用口語,是否有肢體動作可以表達?發揮想像力去勾畫文字畫面,不要「光說不練」。
例如英格瑪.柏格曼某部電影裡的一幕場景。它的片名取得也很巧,就叫做《沉默》(The Silence, 1963)。片中有一名女子在旅館的餐廳裡任由自己讓侍者勾引。這樣的戲該怎麼寫呢?
侍者是不是遞菜單給女子,一一唸出當日的特餐?他會向女子推薦自己最喜歡的菜色嗎?或是讚美女子的衣著品味?他有沒有問女子是否在旅館過夜?是遠行嗎?是否問女子對該地熟不熟悉?隨口提起他再過一小時就下班了,可以當嚮導帶女子四處看看?唉,都是在講話、講話、講話!
柏格曼的處理手法如下:侍者不管有心還是無意,掉了一條餐巾在女子座椅旁邊的地板上。他慢慢彎下腰去撿餐巾,順便一路又吸又聞,從女子的頭頂往下到腿間再到腳邊。女子作出反應,深吸一口氣,帶著喜悅長歎一聲。之後,柏格曼把鏡頭切換到旅館房間,女子和侍者在床上激情交纏。侍者和女子兩人在餐廳那一場勾引戲,散發強烈的情慾,純屬影像,只用肢體,不發一語,再由女子發出那一聲吸氣與長歎,帶到轉捩點。
沉默無語是精簡到極致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