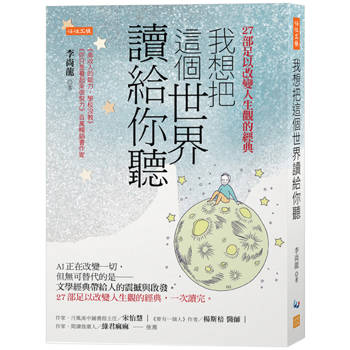夢想與金錢,你可以兩者都要──《月亮與六便士》
這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選擇月亮還是選擇六便士?所謂六便士,是過去英國面額最小的錢幣(按:已於1980年停止流通),它像月亮一樣,圓圓的、亮亮的,但尺寸和重要性又遠遠比不上月亮。
現在我們知道,月亮可以說是一種成分複雜的大石頭,但以前的人沒有現在的高科技,他們會覺得月亮就是天堂。
你身邊應該有這樣的朋友:在人群裡不容易一眼認出,長相一般、工作能力一般,但態度老實勤懇,有老婆和孩子。你能想像這個朋友,有天突然離家出走嗎?
我不能,但英國小說家威廉.薩默塞特.毛姆(1874-1965年)卻在小說《月亮與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寫了這樣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查爾斯.史崔蘭(Charles Strickland),在英國證券交易所當證券經紀人,雖然不是什麼傑出人物,但他擁有體面的工作、穩固的社會地位和外人看來美滿的家庭。結婚16年來,他每天都是如此生活。
但就在婚後第17年的一天,他突然離開家奔赴巴黎,拋棄了別人眼裡的好工作和幸福家庭。
聽到這裡,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你跟那群鄰居的想法可能一樣:他是不是愛上了誰,跟誰私奔了?但並不是,查爾斯沒有跟別的女人私奔,他離家出走的原因,是瘋狂迷戀繪畫。
繪畫代表著什麼?我們通常認為,繪畫是藝術,畫作都是藝術品。你若有機會可以看看2011年上映的法國電影《逆轉人生》(Intouchables),裡面有句臺詞這樣說:藝術品就是證明我們曾活過的東西。對查爾斯而言也是如此,在他眼裡繪畫代表著月亮,那是他身邊誰也無法到達的遠方。
用小說裡的話來說,他彷彿「被魔鬼附身」,他去巴黎就是為了追求這個理想。他太太聽說他住在很昂貴的豪華大飯店裡,但事實上根本不是如此:他寄居在巴黎一間旅館,「那裡並非時髦的區段,甚至不大入流」。
作者當然也不信:第一眼看到這家旅店時,全文敘述者「我」感到萬分惱火,懷疑自己被耍了。怎麼可能?
查爾斯學過繪畫嗎?沒有,不僅沒有,甚至也毫無任何喜歡繪畫的跡象,除了讀過一年的夜校之外,他毫無繪畫基礎。可是,當他被人找到時,他說:「我就跟你說了我得畫。我也沒辦法克制自己。一個人掉進水裡的時候,他游得好或不好並不重要:他就是得游出來,不然就等著溺水。」
就這樣,查爾斯一直堅持畫畫,但是他的作品太差了,要靠什麼活下來呢?這個時候,一名商業上成功但已過氣的荷蘭畫家德克.史特洛夫(Dirk Stroeve)登場了。這個人心地善良,眼光獨到,在別人覺得查爾斯的作品陳腐不堪、過分鮮豔繁雜的時候,只有他一眼看出查爾斯的繪畫天賦,把他當成上帝一般侍奉,不僅在生活上提供各種服務,還在他病重時把他接到家裡悉心照顧。
結果,查爾斯非但沒有絲毫感激,還在養病時勾引了史特洛夫的太太。不過,查爾斯很快就拋棄了史特洛夫的太太,最終她自殺身亡。
再後來,因為一些巧合,「我」遇上了一些人,他們在查爾斯人生最後幾年和他有過交集,包括船長、醫生等,從他們口中,「我」才聽說了查爾斯後半生的故事。
原來,查爾斯一路輾轉了幾個國家,最後落腳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島(Tahiti)。他跟一個名叫愛塔的當地人結婚,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在那裡,他遠離喧囂與紛擾,全心投入藝術創作。在大溪地,他好像真正找到了自己喜愛的生活方式。可是很不幸的,沒過多久,查理斯就感染了漢生病(Hansen's Disease,過去俗稱痲瘋病),這是一種由麻風桿菌引起的慢性傳染病,主要病變在皮膚和周圍神經。過世的前一年,查爾斯甚至成了一個瞎子。一個畫家竟看不見,多麼諷刺和荒謬!
那麼,他後悔嗎?他不後悔。
他的眼裡只有自己,沒有別人。他自私,沒有責任心,不屑和「社會」發生任何關係。但他又很無辜,因為他的眼裡豈止沒有別人,甚至沒有自己,只有夢想。
他不是選擇了夢想,而是被夢想選擇。
有些人在時代變幻下四處逃竄,逃向功名,或者利祿。但是,查爾斯拒絕成為和他們一樣的人,被控制在無休止的工業機器裡。滿地都是六便士,他卻抬頭看見了月亮。
在查爾斯最落魄的時候,愛塔不離不棄,一直在身邊照顧他,陪伴他完成了凝聚天賦與一生心血的巨型壁畫。正當大家期待著這幅畫的模樣時,故事卻迎來了讓人嘆惋的結局:「他要她(愛塔)答應,放火燒掉房子,而且直到房子化為焦土,半根木材都不剩之後才能離開。」
這幅畫最後就這樣被燒掉了。
跑下去,能看到什麼?──《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
「開始想寫小說的日期和時間,我可以明確指出。那是1978年4月1日的下午一點半左右。那一天,我在神宮球場外野席,一個人一面喝著啤酒一面看著棒球比賽……帶頭的打者是戴普.希爾頓(才剛剛從美國來到的新面孔年輕外野手)在左打線打出球。球棒剛好打到快速球,尖銳響亮的聲音響徹整個球場。希爾頓快速奔向一壘,輕易到達二壘。就在那個瞬間,我想到:『對了,來寫小說看看。』我還記得晴朗的天空,和剛剛新長的綠色鮮嫩草坪的觸感,以及球棒的爽脆聲音。那時候,從天上靜靜飄下來什麼,而我確實的接到了。」
我想,這也許是命運在敲他的門。每次命運的敲門聲,都需要你聽到。
「到了秋天已經寫完400字稿紙200頁左右的作品。寫完之後心情很爽快。完成的作品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因為像是一鼓作氣之下的產物,所以想試投文藝雜誌的新人賞看看。從投稿時並沒有影印留底來看,可能想到就算落選,原稿就那樣不知去向的消失也無所謂……第二年的初春,『群像』的編輯部打電話來說:『你的作品進入最後決審階段』……我30歲了,就在莫名其妙、毫無心理準備下,以新進小說家的姿態踏出了出道的第一步。雖然我也很驚訝,不過周圍的人一定更驚訝吧。」
這個故事其實也帶給我很多啟示。我三十多歲了,雖然25歲就開始寫東西,也得了很多獎,但我才剛剛開始。尤其是看到村上的經歷,我覺得我還有機會。我想聊聊村上春樹,其實更是想聊聊我自己。
1982年秋天,33歲的村上春樹開始了職業作家的生涯。也是那一年,他開始練習長跑。他每天凌晨4點起床,寫作4小時,跑10公里。
他說,寫作和跑步最大的相同處只有一個:堅持和磨練。在無人能理解、無人跟你溝通的狀態下,一步一步,走向遠方。這的確給了我巨大的啟發,因為自從讀了他的書,我開始每天早上寫2,000字,也一定會跑5公里。
跑步到底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願意以另一種眼光去看世界。
村上在這書中提到,他在一篇馬拉松跑者的專題報導中,讀到一句話: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簡單翻譯就是「痛是難免的,苦卻是甘願的」。
這句話為什麼好?因為這就是日本文化典型的特點,時刻告訴你:痛是生命的本質。這也是許多哲學的底層邏輯。但村上為什麼厲害?他加了後面一句,雖然痛苦你無法避免,但是否忍受痛苦,是你的選擇。
請注意,一個小小的「選擇忍受」,就把痛苦變成主動了。我們經常講,要過主動的人生。你有沒有發現,許多主動的人生,本質上都有一個特點:我知道命運艱難,但我至少有主動的可能性,哪怕只有一點點。
多一個人讀,世界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1984》
《1984》畢竟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它並沒有帶給我們正能量,因為當溫斯頓和茱莉亞被捕之後,他們相互背叛。在他們的思想變得「純潔」之後──這個「純潔」一定要打引號,因為這是黨對他們的要求──他們以為可以得到重生,但依舊被黨剷除。
在監獄裡,歐布萊恩遇見了溫斯頓,兩人有過許多對話。歐布萊恩在刑求溫斯頓時告訴他:「如果你是人,也會是最後一個,你的族類已經絕種了。」我讀到這句話時,背一直發抖。如果有一天,這個世界都是人工智慧,每個人的思考都只會循規蹈矩,每個人的人生都只能朝九晚五。那麼,最後一個人會不會是你、會不會是我呢?
故事最後,溫斯頓問了歐布萊恩一個問題:為什麼?這或許也是所有讀者的疑問,而作者借用歐布萊恩的嘴回答了這個問題:「黨完全是為了自己才會追求權力,我們對別人的福祉沒有興趣,我們只對權力有興趣……權力不是工具,而是目的……迫害的目的就是要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要折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只要以權力看這個世界,很多事情就能看明白了。同樣的,你以利益看人際關係,很多事情也能看得懂。權力是個好東西,即使排斥特權,但當特權走到我們身邊時,每一個人都會擁抱它。我們都討厭那些排隊插隊的人,可當你有機會成為那個插隊的人,你會不惜一切代價成為他。這就是權力的意義。
歐威爾在這本書裡告訴我們一個觀點:權力帶來的施虐感,或許才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實施權力,讓他受折磨,證明自己有力量,這就是尼采說的權力意志。其實,尼采說的權力意志,不僅是世俗的、資源性的權力,更重要的是精神權力。也就是你在精神上可以壓倒別人、征服別人,從而可以控制、統治別人的權力。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想做一個簡單的昇華。《1984》它不能被簡單的理解是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集權主義國家的批判。我認為它是世界性的,因為每一個國家的人,都有對權力的追求,甚至每一個人都希望追求最大的權力。我認為人性並不因國家和制度而改變。歐威爾以這本書探討了人性,探討人在權力不受約束之下,會變成什麼樣子。
書裡的黨無非是由眾人疊加而成的組織,它無非就是每一個對權力執著的人。但換句話說,這些只追求於權力、一直篡改是非的人,他們還能稱作是人嗎?讀完這本書後,我們都可以思考這個問題。當所有人都秉持同一個觀點,所有人都在追尋權力之時,你作為一個個體是不是成為了人呢?溫斯頓不放棄,以人性反抗黨。但歐布萊恩說:「人性就是黨說了算。」隱藏在溫斯頓身上最大的人性祕密,就是他身為一個人有愛、有思想,且懂得孤獨。他敢於跟世界不一樣,他敢於用人性挑戰黨性,但結局確實令人唏噓。
歐威爾在1948年完成了這本書。那個時候,蘇聯和美國正在冷戰,他很巧妙的在1948和1984之間做了個調整。他認為,1984年時世界會變成這樣,雖然他的預言失敗了,但人性的預言從來沒有失敗。在他之後,有多少的老大哥正在看著你我每一個人;在他之後,有多少的祕密警察正圍繞著這個世界。
《1984》這本小說改變了很多人,這本書也被人稱之為英語文學中最偉大的道德力量。也有人說,多一個人讀《1984》,這世界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讀這本書時你或許也會感覺到不適,因為我們會感覺自己也活在那個窒息的世界裡,喘不過氣。
我想這就是文學的魅力。它告訴我們,在平行世界裡可能擁有那樣的1984年。而在美好時代的今天,我們更能透過文學點亮我們的生活,警醒我們的現在,保護我們的未來。最後,我想再重複那句話:多一個人讀《1984》,世界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
這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選擇月亮還是選擇六便士?所謂六便士,是過去英國面額最小的錢幣(按:已於1980年停止流通),它像月亮一樣,圓圓的、亮亮的,但尺寸和重要性又遠遠比不上月亮。
現在我們知道,月亮可以說是一種成分複雜的大石頭,但以前的人沒有現在的高科技,他們會覺得月亮就是天堂。
你身邊應該有這樣的朋友:在人群裡不容易一眼認出,長相一般、工作能力一般,但態度老實勤懇,有老婆和孩子。你能想像這個朋友,有天突然離家出走嗎?
我不能,但英國小說家威廉.薩默塞特.毛姆(1874-1965年)卻在小說《月亮與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寫了這樣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查爾斯.史崔蘭(Charles Strickland),在英國證券交易所當證券經紀人,雖然不是什麼傑出人物,但他擁有體面的工作、穩固的社會地位和外人看來美滿的家庭。結婚16年來,他每天都是如此生活。
但就在婚後第17年的一天,他突然離開家奔赴巴黎,拋棄了別人眼裡的好工作和幸福家庭。
聽到這裡,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你跟那群鄰居的想法可能一樣:他是不是愛上了誰,跟誰私奔了?但並不是,查爾斯沒有跟別的女人私奔,他離家出走的原因,是瘋狂迷戀繪畫。
繪畫代表著什麼?我們通常認為,繪畫是藝術,畫作都是藝術品。你若有機會可以看看2011年上映的法國電影《逆轉人生》(Intouchables),裡面有句臺詞這樣說:藝術品就是證明我們曾活過的東西。對查爾斯而言也是如此,在他眼裡繪畫代表著月亮,那是他身邊誰也無法到達的遠方。
用小說裡的話來說,他彷彿「被魔鬼附身」,他去巴黎就是為了追求這個理想。他太太聽說他住在很昂貴的豪華大飯店裡,但事實上根本不是如此:他寄居在巴黎一間旅館,「那裡並非時髦的區段,甚至不大入流」。
作者當然也不信:第一眼看到這家旅店時,全文敘述者「我」感到萬分惱火,懷疑自己被耍了。怎麼可能?
查爾斯學過繪畫嗎?沒有,不僅沒有,甚至也毫無任何喜歡繪畫的跡象,除了讀過一年的夜校之外,他毫無繪畫基礎。可是,當他被人找到時,他說:「我就跟你說了我得畫。我也沒辦法克制自己。一個人掉進水裡的時候,他游得好或不好並不重要:他就是得游出來,不然就等著溺水。」
就這樣,查爾斯一直堅持畫畫,但是他的作品太差了,要靠什麼活下來呢?這個時候,一名商業上成功但已過氣的荷蘭畫家德克.史特洛夫(Dirk Stroeve)登場了。這個人心地善良,眼光獨到,在別人覺得查爾斯的作品陳腐不堪、過分鮮豔繁雜的時候,只有他一眼看出查爾斯的繪畫天賦,把他當成上帝一般侍奉,不僅在生活上提供各種服務,還在他病重時把他接到家裡悉心照顧。
結果,查爾斯非但沒有絲毫感激,還在養病時勾引了史特洛夫的太太。不過,查爾斯很快就拋棄了史特洛夫的太太,最終她自殺身亡。
再後來,因為一些巧合,「我」遇上了一些人,他們在查爾斯人生最後幾年和他有過交集,包括船長、醫生等,從他們口中,「我」才聽說了查爾斯後半生的故事。
原來,查爾斯一路輾轉了幾個國家,最後落腳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島(Tahiti)。他跟一個名叫愛塔的當地人結婚,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在那裡,他遠離喧囂與紛擾,全心投入藝術創作。在大溪地,他好像真正找到了自己喜愛的生活方式。可是很不幸的,沒過多久,查理斯就感染了漢生病(Hansen's Disease,過去俗稱痲瘋病),這是一種由麻風桿菌引起的慢性傳染病,主要病變在皮膚和周圍神經。過世的前一年,查爾斯甚至成了一個瞎子。一個畫家竟看不見,多麼諷刺和荒謬!
那麼,他後悔嗎?他不後悔。
他的眼裡只有自己,沒有別人。他自私,沒有責任心,不屑和「社會」發生任何關係。但他又很無辜,因為他的眼裡豈止沒有別人,甚至沒有自己,只有夢想。
他不是選擇了夢想,而是被夢想選擇。
有些人在時代變幻下四處逃竄,逃向功名,或者利祿。但是,查爾斯拒絕成為和他們一樣的人,被控制在無休止的工業機器裡。滿地都是六便士,他卻抬頭看見了月亮。
在查爾斯最落魄的時候,愛塔不離不棄,一直在身邊照顧他,陪伴他完成了凝聚天賦與一生心血的巨型壁畫。正當大家期待著這幅畫的模樣時,故事卻迎來了讓人嘆惋的結局:「他要她(愛塔)答應,放火燒掉房子,而且直到房子化為焦土,半根木材都不剩之後才能離開。」
這幅畫最後就這樣被燒掉了。
跑下去,能看到什麼?──《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
「開始想寫小說的日期和時間,我可以明確指出。那是1978年4月1日的下午一點半左右。那一天,我在神宮球場外野席,一個人一面喝著啤酒一面看著棒球比賽……帶頭的打者是戴普.希爾頓(才剛剛從美國來到的新面孔年輕外野手)在左打線打出球。球棒剛好打到快速球,尖銳響亮的聲音響徹整個球場。希爾頓快速奔向一壘,輕易到達二壘。就在那個瞬間,我想到:『對了,來寫小說看看。』我還記得晴朗的天空,和剛剛新長的綠色鮮嫩草坪的觸感,以及球棒的爽脆聲音。那時候,從天上靜靜飄下來什麼,而我確實的接到了。」
我想,這也許是命運在敲他的門。每次命運的敲門聲,都需要你聽到。
「到了秋天已經寫完400字稿紙200頁左右的作品。寫完之後心情很爽快。完成的作品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因為像是一鼓作氣之下的產物,所以想試投文藝雜誌的新人賞看看。從投稿時並沒有影印留底來看,可能想到就算落選,原稿就那樣不知去向的消失也無所謂……第二年的初春,『群像』的編輯部打電話來說:『你的作品進入最後決審階段』……我30歲了,就在莫名其妙、毫無心理準備下,以新進小說家的姿態踏出了出道的第一步。雖然我也很驚訝,不過周圍的人一定更驚訝吧。」
這個故事其實也帶給我很多啟示。我三十多歲了,雖然25歲就開始寫東西,也得了很多獎,但我才剛剛開始。尤其是看到村上的經歷,我覺得我還有機會。我想聊聊村上春樹,其實更是想聊聊我自己。
1982年秋天,33歲的村上春樹開始了職業作家的生涯。也是那一年,他開始練習長跑。他每天凌晨4點起床,寫作4小時,跑10公里。
他說,寫作和跑步最大的相同處只有一個:堅持和磨練。在無人能理解、無人跟你溝通的狀態下,一步一步,走向遠方。這的確給了我巨大的啟發,因為自從讀了他的書,我開始每天早上寫2,000字,也一定會跑5公里。
跑步到底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願意以另一種眼光去看世界。
村上在這書中提到,他在一篇馬拉松跑者的專題報導中,讀到一句話: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簡單翻譯就是「痛是難免的,苦卻是甘願的」。
這句話為什麼好?因為這就是日本文化典型的特點,時刻告訴你:痛是生命的本質。這也是許多哲學的底層邏輯。但村上為什麼厲害?他加了後面一句,雖然痛苦你無法避免,但是否忍受痛苦,是你的選擇。
請注意,一個小小的「選擇忍受」,就把痛苦變成主動了。我們經常講,要過主動的人生。你有沒有發現,許多主動的人生,本質上都有一個特點:我知道命運艱難,但我至少有主動的可能性,哪怕只有一點點。
多一個人讀,世界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1984》
《1984》畢竟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它並沒有帶給我們正能量,因為當溫斯頓和茱莉亞被捕之後,他們相互背叛。在他們的思想變得「純潔」之後──這個「純潔」一定要打引號,因為這是黨對他們的要求──他們以為可以得到重生,但依舊被黨剷除。
在監獄裡,歐布萊恩遇見了溫斯頓,兩人有過許多對話。歐布萊恩在刑求溫斯頓時告訴他:「如果你是人,也會是最後一個,你的族類已經絕種了。」我讀到這句話時,背一直發抖。如果有一天,這個世界都是人工智慧,每個人的思考都只會循規蹈矩,每個人的人生都只能朝九晚五。那麼,最後一個人會不會是你、會不會是我呢?
故事最後,溫斯頓問了歐布萊恩一個問題:為什麼?這或許也是所有讀者的疑問,而作者借用歐布萊恩的嘴回答了這個問題:「黨完全是為了自己才會追求權力,我們對別人的福祉沒有興趣,我們只對權力有興趣……權力不是工具,而是目的……迫害的目的就是要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要折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只要以權力看這個世界,很多事情就能看明白了。同樣的,你以利益看人際關係,很多事情也能看得懂。權力是個好東西,即使排斥特權,但當特權走到我們身邊時,每一個人都會擁抱它。我們都討厭那些排隊插隊的人,可當你有機會成為那個插隊的人,你會不惜一切代價成為他。這就是權力的意義。
歐威爾在這本書裡告訴我們一個觀點:權力帶來的施虐感,或許才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實施權力,讓他受折磨,證明自己有力量,這就是尼采說的權力意志。其實,尼采說的權力意志,不僅是世俗的、資源性的權力,更重要的是精神權力。也就是你在精神上可以壓倒別人、征服別人,從而可以控制、統治別人的權力。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想做一個簡單的昇華。《1984》它不能被簡單的理解是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集權主義國家的批判。我認為它是世界性的,因為每一個國家的人,都有對權力的追求,甚至每一個人都希望追求最大的權力。我認為人性並不因國家和制度而改變。歐威爾以這本書探討了人性,探討人在權力不受約束之下,會變成什麼樣子。
書裡的黨無非是由眾人疊加而成的組織,它無非就是每一個對權力執著的人。但換句話說,這些只追求於權力、一直篡改是非的人,他們還能稱作是人嗎?讀完這本書後,我們都可以思考這個問題。當所有人都秉持同一個觀點,所有人都在追尋權力之時,你作為一個個體是不是成為了人呢?溫斯頓不放棄,以人性反抗黨。但歐布萊恩說:「人性就是黨說了算。」隱藏在溫斯頓身上最大的人性祕密,就是他身為一個人有愛、有思想,且懂得孤獨。他敢於跟世界不一樣,他敢於用人性挑戰黨性,但結局確實令人唏噓。
歐威爾在1948年完成了這本書。那個時候,蘇聯和美國正在冷戰,他很巧妙的在1948和1984之間做了個調整。他認為,1984年時世界會變成這樣,雖然他的預言失敗了,但人性的預言從來沒有失敗。在他之後,有多少的老大哥正在看著你我每一個人;在他之後,有多少的祕密警察正圍繞著這個世界。
《1984》這本小說改變了很多人,這本書也被人稱之為英語文學中最偉大的道德力量。也有人說,多一個人讀《1984》,這世界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讀這本書時你或許也會感覺到不適,因為我們會感覺自己也活在那個窒息的世界裡,喘不過氣。
我想這就是文學的魅力。它告訴我們,在平行世界裡可能擁有那樣的1984年。而在美好時代的今天,我們更能透過文學點亮我們的生活,警醒我們的現在,保護我們的未來。最後,我想再重複那句話:多一個人讀《1984》,世界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