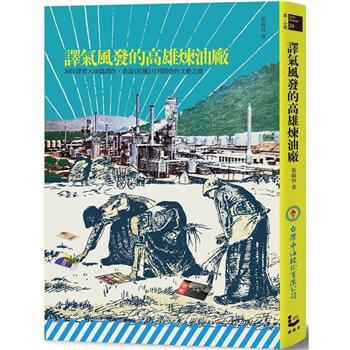「有《現代文學》嗎?」龍眉鳳眼的少年翻看著書攤上的《拾穗》雜誌,漫不經心問道。這是一九六○年三月,驚蟄剛過,早春的空氣裡滲著寒涼,攤販的十指縮在外套的口袋裡,搖著頭說:「沒聽過。」少年斜飛的眼梢掩不住失望,道了聲「謝謝」,闔上手裡的《拾穗》雜誌,沿著重慶南路往下一攤走。
這位少年名叫白先勇,二十三歲,臺大外文系三年級學生,選在驚蟄這天創辦了《現代文學》,期盼創刊號能如平地一聲春響——聲名陡起,沒想到實地走訪重慶南路的書攤查看銷路,攤販不是沒聽過,就是從一大疊雜誌底下抽出《現代文學》,藍底白線的封面蒙上了一層灰,給別家暢銷雜誌壓得黯然失色。「要不要?」攤販問,白先勇不忍再看下去,掉頭就走。
一轉眼,六十年過去,白先勇成了華文文學大師,創刊時乏人問津的《現代文學》躋身學術殿堂,銷聲匿跡的反倒是當年重慶南路書攤上的暢銷雜誌《拾穗》────白先勇翻看的那一期封面是一幅黑白照片,左上方印著紅底白字的「拾穗」大字,頗有美國《生活》(Life)雜誌的味道,新潮而且時髦,每期銷售量超過一萬冊,文藝青年人手一本。一九五四年平鑫濤創辦《皇冠》雜誌,便把《拾穗》當作競爭對手,誓言「一年內打垮《拾穗》」。然而,最終打垮《拾穗》的不是《皇冠》,而是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時間洪流。
遭歷史遺忘的《拾穗》,是臺灣戰後第一份純翻譯雜誌,一九五○年五月一日創刊,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停刊,總共出版462期,每月按時出刊,譯介域外新知將近四十載,內容囊括文學、音樂、科學、醫學……等,雖然是綜合性月刊,但翻譯文學貢獻卓越,不在《皇冠》和《現代文學》之下,總計翻譯三十一國的文學作品,文類涵蓋詩歌、小說、戲劇、兒童文學,其中不乏臺灣文壇首見中譯。要論譯介英美現代主義文學,《拾穗》走得比《現代文學》更前面,要論流通量,《拾穗》的發行網比《皇冠》更廣,怪不得白先勇和平鑫濤欽慕一時,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雄心壯志。
《拾穗》刊行的四十年間,正值臺灣白色恐怖時期,人民不能自由出國,電視也還不普及,更別提電腦、網路和智慧型手機。在那資訊閉塞的年代,《拾穗》雜誌月月翻譯域外新知,從而打開了一代青年的視野、豐富了年輕學子的心靈。透過《拾穗》,林懷民接觸到了西方舞蹈,洪蘭讀到了《船場》、《白衣女郎》等域外小說。譯作等身(超過兩百本)的陳蒼多從小受到《拾穗》啟發而走上翻譯這條路,根據他在〈買書.譯書〉一文中回憶:一九五八年,從高雄搭火車上臺北參觀軍校:「在高雄的一家書店買了一堆過期的《拾穗》雜誌,有的都沒有封面了,但還是興沖沖地帶著坐上火車。」
《拾穗》不僅每月發行雜誌,還出版了「拾穗譯叢」一百多種,譯者都是一時之選,譯筆不俗,影響既深且廣,一九七七年榮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優良雜誌獎」。而今獎盃猶在,無奈人事已非,《拾穗》的編輯和譯者多已不知去向。曾經「書店一條街」的重慶南路如今商旅林立,賣書的攤販和買書的少年都沒了蹤影。昔日的「舊書街」牯嶺街也少了書香,我走進僅存的舊書店,從那一落落的古書底下抽出一本塵封的《現代文學》,拍一拍,假裝漫不經心地問道:「有《拾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