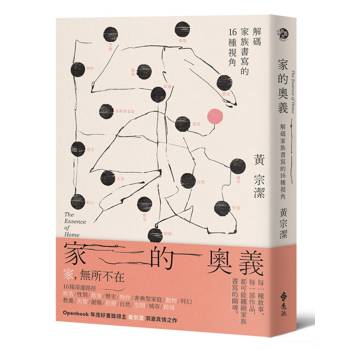內文精摘
〔姓名篇〕
禮物
◎《同名之人》,鍾芭.拉希莉著,彭玲嫻譯,天培,二○○四
◎《姓司武的都得死》,譚劍著,蓋亞,二○二三
二○二一年,台灣某間連鎖壽司店推出限時優惠方案,若名字與鮭魚同音即可享有折扣,名為「鮭魚」則全桌免費招待。業者顯然預期一般人不會以鮭魚為名,免費僅是招徠顧客與製造話題的行銷手法,不料卻有三百多名消費者前往戶政事務所改名,一時之間各種姓氏的鮭魚盡出,還有高價鮭魚、大口吃鮭魚、同鮭魚盡、鮭魚之夢等創意姓名,命名彷彿成了一場「鮭魚遊戲」。此一被稱為「鮭魚之亂」的事件不只登上國際新聞版面,後續也引發了對命名權、改名權的討論。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們既然擁有自己的姓名,那麼姓名的「使用方式」自然也應該完全操之在我,「鮭魚之亂」中動輒將名字改為四、五十個字,字數多到身分證幾乎塞不下的案例,想必抱著這樣的態度。改名對他們而言,形同在網路世界的不同平台取暱稱。然而,我們可以擁有無數個代號來維護自己的網路匿名性,現實世界卻無法如此,否則法律也無須對改名次數進行規範。至於利用免費吃到飽的福利,以數百元的價格組團用餐再收取餐費的少數「鮭魚」,將改名一事轉化為商業行為,名字在此模式中形同可以獲利的「商品」。從這個角度來看,「鮭魚之亂」不僅僅是一場令廠商始料未及的風波,或茶餘飯後的有趣話題,而是隱含著我們看待姓名的態度,以及一個深層的提問:我們的名字,屬於我們自己嗎?
無論法律如何規定改名的次數與程序,或是不同國家對姓名看法的文化差異,一個跨文化的事實是,我們日後想幫自己取多少筆名、藝名、小名都好,人生的第一個名字必然是被決定的。因此,它是一份禮物,而且是生命中第一份禮物。名字承載著命名者對新生兒的期盼與祝福,但它也一如所有的禮物,送禮者與收受者之間,對價值的認知、喜好與感受都未必相同。與其他禮物唯一的差異,或許在於就算不喜歡,它也無法轉贈。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同名之人》(The Namesake)與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儘管在故事風格與小說類型上都大相逕庭,卻同樣能帶我們看到姓名在生命中,作為一份禮物(或負資產?)的角色與意義。
——
●名字是一道咒語或一個祝福
「這世上最短的咒正是『名』。所謂咒,簡單說來就是束縛。要知道,名稱正是束縛事物本質的一種東西。」《同名之人》裡的主角果戈理,若是讀到夢枕獏在《陰陽師》中透過安倍晴明之口說出的這段話,想必深有同感。這部處理兩代印裔美籍移民人生的小說,深刻細膩地透過一個糾結一生的名字,突顯出姓名作為符號,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遠比我們意識到的更重要。
果戈理這個名字,原是一場文化衝擊下的意外產物。年輕的移民夫婦阿碩可與愛希瑪依照傳統,將新生兒的命名權交託給愛希瑪的外婆。在那個仍然依賴電報與信件往返的年代,寫上小嬰兒名字的信,卻未能及時在他出生前抵達。儘管如此,他們並不焦慮,因為根據孟加拉的命名規則,每個人都有兩個名字,一個乳名,一個學名。學名是長大之後在正式場合使用,對於襁褓中的嬰兒來說,他只需要父母長輩表達親暱與祝福的乳名。問題是,在美國,嬰兒若沒有名字,就無法開立出生證明,也無法出院。
情急之下,阿碩可想起一個無懈可擊的名字——在火車事故時,從他緊握的手中掉落,讓他得以被搜救人員發現,救了他一命的那本小說,作者的名字,果戈理。愛希瑪同意了,因為她知道,「這名字代表的不只是她兒子的生命,也是她丈夫的生命。」那是一個父親送給兒子的第一份禮物。
對於這份禮物,年幼的果戈理並非一開始就感受到它的特別之處,卻也並不排斥。儘管他從來不曾在那些印著名字的紀念品上找到自己的名字,但他會在路牌上看到GO LEFT、GO RIGHT,遇見這些「Gogol 的片段」是種樂趣,也讓他得以指認自己的一部分。名字所帶來的種種認同困惑與困擾,是從進入學校這個小型社會才出現的。
好不容易選定了一個完美的孟加拉學名「倪克熙爾」,果戈理的父母卻再次在命名這件事情上,意識到移民生活是一場永恆的,文化與文化之間折衝磨合的過程。幼稚園無法理解父母為何要使用一個不存在於出生證明上,既非中間名也不是暱稱的名字。愛希瑪與阿碩可只能無奈接受父母的意願被學校無視的現實。至於果戈理,那卻是他與這個名字磨合的真正起點。他不明白人為何需要兩個名字,因此在幼稚園校長詢問時,斷然放棄了陌生的「倪克熙爾」之名,但慢慢地,他發現除了自己之外,沒有人叫做果戈理。他討厭老師點名時對自己名字的遲疑,更無法想像追求女孩時在浪漫氛圍中說出「嗨,我是果戈理。」名字這個沒有形體的東西甚至「會對他的身體造成不適,像襯衫上扎著皮膚的標籤,永恆不能褪下。」
●藉以指認「我是誰」與「我不是誰」
對於許多動輒「撞名」的人來說,果戈理的煩惱看似「奢侈」,更何況,獨一無二的名字,不是更能滿足我們期待與眾不同的心理需求?但自我認同其實是不斷在獨特性與歸屬感的天平間擺盪挪移、尋找位置的過程。果戈理這個過度特別的名字,反而令他在同儕中感到格格不入。更困擾的是,為此他必須不斷解釋:這個字在印度文中沒有任何意義,而是與他毫無關係的俄文。相對於那些連結著美好語意的傳統名字,姓名對他的意義與其說指認了「我是誰」,不如說是「我不是誰」——不是印度人,也不是美國人,當然更不可能是俄國人。甚至連他的姓名來源,那位同名之人,作家果戈理,也不叫果戈理——那是他的姓而非名。
身為移民後裔的認同困惑與孤獨感,被果戈理這個獨一無二的名字,徹底地具象化了。果戈理決定成為他童年時拒絕的那個名字,倪克熙爾。這並未讓他的生活顯得比較輕易,他依然在旁人討論姓名時感到不自在,更諷刺的是,他最後選擇的婚姻對象,是從小就認識,因此知道他本名的茉淑蜜——一個同樣苦於自己名字既罕見又難以發音的女孩。
鍾芭.拉希莉既未簡化,也未誇大姓名的重要性。果戈理的婚姻當然不只是基於名字的相似性,但他確實在某次朋友聚會後,意識到「吸引他倆結合的奇特情愫」,與這孤單的,未能輕易找到同名之人的認同感有關,一如他童年時總會留意墓園裡那些古怪又古老的名字,並且被那些擁有「過時的,無法想像的名字的人」深深吸引。他所依附的認同對象,從來不是印度人或美國人這樣的族群劃分,而是那些與他一樣,落單的、無法被妥善安放在群體中的,畸零者。
這世界上並不存在「完美的名字」,認同自己的姓名,當然也不至於就能擁有「完美的人生」。當父親終於告訴果戈里命名的源由,同樣不會讓彆扭、厭棄了一輩子的名字,搖身一變成為帶著光圈的名牌。果戈理三個字依然如同某個應該被隱藏的汙點,一場災難的分身與見證,但他對這個被自己放棄的名字,從此多了一份歉疚感。
當歉疚感悄悄萌芽,當他明白了這個在印度文與英文裡都沒有任何意義的名字,在父親的字典裡,卻意味著重生與祝福,他看待自己、看待父親、看待果戈理三個字的眼光都已不同。禮物之為禮物,也唯有在收禮者意識到那作為一份禮物時,意義才得以被指認。
●標誌著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進一步來說,姓名這個符號,可能是所有身分標籤中,最複雜的一種。在公開與隱匿之間,它以全稱、敬稱、暱稱、化名等各式各樣的形式,標誌著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名字作為禮物的意義,不僅止於命名者與被命名的關係,在某些文化或情境中,分享自己的名字,亦具有託付信任與交出一部分自己的象徵意義。韓劇《魷魚遊戲》裡,在殘酷的生存遊戲中一步步踏入死亡陷阱的參賽者,就被剝奪了姓名,只以去人性化的編號受到掌控。女主角姜曉與她編號240的同伴智英,在死亡面前,最後唯一能交換的珍貴物事,僅僅剩下彼此的姓名。這令人動容的一幕,可說是姓名作為禮物的最好彰顯。
至於村上春樹《東京奇譚集》裡那隻愛偷名字的「品川猴」,更說出「在這同時,也把附著在名字上的負面要素,多少也帶走一些」的話,同樣暗示名字既是「身分」,也作為某種「分身」的意義。
〈品川猴〉裡另一個有趣的細節,是主角婚後覺得一一向客戶通知自己改姓太麻煩了,在職場上仍保留婚前的姓名,發現有時會突如其來地遺忘姓名之後,她去珠寶店訂購了一個刻上「安藤(大澤)美月」的銀手鐲來提醒自己,就像寵物項圈的概念一樣。「安藤(大澤)」的身分,突顯出婚後冠上夫姓的情況,讓女性需要經歷一段重新適應自己新姓名的過程。儘管未必每個人都會為此困擾,卻提醒我們鑲嵌在身分符號之中的姓氏,作為「家庭/家族單位」的意義遠大於代表「個人」。這是何以傳統婚宴場合,餐廳往往會掛上「X府喜宴」或「XX聯姻」標語,而非新人的名字,隱然標誌著婚姻作為兩個家族而非兩個個體結合的現實。
正因姓氏作為一個集體符號,雖說同姓三分親,但除了罕見姓氏,一般人對於「同姓之人」通常不會產生特別親近的感受。姓氏帶來的苦惱除非特殊狀況(例如傳統社會對同姓婚姻的反對),否則不會像名字這種更具個別性的符號一般讓人念茲在茲。但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這部小說,卻透過一個虛構的滅族式謀殺案,對姓氏背後所連結的,「家」與「家族」的概念進行了反思。
●姓氏是斬斷不了的親緣束縛
「姓司武的都得死」是個奇特的謀殺委託案,雖然不少人在結怨時會以對方全家作為咒罵的對象,但真要實際執行,即使以「全世界加起來只有五十多個成員」來說,也是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暗殺任務。但譚劍賦予這個虛構姓氏一個「香港限定」的獨特設定——他們是居住在大嶼山圍村的原居民。四散的家族成員有一個合理與必要的聚集契機,就是三年一次的家祭。這讓職業殺手的「工作難度」瞬間減輕不少。一場大規模的集體毒殺案,就成為小說驚人的開場序曲。
香港的圍村有其非常獨特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傳統,相對也更父權中心。根據「丁屋政策」,新界原居民的男丁只要年滿十八歲,即可申請建造一間三層以下、每層七百平方呎的丁屋,無須向政府繳付地價。小說裡的司武家族成員,單是這被動收入已可不愁吃穿,每個月都有豐厚的生活津貼。姓氏對他們來說,確實如同一份權利與禮物,尤其是男性成員。當然,對那些只因同姓就莫名枉死的人來說,司武這個姓氏卻是不折不扣的負資產。
既然是推理小說,故事最後自然解釋了兇手要殺掉整個家族的動機,但謎團的設計並非本文要討論的重點,這部小說最吸引人之處,事實上也不在於那關鍵的動機與解謎的趣味,而是作者在〈後記〉提到的,「活在一個丁權家族裡各成員的感受。」幾位倖存者多半在情感上或生活上與家族疏離,卻又在經濟上或心理上被這個姓氏束縛著。
活得像個浪子的志義,自嘲名字中英夾雜、不中不西:「志」來自族譜輩分,「義」是家族天主教信仰的影響,「justice」、「faith」、「charity」這些單字被直接當成正式英文名,印在身分證上。但當他說出:「名字取得亂七八糟,反映那些人的想法也亂七八糟。有時我懷疑我這種人生過得亂七八糟的基因也是遺傳。」卻又隱然在自棄的情緒中流露出無法斬斷親緣的體悟。表妹志愛身為女性,對封建保守的家族從無好感,集體毒殺案發生後,她甚至覺得他們死了也不可惜,因為,「那些人包括雙親就算沒死,活下去也是行屍走肉,除了消費以外,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但她同樣清楚自己「一輩子不必出來工作的人生,是司武家賜與的。」他們的處境,就如同與司武家早已斷絕往來,卻因為案情重新被捲入家族糾葛,並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不得不積極參與查案的私家偵探志信形容的,是一個開放式監獄,囚友每個月都可以領到生活費,靈魂卻被禁錮著。
●家也可能如怪物般吞噬成員
在推理小說的框架下,血緣關係的感受與思考,並不只是感性的惆悵,更是務實的「誰會是加害者/受害者」之考量。外嫁的女兒不姓司武,卻同樣被納入謀殺名單,因為無論父系或母系,他們都擁有司武家的基因。但基因作為看似科學又可靠的線索,除了外貌上的相似特徵、隱藏的遺傳疾病,甚至志義形容的,性格與生活方式,足以作為辨識「一家人」的條件,那接受骨髓移植而擁有受贈者基因的人,也算是一家人嗎?當事者顯然並不這麼認為。於是,血緣、法律、同居,再加上「把事情變複雜」的科技,沒有一個能充分回答「什麼是家人?」這個問題。
對志愛和志信來說,更能給他們「家人」感受的,從來不是形同陌路的原生家庭。相較於親生父親,志愛覺得指導教授給她的關懷和啟發,更足以勝任父親這個角色,「即使教授是為天主教不容的同性戀者。誰說同性戀者不會給人父愛?」至於志信,更在警方質疑他「寧願陪狗也不去和家人共聚」時,理直氣壯地回覆:「家人的定義並不限於人,只要一起生活又有感情交流就是家人。我的狗當然是我家人,而且比姓司武的親近得多。」在釐清案情的過程中,這些司武家的成員們,無非也在澄清家與家人的定義。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可以視為家的地方」,但即使身處同一屋簷下,對家的樣貌也未必有共識。其中的歧異既受到世代觀念遞嬗的影響,自然也有個別差異。儘管司武這個姓氏是虛構的,圍村家族的處境即使對應在現實香港社會也屬少數,幾位司武家族成員對原生家庭的感受,卻足以讓我們看到姓氏作為「家」這個單位的辨識符號,可以是凝聚認同感的來源,也可能是「如怪物般吞噬成員」的深淵。原生家庭給予的是禮物還是負資產,儘管全憑運氣,但我們仍然擁有以自由意志去動搖無形禁錮的力量。如何找出那個可以視為家的所在,重新描摩自己心中家的形貌,或許才是小說留待讀者破譯的,真正謎團。
(未完待續)
〔姓名篇〕
禮物
◎《同名之人》,鍾芭.拉希莉著,彭玲嫻譯,天培,二○○四
◎《姓司武的都得死》,譚劍著,蓋亞,二○二三
二○二一年,台灣某間連鎖壽司店推出限時優惠方案,若名字與鮭魚同音即可享有折扣,名為「鮭魚」則全桌免費招待。業者顯然預期一般人不會以鮭魚為名,免費僅是招徠顧客與製造話題的行銷手法,不料卻有三百多名消費者前往戶政事務所改名,一時之間各種姓氏的鮭魚盡出,還有高價鮭魚、大口吃鮭魚、同鮭魚盡、鮭魚之夢等創意姓名,命名彷彿成了一場「鮭魚遊戲」。此一被稱為「鮭魚之亂」的事件不只登上國際新聞版面,後續也引發了對命名權、改名權的討論。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們既然擁有自己的姓名,那麼姓名的「使用方式」自然也應該完全操之在我,「鮭魚之亂」中動輒將名字改為四、五十個字,字數多到身分證幾乎塞不下的案例,想必抱著這樣的態度。改名對他們而言,形同在網路世界的不同平台取暱稱。然而,我們可以擁有無數個代號來維護自己的網路匿名性,現實世界卻無法如此,否則法律也無須對改名次數進行規範。至於利用免費吃到飽的福利,以數百元的價格組團用餐再收取餐費的少數「鮭魚」,將改名一事轉化為商業行為,名字在此模式中形同可以獲利的「商品」。從這個角度來看,「鮭魚之亂」不僅僅是一場令廠商始料未及的風波,或茶餘飯後的有趣話題,而是隱含著我們看待姓名的態度,以及一個深層的提問:我們的名字,屬於我們自己嗎?
無論法律如何規定改名的次數與程序,或是不同國家對姓名看法的文化差異,一個跨文化的事實是,我們日後想幫自己取多少筆名、藝名、小名都好,人生的第一個名字必然是被決定的。因此,它是一份禮物,而且是生命中第一份禮物。名字承載著命名者對新生兒的期盼與祝福,但它也一如所有的禮物,送禮者與收受者之間,對價值的認知、喜好與感受都未必相同。與其他禮物唯一的差異,或許在於就算不喜歡,它也無法轉贈。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同名之人》(The Namesake)與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儘管在故事風格與小說類型上都大相逕庭,卻同樣能帶我們看到姓名在生命中,作為一份禮物(或負資產?)的角色與意義。
——
●名字是一道咒語或一個祝福
「這世上最短的咒正是『名』。所謂咒,簡單說來就是束縛。要知道,名稱正是束縛事物本質的一種東西。」《同名之人》裡的主角果戈理,若是讀到夢枕獏在《陰陽師》中透過安倍晴明之口說出的這段話,想必深有同感。這部處理兩代印裔美籍移民人生的小說,深刻細膩地透過一個糾結一生的名字,突顯出姓名作為符號,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遠比我們意識到的更重要。
果戈理這個名字,原是一場文化衝擊下的意外產物。年輕的移民夫婦阿碩可與愛希瑪依照傳統,將新生兒的命名權交託給愛希瑪的外婆。在那個仍然依賴電報與信件往返的年代,寫上小嬰兒名字的信,卻未能及時在他出生前抵達。儘管如此,他們並不焦慮,因為根據孟加拉的命名規則,每個人都有兩個名字,一個乳名,一個學名。學名是長大之後在正式場合使用,對於襁褓中的嬰兒來說,他只需要父母長輩表達親暱與祝福的乳名。問題是,在美國,嬰兒若沒有名字,就無法開立出生證明,也無法出院。
情急之下,阿碩可想起一個無懈可擊的名字——在火車事故時,從他緊握的手中掉落,讓他得以被搜救人員發現,救了他一命的那本小說,作者的名字,果戈理。愛希瑪同意了,因為她知道,「這名字代表的不只是她兒子的生命,也是她丈夫的生命。」那是一個父親送給兒子的第一份禮物。
對於這份禮物,年幼的果戈理並非一開始就感受到它的特別之處,卻也並不排斥。儘管他從來不曾在那些印著名字的紀念品上找到自己的名字,但他會在路牌上看到GO LEFT、GO RIGHT,遇見這些「Gogol 的片段」是種樂趣,也讓他得以指認自己的一部分。名字所帶來的種種認同困惑與困擾,是從進入學校這個小型社會才出現的。
好不容易選定了一個完美的孟加拉學名「倪克熙爾」,果戈理的父母卻再次在命名這件事情上,意識到移民生活是一場永恆的,文化與文化之間折衝磨合的過程。幼稚園無法理解父母為何要使用一個不存在於出生證明上,既非中間名也不是暱稱的名字。愛希瑪與阿碩可只能無奈接受父母的意願被學校無視的現實。至於果戈理,那卻是他與這個名字磨合的真正起點。他不明白人為何需要兩個名字,因此在幼稚園校長詢問時,斷然放棄了陌生的「倪克熙爾」之名,但慢慢地,他發現除了自己之外,沒有人叫做果戈理。他討厭老師點名時對自己名字的遲疑,更無法想像追求女孩時在浪漫氛圍中說出「嗨,我是果戈理。」名字這個沒有形體的東西甚至「會對他的身體造成不適,像襯衫上扎著皮膚的標籤,永恆不能褪下。」
●藉以指認「我是誰」與「我不是誰」
對於許多動輒「撞名」的人來說,果戈理的煩惱看似「奢侈」,更何況,獨一無二的名字,不是更能滿足我們期待與眾不同的心理需求?但自我認同其實是不斷在獨特性與歸屬感的天平間擺盪挪移、尋找位置的過程。果戈理這個過度特別的名字,反而令他在同儕中感到格格不入。更困擾的是,為此他必須不斷解釋:這個字在印度文中沒有任何意義,而是與他毫無關係的俄文。相對於那些連結著美好語意的傳統名字,姓名對他的意義與其說指認了「我是誰」,不如說是「我不是誰」——不是印度人,也不是美國人,當然更不可能是俄國人。甚至連他的姓名來源,那位同名之人,作家果戈理,也不叫果戈理——那是他的姓而非名。
身為移民後裔的認同困惑與孤獨感,被果戈理這個獨一無二的名字,徹底地具象化了。果戈理決定成為他童年時拒絕的那個名字,倪克熙爾。這並未讓他的生活顯得比較輕易,他依然在旁人討論姓名時感到不自在,更諷刺的是,他最後選擇的婚姻對象,是從小就認識,因此知道他本名的茉淑蜜——一個同樣苦於自己名字既罕見又難以發音的女孩。
鍾芭.拉希莉既未簡化,也未誇大姓名的重要性。果戈理的婚姻當然不只是基於名字的相似性,但他確實在某次朋友聚會後,意識到「吸引他倆結合的奇特情愫」,與這孤單的,未能輕易找到同名之人的認同感有關,一如他童年時總會留意墓園裡那些古怪又古老的名字,並且被那些擁有「過時的,無法想像的名字的人」深深吸引。他所依附的認同對象,從來不是印度人或美國人這樣的族群劃分,而是那些與他一樣,落單的、無法被妥善安放在群體中的,畸零者。
這世界上並不存在「完美的名字」,認同自己的姓名,當然也不至於就能擁有「完美的人生」。當父親終於告訴果戈里命名的源由,同樣不會讓彆扭、厭棄了一輩子的名字,搖身一變成為帶著光圈的名牌。果戈理三個字依然如同某個應該被隱藏的汙點,一場災難的分身與見證,但他對這個被自己放棄的名字,從此多了一份歉疚感。
當歉疚感悄悄萌芽,當他明白了這個在印度文與英文裡都沒有任何意義的名字,在父親的字典裡,卻意味著重生與祝福,他看待自己、看待父親、看待果戈理三個字的眼光都已不同。禮物之為禮物,也唯有在收禮者意識到那作為一份禮物時,意義才得以被指認。
●標誌著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進一步來說,姓名這個符號,可能是所有身分標籤中,最複雜的一種。在公開與隱匿之間,它以全稱、敬稱、暱稱、化名等各式各樣的形式,標誌著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名字作為禮物的意義,不僅止於命名者與被命名的關係,在某些文化或情境中,分享自己的名字,亦具有託付信任與交出一部分自己的象徵意義。韓劇《魷魚遊戲》裡,在殘酷的生存遊戲中一步步踏入死亡陷阱的參賽者,就被剝奪了姓名,只以去人性化的編號受到掌控。女主角姜曉與她編號240的同伴智英,在死亡面前,最後唯一能交換的珍貴物事,僅僅剩下彼此的姓名。這令人動容的一幕,可說是姓名作為禮物的最好彰顯。
至於村上春樹《東京奇譚集》裡那隻愛偷名字的「品川猴」,更說出「在這同時,也把附著在名字上的負面要素,多少也帶走一些」的話,同樣暗示名字既是「身分」,也作為某種「分身」的意義。
〈品川猴〉裡另一個有趣的細節,是主角婚後覺得一一向客戶通知自己改姓太麻煩了,在職場上仍保留婚前的姓名,發現有時會突如其來地遺忘姓名之後,她去珠寶店訂購了一個刻上「安藤(大澤)美月」的銀手鐲來提醒自己,就像寵物項圈的概念一樣。「安藤(大澤)」的身分,突顯出婚後冠上夫姓的情況,讓女性需要經歷一段重新適應自己新姓名的過程。儘管未必每個人都會為此困擾,卻提醒我們鑲嵌在身分符號之中的姓氏,作為「家庭/家族單位」的意義遠大於代表「個人」。這是何以傳統婚宴場合,餐廳往往會掛上「X府喜宴」或「XX聯姻」標語,而非新人的名字,隱然標誌著婚姻作為兩個家族而非兩個個體結合的現實。
正因姓氏作為一個集體符號,雖說同姓三分親,但除了罕見姓氏,一般人對於「同姓之人」通常不會產生特別親近的感受。姓氏帶來的苦惱除非特殊狀況(例如傳統社會對同姓婚姻的反對),否則不會像名字這種更具個別性的符號一般讓人念茲在茲。但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這部小說,卻透過一個虛構的滅族式謀殺案,對姓氏背後所連結的,「家」與「家族」的概念進行了反思。
●姓氏是斬斷不了的親緣束縛
「姓司武的都得死」是個奇特的謀殺委託案,雖然不少人在結怨時會以對方全家作為咒罵的對象,但真要實際執行,即使以「全世界加起來只有五十多個成員」來說,也是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暗殺任務。但譚劍賦予這個虛構姓氏一個「香港限定」的獨特設定——他們是居住在大嶼山圍村的原居民。四散的家族成員有一個合理與必要的聚集契機,就是三年一次的家祭。這讓職業殺手的「工作難度」瞬間減輕不少。一場大規模的集體毒殺案,就成為小說驚人的開場序曲。
香港的圍村有其非常獨特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傳統,相對也更父權中心。根據「丁屋政策」,新界原居民的男丁只要年滿十八歲,即可申請建造一間三層以下、每層七百平方呎的丁屋,無須向政府繳付地價。小說裡的司武家族成員,單是這被動收入已可不愁吃穿,每個月都有豐厚的生活津貼。姓氏對他們來說,確實如同一份權利與禮物,尤其是男性成員。當然,對那些只因同姓就莫名枉死的人來說,司武這個姓氏卻是不折不扣的負資產。
既然是推理小說,故事最後自然解釋了兇手要殺掉整個家族的動機,但謎團的設計並非本文要討論的重點,這部小說最吸引人之處,事實上也不在於那關鍵的動機與解謎的趣味,而是作者在〈後記〉提到的,「活在一個丁權家族裡各成員的感受。」幾位倖存者多半在情感上或生活上與家族疏離,卻又在經濟上或心理上被這個姓氏束縛著。
活得像個浪子的志義,自嘲名字中英夾雜、不中不西:「志」來自族譜輩分,「義」是家族天主教信仰的影響,「justice」、「faith」、「charity」這些單字被直接當成正式英文名,印在身分證上。但當他說出:「名字取得亂七八糟,反映那些人的想法也亂七八糟。有時我懷疑我這種人生過得亂七八糟的基因也是遺傳。」卻又隱然在自棄的情緒中流露出無法斬斷親緣的體悟。表妹志愛身為女性,對封建保守的家族從無好感,集體毒殺案發生後,她甚至覺得他們死了也不可惜,因為,「那些人包括雙親就算沒死,活下去也是行屍走肉,除了消費以外,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但她同樣清楚自己「一輩子不必出來工作的人生,是司武家賜與的。」他們的處境,就如同與司武家早已斷絕往來,卻因為案情重新被捲入家族糾葛,並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不得不積極參與查案的私家偵探志信形容的,是一個開放式監獄,囚友每個月都可以領到生活費,靈魂卻被禁錮著。
●家也可能如怪物般吞噬成員
在推理小說的框架下,血緣關係的感受與思考,並不只是感性的惆悵,更是務實的「誰會是加害者/受害者」之考量。外嫁的女兒不姓司武,卻同樣被納入謀殺名單,因為無論父系或母系,他們都擁有司武家的基因。但基因作為看似科學又可靠的線索,除了外貌上的相似特徵、隱藏的遺傳疾病,甚至志義形容的,性格與生活方式,足以作為辨識「一家人」的條件,那接受骨髓移植而擁有受贈者基因的人,也算是一家人嗎?當事者顯然並不這麼認為。於是,血緣、法律、同居,再加上「把事情變複雜」的科技,沒有一個能充分回答「什麼是家人?」這個問題。
對志愛和志信來說,更能給他們「家人」感受的,從來不是形同陌路的原生家庭。相較於親生父親,志愛覺得指導教授給她的關懷和啟發,更足以勝任父親這個角色,「即使教授是為天主教不容的同性戀者。誰說同性戀者不會給人父愛?」至於志信,更在警方質疑他「寧願陪狗也不去和家人共聚」時,理直氣壯地回覆:「家人的定義並不限於人,只要一起生活又有感情交流就是家人。我的狗當然是我家人,而且比姓司武的親近得多。」在釐清案情的過程中,這些司武家的成員們,無非也在澄清家與家人的定義。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可以視為家的地方」,但即使身處同一屋簷下,對家的樣貌也未必有共識。其中的歧異既受到世代觀念遞嬗的影響,自然也有個別差異。儘管司武這個姓氏是虛構的,圍村家族的處境即使對應在現實香港社會也屬少數,幾位司武家族成員對原生家庭的感受,卻足以讓我們看到姓氏作為「家」這個單位的辨識符號,可以是凝聚認同感的來源,也可能是「如怪物般吞噬成員」的深淵。原生家庭給予的是禮物還是負資產,儘管全憑運氣,但我們仍然擁有以自由意志去動搖無形禁錮的力量。如何找出那個可以視為家的所在,重新描摩自己心中家的形貌,或許才是小說留待讀者破譯的,真正謎團。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