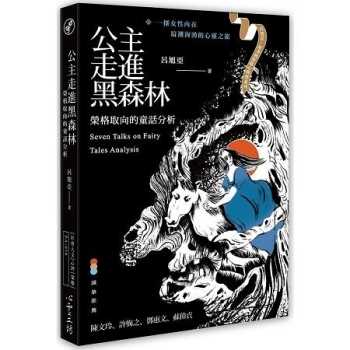1-1
第一章 榮格心理學的童話分析
現代人提起童話,多半認為它們是專屬於孩童的讀物,或是媽媽讀給小孩聽的床邊故事,似乎難登大雅之堂。就連「童話」這個詞彙也常作為帶有貶意的形容詞,像是:童話般的愛情、童話裡的生活,在這些句子裡,童話就是幼稚、不真實與不切實際的同義詞,但這也正意味著童話所反映的不是發生在意識層面,而是潛意識之內的歷程。
童話通常短短的,頂多兩、三頁,故事人物的性格也不像文學作品裡的角色那般複雜,許多童話的主人翁是沒有名字的,僅以他們的排行或地位稱呼他們為三公主、小女兒、王子,或根據穿著就被叫做「小紅帽」、「熊皮人」。故事情節也挺樣板的,總是從「很久很久以前」開場,以「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結尾,主角遇到的挑戰總是三次,三位武士、三把斧頭、三件任務.......了無新意。然而,正因為童話簡單、重複、古老並流傳久遠的特質,顯示出一種無歷史感、無地域限制的原始集體性,可以跨越文化而被喜愛。
本書以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所提出的心理學概念為內在座標,描述、比對、解構並反轉七個有關女性的童話故事,以此探索女性心靈發展的不同面向。
走進精靈、神話與夢的國度
童話的英文叫做 Fairy Tale,直譯就是「精靈的故事」。精靈的意象,是長著輕盈翅膀的小仙女,她們屬於夜晚與森林,和會說話的動物做朋友,飛過之處會留下閃閃金光,還擁有各種神奇的魔法。人類心靈深處,有著這樣一座魔幻原始森林,每當我們講起童話故事,彷彿就走進了精靈居住的世界,走進一個意識之外、潛藏著無數可能的領域。在潛意識的國度,童話與夢比鄰而居,它們都以象徵的方式、意象的語言傳達意識之外的訊息。深度心理學為了理解人的心靈而探索夢的世界,用分析意象的方法,企圖從夢中找到進入個人潛意識(unconscious)的途徑;榮格與其他分析心理學家們發現,研讀、分析、理解童話,可以為我們找到進入人類更深層的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方法,藉此認識心靈運作的模式與歷程,看見人類心靈的基本圖譜。此外,榮格認為童話與神話都是集體無意識中最原初的結構。神話受到起源地的影響,例如中國、印度與希臘的神話,明顯映照出在地族群創造發展的文化與歷史痕跡,而童話相對是自發的、天真的、沒有計畫的自然心靈產物,被特定文化歷史沾染的痕跡較少。此外,與神話相比,童話精簡短小許多,在文學裡的位置如同阿米巴原蟲之於生物界,以最簡單的形式描述集體心靈類單細胞般的存在樣貌,也就是所謂的原型。我們重返童話,所看重的,正是這條簡單、重複、古老與神祕的心靈之路,藉此途徑,開啟一扇集體無意識的原型之門,在其中學習陌生的語言,認識用意象說話的象徵世界,最後重拾自身創造象徵的能力,以便與自己內在無意識、那個「很久很久以前」的世界再度相遇。
與原型和情結相遇
榮格提出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學理論,把我們對心靈的視野從自己可以覺察的「我」的位置裡拉開,讓我們彷彿置身巨大浩瀚的宇宙,回頭看才明白,不僅地球如微塵,連太陽系也只是渺小的存在,而銀河深處,還有許許多多像太陽系這樣運行的星系。心靈銀河涵容數不清的星系,榮格稱它們為原型(archetypes),人類有多少種現象,世間就有多少種原型,換言之,每種生命現象都是一種原型。榮格認為原型就是集體無意識的結構,深埋在各種心靈的活動中,意識很難直接捕捉,通常只能從行為、圖像、藝術、宗教、夢或是神話與童話中窺得一斑。某些人在經驗無意識的集體能量時,會感覺自己被某種力量灌注、以致無比強大,它會讓人有如神般的全能感,無所不能,甚至有種承接天諭、非做什麼不可的自我膨脹。如果個人內在並沒有足夠強壯的心靈結構可以涵容,賦予原型能量適度的理解與判斷,強大的原型有時會讓個人陷入無自我、非理性的混亂與狂熱裡,這就像我們文化裡描述被附身的狀況,自我被原型擄獲,成為非我的原型工具,陷入沒有自我規範心靈能量的危險。儘管原型多到數不清,在榮格心理學中,主要常被討論的原型圖像有:自性(真我)、阿尼瑪、阿尼姆斯、陰影、父親、母親、老者、孩子、國王、王后、魔法師……等。每個人一生之中可以真正經驗或是認識到的原型只有幾個。榮格認為我們是透過個人的情結來經驗發自心靈深處的原型。情結浮游在個人意識與潛意識之間,是心靈的另一種結構,其中聚存了我們個人生命的歷史,這些個人的歷史檔案以不同的主題被歸納在一起,像是母親情結就保存了我們生活中許多重要的母性人物和經驗,大部分人的母親情結是以自己的母親作為情結的核心,圍繞著的才是其他生命中出現過的母性人物。情結之中不只有個人與家庭記憶,更重要的是儲存了相關的情感,他們會影響我們的情緒、行為與人際互動。
每個情結的核心都有個原型圖像,透過情結就成為我們覺察原型的一個路徑,當原型浮升,顯現出來的重要線索就是情結。當情結被引動時,我們會感覺情緒波動、不可自抑,身體充滿各式各樣的感受,憤怒、悲傷都變得無法控制。有位男性師長曾與我們分享他的個人經驗:這位高大英俊的白人男性曾有無法發展穩定情感關係的困境,他總是被大塊頭、大胸脯、能幹體力活的黑人女性所吸引,然後與她們產生一種拉扯衝突的激烈關係,在接受分析中,他找到與自己兩、三歲時相關的記憶,與照顧他的保母有關。他的保母很愛他,每天抱他、餵他、照顧他,當他不乖時,保母會生氣的用力打他的屁股。對他來說,保母就是早年最重要的女性經驗,他總是被類似大母神原型的女性所吸引,也著迷於類似的互動方式,而形成他情感慾望的主調。當他透過分析回到一切的起始,嘗試面對這個情結之後,類似的吸引仍然存在,但是力度卻降低了,這個母親情結不再像鬼魅般抓住他、驅動他,他變得比較自由,而他也找到他心中的女神最原初的樣貌,她們出現在人類最早的文明,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遺跡裡,泥塑的母親神有著巨大臀部和乳房,在他的情感裡,不只有他兩三歲的記憶,也有人類亙古的渴望。
榮格提到將情緒轉化為意象,並深掘出這些意象在個人歷史中的遺跡,使我們從向外尋找生命無法安適的理由,轉而聚焦於內在意象,是一種有強大效力的治療方法。這個認識情結以及其背後原型的治療方法,他親身體驗過,在自傳中他說:「只要我得以把各種情緒變成意象,也就是說找到隱藏在情緒之中的意象後,我就能再次平靜安心。倘若讓這些意象繼續藏在情緒背後,我可能已經被他們撕碎。......從我個人的實驗結果,以及從治療的角度來看,找到情緒背後的特定意象是極有幫助的。」(全文未完)8-1
第八章 爬出玻璃山:老頭倫克朗
女性的現代化議題
阿尼姆斯作為女性內在陽性質地的原型,它的心理動能的概念如果對應到中國文化,舉凡「陽」這個字所指涉的似乎都適用。它是太陽,日出的力量;它是能量,帶出發展與成長;它是行動,而且往往奠基于思考、組織與邏輯。
心靈原型的發展受到意識生活的影響。傳統社會不鼓勵女性讀書、投身公共領域,也不鼓勵女性發展個人事業,限縮了女性發展其自身的理性與行動力。這些女性進入中年,內在發展的渴望啟動時,有許多人會把自身的「陽」投入純知識性或者宗教靈性的團體,例如組讀書會、修一個學位、參加服務性社團、在教會服事、去廟裡修行或者擔任各式各樣的義工。儘管近代社會開放對女性求學與工作的機會與資源,但回顧歷史,如同提出「平庸的邪惡」的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一樣透過發展思想而成為重要思想家的女性仍屬少數。
榮格談女性內在的阿尼姆斯,討論的是思維與靈性、精神性向度。在榮格那個時代的女性,主要工作多在處理家務、照顧家人、維繫人際關係,是紮根於現實生活的功能。因此女性的陽性能量的發展,在中年之後顯現出來的樣貌就多為向上的超越性,通往精神性的路徑,而非現今社會裡的職場競爭或者權力競逐。
然而,職場競爭與權力競逐卻是許多女性此刻所處的生活現實。越來越多女性成為國家或地區領袖、跨國企業總裁,許多女性在過去被男性所壟斷的政治、社會、科技與文化版圖裡佔有一席之地。以前我們說「男主外、女主內」,但現在,家庭以外的世界,充滿了女性的身影,這些集權力與能力於一身的女性,她們的精神世界,陽性能量一定是非常活躍的,走出家門趕赴職場/沙場競逐的女戰士們,是否就是一群把內在陽性特質發展得很好的女性,這是一個需要探討的主題。現代職場上的女性,若要達到社會所認可的成就,內在的陽性能量必定是被高度激發,可是心靈長久處在這種激發的亢奮裡,很容易會疏離了內在的陰性質地。這個現象,正是二十一世紀女性心靈發展所遇到的獨特挑戰:在男性已然熟稔而女性才正要參與的權力遊戲裡,女性要怎樣才能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在童話〈白雪與紅玫瑰〉的故事(本書第七章)裡,談的是對於純粹女性的過度認同,一個完全不曾發展阿尼姆斯的女性,必須奮力掙脫,才能打破長久以來主流文化對於女性認同所塑造的單一樣貌,完成個人內在的發展歷程,而這個篇章我們要聚焦的是女性在自我發展上,如何與內在的阿尼姆斯或外在世界的男性形成平衡與和諧的關係,乃至最後達到自我整合。
認識原型
〈老頭倫克朗〉被收在第六版的《格林童話》裡,是一個源自德國北邊,用當地方言講述,透過口語流傳下來的故事,被轉譯成文本時有其難度,所以我們可能讀到好幾個不同的版本。這是個簡單的故事,場景很少,只有兩幕。故事發生在兩個世界之間,從地上世界移動到地下世界,在地下世界停留、經歷,然後回來。它具備許多童話故事共有的老套元素,而這些熟悉的元素就是值得審視的心靈原型。
閱讀這些古老的故事不是為了找到新鮮的創意表現,而是為了對這些具備原型力量的象徵增加熟悉、豐富對象徵的感受、打開對象徵的想法。如此一來,我們就開始養成一些能力,藉由象徵的力量,脫開既是個別性又是集體性的侷限。對童話的理解,必須有個人性的參與才能產生意義,也就是從故事情節連結到個人的生命經驗、歷史,以及自我所認知的世界。
但童話還提供另外一種同時並存的,我們姑且先稱之為「老套」的閱讀體驗。因為讀過這類故事跟這類情節多次之後,人人都開始體會到存在於老套裡的某種恆常與永恆,好比某個角色又做了同樣的蠢事,某個角色又掉進同樣的地洞。當我們一次又一次在心裡喊叫「啊,又是這樣!」就是代表自己一次又一次覺察同樣的原型和故事母題,童話故事對於我們之所以有意義,不是故事寫得多麼奇巧,而是讓我們有機會捕捉存在於這種古老形式裡面的永恆,看出我們與原型以及其象徵意義之間的關係,透過詮釋,擁有屬於自己個人或者這個時代的新的意涵。許多家有幼兒的父母會有這樣的經驗,為小朋友說床邊故事時,一模一樣的故事,爸媽講煩了,孩子還要一再的聽和講。我認為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心靈狀態,由於孩子內在還沒有一個清楚的「我」出現,他們可以反覆浸泡在原型的世界裏面,不斷享用故事裡的古老永恆,而我們成年人,大多已經離那個世界非常遙遠了。(全文未完)
第一章 榮格心理學的童話分析
現代人提起童話,多半認為它們是專屬於孩童的讀物,或是媽媽讀給小孩聽的床邊故事,似乎難登大雅之堂。就連「童話」這個詞彙也常作為帶有貶意的形容詞,像是:童話般的愛情、童話裡的生活,在這些句子裡,童話就是幼稚、不真實與不切實際的同義詞,但這也正意味著童話所反映的不是發生在意識層面,而是潛意識之內的歷程。
童話通常短短的,頂多兩、三頁,故事人物的性格也不像文學作品裡的角色那般複雜,許多童話的主人翁是沒有名字的,僅以他們的排行或地位稱呼他們為三公主、小女兒、王子,或根據穿著就被叫做「小紅帽」、「熊皮人」。故事情節也挺樣板的,總是從「很久很久以前」開場,以「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結尾,主角遇到的挑戰總是三次,三位武士、三把斧頭、三件任務.......了無新意。然而,正因為童話簡單、重複、古老並流傳久遠的特質,顯示出一種無歷史感、無地域限制的原始集體性,可以跨越文化而被喜愛。
本書以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所提出的心理學概念為內在座標,描述、比對、解構並反轉七個有關女性的童話故事,以此探索女性心靈發展的不同面向。
走進精靈、神話與夢的國度
童話的英文叫做 Fairy Tale,直譯就是「精靈的故事」。精靈的意象,是長著輕盈翅膀的小仙女,她們屬於夜晚與森林,和會說話的動物做朋友,飛過之處會留下閃閃金光,還擁有各種神奇的魔法。人類心靈深處,有著這樣一座魔幻原始森林,每當我們講起童話故事,彷彿就走進了精靈居住的世界,走進一個意識之外、潛藏著無數可能的領域。在潛意識的國度,童話與夢比鄰而居,它們都以象徵的方式、意象的語言傳達意識之外的訊息。深度心理學為了理解人的心靈而探索夢的世界,用分析意象的方法,企圖從夢中找到進入個人潛意識(unconscious)的途徑;榮格與其他分析心理學家們發現,研讀、分析、理解童話,可以為我們找到進入人類更深層的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方法,藉此認識心靈運作的模式與歷程,看見人類心靈的基本圖譜。此外,榮格認為童話與神話都是集體無意識中最原初的結構。神話受到起源地的影響,例如中國、印度與希臘的神話,明顯映照出在地族群創造發展的文化與歷史痕跡,而童話相對是自發的、天真的、沒有計畫的自然心靈產物,被特定文化歷史沾染的痕跡較少。此外,與神話相比,童話精簡短小許多,在文學裡的位置如同阿米巴原蟲之於生物界,以最簡單的形式描述集體心靈類單細胞般的存在樣貌,也就是所謂的原型。我們重返童話,所看重的,正是這條簡單、重複、古老與神祕的心靈之路,藉此途徑,開啟一扇集體無意識的原型之門,在其中學習陌生的語言,認識用意象說話的象徵世界,最後重拾自身創造象徵的能力,以便與自己內在無意識、那個「很久很久以前」的世界再度相遇。
與原型和情結相遇
榮格提出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學理論,把我們對心靈的視野從自己可以覺察的「我」的位置裡拉開,讓我們彷彿置身巨大浩瀚的宇宙,回頭看才明白,不僅地球如微塵,連太陽系也只是渺小的存在,而銀河深處,還有許許多多像太陽系這樣運行的星系。心靈銀河涵容數不清的星系,榮格稱它們為原型(archetypes),人類有多少種現象,世間就有多少種原型,換言之,每種生命現象都是一種原型。榮格認為原型就是集體無意識的結構,深埋在各種心靈的活動中,意識很難直接捕捉,通常只能從行為、圖像、藝術、宗教、夢或是神話與童話中窺得一斑。某些人在經驗無意識的集體能量時,會感覺自己被某種力量灌注、以致無比強大,它會讓人有如神般的全能感,無所不能,甚至有種承接天諭、非做什麼不可的自我膨脹。如果個人內在並沒有足夠強壯的心靈結構可以涵容,賦予原型能量適度的理解與判斷,強大的原型有時會讓個人陷入無自我、非理性的混亂與狂熱裡,這就像我們文化裡描述被附身的狀況,自我被原型擄獲,成為非我的原型工具,陷入沒有自我規範心靈能量的危險。儘管原型多到數不清,在榮格心理學中,主要常被討論的原型圖像有:自性(真我)、阿尼瑪、阿尼姆斯、陰影、父親、母親、老者、孩子、國王、王后、魔法師……等。每個人一生之中可以真正經驗或是認識到的原型只有幾個。榮格認為我們是透過個人的情結來經驗發自心靈深處的原型。情結浮游在個人意識與潛意識之間,是心靈的另一種結構,其中聚存了我們個人生命的歷史,這些個人的歷史檔案以不同的主題被歸納在一起,像是母親情結就保存了我們生活中許多重要的母性人物和經驗,大部分人的母親情結是以自己的母親作為情結的核心,圍繞著的才是其他生命中出現過的母性人物。情結之中不只有個人與家庭記憶,更重要的是儲存了相關的情感,他們會影響我們的情緒、行為與人際互動。
每個情結的核心都有個原型圖像,透過情結就成為我們覺察原型的一個路徑,當原型浮升,顯現出來的重要線索就是情結。當情結被引動時,我們會感覺情緒波動、不可自抑,身體充滿各式各樣的感受,憤怒、悲傷都變得無法控制。有位男性師長曾與我們分享他的個人經驗:這位高大英俊的白人男性曾有無法發展穩定情感關係的困境,他總是被大塊頭、大胸脯、能幹體力活的黑人女性所吸引,然後與她們產生一種拉扯衝突的激烈關係,在接受分析中,他找到與自己兩、三歲時相關的記憶,與照顧他的保母有關。他的保母很愛他,每天抱他、餵他、照顧他,當他不乖時,保母會生氣的用力打他的屁股。對他來說,保母就是早年最重要的女性經驗,他總是被類似大母神原型的女性所吸引,也著迷於類似的互動方式,而形成他情感慾望的主調。當他透過分析回到一切的起始,嘗試面對這個情結之後,類似的吸引仍然存在,但是力度卻降低了,這個母親情結不再像鬼魅般抓住他、驅動他,他變得比較自由,而他也找到他心中的女神最原初的樣貌,她們出現在人類最早的文明,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遺跡裡,泥塑的母親神有著巨大臀部和乳房,在他的情感裡,不只有他兩三歲的記憶,也有人類亙古的渴望。
榮格提到將情緒轉化為意象,並深掘出這些意象在個人歷史中的遺跡,使我們從向外尋找生命無法安適的理由,轉而聚焦於內在意象,是一種有強大效力的治療方法。這個認識情結以及其背後原型的治療方法,他親身體驗過,在自傳中他說:「只要我得以把各種情緒變成意象,也就是說找到隱藏在情緒之中的意象後,我就能再次平靜安心。倘若讓這些意象繼續藏在情緒背後,我可能已經被他們撕碎。......從我個人的實驗結果,以及從治療的角度來看,找到情緒背後的特定意象是極有幫助的。」(全文未完)8-1
第八章 爬出玻璃山:老頭倫克朗
女性的現代化議題
阿尼姆斯作為女性內在陽性質地的原型,它的心理動能的概念如果對應到中國文化,舉凡「陽」這個字所指涉的似乎都適用。它是太陽,日出的力量;它是能量,帶出發展與成長;它是行動,而且往往奠基于思考、組織與邏輯。
心靈原型的發展受到意識生活的影響。傳統社會不鼓勵女性讀書、投身公共領域,也不鼓勵女性發展個人事業,限縮了女性發展其自身的理性與行動力。這些女性進入中年,內在發展的渴望啟動時,有許多人會把自身的「陽」投入純知識性或者宗教靈性的團體,例如組讀書會、修一個學位、參加服務性社團、在教會服事、去廟裡修行或者擔任各式各樣的義工。儘管近代社會開放對女性求學與工作的機會與資源,但回顧歷史,如同提出「平庸的邪惡」的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一樣透過發展思想而成為重要思想家的女性仍屬少數。
榮格談女性內在的阿尼姆斯,討論的是思維與靈性、精神性向度。在榮格那個時代的女性,主要工作多在處理家務、照顧家人、維繫人際關係,是紮根於現實生活的功能。因此女性的陽性能量的發展,在中年之後顯現出來的樣貌就多為向上的超越性,通往精神性的路徑,而非現今社會裡的職場競爭或者權力競逐。
然而,職場競爭與權力競逐卻是許多女性此刻所處的生活現實。越來越多女性成為國家或地區領袖、跨國企業總裁,許多女性在過去被男性所壟斷的政治、社會、科技與文化版圖裡佔有一席之地。以前我們說「男主外、女主內」,但現在,家庭以外的世界,充滿了女性的身影,這些集權力與能力於一身的女性,她們的精神世界,陽性能量一定是非常活躍的,走出家門趕赴職場/沙場競逐的女戰士們,是否就是一群把內在陽性特質發展得很好的女性,這是一個需要探討的主題。現代職場上的女性,若要達到社會所認可的成就,內在的陽性能量必定是被高度激發,可是心靈長久處在這種激發的亢奮裡,很容易會疏離了內在的陰性質地。這個現象,正是二十一世紀女性心靈發展所遇到的獨特挑戰:在男性已然熟稔而女性才正要參與的權力遊戲裡,女性要怎樣才能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在童話〈白雪與紅玫瑰〉的故事(本書第七章)裡,談的是對於純粹女性的過度認同,一個完全不曾發展阿尼姆斯的女性,必須奮力掙脫,才能打破長久以來主流文化對於女性認同所塑造的單一樣貌,完成個人內在的發展歷程,而這個篇章我們要聚焦的是女性在自我發展上,如何與內在的阿尼姆斯或外在世界的男性形成平衡與和諧的關係,乃至最後達到自我整合。
認識原型
〈老頭倫克朗〉被收在第六版的《格林童話》裡,是一個源自德國北邊,用當地方言講述,透過口語流傳下來的故事,被轉譯成文本時有其難度,所以我們可能讀到好幾個不同的版本。這是個簡單的故事,場景很少,只有兩幕。故事發生在兩個世界之間,從地上世界移動到地下世界,在地下世界停留、經歷,然後回來。它具備許多童話故事共有的老套元素,而這些熟悉的元素就是值得審視的心靈原型。
閱讀這些古老的故事不是為了找到新鮮的創意表現,而是為了對這些具備原型力量的象徵增加熟悉、豐富對象徵的感受、打開對象徵的想法。如此一來,我們就開始養成一些能力,藉由象徵的力量,脫開既是個別性又是集體性的侷限。對童話的理解,必須有個人性的參與才能產生意義,也就是從故事情節連結到個人的生命經驗、歷史,以及自我所認知的世界。
但童話還提供另外一種同時並存的,我們姑且先稱之為「老套」的閱讀體驗。因為讀過這類故事跟這類情節多次之後,人人都開始體會到存在於老套裡的某種恆常與永恆,好比某個角色又做了同樣的蠢事,某個角色又掉進同樣的地洞。當我們一次又一次在心裡喊叫「啊,又是這樣!」就是代表自己一次又一次覺察同樣的原型和故事母題,童話故事對於我們之所以有意義,不是故事寫得多麼奇巧,而是讓我們有機會捕捉存在於這種古老形式裡面的永恆,看出我們與原型以及其象徵意義之間的關係,透過詮釋,擁有屬於自己個人或者這個時代的新的意涵。許多家有幼兒的父母會有這樣的經驗,為小朋友說床邊故事時,一模一樣的故事,爸媽講煩了,孩子還要一再的聽和講。我認為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心靈狀態,由於孩子內在還沒有一個清楚的「我」出現,他們可以反覆浸泡在原型的世界裏面,不斷享用故事裡的古老永恆,而我們成年人,大多已經離那個世界非常遙遠了。(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