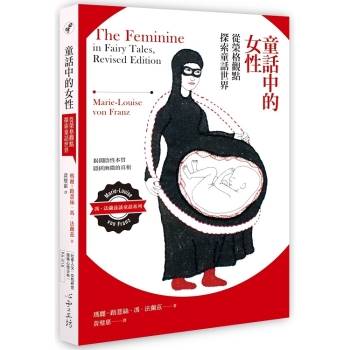當代西方女性似乎在尋求足以界定自我認同的意象,這種追尋的動機,來自於現代女性的迷惘以及深層不確定感。正如榮格所指出的,西方世界這種不確定感是因為在基督宗教中,女性缺乏形上學的典範所致。新教教義必須接受這樣的責難:它是純男性的宗教。天主教至少還有聖母瑪利亞(Virgin Mary)作為女性原型的(archetypal)代表,但是這種女性原型的意象仍不完整,因為她只包含了神聖女性原則當中崇高和光明的那一面,無法表達完整的女性原則。我在研究童話時,偶然首次發現其中的女性形象對我而言似乎能彌補這種缺憾。童話表現了鄉野中教育程度較低的村民,所擁有的創造性想像。童話的優勢是質樸的(非文學性或修飾過的),並且是在集體中經洗鍊,未曾被個人問題所混淆的純粹原型素材。在十七世紀之前,對童話感興趣的都是成人,童話被放在育兒的位置是後來才有的發展,這可能和西方文化排斥非理性並強調理性觀點有關,導致童話被認為是沒有意義的,這種荒誕故事只適合兒童閱讀而已。一直到今天我們才重新發現,童話具有深廣的心理學價值。
童話中的女性形象
如果我們想尋找人類行為中的女性原型模式,馬上會被一個問題給困住,那就是:童話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很可能是男性塑造出來的,因此並不能代表女人心中的女性特質概念,反而是代表榮格所稱的阿尼瑪(Anima)——也就是男性心中的女性特質。最近有些研究聚焦在「說故事者是誰」這個問題上,這些研究顯示故事的敘述者有時候是男性有時候是女性,因此故事的創始者也可能是如此。即使整個童話故事都圍繞著一個女主角,也很難證明那個故事是和女性心理學有關。許多有關女人受苦的長篇故事都是男人寫的,也因此存在著男性阿尼瑪問題的投射。尤其是那些女性屢遭拒絕的母題,她們必須經歷很長的受苦歷程才能夠找到適合的新郎,例如在阿普留斯(Apuleius)《金驢記》(Golden Ass)中的〈丘比德與賽姬〉(Amor and Psyche)。在古代不同的靈知教派(gnostic)教示中也出現了蘇菲亞(Sophia)這樣的人物,她是神聖智慧的女性化身,許多神奇的故事都是關於她的敘述:她是首神(Godhead)最小的女兒,想要認識名為深淵(Abyss)的未知天父,卻因這個大膽的願望而捲入眾多麻煩與苦難當中,墮入物質世界而後懇求救贖。這種蘇菲亞墮入物質世界的主題不只出現在近古,也出現在猶太教卡巴拉(Jewish kabbalistic)傳統中失傳的女性神性「舍姬娜」(Shekhinah)觀念中。這些宗教著作的作者都是男性,因此我們可以說蘇菲亞這個角色代表了男性阿尼瑪的某些面向,而在其他時候我們也可以說這個角色同樣代表了女性的心理學。如果我們想要關注女性心理學和阿尼瑪心理學這兩者如何互相交織在一起,問題多少就變得有點複雜。
現實中的女人對男性的阿尼瑪會有影響,而男性心中的阿尼瑪也會對現實存在的女人造成影響。女性對男性的愛欲(eros)具有教育及轉化的影響力,尤其是對從事許多智性活動的男性,因為他們的愛欲多少都有混亂或未分化的傾向。當先生拖著疲累的身子回家,看完報紙後就去睡覺(如果他是個瑞士人的話尤其如此),他並不認為需要對太太展現任何的情感,也看不見這個女性的個人及她的需求。對此,女性就可以發揮轉化的效用了,如果她可以挺身為自己的權利說話而不要展現阿尼姆斯(Animus),並且如果她和自己所愛的男人關係良好的話,就可以告訴他有關女性心理的事情,幫助他區分自己的情感。因為男性的阿尼瑪會帶有他母親的許多特質,那是他的第一個女性經驗。一般而言,對於男性與其愛欲功能關係的形成與建構,女性具有很強的影響力。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女性受到男性阿尼瑪投射的影響也很深。例如,當女性表現出某些特定行為時,她們很快就會注意到男性混亂或震驚的反應,因為這些行為並不符合他的阿尼瑪形象。即便是很小的女孩也會發現,如果她們扮演父親的阿尼瑪,把手臂環繞著他的脖子等等,她們就可以從父親那裡得到許多自己想要的東西。爸爸的女兒們會把媽媽推到一邊,因為媽媽總是嚴格要求指甲乾淨並乖乖上學。她們會用一種迷人的方式叫著爹地,於是爸爸就落入圈套了。她們就是這樣經由調適自己而學會如何使用男性的阿尼瑪。習慣以這種方式表現的女性,我們稱之為「阿尼瑪女性」(anima woman)。這種女性只是單純地扮演著自己當下中意的男性所暗示給她的角色而已,她們對於自己的知覺僅止於作為男性反應的鏡映。她們的愛人會讚揚她們有多麼美好,但如果她們身邊沒有男人的話,她們就會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不是。只有透過男人對她們的反應,才會讓她們覺察到自己的女性人格。
因此有些女性把自己完全置身於阿尼瑪的投射當中。我認識一位女性,她的腳很纖細,但是她先生卻喜歡她穿著高跟鞋。雖然醫生告訴她不應該這麼做,但她還是穿著高跟鞋來折磨自己。像這樣的女性她們會害怕失去先生的寵愛,於是如果先生只喜歡她作為一個阿尼瑪人物,她就被迫要扮演那個阿尼瑪角色。這樣的互動可好可壞,但是女人就會深受男性阿尼瑪角色的影響。這個現象將我們帶到一個既原始、簡單但卻是集體性的層次上,使我們無法將阿尼瑪的特質和真正的女性區分開來,因為這兩者經常混在一起,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彼此相互作用的。
如同我先前提過的,在基督教文明中女性意象的代表並不完整;如同榮格曾經說過,「她」在上議會(Upper Parliament)並沒有代表。我們可以說阿尼瑪是受到忽視的,而真實的女人對於她的存在、她的本質、她是什麼、或她可以成為什麼並不確定。因此她或者退化到一種原始的本能模式並緊守不放,以保護自己免受文明加諸在她身上的投射;或者就落入阿尼姆斯之中,建構出她自己的一種圖像以彌補內在的不確定感。在像南印度一樣的母系社會結構中,女人對於自己的女性氣質具有自然的信心。她們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也知道自己以特殊的方式有別於男人,但這並不隱含任何的自卑。因此她們可以展現自己人性的存在,並以自然的方式生活著。
在原始的層次上,真實女性的意象和男性阿尼瑪的意象,或多或少是同一種東西,而且,人類的文明正在經歷某種緩慢而循環的轉換歷程,大約得要三百到四百年。這種緩慢的發展運動極可能是成千上萬個別反應的總和,或許是由許多女性被拒絕和不被欣賞的痛苦經驗所組成,並在暗地裡醞釀,經過幾世紀之後浮上台面,使得二十世紀初的集體女性解放爆發成為一種運動引起人們的注意。
於是我們就以這樣的兩難情境揭開序幕:童話故事中的女性人物既不是阿尼瑪模型,也不是真實的女人,而是兩者兼具,因為有時候是前者,有時候又是後者。而且有些童話故事闡述真實的女性多一點,有些則說明男性的阿尼瑪多一點,端視最後一位寫故事的人的性別而有差異,這樣的猜測是很公允的。我有一位朋友在學校裡擔任繪畫老師,有一次上課時,他以童話故事〈忠實的約翰〉(Faithful John)為主題,要學生從中選擇一個場景來作畫。在我看來,那個故事鏡映的是男性的心理學,其中只有一個蒼白的阿尼瑪角色而已。這位老師把這個故事給了男女合班的學生,讓他們自由挑選任何場景作畫。所有的小孩都充滿熱情,男孩們自然而然就選擇了英雄和戲劇性的場景,而女孩們則挑選了故事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她們認同那個女性角色就如同男孩們認同那些男性角色一樣,因此他們所畫出來的圖畫,就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故事面貌。
由此可見,依照重述故事者的性別,就會強調出不同的特質。於是我們可以如此假設:在某些童話故事中,女性的造型有較大的影響力,有些則是男性造型影響較多,但我們永遠都無法確定其中女性角色所代表的是女人或者是阿尼瑪。比較好的辦法是同時以這兩種角度去詮釋童話,那我們就會看到有些童話從女性的角度去詮釋時會得到很豐富的素材,但若從男性的角度去詮釋時,卻似乎並沒有那麼發人深省。有了這樣的印象之後,我選擇了幾則可以由女性角度詮釋的格林童話,但是我並不能說它們和阿尼瑪的問題毫無關連。
童話乃集體無意識的補償
至於故事當中的角色,一般都會說神話是神的故事,而童話是凡人的故事,亦即在童話中的英雄和參與者是凡人,在神話中的則是神和半神;但我卻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這種理論的問題在於,有些童話故事中的人名指的是神。例如在我即將討論的〈睡美人〉(The Sleeping Beauty)或〈野玫瑰〉(Briar Rose)故事的許多版本中,小孩被稱為太陽和月亮。那麼,太陽和月亮的媽媽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你可以稱它是一種象徵。若小孩被稱為太陽和月亮,或在其他版本中叫做清晨與黃昏,那麼你就知道這講的是神的國度了。因此你無法根據這種差異來建立一種理論。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知道他們是原型人物,當我們用人類的心理學來理解他們時,我們知道在本質上他們和凡人及人類人格並沒有任何關係。因此我會假設童話故事和神話並沒有什麼差別,但他們都和原型人物有關。
如果我們真的想對這個概念有所感覺的話,我們就必須問問自己,為什麼人們在敘說故事時,有時候會使用自己國家宗教所崇拜的神祇之名、以其集體表徵(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來命名故事人物,而在其他故事中卻不這麼做。這兩者的差異和歷史性的因素有關,在此我無法進一步討論它。我們姑且這樣假設:人們可以利用夢境和醒著時的幻象,將自己無意識中的人物投射到虛空之中,並且也能夠討論這些人物。
我有一個非常單純的女性個案,她是個木匠的女兒,在原始的鄉間長大,生活非常貧窮。她就算不是個真正的思覺失調症患者,也是個嚴重的邊緣型思覺失調個案。她有最令人驚奇的聲音、幻象、夢境以及原型的素材,雖然她去學做美髮師,但卻因為有許多幻想而無法繼續下去,只好去做一名清潔工,但又因為她很容易與人爭吵,既有點瘋狂又難以相處,因此必須等到四下無人的時候才可以開始清理空曠的公司。她已經被丟棄到人類社會的邊緣地帶,但她卻是個很有宗教信仰的人,除了被自己的幻象所吞噬而不具外在功能之外,她甚至可以和德國天主教神祕主義者德雷絲.馮.科內爾斯羅伊特(Teresa von Konnersreuth)相比。她曾想與我進一步接觸,但在分析的前60 分鐘卻毫無進展,因為她的自我情結過於脆弱。起先,她必須對場地和我產生感覺,然後她說她沒有辦法馬上談論像上帝這樣的主題。我想那也的確是,因為她的情況是需要有親密感和友誼才能夠分享一個天大的祕密,於是對這個特殊的個案我同意不要那麼常見面,並可以挪出整個下午見她。我們也不在諮商室會面,而是會去小酒館一起喝點飲料,或是到別處去。她有時都不說話,或是講了一個半鐘頭盡是說些無關緊要的話題,讓我非常精神耗竭。通常我要不是開始緊張地看著手錶,要不就是告訴她我必須在七點前回去,好將她拉回現實。然後她才突然開始談她的內在經驗,就像突然跳進夢境,而且當它是真的一樣。為了加強她的意識面好讓她從原型世界出來,我會對她說:「對啊!但那只是一個夢。」對此她總是表示贊同沒有太感困惑,但我注意到她隨後就無法再進行下去了,因為她就像個藝術家在工作時被打斷一樣受到了干擾。如果你的藝術靈感正在萌芽,新的靈感正傾洩而出,卻遭到這種阻斷的話,你就會像殘廢一樣的失去線索。剛湧出來的創造性靈感必須不被打擾,特別是當這些靈感還沒有確實成形之前,人們不該去談論它,因為它們就像新生兒一樣的脆弱。
具有創造力的人們通常都很容易受到干擾,我在這個女人身上也注意到同樣的情形。因此我通常都把我的評論留到最後,在那時候我想我應該有幫助她更接近現實了,因此就順著童話的模式,在故事最後通常會有個評語把你從故事情境中踢出來——但那也只在最後才會出現。
那個女人告訴我最不可思議的原型故事,而且把它們當成真的一樣看待,而就在這當下(in fl agranti),就有一個童話故事可能的起源案例了。因為有人告訴你一個經典的文學戲劇故事,並在最後評論說那只是個夢境!像這樣的案例,一開始時敘述者是完全認同故事本身的,但在重新敘述故事的過程中,故事就改變了,其中個人的主題也被排除了。故事最後的評論很可能是這樣:「公雞啼叫咕─咕咕─咕─黎明到了,而我的故事也結束了。」因為該是醒來的時候了!公雞啼叫的時候,就是你該起床的時候了。或者,他也可能這麼說:「有一個美好的婚禮和豐盛的晚宴,但我在廚房裡卻什麼也沒得到,因為廚子一腳把我踢醒,於是我站在這裡告訴你這個故事。」也就是說他飛回現實世界中了。換成吉普賽人的說法:「他們結了婚,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但我們是窮鬼,正飢餓地吸吮自己的牙齒。」接著他們又繼續討錢去了。
如此一來,聽故事的人就知道童話並不是一件普通人的真實事件,他們會很清楚地知道故事裡的人事是發生在另一個場域,是我們稱之為無意識(unconscious)的領域。他們會覺得那是屬於另外一個世界,並且和我們意識中的現實有很大的差異。人們以這種方式在非常原始的層次上和無意識有一種切換式的接觸。場景的切換並沒有明確的界線,強調的反而是感覺層次。童話故事真正告訴我們的是無意識中的人物,他們屬於另外一個世界。我們可以說神話中的人物和宗教上的神會互相混淆,因為他們都符合了法國人類學家呂西安‧列維.布魯爾(Lucien Lévy-Bruhl)所稱的集體表徵,但童話恰恰相反,童話是會遷移的,也不能連結到國族的集體意識,它含有大量補償性的素材,並且通常和集體的意識觀念相衝突或者互補。
我那位思覺失調的清潔女工有時候會帶來充滿了基督教傳統的夢境,例如天父會出現並對她說話,隨後出現的事情就和她在基督教教育中所學相符。要稱呼一個人物為天父,而稱另外一個為聖靈(Holy Ghost),這對她而言並不太困難。有一次她的幻境中出現一位俊美男子,那時她在山上,而他就站在她身邊,有個聲音說:「妳必須把這漆成綠色以救贖自己和人類。」她說她做不到,那聲音說:「我會幫助妳。」她後來似乎不知怎樣就完成了任務,因而被准許從山上下來。下一幕是她在一個旅館中醒了過來。我問那是誰的聲音,她說那是聖靈。雖然那個聲音並不符合,但是那個俊男卻符合集體表徵中的聖靈形象,她也毫不費力地就指認出來了。
若在另外一個宗教系統,那個人物可能會得到不一樣的名字。如果出現一個人物卻不符合集體表徵,或是如果什麼稱呼都無法符合這個人物時,你就只得說有某件事發生了,它似乎像什麼跟什麼,但你無法將它置於任何一個集體觀念上。假設有個這樣的經驗,例如有個女神擁有所有大地之母的特質,但卻像古希臘時期的包玻(Baubo)女神一樣的放肆性感。如果你從小在天主教家庭長大,你不能稱這個人物是聖母瑪利亞,但既然那是你唯一擁有的女性神聖人物代表,你就只能稱這位為大母神(Mother),或者給她一個怪誕的名字,像是長青小母(Little Mother Evergreen)之類的。但是那並不是一個正式的名字,我們也不會用宗教的態度去崇拜這個人物。童話故事就是以這種方式產生的,很多時候都是建立在這種內在經驗之上,它們並不那麼符合集體表徵,因此童話人物通常沒有名字,或是使用很古老的名字,而不會用宗教性的象徵或已知宗教系統中的名諱。他們比神話提供更多關於無意識正在進行的補償功能訊息。這種在集體表徵中沒有被表達出來,但在某種集體層面又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東西呢?我們可以從這一點得到有價值的訊息,因為童話故事也會採用正式的名字並敘述關於宗教人物的卑劣行徑。有一個國家流傳著不少關於耶穌基督的故事,他的行為蠻橫,例如他和聖彼得四處閒逛,害得他被旅館主人毆打,因為聖彼得總是過於天真,自然就成了那個挨打的人。捷克斯拉夫還有這麼一則童話:一名無助的老人坐在樹上,需要人幫忙攙扶才能從樹上下來,在故事最後,竟然說那個緊張無助的老男人,正是上帝本人。你能想像上帝本人是個無助的老男人無法從樹上爬下來嗎?但是故事裡有個心地善良的小女孩必須幫助他從樹上下來,這對我們既存的上帝概念就是很有用的補償作用。
童話中的女性形象
如果我們想尋找人類行為中的女性原型模式,馬上會被一個問題給困住,那就是:童話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很可能是男性塑造出來的,因此並不能代表女人心中的女性特質概念,反而是代表榮格所稱的阿尼瑪(Anima)——也就是男性心中的女性特質。最近有些研究聚焦在「說故事者是誰」這個問題上,這些研究顯示故事的敘述者有時候是男性有時候是女性,因此故事的創始者也可能是如此。即使整個童話故事都圍繞著一個女主角,也很難證明那個故事是和女性心理學有關。許多有關女人受苦的長篇故事都是男人寫的,也因此存在著男性阿尼瑪問題的投射。尤其是那些女性屢遭拒絕的母題,她們必須經歷很長的受苦歷程才能夠找到適合的新郎,例如在阿普留斯(Apuleius)《金驢記》(Golden Ass)中的〈丘比德與賽姬〉(Amor and Psyche)。在古代不同的靈知教派(gnostic)教示中也出現了蘇菲亞(Sophia)這樣的人物,她是神聖智慧的女性化身,許多神奇的故事都是關於她的敘述:她是首神(Godhead)最小的女兒,想要認識名為深淵(Abyss)的未知天父,卻因這個大膽的願望而捲入眾多麻煩與苦難當中,墮入物質世界而後懇求救贖。這種蘇菲亞墮入物質世界的主題不只出現在近古,也出現在猶太教卡巴拉(Jewish kabbalistic)傳統中失傳的女性神性「舍姬娜」(Shekhinah)觀念中。這些宗教著作的作者都是男性,因此我們可以說蘇菲亞這個角色代表了男性阿尼瑪的某些面向,而在其他時候我們也可以說這個角色同樣代表了女性的心理學。如果我們想要關注女性心理學和阿尼瑪心理學這兩者如何互相交織在一起,問題多少就變得有點複雜。
現實中的女人對男性的阿尼瑪會有影響,而男性心中的阿尼瑪也會對現實存在的女人造成影響。女性對男性的愛欲(eros)具有教育及轉化的影響力,尤其是對從事許多智性活動的男性,因為他們的愛欲多少都有混亂或未分化的傾向。當先生拖著疲累的身子回家,看完報紙後就去睡覺(如果他是個瑞士人的話尤其如此),他並不認為需要對太太展現任何的情感,也看不見這個女性的個人及她的需求。對此,女性就可以發揮轉化的效用了,如果她可以挺身為自己的權利說話而不要展現阿尼姆斯(Animus),並且如果她和自己所愛的男人關係良好的話,就可以告訴他有關女性心理的事情,幫助他區分自己的情感。因為男性的阿尼瑪會帶有他母親的許多特質,那是他的第一個女性經驗。一般而言,對於男性與其愛欲功能關係的形成與建構,女性具有很強的影響力。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女性受到男性阿尼瑪投射的影響也很深。例如,當女性表現出某些特定行為時,她們很快就會注意到男性混亂或震驚的反應,因為這些行為並不符合他的阿尼瑪形象。即便是很小的女孩也會發現,如果她們扮演父親的阿尼瑪,把手臂環繞著他的脖子等等,她們就可以從父親那裡得到許多自己想要的東西。爸爸的女兒們會把媽媽推到一邊,因為媽媽總是嚴格要求指甲乾淨並乖乖上學。她們會用一種迷人的方式叫著爹地,於是爸爸就落入圈套了。她們就是這樣經由調適自己而學會如何使用男性的阿尼瑪。習慣以這種方式表現的女性,我們稱之為「阿尼瑪女性」(anima woman)。這種女性只是單純地扮演著自己當下中意的男性所暗示給她的角色而已,她們對於自己的知覺僅止於作為男性反應的鏡映。她們的愛人會讚揚她們有多麼美好,但如果她們身邊沒有男人的話,她們就會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不是。只有透過男人對她們的反應,才會讓她們覺察到自己的女性人格。
因此有些女性把自己完全置身於阿尼瑪的投射當中。我認識一位女性,她的腳很纖細,但是她先生卻喜歡她穿著高跟鞋。雖然醫生告訴她不應該這麼做,但她還是穿著高跟鞋來折磨自己。像這樣的女性她們會害怕失去先生的寵愛,於是如果先生只喜歡她作為一個阿尼瑪人物,她就被迫要扮演那個阿尼瑪角色。這樣的互動可好可壞,但是女人就會深受男性阿尼瑪角色的影響。這個現象將我們帶到一個既原始、簡單但卻是集體性的層次上,使我們無法將阿尼瑪的特質和真正的女性區分開來,因為這兩者經常混在一起,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彼此相互作用的。
如同我先前提過的,在基督教文明中女性意象的代表並不完整;如同榮格曾經說過,「她」在上議會(Upper Parliament)並沒有代表。我們可以說阿尼瑪是受到忽視的,而真實的女人對於她的存在、她的本質、她是什麼、或她可以成為什麼並不確定。因此她或者退化到一種原始的本能模式並緊守不放,以保護自己免受文明加諸在她身上的投射;或者就落入阿尼姆斯之中,建構出她自己的一種圖像以彌補內在的不確定感。在像南印度一樣的母系社會結構中,女人對於自己的女性氣質具有自然的信心。她們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也知道自己以特殊的方式有別於男人,但這並不隱含任何的自卑。因此她們可以展現自己人性的存在,並以自然的方式生活著。
在原始的層次上,真實女性的意象和男性阿尼瑪的意象,或多或少是同一種東西,而且,人類的文明正在經歷某種緩慢而循環的轉換歷程,大約得要三百到四百年。這種緩慢的發展運動極可能是成千上萬個別反應的總和,或許是由許多女性被拒絕和不被欣賞的痛苦經驗所組成,並在暗地裡醞釀,經過幾世紀之後浮上台面,使得二十世紀初的集體女性解放爆發成為一種運動引起人們的注意。
於是我們就以這樣的兩難情境揭開序幕:童話故事中的女性人物既不是阿尼瑪模型,也不是真實的女人,而是兩者兼具,因為有時候是前者,有時候又是後者。而且有些童話故事闡述真實的女性多一點,有些則說明男性的阿尼瑪多一點,端視最後一位寫故事的人的性別而有差異,這樣的猜測是很公允的。我有一位朋友在學校裡擔任繪畫老師,有一次上課時,他以童話故事〈忠實的約翰〉(Faithful John)為主題,要學生從中選擇一個場景來作畫。在我看來,那個故事鏡映的是男性的心理學,其中只有一個蒼白的阿尼瑪角色而已。這位老師把這個故事給了男女合班的學生,讓他們自由挑選任何場景作畫。所有的小孩都充滿熱情,男孩們自然而然就選擇了英雄和戲劇性的場景,而女孩們則挑選了故事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她們認同那個女性角色就如同男孩們認同那些男性角色一樣,因此他們所畫出來的圖畫,就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故事面貌。
由此可見,依照重述故事者的性別,就會強調出不同的特質。於是我們可以如此假設:在某些童話故事中,女性的造型有較大的影響力,有些則是男性造型影響較多,但我們永遠都無法確定其中女性角色所代表的是女人或者是阿尼瑪。比較好的辦法是同時以這兩種角度去詮釋童話,那我們就會看到有些童話從女性的角度去詮釋時會得到很豐富的素材,但若從男性的角度去詮釋時,卻似乎並沒有那麼發人深省。有了這樣的印象之後,我選擇了幾則可以由女性角度詮釋的格林童話,但是我並不能說它們和阿尼瑪的問題毫無關連。
童話乃集體無意識的補償
至於故事當中的角色,一般都會說神話是神的故事,而童話是凡人的故事,亦即在童話中的英雄和參與者是凡人,在神話中的則是神和半神;但我卻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這種理論的問題在於,有些童話故事中的人名指的是神。例如在我即將討論的〈睡美人〉(The Sleeping Beauty)或〈野玫瑰〉(Briar Rose)故事的許多版本中,小孩被稱為太陽和月亮。那麼,太陽和月亮的媽媽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你可以稱它是一種象徵。若小孩被稱為太陽和月亮,或在其他版本中叫做清晨與黃昏,那麼你就知道這講的是神的國度了。因此你無法根據這種差異來建立一種理論。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知道他們是原型人物,當我們用人類的心理學來理解他們時,我們知道在本質上他們和凡人及人類人格並沒有任何關係。因此我會假設童話故事和神話並沒有什麼差別,但他們都和原型人物有關。
如果我們真的想對這個概念有所感覺的話,我們就必須問問自己,為什麼人們在敘說故事時,有時候會使用自己國家宗教所崇拜的神祇之名、以其集體表徵(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來命名故事人物,而在其他故事中卻不這麼做。這兩者的差異和歷史性的因素有關,在此我無法進一步討論它。我們姑且這樣假設:人們可以利用夢境和醒著時的幻象,將自己無意識中的人物投射到虛空之中,並且也能夠討論這些人物。
我有一個非常單純的女性個案,她是個木匠的女兒,在原始的鄉間長大,生活非常貧窮。她就算不是個真正的思覺失調症患者,也是個嚴重的邊緣型思覺失調個案。她有最令人驚奇的聲音、幻象、夢境以及原型的素材,雖然她去學做美髮師,但卻因為有許多幻想而無法繼續下去,只好去做一名清潔工,但又因為她很容易與人爭吵,既有點瘋狂又難以相處,因此必須等到四下無人的時候才可以開始清理空曠的公司。她已經被丟棄到人類社會的邊緣地帶,但她卻是個很有宗教信仰的人,除了被自己的幻象所吞噬而不具外在功能之外,她甚至可以和德國天主教神祕主義者德雷絲.馮.科內爾斯羅伊特(Teresa von Konnersreuth)相比。她曾想與我進一步接觸,但在分析的前60 分鐘卻毫無進展,因為她的自我情結過於脆弱。起先,她必須對場地和我產生感覺,然後她說她沒有辦法馬上談論像上帝這樣的主題。我想那也的確是,因為她的情況是需要有親密感和友誼才能夠分享一個天大的祕密,於是對這個特殊的個案我同意不要那麼常見面,並可以挪出整個下午見她。我們也不在諮商室會面,而是會去小酒館一起喝點飲料,或是到別處去。她有時都不說話,或是講了一個半鐘頭盡是說些無關緊要的話題,讓我非常精神耗竭。通常我要不是開始緊張地看著手錶,要不就是告訴她我必須在七點前回去,好將她拉回現實。然後她才突然開始談她的內在經驗,就像突然跳進夢境,而且當它是真的一樣。為了加強她的意識面好讓她從原型世界出來,我會對她說:「對啊!但那只是一個夢。」對此她總是表示贊同沒有太感困惑,但我注意到她隨後就無法再進行下去了,因為她就像個藝術家在工作時被打斷一樣受到了干擾。如果你的藝術靈感正在萌芽,新的靈感正傾洩而出,卻遭到這種阻斷的話,你就會像殘廢一樣的失去線索。剛湧出來的創造性靈感必須不被打擾,特別是當這些靈感還沒有確實成形之前,人們不該去談論它,因為它們就像新生兒一樣的脆弱。
具有創造力的人們通常都很容易受到干擾,我在這個女人身上也注意到同樣的情形。因此我通常都把我的評論留到最後,在那時候我想我應該有幫助她更接近現實了,因此就順著童話的模式,在故事最後通常會有個評語把你從故事情境中踢出來——但那也只在最後才會出現。
那個女人告訴我最不可思議的原型故事,而且把它們當成真的一樣看待,而就在這當下(in fl agranti),就有一個童話故事可能的起源案例了。因為有人告訴你一個經典的文學戲劇故事,並在最後評論說那只是個夢境!像這樣的案例,一開始時敘述者是完全認同故事本身的,但在重新敘述故事的過程中,故事就改變了,其中個人的主題也被排除了。故事最後的評論很可能是這樣:「公雞啼叫咕─咕咕─咕─黎明到了,而我的故事也結束了。」因為該是醒來的時候了!公雞啼叫的時候,就是你該起床的時候了。或者,他也可能這麼說:「有一個美好的婚禮和豐盛的晚宴,但我在廚房裡卻什麼也沒得到,因為廚子一腳把我踢醒,於是我站在這裡告訴你這個故事。」也就是說他飛回現實世界中了。換成吉普賽人的說法:「他們結了婚,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但我們是窮鬼,正飢餓地吸吮自己的牙齒。」接著他們又繼續討錢去了。
如此一來,聽故事的人就知道童話並不是一件普通人的真實事件,他們會很清楚地知道故事裡的人事是發生在另一個場域,是我們稱之為無意識(unconscious)的領域。他們會覺得那是屬於另外一個世界,並且和我們意識中的現實有很大的差異。人們以這種方式在非常原始的層次上和無意識有一種切換式的接觸。場景的切換並沒有明確的界線,強調的反而是感覺層次。童話故事真正告訴我們的是無意識中的人物,他們屬於另外一個世界。我們可以說神話中的人物和宗教上的神會互相混淆,因為他們都符合了法國人類學家呂西安‧列維.布魯爾(Lucien Lévy-Bruhl)所稱的集體表徵,但童話恰恰相反,童話是會遷移的,也不能連結到國族的集體意識,它含有大量補償性的素材,並且通常和集體的意識觀念相衝突或者互補。
我那位思覺失調的清潔女工有時候會帶來充滿了基督教傳統的夢境,例如天父會出現並對她說話,隨後出現的事情就和她在基督教教育中所學相符。要稱呼一個人物為天父,而稱另外一個為聖靈(Holy Ghost),這對她而言並不太困難。有一次她的幻境中出現一位俊美男子,那時她在山上,而他就站在她身邊,有個聲音說:「妳必須把這漆成綠色以救贖自己和人類。」她說她做不到,那聲音說:「我會幫助妳。」她後來似乎不知怎樣就完成了任務,因而被准許從山上下來。下一幕是她在一個旅館中醒了過來。我問那是誰的聲音,她說那是聖靈。雖然那個聲音並不符合,但是那個俊男卻符合集體表徵中的聖靈形象,她也毫不費力地就指認出來了。
若在另外一個宗教系統,那個人物可能會得到不一樣的名字。如果出現一個人物卻不符合集體表徵,或是如果什麼稱呼都無法符合這個人物時,你就只得說有某件事發生了,它似乎像什麼跟什麼,但你無法將它置於任何一個集體觀念上。假設有個這樣的經驗,例如有個女神擁有所有大地之母的特質,但卻像古希臘時期的包玻(Baubo)女神一樣的放肆性感。如果你從小在天主教家庭長大,你不能稱這個人物是聖母瑪利亞,但既然那是你唯一擁有的女性神聖人物代表,你就只能稱這位為大母神(Mother),或者給她一個怪誕的名字,像是長青小母(Little Mother Evergreen)之類的。但是那並不是一個正式的名字,我們也不會用宗教的態度去崇拜這個人物。童話故事就是以這種方式產生的,很多時候都是建立在這種內在經驗之上,它們並不那麼符合集體表徵,因此童話人物通常沒有名字,或是使用很古老的名字,而不會用宗教性的象徵或已知宗教系統中的名諱。他們比神話提供更多關於無意識正在進行的補償功能訊息。這種在集體表徵中沒有被表達出來,但在某種集體層面又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東西呢?我們可以從這一點得到有價值的訊息,因為童話故事也會採用正式的名字並敘述關於宗教人物的卑劣行徑。有一個國家流傳著不少關於耶穌基督的故事,他的行為蠻橫,例如他和聖彼得四處閒逛,害得他被旅館主人毆打,因為聖彼得總是過於天真,自然就成了那個挨打的人。捷克斯拉夫還有這麼一則童話:一名無助的老人坐在樹上,需要人幫忙攙扶才能從樹上下來,在故事最後,竟然說那個緊張無助的老男人,正是上帝本人。你能想像上帝本人是個無助的老男人無法從樹上爬下來嗎?但是故事裡有個心地善良的小女孩必須幫助他從樹上下來,這對我們既存的上帝概念就是很有用的補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