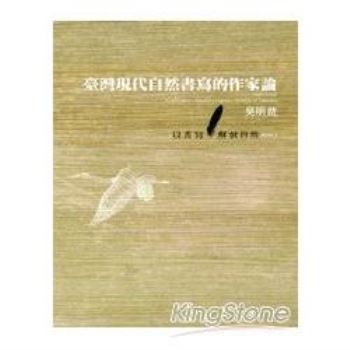<Chapter 3 從孤獨的旅行者到多元的導覽者-劉克襄>(節錄)
劉克襄(1957-)在1996年的〈台灣的自然書寫初論〉中,提及了有別於環保文學(本文稱環境議題報導)與田園文學(本文稱簡樸生活文學)的第三種自然書寫途徑。這些作品的特質是:「表現的語言,充滿更多的自然科學元素與知識性的描述。經常長時間定點在野外從事調查,特別強調土地現場的經驗和時空。創作者也認清自己扮演的角色,體認都市文明的無所不在,以及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這種現實性的思考和實踐,通常也是田園式文章較付之闕如的部分。」(劉克襄,1996a)
這段話恰可說是劉克襄於自然書寫實踐的自我指涉:不斷旅行、觀察、記錄,而後反芻為文字。既不棄離都市,反而在觀察中思考如何建立都市與自然的渠道,甚或於都市中尋找一個「開窗就能觀察」的可能性。並且,在經過長期觀察,投注於史料的整裝,劉克襄又以一個兼具自然知識與人文修養的導覽者身份出現。
這一章我將先略述劉克襄自然書寫的歷程,再由其階段性的轉變中觀察其書寫模式的轉變,並從中理解其在作品中透顯出來的,對應臺灣環境的環境倫理觀。
不斷把新的概念放進旅行背包:劉克襄的自然書寫歷程
劉克襄的自然書寫歷程,可以說是在不斷自我修正的變動中多向前進的。他從不拘於一種書寫模式,也極少在內容上自我重複。
21歲的劉克襄,自費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河下游》,23歲時因服役於海軍因此在澎湖初步接觸到鳥類,引發了興趣。退伍後他參與鳥會學習觀察的方式,1981年開始獨自在中部大肚溪、大甲溪等流域觀察鳥類。在這些「河下游」,孤獨旅行的自然觀察者劉克襄逐漸走出屬於他的流域。
劉克襄書寫的轉向,「出現新的書寫類型」的作品,或許是頗為適當的觀察指標。不過,當他創造出新的書寫模式(或說思考模式)的同時,舊的模式仍會持續進行。也就是說,導覽者劉克襄出現後,仍存在著一個一有時間就享受孤獨旅行的劉克襄。因此,準確一點說,劉克襄的自然書寫模式的改變不能說是轉向,而是匯聚了新的意識、新的支流。
第一個時期約略從《旅次札記》(1982)到《消失中的亞熱帶》與《荒野之心》為止(1986)。這階段劉克襄不斷走訪各個聚集了旅鳥的「驛站」,四處觀察、記錄是他了解這些自然生命的方式。他並認為可以從中得知怎麼做,才能真正保護牠們的生存環境。在《隨鳥走天涯》(1985)、《消失中的亞熱帶》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克襄在實踐只帶著望遠鏡、圖鑑、筆記本與詩集的「蝸牛式的旅行觀察」。這時期他還寫詩,《松鼠班比曹》(1983)、《漂鳥的故鄉》(1984)、《在測天島》(1985)中的作品,雖還潛存著濃厚關涉時政的意味,但時而會將自然觀察的對象化為某種象徵,化為詩句。同時,這時期劉克襄的自然書寫,行文上仍常有「詩的意味」。《荒野之心》是較特殊的作品,與同一時期洪素麗的作品相似,這部作品是參考自然歷史雜誌中國外博物學者所寫的關於自然生態的文章,改寫而成的。其內容通常是不在場的觀察,而是一些生態記錄文獻的改寫譯述。(劉克襄,1986,頁2)但與洪素麗不同,劉克襄並未長久經營這類作品,而是朝不斷旅行觀察的路向走去。
1988年所編寫的《探險家在臺灣》,意味著劉克襄走進第二個時期,另一條探索自然的途徑─是歷史的,人文的幽微進路。其後《臺灣鳥類研究開拓史1840-1912》(1989)、《橫越福爾摩沙》(1989)這些作品,都是在處理過去旅行者認識臺灣的姿態,或者說是理解臺灣「如何被逐步認識」的歷程。這些作品顯露出兩種層次的寄託:第一,劉克襄嚮往能像這些前行的旅行者一樣,在旅途中發現福爾摩沙的豐美本質。其次,光是了解鳥名、鳥的習性、進行觀察記錄已不能滿足他,他意圖將他對觀察對象的認識,往更長久的時空裡深探。這時期的詩集《小鼯鼠的看法》,也和第一時期的詩作大不相同,作者多半是抒發對觀察對象的敏銳感知,而不是藉其依託,或引為象徵。另一部《臺灣鳥木刻記實六十》(1990)則是結合何華仁木刻版畫的筆記書,文字部分是介紹性地在版畫作品旁說明鳥的生態。
《風鳥皮諾查》(1991)是國內第一部以生物知識、生態認知為背景的動物小說。它是架構在對鳥類生活背景有生態認識上的寓言。故事主人翁是探索環頸?英雄落地生根歷史的皮諾查,可以說是劉克襄第一時期的部分觀察,與第二時期探討歷史的姿態的一種想像性融合的化身。《座頭鯨赫連麼麼》(1993)採用的也是同一個書寫模式─對自然觀察配合自然知識具象化為一個虛擬的動物主角,而這動物主角同時也懷著書寫者的思維與觀看的姿態。此外,前兩個時期的書寫模式仍在持續進行,但有了些許的改變。《自然旅情》(1992)、《山黃麻家書》(1994)較近第一階段,《後山探險》(1992)、《深入陌生地》(1993)則是第二階段的續篇。其中《山黃麻家書》是以一個父親的姿態寫給孩子的自然書,《自然旅情》則已有將人文、自然綜合思考,並有將觀察、旅行的方式,介紹給讀者,邀讀者共遊的意向。這兩本書都象徵著劉克襄擺脫孤獨旅行者的形象,而嘗試「對孩子說」,或「對人們說」:如何尋訪觀察自然的蹊徑。
1995年的「小綠山系列」則是第一種類型的深化。小綠山的觀察不再像過去的劉克襄背著孤獨的背包到冰冷的沙岸或茫莽的深山溪河旅行,而是在自己家裡周圍每天進行的長期觀察。《臺灣舊路踏查記》(1995)則把平面的史料蒐整化為立體的循跡重行,明確的地圖、地點、旅行的路徑,劉克襄意在邀集更多的人走入自然史。
1996年以後的劉克襄與其說是一個孤獨的旅行者,不如說是一個經驗豐富、思考周全的導覽領隊。他帶領人們《偷窺自然》(1996),背著《快樂綠背包》(1998)出外旅行,也把自然的故事說給孩子們聽,或畫給孩子們看(《豆鼠私生活》、《鯨魚不快樂時》、《不需要名字的水鳥》,以上1996),有時則告訴孩子們如何結識自然的方法、生態知識並闡揚自然的啟發力量。(《望遠鏡裡的精靈》,1997;《劉克襄自然生態綠皮書》,1999;《綠色童年》,2000)甚而把他對自然、人文、政治的一些想法,化成想像的國度,創造出一個虛構的豆鼠世界。(《小島飛行》、《扁豆森林》、《草原鬼雨》,以上1997)這時期劉克襄也將他過去走過的自然途徑開放,包括《台北市自然景觀導覽》(1999)、《草嶺古道》(2000)、《北台灣自然旅遊指南》(2000)都可視為是同樣概念下的產物:唯有更多人帶著豐富的背包旅行,才可能教育這些人懂得尊敬自然。當然,他也並沒有放棄繼續深研自然史(《福爾摩沙大旅行》,1999),而在2001 年出版的《安靜的遊蕩》,則是較偏重於人文式旅行的筆記。
由於本書的排除性定義已先將詩與小說排除在討論的對象之外,上述這類作品,將不列入討論對象。
排除詩與動物小說、寓言小說外,劉克襄的自然書寫概略可分為四種模式:第一種是揉合知性材料,理性思考,偶見文學性筆觸寫作的散文或觀察記錄。如《旅次札記》、《隨鳥走天涯》、「小綠山系列」等。第二種是自然史的探討,包括《臺灣鳥類研究開拓史1840-1912》、《深入陌生地》等。第三種是為兒童閱讀所書寫的觀察書籍以及繪本,包括《鯨魚不快樂時》、《不需要名字的水鳥》、《綠色童年》(2000)等等。第四種是導覽型的書籍,包括《草嶺古道》(2000)、《北臺灣自然旅遊指南》(2000)等。當然,有些書籍是跨類的,比方說《臺灣舊路踏查記》(1995)就兼有自然史與旅行導覽的意義與價值。為了討論的焦點能夠集中,純粹的自然史研究與導覽書籍不是本文的主要討論文本,而專給兒童閱讀的童書或繪本,則因其訴求對象特別,並無法與其自然書寫的作品置於同一個標準衡量,因此也排除在外。是故,這裡所討論的文本是以第一個類型為主,其它類型為輔。(待續)劉克襄自然書寫的書寫特質
1. 揉合歷史、自然科學的文學性表述
早期劉克襄所採的多半是定點觀察─即是在固定的地點,經常性地記錄以觀察其生態變化的模式。它必須先篩選出觀察對象較常聚集的地點,再進行密集性的觀察記錄。以觀鳥為例,通常國外鳥人會彙集自己的觀察記錄,交給鳥會或研究機構,聚集成一個長年的觀察記錄史,再由專業人士解讀出其中的鳥況變化。以此資料配合相關環境的研究,藉以探討鳥況起伏的原因。
劉克襄一開始先選擇大肚溪、大甲溪為觀察定點,而後又選擇淡水河下游為觀察定點。原因之一是這些河口是觀察候鳥的適當地點,第二則是這裡過去有部分前行探險家或觀察者已經觀察過,可資比對。尤其選擇淡水河口,與郇和(Robert Swinhoe,1836-1877。劉克襄則譯為史溫侯)這位令劉克襄傾心的生物學家曾經在此觀察過,有絕對的關係。是故,劉克襄一開始的觀察行為,就具有「歷史的」視點,所以後來他往這個視點的深處探訪,並不令人意外。
基本上,自然書寫的書寫本是一種揉合自然科學與文學性的語言。但國內的自然書寫者,卻少見像劉克襄一樣,初下筆就能將臺灣的自然史,或人文史揉入書寫當中:
二十年前,當大漢溪上游的毛蟹開始順河下來,準備到淡水河口產卵時,中途碰到了高大的石門水庫攔阻。石門水庫沒有鮭魚,自然沒有水道讓毛蟹前進。生態上,毛蟹也沒有陸封型。從此,石門水庫以上的大漢溪毛蟹絕種了。(劉克襄,1982,頁6)
這樣的寫法不僅揉入自然史,且特別是「臺灣的自然史」,對生態的描寫也不只是參考國外圖鑑書裡的生物資料的整理。
另外一種則不是回溯自然史的角度,而是對過去中國詩、畫中,模糊不清的動物描寫,藉由作者的觀察經驗,與累積的生態知識,加以再推測或者反駁:
關於雁的遷徙:如果我早生百年,也許能替古人翻案。《山海經》的時代,古人觀雁,知道雁門山雁出其間,至於何種雁,無深一層說詞。到了一千多年前,唐代宗時,嶺南節度使徐浩,在五嶺間發現雁群。在這以前,古人以為雁群只到衡山,所以有話:衡州有回雁峰,雁至北不過,遇春而回。但徐浩表奏代宗時過於諂媚了,雁群在五嶺出現的記錄須打折扣。要等宋時正直的寇準說「誰道衡陽無雁過?數聲殘日下江陵。」才能確知雁群已經飛越衡陽。三十年前,上一代的人又補充:雁群已經抵達臺灣。其實還描述得不當。如今雁群已從臺灣過境,有的遠抵馬來半島。經過臺灣的雁也登記了三十八種。(劉克襄,1982,頁122)第一種,古人稱燕子者,通常是指現今的家燕,這也是臺灣島上燕科裡,唯一有可能自大陸飛來避冬的。白先勇的《臺北人》有首序詩,劉禹錫的〈烏衣巷〉,從其習性推研,由唐至今可以斷定烏衣就是家燕。也只有家燕才能舊時王謝堂前,再飛入尋常百姓家,十足表現冬候鳥的特性。(同前書,頁134)
這種「文學式的反省」,在後起的陳煌、王家祥、陳玉峰的作品中,都未曾見。這書寫特質應該與劉克襄的文學底子有深刻的相關,文字間存在著某種浪漫的想像,使得他在觀察之間,往往能縱橫書海,尋得與古人對話的秘徑。因此,即便是觀察札記,作者的文學想像時隱時現於文句之間,在描寫鳥的動態與靜態時,觀察者的聽覺與嗅覺,遂得以合構成人鳥於自然中相遇的詩味:
我也發現了蒼鷺,我們島上最大的鷺鷥,正飄在天空。我只能用飄形容。這時海風高達八級,蒼鷺想越過大肚溪,正與海風爭執不下,彷若風箏,結果越飛越退後,過了兩三分鐘,只好停在小水鴨群中憩息。(劉克襄,1982,頁46)
正午時,白鸛飛進河口來,一隻蒼鷺伴著。牠像紙鳶一樣徐徐降落,彷彿在天空寫了一首立體的詩。這是我賞鳥以來見過最美麗的鳥種,白身黑尾紅腳,大若火雞,體型像鶴。(劉克襄,1987,頁27)
與海風「爭執不下」的蒼鷺,降落時在空中「寫了一首立體的詩」的白鸛,無非因此有劉克襄的存在與關注,「美」才在其間發生意義。這種既描寫了觀察景象也發揮了作者詩意想像的句子,在下一階段卻逐漸在劉克襄的書寫裡消失。
然而自然書寫的文學性描寫,並不能停留在詩境的營造與感官的鋪陳,若能在描述中與生態知識有若干符節之處,則更能增添文學性描寫的獨特魅力。比方說劉克襄在一次極接近濱鷸的觀察裡,從牠們眼裡看到「陌生、不馴與無可言喻的神秘」。同時又從濱鷸灰褐,如草澤的保護色聯想,認為這種色澤不僅是安全,且是遷徙、冒險、流浪的顏色。草澤/安全、遷徙/冒險、流浪,這種由知性理解導致感性發抒的修辭,致使詩人之眼所探望出的顏色,「不是底片或是顏料所能拍攝、渲染得體,完滿表現出來的」。(劉克襄,1985,頁49)而有些時候,這種聯想會和作者關心環境的情緒合為一脈:「風鳥的長相猶如魔鬼先派來人間的小無常,而那怪異的鳴聲與飛行,正是在向人類提出嚴重的警告,對地球做最後的嘶喊。」(劉克襄,1987,頁100)
將濱鷸的顏色形容為「冒險、流浪」的色澤,到後來創造出具有浪漫冒險性格的皮諾丘,這些文學性的描寫中其實或多或少有著劉克襄個人性格的投射。他曾說:「每個人都有到陌生、遙遠地域旅行、流浪的夢想,我藉助不停地賞鳥觀察去實踐它。」(劉克襄,1985,頁1)觀察流浪風鳥的意義是為了實踐自身流浪夢想,這或許是早期孤獨旅行者劉克襄筆下總充滿了情致的緣由。而因為實踐的是一種「孤獨的旅行」,在早年的作品中,往往體現出一個靜謐的自然空間、寂然的精神世界:
我喜歡這樣靜止不動,然後微閉雙眼,讓耳朵突發清澈,更認真的聆聽。閉眼時,自然有山的聲音抵達心靈。這種聲音或許藉鳥聲傳入,也可能託蟲鳴轉達,等鳥聲蟲鳴也走了,卻有種說不上來的無聲,如露水侵襪,涼進肺腑。有時也藉氣味而至,在鼻尖冷冷輕撫,暖慰胸壑。如此感受或者稍冷了點,卻只有這樣的冷,最是山樣。要進谷來靜坐才能體會。從鳥聲開始,轉而蟲鳴,進至無聲。上山賞鳥,無非是識山而已。(劉克襄,1982,頁200-201)
這樣的觀鳥過程,當然不只是專業生物學家的觀察模式,而帶著人文的情懷。是故,劉克襄稱之為「軟性調查」。但這種帶著詩人孤獨身影旅行的方式,劉克襄並不覺得滿意。他「覺得只完成一個地點的調查雛型架構,雖然有專業知識的涉獵也未做得深入」。他想把更專業的物事放進旅行背包,「希望日後能依這個雛型,繼續找一個X 點的地方,再展開長期的調查旅行。」
而「下一個X 點在那裡呢」?這必須等到他深掘自然史,並找到小綠山後,問號才獲得回應。
劉克襄(1957-)在1996年的〈台灣的自然書寫初論〉中,提及了有別於環保文學(本文稱環境議題報導)與田園文學(本文稱簡樸生活文學)的第三種自然書寫途徑。這些作品的特質是:「表現的語言,充滿更多的自然科學元素與知識性的描述。經常長時間定點在野外從事調查,特別強調土地現場的經驗和時空。創作者也認清自己扮演的角色,體認都市文明的無所不在,以及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這種現實性的思考和實踐,通常也是田園式文章較付之闕如的部分。」(劉克襄,1996a)
這段話恰可說是劉克襄於自然書寫實踐的自我指涉:不斷旅行、觀察、記錄,而後反芻為文字。既不棄離都市,反而在觀察中思考如何建立都市與自然的渠道,甚或於都市中尋找一個「開窗就能觀察」的可能性。並且,在經過長期觀察,投注於史料的整裝,劉克襄又以一個兼具自然知識與人文修養的導覽者身份出現。
這一章我將先略述劉克襄自然書寫的歷程,再由其階段性的轉變中觀察其書寫模式的轉變,並從中理解其在作品中透顯出來的,對應臺灣環境的環境倫理觀。
不斷把新的概念放進旅行背包:劉克襄的自然書寫歷程
劉克襄的自然書寫歷程,可以說是在不斷自我修正的變動中多向前進的。他從不拘於一種書寫模式,也極少在內容上自我重複。
21歲的劉克襄,自費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河下游》,23歲時因服役於海軍因此在澎湖初步接觸到鳥類,引發了興趣。退伍後他參與鳥會學習觀察的方式,1981年開始獨自在中部大肚溪、大甲溪等流域觀察鳥類。在這些「河下游」,孤獨旅行的自然觀察者劉克襄逐漸走出屬於他的流域。
劉克襄書寫的轉向,「出現新的書寫類型」的作品,或許是頗為適當的觀察指標。不過,當他創造出新的書寫模式(或說思考模式)的同時,舊的模式仍會持續進行。也就是說,導覽者劉克襄出現後,仍存在著一個一有時間就享受孤獨旅行的劉克襄。因此,準確一點說,劉克襄的自然書寫模式的改變不能說是轉向,而是匯聚了新的意識、新的支流。
第一個時期約略從《旅次札記》(1982)到《消失中的亞熱帶》與《荒野之心》為止(1986)。這階段劉克襄不斷走訪各個聚集了旅鳥的「驛站」,四處觀察、記錄是他了解這些自然生命的方式。他並認為可以從中得知怎麼做,才能真正保護牠們的生存環境。在《隨鳥走天涯》(1985)、《消失中的亞熱帶》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克襄在實踐只帶著望遠鏡、圖鑑、筆記本與詩集的「蝸牛式的旅行觀察」。這時期他還寫詩,《松鼠班比曹》(1983)、《漂鳥的故鄉》(1984)、《在測天島》(1985)中的作品,雖還潛存著濃厚關涉時政的意味,但時而會將自然觀察的對象化為某種象徵,化為詩句。同時,這時期劉克襄的自然書寫,行文上仍常有「詩的意味」。《荒野之心》是較特殊的作品,與同一時期洪素麗的作品相似,這部作品是參考自然歷史雜誌中國外博物學者所寫的關於自然生態的文章,改寫而成的。其內容通常是不在場的觀察,而是一些生態記錄文獻的改寫譯述。(劉克襄,1986,頁2)但與洪素麗不同,劉克襄並未長久經營這類作品,而是朝不斷旅行觀察的路向走去。
1988年所編寫的《探險家在臺灣》,意味著劉克襄走進第二個時期,另一條探索自然的途徑─是歷史的,人文的幽微進路。其後《臺灣鳥類研究開拓史1840-1912》(1989)、《橫越福爾摩沙》(1989)這些作品,都是在處理過去旅行者認識臺灣的姿態,或者說是理解臺灣「如何被逐步認識」的歷程。這些作品顯露出兩種層次的寄託:第一,劉克襄嚮往能像這些前行的旅行者一樣,在旅途中發現福爾摩沙的豐美本質。其次,光是了解鳥名、鳥的習性、進行觀察記錄已不能滿足他,他意圖將他對觀察對象的認識,往更長久的時空裡深探。這時期的詩集《小鼯鼠的看法》,也和第一時期的詩作大不相同,作者多半是抒發對觀察對象的敏銳感知,而不是藉其依託,或引為象徵。另一部《臺灣鳥木刻記實六十》(1990)則是結合何華仁木刻版畫的筆記書,文字部分是介紹性地在版畫作品旁說明鳥的生態。
《風鳥皮諾查》(1991)是國內第一部以生物知識、生態認知為背景的動物小說。它是架構在對鳥類生活背景有生態認識上的寓言。故事主人翁是探索環頸?英雄落地生根歷史的皮諾查,可以說是劉克襄第一時期的部分觀察,與第二時期探討歷史的姿態的一種想像性融合的化身。《座頭鯨赫連麼麼》(1993)採用的也是同一個書寫模式─對自然觀察配合自然知識具象化為一個虛擬的動物主角,而這動物主角同時也懷著書寫者的思維與觀看的姿態。此外,前兩個時期的書寫模式仍在持續進行,但有了些許的改變。《自然旅情》(1992)、《山黃麻家書》(1994)較近第一階段,《後山探險》(1992)、《深入陌生地》(1993)則是第二階段的續篇。其中《山黃麻家書》是以一個父親的姿態寫給孩子的自然書,《自然旅情》則已有將人文、自然綜合思考,並有將觀察、旅行的方式,介紹給讀者,邀讀者共遊的意向。這兩本書都象徵著劉克襄擺脫孤獨旅行者的形象,而嘗試「對孩子說」,或「對人們說」:如何尋訪觀察自然的蹊徑。
1995年的「小綠山系列」則是第一種類型的深化。小綠山的觀察不再像過去的劉克襄背著孤獨的背包到冰冷的沙岸或茫莽的深山溪河旅行,而是在自己家裡周圍每天進行的長期觀察。《臺灣舊路踏查記》(1995)則把平面的史料蒐整化為立體的循跡重行,明確的地圖、地點、旅行的路徑,劉克襄意在邀集更多的人走入自然史。
1996年以後的劉克襄與其說是一個孤獨的旅行者,不如說是一個經驗豐富、思考周全的導覽領隊。他帶領人們《偷窺自然》(1996),背著《快樂綠背包》(1998)出外旅行,也把自然的故事說給孩子們聽,或畫給孩子們看(《豆鼠私生活》、《鯨魚不快樂時》、《不需要名字的水鳥》,以上1996),有時則告訴孩子們如何結識自然的方法、生態知識並闡揚自然的啟發力量。(《望遠鏡裡的精靈》,1997;《劉克襄自然生態綠皮書》,1999;《綠色童年》,2000)甚而把他對自然、人文、政治的一些想法,化成想像的國度,創造出一個虛構的豆鼠世界。(《小島飛行》、《扁豆森林》、《草原鬼雨》,以上1997)這時期劉克襄也將他過去走過的自然途徑開放,包括《台北市自然景觀導覽》(1999)、《草嶺古道》(2000)、《北台灣自然旅遊指南》(2000)都可視為是同樣概念下的產物:唯有更多人帶著豐富的背包旅行,才可能教育這些人懂得尊敬自然。當然,他也並沒有放棄繼續深研自然史(《福爾摩沙大旅行》,1999),而在2001 年出版的《安靜的遊蕩》,則是較偏重於人文式旅行的筆記。
由於本書的排除性定義已先將詩與小說排除在討論的對象之外,上述這類作品,將不列入討論對象。
排除詩與動物小說、寓言小說外,劉克襄的自然書寫概略可分為四種模式:第一種是揉合知性材料,理性思考,偶見文學性筆觸寫作的散文或觀察記錄。如《旅次札記》、《隨鳥走天涯》、「小綠山系列」等。第二種是自然史的探討,包括《臺灣鳥類研究開拓史1840-1912》、《深入陌生地》等。第三種是為兒童閱讀所書寫的觀察書籍以及繪本,包括《鯨魚不快樂時》、《不需要名字的水鳥》、《綠色童年》(2000)等等。第四種是導覽型的書籍,包括《草嶺古道》(2000)、《北臺灣自然旅遊指南》(2000)等。當然,有些書籍是跨類的,比方說《臺灣舊路踏查記》(1995)就兼有自然史與旅行導覽的意義與價值。為了討論的焦點能夠集中,純粹的自然史研究與導覽書籍不是本文的主要討論文本,而專給兒童閱讀的童書或繪本,則因其訴求對象特別,並無法與其自然書寫的作品置於同一個標準衡量,因此也排除在外。是故,這裡所討論的文本是以第一個類型為主,其它類型為輔。(待續)劉克襄自然書寫的書寫特質
1. 揉合歷史、自然科學的文學性表述
早期劉克襄所採的多半是定點觀察─即是在固定的地點,經常性地記錄以觀察其生態變化的模式。它必須先篩選出觀察對象較常聚集的地點,再進行密集性的觀察記錄。以觀鳥為例,通常國外鳥人會彙集自己的觀察記錄,交給鳥會或研究機構,聚集成一個長年的觀察記錄史,再由專業人士解讀出其中的鳥況變化。以此資料配合相關環境的研究,藉以探討鳥況起伏的原因。
劉克襄一開始先選擇大肚溪、大甲溪為觀察定點,而後又選擇淡水河下游為觀察定點。原因之一是這些河口是觀察候鳥的適當地點,第二則是這裡過去有部分前行探險家或觀察者已經觀察過,可資比對。尤其選擇淡水河口,與郇和(Robert Swinhoe,1836-1877。劉克襄則譯為史溫侯)這位令劉克襄傾心的生物學家曾經在此觀察過,有絕對的關係。是故,劉克襄一開始的觀察行為,就具有「歷史的」視點,所以後來他往這個視點的深處探訪,並不令人意外。
基本上,自然書寫的書寫本是一種揉合自然科學與文學性的語言。但國內的自然書寫者,卻少見像劉克襄一樣,初下筆就能將臺灣的自然史,或人文史揉入書寫當中:
二十年前,當大漢溪上游的毛蟹開始順河下來,準備到淡水河口產卵時,中途碰到了高大的石門水庫攔阻。石門水庫沒有鮭魚,自然沒有水道讓毛蟹前進。生態上,毛蟹也沒有陸封型。從此,石門水庫以上的大漢溪毛蟹絕種了。(劉克襄,1982,頁6)
這樣的寫法不僅揉入自然史,且特別是「臺灣的自然史」,對生態的描寫也不只是參考國外圖鑑書裡的生物資料的整理。
另外一種則不是回溯自然史的角度,而是對過去中國詩、畫中,模糊不清的動物描寫,藉由作者的觀察經驗,與累積的生態知識,加以再推測或者反駁:
關於雁的遷徙:如果我早生百年,也許能替古人翻案。《山海經》的時代,古人觀雁,知道雁門山雁出其間,至於何種雁,無深一層說詞。到了一千多年前,唐代宗時,嶺南節度使徐浩,在五嶺間發現雁群。在這以前,古人以為雁群只到衡山,所以有話:衡州有回雁峰,雁至北不過,遇春而回。但徐浩表奏代宗時過於諂媚了,雁群在五嶺出現的記錄須打折扣。要等宋時正直的寇準說「誰道衡陽無雁過?數聲殘日下江陵。」才能確知雁群已經飛越衡陽。三十年前,上一代的人又補充:雁群已經抵達臺灣。其實還描述得不當。如今雁群已從臺灣過境,有的遠抵馬來半島。經過臺灣的雁也登記了三十八種。(劉克襄,1982,頁122)第一種,古人稱燕子者,通常是指現今的家燕,這也是臺灣島上燕科裡,唯一有可能自大陸飛來避冬的。白先勇的《臺北人》有首序詩,劉禹錫的〈烏衣巷〉,從其習性推研,由唐至今可以斷定烏衣就是家燕。也只有家燕才能舊時王謝堂前,再飛入尋常百姓家,十足表現冬候鳥的特性。(同前書,頁134)
這種「文學式的反省」,在後起的陳煌、王家祥、陳玉峰的作品中,都未曾見。這書寫特質應該與劉克襄的文學底子有深刻的相關,文字間存在著某種浪漫的想像,使得他在觀察之間,往往能縱橫書海,尋得與古人對話的秘徑。因此,即便是觀察札記,作者的文學想像時隱時現於文句之間,在描寫鳥的動態與靜態時,觀察者的聽覺與嗅覺,遂得以合構成人鳥於自然中相遇的詩味:
我也發現了蒼鷺,我們島上最大的鷺鷥,正飄在天空。我只能用飄形容。這時海風高達八級,蒼鷺想越過大肚溪,正與海風爭執不下,彷若風箏,結果越飛越退後,過了兩三分鐘,只好停在小水鴨群中憩息。(劉克襄,1982,頁46)
正午時,白鸛飛進河口來,一隻蒼鷺伴著。牠像紙鳶一樣徐徐降落,彷彿在天空寫了一首立體的詩。這是我賞鳥以來見過最美麗的鳥種,白身黑尾紅腳,大若火雞,體型像鶴。(劉克襄,1987,頁27)
與海風「爭執不下」的蒼鷺,降落時在空中「寫了一首立體的詩」的白鸛,無非因此有劉克襄的存在與關注,「美」才在其間發生意義。這種既描寫了觀察景象也發揮了作者詩意想像的句子,在下一階段卻逐漸在劉克襄的書寫裡消失。
然而自然書寫的文學性描寫,並不能停留在詩境的營造與感官的鋪陳,若能在描述中與生態知識有若干符節之處,則更能增添文學性描寫的獨特魅力。比方說劉克襄在一次極接近濱鷸的觀察裡,從牠們眼裡看到「陌生、不馴與無可言喻的神秘」。同時又從濱鷸灰褐,如草澤的保護色聯想,認為這種色澤不僅是安全,且是遷徙、冒險、流浪的顏色。草澤/安全、遷徙/冒險、流浪,這種由知性理解導致感性發抒的修辭,致使詩人之眼所探望出的顏色,「不是底片或是顏料所能拍攝、渲染得體,完滿表現出來的」。(劉克襄,1985,頁49)而有些時候,這種聯想會和作者關心環境的情緒合為一脈:「風鳥的長相猶如魔鬼先派來人間的小無常,而那怪異的鳴聲與飛行,正是在向人類提出嚴重的警告,對地球做最後的嘶喊。」(劉克襄,1987,頁100)
將濱鷸的顏色形容為「冒險、流浪」的色澤,到後來創造出具有浪漫冒險性格的皮諾丘,這些文學性的描寫中其實或多或少有著劉克襄個人性格的投射。他曾說:「每個人都有到陌生、遙遠地域旅行、流浪的夢想,我藉助不停地賞鳥觀察去實踐它。」(劉克襄,1985,頁1)觀察流浪風鳥的意義是為了實踐自身流浪夢想,這或許是早期孤獨旅行者劉克襄筆下總充滿了情致的緣由。而因為實踐的是一種「孤獨的旅行」,在早年的作品中,往往體現出一個靜謐的自然空間、寂然的精神世界:
我喜歡這樣靜止不動,然後微閉雙眼,讓耳朵突發清澈,更認真的聆聽。閉眼時,自然有山的聲音抵達心靈。這種聲音或許藉鳥聲傳入,也可能託蟲鳴轉達,等鳥聲蟲鳴也走了,卻有種說不上來的無聲,如露水侵襪,涼進肺腑。有時也藉氣味而至,在鼻尖冷冷輕撫,暖慰胸壑。如此感受或者稍冷了點,卻只有這樣的冷,最是山樣。要進谷來靜坐才能體會。從鳥聲開始,轉而蟲鳴,進至無聲。上山賞鳥,無非是識山而已。(劉克襄,1982,頁200-201)
這樣的觀鳥過程,當然不只是專業生物學家的觀察模式,而帶著人文的情懷。是故,劉克襄稱之為「軟性調查」。但這種帶著詩人孤獨身影旅行的方式,劉克襄並不覺得滿意。他「覺得只完成一個地點的調查雛型架構,雖然有專業知識的涉獵也未做得深入」。他想把更專業的物事放進旅行背包,「希望日後能依這個雛型,繼續找一個X 點的地方,再展開長期的調查旅行。」
而「下一個X 點在那裡呢」?這必須等到他深掘自然史,並找到小綠山後,問號才獲得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