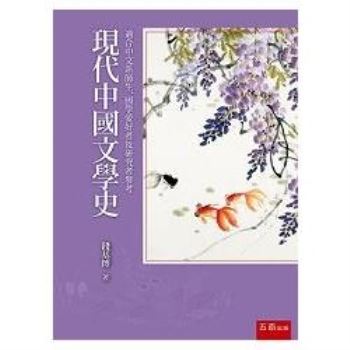緒論
1.文學
治文學史,不可不知何謂文學;而欲知何謂文學,不可不先知何謂文。請先述文之涵義。
文之涵義有三:
(甲)複雜。非單調之謂複雜。《易.繫辭傳》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文部》:「文錯畫,象交文。」是也。
(乙)組織。有條理之謂組織。《周禮.天官.典絲》:「供其絲纊組文之物」,注:「繪畫之事:青與赤謂之文。」《禮記.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是也。
(丙)美麗。適娛悅之謂美麗。《釋名.釋言語》:「文者會集眾彩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是也。綜合而言:所謂文者,蓋複雜而有組織,美麗而適娛悅者也。複雜,乃言之有物。組織,斯言之有序。然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美麗為文之止境焉。
文之涵義既明,乃可與論文學。
文學之定義亦不一:
(甲)狹義的文學。專指「美的文學」而言。所謂美的文學者,論內容,則情感豐富,而不必合義理;論形式,則音韻鏗鏘,而或出於整比;可以被弦誦,可以動欣賞。梁昭明太子序《文選》:「譬諸陶匏為入耳之娛;黼黻為悅目之玩」者也。「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活,辯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夫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名曰《文選》云耳。」所謂「篇什」者(《詩》〈雅〉、〈頌〉十篇為一什,後世因稱詩卷曰篇什),由〈蕭序〉上文觀之,則賦耳、詩耳、騷耳、頌贊耳、箴銘耳、哀誄耳,皆韻文也。然則經(姬公之籍,孔父之書)非文學也,子(老莊之作,管孟之流)非文學也,史(記事之文、繫年之書)非文學也,惟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沉思」、「義歸翰藻」,與夫詩賦騷頌之稱「篇什」者,方得與於斯文之選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揚榷前言,扺掌多識者謂之筆;詠嘆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搖會,情靈搖蕩。」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有韻者『文』也。」持此以衡。雖唐宋韓、柳、歐、蘇、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廁於文學之林;以事雖出於沉思,而義不歸乎翰藻;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者也。夫文學限於韻文,此義蓋有由來;然而非其朔也。大抵六朝以前,所謂「文學」者,「著述之總稱」,所包者廣。六朝以下,則「文學」者,「有韻之殊名」,立界也嚴。其大較然也。然吾人倘必持狹義以繩文學,則所謂文學者,殆韻文之專利品耳。倘求文學之平民化,則不得不捨狹義而取廣義。
(乙)廣義的文學。「文學」二字,始見《論語》,子曰:「博學於文。」「文」指《詩》、《書》六藝而言,不限於韻文也。孔門四科,文學子游子夏,不聞游夏能韻文也。韓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學而指斥及藏管、商、孫、吳之書者,管商之書,法家言也;孫吳之書,兵家言也;而亦謂之文學。漢司馬遷《史記.自序》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舉凡律令、軍法、章程、禮儀,皆歸於文學。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凡六略:六藝百三家,諸子百八十九家,詩賦百六家,兵書五十三家,數術百九十家,方技三十六家,皆入焉。倘以狹義的文學繩之,六略之中,堪入藝文者,惟詩賦百六家耳;其六藝百三家,則《蕭序》所謂「姬公之籍,孔父之書」也;至《國語》、《國策》與夫《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之並隸入《春秋》家者,則《蕭序》所謂「記事之史,繫年之書」也。諸子、兵書、方技、數術之屬,則《蕭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者也。然則「文學」者,述作之總稱,用以會通眾心,互納群想,而表諸文章,兼發智情:其中有偏於發智者,如論辨、序跋、傳記等是也。有偏於抒情者,如詩歌、戲曲、小說等是也。大抵知在啟悟,情主感興。《易》、《老》闡道而文間韻語,《左》、《史》記事而辭多詭誕,此發知之文而以感興之體為之者也。後世詩人好質言道德,明議是非,作俑於唐之昌黎,極盛於宋之江西,忘比興之恉,失諷喻之義,則又以主情之文而為發知之用矣。譬如舟焉,智是其舵,情為帆棹;智標理悟,情通和樂,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
1.文學
治文學史,不可不知何謂文學;而欲知何謂文學,不可不先知何謂文。請先述文之涵義。
文之涵義有三:
(甲)複雜。非單調之謂複雜。《易.繫辭傳》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文部》:「文錯畫,象交文。」是也。
(乙)組織。有條理之謂組織。《周禮.天官.典絲》:「供其絲纊組文之物」,注:「繪畫之事:青與赤謂之文。」《禮記.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是也。
(丙)美麗。適娛悅之謂美麗。《釋名.釋言語》:「文者會集眾彩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是也。綜合而言:所謂文者,蓋複雜而有組織,美麗而適娛悅者也。複雜,乃言之有物。組織,斯言之有序。然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美麗為文之止境焉。
文之涵義既明,乃可與論文學。
文學之定義亦不一:
(甲)狹義的文學。專指「美的文學」而言。所謂美的文學者,論內容,則情感豐富,而不必合義理;論形式,則音韻鏗鏘,而或出於整比;可以被弦誦,可以動欣賞。梁昭明太子序《文選》:「譬諸陶匏為入耳之娛;黼黻為悅目之玩」者也。「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活,辯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夫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名曰《文選》云耳。」所謂「篇什」者(《詩》〈雅〉、〈頌〉十篇為一什,後世因稱詩卷曰篇什),由〈蕭序〉上文觀之,則賦耳、詩耳、騷耳、頌贊耳、箴銘耳、哀誄耳,皆韻文也。然則經(姬公之籍,孔父之書)非文學也,子(老莊之作,管孟之流)非文學也,史(記事之文、繫年之書)非文學也,惟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沉思」、「義歸翰藻」,與夫詩賦騷頌之稱「篇什」者,方得與於斯文之選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揚榷前言,扺掌多識者謂之筆;詠嘆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搖會,情靈搖蕩。」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有韻者『文』也。」持此以衡。雖唐宋韓、柳、歐、蘇、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廁於文學之林;以事雖出於沉思,而義不歸乎翰藻;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者也。夫文學限於韻文,此義蓋有由來;然而非其朔也。大抵六朝以前,所謂「文學」者,「著述之總稱」,所包者廣。六朝以下,則「文學」者,「有韻之殊名」,立界也嚴。其大較然也。然吾人倘必持狹義以繩文學,則所謂文學者,殆韻文之專利品耳。倘求文學之平民化,則不得不捨狹義而取廣義。
(乙)廣義的文學。「文學」二字,始見《論語》,子曰:「博學於文。」「文」指《詩》、《書》六藝而言,不限於韻文也。孔門四科,文學子游子夏,不聞游夏能韻文也。韓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學而指斥及藏管、商、孫、吳之書者,管商之書,法家言也;孫吳之書,兵家言也;而亦謂之文學。漢司馬遷《史記.自序》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舉凡律令、軍法、章程、禮儀,皆歸於文學。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凡六略:六藝百三家,諸子百八十九家,詩賦百六家,兵書五十三家,數術百九十家,方技三十六家,皆入焉。倘以狹義的文學繩之,六略之中,堪入藝文者,惟詩賦百六家耳;其六藝百三家,則《蕭序》所謂「姬公之籍,孔父之書」也;至《國語》、《國策》與夫《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之並隸入《春秋》家者,則《蕭序》所謂「記事之史,繫年之書」也。諸子、兵書、方技、數術之屬,則《蕭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者也。然則「文學」者,述作之總稱,用以會通眾心,互納群想,而表諸文章,兼發智情:其中有偏於發智者,如論辨、序跋、傳記等是也。有偏於抒情者,如詩歌、戲曲、小說等是也。大抵知在啟悟,情主感興。《易》、《老》闡道而文間韻語,《左》、《史》記事而辭多詭誕,此發知之文而以感興之體為之者也。後世詩人好質言道德,明議是非,作俑於唐之昌黎,極盛於宋之江西,忘比興之恉,失諷喻之義,則又以主情之文而為發知之用矣。譬如舟焉,智是其舵,情為帆棹;智標理悟,情通和樂,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