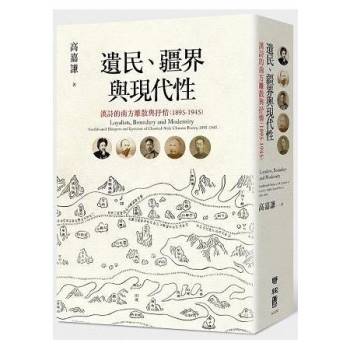第一章
漢詩的文化審美與南方想像
緒言
本書考察十九世紀以降,面對世紀的新舊交替,殖民與西學衝擊,在中國南方、臺灣、香港與南洋的詩人群體的離散際遇。從他們寫於境外的漢詩創作,探究一個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及漢詩文類的越界與現代性脈絡。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為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的重要文學實踐。尤其經歷乙未、辛亥兩次政治鉅變,仕紳百姓大規模遷徙,文化與文學的播遷軌跡尤其繁複,漢詩的流動與生產由此構成理解與辯證現代性最值得注意的文學形式。
漢詩的發展不僅僅侷限於中原國土疆界,從明清使臣、商賈的朝貢外交、貿易網絡,甚至更早的僧人、儒者的文化交流,促成中國邊境之外的漢字文化圈和漢字文化流動的區域―朝鮮半島、日本、琉球、越南、臺灣、新馬,都曾經有過漢詩蓬勃發展的生態。我們著眼十九世紀後期以降的文人跨洋出境,更大的意義是在「域外」或「境外」的位置上,突出一個漢詩寫作的意義和譜系。儘管本書聚焦的對象仍有自中國/境外遷徙往返的現象,近代時局變革也離不開中國的參照位置,但隨著文人移動而寫於境外的漢詩,無論就文人感受,或是詩語言跨境的刺激改變而言,已有獨立觀察和自成體系的學術意義。換言之,我們強調近代漢詩的離散,旨在突出變局下的傳統文人在東亞和東南亞的跨境流動、吟詠酬唱,以及衍生的各地漢詩發展生態。我們不妨將其視為中國疆界之外的南方離散詩學。
本書處理的時間跨度,始於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臺事件,收束在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前者從近代中國第一批遺民的誕生展開論述,後者以戰爭期間南來作家郁達夫的失蹤死亡,作為流寓詩學一個曖昧的結束或再生產。
乙未割臺是近代中國一次現代性體驗的象徵性起點,也可看作一次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清廷割地和日本殖民,為以下幾個層面帶來深遠的影響。
一、帝國視域、體系和權威的破壞和解體。
二、臺灣進入殖民情境,誕生的「地方」(Place)意識或地域性認同。同時殖民建設帶來的知識體系與生活景觀的改變。
三、境外的文人流寓與文化播遷轉向一種遺民和流亡性質,構成了另一層次的「南渡」遺民詩學。
四、傳統概念的境外交通史,同時是文化與文學播遷史,形成新興的文學場。因此帝國境內政局動盪,締造了境外漢詩的融合與交流契機。各地文學場的形成與互動,凸顯了漢詩的跨境生產脈絡,不再是單一的中原意識。
換言之,士人在一八九五年以降面臨的時代鉅變,產生悲憤憂患的國族書寫、現代的時間與地理感受,造就晚清曖昧的政治或文化遺民,並連同中原境內和境外的知識分子,捲入了一種我們稱之為離散現代性(diasporic modernity)的體驗。他們透過文學試圖描述與定位自身的遷徙,卻必須面對時代的變化與衝擊,同時回望、召喚難以斷絕的傳統。他們分別在不同區域之間流動,從中國大陸到殖民地臺灣、香港,由臺灣內渡中國,再從中國、臺灣奔往南洋,數個區域的互涉,凸顯出清末民初的傳統士人型態各異,但又共同處身一個裂變下的帝國解體與現代體驗。無論他們生根中國、臺灣,或流寓、移居南洋,文人遊走區域之間,表現出不同的文化想像與文學生產。
因此,他們在境外的文化播遷與文學實踐,以及漢文人置身傳統與現代的境外複雜體驗,可以看作一種東亞現代性的論述。本書關注的現代性面向,將放在時間和離散兩個部分。前者陳述了帝國覆滅、國體肇新,殖民體驗、都市化和文化與語言變革等等鉅變,將中國及東亞周邊導入現代化的線性時間。當中的歷史敘事強調了過去與現在的急速斷裂,傳統與革新的儼然對立,在允諾了一個美好未來的同時,飄零且無所適從的存在感,卻留下一種時間的創傷。這種創傷正是一種現代體驗。誠如馬克思(Karl Marx)的說法:「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日常節奏的撕裂、文化秩序的破壞,還有無法抗逆的暴力動盪,呈現出主體生命在歷史進程中無法承受的創痛與感傷。面對曠古鉅變,時間展示著一種現代性的弔詭,王德威教授指稱:「一方面強調時間斷裂、一切俱往的感受,一方面又流露綿綿不盡的鄉愁;一方面誇張意義、價值前無來者的必要,一方面又不能忘本清源、或追求終極目的的誘惑。」這是一種歷史的迷妄(historical illusionism),因此時間對傳統知識分子,或文化遺民而言,顯然是不連續性、破碎的體驗。他們彷彿放逐在現代世界之外,以飄零孤獨的姿態面對不可復原的傳統,以及自身在新興時間秩序裡的困窘尷尬。
相對於此,時間效應也發生在暴力和災難的體驗。國族與個人所面對、經歷的變革,是感時憂國框架底下一種創傷時間的呈現。從集體的國家社會鉅變,到庶民日常生活的改造,他們面對殖民侵略、兵燹戰爭、動亂浩劫、政治暴力,歷史的破壞和生活的陷落,讓他們在感受整體的文化摧殘中,處在更大的現代時間風暴。
除了時間感,本書強調的現代性視域,另指向空間地理變異的體驗。「離散」(Diaspora)的原初概念始於猶太人的大遷徙,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的規模龐大的流動遷徙經驗,卻不曾在中國境內境外缺席。尤其十九世紀中國周邊的境外流動涉及更多庶民百姓和知識階層。乙未割臺的殖民情境、帝國鉅變引發的改革和暴力,造成文化人跨出境外走向世界。他們的足跡開啟了主體意識的現代體驗。但傳統士人的流動,涉及生存暴力威脅的被迫式散居和遷徙,當中無法迴避的殖民創傷、地域認同和流離的存在感受,改變了流動者的經驗結構。因此,隨著遷徙而帶動的境外漢文學播遷,其中的生產和交流,都離不開離散的現代性條件。無論是憂患或流亡寫作,寫在境外都是一種越界。於是文人在離散過程當中建構了文化主體與認同的存在特質。在這個區域漢文學交流與互動的文學現場,基本是以漢詩為主導文類。由傳統士大夫群體生產的漢詩與遺民意識有著複雜的辯證關係。面對帝國政治傳統與文化同時終結的關鍵時刻,傳統文人複雜幽微的感受,見證了文化遺民的誕生。他們普遍具有時代匆促之感、窮於應對不確定性的未來,而歷史的殘骸與碎片已在堆積。由此時代以降,士人投入古典詩學的寫作與論述顯得更為艱難和愴然。他們承擔著憂患與流亡意識,漢詩因此成為一個需要重新審視的文類範疇,或遺民的抒情形式。
在離散情境與漢詩生產的集體氛圍當中,我們可以再次提問,遺民如何構成晚清以降傳統士人群體的身分認知與特徵?相對古典的遺民論述,十九世紀末以降的乙未及辛亥生成的遺民群體,又如何辯證其政治與文化的向度?這些不因為帝國覆滅而消逝無蹤的遺民想像,反而透過漢詩寫作見證了一個遺民論述的「道統」。換言之,我們檢視晚清到民國的遺民書寫,分殊不同意識型態下的傳統士人心態,既批判性的對遺民意識展開辯證,同時重構了漢詩作為二十世紀士人文化心靈的一種投射。這是一個透過漢詩與離散的詮釋,辨析文化遺民境遇的詩學前提。如此一來,我們將有一組討論遺民意識與近代漢詩生產機制無法迴避的問題。
詩人如何對詩的審美意義重新認知,漢詩又如何構成文化遺民的根柢?詩的抒情技藝如何成為遺民的生存及自我想像文化母體及生存倫理證成的手段?詩與文化主體的結合,漢詩作為文化之魂、詩魂之表現,無疑是晚清以降漢詩的生產意識,以及文人區域性流動建立漢詩場域的主導精神。因此,我們進一步追問,漢詩如何想像南方?尤其境外南方的遷徙流動,改變了詩的感覺結構,構成漢詩的流亡視野?這會是一個近代漢詩的離散詩學框架?對於以上問題的回應,本書將針對漢詩作為文化遺民的審美共同體,及其南方想像的詩學脈絡,試圖進行一些理論性的鋪陳。
第二章
遺民、詩與時間的敘事
第一節 遺民的三個歷史時間:甲申、乙未、辛亥
中國傳統上的歷代遺民,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亡明與亡清兩個關鍵時間點。亡明之際,士大夫一方面必須面對腐敗、積弱不振的南明小朝廷與難挽大局的抗清活動;另一方面則是滿人建立新朝氣象,漢人政統、道統衰亡,其中攸關士大夫群體教化、安身立命的道德倫理與文化根本,最令他們感覺焦慮不安。因而,甲申之變對顧炎武等亡明遺民而言,觸碰的是一次激烈的「亡國」與「亡天下」的內在煎熬,國體與文化的辯證。同樣在晚清時期,統治二百餘年的清王朝面臨下臺命運。這次面對的文化撞擊與時間斷裂感,源自於西方殖民勢力與現代化的革命思潮。亡清,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進入新興民族國家序列;遺民再也不是傳統遺民,反而處身在令遺民窘迫的「新學」與「新文化」的歷史 作為士大夫認知下的一種身分傳統,「遺民」標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正統質疑。他們對政治與文化道統的忠誠顯得尷尬,因為遜位的清帝只能困居紫禁城一角,維繫帝國末代政權的象徵性香火。最後還被趕入民間,作為一次又一次政治權力交換時被利用的傀儡。民國新興的文化氛圍也難有遺民容身之地,他們被迫幽居於租界的半殖民異質空間。這些遜清遺民群體,有的是前清官僚,但也有未曾出仕,只是以舊王朝為文化依歸的傳統眷戀者。這些人變得進退兩難,他們是無法躋身遺民正統的末代遺老,或是傳統凋零下流離失所的文化人,只能在新興時代腐朽的老去、亡逝。換言之,他們可視為二十世紀的「現代」遺民,有著堅守文化立場與效忠政治道統的象徵意義。他們既以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對抗現代性的進程,同時也在現代性革命風暴裡見證著遺民的無以為繼。
然而,早在清帝國消亡以前,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臺,首先誕生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批遺民。那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時間。他們聚首於臺灣島嶼,從清帝國的棄民成為日本新興殖民地的被殖民者,內渡大陸中原與滯留臺島,成為儒家士大夫在棄地經驗下第一次面臨「現代」的遺民處境。他們跟殖民者對抗、周旋進而妥協、認同、協力的過程,展現了一種遺民身分與價值的變異。尤其是漢詩的型態,出入遺民與殖民之間的抒情變奏,凸顯了一次最弔詭的遺民現代體驗。
以上提及的歷史時段,可以作為我們觀察遺民群體誕生的重要指標。遺民固然是易代或政治變革的時代產物,但其生成的脈絡卻顯得繁複與弔詭。晚清時期排滿抗清的激進革命思潮正盛,但亡明的遺風卻死灰復燃,構成晚清官方與民間舞臺上重建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風景。明清易代因此是一套需要重新展示的歷史氛圍、政治熱情和語言表述。當時人們為明朝遺烈修祠建廟,重現與確認「晚明三大家」的學術與文化意義,在海內外蒐集明末遺民著述,進而在中國境內重刊。尤其是海外心懸落日的遺老孤臣,如避居終老日本的朱舜水,堂堂正正走入晚清到民初時刻的民族主義革命視野,在振興中華故國與愛國民族大義的層面,受到廣泛推崇。這一套晚明記憶的重述與重建顯得轟轟烈烈,卻難掩其詭異之處。當時梁啟超以「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總結這種現象的根源,強調知識分子援引明清易代「經世致用」資源的現實需求。然而,這不也暗示了這些殘明遺老的思想精華和事蹟,同時發揮效力的乃是一套遺民話語。遺民的「正統」,恰好補強了革命的力道。在推翻帝國,建立民國的進程中,他們率先肯定了一套遺民邏輯。為清末民初的鼎革,埋下歷史與政治的內在連結,一道文化想像的理路。
其時人們周旋在這套遺民話語,無形之中提醒在乙未、辛亥歷史時機生成的遺民文化,已內化為國家建構與歷史記憶的一個關鍵部分。換言之,甲申的晚明記憶的鋪陳,顯然為乙未、辛亥的遺民存在氛圍,找到一個辯證的參照點。乙未生產一批帝國地域割裂下的棄地遺民,提早在清朝覆滅以前驗證了孤臣孽子飄零異域的遺民體驗。相對朱舜水、沈光文等殘明遺民遊走絕域,仍以恢復中原為念;此際乙未遺民顧盼的故國已是中原之南的臺灣島嶼,島內遺民轉換為殖民新興景觀下的另類地域性認同。同樣在辛亥後的遜清遺民,傳統文化面臨跟帝國一起崩塌潰散的命運。殘明遺獻表徵的文化正統與道統,甲申遺民的正牌形象,為生活在民國階段的文化遺民,預先演練了他們的歷史位置與際遇。因此,晚清時刻想像與建立的明季遺民符號,正是因為乙未、辛亥的變革,而構成一個值得重新辨識與深化的價值系統。甲申的亡明傷痛,在清末民初的歷史機遇中變得更為劇烈,以放大鏡檢視明清易代經驗,反而更清晰映襯出乙未、辛亥的知識分子面臨帝國斷裂的無所適從,不知去向的創傷。如此說來,召喚晚明記憶,超越了歷史懷舊,而是在遺民傳統的意義上,為「認同」與「身分」尋求由帝國疆域走向現代世界的經驗辯證與對話可能。此際重提「遺民」,不再是古老話題,而是清末民初的總體經驗結構當中,一項有效解釋知識分子傳統倫理與文化想像的論述。「遺民」因此進駐到「現代」氛圍,形成值得探究的現代性意義。
如此一個斷裂、支離的文化與歷史氛圍,遺民主導下的詩學與時間產生了微妙辯證,試圖為這種歷史的感覺結構賦形,投射了其時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的心靈與存有經驗。遺民在此時間變革的過程中,以大量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和實踐,呈現出值得探究的遺民詩學典範。詩人處身歷史的轉折點,集中表徵的繁複時間―歷史廢墟、殘骸下的時間,文化撞擊的心靈時間,甚至流放的主體時間,顯然呈現了古典詩學的另一種形貌。用一種文學性的譬喻式形容:詩,在遺民與時間的辯證下,走上流亡之路。
然而,詩何以「流亡」?
清代章學誠有一段話精確描述了古典詩教的有效範疇:「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從《詩》三百、《楚辭》以降的抒情詩傳統,早就構成回應詩人個體處境的文學類型。
詩作為表達時代際遇的古今媒介,貼近歷史情境下的生命形式,尤其最能展現「末世」經驗。無論清初、民初,甚至曖昧的乙未晚清時刻,面對歷史時空下的亂離,詩人未嘗沒有「末世」感,詩所表述的個人或集體感受,調動的象徵或符號系統,總是在想像那斷裂的文化傳統。當詩人與文化之間跨越著愈來愈大的時間鴻溝,詩因此「流亡」,在這層意義上導向遺民倫理的自我證成與安頓的有效性。
亡明以後,遺民周旋於史與抒情詩之間的向度,無異再次質疑了審美與紀實的詩學想像。詩如何模仿、記錄外在世界,卻同時保持抒情傳統內的美學價值。「詩史」,是當時整合的關鍵概念,卻由此開啟了詩與時間有效的對話關係。乙未以降,辛亥以後,現代性境遇變革了古典氛圍,面對現代時間感的嚴峻挑戰,古典詩學的美學範疇是否有效轉化為一種現成的近代漢詩處境?根源於傳統詩教的抒情傳統,如何在此變局中為個體經驗賦予形式?詩教的變異,還可能有效回應詩人的心靈想像與寄託?這是一組攸關易代與現代經驗變遷下,遺民與詩之間必然遇上的問題。
因此,探討遺民詩人的抒情倫理將成為理解漢詩軸向的重要層面。抒情倫理,顧名思義展示了本書對近代漢詩生產的內在精神的關切。那是對抒情自我的實踐,一種倫理―政治性經驗的考究。遺民的漢詩生產,某個程度上回應、重建和鞏固了抒情詩在古典時代的理論預設。這套理論預設,指向和諧、自足、圓滿、融通等哲學範疇,在古典帝國與傳統文化潰散的時刻,詩人的傳統生命與心靈無以為繼,漢詩的實踐呼應著抒情傳統,等於在表徵與重構詩背後的文化邏輯。一套足以在現代經驗世界存續的價值體系。我們探問遺民詩學的抒情倫理,旨在勾勒遺民詩人內在「抒情性」、「抒情精神」的詩學根據。在遺民與詩表述的經驗當中,首要觸及的外在經驗,基本是時間意識的變遷與生成的結構性經驗。因此,時間是近代遺民詩學的重要命題,詩人自我安頓與解釋外在世界的據點。
但在時間之外,還有一個空間的軸向必須兼顧。亡明以降的亂離,地理的遷徙流動,造就了境外離散書寫的脈絡,尤其在晚清以後達到顛峰。在狀似保守的遺民詩學生產過程中,境外書寫反而構成漢詩「現代性體驗」的最初形式。境外南方,這個傳統的域外概念,從晚清時刻開始成為我們理解和想像遺民漢詩,一個有效的文化地理詮釋框架。地理移動,導致的文學與文化生產空間的變異,呈現了遺民詩學新的越界意涵。因此,遺民與詩,顯然有一個無法繞過的時間與地理相互勾連的軌跡。
本章試圖從甲申、乙未與辛亥,遺民應世進退的三個歷史時刻切入,以晚明四位際遇不同的遺民錢牧齋、王船山、沈光文和朱舜水起頭,架構遺民詩設定的議題和演繹軌跡。然後再從乙未、辛亥遺民詩人連雅堂、王國維、陳三立等個案的詩學實踐,回應甲申以降的遺民傳統,強調晚明想像和遺民論述在清末民初浮現的文化效應。從甲申、乙未、辛亥三個時段的不同遺民個案,我們建立近代遺民精神的譜系與辯證關係,在晚清帝國崩壞的前夕,探究中原境內境外的漢詩流亡軌跡,以期有效說明近代漢詩意識裡的「遺民化」脈絡。
因此我們試著回應一組核心問題:遺民與詩處理時間的形式,漢詩的現代經驗到底是什麼樣的遭遇?在舊體制、典範、秩序傾塌與瓦解的現代前夜,漢詩產生什麼樣的心理需求?那會是詩人的一種文化共同體想像?境外地理又如何建立漢詩的離散書寫,如何重構遺民的文化與政治意識?這些問題將隨著本章幾組不同個案的解讀分析,加以鋪陳和脈絡化,整合視野,描繪出一個遺民、詩與時間交織的基本輪廓。
漢詩的文化審美與南方想像
緒言
本書考察十九世紀以降,面對世紀的新舊交替,殖民與西學衝擊,在中國南方、臺灣、香港與南洋的詩人群體的離散際遇。從他們寫於境外的漢詩創作,探究一個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及漢詩文類的越界與現代性脈絡。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為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的重要文學實踐。尤其經歷乙未、辛亥兩次政治鉅變,仕紳百姓大規模遷徙,文化與文學的播遷軌跡尤其繁複,漢詩的流動與生產由此構成理解與辯證現代性最值得注意的文學形式。
漢詩的發展不僅僅侷限於中原國土疆界,從明清使臣、商賈的朝貢外交、貿易網絡,甚至更早的僧人、儒者的文化交流,促成中國邊境之外的漢字文化圈和漢字文化流動的區域―朝鮮半島、日本、琉球、越南、臺灣、新馬,都曾經有過漢詩蓬勃發展的生態。我們著眼十九世紀後期以降的文人跨洋出境,更大的意義是在「域外」或「境外」的位置上,突出一個漢詩寫作的意義和譜系。儘管本書聚焦的對象仍有自中國/境外遷徙往返的現象,近代時局變革也離不開中國的參照位置,但隨著文人移動而寫於境外的漢詩,無論就文人感受,或是詩語言跨境的刺激改變而言,已有獨立觀察和自成體系的學術意義。換言之,我們強調近代漢詩的離散,旨在突出變局下的傳統文人在東亞和東南亞的跨境流動、吟詠酬唱,以及衍生的各地漢詩發展生態。我們不妨將其視為中國疆界之外的南方離散詩學。
本書處理的時間跨度,始於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臺事件,收束在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前者從近代中國第一批遺民的誕生展開論述,後者以戰爭期間南來作家郁達夫的失蹤死亡,作為流寓詩學一個曖昧的結束或再生產。
乙未割臺是近代中國一次現代性體驗的象徵性起點,也可看作一次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清廷割地和日本殖民,為以下幾個層面帶來深遠的影響。
一、帝國視域、體系和權威的破壞和解體。
二、臺灣進入殖民情境,誕生的「地方」(Place)意識或地域性認同。同時殖民建設帶來的知識體系與生活景觀的改變。
三、境外的文人流寓與文化播遷轉向一種遺民和流亡性質,構成了另一層次的「南渡」遺民詩學。
四、傳統概念的境外交通史,同時是文化與文學播遷史,形成新興的文學場。因此帝國境內政局動盪,締造了境外漢詩的融合與交流契機。各地文學場的形成與互動,凸顯了漢詩的跨境生產脈絡,不再是單一的中原意識。
換言之,士人在一八九五年以降面臨的時代鉅變,產生悲憤憂患的國族書寫、現代的時間與地理感受,造就晚清曖昧的政治或文化遺民,並連同中原境內和境外的知識分子,捲入了一種我們稱之為離散現代性(diasporic modernity)的體驗。他們透過文學試圖描述與定位自身的遷徙,卻必須面對時代的變化與衝擊,同時回望、召喚難以斷絕的傳統。他們分別在不同區域之間流動,從中國大陸到殖民地臺灣、香港,由臺灣內渡中國,再從中國、臺灣奔往南洋,數個區域的互涉,凸顯出清末民初的傳統士人型態各異,但又共同處身一個裂變下的帝國解體與現代體驗。無論他們生根中國、臺灣,或流寓、移居南洋,文人遊走區域之間,表現出不同的文化想像與文學生產。
因此,他們在境外的文化播遷與文學實踐,以及漢文人置身傳統與現代的境外複雜體驗,可以看作一種東亞現代性的論述。本書關注的現代性面向,將放在時間和離散兩個部分。前者陳述了帝國覆滅、國體肇新,殖民體驗、都市化和文化與語言變革等等鉅變,將中國及東亞周邊導入現代化的線性時間。當中的歷史敘事強調了過去與現在的急速斷裂,傳統與革新的儼然對立,在允諾了一個美好未來的同時,飄零且無所適從的存在感,卻留下一種時間的創傷。這種創傷正是一種現代體驗。誠如馬克思(Karl Marx)的說法:「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日常節奏的撕裂、文化秩序的破壞,還有無法抗逆的暴力動盪,呈現出主體生命在歷史進程中無法承受的創痛與感傷。面對曠古鉅變,時間展示著一種現代性的弔詭,王德威教授指稱:「一方面強調時間斷裂、一切俱往的感受,一方面又流露綿綿不盡的鄉愁;一方面誇張意義、價值前無來者的必要,一方面又不能忘本清源、或追求終極目的的誘惑。」這是一種歷史的迷妄(historical illusionism),因此時間對傳統知識分子,或文化遺民而言,顯然是不連續性、破碎的體驗。他們彷彿放逐在現代世界之外,以飄零孤獨的姿態面對不可復原的傳統,以及自身在新興時間秩序裡的困窘尷尬。
相對於此,時間效應也發生在暴力和災難的體驗。國族與個人所面對、經歷的變革,是感時憂國框架底下一種創傷時間的呈現。從集體的國家社會鉅變,到庶民日常生活的改造,他們面對殖民侵略、兵燹戰爭、動亂浩劫、政治暴力,歷史的破壞和生活的陷落,讓他們在感受整體的文化摧殘中,處在更大的現代時間風暴。
除了時間感,本書強調的現代性視域,另指向空間地理變異的體驗。「離散」(Diaspora)的原初概念始於猶太人的大遷徙,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的規模龐大的流動遷徙經驗,卻不曾在中國境內境外缺席。尤其十九世紀中國周邊的境外流動涉及更多庶民百姓和知識階層。乙未割臺的殖民情境、帝國鉅變引發的改革和暴力,造成文化人跨出境外走向世界。他們的足跡開啟了主體意識的現代體驗。但傳統士人的流動,涉及生存暴力威脅的被迫式散居和遷徙,當中無法迴避的殖民創傷、地域認同和流離的存在感受,改變了流動者的經驗結構。因此,隨著遷徙而帶動的境外漢文學播遷,其中的生產和交流,都離不開離散的現代性條件。無論是憂患或流亡寫作,寫在境外都是一種越界。於是文人在離散過程當中建構了文化主體與認同的存在特質。在這個區域漢文學交流與互動的文學現場,基本是以漢詩為主導文類。由傳統士大夫群體生產的漢詩與遺民意識有著複雜的辯證關係。面對帝國政治傳統與文化同時終結的關鍵時刻,傳統文人複雜幽微的感受,見證了文化遺民的誕生。他們普遍具有時代匆促之感、窮於應對不確定性的未來,而歷史的殘骸與碎片已在堆積。由此時代以降,士人投入古典詩學的寫作與論述顯得更為艱難和愴然。他們承擔著憂患與流亡意識,漢詩因此成為一個需要重新審視的文類範疇,或遺民的抒情形式。
在離散情境與漢詩生產的集體氛圍當中,我們可以再次提問,遺民如何構成晚清以降傳統士人群體的身分認知與特徵?相對古典的遺民論述,十九世紀末以降的乙未及辛亥生成的遺民群體,又如何辯證其政治與文化的向度?這些不因為帝國覆滅而消逝無蹤的遺民想像,反而透過漢詩寫作見證了一個遺民論述的「道統」。換言之,我們檢視晚清到民國的遺民書寫,分殊不同意識型態下的傳統士人心態,既批判性的對遺民意識展開辯證,同時重構了漢詩作為二十世紀士人文化心靈的一種投射。這是一個透過漢詩與離散的詮釋,辨析文化遺民境遇的詩學前提。如此一來,我們將有一組討論遺民意識與近代漢詩生產機制無法迴避的問題。
詩人如何對詩的審美意義重新認知,漢詩又如何構成文化遺民的根柢?詩的抒情技藝如何成為遺民的生存及自我想像文化母體及生存倫理證成的手段?詩與文化主體的結合,漢詩作為文化之魂、詩魂之表現,無疑是晚清以降漢詩的生產意識,以及文人區域性流動建立漢詩場域的主導精神。因此,我們進一步追問,漢詩如何想像南方?尤其境外南方的遷徙流動,改變了詩的感覺結構,構成漢詩的流亡視野?這會是一個近代漢詩的離散詩學框架?對於以上問題的回應,本書將針對漢詩作為文化遺民的審美共同體,及其南方想像的詩學脈絡,試圖進行一些理論性的鋪陳。
第二章
遺民、詩與時間的敘事
第一節 遺民的三個歷史時間:甲申、乙未、辛亥
中國傳統上的歷代遺民,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亡明與亡清兩個關鍵時間點。亡明之際,士大夫一方面必須面對腐敗、積弱不振的南明小朝廷與難挽大局的抗清活動;另一方面則是滿人建立新朝氣象,漢人政統、道統衰亡,其中攸關士大夫群體教化、安身立命的道德倫理與文化根本,最令他們感覺焦慮不安。因而,甲申之變對顧炎武等亡明遺民而言,觸碰的是一次激烈的「亡國」與「亡天下」的內在煎熬,國體與文化的辯證。同樣在晚清時期,統治二百餘年的清王朝面臨下臺命運。這次面對的文化撞擊與時間斷裂感,源自於西方殖民勢力與現代化的革命思潮。亡清,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進入新興民族國家序列;遺民再也不是傳統遺民,反而處身在令遺民窘迫的「新學」與「新文化」的歷史 作為士大夫認知下的一種身分傳統,「遺民」標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正統質疑。他們對政治與文化道統的忠誠顯得尷尬,因為遜位的清帝只能困居紫禁城一角,維繫帝國末代政權的象徵性香火。最後還被趕入民間,作為一次又一次政治權力交換時被利用的傀儡。民國新興的文化氛圍也難有遺民容身之地,他們被迫幽居於租界的半殖民異質空間。這些遜清遺民群體,有的是前清官僚,但也有未曾出仕,只是以舊王朝為文化依歸的傳統眷戀者。這些人變得進退兩難,他們是無法躋身遺民正統的末代遺老,或是傳統凋零下流離失所的文化人,只能在新興時代腐朽的老去、亡逝。換言之,他們可視為二十世紀的「現代」遺民,有著堅守文化立場與效忠政治道統的象徵意義。他們既以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對抗現代性的進程,同時也在現代性革命風暴裡見證著遺民的無以為繼。
然而,早在清帝國消亡以前,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臺,首先誕生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批遺民。那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時間。他們聚首於臺灣島嶼,從清帝國的棄民成為日本新興殖民地的被殖民者,內渡大陸中原與滯留臺島,成為儒家士大夫在棄地經驗下第一次面臨「現代」的遺民處境。他們跟殖民者對抗、周旋進而妥協、認同、協力的過程,展現了一種遺民身分與價值的變異。尤其是漢詩的型態,出入遺民與殖民之間的抒情變奏,凸顯了一次最弔詭的遺民現代體驗。
以上提及的歷史時段,可以作為我們觀察遺民群體誕生的重要指標。遺民固然是易代或政治變革的時代產物,但其生成的脈絡卻顯得繁複與弔詭。晚清時期排滿抗清的激進革命思潮正盛,但亡明的遺風卻死灰復燃,構成晚清官方與民間舞臺上重建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風景。明清易代因此是一套需要重新展示的歷史氛圍、政治熱情和語言表述。當時人們為明朝遺烈修祠建廟,重現與確認「晚明三大家」的學術與文化意義,在海內外蒐集明末遺民著述,進而在中國境內重刊。尤其是海外心懸落日的遺老孤臣,如避居終老日本的朱舜水,堂堂正正走入晚清到民初時刻的民族主義革命視野,在振興中華故國與愛國民族大義的層面,受到廣泛推崇。這一套晚明記憶的重述與重建顯得轟轟烈烈,卻難掩其詭異之處。當時梁啟超以「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總結這種現象的根源,強調知識分子援引明清易代「經世致用」資源的現實需求。然而,這不也暗示了這些殘明遺老的思想精華和事蹟,同時發揮效力的乃是一套遺民話語。遺民的「正統」,恰好補強了革命的力道。在推翻帝國,建立民國的進程中,他們率先肯定了一套遺民邏輯。為清末民初的鼎革,埋下歷史與政治的內在連結,一道文化想像的理路。
其時人們周旋在這套遺民話語,無形之中提醒在乙未、辛亥歷史時機生成的遺民文化,已內化為國家建構與歷史記憶的一個關鍵部分。換言之,甲申的晚明記憶的鋪陳,顯然為乙未、辛亥的遺民存在氛圍,找到一個辯證的參照點。乙未生產一批帝國地域割裂下的棄地遺民,提早在清朝覆滅以前驗證了孤臣孽子飄零異域的遺民體驗。相對朱舜水、沈光文等殘明遺民遊走絕域,仍以恢復中原為念;此際乙未遺民顧盼的故國已是中原之南的臺灣島嶼,島內遺民轉換為殖民新興景觀下的另類地域性認同。同樣在辛亥後的遜清遺民,傳統文化面臨跟帝國一起崩塌潰散的命運。殘明遺獻表徵的文化正統與道統,甲申遺民的正牌形象,為生活在民國階段的文化遺民,預先演練了他們的歷史位置與際遇。因此,晚清時刻想像與建立的明季遺民符號,正是因為乙未、辛亥的變革,而構成一個值得重新辨識與深化的價值系統。甲申的亡明傷痛,在清末民初的歷史機遇中變得更為劇烈,以放大鏡檢視明清易代經驗,反而更清晰映襯出乙未、辛亥的知識分子面臨帝國斷裂的無所適從,不知去向的創傷。如此說來,召喚晚明記憶,超越了歷史懷舊,而是在遺民傳統的意義上,為「認同」與「身分」尋求由帝國疆域走向現代世界的經驗辯證與對話可能。此際重提「遺民」,不再是古老話題,而是清末民初的總體經驗結構當中,一項有效解釋知識分子傳統倫理與文化想像的論述。「遺民」因此進駐到「現代」氛圍,形成值得探究的現代性意義。
如此一個斷裂、支離的文化與歷史氛圍,遺民主導下的詩學與時間產生了微妙辯證,試圖為這種歷史的感覺結構賦形,投射了其時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的心靈與存有經驗。遺民在此時間變革的過程中,以大量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和實踐,呈現出值得探究的遺民詩學典範。詩人處身歷史的轉折點,集中表徵的繁複時間―歷史廢墟、殘骸下的時間,文化撞擊的心靈時間,甚至流放的主體時間,顯然呈現了古典詩學的另一種形貌。用一種文學性的譬喻式形容:詩,在遺民與時間的辯證下,走上流亡之路。
然而,詩何以「流亡」?
清代章學誠有一段話精確描述了古典詩教的有效範疇:「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從《詩》三百、《楚辭》以降的抒情詩傳統,早就構成回應詩人個體處境的文學類型。
詩作為表達時代際遇的古今媒介,貼近歷史情境下的生命形式,尤其最能展現「末世」經驗。無論清初、民初,甚至曖昧的乙未晚清時刻,面對歷史時空下的亂離,詩人未嘗沒有「末世」感,詩所表述的個人或集體感受,調動的象徵或符號系統,總是在想像那斷裂的文化傳統。當詩人與文化之間跨越著愈來愈大的時間鴻溝,詩因此「流亡」,在這層意義上導向遺民倫理的自我證成與安頓的有效性。
亡明以後,遺民周旋於史與抒情詩之間的向度,無異再次質疑了審美與紀實的詩學想像。詩如何模仿、記錄外在世界,卻同時保持抒情傳統內的美學價值。「詩史」,是當時整合的關鍵概念,卻由此開啟了詩與時間有效的對話關係。乙未以降,辛亥以後,現代性境遇變革了古典氛圍,面對現代時間感的嚴峻挑戰,古典詩學的美學範疇是否有效轉化為一種現成的近代漢詩處境?根源於傳統詩教的抒情傳統,如何在此變局中為個體經驗賦予形式?詩教的變異,還可能有效回應詩人的心靈想像與寄託?這是一組攸關易代與現代經驗變遷下,遺民與詩之間必然遇上的問題。
因此,探討遺民詩人的抒情倫理將成為理解漢詩軸向的重要層面。抒情倫理,顧名思義展示了本書對近代漢詩生產的內在精神的關切。那是對抒情自我的實踐,一種倫理―政治性經驗的考究。遺民的漢詩生產,某個程度上回應、重建和鞏固了抒情詩在古典時代的理論預設。這套理論預設,指向和諧、自足、圓滿、融通等哲學範疇,在古典帝國與傳統文化潰散的時刻,詩人的傳統生命與心靈無以為繼,漢詩的實踐呼應著抒情傳統,等於在表徵與重構詩背後的文化邏輯。一套足以在現代經驗世界存續的價值體系。我們探問遺民詩學的抒情倫理,旨在勾勒遺民詩人內在「抒情性」、「抒情精神」的詩學根據。在遺民與詩表述的經驗當中,首要觸及的外在經驗,基本是時間意識的變遷與生成的結構性經驗。因此,時間是近代遺民詩學的重要命題,詩人自我安頓與解釋外在世界的據點。
但在時間之外,還有一個空間的軸向必須兼顧。亡明以降的亂離,地理的遷徙流動,造就了境外離散書寫的脈絡,尤其在晚清以後達到顛峰。在狀似保守的遺民詩學生產過程中,境外書寫反而構成漢詩「現代性體驗」的最初形式。境外南方,這個傳統的域外概念,從晚清時刻開始成為我們理解和想像遺民漢詩,一個有效的文化地理詮釋框架。地理移動,導致的文學與文化生產空間的變異,呈現了遺民詩學新的越界意涵。因此,遺民與詩,顯然有一個無法繞過的時間與地理相互勾連的軌跡。
本章試圖從甲申、乙未與辛亥,遺民應世進退的三個歷史時刻切入,以晚明四位際遇不同的遺民錢牧齋、王船山、沈光文和朱舜水起頭,架構遺民詩設定的議題和演繹軌跡。然後再從乙未、辛亥遺民詩人連雅堂、王國維、陳三立等個案的詩學實踐,回應甲申以降的遺民傳統,強調晚明想像和遺民論述在清末民初浮現的文化效應。從甲申、乙未、辛亥三個時段的不同遺民個案,我們建立近代遺民精神的譜系與辯證關係,在晚清帝國崩壞的前夕,探究中原境內境外的漢詩流亡軌跡,以期有效說明近代漢詩意識裡的「遺民化」脈絡。
因此我們試著回應一組核心問題:遺民與詩處理時間的形式,漢詩的現代經驗到底是什麼樣的遭遇?在舊體制、典範、秩序傾塌與瓦解的現代前夜,漢詩產生什麼樣的心理需求?那會是詩人的一種文化共同體想像?境外地理又如何建立漢詩的離散書寫,如何重構遺民的文化與政治意識?這些問題將隨著本章幾組不同個案的解讀分析,加以鋪陳和脈絡化,整合視野,描繪出一個遺民、詩與時間交織的基本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