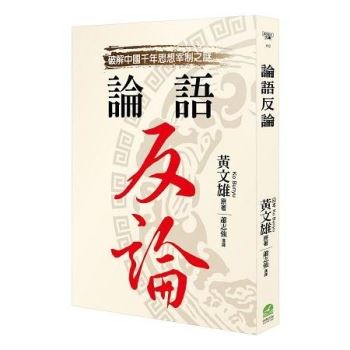【序章】
認識《論語》
▍一、從舉國人民讀誦《論語》的社會看清《論語》真相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讀《論語》的知識份子比江戶時代少得多,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加稀少。另一方面,和日本維新同時代的清朝,也爆發追求「洋化」(西洋化)或維護「國風」(傳統文化思想)的論戰。
至少到一九○五年廢除科舉制度為止,清朝知識份子的思想主張可說有兩大派,一派是皓首窮經、終生背誦《論語》等《四書五經》及其注疏,希望藉此「登龍門」、取得科舉功名的文人;另一派是太平天國等斷然禁除儒學的叛亂集團所建立的政治勢力範圍。
進入二十世紀,中國「支持」與「反對」儒學的二分化現象從未斷絕,雙方的對抗,可說從帝國、民國到人民共和國時代綿延不絕。另外,日本人與中國人對《論語》的理解與看法有的類似,有的完全不同。事實上,日本學者乃至於知識份子、文化人,對《論語》等中國思想主張經常出現誤解甚至曲解,也有很多人不清楚中國倫理與歷史社會的關係。以下是我的幾點淺見:
①有人認為,就是因為今天讀《論語》的人變少,所以日本道德頹廢、犯罪激增,但這種主張毫無根據。事實剛好相反,中國以儒教為國教超過二千年,即使中國人這麼長時期大量閱讀《論語》、《四書五經》,推廣「三德」、「四維」、「五倫」等教化,結果還不是變成堪稱全球「最無道德感」的國家?
②包括《論語》在內的中國《四書五經》,到處都是「仁義」與「道德」等訓示與主張。深入探究後發現,中國古代典籍的眾多道德宣示,都不是那個時代中國的「實況」,而是相反的情形,正因為「沒有」,所以需要大力鼓吹。換言之,《四書五經》所寫的都是「當為」,不料江戶儒學者卻誤以為中國古典著作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描繪,從而產生錯覺,以為中國是「仁義之國」、「道德之國」、「聖人之國」。換言之,其實很多中國人都有一種習慣,那就是「社會上不存在的東西,只好在書本裡大肆宣稱」。
③西洋頂尖哲學家黑格爾與馬克斯.韋伯都指出,儒教道德價值不高,給予很低的評價。中國人道德如此低落的原因,很多人從文化與社會層面尋找各種說明,但我想最根本的癥結是,中國人因為信奉儒教,結果反而喪失了「良心」。
④日本近代化功臣之一澀澤榮一(一八四○∼一九三一)寫了一本《論語與算盤》。第二世界大戰後也有一些日本學者撰寫《論語經濟學》,或者模仿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說「儒教精神」是中國近代化的主要動因。但事實上,儒教掌控中國人的腦袋二千年,根本不曾重視商人,「反商」其實正是儒教的核心教條。
雖然《論語》等《四書五經》都是所謂的「經世濟民之學」,超過二千年被中國人認定為最有價值的學問,但從實證主義史觀的角度觀察,《四書五經》能否稱得上是「經世之學」?還得看中國社會如何演變。結果卻發現,這些學問主張與社會的實際發展毫無關聯,中國所謂的「經世之學」根本是作文比賽,只是學者的空思妄想罷了。
從十八世紀末白蓮教之亂到二十世紀文革結束為止,中國近二百年天下大亂。首先,北方的宗教集團白蓮教叛變,「捻軍」大約數萬人攻入山東省,搗毀孔廟在內的孔子家族宗廟與墳墓,孔氏子孫遭受屠殺。南方也有信仰基督教的宗教集團「拜上帝會」,成立太平天國後禁止儒教,颳起「反儒」風暴,動盪持續到二十世紀。
台灣出生的我,未曾經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儒批孔,中小學一直到高中,唸的是台灣中華民國所實施的儒教教育。而且,進入國民小學之前,我跟隨「漢學老師」讀誦《三字經》、《千字文》以及「四書」的《大學》、《論語》、《孟子》等等,用朱筆標記句讀,努力背誦文章。
高中國文課本則充斥朱子學與陽明學的文章及注疏,而且必須背誦《論語》。原本是生活用語的成語,很多也納入儒教系統,拼命「說教」。這樣的社會,當然是扭曲異常。事實上,不只《論語》,《四書五經》等中國古文都有許多意思模糊、難以理解之處,自古以來因而出現很多爭論。針對這部分,我有以下幾點看法:
①不只《論語》,幾乎中國古代經書都得倚賴大量注與疏,否則難以理解其原意;但各家看法不同,特別是與《論語》相關、名為「正義」的注疏,更是眾說紛紜。甚至,就連如何斷句,各「學派」都有不同主張。除此之外,許多注疏者有其政治目的,從而牽扯各種利害。
②針對古典經書進行注或疏的大學者,除了必須擁有豐富「經」的知識,也得熟稔「史」、「詩」、「集」等知識,以及對時代的透徹認識。因此各家解釋不同,乃屬當然。
③中國古代經書遣詞用字簡練,句子壓縮得很短,因此不只注疏,就連精確掌握語彙內容、傳達其概念,都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
④《論語》很早就傳到日本,到了江戶時代,出現各種《論語》相關的「正義」(解釋),其中有些頗具創見,展現日本人特有觀點,成就斐然。但江戶距離孔子時代相當遙遠,加上日中兩國文化與文明差異,許多《論語》詞句無法精確譯為日語,即便今天進行《論語》的「現代語譯」,仍然很難符合原意。這是日本人理解《論語》的侷限。
⑤日本有許多《論語》的「現代語譯」版本,雖然做了相當大的努力,但不諱言,仍有許多誤譯與誤解。這可說和學識的造詣深淺無關,而是時代與文化差異的限制所致,日本人確實很難精確透徹地了解《論語》原文。
⑥《論語》一書不只呈現孔子的人生觀與天下觀,提出他對那個時代的看法與價值觀,背後其實也有改變社會與國家的政治目的。不容否認,古希臘、古印度乃至於古中國,都有一些普世的人生觀與萬古不易的人類共有價值觀,這些人生觀與價值觀凝聚成的知識與智慧,確實值得後人學習、傳承,但沒必要反覆背誦,當成教條。在我看來,中國人拼命背誦論語、「非背不可」,已經是一種變態。這也是我對「論語在中國」的基本判斷。
▍二、《論語》的真面目
很多人認為,《論語》是關於「修身」也就是品格教養的著作。要成為社會大眾品格教養的教科書,前提是民眾普遍閱讀,但事實上,《論語》普及的時間點比佛經大眾化來得晚。《論語》一開始是「孔子補習班」的「政論教材」,主要是鋪陳以禮及仁為工具、用來改變社會的方法,堪稱是「推銷、說教色彩濃厚」的說帖。換言之,孔子再傳弟子們把孔子發牢騷、罵人的話編成《論語》,一開始動機就是政治目的。
紙張普及之前,中國人是以甲骨、金石、木竹與布帛作為書寫工具。這些工具並不方便,所以中國古文非常簡練,字數極度壓縮,因此如前所述,想正確閱讀古文,得依賴「注」以及堪稱「注之注」的「疏」。
首先,《論語》成立於何時,這部分就有各種不同說法。可以確認的是,該書在孔子死後才成立,而且是孔子死後數百年的漢代、經由眾人合力編纂完成。許多研究者指出,《論語》出現太多「孔子那個時代不可能有的想法或遣詞用字」。
另外,孔子是否曾閱讀《易經》,學者之間也有許多爭論。孔子是春秋時代末期的人,《論語》卻出現許多戰國時代常見用語,以及再傳弟子孟子甚至更後面的荀子等各種論述,可見,與其說《論語》是孔子語錄,不如視之為古代儒家的思想摘要。
當然,《論語》即便不完全是二千五百年前孔子這個人的語錄,然而漢代之後許多大學者進行注與疏,日本儒學者也有許多有關「論語正義」的注疏研究,出現非常多具創意、獨特的見解。特別是日本學者提出不少有關《論語》的獨特看法,獲得中國漢學者的高度評價。
《論語》有《古論》、《齊論》、《魯論》三種版本,合計高達數百篇。江戶時代,日本學者伊藤仁齋根據漢代王充的《論衡.正說篇》與皇侃的《論語義疏》進行考證,整理出上論十篇與下論十篇,合計二十篇的《論語》。
伊藤仁齋的《論語古義》和荻生徂徠的《論語徵》,都是日本儒學指標、獨特性的儒學論述。日本漢學者的《論語》研究與注疏,許多見解超越中國學者,但我仍不免疑惑,距離孔子時代那麼遙遠,日中兩國風土也完全不同,日本人真的能正確解讀《論語》?
同理,西洋思想哲學與東洋思想哲學,內涵大相逕庭。我曾寫一篇討論空海《十住心論》與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論文,打算請台灣某大學教授歐洲現象學的朋友「漢譯」,卻被那位做過西田哲學研究的友人婉拒,說:「漢語在這些哲學領域的表達能力嚴重不足,不可能完成漢譯」。
確實如此,日本與中國歷史文化乃至於風土都有明顯差異,特別是萬世一系的日本政治架構與不斷易姓革命的中國,文化與文明架構乃至於社會都全然不同,加上文字與語言體系差異,所以「仁」、「恕」這類儒教特有概念,不要說日本人,就連中國人也都一知半解。反之,日本人特有的「思いやり」(omoiyari),乃至於「もののあはれ」(mononoaware)、「わび」(wabi)、「さび」(sabi)等等,中國人也不能精確了解其涵義,頂多翻譯為「體貼」、「物哀感觸」、「閑寂恬靜」以及「素樸優雅」。不同風土彼此都有隔閡,想打破障壁深入理解異文化,都比想像難太多。
津田左右吉博士在著作中一再強調、論證「儒教不可能在日本落地生根」、「日本其實不存在儒教」,他對《論語》的相關見解,讓我深感共鳴。很多漢學者認為,閱讀《論語》就能全面理解孔子思想,但津田博士從中國思想發展演變的角度,澈底探究《論語》各篇章內容,發現《論語》出現許多當時中國還沒有的思想。
例如,比對研究荀子與孟子的著作後發現,《論語》有許多戰國時代思想。津田博士明確指出,《論語》不完全是孔語錄,也參雜《孟子》與《荀子》等思想主張。整部《論語》「純孔語錄」的部分,只有「子曰」開頭不到十篇。
參雜不同時代內容的狀況,也出現在其他中國古代典籍,這可說是非常普遍的基本現象。比如,公認是中國第一部古典文籍與最早歷史文獻的《書經》(尚書),漢代就出現《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的真偽論爭。這項論爭持續近二千年,直到清代考據學者閻若璩精密考證,才確認《古文尚書》是孔子子孫孔安國〔譯按:西漢經學家,孔子十一代孫〕偽作。
這些年來,流通全球的仿冒商品,高達近九成產自中國。製造「假貨」早就是中國人的習慣,古代中國兵法家推崇「詐道」;孫吳兵法等兵法著作,更有許多「詐術」。「偽經」、「偽史」充斥,造假仿冒顯然是這個國家自古以來的「國風」與「國粹」。
所以,清代出現重視事實真相的「考據學」(考證學),也算不容易了。
相對於此,日本社會不太需要類似這種「辨偽」的學問。因為日本人自古養成清明潔白的心靈,最重視純潔與至誠,那已經成為日本社會的精神基礎和共同性格,所以自古以來,日本社會不需要辨別真假的「辨偽學」。
日本人和中國還有一項明顯差異,那就是中國人自古喜歡專制獨裁,日本則是多元社會,重視存異求同、「和」好相處。比如,針對「仁義」如何解釋,中國社會絕不許有人提出「反命題」(Antithese),日本人的做法則不同。
比如,伊達政宗「家訓」強調,「過仁則弱,過義則固,過禮則諂,過智則偽,過信則損」,呈現和中國人完全不同的倫理觀。
明治時代政治家陸奧宗光在獄中翻譯英國哲學家邊沁的《功利主義》,了解所謂「義」,其實就是「利」。中國也曾經出現類似的思想主張,那就是墨子,但宗光這樣的政治家乃至於墨子的思想主張,終究不見容於中國社會。換言之,中國人根本缺點是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卻不在乎,缺乏開放與多元的價值觀。
話說回來,《論語》應如何解讀,從什麼角度看待?基本上,中國人多半把《論語》視為能用來治理國家的「政治理論」,有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反之,古代日本人認為,《論語》是闡述「修身」方法的著作。只是我不免困惑,只讀《論語》就能了解為人處世之道嗎?
認識《論語》
▍一、從舉國人民讀誦《論語》的社會看清《論語》真相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讀《論語》的知識份子比江戶時代少得多,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加稀少。另一方面,和日本維新同時代的清朝,也爆發追求「洋化」(西洋化)或維護「國風」(傳統文化思想)的論戰。
至少到一九○五年廢除科舉制度為止,清朝知識份子的思想主張可說有兩大派,一派是皓首窮經、終生背誦《論語》等《四書五經》及其注疏,希望藉此「登龍門」、取得科舉功名的文人;另一派是太平天國等斷然禁除儒學的叛亂集團所建立的政治勢力範圍。
進入二十世紀,中國「支持」與「反對」儒學的二分化現象從未斷絕,雙方的對抗,可說從帝國、民國到人民共和國時代綿延不絕。另外,日本人與中國人對《論語》的理解與看法有的類似,有的完全不同。事實上,日本學者乃至於知識份子、文化人,對《論語》等中國思想主張經常出現誤解甚至曲解,也有很多人不清楚中國倫理與歷史社會的關係。以下是我的幾點淺見:
①有人認為,就是因為今天讀《論語》的人變少,所以日本道德頹廢、犯罪激增,但這種主張毫無根據。事實剛好相反,中國以儒教為國教超過二千年,即使中國人這麼長時期大量閱讀《論語》、《四書五經》,推廣「三德」、「四維」、「五倫」等教化,結果還不是變成堪稱全球「最無道德感」的國家?
②包括《論語》在內的中國《四書五經》,到處都是「仁義」與「道德」等訓示與主張。深入探究後發現,中國古代典籍的眾多道德宣示,都不是那個時代中國的「實況」,而是相反的情形,正因為「沒有」,所以需要大力鼓吹。換言之,《四書五經》所寫的都是「當為」,不料江戶儒學者卻誤以為中國古典著作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描繪,從而產生錯覺,以為中國是「仁義之國」、「道德之國」、「聖人之國」。換言之,其實很多中國人都有一種習慣,那就是「社會上不存在的東西,只好在書本裡大肆宣稱」。
③西洋頂尖哲學家黑格爾與馬克斯.韋伯都指出,儒教道德價值不高,給予很低的評價。中國人道德如此低落的原因,很多人從文化與社會層面尋找各種說明,但我想最根本的癥結是,中國人因為信奉儒教,結果反而喪失了「良心」。
④日本近代化功臣之一澀澤榮一(一八四○∼一九三一)寫了一本《論語與算盤》。第二世界大戰後也有一些日本學者撰寫《論語經濟學》,或者模仿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說「儒教精神」是中國近代化的主要動因。但事實上,儒教掌控中國人的腦袋二千年,根本不曾重視商人,「反商」其實正是儒教的核心教條。
雖然《論語》等《四書五經》都是所謂的「經世濟民之學」,超過二千年被中國人認定為最有價值的學問,但從實證主義史觀的角度觀察,《四書五經》能否稱得上是「經世之學」?還得看中國社會如何演變。結果卻發現,這些學問主張與社會的實際發展毫無關聯,中國所謂的「經世之學」根本是作文比賽,只是學者的空思妄想罷了。
從十八世紀末白蓮教之亂到二十世紀文革結束為止,中國近二百年天下大亂。首先,北方的宗教集團白蓮教叛變,「捻軍」大約數萬人攻入山東省,搗毀孔廟在內的孔子家族宗廟與墳墓,孔氏子孫遭受屠殺。南方也有信仰基督教的宗教集團「拜上帝會」,成立太平天國後禁止儒教,颳起「反儒」風暴,動盪持續到二十世紀。
台灣出生的我,未曾經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儒批孔,中小學一直到高中,唸的是台灣中華民國所實施的儒教教育。而且,進入國民小學之前,我跟隨「漢學老師」讀誦《三字經》、《千字文》以及「四書」的《大學》、《論語》、《孟子》等等,用朱筆標記句讀,努力背誦文章。
高中國文課本則充斥朱子學與陽明學的文章及注疏,而且必須背誦《論語》。原本是生活用語的成語,很多也納入儒教系統,拼命「說教」。這樣的社會,當然是扭曲異常。事實上,不只《論語》,《四書五經》等中國古文都有許多意思模糊、難以理解之處,自古以來因而出現很多爭論。針對這部分,我有以下幾點看法:
①不只《論語》,幾乎中國古代經書都得倚賴大量注與疏,否則難以理解其原意;但各家看法不同,特別是與《論語》相關、名為「正義」的注疏,更是眾說紛紜。甚至,就連如何斷句,各「學派」都有不同主張。除此之外,許多注疏者有其政治目的,從而牽扯各種利害。
②針對古典經書進行注或疏的大學者,除了必須擁有豐富「經」的知識,也得熟稔「史」、「詩」、「集」等知識,以及對時代的透徹認識。因此各家解釋不同,乃屬當然。
③中國古代經書遣詞用字簡練,句子壓縮得很短,因此不只注疏,就連精確掌握語彙內容、傳達其概念,都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
④《論語》很早就傳到日本,到了江戶時代,出現各種《論語》相關的「正義」(解釋),其中有些頗具創見,展現日本人特有觀點,成就斐然。但江戶距離孔子時代相當遙遠,加上日中兩國文化與文明差異,許多《論語》詞句無法精確譯為日語,即便今天進行《論語》的「現代語譯」,仍然很難符合原意。這是日本人理解《論語》的侷限。
⑤日本有許多《論語》的「現代語譯」版本,雖然做了相當大的努力,但不諱言,仍有許多誤譯與誤解。這可說和學識的造詣深淺無關,而是時代與文化差異的限制所致,日本人確實很難精確透徹地了解《論語》原文。
⑥《論語》一書不只呈現孔子的人生觀與天下觀,提出他對那個時代的看法與價值觀,背後其實也有改變社會與國家的政治目的。不容否認,古希臘、古印度乃至於古中國,都有一些普世的人生觀與萬古不易的人類共有價值觀,這些人生觀與價值觀凝聚成的知識與智慧,確實值得後人學習、傳承,但沒必要反覆背誦,當成教條。在我看來,中國人拼命背誦論語、「非背不可」,已經是一種變態。這也是我對「論語在中國」的基本判斷。
▍二、《論語》的真面目
很多人認為,《論語》是關於「修身」也就是品格教養的著作。要成為社會大眾品格教養的教科書,前提是民眾普遍閱讀,但事實上,《論語》普及的時間點比佛經大眾化來得晚。《論語》一開始是「孔子補習班」的「政論教材」,主要是鋪陳以禮及仁為工具、用來改變社會的方法,堪稱是「推銷、說教色彩濃厚」的說帖。換言之,孔子再傳弟子們把孔子發牢騷、罵人的話編成《論語》,一開始動機就是政治目的。
紙張普及之前,中國人是以甲骨、金石、木竹與布帛作為書寫工具。這些工具並不方便,所以中國古文非常簡練,字數極度壓縮,因此如前所述,想正確閱讀古文,得依賴「注」以及堪稱「注之注」的「疏」。
首先,《論語》成立於何時,這部分就有各種不同說法。可以確認的是,該書在孔子死後才成立,而且是孔子死後數百年的漢代、經由眾人合力編纂完成。許多研究者指出,《論語》出現太多「孔子那個時代不可能有的想法或遣詞用字」。
另外,孔子是否曾閱讀《易經》,學者之間也有許多爭論。孔子是春秋時代末期的人,《論語》卻出現許多戰國時代常見用語,以及再傳弟子孟子甚至更後面的荀子等各種論述,可見,與其說《論語》是孔子語錄,不如視之為古代儒家的思想摘要。
當然,《論語》即便不完全是二千五百年前孔子這個人的語錄,然而漢代之後許多大學者進行注與疏,日本儒學者也有許多有關「論語正義」的注疏研究,出現非常多具創意、獨特的見解。特別是日本學者提出不少有關《論語》的獨特看法,獲得中國漢學者的高度評價。
《論語》有《古論》、《齊論》、《魯論》三種版本,合計高達數百篇。江戶時代,日本學者伊藤仁齋根據漢代王充的《論衡.正說篇》與皇侃的《論語義疏》進行考證,整理出上論十篇與下論十篇,合計二十篇的《論語》。
伊藤仁齋的《論語古義》和荻生徂徠的《論語徵》,都是日本儒學指標、獨特性的儒學論述。日本漢學者的《論語》研究與注疏,許多見解超越中國學者,但我仍不免疑惑,距離孔子時代那麼遙遠,日中兩國風土也完全不同,日本人真的能正確解讀《論語》?
同理,西洋思想哲學與東洋思想哲學,內涵大相逕庭。我曾寫一篇討論空海《十住心論》與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論文,打算請台灣某大學教授歐洲現象學的朋友「漢譯」,卻被那位做過西田哲學研究的友人婉拒,說:「漢語在這些哲學領域的表達能力嚴重不足,不可能完成漢譯」。
確實如此,日本與中國歷史文化乃至於風土都有明顯差異,特別是萬世一系的日本政治架構與不斷易姓革命的中國,文化與文明架構乃至於社會都全然不同,加上文字與語言體系差異,所以「仁」、「恕」這類儒教特有概念,不要說日本人,就連中國人也都一知半解。反之,日本人特有的「思いやり」(omoiyari),乃至於「もののあはれ」(mononoaware)、「わび」(wabi)、「さび」(sabi)等等,中國人也不能精確了解其涵義,頂多翻譯為「體貼」、「物哀感觸」、「閑寂恬靜」以及「素樸優雅」。不同風土彼此都有隔閡,想打破障壁深入理解異文化,都比想像難太多。
津田左右吉博士在著作中一再強調、論證「儒教不可能在日本落地生根」、「日本其實不存在儒教」,他對《論語》的相關見解,讓我深感共鳴。很多漢學者認為,閱讀《論語》就能全面理解孔子思想,但津田博士從中國思想發展演變的角度,澈底探究《論語》各篇章內容,發現《論語》出現許多當時中國還沒有的思想。
例如,比對研究荀子與孟子的著作後發現,《論語》有許多戰國時代思想。津田博士明確指出,《論語》不完全是孔語錄,也參雜《孟子》與《荀子》等思想主張。整部《論語》「純孔語錄」的部分,只有「子曰」開頭不到十篇。
參雜不同時代內容的狀況,也出現在其他中國古代典籍,這可說是非常普遍的基本現象。比如,公認是中國第一部古典文籍與最早歷史文獻的《書經》(尚書),漢代就出現《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的真偽論爭。這項論爭持續近二千年,直到清代考據學者閻若璩精密考證,才確認《古文尚書》是孔子子孫孔安國〔譯按:西漢經學家,孔子十一代孫〕偽作。
這些年來,流通全球的仿冒商品,高達近九成產自中國。製造「假貨」早就是中國人的習慣,古代中國兵法家推崇「詐道」;孫吳兵法等兵法著作,更有許多「詐術」。「偽經」、「偽史」充斥,造假仿冒顯然是這個國家自古以來的「國風」與「國粹」。
所以,清代出現重視事實真相的「考據學」(考證學),也算不容易了。
相對於此,日本社會不太需要類似這種「辨偽」的學問。因為日本人自古養成清明潔白的心靈,最重視純潔與至誠,那已經成為日本社會的精神基礎和共同性格,所以自古以來,日本社會不需要辨別真假的「辨偽學」。
日本人和中國還有一項明顯差異,那就是中國人自古喜歡專制獨裁,日本則是多元社會,重視存異求同、「和」好相處。比如,針對「仁義」如何解釋,中國社會絕不許有人提出「反命題」(Antithese),日本人的做法則不同。
比如,伊達政宗「家訓」強調,「過仁則弱,過義則固,過禮則諂,過智則偽,過信則損」,呈現和中國人完全不同的倫理觀。
明治時代政治家陸奧宗光在獄中翻譯英國哲學家邊沁的《功利主義》,了解所謂「義」,其實就是「利」。中國也曾經出現類似的思想主張,那就是墨子,但宗光這樣的政治家乃至於墨子的思想主張,終究不見容於中國社會。換言之,中國人根本缺點是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卻不在乎,缺乏開放與多元的價值觀。
話說回來,《論語》應如何解讀,從什麼角度看待?基本上,中國人多半把《論語》視為能用來治理國家的「政治理論」,有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反之,古代日本人認為,《論語》是闡述「修身」方法的著作。只是我不免困惑,只讀《論語》就能了解為人處世之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