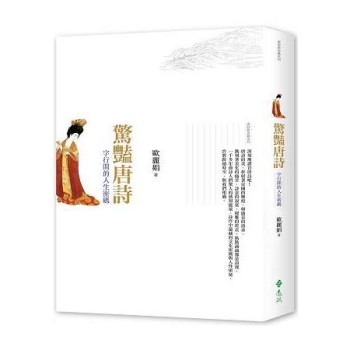〈〈錦瑟〉詩的意象特點〉
美麗與哀愁的共同結晶
現在我們來看〈錦瑟〉這首詩: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詩中的意象充滿了淒美浪漫的情調,但首先必須注意到,不僅這首詩的創作時間是在作者人生的最終時刻,並且其中所運用的意象也都是李商隱一生所偏好的集大成,過去在創作文字中持續閃爍的吉光片羽,都匯聚到這首壓卷的代表作裡。
其實,凡是李商隱所好用的詩歌意象,大都具有同一特點,也就是美麗與哀愁的共同結晶,「錦瑟」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種意象,其他還有「曉夢」、「春心」、「無端」等等。以「春心」而言,這個詞一共出現兩次,包括:「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無題四首〉之二),以及〈錦瑟〉這首詩所說的「望帝春心託杜鵑」。追蹤這個詞彙最早的源頭,是來自《楚辭‧招魂》的「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如此一來,屈原那執著不悔的、浪漫多情的精神已經為它灌注了純淨優美的血脈。
這是一份無比純潔、執著、美好的心靈,可又那麼脆弱而容易受到傷害,於是李商隱的詩中更常出現「傷春」這個詞,例如:
‧我為傷春心自醉,不勞君勸石榴花。(〈寄惱韓同年二首〉之二)
‧年華無一事,只是自傷春。(〈清河〉)
‧莫驚五勝埋香骨,地下傷春亦白頭。(〈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閑話戲作〉)
‧曾苦傷春不忍聽,鳳城何處有花枝。(〈流鶯〉)
‧君問傷春句,千辭不可刪。(〈朱槿花二首〉之二)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曲江〉)
‧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落花〉)
其中,〈落花〉詩所說的「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雖然沒有直接出現「傷春」這個詞彙,但其實更加清楚地表現出傷春的悲哀,因為那份無比美好的心靈,隨著春天的流逝逐漸殘缺殆盡,而所得的竟只有沾衣的眼淚而已。這已經初步顯示了李商隱一心追求美好的事物,卻又總是受到傷害的人生體驗。而李商隱對這樣的人生充滿了無法理解的困惑,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遭遇?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而造成這些現象的道理又何在?往往油然生起一種莫名所以的、無緣無故的無奈感,於是常常發出「無端」的感慨,成為李商隱詩中常常出現的語詞,諸如:
‧潭州官舍暮樓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潭州〉)
‧秋蝶無端麗,寒花只暫香。(〈屬疾〉)
‧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為有〉)
‧雲鬢無端怨別離,十年移易住山期。(〈別智玄法師〉)
‧人豈無端別,猿應有意哀。(〈晉昌晚歸馬上贈〉)
這些例句,都以「無端」表達一種事出意外、難以言詮而莫名所以的感受。不過,以上這幾個詞雖然在數量上頗為令人注目,卻並不是李商隱的特有現象,而是中晚唐詩人普遍常見的慣用詞,搜尋起來,不僅數量很多,而且內涵也很相近;因此,真正專屬於李商隱的專利,可以展現出他與眾不同的美學品味與心靈趨向的,是「曉夢」和「錦瑟」這兩個用語。
在《全唐詩》裡,「曉夢」這個詞一共出現二十一次,李商隱就占了四次,將近五分之一,是別的詩人所難以望其項背的,包括:
‧可要五更驚曉夢,不辭風雪為陽烏。(〈賦得雞〉)
‧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盤。(〈詠史〉)
‧山驛荒涼白竹扉,殘燈向曉夢清暉。(〈夢令狐學士〉)
當然還有〈錦瑟〉這首詩的「莊生曉夢迷蝴蝶」,可見李商隱對這個詞彙的鍾愛。「曉夢」就是清晨破曉時所作的夢,由於接近日出的時刻,又是清醒之前所作的最後一場夢,因此曉夢的特點是短暫而清晰,正道出了追憶平生時,那記憶猶新卻又稍縱即逝的感受;何況「莊生曉夢迷蝴蝶」的夢境是如此美麗繽紛,有如莊子夢蝶一般,彩翼雙飛,栩栩然、翩翩然,與繁花互相輝映,夢中人當然流連忘返,沉迷不可自拔。
果然,李商隱直接提到「蝴蝶」的詩篇,約計有二十九首,並且這些蝴蝶意象多用於其首創的無題和準無題詩,點綴在詩人的夢裡夢外,正是那一片春心的化身;然而那小小的、輕盈的春天精靈,同樣是那麼脆弱而容易受到傷害,與春花一樣短暫,可以說是「傷春」的典型事物,點綴在曉夢中,更增加好夢難留的惆悵感。
更值得注意的是「錦瑟」這個意象,《全唐詩》裡總共只出現十一次,單單李商隱便用了四次,包括:‧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房中曲〉)
‧新知他日好,錦瑟傍朱櫳。(〈寓目〉)
‧玉盤迸淚傷心數,錦瑟驚絃破夢頻。(〈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之二)
再加上〈錦瑟〉這首詩,比例高達三分之一強!最關鍵的是,〈錦瑟〉這首詩也是《全唐詩》中唯一一首用「錦瑟」作標題的詩篇。換句話說,唐代的兩千兩百多位詩人中,沒有一個像李商隱一樣,眼光在錦瑟上流連注目,凝視著它不肯離開,到最後還全力為錦瑟打造出一首傑作,成為五萬首唐詩裡唯一一首以錦瑟為對象的詠物詩。可想而知,李商隱對之是多麼情有獨鍾!
作為李商隱所鍾愛的詩歌意象,李商隱特別偏好錦瑟的原因,一是它的美麗高貴。「錦」是華麗的織物,與「錦繡」有關的詞彙都是最美麗的象徵,所謂錦繡文章、錦繡大地、錦心繡口,都是如此;同樣地,瑟加上「錦」字,可見造型十分精美。《周禮•樂器圖》云:「雅瑟二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飾以寶玉者曰寶瑟,繪文如錦者曰錦瑟。」可見錦瑟的美不是珠光寶氣的寶瑟,而是以「繪文如錦」展現出人文藝術的文化精神,代表一種知識的、性靈的美。
至於李商隱特別偏好的原因之二,則是「瑟」這種樂器本為悲哀的象徵,來自一個神話傳說,出於《史記‧封禪書》所載:
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原來「瑟」本身就是一個哀愁的意象,瑟之所以為二十五根絃,是被減半的結果,原本的五十根絃悲淒愴楚至極,甚至連太上忘情的天神也為之動容,到了完全無法承受的地步。可見瑟這種樂器的聲調何其哀怨,它那內在深蘊著的哀傷,令人推測如果琴絃加倍的話,就連最偉大的神也都會被悲哀淹沒。這可以說是一個後設的神話,用來解釋瑟的悲劇感染力,而濃厚的神話色彩更反過來使它染上了迷離淒美的深沉悲劇感。李商隱不僅選了瑟這個悲哀的樂器,更偏偏要用五十根絃的瑟,所謂「錦瑟無端五十絃」,一方面是切合當時的年齡約數,一方面更是要藉以傳達那「載不動許多愁」的悲劇一生。於是,錦瑟這種文彩華美卻音聲甚悲的樂器,金玉其外、酸澀其內,代表了一種柔美深情的心靈,而寓有無限的沉痛與悲感,本來就是一個美麗與哀愁的共同結晶。就像李商隱的心靈和他的人生一樣,努力追求美麗,但美麗卻同時滲透了悲傷的淚水,很美又很沉重,遂成為李商隱反覆致意的一個特殊象徵。
四句神話傳說,迷離不清的暈染效果
除了大量總匯了這類美麗與哀愁的意象之外,〈錦瑟〉這首詩的第二大特點,就是充滿了迷離不清的暈染效果,而這種效果主要是運用超現實的神話傳說來達到的。
第一句的「錦瑟無端五十絃」已經開啟了神話視野,中間兩聯的四句更是一路神遊物外,讓我們深入到陸地、海底中展開無限的想像。以第三句的「莊生曉夢迷蝴蝶」來看,此句用「莊周夢蝶」的典故,《莊子‧齊物論》云: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其中夢是虛幻的,化蝶更是幻中之幻,一切都失去了真實的界限,已經展開了一個超現實的空間。
接下來的第四句「望帝春心託杜鵑」,運用的是周朝末年蜀王望帝死後化為杜鵑(即子規)鳥的傳說,來表達一種生生世世傳承不絕的執著。《說文解字‧隹部》於「巂」字下云:「一曰蜀王望帝婬其相(即鱉靈)妻,慚,亡去,為子巂(即子規)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曰是望帝也。」又唐代劉良注左思〈蜀都賦〉時,引《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為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另外,晉朝常璩《華陽國志‧蜀志》亦載:
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案:開明即鱉靈之號)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各種的傳說版本有詳有簡,互有出入之處,但都表現了一種生死不移的執著,而人鳥之間的異類轉化、世世代代的生命流轉,都只有在傳說中才能出現。同時,望帝化為杜鵑鳥,又延續了莊周夢蝶的物化形態,只是一個迷醉不已、一個悲願不息,都表現出不為現實所拘限的超越性。
至於第五句的「滄海月明珠有淚」,更可以說是李商隱運用典故純熟至極的表現,把「月明珠圓」及「鮫人泣珠」兩個傳說巧妙地融為一爐,毫無「獺祭魚」式的堆砌,反倒天衣無縫、出神入化。前一個典故反映了古代天人感應的連動思維,左思〈吳都賦〉云:「蚌蛤珠胎,與月虧全。」李善注引《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意謂蚌珠隨月亮圓缺的形狀而產生相應的變化,則當月明之時,蚌珠的形態體積勢必最為碩大圓潤。
鮫人泣珠的故事則見於《博物志》卷三:
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
又左思〈吳都賦〉劉良注云:
鮫人,水底居也。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據此而言,珍珠便是海中鮫人的眼淚所化成的。如此一來,「月明珠圓」及「鮫人泣珠」這兩個傳說就擴大了眼淚的滲透力,形成了以下的等同關係:
月(明)=珠(碩大)=眼淚(盈溢)=悲傷哀淒(至痛)
於是從天上的月亮到海中的珍珠,都被淚水所浸透,處處也就瀰漫著悲哀的本質;何況那由淚水所凝結而成的碩大珍珠上,竟又「有淚」,是為「淚中之淚」,原來眼淚作為悲哀的結果,又可以進一步悲哀到流出眼淚,那淚水綿延不盡又生生不息,其悲哀傷痛的非常程度實在難以想像!
接下來,李商隱從另一個截然相反的角度,跳躍到溫馨和暖的幸福體驗,第六句「藍田日暖玉生煙」呈現了一片春夏沖融的氤氳氣息。藍田,又名玉山、覆車山,在今陝西藍田縣,唐朝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七引《京兆記》云:「藍田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而李商隱這一句所用的意象,很可能是來自中唐詩人戴叔倫所說的幾句話,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八提到:
司空表聖(案:即晚唐詩人司空圖)云:「戴容州(案:即戴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這一句雖然不是來自神話傳說,仍然充滿了一種神話世界般的意境,那「玉生煙」的景象可望而不可及,可遠觀而不可近看,可以具體感受卻無從描述,有如置身於寧靜安詳的樂園裡。
「遺貌取神」,回顧一生的過眼雲煙
解釋至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指出,李商隱之所以要運用超現實的神話傳說來達到迷離不清的暈染效果,主要就是為了呈現「追憶」的特質。
一開始李商隱就說「錦瑟無端五十絃」,以「五十絃」為言者,乃如李商隱在〈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一詩中所說的「雨打湘靈五十絃」一般,都是捨棄現實世界中瑟器二十五絃的通俗形製,以極言其人神同悲的哀淒怨苦;又因為「五十」之整數恰恰是李商隱此際年歲的近似值,更能夠觸動詩人因物起興的微妙感應,所以下一句便接言「一絃一柱思華年」,意謂五十根絃繫在五十根琴柱上,每一絃一柱都令人想到過去四十七年來的美好時光,從而引發中間兩聯四種不同的人生感受。
然而,「錦瑟五十絃」固然完備地呈現其一生的整體歷程,卻又加以「無端」一詞,則更添注一種無可奈何的迷惘惆悵之情。「無端」者,謂無緣無故、沒有原因;一說為「無心」之意,其實應以前者為是。也就是當詩人面對如此兼具美麗與哀愁的錦瑟時,內心中所興起的,竟是一種難以理解而充滿疑惑的無端之感。原來整個一生悲歡離合的經歷與喜怒哀樂的遭遇竟然都是無法解釋,也無從究詰,更欠缺理性的答案;一切都是冥冥中一股無名力量的展現,它隱身在茫昧之中隨意撥弄命運的齒輪,於是被迫啟動而不斷向前展開的無常人生,「存在」的本身就是一切的解答。
換言之,無論是幸或不幸,是美麗或哀愁,是人生際遇或歷史發展,都是出自那深不可測的形上命運的奇異決策,受贈者只能被動承接命定的結果,根本無從預知,也無力抗拒,更不可能扣問答案。因此,當李商隱在代表了一生的「五十絃」之前冠以「無端」一語,便深深呈現出李商隱回首一生的前塵往事時,那種無以名狀、難以言詮的迷惘之感。因此清人薛雪評曰:此詩全在起句「無端」二字,通體妙處,俱從此出。意云:錦瑟一絃一柱,已足令人悵望年華,不知何故有此許多絃柱,令人悵望不盡;全似埋怨錦瑟無端有此絃柱,遂致無端有此悵望。卽達若莊生,亦迷曉夢;魂為杜宇,猶託春心。滄海珠光,無非是淚;藍田玉氣,恍若生煙。觸此情懷,垂垂追溯,當時種種,盡付惘然。對錦瑟而興悲,歎無端而感切。如此體會,則詩神詩旨,躍然紙上。(《一瓢詩話》)
被「五十絃」所觸動的詩人,在悵望不已之後,禁不住從「五十絃」的籠統中進一步深入,將此無端形成的五十絃一一玩味、細細尋索,而產生「一絃一柱思華年」的悠然懷想。
所謂「華年」者,與一般作為「年歲」同義詞的「年華」不同,意指美好的歲月。此處作「華年」而不作「年華」,固然是因為「華年」一詞以「年」字為句尾,正可以和全詩押韻,而更收音節流動諧暢的音樂美感;但另一方面,「年華」一語不過是對人生歲月的泛泛描述,具備的僅僅是對應於物理現象的客觀意義,而「華年」一詞則是對此人生歲月無比珍愛的特殊指稱,其中蘊含的更是一種出於個人情感的主觀評價。
換言之,無論一生遍歷多少傷痛苦楚,詩人對這樣的一生都還是充滿了珍愛憐惜之情,因此生命中所經歷的每一年、每一事,都同樣促使他緬懷不已;或者說,詩人對他所經歷的每一年、每一事,都那麼清楚地意識到它的存在重量,因此事事物物都深深刻鏤在他的生命歷程中,有如淪肌浹髓般無時或忘。
如此,則「思」字並不僅僅是出於情感耽湎的「懷思」之思,而也是來自心靈觀照的「省思」之思。對過去一生種種情事既懷思又省思的李商隱,在一往情深的耽迷之中,卻又深深體認到一往不返的幻滅,當那眷戀難捨的懷思與悲觀察照的省思交織雜糅之際,便迴盪出一首纏綿悱惻的哀歌。
而接下來的「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這四句,分別是李商隱所懷思的華年中,種種令他終身緬懷不已的遭遇與感受,同時也直接貫徹到第七句的「此情可待成追憶」,是為「此情」所綜攝的幾個內涵。首先,「莊生曉夢迷蝴蝶」即領銜展現出一種耽溺執迷的情感型態,而這正是李商隱性格中最鮮明的一個特徵。此句用莊周夢蝶的典故,但李商隱除了藉以呈現他對人生中美好事物深深沉湎的忘我情境之外,復又加上原典所無的「曉」字、「迷」字,用以表現往事的美好如清晨的曉夢般短暫,卻又如蝴蝶般令人深深眷戀而迷醉。清晨時那令人迷醉的美夢是何其清晰,又何其短暫!
李商隱便藉由這樣的曉夢傳達了無限美好、無比眷戀卻又無力挽留的無奈愴痛,如此一來,整句詩非但沒有莊子的達觀逍遙,更欠缺與萬物同化的灑脫自適,反而帶有李商隱特有的性格烙印――亦即將全部的情感投注在美好卻十分短暫的對象上,一往情深而執迷不悔。當他將全部的情感投入時,獲得的固然是酣然昇華的深美體驗,然而因為投入其全部情感的對象卻只有極為短暫的存在時間,則傾心投入之後不久,便幾乎是立刻就要面臨幻滅,那先前投入的全部情感因為失去基點而陡然落空,整個生命也就勢必被架空而徬徨無託。
因此,在投入了全部的情感之後,那如清晨曉夢般令人沉迷的短暫時光,就像流星霎時照亮了生命的黑幕卻又瞬間消逝,除了留下清晰的回憶之外,便只創造出無盡的苦澀與無望的緬懷;徬徨無所託的熾熱情感又必須尋求出路,於是終其一生,李商隱都在迷醉與幻滅中擺盪掙扎,塑造出一個失落了美好記憶而在無垠的黑暗中徬徨無依的靈魂,注定只能孤獨地在無底的深淵中無望追尋。
而此一追尋僅僅只用「春蠶到死絲方盡」的一生是不夠的,為了把情感意志繼續擴延下去,就必須跨越死亡的界線,更進一步將希望託諸來生的緣會。因此接著「莊生曉夢迷蝴蝶」之後的「望帝春心託杜鵑」一句,便是運用周朝末年蜀王望帝死後化為杜鵑鳥的傳說,來表達一種永世不息的盼望。李商隱在原始內容上又復添加了「春心」與「託」字,則更傳達其情志如春般的珍貴芳美,以及那嘔心泣血般的悲淒哀苦;而這美好卻悽愴的心靈,將如望帝一般寄託在杜鵑鳥世世代代的啼鳴中而永恆不絕、生死不滅。其「美好」啟下聯下句的「藍田日暖玉生煙」,而其「悽愴」則引出下聯上句的「滄海月明珠有淚」。「月明珠圓」及「鮫人泣珠」兩個典故經過李商隱的融併裁鑄之後,便產生了新的意義,即在此月明之際,由淚所凝成的珠最為碩大圓潤;而這同時,最充盈飽滿的眼淚之上竟又「有淚」,這就形成了「淚中之淚」此一哀甚悲絕的徹底傷心之境。此乃昔日人生遭遇中,包括漂泊之苦、喪妻之痛和失志之悲在內的種種不幸的寫照,而至今淚光依然閃爍。
但除了飽漲的淚水之外,浮光掠影的往事中依然閃現了幾許溫存的記憶,當那記憶被召喚而來時,暖融輕柔的氛圍沁人肌骨,足以令人遍體生春,接下來的「藍田日暖玉生煙」一句,就是總括李商隱一生的甜美夢想的意象感受。全句以日之溫熱、玉之瑩潤和煙之迷離,交織出一種遍身和融、暖馨洋溢的無限溫藹之情,代表過去所擁有過的美好經歷和溫暖感受,但其存在卻如煙似霧一般的虛幻而難以把捉。
整體來看,當李商隱「一絃一柱思華年」時,令他繾綣緬懷的種種追憶,濃縮了人生中重要的各種人生體驗,詩中用「曉夢迷」、「玉生煙」的層層皴染,以及「託杜鵑」、「珠有淚」等神話傳說的幻化虛寫,渲染出極其濃厚的非現實的夢幻色彩,使得全詩籠罩在一片朦朧迷茫的意境中,這正顯示了回顧往事的特質。
李白在〈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一詩中,也寫到他在結束一天的活動之後,「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於下山的小徑上忍不住回首來時路,但當他反觀回顧之所見,已不是歷歷如繪的一草一木,而是「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方才一路行經的風光景致已然瞬間化為昨日黃花,淪滅於遺忘的深淵中,早已瀰漫著一片蒼蒼茫茫的雲霧煙嵐,迷離恍惚,而無從把捉。比觀這首〈錦瑟〉詩,豈不也正是如此?差別只在於李白回顧的只是當天「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的一小段路程,而李商隱回顧的卻是他漫長而曲折的一生,但都體現出「蒼蒼橫翠微」的迷茫之感。
美麗與哀愁的共同結晶
現在我們來看〈錦瑟〉這首詩: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詩中的意象充滿了淒美浪漫的情調,但首先必須注意到,不僅這首詩的創作時間是在作者人生的最終時刻,並且其中所運用的意象也都是李商隱一生所偏好的集大成,過去在創作文字中持續閃爍的吉光片羽,都匯聚到這首壓卷的代表作裡。
其實,凡是李商隱所好用的詩歌意象,大都具有同一特點,也就是美麗與哀愁的共同結晶,「錦瑟」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種意象,其他還有「曉夢」、「春心」、「無端」等等。以「春心」而言,這個詞一共出現兩次,包括:「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無題四首〉之二),以及〈錦瑟〉這首詩所說的「望帝春心託杜鵑」。追蹤這個詞彙最早的源頭,是來自《楚辭‧招魂》的「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如此一來,屈原那執著不悔的、浪漫多情的精神已經為它灌注了純淨優美的血脈。
這是一份無比純潔、執著、美好的心靈,可又那麼脆弱而容易受到傷害,於是李商隱的詩中更常出現「傷春」這個詞,例如:
‧我為傷春心自醉,不勞君勸石榴花。(〈寄惱韓同年二首〉之二)
‧年華無一事,只是自傷春。(〈清河〉)
‧莫驚五勝埋香骨,地下傷春亦白頭。(〈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閑話戲作〉)
‧曾苦傷春不忍聽,鳳城何處有花枝。(〈流鶯〉)
‧君問傷春句,千辭不可刪。(〈朱槿花二首〉之二)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曲江〉)
‧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落花〉)
其中,〈落花〉詩所說的「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雖然沒有直接出現「傷春」這個詞彙,但其實更加清楚地表現出傷春的悲哀,因為那份無比美好的心靈,隨著春天的流逝逐漸殘缺殆盡,而所得的竟只有沾衣的眼淚而已。這已經初步顯示了李商隱一心追求美好的事物,卻又總是受到傷害的人生體驗。而李商隱對這樣的人生充滿了無法理解的困惑,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遭遇?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而造成這些現象的道理又何在?往往油然生起一種莫名所以的、無緣無故的無奈感,於是常常發出「無端」的感慨,成為李商隱詩中常常出現的語詞,諸如:
‧潭州官舍暮樓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潭州〉)
‧秋蝶無端麗,寒花只暫香。(〈屬疾〉)
‧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為有〉)
‧雲鬢無端怨別離,十年移易住山期。(〈別智玄法師〉)
‧人豈無端別,猿應有意哀。(〈晉昌晚歸馬上贈〉)
這些例句,都以「無端」表達一種事出意外、難以言詮而莫名所以的感受。不過,以上這幾個詞雖然在數量上頗為令人注目,卻並不是李商隱的特有現象,而是中晚唐詩人普遍常見的慣用詞,搜尋起來,不僅數量很多,而且內涵也很相近;因此,真正專屬於李商隱的專利,可以展現出他與眾不同的美學品味與心靈趨向的,是「曉夢」和「錦瑟」這兩個用語。
在《全唐詩》裡,「曉夢」這個詞一共出現二十一次,李商隱就占了四次,將近五分之一,是別的詩人所難以望其項背的,包括:
‧可要五更驚曉夢,不辭風雪為陽烏。(〈賦得雞〉)
‧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盤。(〈詠史〉)
‧山驛荒涼白竹扉,殘燈向曉夢清暉。(〈夢令狐學士〉)
當然還有〈錦瑟〉這首詩的「莊生曉夢迷蝴蝶」,可見李商隱對這個詞彙的鍾愛。「曉夢」就是清晨破曉時所作的夢,由於接近日出的時刻,又是清醒之前所作的最後一場夢,因此曉夢的特點是短暫而清晰,正道出了追憶平生時,那記憶猶新卻又稍縱即逝的感受;何況「莊生曉夢迷蝴蝶」的夢境是如此美麗繽紛,有如莊子夢蝶一般,彩翼雙飛,栩栩然、翩翩然,與繁花互相輝映,夢中人當然流連忘返,沉迷不可自拔。
果然,李商隱直接提到「蝴蝶」的詩篇,約計有二十九首,並且這些蝴蝶意象多用於其首創的無題和準無題詩,點綴在詩人的夢裡夢外,正是那一片春心的化身;然而那小小的、輕盈的春天精靈,同樣是那麼脆弱而容易受到傷害,與春花一樣短暫,可以說是「傷春」的典型事物,點綴在曉夢中,更增加好夢難留的惆悵感。
更值得注意的是「錦瑟」這個意象,《全唐詩》裡總共只出現十一次,單單李商隱便用了四次,包括:‧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房中曲〉)
‧新知他日好,錦瑟傍朱櫳。(〈寓目〉)
‧玉盤迸淚傷心數,錦瑟驚絃破夢頻。(〈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之二)
再加上〈錦瑟〉這首詩,比例高達三分之一強!最關鍵的是,〈錦瑟〉這首詩也是《全唐詩》中唯一一首用「錦瑟」作標題的詩篇。換句話說,唐代的兩千兩百多位詩人中,沒有一個像李商隱一樣,眼光在錦瑟上流連注目,凝視著它不肯離開,到最後還全力為錦瑟打造出一首傑作,成為五萬首唐詩裡唯一一首以錦瑟為對象的詠物詩。可想而知,李商隱對之是多麼情有獨鍾!
作為李商隱所鍾愛的詩歌意象,李商隱特別偏好錦瑟的原因,一是它的美麗高貴。「錦」是華麗的織物,與「錦繡」有關的詞彙都是最美麗的象徵,所謂錦繡文章、錦繡大地、錦心繡口,都是如此;同樣地,瑟加上「錦」字,可見造型十分精美。《周禮•樂器圖》云:「雅瑟二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飾以寶玉者曰寶瑟,繪文如錦者曰錦瑟。」可見錦瑟的美不是珠光寶氣的寶瑟,而是以「繪文如錦」展現出人文藝術的文化精神,代表一種知識的、性靈的美。
至於李商隱特別偏好的原因之二,則是「瑟」這種樂器本為悲哀的象徵,來自一個神話傳說,出於《史記‧封禪書》所載:
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原來「瑟」本身就是一個哀愁的意象,瑟之所以為二十五根絃,是被減半的結果,原本的五十根絃悲淒愴楚至極,甚至連太上忘情的天神也為之動容,到了完全無法承受的地步。可見瑟這種樂器的聲調何其哀怨,它那內在深蘊著的哀傷,令人推測如果琴絃加倍的話,就連最偉大的神也都會被悲哀淹沒。這可以說是一個後設的神話,用來解釋瑟的悲劇感染力,而濃厚的神話色彩更反過來使它染上了迷離淒美的深沉悲劇感。李商隱不僅選了瑟這個悲哀的樂器,更偏偏要用五十根絃的瑟,所謂「錦瑟無端五十絃」,一方面是切合當時的年齡約數,一方面更是要藉以傳達那「載不動許多愁」的悲劇一生。於是,錦瑟這種文彩華美卻音聲甚悲的樂器,金玉其外、酸澀其內,代表了一種柔美深情的心靈,而寓有無限的沉痛與悲感,本來就是一個美麗與哀愁的共同結晶。就像李商隱的心靈和他的人生一樣,努力追求美麗,但美麗卻同時滲透了悲傷的淚水,很美又很沉重,遂成為李商隱反覆致意的一個特殊象徵。
四句神話傳說,迷離不清的暈染效果
除了大量總匯了這類美麗與哀愁的意象之外,〈錦瑟〉這首詩的第二大特點,就是充滿了迷離不清的暈染效果,而這種效果主要是運用超現實的神話傳說來達到的。
第一句的「錦瑟無端五十絃」已經開啟了神話視野,中間兩聯的四句更是一路神遊物外,讓我們深入到陸地、海底中展開無限的想像。以第三句的「莊生曉夢迷蝴蝶」來看,此句用「莊周夢蝶」的典故,《莊子‧齊物論》云: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其中夢是虛幻的,化蝶更是幻中之幻,一切都失去了真實的界限,已經展開了一個超現實的空間。
接下來的第四句「望帝春心託杜鵑」,運用的是周朝末年蜀王望帝死後化為杜鵑(即子規)鳥的傳說,來表達一種生生世世傳承不絕的執著。《說文解字‧隹部》於「巂」字下云:「一曰蜀王望帝婬其相(即鱉靈)妻,慚,亡去,為子巂(即子規)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曰是望帝也。」又唐代劉良注左思〈蜀都賦〉時,引《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為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另外,晉朝常璩《華陽國志‧蜀志》亦載:
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案:開明即鱉靈之號)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各種的傳說版本有詳有簡,互有出入之處,但都表現了一種生死不移的執著,而人鳥之間的異類轉化、世世代代的生命流轉,都只有在傳說中才能出現。同時,望帝化為杜鵑鳥,又延續了莊周夢蝶的物化形態,只是一個迷醉不已、一個悲願不息,都表現出不為現實所拘限的超越性。
至於第五句的「滄海月明珠有淚」,更可以說是李商隱運用典故純熟至極的表現,把「月明珠圓」及「鮫人泣珠」兩個傳說巧妙地融為一爐,毫無「獺祭魚」式的堆砌,反倒天衣無縫、出神入化。前一個典故反映了古代天人感應的連動思維,左思〈吳都賦〉云:「蚌蛤珠胎,與月虧全。」李善注引《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意謂蚌珠隨月亮圓缺的形狀而產生相應的變化,則當月明之時,蚌珠的形態體積勢必最為碩大圓潤。
鮫人泣珠的故事則見於《博物志》卷三:
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
又左思〈吳都賦〉劉良注云:
鮫人,水底居也。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據此而言,珍珠便是海中鮫人的眼淚所化成的。如此一來,「月明珠圓」及「鮫人泣珠」這兩個傳說就擴大了眼淚的滲透力,形成了以下的等同關係:
月(明)=珠(碩大)=眼淚(盈溢)=悲傷哀淒(至痛)
於是從天上的月亮到海中的珍珠,都被淚水所浸透,處處也就瀰漫著悲哀的本質;何況那由淚水所凝結而成的碩大珍珠上,竟又「有淚」,是為「淚中之淚」,原來眼淚作為悲哀的結果,又可以進一步悲哀到流出眼淚,那淚水綿延不盡又生生不息,其悲哀傷痛的非常程度實在難以想像!
接下來,李商隱從另一個截然相反的角度,跳躍到溫馨和暖的幸福體驗,第六句「藍田日暖玉生煙」呈現了一片春夏沖融的氤氳氣息。藍田,又名玉山、覆車山,在今陝西藍田縣,唐朝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七引《京兆記》云:「藍田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而李商隱這一句所用的意象,很可能是來自中唐詩人戴叔倫所說的幾句話,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八提到:
司空表聖(案:即晚唐詩人司空圖)云:「戴容州(案:即戴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這一句雖然不是來自神話傳說,仍然充滿了一種神話世界般的意境,那「玉生煙」的景象可望而不可及,可遠觀而不可近看,可以具體感受卻無從描述,有如置身於寧靜安詳的樂園裡。
「遺貌取神」,回顧一生的過眼雲煙
解釋至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指出,李商隱之所以要運用超現實的神話傳說來達到迷離不清的暈染效果,主要就是為了呈現「追憶」的特質。
一開始李商隱就說「錦瑟無端五十絃」,以「五十絃」為言者,乃如李商隱在〈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一詩中所說的「雨打湘靈五十絃」一般,都是捨棄現實世界中瑟器二十五絃的通俗形製,以極言其人神同悲的哀淒怨苦;又因為「五十」之整數恰恰是李商隱此際年歲的近似值,更能夠觸動詩人因物起興的微妙感應,所以下一句便接言「一絃一柱思華年」,意謂五十根絃繫在五十根琴柱上,每一絃一柱都令人想到過去四十七年來的美好時光,從而引發中間兩聯四種不同的人生感受。
然而,「錦瑟五十絃」固然完備地呈現其一生的整體歷程,卻又加以「無端」一詞,則更添注一種無可奈何的迷惘惆悵之情。「無端」者,謂無緣無故、沒有原因;一說為「無心」之意,其實應以前者為是。也就是當詩人面對如此兼具美麗與哀愁的錦瑟時,內心中所興起的,竟是一種難以理解而充滿疑惑的無端之感。原來整個一生悲歡離合的經歷與喜怒哀樂的遭遇竟然都是無法解釋,也無從究詰,更欠缺理性的答案;一切都是冥冥中一股無名力量的展現,它隱身在茫昧之中隨意撥弄命運的齒輪,於是被迫啟動而不斷向前展開的無常人生,「存在」的本身就是一切的解答。
換言之,無論是幸或不幸,是美麗或哀愁,是人生際遇或歷史發展,都是出自那深不可測的形上命運的奇異決策,受贈者只能被動承接命定的結果,根本無從預知,也無力抗拒,更不可能扣問答案。因此,當李商隱在代表了一生的「五十絃」之前冠以「無端」一語,便深深呈現出李商隱回首一生的前塵往事時,那種無以名狀、難以言詮的迷惘之感。因此清人薛雪評曰:此詩全在起句「無端」二字,通體妙處,俱從此出。意云:錦瑟一絃一柱,已足令人悵望年華,不知何故有此許多絃柱,令人悵望不盡;全似埋怨錦瑟無端有此絃柱,遂致無端有此悵望。卽達若莊生,亦迷曉夢;魂為杜宇,猶託春心。滄海珠光,無非是淚;藍田玉氣,恍若生煙。觸此情懷,垂垂追溯,當時種種,盡付惘然。對錦瑟而興悲,歎無端而感切。如此體會,則詩神詩旨,躍然紙上。(《一瓢詩話》)
被「五十絃」所觸動的詩人,在悵望不已之後,禁不住從「五十絃」的籠統中進一步深入,將此無端形成的五十絃一一玩味、細細尋索,而產生「一絃一柱思華年」的悠然懷想。
所謂「華年」者,與一般作為「年歲」同義詞的「年華」不同,意指美好的歲月。此處作「華年」而不作「年華」,固然是因為「華年」一詞以「年」字為句尾,正可以和全詩押韻,而更收音節流動諧暢的音樂美感;但另一方面,「年華」一語不過是對人生歲月的泛泛描述,具備的僅僅是對應於物理現象的客觀意義,而「華年」一詞則是對此人生歲月無比珍愛的特殊指稱,其中蘊含的更是一種出於個人情感的主觀評價。
換言之,無論一生遍歷多少傷痛苦楚,詩人對這樣的一生都還是充滿了珍愛憐惜之情,因此生命中所經歷的每一年、每一事,都同樣促使他緬懷不已;或者說,詩人對他所經歷的每一年、每一事,都那麼清楚地意識到它的存在重量,因此事事物物都深深刻鏤在他的生命歷程中,有如淪肌浹髓般無時或忘。
如此,則「思」字並不僅僅是出於情感耽湎的「懷思」之思,而也是來自心靈觀照的「省思」之思。對過去一生種種情事既懷思又省思的李商隱,在一往情深的耽迷之中,卻又深深體認到一往不返的幻滅,當那眷戀難捨的懷思與悲觀察照的省思交織雜糅之際,便迴盪出一首纏綿悱惻的哀歌。
而接下來的「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這四句,分別是李商隱所懷思的華年中,種種令他終身緬懷不已的遭遇與感受,同時也直接貫徹到第七句的「此情可待成追憶」,是為「此情」所綜攝的幾個內涵。首先,「莊生曉夢迷蝴蝶」即領銜展現出一種耽溺執迷的情感型態,而這正是李商隱性格中最鮮明的一個特徵。此句用莊周夢蝶的典故,但李商隱除了藉以呈現他對人生中美好事物深深沉湎的忘我情境之外,復又加上原典所無的「曉」字、「迷」字,用以表現往事的美好如清晨的曉夢般短暫,卻又如蝴蝶般令人深深眷戀而迷醉。清晨時那令人迷醉的美夢是何其清晰,又何其短暫!
李商隱便藉由這樣的曉夢傳達了無限美好、無比眷戀卻又無力挽留的無奈愴痛,如此一來,整句詩非但沒有莊子的達觀逍遙,更欠缺與萬物同化的灑脫自適,反而帶有李商隱特有的性格烙印――亦即將全部的情感投注在美好卻十分短暫的對象上,一往情深而執迷不悔。當他將全部的情感投入時,獲得的固然是酣然昇華的深美體驗,然而因為投入其全部情感的對象卻只有極為短暫的存在時間,則傾心投入之後不久,便幾乎是立刻就要面臨幻滅,那先前投入的全部情感因為失去基點而陡然落空,整個生命也就勢必被架空而徬徨無託。
因此,在投入了全部的情感之後,那如清晨曉夢般令人沉迷的短暫時光,就像流星霎時照亮了生命的黑幕卻又瞬間消逝,除了留下清晰的回憶之外,便只創造出無盡的苦澀與無望的緬懷;徬徨無所託的熾熱情感又必須尋求出路,於是終其一生,李商隱都在迷醉與幻滅中擺盪掙扎,塑造出一個失落了美好記憶而在無垠的黑暗中徬徨無依的靈魂,注定只能孤獨地在無底的深淵中無望追尋。
而此一追尋僅僅只用「春蠶到死絲方盡」的一生是不夠的,為了把情感意志繼續擴延下去,就必須跨越死亡的界線,更進一步將希望託諸來生的緣會。因此接著「莊生曉夢迷蝴蝶」之後的「望帝春心託杜鵑」一句,便是運用周朝末年蜀王望帝死後化為杜鵑鳥的傳說,來表達一種永世不息的盼望。李商隱在原始內容上又復添加了「春心」與「託」字,則更傳達其情志如春般的珍貴芳美,以及那嘔心泣血般的悲淒哀苦;而這美好卻悽愴的心靈,將如望帝一般寄託在杜鵑鳥世世代代的啼鳴中而永恆不絕、生死不滅。其「美好」啟下聯下句的「藍田日暖玉生煙」,而其「悽愴」則引出下聯上句的「滄海月明珠有淚」。「月明珠圓」及「鮫人泣珠」兩個典故經過李商隱的融併裁鑄之後,便產生了新的意義,即在此月明之際,由淚所凝成的珠最為碩大圓潤;而這同時,最充盈飽滿的眼淚之上竟又「有淚」,這就形成了「淚中之淚」此一哀甚悲絕的徹底傷心之境。此乃昔日人生遭遇中,包括漂泊之苦、喪妻之痛和失志之悲在內的種種不幸的寫照,而至今淚光依然閃爍。
但除了飽漲的淚水之外,浮光掠影的往事中依然閃現了幾許溫存的記憶,當那記憶被召喚而來時,暖融輕柔的氛圍沁人肌骨,足以令人遍體生春,接下來的「藍田日暖玉生煙」一句,就是總括李商隱一生的甜美夢想的意象感受。全句以日之溫熱、玉之瑩潤和煙之迷離,交織出一種遍身和融、暖馨洋溢的無限溫藹之情,代表過去所擁有過的美好經歷和溫暖感受,但其存在卻如煙似霧一般的虛幻而難以把捉。
整體來看,當李商隱「一絃一柱思華年」時,令他繾綣緬懷的種種追憶,濃縮了人生中重要的各種人生體驗,詩中用「曉夢迷」、「玉生煙」的層層皴染,以及「託杜鵑」、「珠有淚」等神話傳說的幻化虛寫,渲染出極其濃厚的非現實的夢幻色彩,使得全詩籠罩在一片朦朧迷茫的意境中,這正顯示了回顧往事的特質。
李白在〈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一詩中,也寫到他在結束一天的活動之後,「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於下山的小徑上忍不住回首來時路,但當他反觀回顧之所見,已不是歷歷如繪的一草一木,而是「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方才一路行經的風光景致已然瞬間化為昨日黃花,淪滅於遺忘的深淵中,早已瀰漫著一片蒼蒼茫茫的雲霧煙嵐,迷離恍惚,而無從把捉。比觀這首〈錦瑟〉詩,豈不也正是如此?差別只在於李白回顧的只是當天「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的一小段路程,而李商隱回顧的卻是他漫長而曲折的一生,但都體現出「蒼蒼橫翠微」的迷茫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