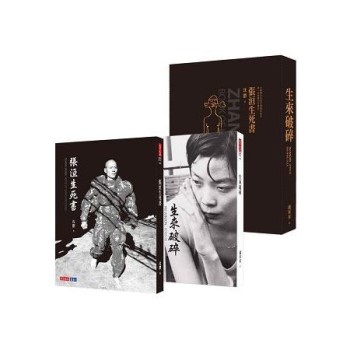《張洹生死書》
前言
張洹來自中國河南歷史悠久的古都安陽,二十世紀九○年代初到北京闖蕩,後成為獨立藝術家。在北京生活的八年,他創作了一大批引起廣泛社會輿論的行為藝術作品,並與其他當時生活在北京東郊大山莊的藝術家們共同創立藝術聚落地「北京東村」,以獨立、反叛、針對現實、身體行為等創作特點,形成了有別於中國藝術史上著名的「圓明園西村」的另一派自由藝術生態。
「我的靈感來源於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小事,如每天吃飯、睡覺、工作、拉屎,在這些極不被人注意的平淡生活中去發現和體會人性的本質。」他說:「在作品過程中我努力要體驗的是生存、身體和真實,而厭惡作品中的表演成分。」秉持這一理念,他的行為藝術呈現出未經粉飾的真實,狀如一顆尖釘,小而強硬,拒不淹沒在改革開放的滾滾洪流中,在時代重錘的擊打之下,發出了屬於個人小而頑強的聲音。
九○年代末期,張洹隻身前往美國,以紐約做為起點,將他的行為藝術版圖擴展至全球,成為最早在國際上引起迴響的中國藝術家之一。他的行為藝術表演經歷了從個人出發並跨越國界與文化的歷程,最終成為當代藝術史上一個獨特的存在,既富有爭議,也值得研究。
「12平方米」、「65KG」、「為無名山增高一米」、「為魚塘增高水位」、「朝聖——紐約風水」、「龍之夢」、「我的澳大利亞」、「家譜」、「水痘」、「朝聖聖地牙哥」、「我的日本」、「梨花飄香」、「上海家譜」、「我的紐約」、「漢堡種子」、「出走」、「日出」、「和平」、「五十顆星」、「舍利子」、「我的悉尼」、「窗」……。北京八年,紐約八年,張洹帶著自己的身體與大腦走遍了世界,他的行為藝術既是個人生活的一種見證,也讓他在求新求變的路上愈走愈遠。最終他選擇放棄行為藝術,只因不願意重複自己。二○○五年回國後,張洹定居上海。自二○○○年以來,他開始做不同材料的裝置和雕塑作品。由於在國外多年積累很多想法,再加上回國後感觸良多,他有許許多多的作品迫切需要實現,從前委託別人製作作品的模式已經不適用,為了更加高效地進行創作,他組建了個人工作室。不知道當時張洹是否已經意識到,他的這個舉動將意謂著開創一種全新的創作機制——請具有不同技術才能的人匯聚一堂,按照一名領導者的想法來集體完成作品。此後,國內日新月異的社會環境使張洹感觸很深,想法層出不窮,工作室隨之進入一個「井噴」式作品高產期。
「回到中國後,我對傳統和信仰有了更深的體會,這種體會就來自於今天的日常生活。於是,我發現了香灰、門板、牛皮……,不斷有新的靈感閃現。傳統是一個民族的身體,信仰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身體和精神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存在。」張洹的感觸,正是中國當下時代發出的聲音,他在這個新的環境中如魚得水,「中國正在全力向前發展,但不可能拋開自身的軀體和精神。回到自己的母語文化,我感到更加腳踏實地和根深柢固。」
張洹的個人工作室由最開始的小規模逐漸發展至員工兩百多人,占地面積五十畝,由門板木雕組、版畫組、油畫組、香灰創作組、香灰基礎組、木工組、焊工組、鍛銅組、標本組、包裝組、後勤組、辦公室等部門構成;員工有五分之一是藝術院校畢業的青年藝術家和作家,也有不同工種的民間傳統工藝師傅。他們來自全國各地,語言、文化各不相同,在規模上創造中國藝術家工作室之最。「這裡是一個工作室,我希望每個人的智慧都能出來,能幫助我、豐富我的想法,我能從每個人的經歷和想法中借鑑一些東西,不管他是藝術家還是非藝術家,我會注重每一個人的亮點。」
一個偶然的機會,張洹在上海靜安寺被香客燒香拜佛的場景觸動,發現了香灰這種特殊的材料,並將其引入到藝術創作中。「香灰畫」橫空出世,在中國已經綿延數千年的宗教儀式殘餘物,成為一種新的符號與表達方式,通過材料的再加工與作品的創作,將香客燒香時內心的祈願力量,轉化為灰燼重生的藝術語言。張洹敏銳地捕捉到歷史、時間、人類內心深處千百年不變的共通點,他成了「香灰之王」,用一種帶有「佛性」的現實主義再次顛覆當代藝術創作的形式與概念。一切似乎籠罩著超現實的感覺,就如香灰畫給人的感覺一樣,似乎有一種無法解釋的力量隱藏在畫面中,飄渺而現實,宏大而沉默。「每年我們從江浙一帶幾十座寺廟請來幾千立方的香灰,寺廟裡拉回來的香灰是放在油桶裡的,通常要繼續燃燒一、兩個月。當香灰運到車間¹裡時仍在燃燒,冒著巨煙和火苗,香灰車間整天瀰漫著煙灰,但是很多人到了那裡都覺得走不動了,覺得那裡面有一種東西,這種東西是莫名奇妙的,你看不到,就像那裡有一個『場』」。
二十多年的藝術實踐讓張洹成了藝術界一個特殊的「角色」,他遠遠不滿足於曾經做過的事情,還渴望去探索更多的領域。於是他做公共藝術,成立公益基金會,現在還要拍電影。這或許是已經到了「知天命」的階段,而另一方面,他對藝術的思考和表現則呈現出超越現實的特徵。
從某個時期開始,張洹在作品中所涉及的幾乎都是形而上的精神層面,內容既關於生命,也關於死亡。毫無疑問,宗教信仰給他的生命打開了更多的維度,彷彿肉體已經無法承載他思考的結果。他追求的是死亡之後的東西——另一個開始,所謂的涅槃,或者……完全歸零、並無限接近永恆。
之所以用不確定的語氣提及這種「永恆」,是因為它基本上無法描述。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永恆」或許更類似於一個模糊的夢。在低維度的生存空間內,人很難、或者幾乎不可能去理解那些超越了生活表象的事物,即便它們往往以最直接、簡單和不留餘地的方式彰顯,比如生和死。
生和死都是大事,但對張洹來說後者的重要性顯然要遠大於前者,這與他所信仰的藏傳佛教有關,但又不僅止於此。在他的思考中,死亡可能不是一個結束,反而是一個開始,全然未知,但又充滿無限的可能性。有時候你很難分辨,宗教究竟是為人解決了問題,還是向你提出了更多的問題,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宗教在某種程度上為生命的種種矛盾和悖論提供了一個出口——輪迴或重生,解脫不在此地而在彼岸,這一世的修行僅僅只是轉世的鋪墊。假如追本溯源,則不難發現:張洹對死亡和死後的世界向來有一種執迷,他一直在研究天葬、古代墓穴和與之相關的文物,似乎想從中找到什麼祕密。因緣際會,後來他成了迄今世界上唯一的漢族天葬師,儘管目前尚未親自主持過天葬儀式,但種種類似的事情無不在他身上營造出一種神祕氛圍——對於那些隱沒在日常生活背後的事物,似乎他的確了解得比旁人更多一些。
北京、紐約、上海、西藏……,張洹用半生時間在不同的地點之間位移,他在每個地方的生命歷程,都如實呈現在不同階段的創作裡。在這個過程中,他不斷修行,也不斷參透著生與死。他認為正能量的死亡並不是死,而是一種開始。無論是出於宗教也好,人生經驗也罷,這一生存哲學不由得令人想到「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他說:「人的命運難以捉摸,有一種神祕的東西在控制我們的命運。」每一個死去的昨天,在他這裡都成了新的開始,輪迴與重生的意義,大概就在於此。
在這本書裡可以看到張洹前半生的經歷,包括他早期在北京從事行為藝術創作背後隱祕而不為人知的艱辛,以及他隻身飄零國外時靈感的爆發與內心的孤獨。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張洹是無法複製的個案,他的藝術創造、他的決絕堅持,以及他身上似乎是與生俱來的那種執拗的力量,一直處於不斷自我進化、不斷改變重生的過程中。
我們有理由相信,張洹多年來觸目所及的一切和內心堅守的世界,某種程度上是超越了現世的另一種存在,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接近並驗證永恆。正如他無比確信地認為自己的前世是藏獒和禿鷲這兩種動物裡的一個,「藏獒只認死理兒,跟我的個性很像,就是一根筋走到底;而禿鷲有一種靈性的、神性的東西,所以它被稱為火鳥。」
所以,這故事離結束還早著呢。
摘自《張洹生死書》
《生來破碎》
胡軍軍答客問:生命包含的潛力,連你自己都驚嘆
天下:一九九二年妳移居北京,從此開展一生的藝術創作。妳什麼時候喜歡上詩歌和繪畫?胡:我自小嗜書如命,童年許多時光在書店裡「蹭書」看。八○年代的家庭沒有太多的零錢可以恣意買書,所以就在書店裡找各種書來讀。小時候的夢想是,有一天我能死在圖書館裡,那一定很幸福。中學時,我參加了所在城市的作文比賽,得了獎,從此我知道自己是個能寫文章的人。我想我不是某一天喜歡上了詩歌和繪畫,而是覺得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天下:妳在北京時剃了光頭,儼然是個頹廢女憤青,能分享當時的心境嗎?
胡:九○年代的北京是非常特殊的一段時期,那時候聚集的詩人、藝術家等等,都很異類,又頗有情懷,大有為了藝術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氣質。當時的社會氛圍還是相當壓抑保守,那些年有一股蠢蠢欲動的暗流洶湧,在這批特殊的人群中傳播擴散,我只是其中一個。青年時期的悲憤也罷、惆悵也罷,甚至憂國憂民,總是天真而無畏的。
天下:妳在北京藝術圈迅速嶄露頭角,不久就獲得當時少數的民間詩歌大獎「劉麗安詩歌獎」,這對當時二十四歲的妳,意義是什麼?
胡:安的存在像一束光,她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我想她是上帝派來的天使。她不僅對我,也幫助了數量眾多的詩人和藝術家們,她的名字應該被銘記和傳誦。
天下:《生來破碎》是妳第一本詩集,也是最後一本詩集,回首爬梳,妳希望這些詩作傳達什麼意念或情感?
胡:其實在北京出過一本詩集,只是沒有公開出版;也發表過一些,在民間和海外的詩歌刊物上。詩歌是為自己而寫,與別人的世界完全無關。這些零碎的文字,如同孤獨中乍現的星星火火,算是對那段歲月的驚鴻一瞥。
天下:在詩歌的創作時期,妳也同時經歷了單身、妻子、母親的人生變化,以及從北京搬居到紐約的文化衝擊,這些生命動盪是否影響了妳的創作?
胡:生命的軌跡不是你自己能設計的,我強烈地感受到,其實所有的劇本都早已寫就了,就等著我們這些芸芸眾生,一個個挑了角色,各演各的戲。生命中的每一個事件都是絲絲相扣的。
天下:在紐約形形色色的人生探索中,妳接觸了佛教,也拜禪宗高僧為師,信仰如何為妳打開新的生命視角?胡:我經常跟朋友分享,如果你真的能領略到佛法所揭示的真相,你的雙腿會不由自主地跪拜下去。佛法給了你一種「觀照」的能力,我們迷糊通常是因為跳不開自我的束縛,所謂「當局者迷」,只有「無我」,才能冷靜而理智地看待生命,所以這樣的影響無日不在我的生活中、創作中,甚至是以後的來世。
天下:在繪畫創作中,妳先是以抽象極簡的網格方式繪製天地自然景物,二○一三年、二○一五年先後舉辦了「山外有山」、「常觀無常」畫展,打開當代藝術的視野。能否分享創作背後的觀念?
胡:我對「觀念性」的藝術一直懷有極大的興趣,年輕時就以「反傳統」為榮。網格這樣的創作方式有點接近禪修時的呼吸法門,只要當下照顧好每一個呼吸,最後呈現什麼已不重要。專注地去描繪每一個格子,都是抽象迷離的,並不代表什麼,也不是要達到什麼。「醉翁之意不在酒」,用在這裡,是很恰當的。
天下:如今妳轉而投入涅槃創作,畫筆下的佛,姿態從容、色彩繽紛、筆觸率真,再現北魏佛像壁畫風采,走向全新的藝術境界。能否分享妳的改變?
胡:以創作「涅槃」佛像為己任,是我這一生最大的轉折,這是一件從未計劃過的、最意想不到的事件。我不敢妄言自己對佛法的領會有多深刻,事實上,如果把佛法的智慧比作大海,我僅只是觸摸到了一滴水珠而已。通常藝術創作裡最強調的是創作者本人的想法,對我來講,在信仰和藝術之間,我選擇了信仰至上,只是依然用藝術形式來表達而已。涅槃寂靜是佛法修行中最高深、最終極的法門,這條「涅槃之道」,我是走定了。從我創作「涅槃」佛像以來,從表象上看似乎我的畫風有了極大的轉變,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其實我說的是同一個意思,只是這個意思終於說明白了,說瞭然了,說透徹了。中國有幾萬座寺院,居然還沒有一座叫「涅槃寺」,也許有朝一日,我懷著拳拳之心所創作的涅槃佛像能在其中吧。冷的上演:第一幕
技巧。純粹的技巧
劍氣逼人置你於妙不可言的頂點
亦輕而易舉地指引,對視中的生命含羞自盡
寧為玉碎
但所謂圓滿,更富殺傷力的傳奇
我什麼也看不見
似乎對一切了然於胸
詞和物。有限的事物
有限的光陰,確定的寒冷
二十四年,我大部分的根據
高不可及,陽光下的繁衍之序
你曾被命名不可逾越的天才
很有可能,你什麼也不是
我無力染指一種安寧的聲音
這其中孰是孰非,景仰的大師
我只能用永不綻放的受難之蓮來說明
處處遊蕩不定的悲鳴
浪漫主義時代無懈可擊的蒼穹
開得通體透明
他們之中必有苟延殘喘的家族
其中的殺機重重但祕而不宣
偉大的風尚無恥地賣弄,做為原始的憑證流傳至今
安寧,幸福定義裡唯美的詮釋
血泊裡放肆地扭動背脊
驟見玄衣人破門而出的驚蹶
一片白霧,不復歸來的寂靜
這孤獨的寂靜,不可替代的意義
在天空咫尺,人是沒有沒有表情的怪異動物
說到底,安寧也是一邊的冷
冷是死前的預兆,平靜地誦念
做為人的代價
摘自《生來破碎》
前言
張洹來自中國河南歷史悠久的古都安陽,二十世紀九○年代初到北京闖蕩,後成為獨立藝術家。在北京生活的八年,他創作了一大批引起廣泛社會輿論的行為藝術作品,並與其他當時生活在北京東郊大山莊的藝術家們共同創立藝術聚落地「北京東村」,以獨立、反叛、針對現實、身體行為等創作特點,形成了有別於中國藝術史上著名的「圓明園西村」的另一派自由藝術生態。
「我的靈感來源於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小事,如每天吃飯、睡覺、工作、拉屎,在這些極不被人注意的平淡生活中去發現和體會人性的本質。」他說:「在作品過程中我努力要體驗的是生存、身體和真實,而厭惡作品中的表演成分。」秉持這一理念,他的行為藝術呈現出未經粉飾的真實,狀如一顆尖釘,小而強硬,拒不淹沒在改革開放的滾滾洪流中,在時代重錘的擊打之下,發出了屬於個人小而頑強的聲音。
九○年代末期,張洹隻身前往美國,以紐約做為起點,將他的行為藝術版圖擴展至全球,成為最早在國際上引起迴響的中國藝術家之一。他的行為藝術表演經歷了從個人出發並跨越國界與文化的歷程,最終成為當代藝術史上一個獨特的存在,既富有爭議,也值得研究。
「12平方米」、「65KG」、「為無名山增高一米」、「為魚塘增高水位」、「朝聖——紐約風水」、「龍之夢」、「我的澳大利亞」、「家譜」、「水痘」、「朝聖聖地牙哥」、「我的日本」、「梨花飄香」、「上海家譜」、「我的紐約」、「漢堡種子」、「出走」、「日出」、「和平」、「五十顆星」、「舍利子」、「我的悉尼」、「窗」……。北京八年,紐約八年,張洹帶著自己的身體與大腦走遍了世界,他的行為藝術既是個人生活的一種見證,也讓他在求新求變的路上愈走愈遠。最終他選擇放棄行為藝術,只因不願意重複自己。二○○五年回國後,張洹定居上海。自二○○○年以來,他開始做不同材料的裝置和雕塑作品。由於在國外多年積累很多想法,再加上回國後感觸良多,他有許許多多的作品迫切需要實現,從前委託別人製作作品的模式已經不適用,為了更加高效地進行創作,他組建了個人工作室。不知道當時張洹是否已經意識到,他的這個舉動將意謂著開創一種全新的創作機制——請具有不同技術才能的人匯聚一堂,按照一名領導者的想法來集體完成作品。此後,國內日新月異的社會環境使張洹感觸很深,想法層出不窮,工作室隨之進入一個「井噴」式作品高產期。
「回到中國後,我對傳統和信仰有了更深的體會,這種體會就來自於今天的日常生活。於是,我發現了香灰、門板、牛皮……,不斷有新的靈感閃現。傳統是一個民族的身體,信仰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身體和精神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存在。」張洹的感觸,正是中國當下時代發出的聲音,他在這個新的環境中如魚得水,「中國正在全力向前發展,但不可能拋開自身的軀體和精神。回到自己的母語文化,我感到更加腳踏實地和根深柢固。」
張洹的個人工作室由最開始的小規模逐漸發展至員工兩百多人,占地面積五十畝,由門板木雕組、版畫組、油畫組、香灰創作組、香灰基礎組、木工組、焊工組、鍛銅組、標本組、包裝組、後勤組、辦公室等部門構成;員工有五分之一是藝術院校畢業的青年藝術家和作家,也有不同工種的民間傳統工藝師傅。他們來自全國各地,語言、文化各不相同,在規模上創造中國藝術家工作室之最。「這裡是一個工作室,我希望每個人的智慧都能出來,能幫助我、豐富我的想法,我能從每個人的經歷和想法中借鑑一些東西,不管他是藝術家還是非藝術家,我會注重每一個人的亮點。」
一個偶然的機會,張洹在上海靜安寺被香客燒香拜佛的場景觸動,發現了香灰這種特殊的材料,並將其引入到藝術創作中。「香灰畫」橫空出世,在中國已經綿延數千年的宗教儀式殘餘物,成為一種新的符號與表達方式,通過材料的再加工與作品的創作,將香客燒香時內心的祈願力量,轉化為灰燼重生的藝術語言。張洹敏銳地捕捉到歷史、時間、人類內心深處千百年不變的共通點,他成了「香灰之王」,用一種帶有「佛性」的現實主義再次顛覆當代藝術創作的形式與概念。一切似乎籠罩著超現實的感覺,就如香灰畫給人的感覺一樣,似乎有一種無法解釋的力量隱藏在畫面中,飄渺而現實,宏大而沉默。「每年我們從江浙一帶幾十座寺廟請來幾千立方的香灰,寺廟裡拉回來的香灰是放在油桶裡的,通常要繼續燃燒一、兩個月。當香灰運到車間¹裡時仍在燃燒,冒著巨煙和火苗,香灰車間整天瀰漫著煙灰,但是很多人到了那裡都覺得走不動了,覺得那裡面有一種東西,這種東西是莫名奇妙的,你看不到,就像那裡有一個『場』」。
二十多年的藝術實踐讓張洹成了藝術界一個特殊的「角色」,他遠遠不滿足於曾經做過的事情,還渴望去探索更多的領域。於是他做公共藝術,成立公益基金會,現在還要拍電影。這或許是已經到了「知天命」的階段,而另一方面,他對藝術的思考和表現則呈現出超越現實的特徵。
從某個時期開始,張洹在作品中所涉及的幾乎都是形而上的精神層面,內容既關於生命,也關於死亡。毫無疑問,宗教信仰給他的生命打開了更多的維度,彷彿肉體已經無法承載他思考的結果。他追求的是死亡之後的東西——另一個開始,所謂的涅槃,或者……完全歸零、並無限接近永恆。
之所以用不確定的語氣提及這種「永恆」,是因為它基本上無法描述。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永恆」或許更類似於一個模糊的夢。在低維度的生存空間內,人很難、或者幾乎不可能去理解那些超越了生活表象的事物,即便它們往往以最直接、簡單和不留餘地的方式彰顯,比如生和死。
生和死都是大事,但對張洹來說後者的重要性顯然要遠大於前者,這與他所信仰的藏傳佛教有關,但又不僅止於此。在他的思考中,死亡可能不是一個結束,反而是一個開始,全然未知,但又充滿無限的可能性。有時候你很難分辨,宗教究竟是為人解決了問題,還是向你提出了更多的問題,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宗教在某種程度上為生命的種種矛盾和悖論提供了一個出口——輪迴或重生,解脫不在此地而在彼岸,這一世的修行僅僅只是轉世的鋪墊。假如追本溯源,則不難發現:張洹對死亡和死後的世界向來有一種執迷,他一直在研究天葬、古代墓穴和與之相關的文物,似乎想從中找到什麼祕密。因緣際會,後來他成了迄今世界上唯一的漢族天葬師,儘管目前尚未親自主持過天葬儀式,但種種類似的事情無不在他身上營造出一種神祕氛圍——對於那些隱沒在日常生活背後的事物,似乎他的確了解得比旁人更多一些。
北京、紐約、上海、西藏……,張洹用半生時間在不同的地點之間位移,他在每個地方的生命歷程,都如實呈現在不同階段的創作裡。在這個過程中,他不斷修行,也不斷參透著生與死。他認為正能量的死亡並不是死,而是一種開始。無論是出於宗教也好,人生經驗也罷,這一生存哲學不由得令人想到「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他說:「人的命運難以捉摸,有一種神祕的東西在控制我們的命運。」每一個死去的昨天,在他這裡都成了新的開始,輪迴與重生的意義,大概就在於此。
在這本書裡可以看到張洹前半生的經歷,包括他早期在北京從事行為藝術創作背後隱祕而不為人知的艱辛,以及他隻身飄零國外時靈感的爆發與內心的孤獨。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張洹是無法複製的個案,他的藝術創造、他的決絕堅持,以及他身上似乎是與生俱來的那種執拗的力量,一直處於不斷自我進化、不斷改變重生的過程中。
我們有理由相信,張洹多年來觸目所及的一切和內心堅守的世界,某種程度上是超越了現世的另一種存在,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接近並驗證永恆。正如他無比確信地認為自己的前世是藏獒和禿鷲這兩種動物裡的一個,「藏獒只認死理兒,跟我的個性很像,就是一根筋走到底;而禿鷲有一種靈性的、神性的東西,所以它被稱為火鳥。」
所以,這故事離結束還早著呢。
摘自《張洹生死書》
《生來破碎》
胡軍軍答客問:生命包含的潛力,連你自己都驚嘆
天下:一九九二年妳移居北京,從此開展一生的藝術創作。妳什麼時候喜歡上詩歌和繪畫?胡:我自小嗜書如命,童年許多時光在書店裡「蹭書」看。八○年代的家庭沒有太多的零錢可以恣意買書,所以就在書店裡找各種書來讀。小時候的夢想是,有一天我能死在圖書館裡,那一定很幸福。中學時,我參加了所在城市的作文比賽,得了獎,從此我知道自己是個能寫文章的人。我想我不是某一天喜歡上了詩歌和繪畫,而是覺得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天下:妳在北京時剃了光頭,儼然是個頹廢女憤青,能分享當時的心境嗎?
胡:九○年代的北京是非常特殊的一段時期,那時候聚集的詩人、藝術家等等,都很異類,又頗有情懷,大有為了藝術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氣質。當時的社會氛圍還是相當壓抑保守,那些年有一股蠢蠢欲動的暗流洶湧,在這批特殊的人群中傳播擴散,我只是其中一個。青年時期的悲憤也罷、惆悵也罷,甚至憂國憂民,總是天真而無畏的。
天下:妳在北京藝術圈迅速嶄露頭角,不久就獲得當時少數的民間詩歌大獎「劉麗安詩歌獎」,這對當時二十四歲的妳,意義是什麼?
胡:安的存在像一束光,她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我想她是上帝派來的天使。她不僅對我,也幫助了數量眾多的詩人和藝術家們,她的名字應該被銘記和傳誦。
天下:《生來破碎》是妳第一本詩集,也是最後一本詩集,回首爬梳,妳希望這些詩作傳達什麼意念或情感?
胡:其實在北京出過一本詩集,只是沒有公開出版;也發表過一些,在民間和海外的詩歌刊物上。詩歌是為自己而寫,與別人的世界完全無關。這些零碎的文字,如同孤獨中乍現的星星火火,算是對那段歲月的驚鴻一瞥。
天下:在詩歌的創作時期,妳也同時經歷了單身、妻子、母親的人生變化,以及從北京搬居到紐約的文化衝擊,這些生命動盪是否影響了妳的創作?
胡:生命的軌跡不是你自己能設計的,我強烈地感受到,其實所有的劇本都早已寫就了,就等著我們這些芸芸眾生,一個個挑了角色,各演各的戲。生命中的每一個事件都是絲絲相扣的。
天下:在紐約形形色色的人生探索中,妳接觸了佛教,也拜禪宗高僧為師,信仰如何為妳打開新的生命視角?胡:我經常跟朋友分享,如果你真的能領略到佛法所揭示的真相,你的雙腿會不由自主地跪拜下去。佛法給了你一種「觀照」的能力,我們迷糊通常是因為跳不開自我的束縛,所謂「當局者迷」,只有「無我」,才能冷靜而理智地看待生命,所以這樣的影響無日不在我的生活中、創作中,甚至是以後的來世。
天下:在繪畫創作中,妳先是以抽象極簡的網格方式繪製天地自然景物,二○一三年、二○一五年先後舉辦了「山外有山」、「常觀無常」畫展,打開當代藝術的視野。能否分享創作背後的觀念?
胡:我對「觀念性」的藝術一直懷有極大的興趣,年輕時就以「反傳統」為榮。網格這樣的創作方式有點接近禪修時的呼吸法門,只要當下照顧好每一個呼吸,最後呈現什麼已不重要。專注地去描繪每一個格子,都是抽象迷離的,並不代表什麼,也不是要達到什麼。「醉翁之意不在酒」,用在這裡,是很恰當的。
天下:如今妳轉而投入涅槃創作,畫筆下的佛,姿態從容、色彩繽紛、筆觸率真,再現北魏佛像壁畫風采,走向全新的藝術境界。能否分享妳的改變?
胡:以創作「涅槃」佛像為己任,是我這一生最大的轉折,這是一件從未計劃過的、最意想不到的事件。我不敢妄言自己對佛法的領會有多深刻,事實上,如果把佛法的智慧比作大海,我僅只是觸摸到了一滴水珠而已。通常藝術創作裡最強調的是創作者本人的想法,對我來講,在信仰和藝術之間,我選擇了信仰至上,只是依然用藝術形式來表達而已。涅槃寂靜是佛法修行中最高深、最終極的法門,這條「涅槃之道」,我是走定了。從我創作「涅槃」佛像以來,從表象上看似乎我的畫風有了極大的轉變,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其實我說的是同一個意思,只是這個意思終於說明白了,說瞭然了,說透徹了。中國有幾萬座寺院,居然還沒有一座叫「涅槃寺」,也許有朝一日,我懷著拳拳之心所創作的涅槃佛像能在其中吧。冷的上演:第一幕
技巧。純粹的技巧
劍氣逼人置你於妙不可言的頂點
亦輕而易舉地指引,對視中的生命含羞自盡
寧為玉碎
但所謂圓滿,更富殺傷力的傳奇
我什麼也看不見
似乎對一切了然於胸
詞和物。有限的事物
有限的光陰,確定的寒冷
二十四年,我大部分的根據
高不可及,陽光下的繁衍之序
你曾被命名不可逾越的天才
很有可能,你什麼也不是
我無力染指一種安寧的聲音
這其中孰是孰非,景仰的大師
我只能用永不綻放的受難之蓮來說明
處處遊蕩不定的悲鳴
浪漫主義時代無懈可擊的蒼穹
開得通體透明
他們之中必有苟延殘喘的家族
其中的殺機重重但祕而不宣
偉大的風尚無恥地賣弄,做為原始的憑證流傳至今
安寧,幸福定義裡唯美的詮釋
血泊裡放肆地扭動背脊
驟見玄衣人破門而出的驚蹶
一片白霧,不復歸來的寂靜
這孤獨的寂靜,不可替代的意義
在天空咫尺,人是沒有沒有表情的怪異動物
說到底,安寧也是一邊的冷
冷是死前的預兆,平靜地誦念
做為人的代價
摘自《生來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