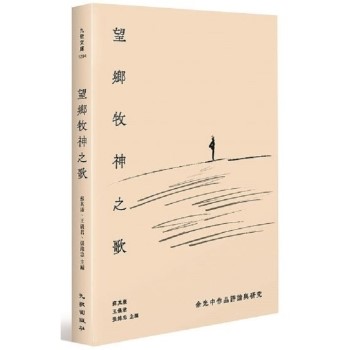緒論
回到藍墨水的上游/張錦忠
壹
在余光中教授去世前半年左右,蘇其康老師發起籌編一本論余光中作品的文集,預計二〇一八年出版,既為詩人重九九十華誕祝壽,也為余學累積研究彙編。這個心意顯然因余光中於去年底辭世而落空了一半。不過,我們幾位編者覺得原本的心意還有一半可以實現,如果原先答允撰稿邀稿的文友與學界同人多數能夠如期供稿,編一本研究余光中的人無法繞過的論文集還是很值得做的事。
世人所知道的余光中,當然是當代中文文學世界的重要詩人與散文家。在戰後臺灣文壇開啓「現代詩紀」的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詩人們像崛起的星群,在文學的夜空中競相放光,到了五〇年代中葉,藍星、現代詩社、創世紀三分詩壇天下,爾後才有笠詩社冒現,三分變成四方,於是臺灣現代詩風從超現實到鄉土,都有所表現,各自展顏。現代詩能在彼時成為臺灣文學的主要能動力量,余光中、覃子豪、紀弦、洛夫等前行者為現代詩搖旗,在寫詩,交出作品之外,編詩刊、釋詩、譯詩、論詩,乃至論戰,為當時的現代詩運動推波助瀾,居功至偉,余光中更是其中的重要代言人。余光中以其外文系背景,熟悉西方現代文學,詩尤其是他的「第一興趣」,一方面取法英美詩歌以鍛鍊詩藝,另一方面向英詩傳統與演變取經以論述中文現代詩的表現與語言,頗多建樹,可謂詩與詩論左右開弓,阿波羅與繆思分別在他雙掌上呼風喚雨,各顯神通。
可是這不表示余光中乃全盤西化的擁護者。他寫新詩, 認為「新詩是反傳統的」、「新詩應該大量吸收西洋的影響」,但也認為新詩「事實上也未與傳統脫節」,西化的新詩「仍是中國人寫的新詩」(1968:123)。傳統與反傳統乃五四以降新詩運動乃至新文學史的重要議題,新詩的求變求新(龐德[Ezra Pound]所說的“make it new”),總已是從傳統出發又反傳統的,同時也是傳統與個人才力之間的拔河。用這個觀點來看余光中的新詩志業,應該也是合宜的。余光中投入新詩的長河,早在一九五〇年夏天經香港橫渡臺灣海峽在「美麗的島」上吟唱望鄉牧神之歌之前,當他還是廈門大學外文系大二學生時,就已在廈門的報紙發表詩作了。
一九五〇年代的中文新詩,格律派的高峰或見諸力匡在香港-南洋的表現,但更有詩學實驗野心的吳興華早在四〇年代就踐行了,雖然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要到五〇年代中葉才發表他署名梁文星的〈致伊娃〉及〈現在的新詩〉等詩文。余光中在那個時代起步寫詩,難免要經過這場格律風雨的洗禮(他彼時所讀的卞之琳與馮至也寫格律詩)。這可以從他早期的幾本詩集見出端倪。在余光中的詩路旅程中,從格律新詩過度到現代主義感性並不成問題,甚至是順著新詩運動之必然趨勢。而這時的余光中所反的是那個五四的白話新詩傳統,先是降下五四的半旗,然後「升起現代文藝的大蠹」,翻開現代文學史的第二章。
我所謂順詩運之勢指的是一九五〇年代中葉的臺灣現代詩潮流向,尤其是余光中在一九五八年留美返國、發表長詩(或組詩)〈天狼星〉、引發論戰那期間臺灣現代詩那幾年的表現。我們不妨從余光中形容為 「那正是臺灣現代詩反傳統的高潮」(1976:153)的一九六一年往前回顧那五年間的大事記:一九五六年,紀弦的現代派成立,主張「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一九五七年,藍星與現代二詩社展開「現代主義/新現代主義」論戰;一九五九年,蘇雪林發表〈新詩壇象徵派創始者李金髮〉指象徵詩幽靈來臺、言曦發表〈新詩閒話〉指責新詩晦澀,遂掀起一場新詩筆戰;同年四月《創世紀》(第十一期)改版,提倡詩的世界性與超現實性,第十二期(七月號)發表洛夫長詩《石室之死亡》;一九六一年,張默與瘂弦主編《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出版;同年《現代文學》先後刊出的余光中的〈天狼星〉與洛夫的長篇評文〈《天狼星》論〉,引發余洛二人筆戰,余光中後來發表〈再見,虛無〉回應。那段期間,一九五八年秋至翌年夏,余光中赴美留學,新大陸的生命經驗與美學感知顯然有助與他闊步邁向現代主義,但是在論戰衝鋒陷陣之餘,也令他反思臺灣現代詩以及他自己的詩志業的出路。那出路就是轉進「新古典主義」;於是便有了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詩集《蓮的聯想》,以及細究古典詩藝的長文〈象牙塔到白玉樓〉。《蓮的聯想》詩題很難不令人聯想到漢詩樂府的「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何況文星版詩集序一開頭就是「身為一半的江南人⋯⋯」(2007:17)。蓮固然是古典的象徵(「古典留我」[2007:44]),也是東方的意象(「是以東方甚遠,東方甚近」[2007:52]、「東方/有一支蓮[2007:130]」),四十多年後他回顧那年夏天的靈光一現(epiphany),自承彼時他「正倦於西方現代主義之飛揚跋扈,並苦於東歸古典之無門。天啓一般,忽有蓮影亭亭,荷香細細,引我踏上歸途」(2007:9)。「拒絕〔向西方〕遠行」的詩人找到了他的「比特麗絲」(Beatrice)(「甄甄/真真」),於是《蓮的聯想》類似但丁的「新生於焉開始」, 然而這卷詩集並非但丁的《新生》那樣的愛情絮語,而是一卷以「新古典主義」對抗現代主義的寓言(allegory)之作,寫的是「詩情,而非「情詩」。因此,新古典主義在勢必也只是過渡。這也是為甚麽在集中的〈燭光中〉有「現代和古典猶未定邊疆」(2007:152)這樣的句子,以及〈第七度〉裏的「這裏 / 是現代的邊境,⋯⋯//⋯⋯現代 / 狹窄的現代能不能收容我們?」(2007:136-138)。換句話說,那年夏天在臺北植物園小蓮池畔第一次看見蓮的詩人,雖然不是打江南走過,很可能跟鄭愁予詩中的說話者一樣「不是歸人,是個過客⋯⋯」(鄭愁予 115),儘管他自己認為那是「歸人心情」(2007:9)。
這麼說其實合乎「正反合」的辯證思維:現代(現代主義)為「正」,古典(新古典主義)為「反」,「合」是彼時隔霧的未來(「古代隔煙,未來隔霧⋯⋯」[2007:137])。余光中的詩文背後的思維其實相當符合辯證法,我們甚至不妨說其詩文的機智趣味也是辯證思維的產物。這一點當年熊秉明(1966)論余光中的《蓮的聯想》中的三聯句時也曾指出。至於那隔霧的未來,余光中自己也在九歌版的新序上說,《蓮的聯想》出版三個月後,同年九月我便二度去了美國,對李賀與李商隱的耽溺也就在新大陸漸漸「解魅」了。等到一九六六年回臺前夕,〈敲打樂〉的重金屬響起,我的詩情已因現實的壓力而進入了《在冷戰的年代》,場景全換了,⋯⋯。 (2007a:10)
一九六〇年代中葉,美蘇冷戰對峙,美越戰爭如火如荼,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正鋪天蓋地展開,美國民權運動方興未艾,彼時人在美國的余光中「獨在異鄉為異客」,難免要「感時憂國」一番。與此同時,余光中也見證了現代詩在美國的典範轉移,維廉.凱樂士.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已取代艾略特(一九六四年過世)成為詩壇要角,余光中在一九五九年首度赴美時見到的佛洛斯特(Robert Frost)重新受肯定,痞世代(Beat Generation)詩人的冒現,在在代表明朗、口語、主感才是王道。對某些文學史家來說,那正是美國後現代主義詩潮的臨界點。
如果我們同意余光中自己說的,寫完〈天狼星〉,他「已經暢所欲言,且已生完了現代詩的痲疹,總之〔他〕已經免疫了。〔他〕再也不怕達達和超現實的細菌了」(1968:184),那麼,寫完《蓮的聯想》,他也告別了他所自詡的新古典主義,從江南回到南國鯤島──「走下新生南路,在冷戰的年代」(1970:106)或走在「廈門街的那邊有一些蠢蠢的記憶的那邊」(1970:46)。《在冷戰的年代》開啓了余光中的「中期」詩路,此後他果真「暢所欲言」,儘管詩觀繼續變化。在詩集出版後接下來四十七年的歲月裏,他出版了從《白玉苦瓜》到《太陽點名》十一部詩集,交出了〈白玉苦瓜〉、〈九廣鐵路〉、〈蜀人贈扇記〉、〈五行無阻〉、〈大衛雕像〉等無數名篇,其詩力的續航能耐不可謂不強大。
夏志清曾說,余光中自承其詩成就高於散文,但他卻認為「後世讀者可能歡迎他〔余光中〕的抒情散文,有甚於他的詩」(156)。余光中在散文上的努力有三個方向:即他名之曰「自傳性的抒情散文」(2008:116)的抒情散文、評論散文(或文藝批評)與專欄隨筆及雜文。在為現代詩搖旗吶喊的同時,他就鼓吹散文革命了。 當年在《文星》刊出的那篇〈剪掉散文的辮子〉今天仍為人所津津樂道。 他指出彼時「學者」、「花花公子」、「浣衣服」三款散文類外的第四款散文才是「新散文」──「現代散文」。這種現代散文──於他其實就是他的抒情散文──「講究彈性、密度、和質料」(2000:56)。寫現代散文的余光中,顯然是將自己視為文字的煉金術士,就像他自己說的:「我倒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摺來且疊去」(2000:262)。後面這句話早已成為他的散文論述名言。這類「字字計較」的抒情散文的典型例子有〈鬼雨〉、〈逍遙遊〉、〈萬里長城〉、〈聽聽那冷雨〉、〈登樓賦〉、〈地圖〉、〈我的四個假想敵〉、〈記憶像鐵軌一樣長〉等,名篇繁多不及備載。這些抒情散文的題材或感性也許多是「陰柔」的,但卻以陽剛的文體展現,可以說是余光中的「陰陽並濟」獨家散文風格,頗能反映他自己說的「心裏有猛虎在細嗅薔薇」(203)。
余光中早期的散文集多是抒情散文與評論散文兼收。他的首三本散文集中,第一本《左手的繆思》出版於一九六三年,裏頭的〈記佛洛斯特〉、〈石城之行〉與〈塔阿爾湖〉應屬自傳性抒情散文(〈猛虎和薔薇〉算是初試美文身手),但其他的大都可歸入批評文章類。第二本《掌上雨》,卻是一本評論與雜文集,並沒有收入抒情散文。其實,余光中認為他的抒情散文與詩頗為接近,「就連論評的散文也不時呈現詩的想像」(2008:116)。他的評論散文多涉及現代詩與當代詩人,以其批評文字之犀利,堪稱當年文壇第一健筆,在那烽火連天的年代,為現代詩開疆闢土立功不小。就臺灣現代詩史而言,他的詩論散文,尤其是析論方旗、方莘、方娥真的「三方論」,以及重新勘繪現代詩版圖的〈新現代詩的起點〉等篇或序,既有伯樂之先見與洞見,復為臺灣現代詩把脈,點出七〇年代現代詩論戰之後的路向,可以說已是建立現代詩典律的文獻。這類評論散文包括他的藝評文字,以及他為其他作家所作的序,甚至是他的自序文。不過,他的評論散文論述對象除了現代詩人外,古典詩人與歐美詩人也在他的視野裏。他的古典論述之作中,〈象牙塔到白玉樓〉與〈龔自珍與雪萊〉尤為重要篇什,後者也屬比較文學研究。歐美詩人評介則是他《左手的繆思》時期的主要關注,那些年他也在如火如荼譯介英美詩人。
回到藍墨水的上游/張錦忠
壹
在余光中教授去世前半年左右,蘇其康老師發起籌編一本論余光中作品的文集,預計二〇一八年出版,既為詩人重九九十華誕祝壽,也為余學累積研究彙編。這個心意顯然因余光中於去年底辭世而落空了一半。不過,我們幾位編者覺得原本的心意還有一半可以實現,如果原先答允撰稿邀稿的文友與學界同人多數能夠如期供稿,編一本研究余光中的人無法繞過的論文集還是很值得做的事。
世人所知道的余光中,當然是當代中文文學世界的重要詩人與散文家。在戰後臺灣文壇開啓「現代詩紀」的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詩人們像崛起的星群,在文學的夜空中競相放光,到了五〇年代中葉,藍星、現代詩社、創世紀三分詩壇天下,爾後才有笠詩社冒現,三分變成四方,於是臺灣現代詩風從超現實到鄉土,都有所表現,各自展顏。現代詩能在彼時成為臺灣文學的主要能動力量,余光中、覃子豪、紀弦、洛夫等前行者為現代詩搖旗,在寫詩,交出作品之外,編詩刊、釋詩、譯詩、論詩,乃至論戰,為當時的現代詩運動推波助瀾,居功至偉,余光中更是其中的重要代言人。余光中以其外文系背景,熟悉西方現代文學,詩尤其是他的「第一興趣」,一方面取法英美詩歌以鍛鍊詩藝,另一方面向英詩傳統與演變取經以論述中文現代詩的表現與語言,頗多建樹,可謂詩與詩論左右開弓,阿波羅與繆思分別在他雙掌上呼風喚雨,各顯神通。
可是這不表示余光中乃全盤西化的擁護者。他寫新詩, 認為「新詩是反傳統的」、「新詩應該大量吸收西洋的影響」,但也認為新詩「事實上也未與傳統脫節」,西化的新詩「仍是中國人寫的新詩」(1968:123)。傳統與反傳統乃五四以降新詩運動乃至新文學史的重要議題,新詩的求變求新(龐德[Ezra Pound]所說的“make it new”),總已是從傳統出發又反傳統的,同時也是傳統與個人才力之間的拔河。用這個觀點來看余光中的新詩志業,應該也是合宜的。余光中投入新詩的長河,早在一九五〇年夏天經香港橫渡臺灣海峽在「美麗的島」上吟唱望鄉牧神之歌之前,當他還是廈門大學外文系大二學生時,就已在廈門的報紙發表詩作了。
一九五〇年代的中文新詩,格律派的高峰或見諸力匡在香港-南洋的表現,但更有詩學實驗野心的吳興華早在四〇年代就踐行了,雖然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要到五〇年代中葉才發表他署名梁文星的〈致伊娃〉及〈現在的新詩〉等詩文。余光中在那個時代起步寫詩,難免要經過這場格律風雨的洗禮(他彼時所讀的卞之琳與馮至也寫格律詩)。這可以從他早期的幾本詩集見出端倪。在余光中的詩路旅程中,從格律新詩過度到現代主義感性並不成問題,甚至是順著新詩運動之必然趨勢。而這時的余光中所反的是那個五四的白話新詩傳統,先是降下五四的半旗,然後「升起現代文藝的大蠹」,翻開現代文學史的第二章。
我所謂順詩運之勢指的是一九五〇年代中葉的臺灣現代詩潮流向,尤其是余光中在一九五八年留美返國、發表長詩(或組詩)〈天狼星〉、引發論戰那期間臺灣現代詩那幾年的表現。我們不妨從余光中形容為 「那正是臺灣現代詩反傳統的高潮」(1976:153)的一九六一年往前回顧那五年間的大事記:一九五六年,紀弦的現代派成立,主張「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一九五七年,藍星與現代二詩社展開「現代主義/新現代主義」論戰;一九五九年,蘇雪林發表〈新詩壇象徵派創始者李金髮〉指象徵詩幽靈來臺、言曦發表〈新詩閒話〉指責新詩晦澀,遂掀起一場新詩筆戰;同年四月《創世紀》(第十一期)改版,提倡詩的世界性與超現實性,第十二期(七月號)發表洛夫長詩《石室之死亡》;一九六一年,張默與瘂弦主編《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出版;同年《現代文學》先後刊出的余光中的〈天狼星〉與洛夫的長篇評文〈《天狼星》論〉,引發余洛二人筆戰,余光中後來發表〈再見,虛無〉回應。那段期間,一九五八年秋至翌年夏,余光中赴美留學,新大陸的生命經驗與美學感知顯然有助與他闊步邁向現代主義,但是在論戰衝鋒陷陣之餘,也令他反思臺灣現代詩以及他自己的詩志業的出路。那出路就是轉進「新古典主義」;於是便有了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詩集《蓮的聯想》,以及細究古典詩藝的長文〈象牙塔到白玉樓〉。《蓮的聯想》詩題很難不令人聯想到漢詩樂府的「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何況文星版詩集序一開頭就是「身為一半的江南人⋯⋯」(2007:17)。蓮固然是古典的象徵(「古典留我」[2007:44]),也是東方的意象(「是以東方甚遠,東方甚近」[2007:52]、「東方/有一支蓮[2007:130]」),四十多年後他回顧那年夏天的靈光一現(epiphany),自承彼時他「正倦於西方現代主義之飛揚跋扈,並苦於東歸古典之無門。天啓一般,忽有蓮影亭亭,荷香細細,引我踏上歸途」(2007:9)。「拒絕〔向西方〕遠行」的詩人找到了他的「比特麗絲」(Beatrice)(「甄甄/真真」),於是《蓮的聯想》類似但丁的「新生於焉開始」, 然而這卷詩集並非但丁的《新生》那樣的愛情絮語,而是一卷以「新古典主義」對抗現代主義的寓言(allegory)之作,寫的是「詩情,而非「情詩」。因此,新古典主義在勢必也只是過渡。這也是為甚麽在集中的〈燭光中〉有「現代和古典猶未定邊疆」(2007:152)這樣的句子,以及〈第七度〉裏的「這裏 / 是現代的邊境,⋯⋯//⋯⋯現代 / 狹窄的現代能不能收容我們?」(2007:136-138)。換句話說,那年夏天在臺北植物園小蓮池畔第一次看見蓮的詩人,雖然不是打江南走過,很可能跟鄭愁予詩中的說話者一樣「不是歸人,是個過客⋯⋯」(鄭愁予 115),儘管他自己認為那是「歸人心情」(2007:9)。
這麼說其實合乎「正反合」的辯證思維:現代(現代主義)為「正」,古典(新古典主義)為「反」,「合」是彼時隔霧的未來(「古代隔煙,未來隔霧⋯⋯」[2007:137])。余光中的詩文背後的思維其實相當符合辯證法,我們甚至不妨說其詩文的機智趣味也是辯證思維的產物。這一點當年熊秉明(1966)論余光中的《蓮的聯想》中的三聯句時也曾指出。至於那隔霧的未來,余光中自己也在九歌版的新序上說,《蓮的聯想》出版三個月後,同年九月我便二度去了美國,對李賀與李商隱的耽溺也就在新大陸漸漸「解魅」了。等到一九六六年回臺前夕,〈敲打樂〉的重金屬響起,我的詩情已因現實的壓力而進入了《在冷戰的年代》,場景全換了,⋯⋯。 (2007a:10)
一九六〇年代中葉,美蘇冷戰對峙,美越戰爭如火如荼,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正鋪天蓋地展開,美國民權運動方興未艾,彼時人在美國的余光中「獨在異鄉為異客」,難免要「感時憂國」一番。與此同時,余光中也見證了現代詩在美國的典範轉移,維廉.凱樂士.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已取代艾略特(一九六四年過世)成為詩壇要角,余光中在一九五九年首度赴美時見到的佛洛斯特(Robert Frost)重新受肯定,痞世代(Beat Generation)詩人的冒現,在在代表明朗、口語、主感才是王道。對某些文學史家來說,那正是美國後現代主義詩潮的臨界點。
如果我們同意余光中自己說的,寫完〈天狼星〉,他「已經暢所欲言,且已生完了現代詩的痲疹,總之〔他〕已經免疫了。〔他〕再也不怕達達和超現實的細菌了」(1968:184),那麼,寫完《蓮的聯想》,他也告別了他所自詡的新古典主義,從江南回到南國鯤島──「走下新生南路,在冷戰的年代」(1970:106)或走在「廈門街的那邊有一些蠢蠢的記憶的那邊」(1970:46)。《在冷戰的年代》開啓了余光中的「中期」詩路,此後他果真「暢所欲言」,儘管詩觀繼續變化。在詩集出版後接下來四十七年的歲月裏,他出版了從《白玉苦瓜》到《太陽點名》十一部詩集,交出了〈白玉苦瓜〉、〈九廣鐵路〉、〈蜀人贈扇記〉、〈五行無阻〉、〈大衛雕像〉等無數名篇,其詩力的續航能耐不可謂不強大。
夏志清曾說,余光中自承其詩成就高於散文,但他卻認為「後世讀者可能歡迎他〔余光中〕的抒情散文,有甚於他的詩」(156)。余光中在散文上的努力有三個方向:即他名之曰「自傳性的抒情散文」(2008:116)的抒情散文、評論散文(或文藝批評)與專欄隨筆及雜文。在為現代詩搖旗吶喊的同時,他就鼓吹散文革命了。 當年在《文星》刊出的那篇〈剪掉散文的辮子〉今天仍為人所津津樂道。 他指出彼時「學者」、「花花公子」、「浣衣服」三款散文類外的第四款散文才是「新散文」──「現代散文」。這種現代散文──於他其實就是他的抒情散文──「講究彈性、密度、和質料」(2000:56)。寫現代散文的余光中,顯然是將自己視為文字的煉金術士,就像他自己說的:「我倒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摺來且疊去」(2000:262)。後面這句話早已成為他的散文論述名言。這類「字字計較」的抒情散文的典型例子有〈鬼雨〉、〈逍遙遊〉、〈萬里長城〉、〈聽聽那冷雨〉、〈登樓賦〉、〈地圖〉、〈我的四個假想敵〉、〈記憶像鐵軌一樣長〉等,名篇繁多不及備載。這些抒情散文的題材或感性也許多是「陰柔」的,但卻以陽剛的文體展現,可以說是余光中的「陰陽並濟」獨家散文風格,頗能反映他自己說的「心裏有猛虎在細嗅薔薇」(203)。
余光中早期的散文集多是抒情散文與評論散文兼收。他的首三本散文集中,第一本《左手的繆思》出版於一九六三年,裏頭的〈記佛洛斯特〉、〈石城之行〉與〈塔阿爾湖〉應屬自傳性抒情散文(〈猛虎和薔薇〉算是初試美文身手),但其他的大都可歸入批評文章類。第二本《掌上雨》,卻是一本評論與雜文集,並沒有收入抒情散文。其實,余光中認為他的抒情散文與詩頗為接近,「就連論評的散文也不時呈現詩的想像」(2008:116)。他的評論散文多涉及現代詩與當代詩人,以其批評文字之犀利,堪稱當年文壇第一健筆,在那烽火連天的年代,為現代詩開疆闢土立功不小。就臺灣現代詩史而言,他的詩論散文,尤其是析論方旗、方莘、方娥真的「三方論」,以及重新勘繪現代詩版圖的〈新現代詩的起點〉等篇或序,既有伯樂之先見與洞見,復為臺灣現代詩把脈,點出七〇年代現代詩論戰之後的路向,可以說已是建立現代詩典律的文獻。這類評論散文包括他的藝評文字,以及他為其他作家所作的序,甚至是他的自序文。不過,他的評論散文論述對象除了現代詩人外,古典詩人與歐美詩人也在他的視野裏。他的古典論述之作中,〈象牙塔到白玉樓〉與〈龔自珍與雪萊〉尤為重要篇什,後者也屬比較文學研究。歐美詩人評介則是他《左手的繆思》時期的主要關注,那些年他也在如火如荼譯介英美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