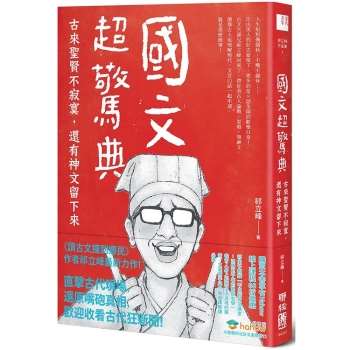14. 《延禧攻略》大解密──後宮擺攤開夜市,我可以
之前有部宮廷劇《延禧攻略》超熱門,主角魏瓔珞在裡面個性耿直,有仇必報的
火辣性格,讓劇迷為之瘋狂。不過劇中也用了不少古文梗,各位若看過第一集,瓔珞建議一個囂張的秀女在鞋底以金粉染蓮花,那就是她第一次耍的心機,這個典故來自於南齊的最後一個皇帝、東昏侯蕭寶卷:
(東昏侯)又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匝飾以金璧。……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剝取以施潘妃殿飾。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桷,便於地畫之,唯須宏麗,不知精密。酷不別畫,但取絢曜而已,故諸匠賴此得不用情。又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南史‧東昏侯傳》)
東昏侯的愛妃名叫潘玉兒,在《延禧攻略》改為潘玉奴,話說因為這潘妃喜歡
Bling-Bling的聖誕樹裝飾,東昏侯就把佛塔的金鈴剝下來裝到潘妃房房裡(為什麼又要講疊字),這事爾後被唐朝仇女戰神李商隱表到飛起來,寫了〈齊宮詞〉來嘲諷她。而除了將佛寺裝飾都給潘妃當做宮殿的掛飾之外,更讓地上鑿金蓮花,讓潘妃走過,仿效當年釋迦牟尼步步生蓮華的典故,只能說金變態。所以在《延禧攻略》裡,乾隆看了那步步生蓮的秀女才會如此森氣氣,大罵秀女「蕭寶卷是昏君,潘妃是妖妃,這豈不是把朕跟蕭寶卷相提並論了嗎」?
劇中雖然沒有說清楚,但魏瓔珞卻對這段史料很熟悉,所以鄉親啊,尼看看讀古文有多重要。而《延禧攻略》裡另外一段,後宮嬪妃全體變裝擺市集的故事,其實也來自東昏侯。要介紹這典故,要先說明南朝貴族的生活與娛樂。話說古典時期的貴族通常養尊處優,生活優渥,在聲色娛樂過度疲乏的情況下,他們難免得找一些新娛樂得到一種扮裝的快感,而其中搞變裝搞得規模最大最鋪張的,也就是咱們這位以昏君出名的南齊東昏侯:
(東昏侯)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豎共為裨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鬥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荊子……每游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褌,著綠絲屩,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於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南史‧東昏侯傳》)
史傳有載說這潘妃啊,其實出自庶民階層,其父在市集做過買賣,基本上就是「夜市人生」的劇情,所以潘妃特別喜歡那種平民市集的雜沓紊亂氣氛。因此寵幸她的東昏侯就給他在其御苑裡搞了個夜市菜市場,全宮的婢女太監都扮成攤販,這種大型變裝派對感覺起來滿high的,和之前高中生扮納粹有得比。按照上述《南史》所載,這市集全都玩真的,鬧事偷竊什麼都有,連皇帝自己亂擺攤位都要被開罰單,還要被鞭刑(根本加入SM元素),聽起來實在有點色色der。但咱們東昏侯顯得玩得很盡興扮得很認真,還自己變裝成殺豬的。於是當時的酸民就編了一首歌:「至尊屠肉,潘妃酤酒。」皇帝自己拿殺豬刀,貴妃變成酒店妹,這成何體統?
但其實整個魏晉南北朝,這樣的扮裝癖與變裝趴竟然比我們想的還要多次,而且多半都是君主或王侯等名人有此嗜好,如以下幾段史書的原文:
(宋少帝劉義符)居帝王之位……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宋書‧少帝紀》)(南齊鬱林王蕭昭業)常裸袒,著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褌,雜采衵服。 好鬥雞,密買雞至數千價。(《南史‧鬱林王紀》)(北齊幼主高恒)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為乞食兒;又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北齊書‧幼主紀》)
我的老天鵝啊,少帝劉義符除了搞市集,還喜歡裝民工,跟著一起去做粗工打石工。至於鬱林王蕭昭業就更ㄎㄧㄤ了,嗜好裸半身,玩那種市井小民的鬥雞遊戲。最94狂的就是北齊的高恒,穿著破爛衣服變裝成犀利哥在路邊乞討,討爽了還跑去貧民窟跟丐幫的混在一起以物易物。前面提到的《延禧攻略》──後宮諸嬪妃當起攤販,魏瓔珞親自賣酒,這種俚俗與低俗的扮裝,其實帶來更多的刺激與新鮮感。至於這背後到底是什麼樣的變態心理呢? 學界推測是一種逐奇尚異。試想,這群王侯貴族跟我們蛇蛇的世界完全不一樣,他們含著金湯匙出生,從小就是人生勝利組,日復一日錦衣玉食飯來張口。庶民的混亂、雜沓與傖俗成了他們嚮往的美學,於是乎在所有娛樂都耗盡而再無新鮮感的時候,他們必須透過這種變裝或自虐來達到娛樂效果。
這種心態微妙而複雜,學者如鄭毓瑜在《文本風景》中更進一步認為,這樣的變裝其實反而有一種特權建構的意味。就好像美女正咩喜歡秀素顏照或玩扮醜扮鬼的APP,那是一種「因為我是貴族所以我爽就可以扮成販夫走卒」的權威,是一種單向度的越界,就像《乞丐王子》的故事。一旦扮窮醜扮乞丐變成了現實,那就再無娛樂歡快而只剩下悲慘。
所以奢談什麼變裝只是好玩,搞笑只因無知,實則太化約了人類行為與自由意志的多元和複雜。每次的選擇與無機的行為,背後都有一連串深刻細碎的符號能指。這也正是學術研究的意義。
19. 月薪十萬,能撈就撈?──唐朝詩人月薪一覽表
關於新世代的困境,二十二K的惡法,什麼台灣年輕人缺乏狼性,社會是不是hen公平等等這類的話題,其實已經討論了好幾年(喂,不是說好不戰這個)。更慘的是每當有些人被破格任用拔擢,當上了什麼總經理董事長還發研人之類的,就會被人家檢討每個月爽領多少等等的。
其實上班族都知道薪水算是隱私的一部分,不好隨便問,雖然過年還是會被一些白目長輩出來說三道四。但其實唐代詩人,尤其是中唐新樂府那一掛,強調詩歌要應時而作,要阿嬤都看得懂的詩人,倒是常常在詩裡曬月薪。
這學期我再度教到元稹〈遣悲懷〉這首悼亡神詩。第一首最後兩句「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說來情感很真摯,但實在白話到ㄎㄅ又傻眼,讓人想回「元稹,母湯喔」。這兩句詩直接翻譯就是「現在月薪破十萬,只能給你辦法會。之前《讀古文撞到鄉民》寫元稹這裡的情感,是只能共貧賤卻無緣共享樂的悲摧,對亡妻有種類似「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後」的無奈,但過去這首詩繫年一般是在元和六年(811),當時元稹轉任監察御史,終於算是當了個像樣的官,於是想到沒機會讓亡妻過好日子,不禁悲從中來。
但監察御史月薪甘有十萬摳嗎?過去國學大師陳寅恪就曾經檢討過這件事,說御史頂多四、五萬,認為元稹不會灌水嘴豪那麼誇張,所以此詩應該作於元和十三年(818),元稹任通州司馬兼領州務,加上額外加給,差不多八、九萬,膨風一下說十萬也還說得過去。
想到古人的薪水就覺得這話題滿妙的,於是我就隨手查了一下。不查不得了,元稹和他的老基友白居易原來都不怕月薪被人家知道,尤其我們熟悉的老白,寫了N首關於自己不同時期的薪水變化。起初白居易剛來到天龍國,被人家嗆說你南部人別來亂,隨後他秀出自己的文章,周遭傻眼貓咪,於是老白就電級移籍長安天龍國,開始他的小官吏奮鬥史。
白居易第一個做的官叫做「校書郎」,這是一個九品小官,也是進士科出身的文人經常初任的官職,他在〈常樂里閒居偶題〉詩中寫到:
茅屋四五間,一馬二樸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白居易說他月薪雖然十六K,但感覺錢夠用就好,於是每天都充實又快樂。這時候長輩就會跳出來罵說,安安,你才十六K就覺得滿足了,請問是不是缺乏狼性?但仔細看這首詩前面說的──茅屋就有四、五間,有配車配司機,其實這待遇很不錯了(謎之聲:月領三十K只能住茅房……)。
苦幹實幹了幾年之後,白居易升遷到了「左拾遺」,在〈酒後走筆〉詩中,他又把工作量和薪水誠實地說出來:
月懶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
這這這,個每月繳交諫書兩千張稿紙,我們大致算一張稿紙寫個一百字好了,那就是二十萬字,然後每年年薪三十萬,平均每個月還不到三萬,平均下來稿費一字才○‧一五元,實在有點辛酸(看向編輯)(嚇到吃手)。但重點還是古早錢比較有價值,如果三萬是美金的話這稿費其實還算不錯了。接著白居易當了翰林學士,兼任京兆尹的「戶曹參軍」,這時候他薪水也開始大提升:
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潭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困。咱們老白的月薪飆到四、五萬,還有以食物穀物代償的制度,可以說越領越多,開始進階成為爽爽領高薪、待退領年金的八百壯士(我又在公啥小)。接著他當「蘇州刺史」,「十萬戶州尤覺貴,兩千石祿敢言貧」;當「賓客分司」,寫「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至於最扯的大概是老白晚年轉任「太子少傅」,他寫了一首〈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
承華東署三分務,履道西池七過春。歌酒優遊聊卒歲,園林蕭灑可終身。留侯爵秩誠虛貴,疏受生涯未苦貧。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
每天到晚就是瀟灑地逛逛園林,每年到頭就是悠哉地唱歌喝酒,真是感慨啊。月薪十萬、官居二品,朝廷還雇我這個能撈就撈、能混就混的閒人。喂喂,你老哥講話會不會太直接了?鬼島的祕密都被你說出來,以後大家還怎麼混下去(讀過後本魯也一時就詩興大發,寫了一句「年薪還沒破百萬,學校雇我作廢人」)。總之老白就是這樣一個鐵漢子真男人,薪水多少也不怕人家知道,洪邁《容齋隨筆》曾經稱讚他:
白樂天仕官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蓋見矣。
這種曬月薪的炫耀或哭哭的行為,在往後得到頌讚。大概就是現在什麼「公務人員財產申報法」或「公務人員財產來源不明法」的由來。不過這篇介紹這些也就是搞笑一下,畢竟我們現在物價不同於唐代,而學者也注意到,中唐之後由於社會開始動盪,物價開始起伏,也面臨通膨等現象,所以這種月薪、年終什麼的,大家參考一下就好,其實社會還是很公平的(又在講幹話),不要拿來亂戰古人、現代人就好。
之前有部宮廷劇《延禧攻略》超熱門,主角魏瓔珞在裡面個性耿直,有仇必報的
火辣性格,讓劇迷為之瘋狂。不過劇中也用了不少古文梗,各位若看過第一集,瓔珞建議一個囂張的秀女在鞋底以金粉染蓮花,那就是她第一次耍的心機,這個典故來自於南齊的最後一個皇帝、東昏侯蕭寶卷:
(東昏侯)又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匝飾以金璧。……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剝取以施潘妃殿飾。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桷,便於地畫之,唯須宏麗,不知精密。酷不別畫,但取絢曜而已,故諸匠賴此得不用情。又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南史‧東昏侯傳》)
東昏侯的愛妃名叫潘玉兒,在《延禧攻略》改為潘玉奴,話說因為這潘妃喜歡
Bling-Bling的聖誕樹裝飾,東昏侯就把佛塔的金鈴剝下來裝到潘妃房房裡(為什麼又要講疊字),這事爾後被唐朝仇女戰神李商隱表到飛起來,寫了〈齊宮詞〉來嘲諷她。而除了將佛寺裝飾都給潘妃當做宮殿的掛飾之外,更讓地上鑿金蓮花,讓潘妃走過,仿效當年釋迦牟尼步步生蓮華的典故,只能說金變態。所以在《延禧攻略》裡,乾隆看了那步步生蓮的秀女才會如此森氣氣,大罵秀女「蕭寶卷是昏君,潘妃是妖妃,這豈不是把朕跟蕭寶卷相提並論了嗎」?
劇中雖然沒有說清楚,但魏瓔珞卻對這段史料很熟悉,所以鄉親啊,尼看看讀古文有多重要。而《延禧攻略》裡另外一段,後宮嬪妃全體變裝擺市集的故事,其實也來自東昏侯。要介紹這典故,要先說明南朝貴族的生活與娛樂。話說古典時期的貴族通常養尊處優,生活優渥,在聲色娛樂過度疲乏的情況下,他們難免得找一些新娛樂得到一種扮裝的快感,而其中搞變裝搞得規模最大最鋪張的,也就是咱們這位以昏君出名的南齊東昏侯:
(東昏侯)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豎共為裨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鬥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荊子……每游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褌,著綠絲屩,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於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南史‧東昏侯傳》)
史傳有載說這潘妃啊,其實出自庶民階層,其父在市集做過買賣,基本上就是「夜市人生」的劇情,所以潘妃特別喜歡那種平民市集的雜沓紊亂氣氛。因此寵幸她的東昏侯就給他在其御苑裡搞了個夜市菜市場,全宮的婢女太監都扮成攤販,這種大型變裝派對感覺起來滿high的,和之前高中生扮納粹有得比。按照上述《南史》所載,這市集全都玩真的,鬧事偷竊什麼都有,連皇帝自己亂擺攤位都要被開罰單,還要被鞭刑(根本加入SM元素),聽起來實在有點色色der。但咱們東昏侯顯得玩得很盡興扮得很認真,還自己變裝成殺豬的。於是當時的酸民就編了一首歌:「至尊屠肉,潘妃酤酒。」皇帝自己拿殺豬刀,貴妃變成酒店妹,這成何體統?
但其實整個魏晉南北朝,這樣的扮裝癖與變裝趴竟然比我們想的還要多次,而且多半都是君主或王侯等名人有此嗜好,如以下幾段史書的原文:
(宋少帝劉義符)居帝王之位……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宋書‧少帝紀》)(南齊鬱林王蕭昭業)常裸袒,著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褌,雜采衵服。 好鬥雞,密買雞至數千價。(《南史‧鬱林王紀》)(北齊幼主高恒)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為乞食兒;又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北齊書‧幼主紀》)
我的老天鵝啊,少帝劉義符除了搞市集,還喜歡裝民工,跟著一起去做粗工打石工。至於鬱林王蕭昭業就更ㄎㄧㄤ了,嗜好裸半身,玩那種市井小民的鬥雞遊戲。最94狂的就是北齊的高恒,穿著破爛衣服變裝成犀利哥在路邊乞討,討爽了還跑去貧民窟跟丐幫的混在一起以物易物。前面提到的《延禧攻略》──後宮諸嬪妃當起攤販,魏瓔珞親自賣酒,這種俚俗與低俗的扮裝,其實帶來更多的刺激與新鮮感。至於這背後到底是什麼樣的變態心理呢? 學界推測是一種逐奇尚異。試想,這群王侯貴族跟我們蛇蛇的世界完全不一樣,他們含著金湯匙出生,從小就是人生勝利組,日復一日錦衣玉食飯來張口。庶民的混亂、雜沓與傖俗成了他們嚮往的美學,於是乎在所有娛樂都耗盡而再無新鮮感的時候,他們必須透過這種變裝或自虐來達到娛樂效果。
這種心態微妙而複雜,學者如鄭毓瑜在《文本風景》中更進一步認為,這樣的變裝其實反而有一種特權建構的意味。就好像美女正咩喜歡秀素顏照或玩扮醜扮鬼的APP,那是一種「因為我是貴族所以我爽就可以扮成販夫走卒」的權威,是一種單向度的越界,就像《乞丐王子》的故事。一旦扮窮醜扮乞丐變成了現實,那就再無娛樂歡快而只剩下悲慘。
所以奢談什麼變裝只是好玩,搞笑只因無知,實則太化約了人類行為與自由意志的多元和複雜。每次的選擇與無機的行為,背後都有一連串深刻細碎的符號能指。這也正是學術研究的意義。
19. 月薪十萬,能撈就撈?──唐朝詩人月薪一覽表
關於新世代的困境,二十二K的惡法,什麼台灣年輕人缺乏狼性,社會是不是hen公平等等這類的話題,其實已經討論了好幾年(喂,不是說好不戰這個)。更慘的是每當有些人被破格任用拔擢,當上了什麼總經理董事長還發研人之類的,就會被人家檢討每個月爽領多少等等的。
其實上班族都知道薪水算是隱私的一部分,不好隨便問,雖然過年還是會被一些白目長輩出來說三道四。但其實唐代詩人,尤其是中唐新樂府那一掛,強調詩歌要應時而作,要阿嬤都看得懂的詩人,倒是常常在詩裡曬月薪。
這學期我再度教到元稹〈遣悲懷〉這首悼亡神詩。第一首最後兩句「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說來情感很真摯,但實在白話到ㄎㄅ又傻眼,讓人想回「元稹,母湯喔」。這兩句詩直接翻譯就是「現在月薪破十萬,只能給你辦法會。之前《讀古文撞到鄉民》寫元稹這裡的情感,是只能共貧賤卻無緣共享樂的悲摧,對亡妻有種類似「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後」的無奈,但過去這首詩繫年一般是在元和六年(811),當時元稹轉任監察御史,終於算是當了個像樣的官,於是想到沒機會讓亡妻過好日子,不禁悲從中來。
但監察御史月薪甘有十萬摳嗎?過去國學大師陳寅恪就曾經檢討過這件事,說御史頂多四、五萬,認為元稹不會灌水嘴豪那麼誇張,所以此詩應該作於元和十三年(818),元稹任通州司馬兼領州務,加上額外加給,差不多八、九萬,膨風一下說十萬也還說得過去。
想到古人的薪水就覺得這話題滿妙的,於是我就隨手查了一下。不查不得了,元稹和他的老基友白居易原來都不怕月薪被人家知道,尤其我們熟悉的老白,寫了N首關於自己不同時期的薪水變化。起初白居易剛來到天龍國,被人家嗆說你南部人別來亂,隨後他秀出自己的文章,周遭傻眼貓咪,於是老白就電級移籍長安天龍國,開始他的小官吏奮鬥史。
白居易第一個做的官叫做「校書郎」,這是一個九品小官,也是進士科出身的文人經常初任的官職,他在〈常樂里閒居偶題〉詩中寫到:
茅屋四五間,一馬二樸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白居易說他月薪雖然十六K,但感覺錢夠用就好,於是每天都充實又快樂。這時候長輩就會跳出來罵說,安安,你才十六K就覺得滿足了,請問是不是缺乏狼性?但仔細看這首詩前面說的──茅屋就有四、五間,有配車配司機,其實這待遇很不錯了(謎之聲:月領三十K只能住茅房……)。
苦幹實幹了幾年之後,白居易升遷到了「左拾遺」,在〈酒後走筆〉詩中,他又把工作量和薪水誠實地說出來:
月懶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
這這這,個每月繳交諫書兩千張稿紙,我們大致算一張稿紙寫個一百字好了,那就是二十萬字,然後每年年薪三十萬,平均每個月還不到三萬,平均下來稿費一字才○‧一五元,實在有點辛酸(看向編輯)(嚇到吃手)。但重點還是古早錢比較有價值,如果三萬是美金的話這稿費其實還算不錯了。接著白居易當了翰林學士,兼任京兆尹的「戶曹參軍」,這時候他薪水也開始大提升:
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潭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困。咱們老白的月薪飆到四、五萬,還有以食物穀物代償的制度,可以說越領越多,開始進階成為爽爽領高薪、待退領年金的八百壯士(我又在公啥小)。接著他當「蘇州刺史」,「十萬戶州尤覺貴,兩千石祿敢言貧」;當「賓客分司」,寫「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至於最扯的大概是老白晚年轉任「太子少傅」,他寫了一首〈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
承華東署三分務,履道西池七過春。歌酒優遊聊卒歲,園林蕭灑可終身。留侯爵秩誠虛貴,疏受生涯未苦貧。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
每天到晚就是瀟灑地逛逛園林,每年到頭就是悠哉地唱歌喝酒,真是感慨啊。月薪十萬、官居二品,朝廷還雇我這個能撈就撈、能混就混的閒人。喂喂,你老哥講話會不會太直接了?鬼島的祕密都被你說出來,以後大家還怎麼混下去(讀過後本魯也一時就詩興大發,寫了一句「年薪還沒破百萬,學校雇我作廢人」)。總之老白就是這樣一個鐵漢子真男人,薪水多少也不怕人家知道,洪邁《容齋隨筆》曾經稱讚他:
白樂天仕官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蓋見矣。
這種曬月薪的炫耀或哭哭的行為,在往後得到頌讚。大概就是現在什麼「公務人員財產申報法」或「公務人員財產來源不明法」的由來。不過這篇介紹這些也就是搞笑一下,畢竟我們現在物價不同於唐代,而學者也注意到,中唐之後由於社會開始動盪,物價開始起伏,也面臨通膨等現象,所以這種月薪、年終什麼的,大家參考一下就好,其實社會還是很公平的(又在講幹話),不要拿來亂戰古人、現代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