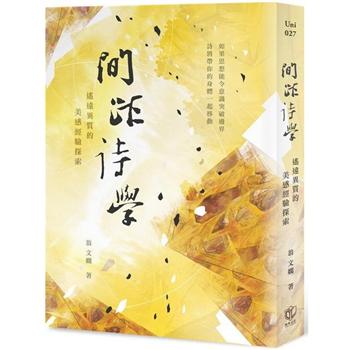長久以來,覺得沒有甚麼「不能讀進去」的詩人作品,愈是眾人難解的詩意,豈非令人愈來勁?因這顯示,準備將原有的眼界與水平向前擴展。例如2006年,一本《法國當代十七位詩人選集》(中譯本)在台灣出版,詩壇也是敬而遠之。對於那些奇怪的詩之載體,一如主編詩人雷文斯基(Jean Lewinski, 1970-)為之定名的:「閃躲˙中途停靠˙碎骨片」,這是書名也是他為當代詩下的定義。因此,除了正常的分行詩之外,戲劇、廣播電台文稿、洗衣精廣告、小孩性教育說明書,以致咖啡機的存在,冰箱與電話的電線,全都是詩的「中途停靠式」的載體。當代詩學工作者,需在這無所不在的文件入侵中,分辨文字及其後的思維方式、種種情狀,哪些是詩哪些不是。這名奇特的編者,有如幫我們做了一個很精彩的,將詩分辨出來的示範。隨著書的閱讀過程,我們有如漸漸蛻去一層皮,在不同載體的文字中,不斷重新塑造與構想:「詩是什麼?」而愈得進入,不同文化種族遮隔後的,一個更其本質的世界。
詩的「本質」世界是什麼呢?我們不能為之下定義,尤其在不同國族與不同朝代的品味中。但「詩」總有一個承載的身體,她是用文字組成的。雖然,現代的多項藝術媒介,如繪畫、電影、音樂歌曲、建築設計等,都可沾染表現出詩意,但說至詩之本尊,大概沒人反對,她應該與書寫的文字有關。1996年《詩探索》刊登石虎先生〈論字思維〉一文,特別加了一段編者按:「〈論字思維〉一文,涉及了漢字的結構與漢語詩歌特質的關係,第一次將『字』的問題提升到一種詩學的價值高度。」(1996:8)特闢「字思維與中國現代詩學」專欄,1996-98年有密集的文章回應,且在2002年結集成書。此後數年,陸續出現相關的討論文章。2006年李志元〈詩歌研究中的話語分析方法〉,大力推介「話語」分析方法之同時,提出巴赫金的名言:「詩歌的語言特徵不屬於語言及其成份,只屬於詩學結構。」(2006-1:26)如果為了追源漢字特徵,或漸漸出現一種漢詩的「本體」研究,則是有違這不斷隨詩學結構而變化的詩語內涵。李志元且指名這「讓人感到沮喪」的典型例子,正是「《詩探索》1996年第二輯起的關於漢語詩歌『字思維』的討論。」(2006-1:24)
循著「字思維」提出,《詩探索》編者也開闢「關於詩歌語言」、或「詩學研究」等專欄。筆者以為,「字思維」、「詩語言」、「話語」、「詩學結構」等等問題,都是不宜分割,全有關「詩本質」的追索與辨解。「詩」的範圍,也隨著「字思維」觀念出現,無分古典與現代詩之隔;如果有外語背景,秉承「字思維」的角度,可以嘗試進入東西方詩學結構的迷宮,讀杜甫的「風急天高猿嘯哀」,一如品嚐《閃躲˙中途停靠˙碎骨片》這些法國當代詩的趣味。但披閱《詩探索》詩刊內,「字思維」或「詩語言」的系列文章時,雖然多篇的文字與見解都很不錯,然而,它們彼此的觀念確是相牴觸的。
二、「字思維」引申的詩學糾纏
石虎本身是畫家,〈論字思維〉一文,文字卻寫得很美,例如說:
「漢字之間的並置,為中國人的意識提供了巨大的舞台。當兩個字自由並置在起,就意味著宇宙中類與類之間發生相撞與相姻,潛合出無限妙悟玄機。由漢字自由並置所造成的兩山相撞兩水相融的象象比隔和融化所產生的義象昇華,是『字思維』的並置美學原則。……漢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意義,象象並置,萬物寓於其間,這就是『字思維』的全部含義。……」(1996-2:10)
石虎提出,每一個字有其永恆不變的「象」,而字象在意義幻化中與物象複合,又產生另一重的思維,所以漢字具有「兩象思維特質」。「兩象相互作用複合,字象便具有了意的延綿,這種字象意延綿具有非言說性,它決定了漢詩詩意本質的不可言說性。」(9)
這麼美的字思維特性,如何在詩中顯現呢?新詩的歷史也有一百年,石虎所提出的「字」之理解,心內隱含的漢詩投影,有當代詩人的字思維表現嗎?抑或當歌頌「五千年的中華,典經歷歷,日月昭昭」之同時,想到的都是文言文?或已具高度藝術的,唐詩裡的「字」的並置方式?我們期待「字思維」與現代詩意的關係辨解。可惜石虎第二篇文章〈字象篇〉,仍繞著漢字造型上特性,討論「六法」(1966-3:37-40)。就算重新釋放字象內的「點」、「線」、「結」符號的神聖寓意,單一字象極限之美,最終或只幫忙了書法藝術。循著石虎文章開出的理念,「字思維」與中國現代詩學的討論軸心,似乎傾向挖掘中國古代典籍之菁華。而且,由於多屬「現代詩學評論」人士,對於古典的舉例與消化,呈現了較為籠統的樣貌。
擅長西方理論的王岳川,認為「字思維」的提出,可以「保存、重釋傳統中開拓並創新出新傳統,並在後殖民文化語境中,申張作為第三世界文化的中國文化存在的合法性,以及作為『他者的他者』與第一世界文化對話的急迫性和重要性。」(1997-2:37)在解讀詩歌思維方式與「象性」密不可分之同時,他悟出一條創作與欣賞雙反雙成的通道:「在詩的創作上,是主體融意為象,凝象為言,以言傳意象,以意象啟無形大象的過程。在詩意欣賞上則是由言視象,由象感意,由象捨言得象,由象而悟大象。」(43)這一連串的「意、象、言」之關係,其實已逸出了石虎關注的,單一的字之「象」性,而進入一首詩內,文字與文字所可能生出的全部弦外之音。「意、象、言」在古典場域原有的豐富意涵,恐怕需借用西方當代詩學(特別是法國詩學),重新論述建構出精確的詩學詮釋。王岳川為了實踐他對「象」的領悟,舉的例子,卻是有名的杜甫〈登高〉詩。但用古典述語解古典詩,在今天的白話文世紀,實是不容易翻出新意。我們更期待這「象」與「言」、「意」之辨,如何在一首新詩,或更前衛的現代詩中變化與互動。
章燕指出,新詩前驅如卞之琳、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甚至魯迅,他們在多種西方現代性洗禮的學習中,保留了「某些古典詩詞文言文的特色」。並提到台灣詩人,如余光中、洛夫、蓉子等,「他們的詩多注重古典意象的重造與更新,以及詩歌意境的創造。……並有一定的突破。」(1997-2:51-60)
回顧「字思維」系列文章,其舉例與「中國現代詩學」的連結,實在不多,留心分辨一下,只能追到台灣去了。但在台灣的古典連系上,如果只留意某些古典意象的重做,音韻節奏的處理;某些古典人物的重寫,甚至洛夫的〈隱題詩〉,被認為是「模仿律詩的結構,進而凸顯單字的份量」(章亞昕1998-2:89)。未知這被論述的台灣詩,能否達致石虎的理想:「當兩個字自由並置在一起,就意味著宇宙中類與類之間發生相撞與相姻」的境界?
漢字之「象」被刻劃創造時的原始能量,運用漢語的詩人,如何穿過五千載溯源那「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的時刻?身為詩現象觀察者,或應在現代的創造品裡揀擇,舉例印證。如果只在古典作品找到,那麼,「字思維」三字,可能與「現代詩學」無關。《詩探索》編者在有意無意間,將凡追尋中國文字、中國詩古典光輝的篇幅,定在「字思維」系列。有趣的是,這是一本「現代詩學」刊物,我們更常看見,另外專輯譬如「詩歌語言問題」、「詩學研究」等,有些文章論調,完全與崇敬古語的石虎是另一個角度。如上文提到的李志元文章(屬「詩學研究」專欄)就明白指出,追源漢詩的「本體」研究,是「讓人感到沮喪」。丘振中〈現代漢語詩歌中的語言問題〉(1995-3:30-35)雖然也憂慮詩的散文化現象,宣稱:「即使是現代詩歌史上膾炙人口的名作,絕大部分都沒有作到語言、意象和含蘊的密合無間,同時保持語言音響、結構、意義組織的非散文化。」(35)彷彿有古典作品永難企及之感歎。但文內,作者最讚揚的,卻仍是譯詩,「能傳達的意象與含蘊的震撼力挾帶著譯詩語言,給詩人們以重要的影響。」(35)隨即舉譯詩,阿特伍德〈所有的只是一件〉,並說:「任何中國現代詩人都會為自己能寫這樣的漢語詩句而驕傲」(35),引詩只七行,且錄如下參考:
不是一棵樹,但是樹
我們看見的,它將永不存在,被風撕裂
在風中起伏
彷彿一次一次。是什麼在推動地球
而後,使它成為夏天,將不是
草、樹葉、複製品,那裡是
另外一些詞。…… (35)
這是一首譯詩,有白話文種種連接詞,這些虛詞恐怕難據石虎「並置美學原則」來追源字中之象。不過,確是一首凝練又精采的詩。詩人視角從事物內部剖析,層層進入:樹,又不是一棵樹。將不必要事物濾清,直接令讀者在一次一次的「被風撕裂」間,感知那些什麼「在推動地球」的,更令人敬畏而宏大,隱在底層的狀貌。──完全與中國古典詩自外綜合觀看的視角相反──非關翻譯,它自然就不能援用字象與字象的「並置美學」原則。
丘振中先生也是一位優秀的詩人,可以直覺感受一首好詩的份量,但不能解的是,這譯詩明顯地重視內容表述而未考慮「音響形式」。作者只得遵其詩學原則,訂之為「妨礙新語言為自己設立更高目標的障礙」(35)。邱文中,詩質內容與音色如何並存,顯得無解。
更徹底相反的論點,屬詩人陳東東2000年〈回顧作為詩歌語言的現代漢語〉(2000-1-2:269-277),文章指出,現代漢語的功能是:「能夠納入突然擴大到幾乎無限的世界或宇宙」(269),它有效表達「中國人之處境和心境的新的語言」(269)。它是「通過譴責古漢語而確立自己的。」(269)
詩人認為:「『口語』從來就是令現代漢語充滿生機的原因。」(272),而「『西方』幾乎是現代漢語最初的全部話語」(273),是通過「譯述」,「使現代漢語成為一種自覺、主動、開放和不斷擴展著疆域的語言。它要說出的,或意欲說對的,是所謂『世界之中國』。」(273-274)陳東東正式宣稱,「如果以古漢語為依據的『漢語性』或『中文性』用作標準,去判定現代漢語,尤其是作為詩歌語言的現代漢語的『地道』或不『地道』,是一件似是而非的事情。」(271)
石虎是畫家而對漢字的歷史、身世感受得那樣深。陳東東是詩人,卻認為,只有富生機的民間「口語」,不斷擴拓新世界視野的「譯述」,才堪令當代中國詩人在世界立足;二種來源,還得加一項更重要的:與現代漢語出生有特殊關係的「知識份子性」。如此,「口語」才不致流俗;「譯述西方」才能具有「甄別、篩選和揚棄」的能力;而且,才可能抗衡某種權力的「整肅、清洗和專政」。陳東東可惜:「知識分子性」已漸被廣泛的日常性應用所淡忘,「詩歌的話語力量越來越只不過是一個詩人個人表達」(277),文章最後呼籲:「作為詩歌語言的現代漢語,仍須不斷回到它特殊的出生……。『知識分子性』,總是能夠在一首以這種語言寫下的『好詩』裡全面恢復它的記憶。」(277)
畫家石虎所提的「字思維」,邀請天下詩人敬重筆下的每一個字,冥想每字原先元氣淋漓的出生,特別注視亙古以來,造型結構的深層象意。但刻刻創作的詩人心念,關注可是中國當前的世界性,與詩身體內質的靈魂狀態:所謂生機、視野、與乎知識分子性格的良知良能。前者傾向作品的美感評鑑,後者是詩人自道,表現了某一時局裡詩歌的觀念。
台灣紀弦,在五○年代「現代派」宣言上,說過令人永遠記得的六大信條,其一即是:「現代詩是橫的連接,而不是縱的繼承。」(2002:70)而且指名要承繼自波特萊爾以降的現代詩傳統。忽忽過了五十年,在大陸2000年的詩人,仍然大有氣勢宣告:「現代漢語跟古漢語的關係特徵不是『延續』而是『斷裂』。這種『斷裂』也最明顯地體現於這兩種語言寫下的不同的詩。……」(陳東東:271)、「現代漢語給自己一個鐵胃。它甚至也盡可能消化著古漢語,但這種消化並不意味著古漢語會是現代漢語的一個過去,哪怕是一個未來的過去。……」(陳東東:270-271)
白話文出現,有如標示了一個與古代中國決裂的世紀。但如果真可以從宗教信仰到哲學,一切自西方基礎源頭汲取,譬如在外國長大的華人。可惜居住這片黃土地一切靠中介隔了一層,譯述者以華人背景的理解和選擇,會傳至腦袋裡自動過濾。可以說,那些吸收物是自古延續至今的漢語基因,再加西文轉換的雜物並置,生出之奇怪混血種。如果一天不能正視這個已經五千年漢語體內種種殘留物與底層意識狀態,則所謂「覺悟於現代的知識分子」(陳東東:275),如果「覺悟主體」有如一切片,與延續的事物切斷歸零,在「詮釋學」的立場看,未成型的主體該如何引出「存在的叩問」,又如何有辯解客體的詮釋能力呢?
詩的「本質」世界是什麼呢?我們不能為之下定義,尤其在不同國族與不同朝代的品味中。但「詩」總有一個承載的身體,她是用文字組成的。雖然,現代的多項藝術媒介,如繪畫、電影、音樂歌曲、建築設計等,都可沾染表現出詩意,但說至詩之本尊,大概沒人反對,她應該與書寫的文字有關。1996年《詩探索》刊登石虎先生〈論字思維〉一文,特別加了一段編者按:「〈論字思維〉一文,涉及了漢字的結構與漢語詩歌特質的關係,第一次將『字』的問題提升到一種詩學的價值高度。」(1996:8)特闢「字思維與中國現代詩學」專欄,1996-98年有密集的文章回應,且在2002年結集成書。此後數年,陸續出現相關的討論文章。2006年李志元〈詩歌研究中的話語分析方法〉,大力推介「話語」分析方法之同時,提出巴赫金的名言:「詩歌的語言特徵不屬於語言及其成份,只屬於詩學結構。」(2006-1:26)如果為了追源漢字特徵,或漸漸出現一種漢詩的「本體」研究,則是有違這不斷隨詩學結構而變化的詩語內涵。李志元且指名這「讓人感到沮喪」的典型例子,正是「《詩探索》1996年第二輯起的關於漢語詩歌『字思維』的討論。」(2006-1:24)
循著「字思維」提出,《詩探索》編者也開闢「關於詩歌語言」、或「詩學研究」等專欄。筆者以為,「字思維」、「詩語言」、「話語」、「詩學結構」等等問題,都是不宜分割,全有關「詩本質」的追索與辨解。「詩」的範圍,也隨著「字思維」觀念出現,無分古典與現代詩之隔;如果有外語背景,秉承「字思維」的角度,可以嘗試進入東西方詩學結構的迷宮,讀杜甫的「風急天高猿嘯哀」,一如品嚐《閃躲˙中途停靠˙碎骨片》這些法國當代詩的趣味。但披閱《詩探索》詩刊內,「字思維」或「詩語言」的系列文章時,雖然多篇的文字與見解都很不錯,然而,它們彼此的觀念確是相牴觸的。
二、「字思維」引申的詩學糾纏
石虎本身是畫家,〈論字思維〉一文,文字卻寫得很美,例如說:
「漢字之間的並置,為中國人的意識提供了巨大的舞台。當兩個字自由並置在起,就意味著宇宙中類與類之間發生相撞與相姻,潛合出無限妙悟玄機。由漢字自由並置所造成的兩山相撞兩水相融的象象比隔和融化所產生的義象昇華,是『字思維』的並置美學原則。……漢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意義,象象並置,萬物寓於其間,這就是『字思維』的全部含義。……」(1996-2:10)
石虎提出,每一個字有其永恆不變的「象」,而字象在意義幻化中與物象複合,又產生另一重的思維,所以漢字具有「兩象思維特質」。「兩象相互作用複合,字象便具有了意的延綿,這種字象意延綿具有非言說性,它決定了漢詩詩意本質的不可言說性。」(9)
這麼美的字思維特性,如何在詩中顯現呢?新詩的歷史也有一百年,石虎所提出的「字」之理解,心內隱含的漢詩投影,有當代詩人的字思維表現嗎?抑或當歌頌「五千年的中華,典經歷歷,日月昭昭」之同時,想到的都是文言文?或已具高度藝術的,唐詩裡的「字」的並置方式?我們期待「字思維」與現代詩意的關係辨解。可惜石虎第二篇文章〈字象篇〉,仍繞著漢字造型上特性,討論「六法」(1966-3:37-40)。就算重新釋放字象內的「點」、「線」、「結」符號的神聖寓意,單一字象極限之美,最終或只幫忙了書法藝術。循著石虎文章開出的理念,「字思維」與中國現代詩學的討論軸心,似乎傾向挖掘中國古代典籍之菁華。而且,由於多屬「現代詩學評論」人士,對於古典的舉例與消化,呈現了較為籠統的樣貌。
擅長西方理論的王岳川,認為「字思維」的提出,可以「保存、重釋傳統中開拓並創新出新傳統,並在後殖民文化語境中,申張作為第三世界文化的中國文化存在的合法性,以及作為『他者的他者』與第一世界文化對話的急迫性和重要性。」(1997-2:37)在解讀詩歌思維方式與「象性」密不可分之同時,他悟出一條創作與欣賞雙反雙成的通道:「在詩的創作上,是主體融意為象,凝象為言,以言傳意象,以意象啟無形大象的過程。在詩意欣賞上則是由言視象,由象感意,由象捨言得象,由象而悟大象。」(43)這一連串的「意、象、言」之關係,其實已逸出了石虎關注的,單一的字之「象」性,而進入一首詩內,文字與文字所可能生出的全部弦外之音。「意、象、言」在古典場域原有的豐富意涵,恐怕需借用西方當代詩學(特別是法國詩學),重新論述建構出精確的詩學詮釋。王岳川為了實踐他對「象」的領悟,舉的例子,卻是有名的杜甫〈登高〉詩。但用古典述語解古典詩,在今天的白話文世紀,實是不容易翻出新意。我們更期待這「象」與「言」、「意」之辨,如何在一首新詩,或更前衛的現代詩中變化與互動。
章燕指出,新詩前驅如卞之琳、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甚至魯迅,他們在多種西方現代性洗禮的學習中,保留了「某些古典詩詞文言文的特色」。並提到台灣詩人,如余光中、洛夫、蓉子等,「他們的詩多注重古典意象的重造與更新,以及詩歌意境的創造。……並有一定的突破。」(1997-2:51-60)
回顧「字思維」系列文章,其舉例與「中國現代詩學」的連結,實在不多,留心分辨一下,只能追到台灣去了。但在台灣的古典連系上,如果只留意某些古典意象的重做,音韻節奏的處理;某些古典人物的重寫,甚至洛夫的〈隱題詩〉,被認為是「模仿律詩的結構,進而凸顯單字的份量」(章亞昕1998-2:89)。未知這被論述的台灣詩,能否達致石虎的理想:「當兩個字自由並置在一起,就意味著宇宙中類與類之間發生相撞與相姻」的境界?
漢字之「象」被刻劃創造時的原始能量,運用漢語的詩人,如何穿過五千載溯源那「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的時刻?身為詩現象觀察者,或應在現代的創造品裡揀擇,舉例印證。如果只在古典作品找到,那麼,「字思維」三字,可能與「現代詩學」無關。《詩探索》編者在有意無意間,將凡追尋中國文字、中國詩古典光輝的篇幅,定在「字思維」系列。有趣的是,這是一本「現代詩學」刊物,我們更常看見,另外專輯譬如「詩歌語言問題」、「詩學研究」等,有些文章論調,完全與崇敬古語的石虎是另一個角度。如上文提到的李志元文章(屬「詩學研究」專欄)就明白指出,追源漢詩的「本體」研究,是「讓人感到沮喪」。丘振中〈現代漢語詩歌中的語言問題〉(1995-3:30-35)雖然也憂慮詩的散文化現象,宣稱:「即使是現代詩歌史上膾炙人口的名作,絕大部分都沒有作到語言、意象和含蘊的密合無間,同時保持語言音響、結構、意義組織的非散文化。」(35)彷彿有古典作品永難企及之感歎。但文內,作者最讚揚的,卻仍是譯詩,「能傳達的意象與含蘊的震撼力挾帶著譯詩語言,給詩人們以重要的影響。」(35)隨即舉譯詩,阿特伍德〈所有的只是一件〉,並說:「任何中國現代詩人都會為自己能寫這樣的漢語詩句而驕傲」(35),引詩只七行,且錄如下參考:
不是一棵樹,但是樹
我們看見的,它將永不存在,被風撕裂
在風中起伏
彷彿一次一次。是什麼在推動地球
而後,使它成為夏天,將不是
草、樹葉、複製品,那裡是
另外一些詞。…… (35)
這是一首譯詩,有白話文種種連接詞,這些虛詞恐怕難據石虎「並置美學原則」來追源字中之象。不過,確是一首凝練又精采的詩。詩人視角從事物內部剖析,層層進入:樹,又不是一棵樹。將不必要事物濾清,直接令讀者在一次一次的「被風撕裂」間,感知那些什麼「在推動地球」的,更令人敬畏而宏大,隱在底層的狀貌。──完全與中國古典詩自外綜合觀看的視角相反──非關翻譯,它自然就不能援用字象與字象的「並置美學」原則。
丘振中先生也是一位優秀的詩人,可以直覺感受一首好詩的份量,但不能解的是,這譯詩明顯地重視內容表述而未考慮「音響形式」。作者只得遵其詩學原則,訂之為「妨礙新語言為自己設立更高目標的障礙」(35)。邱文中,詩質內容與音色如何並存,顯得無解。
更徹底相反的論點,屬詩人陳東東2000年〈回顧作為詩歌語言的現代漢語〉(2000-1-2:269-277),文章指出,現代漢語的功能是:「能夠納入突然擴大到幾乎無限的世界或宇宙」(269),它有效表達「中國人之處境和心境的新的語言」(269)。它是「通過譴責古漢語而確立自己的。」(269)
詩人認為:「『口語』從來就是令現代漢語充滿生機的原因。」(272),而「『西方』幾乎是現代漢語最初的全部話語」(273),是通過「譯述」,「使現代漢語成為一種自覺、主動、開放和不斷擴展著疆域的語言。它要說出的,或意欲說對的,是所謂『世界之中國』。」(273-274)陳東東正式宣稱,「如果以古漢語為依據的『漢語性』或『中文性』用作標準,去判定現代漢語,尤其是作為詩歌語言的現代漢語的『地道』或不『地道』,是一件似是而非的事情。」(271)
石虎是畫家而對漢字的歷史、身世感受得那樣深。陳東東是詩人,卻認為,只有富生機的民間「口語」,不斷擴拓新世界視野的「譯述」,才堪令當代中國詩人在世界立足;二種來源,還得加一項更重要的:與現代漢語出生有特殊關係的「知識份子性」。如此,「口語」才不致流俗;「譯述西方」才能具有「甄別、篩選和揚棄」的能力;而且,才可能抗衡某種權力的「整肅、清洗和專政」。陳東東可惜:「知識分子性」已漸被廣泛的日常性應用所淡忘,「詩歌的話語力量越來越只不過是一個詩人個人表達」(277),文章最後呼籲:「作為詩歌語言的現代漢語,仍須不斷回到它特殊的出生……。『知識分子性』,總是能夠在一首以這種語言寫下的『好詩』裡全面恢復它的記憶。」(277)
畫家石虎所提的「字思維」,邀請天下詩人敬重筆下的每一個字,冥想每字原先元氣淋漓的出生,特別注視亙古以來,造型結構的深層象意。但刻刻創作的詩人心念,關注可是中國當前的世界性,與詩身體內質的靈魂狀態:所謂生機、視野、與乎知識分子性格的良知良能。前者傾向作品的美感評鑑,後者是詩人自道,表現了某一時局裡詩歌的觀念。
台灣紀弦,在五○年代「現代派」宣言上,說過令人永遠記得的六大信條,其一即是:「現代詩是橫的連接,而不是縱的繼承。」(2002:70)而且指名要承繼自波特萊爾以降的現代詩傳統。忽忽過了五十年,在大陸2000年的詩人,仍然大有氣勢宣告:「現代漢語跟古漢語的關係特徵不是『延續』而是『斷裂』。這種『斷裂』也最明顯地體現於這兩種語言寫下的不同的詩。……」(陳東東:271)、「現代漢語給自己一個鐵胃。它甚至也盡可能消化著古漢語,但這種消化並不意味著古漢語會是現代漢語的一個過去,哪怕是一個未來的過去。……」(陳東東:270-271)
白話文出現,有如標示了一個與古代中國決裂的世紀。但如果真可以從宗教信仰到哲學,一切自西方基礎源頭汲取,譬如在外國長大的華人。可惜居住這片黃土地一切靠中介隔了一層,譯述者以華人背景的理解和選擇,會傳至腦袋裡自動過濾。可以說,那些吸收物是自古延續至今的漢語基因,再加西文轉換的雜物並置,生出之奇怪混血種。如果一天不能正視這個已經五千年漢語體內種種殘留物與底層意識狀態,則所謂「覺悟於現代的知識分子」(陳東東:275),如果「覺悟主體」有如一切片,與延續的事物切斷歸零,在「詮釋學」的立場看,未成型的主體該如何引出「存在的叩問」,又如何有辯解客體的詮釋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