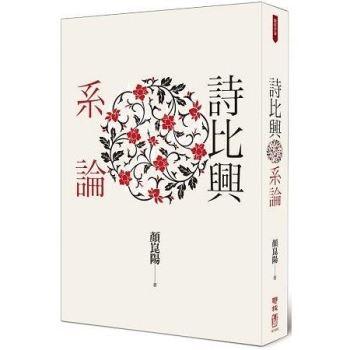從「言意位差」論先秦至六朝「興」義的演變
一、緒論
在學術史上,有關「比興」的論述,群言日出,不可勝數。其中尤以「興」義之說,更為繁複。「興」義論述,從歷史進程來看,應當分為二個大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古典詩歌文化實踐力」尚未衰竭的時期,可稱為「古典詩歌文化實踐期」。所謂「古典詩歌文化實踐力」指的是古典詩歌在社會中被普遍的創作、解讀、使用、論述而所涵具的生命力。這樣的文化情境,我們可以稱它為「古典詩歌文化情境」。在這階段,所有對「興」義發言的人,都還存在於此一情境中,對詩歌文化進行各種實踐;因此,他們的發言都基於對古典詩歌之創作、解讀、使用的切身體驗,去加以省思而作「當下決斷」的論述。這時,由於詩歌文化對他們而言是切身的存在情境,而不是純為認知之客體,故其言說充滿主體性。凡於文化情境中之實踐主體,其言說皆當享有創造之自由,與同一情境中之其他言說相對為義而等待接受詮釋。這一時期之「興」義論述,當作如是觀。
第二時期是「古典詩歌文化實踐力」已漸衰竭的時期。古典詩歌不再是社會中現存的一種普遍文化情境,而是故書堆中的史料,只做為被研究的知識對象。這一時期,可稱為「古典詩歌知識研究期」,多數對「興」義發言者,都已在「古典詩歌文化情境」之外,故其發言都非基於對古典詩歌之創作、解讀、使用的切身體驗,而是擇取古代的文獻當對象,進行分析而綜合的客觀性、系統化論述。這就是現代學術研究下的「興」義。它必須受到文獻證據以及方法學上的客觀限定,絕非可以主觀的自由創說。
社會文化之變遷,其「變」以漸不以頓。因此任何社會文化歷史的分期,都不可能如政治上之改朝換代,以一定點時間為斷限。上述二期的分割,亦大致只能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分水嶺。
這樣的分期,最主要的用意,乃是為了分辨這二個時期有關「興」義論述,其論述目的、知識性質與方法的差異,從而為處在第二期的現代學者做出發言的定位,讓我們明白,在進行「興」義論述時,必須先確認論述的目的、方法與乎所獲致之知識的性質。這樣的分期,也並非截然切割二者,以為第一期之中,完全沒有「詩歌知識的研究」;而第二期之中,完全沒有「詩歌文化的實踐」。實則,有關《詩經》、《楚辭》之「興」義的知識研究,漢代以來即已有之;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古典詩歌的創作,仍然沒有完全斷絕;但是,不可否認的,文化做為一種群體性的社會行為現象看待時,同一種社會行為現象在不同的時代情境中,其為主要性或次要性、大眾性或小眾性,確實可以觀察而分辨。而任何時代的某種主要性、大眾性的文化現象,必然是主流的社會階層在現實生活中,經常的、普遍的反覆性社會行為。它滲透並表現在自身或關涉的各種生活形式上,其深層處隱含著某種生命存在價值的觀念系統;因此,涵具著某一社會階層的普遍主體性。從古典詩歌而言,這一社會階層就是「士人階層」。
「古典詩歌」做為一種群體性的社會行為現象來看待,它在第一期士人階層的現實生活中,一直就是主要性、大眾性的文化,滲透並且表現在自身與關涉的各種生活形式上。所謂「自身」指的是詩歌的創作、解讀;所謂「關涉」,指的是詩的社會性應用,例如賦詩言志、諷諫、酬贈等。甚而其深層處隱涵著生命存在的價值觀念系統,例如詩的本質與功能可以致使人倫和諧、風俗淳厚。在這樣的文化情境中,詩歌的創作、解讀、使用,種種不離現實生活的實踐,才是士人階層從事詩歌文化活動的主要目的。從而詩的知識研究,對他們而言,並不是一種脫離當代社會文化存在情境的客觀認知。因此,論究「比興」,解讀詩騷,雖然也可以說是一種知識研究;但它更重要的意義,卻是士人們經由詮釋歷史以詮釋當代的一種文化承變的創造性行為。「通經致用」、「鑑古知今」,一直就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特殊性能,其當下的存在主體性始終鮮活。準此,類如鍾嶸在《詩品.序》中所說:「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固屬因應當代詩歌文化情境的創發性言說;即使漢儒之詮釋詩騷,其所說「興」義,也不能視為與當代社會文化存在情境無涉,而純為客觀化、系統化的知識研究。因此,相對於第二期來說,第一期在「古典詩歌」相關活動所表現的特徵,應該是「文化實踐」,而不是「知識研究」。至於在第二期的知識階層中,「古典詩歌」的文化實踐力既已日漸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新文化運動」後興起的新文學。「古典詩歌」在創作、解讀、使用方面,雖然還未完全斷絕;但是,不可否認的,它已在我們當代社會文化存在情境中,弱化為相當次要而小眾性的文化,甚而逐漸脫離知識階層的生活,而萎縮了它所涵具的普遍主體性。再加上現代學術受到西方理論的影響,追求客觀性、系統性的論述。大多數研究「興」義的現代學者,在生活上都沒有切身的古典詩歌實踐經驗,也沒有因應當代詩文化情境感受的創發性思維。我們所做的其實就是針對文獻去進行研究,以期獲致客觀性、系統性的知識。雖然詮釋歷史,無法避免其主觀性;但是,卻並非如此就可以完全擺脫詮釋的客觀性限制。而這個客觀性,弔詭的卻又不是由純粹認知客體的屬性所決定,也不是由一套預設的理論系統所保證;而是取決於詮釋主體之虛心面對詮釋對象之歷史語境的理解態度,那是在互為主體的理解限定之下,所形成的相對客觀性。一方面避免以為詮釋歷史可以獲致唯一確切知識的「絕對客觀主義」;另一方面也避免以為詮釋歷史可以完全無視於對象的客觀他在性,而任意虛說的「絕對主觀主義」。
第一時期之中,根據趙沛霖的研究,在「詩歌文化實踐期」之前,還有一段「宗教文化實踐期」,它才是「興」的源頭。此說有其見地;但是,由於文化的演變,宗教崇拜中的原始興象,經過歷史積澱,到《詩經》時代之後,「興」義已聚集展現在詩歌文化中,而宗教性的興象就只剩約略的殘跡而已。因此,我們不特別在「詩歌文化實踐期」之前,另立一個「宗教文化實踐期」。
第一期之興義,若從「詩歌文化」的結構去分析,還可以分析出三個序位:第一序位為詩歌的創作(可以包含詩用)、第二序位為詩歌的詮釋、第三序位為詩學理論。三者之間,層層後設,也就是詮釋乃對創作的後設性論述,而理論又是對創作與詮釋的後設性論述。
第一、二序位的論述,再就其對象的差別,則主要又有「詩經學」與「一般詩學」兩個不同的系統。這兩個系統當然不是涇渭分明。從時間歷程來說,「詩經學」產生在前,「一般詩學」產生在後。後者對前者有所引藉,但是也有所變革或排斥。本文主要是對於第一時期「興」義的後設性論述,斷取的時程是先秦以迄六朝。針對詩歌文化結構中,第二序位的詮釋層,與第三序位的理論層;涉及的領域包括「詩經學」與「一般詩學」。我們所預設的詮釋觀點是:在文學總體情境的活動中,從世界、作者、作品、讀者四種不同的位置發言,會導致同一議題,使用同一關鍵詞的論述,其實質義涵卻有差異。就以本論文來說,孔子、毛亨、鄭玄、王逸、劉勰等,都曾針對詩歌活動中「興」這一議題發言,並且在語言形式上使用同一個關鍵詞「興」,卻因為他們所站立的發言位置不同,而導致所發之「言」在文學理論之「意」上,形成了實質義涵的差異。本論文中,稱這種論述現象為「言意位差」。
假如這種「言意位差」不僅是個人偶有的發言位置所造成,而是在同一時代的詮釋視域中,被某種文化意識形態所限定,以致諸多發言者皆可能站在相同的發言位置;之後,由於時移世改,文化意識形態改變,詮釋視域也改變,而後一代之諸多發言者所論述之議題及所使用之關鍵詞雖同,卻因發言位置移易了,其所發之言的意義也跟著不同。前後代之間,便由此而形成同一議題的「言意位差」。我們通過這種「言意位差」的觀點,對同一議題進行歷時性的研究,便可以詮釋出其意義的演變,而建構此一議題的「觀念史」。
本論文就是從歷時性的「言意位差」觀點,以詮釋先秦至六朝「興」義的演變,建構了「興」的觀念史。我們之所以採取此一時間斷限,是因為有見於從世界、作者、作品、讀者這四種不同的位置,對詩歌文化中的「興」義發言,其「言意位差」自先秦到六朝已四義周備。六朝之後,只是前四種「言意位差」的延續而加以深化而已。
一、緒論
在學術史上,有關「比興」的論述,群言日出,不可勝數。其中尤以「興」義之說,更為繁複。「興」義論述,從歷史進程來看,應當分為二個大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古典詩歌文化實踐力」尚未衰竭的時期,可稱為「古典詩歌文化實踐期」。所謂「古典詩歌文化實踐力」指的是古典詩歌在社會中被普遍的創作、解讀、使用、論述而所涵具的生命力。這樣的文化情境,我們可以稱它為「古典詩歌文化情境」。在這階段,所有對「興」義發言的人,都還存在於此一情境中,對詩歌文化進行各種實踐;因此,他們的發言都基於對古典詩歌之創作、解讀、使用的切身體驗,去加以省思而作「當下決斷」的論述。這時,由於詩歌文化對他們而言是切身的存在情境,而不是純為認知之客體,故其言說充滿主體性。凡於文化情境中之實踐主體,其言說皆當享有創造之自由,與同一情境中之其他言說相對為義而等待接受詮釋。這一時期之「興」義論述,當作如是觀。
第二時期是「古典詩歌文化實踐力」已漸衰竭的時期。古典詩歌不再是社會中現存的一種普遍文化情境,而是故書堆中的史料,只做為被研究的知識對象。這一時期,可稱為「古典詩歌知識研究期」,多數對「興」義發言者,都已在「古典詩歌文化情境」之外,故其發言都非基於對古典詩歌之創作、解讀、使用的切身體驗,而是擇取古代的文獻當對象,進行分析而綜合的客觀性、系統化論述。這就是現代學術研究下的「興」義。它必須受到文獻證據以及方法學上的客觀限定,絕非可以主觀的自由創說。
社會文化之變遷,其「變」以漸不以頓。因此任何社會文化歷史的分期,都不可能如政治上之改朝換代,以一定點時間為斷限。上述二期的分割,亦大致只能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分水嶺。
這樣的分期,最主要的用意,乃是為了分辨這二個時期有關「興」義論述,其論述目的、知識性質與方法的差異,從而為處在第二期的現代學者做出發言的定位,讓我們明白,在進行「興」義論述時,必須先確認論述的目的、方法與乎所獲致之知識的性質。這樣的分期,也並非截然切割二者,以為第一期之中,完全沒有「詩歌知識的研究」;而第二期之中,完全沒有「詩歌文化的實踐」。實則,有關《詩經》、《楚辭》之「興」義的知識研究,漢代以來即已有之;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古典詩歌的創作,仍然沒有完全斷絕;但是,不可否認的,文化做為一種群體性的社會行為現象看待時,同一種社會行為現象在不同的時代情境中,其為主要性或次要性、大眾性或小眾性,確實可以觀察而分辨。而任何時代的某種主要性、大眾性的文化現象,必然是主流的社會階層在現實生活中,經常的、普遍的反覆性社會行為。它滲透並表現在自身或關涉的各種生活形式上,其深層處隱含著某種生命存在價值的觀念系統;因此,涵具著某一社會階層的普遍主體性。從古典詩歌而言,這一社會階層就是「士人階層」。
「古典詩歌」做為一種群體性的社會行為現象來看待,它在第一期士人階層的現實生活中,一直就是主要性、大眾性的文化,滲透並且表現在自身與關涉的各種生活形式上。所謂「自身」指的是詩歌的創作、解讀;所謂「關涉」,指的是詩的社會性應用,例如賦詩言志、諷諫、酬贈等。甚而其深層處隱涵著生命存在的價值觀念系統,例如詩的本質與功能可以致使人倫和諧、風俗淳厚。在這樣的文化情境中,詩歌的創作、解讀、使用,種種不離現實生活的實踐,才是士人階層從事詩歌文化活動的主要目的。從而詩的知識研究,對他們而言,並不是一種脫離當代社會文化存在情境的客觀認知。因此,論究「比興」,解讀詩騷,雖然也可以說是一種知識研究;但它更重要的意義,卻是士人們經由詮釋歷史以詮釋當代的一種文化承變的創造性行為。「通經致用」、「鑑古知今」,一直就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特殊性能,其當下的存在主體性始終鮮活。準此,類如鍾嶸在《詩品.序》中所說:「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固屬因應當代詩歌文化情境的創發性言說;即使漢儒之詮釋詩騷,其所說「興」義,也不能視為與當代社會文化存在情境無涉,而純為客觀化、系統化的知識研究。因此,相對於第二期來說,第一期在「古典詩歌」相關活動所表現的特徵,應該是「文化實踐」,而不是「知識研究」。至於在第二期的知識階層中,「古典詩歌」的文化實踐力既已日漸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新文化運動」後興起的新文學。「古典詩歌」在創作、解讀、使用方面,雖然還未完全斷絕;但是,不可否認的,它已在我們當代社會文化存在情境中,弱化為相當次要而小眾性的文化,甚而逐漸脫離知識階層的生活,而萎縮了它所涵具的普遍主體性。再加上現代學術受到西方理論的影響,追求客觀性、系統性的論述。大多數研究「興」義的現代學者,在生活上都沒有切身的古典詩歌實踐經驗,也沒有因應當代詩文化情境感受的創發性思維。我們所做的其實就是針對文獻去進行研究,以期獲致客觀性、系統性的知識。雖然詮釋歷史,無法避免其主觀性;但是,卻並非如此就可以完全擺脫詮釋的客觀性限制。而這個客觀性,弔詭的卻又不是由純粹認知客體的屬性所決定,也不是由一套預設的理論系統所保證;而是取決於詮釋主體之虛心面對詮釋對象之歷史語境的理解態度,那是在互為主體的理解限定之下,所形成的相對客觀性。一方面避免以為詮釋歷史可以獲致唯一確切知識的「絕對客觀主義」;另一方面也避免以為詮釋歷史可以完全無視於對象的客觀他在性,而任意虛說的「絕對主觀主義」。
第一時期之中,根據趙沛霖的研究,在「詩歌文化實踐期」之前,還有一段「宗教文化實踐期」,它才是「興」的源頭。此說有其見地;但是,由於文化的演變,宗教崇拜中的原始興象,經過歷史積澱,到《詩經》時代之後,「興」義已聚集展現在詩歌文化中,而宗教性的興象就只剩約略的殘跡而已。因此,我們不特別在「詩歌文化實踐期」之前,另立一個「宗教文化實踐期」。
第一期之興義,若從「詩歌文化」的結構去分析,還可以分析出三個序位:第一序位為詩歌的創作(可以包含詩用)、第二序位為詩歌的詮釋、第三序位為詩學理論。三者之間,層層後設,也就是詮釋乃對創作的後設性論述,而理論又是對創作與詮釋的後設性論述。
第一、二序位的論述,再就其對象的差別,則主要又有「詩經學」與「一般詩學」兩個不同的系統。這兩個系統當然不是涇渭分明。從時間歷程來說,「詩經學」產生在前,「一般詩學」產生在後。後者對前者有所引藉,但是也有所變革或排斥。本文主要是對於第一時期「興」義的後設性論述,斷取的時程是先秦以迄六朝。針對詩歌文化結構中,第二序位的詮釋層,與第三序位的理論層;涉及的領域包括「詩經學」與「一般詩學」。我們所預設的詮釋觀點是:在文學總體情境的活動中,從世界、作者、作品、讀者四種不同的位置發言,會導致同一議題,使用同一關鍵詞的論述,其實質義涵卻有差異。就以本論文來說,孔子、毛亨、鄭玄、王逸、劉勰等,都曾針對詩歌活動中「興」這一議題發言,並且在語言形式上使用同一個關鍵詞「興」,卻因為他們所站立的發言位置不同,而導致所發之「言」在文學理論之「意」上,形成了實質義涵的差異。本論文中,稱這種論述現象為「言意位差」。
假如這種「言意位差」不僅是個人偶有的發言位置所造成,而是在同一時代的詮釋視域中,被某種文化意識形態所限定,以致諸多發言者皆可能站在相同的發言位置;之後,由於時移世改,文化意識形態改變,詮釋視域也改變,而後一代之諸多發言者所論述之議題及所使用之關鍵詞雖同,卻因發言位置移易了,其所發之言的意義也跟著不同。前後代之間,便由此而形成同一議題的「言意位差」。我們通過這種「言意位差」的觀點,對同一議題進行歷時性的研究,便可以詮釋出其意義的演變,而建構此一議題的「觀念史」。
本論文就是從歷時性的「言意位差」觀點,以詮釋先秦至六朝「興」義的演變,建構了「興」的觀念史。我們之所以採取此一時間斷限,是因為有見於從世界、作者、作品、讀者這四種不同的位置,對詩歌文化中的「興」義發言,其「言意位差」自先秦到六朝已四義周備。六朝之後,只是前四種「言意位差」的延續而加以深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