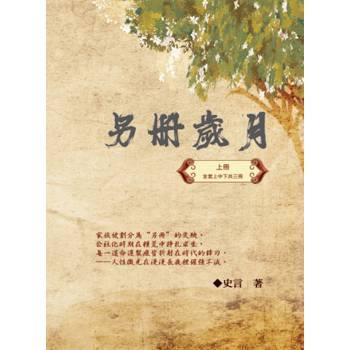1
山東中部有座陶山,陶山以南陶陽縣方莊區——一度叫方莊公社——有個榆樹村,從榆樹村西行十幾裡,就是永遠淌著黃泥湯子的黃河。榆樹村名副其實:不光榆樹多——村裡村外,場邊路旁,溝渠岸邊,地頭井臺,坡坡嶺嶺,到處生長著大大小小的榆樹,而且村南頭程家場院外邊還生長著一棵四裡八鄉聞名,“老當益壯”的大榆樹。大榆樹有多少歲了?沒有人知道,反正村裡年歲最大的人說,他爺爺的爺爺小時候,這榆樹已經是這幅老樣子了;它有多高?少說有5丈(誰也沒量過呀);多粗呢?村裡有個說法兒,不知啥時候,有個熱心人,想量一下老榆樹的“腰圍”,讓三個男人手拉著手,一起抱緊樹身,兩端的人夠不著頭兒,那人又拃了7拃,正巧有個小頑童在樹跟前站著,沒再拃,所以,這老榆樹的腰圍就是“三摟7拃1頑童”。老榆樹樹身已經十分蒼老,黑皮似鐵,褶皺如溝,裂紋挓挲,龇牙裂嘴,看上去老態龍踵,那是年深日久無數次風吹雨打,霜侵雪壓的印記。到了冬季,樹葉落盡,滿樹的虯莖曲枝淩亂乾枯,慘不忍睹,確是垂垂老矣,像是再也活不過來的樣子,但是,冬去春來,卻像突然蘇醒過來一樣,一夜之間,就露出一簇簇新綠,枝條上的榆錢兒挨挨排排,由綠變黃再變白,白花花一片,像梨花一樣好看。榆錢兒落了,跟著春風,飄飄搖搖,去尋找泥土了,枝條上橢圓形的小小綠葉又都竄了出來,不幾天,就長得密不透風,亭亭如蓋的樹冠在春天的豔陽下,展現一派蔥蘢,樹下的蔭涼足有畝把地那麼大一片。趕上春荒,老榆樹和滿村大大小小的榆樹上的榆錢兒、榆葉都被捋下來,填了村裡男女老少的肚腸,枝枝椏椏光禿禿的,忒難看了。榆樹們不惱不怨,過不了多少日子,又十分頑強地再長出滿樹的綠葉。這老榆樹,是忍饑挨餓的人的“菜籃”,是出力流汗的人歇腳的“涼亭”,不止這樣,它還承載著莊稼人的感情寄託。村裡一輩輩人世代流傳,說老榆樹已經有了“靈性”了,甚至成“神”了。逢年過節,老太太,閨女,媳婦兒紛紛來到樹下,燃香燒紙,擺供,元宵節來上燈,如果有什麼心願,就拿紅線或者紅綢布條兒,係到樹枝上,求它保佑自己得償心願。還有,讓人痛惜,也讓老榆樹傷心的是,多少年來,村裡蒙冤受屈的人,有男的,更多的是女人,有年紀大的,也有小年輕的,在風清月明或月黑風高的夜晚,來到老榆樹下,在老榆樹粗壯的樹叉上,係了繩子上弔自殺。老榆樹默默無言,悲憫地送他們從這裡去向另一個世界。風來了,樹枝搖動了,聲音淒慘而沉鬱,是老榆樹在嗚咽。老榆樹是莊稼人血淚苦難的見證。
榆樹村在當地左右方邊算是不小的村莊,全村600多戶,足足有3000來人。村裡祗程、江兩家是大戶,其他除了十來家小財主,“肉頭戶”之外,剩下的人家,無論姓什麼,或有個三、五畝薄地,勉強糊口度日,或者乾脆就是程、江兩家的佃戶了。
程家在榆樹村是老戶人家,大族門,靠上邊幾代勤儉持家,多進少出,據說,他們趁災年,用自己囤裡的存糧,跟快要餓死的人家換地,自家的土地像大水漫過一樣,擴張開來,成了陶陽縣小有名氣的地主,土地越來越多,家業越來越大,在榆樹村當央修建了三進兩出的大宅院,還把村子西南程家祖輩流傳的林地擴大,整修,築牆,建房,人稱“程家林”,凡程姓人家死了人,不論窮富,除了因傷風敗俗,被革出族門的人以外,均可葬此林中。村東南角是一排三個院落,東邊老榆樹跟前是磨房院,緊挨著是柴禾院,西頭是牲口院兒。這程家日子過得十分紅火,但是,人丁卻不旺,一連幾代單傳。清朝同治年間,程家請有名的風水先生看過,說程家宅院所在的位置地勢低窪,後邊有江家欞子門壓著,程家很難興旺發達,必須得建造一座跟江家欞子門一樣高的樓房,才會人財兩旺。程家聽了這話,用將近兩年的時間,把最後邊的院落擴大,拆掉堂屋,建起一座樓房,為了不觸怒江家,高度恰與江家欞子門持平。那是一座東西五間,底上三層,青磚到頂,灰黑色的龐然大物,是榆樹村從來沒有過,以後也沒有過的,在村裡居中聳立,俯視著周圍一大片高高低低,紛亂錯落而又千篇一律的黃泥白灰平屋頂,用文縐縐的話說,像鶴立雞群,也有村裡人說,像羊群裡的一頭駱駝。那年月土匪多,為安全起見,樓房北面,東、西山牆,從底到頂,都嚴嚴實實,祗在南面牆上,各層開兩扇花格子小窗,樓頂上天窗也不大,祗可容一人爬梯而上,夏天天熱,家裡人常爬上樓頂,在一圈女兒牆裡乘涼拉呱兒。因為窗子太少,樓裡常年黑乎乎的,大白天,女人做針線活兒,也得湊到小窗跟前,才能看得清針腳兒,人們給這樓房取個名字叫“暗樓”。莊裡人稱程家,都說是“暗樓上的”。
莊北頭江家,原是本縣北鄉一個山莊的財主,大清道光年間,江家老爺江錫爵花錢捐了官,騎馬從榆樹村北走過,見村後一裡來遠的地方,有東西走向的一道長長的嶺崗,狀似俯臥著的巨龍,從遠處看去,隱約有祥雲盤旋,江錫爵認准了這快風水寶地,找了陶陽縣令,由縣令出面,挾官府之勢,江家遷來榆樹村,在村子北邊,嶺崗以南,置地建宅。宅院門前,按規制築起了欞子門。莊裡人稱江家是“欞子門裡的”。這江家自從來榆樹村落戶以後,不知確實是宅子風水好,還是別的原因,幾代為官,直到大清朝末年,世事紛亂,江崇德辭官歸裡,在本縣做起了鄉紳。
山東中部有座陶山,陶山以南陶陽縣方莊區——一度叫方莊公社——有個榆樹村,從榆樹村西行十幾裡,就是永遠淌著黃泥湯子的黃河。榆樹村名副其實:不光榆樹多——村裡村外,場邊路旁,溝渠岸邊,地頭井臺,坡坡嶺嶺,到處生長著大大小小的榆樹,而且村南頭程家場院外邊還生長著一棵四裡八鄉聞名,“老當益壯”的大榆樹。大榆樹有多少歲了?沒有人知道,反正村裡年歲最大的人說,他爺爺的爺爺小時候,這榆樹已經是這幅老樣子了;它有多高?少說有5丈(誰也沒量過呀);多粗呢?村裡有個說法兒,不知啥時候,有個熱心人,想量一下老榆樹的“腰圍”,讓三個男人手拉著手,一起抱緊樹身,兩端的人夠不著頭兒,那人又拃了7拃,正巧有個小頑童在樹跟前站著,沒再拃,所以,這老榆樹的腰圍就是“三摟7拃1頑童”。老榆樹樹身已經十分蒼老,黑皮似鐵,褶皺如溝,裂紋挓挲,龇牙裂嘴,看上去老態龍踵,那是年深日久無數次風吹雨打,霜侵雪壓的印記。到了冬季,樹葉落盡,滿樹的虯莖曲枝淩亂乾枯,慘不忍睹,確是垂垂老矣,像是再也活不過來的樣子,但是,冬去春來,卻像突然蘇醒過來一樣,一夜之間,就露出一簇簇新綠,枝條上的榆錢兒挨挨排排,由綠變黃再變白,白花花一片,像梨花一樣好看。榆錢兒落了,跟著春風,飄飄搖搖,去尋找泥土了,枝條上橢圓形的小小綠葉又都竄了出來,不幾天,就長得密不透風,亭亭如蓋的樹冠在春天的豔陽下,展現一派蔥蘢,樹下的蔭涼足有畝把地那麼大一片。趕上春荒,老榆樹和滿村大大小小的榆樹上的榆錢兒、榆葉都被捋下來,填了村裡男女老少的肚腸,枝枝椏椏光禿禿的,忒難看了。榆樹們不惱不怨,過不了多少日子,又十分頑強地再長出滿樹的綠葉。這老榆樹,是忍饑挨餓的人的“菜籃”,是出力流汗的人歇腳的“涼亭”,不止這樣,它還承載著莊稼人的感情寄託。村裡一輩輩人世代流傳,說老榆樹已經有了“靈性”了,甚至成“神”了。逢年過節,老太太,閨女,媳婦兒紛紛來到樹下,燃香燒紙,擺供,元宵節來上燈,如果有什麼心願,就拿紅線或者紅綢布條兒,係到樹枝上,求它保佑自己得償心願。還有,讓人痛惜,也讓老榆樹傷心的是,多少年來,村裡蒙冤受屈的人,有男的,更多的是女人,有年紀大的,也有小年輕的,在風清月明或月黑風高的夜晚,來到老榆樹下,在老榆樹粗壯的樹叉上,係了繩子上弔自殺。老榆樹默默無言,悲憫地送他們從這裡去向另一個世界。風來了,樹枝搖動了,聲音淒慘而沉鬱,是老榆樹在嗚咽。老榆樹是莊稼人血淚苦難的見證。
榆樹村在當地左右方邊算是不小的村莊,全村600多戶,足足有3000來人。村裡祗程、江兩家是大戶,其他除了十來家小財主,“肉頭戶”之外,剩下的人家,無論姓什麼,或有個三、五畝薄地,勉強糊口度日,或者乾脆就是程、江兩家的佃戶了。
程家在榆樹村是老戶人家,大族門,靠上邊幾代勤儉持家,多進少出,據說,他們趁災年,用自己囤裡的存糧,跟快要餓死的人家換地,自家的土地像大水漫過一樣,擴張開來,成了陶陽縣小有名氣的地主,土地越來越多,家業越來越大,在榆樹村當央修建了三進兩出的大宅院,還把村子西南程家祖輩流傳的林地擴大,整修,築牆,建房,人稱“程家林”,凡程姓人家死了人,不論窮富,除了因傷風敗俗,被革出族門的人以外,均可葬此林中。村東南角是一排三個院落,東邊老榆樹跟前是磨房院,緊挨著是柴禾院,西頭是牲口院兒。這程家日子過得十分紅火,但是,人丁卻不旺,一連幾代單傳。清朝同治年間,程家請有名的風水先生看過,說程家宅院所在的位置地勢低窪,後邊有江家欞子門壓著,程家很難興旺發達,必須得建造一座跟江家欞子門一樣高的樓房,才會人財兩旺。程家聽了這話,用將近兩年的時間,把最後邊的院落擴大,拆掉堂屋,建起一座樓房,為了不觸怒江家,高度恰與江家欞子門持平。那是一座東西五間,底上三層,青磚到頂,灰黑色的龐然大物,是榆樹村從來沒有過,以後也沒有過的,在村裡居中聳立,俯視著周圍一大片高高低低,紛亂錯落而又千篇一律的黃泥白灰平屋頂,用文縐縐的話說,像鶴立雞群,也有村裡人說,像羊群裡的一頭駱駝。那年月土匪多,為安全起見,樓房北面,東、西山牆,從底到頂,都嚴嚴實實,祗在南面牆上,各層開兩扇花格子小窗,樓頂上天窗也不大,祗可容一人爬梯而上,夏天天熱,家裡人常爬上樓頂,在一圈女兒牆裡乘涼拉呱兒。因為窗子太少,樓裡常年黑乎乎的,大白天,女人做針線活兒,也得湊到小窗跟前,才能看得清針腳兒,人們給這樓房取個名字叫“暗樓”。莊裡人稱程家,都說是“暗樓上的”。
莊北頭江家,原是本縣北鄉一個山莊的財主,大清道光年間,江家老爺江錫爵花錢捐了官,騎馬從榆樹村北走過,見村後一裡來遠的地方,有東西走向的一道長長的嶺崗,狀似俯臥著的巨龍,從遠處看去,隱約有祥雲盤旋,江錫爵認准了這快風水寶地,找了陶陽縣令,由縣令出面,挾官府之勢,江家遷來榆樹村,在村子北邊,嶺崗以南,置地建宅。宅院門前,按規制築起了欞子門。莊裡人稱江家是“欞子門裡的”。這江家自從來榆樹村落戶以後,不知確實是宅子風水好,還是別的原因,幾代為官,直到大清朝末年,世事紛亂,江崇德辭官歸裡,在本縣做起了鄉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