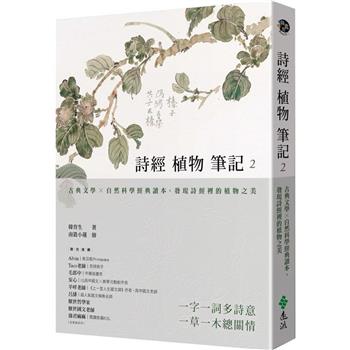蘆葦|鏡花水月覓傑作
《秦風.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坻」音同「池」。
▓雜家題解
曹植作《洛神賦》,李商隱作《錦瑟》,就像是對《蒹葭》一詩所引領的中國詩學傳統中縹緲又恍惚迷離的一脈(所謂幻詩)作出的至高回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和「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引領的詩境,下筆猶如神助,好像將變化奧祕的結晶看透了一般。但那種天才筆力驚人的華彩,落在《蒹葭》一詩洗盡鉛華的背景裡,立刻就變得平和安靜下來。
《蒹葭》依水而寫,幾乎寫盡了水性之變。水即情的代言,水的流動牽引著情的追慕,這情字很自然便是愛情的一面鏡子。這情絲的涓流,彙聚的水勢,如此充沛,不管霜露如何動變,不管河道如何悠長,都無法泯滅生命對美與愛的追尋。情字代表的含義當然不止愛情一種,它還包含人對理想的追求。當詩情從愛情感性的柔媚一變為理性的雄壯,《蒹葭》的色調也從明麗變得灰暗起來。欲從詩本義重新釋《詩》的朱熹,一定從《蒹葭》的多層次,進逼那個恍若隔世的空間時,一時迷糊,在《詩集傳》裡,他說:「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蒹葭》柔情似水的另一面,是它的「古奧雄深」(清朝女訓詁家王照圓《詩問》語),詩意的深闊與純真,正是生命之水蔚藍的色澤,就像蔚藍地球所形成的開放世界。《蒹葭》驚動了生命,打開了執念,連通了不確定性和自我價值認定的橋樑。那種「可見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的感受,將幻的曲折晦澀與真的簡明純一同時呈現在文學所關照的廣博世界裡,同時也為每一位讀者打通了一條連同真與幻的通途。
順心而寫,詩意自然極簡明,《蒹葭》寫的就是如「孔雀東南飛,五裡一徘徊」那樣追慕的事,但它寫作的驚人之處,就在於,每一個句子同時驚動和刺激著所有感官的參與,每一種參與,如王國維所言,都有那種「風人深致」的姿態,比如「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的驚心,「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心神搖曳,「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的出神欲飛。追慕而不得的餘味,構成了水天一色的混融。方玉潤《詩經原始》忍不住說:「以好戰樂鬥之邦,忽遇高超遠舉之作,可謂鶴立雞群。……其實首章已成絕唱。」
《漢書.地理志》說,秦地的邊疆與遊牧的戎狄交接,為保護家園,秦人常年修習戰備,崇尚武技和射獵,所以,秦風中有一種別的詩風裡少見的尚武精神和悲壯慷慨的情調。這種尚武之風,讓秦人顯出了性格中耿直粗獷的一面,從《蒹葭》,突然察覺到秦人性格裡善柔多情的一面,如此飄逸雋永,總令人有些猝不及防。
《蒹葭》以虛寫實的寫法,對後世中國文學和情感的表達影響深遠,《蒹葭》詩情內含的空泛與虛蕩,如同心靈巨大的峽谷,在這樣的峽谷裡,人們細密敏感的情感總能傳來獨特動人千折百應的回聲。
▓植物筆記
蒹葭,古代很多同物異名。蒹,嚴粲《詩集》云:「蒹,一名薕,又名荻。」現代認為是沒長穗的蘆葦。葭,《本草綱目》中,初生蘆葦稱為「葭」,開花之前稱為「蘆」,開花結實稱作「葦」,因此,蒹、葭、蘆、葦、蒹葭都可代稱蘆葦。蘆荻形貌相似,容易混淆,吳其濬在《植物名實圖考》中描述了蘆葦和荻的區別:「強脆而心實者為荻,矛纖而中虛者為葦。」古代,蘆葦的柔軟細莖可編成「葭簾」,莖粗壯柔韌的部分可編成「葦席」。《淮南子.覽冥》記載:「於是女媧煉五彩石以補蒼天……積蘆灰以止滔水。」《孝子傳》中,寒冬臘月,閔子騫的後母讓親生兒子穿棉花的棉襖,而讓閔子騫穿不能保暖的蘆花棉襖,因此「蘆花衣」用來比喻後母虐待非親生子女的代用語。戰國時,齊國的田單以火牛陣大破敵軍,牛尾所系的便是蘆葦。蘆葦還是西北河岸邊夯築城牆、固堤的先鋒環保植物。
蘆葦,禾本科蘆葦屬多年生高大草本,稈可高達三公尺,莖中空,根莖地下橫走,四處延伸。葉片狹長披針形,寬兩公分,邊緣粗糙尖端尖銳。大型圓錐花序。小穗通常呈三小花,第一小花常為雄花,其他兩小花為雌花。花後結實,有絲狀白毛,以助種子飛散。北半球廣布,蘆葦在中國分布很廣,《中國植物志》載,因為分布環境的變化,像沙漠地帶、沼澤地帶、高原地帶、鹹水地帶,會有不同的變異蘆葦群。
▓「我」注《詩經》
(中略)
▓《詩經》注我
再大的詩人,在這首詩面前都覺得自己短了,缺了。這首詩裡,讓人感覺虛到無垠,真到盡頭,心性所追慕的朦朧幻境裡一定會出現一個透明的地方。即使不善讀詩的人,讀到這樣的文字,也一樣會心裡一抖,抖的心亂了,生命卻清了。
我讀的時候,心裡也是這麼一抖,下面這首詩,連同那些彷彿追隨幻境的文字,便是在這樣一抖的激情裡自然而然生成的:
在東門,我初見你,
你夾雜在人群裡,像飄絮,如鳥鳴,是春風;
在溪邊的黃昏,我又見你,
在汲水的女孩子們中間,你如倒影,似水聲,若煙霞;
三月三的上巳節,在眾人注目的舞臺上,我看著你,你像烈火,如妖魅,是飛霜。
你——是我的驚雷。
風起時,你要走了,你登車入了幔帳,霧被吹得散亂,塵土迷了我的雙眼,殘葉敲著世界哢哢響。你伸出幔外輕拂幔帳的手指,我快攆著步伐,追著它。那一刻,那只手就是我的靜夜,是我的太陽,是千丈冰下剛剛融化的水滴。我追它不上,追你不著,唯有怔怔站在路中央,看你消失在蘆花的盡頭。感覺自己彷彿一瞬間死去,殘骨酥解,魂靈飄散,它們沖入大地,化成了一路上跳進你眼裡的柔柳風楊。
夢裡,見你站立在蘆羽如雪的地方。醒來,月影交織著殘夜,把雪地上長長的身影披到我身上。
五月,浮水東邊,月亮薄得如磨了千百遍的鏡子,太陽厚得像燒不盡的山火。真羡慕它們,在每個薄涼的清晨,能像是約好了一般,在不期而遇中淡淡分別。這個時候,百鳥歡鳴,蟲兒歌唱。風來了,拂動蘆葦葉上的露珠,暗露的濕痕未乾,你的影子不在。我心裡惶惶然,看煙波浸不透的水波,問水邊忙碌的漁女:「能不能告訴我,所謂伊人,可是在水一方?」
七月,濺著浪花嬉戲的孩童,把骨刺插著的黃魚摔到岸邊,滑下垂柳的小孩把碎葉撒在我身上。我尋著存了你腳印的水流的聲息,在這個煙波蕩漾的水邊,可以看到蘆花初開,蘆葦小穗上針一樣的碎花,像極了你眼睫毛上寒星一樣的水珠,那是三月三令我心醉的舞場。在風搖蘆花蕭疏淡蕩的節奏裡,那個霧裡不在的你,像風,像雨,又像雪,落在盛開在水鏡裡飄飄渺渺的花上。我呆呆看著水色流淌,忘了正捉弄我的孩子們的笑聲。在岸邊的岩石後面,孩子們搶著架子上烤熟了的黃魚,我心裡惴惴的,想要從他們的嘴裡探問:「所謂伊人,可是見過在水一方?」
十一月,奔馬濺碎枯黃的草屑,寒鴉震落瘦枝上的凝霜,冰河地,殘葉黃,蘆羽如雪似弓張。夢裡,見到你正在雪中央。
我問路翁:「春露起,秋分時,冬至日,能不能告訴我,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他看著我,長歎一聲,指著水波浩渺的地方:「孩子,順水去找,不要停下你的腳步,等到春暖花開時,她就會出現在河流盡頭的水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