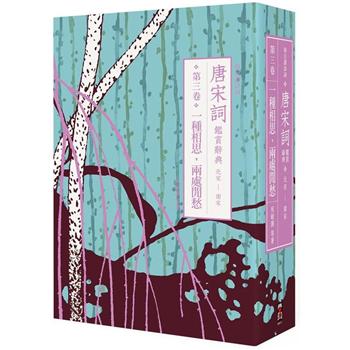〈一剪梅〉 李清照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這首詞,據舊題元人伊世珍作的《瑯嬛記》引《外傳》云:「易安結縭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但如王學初在《李清照集校註》中所指出:「清照適趙明誠時,兩家俱在東京,明誠正為太學生,無負笈遠遊事。此則所云,顯非事實。」何況《瑯嬛記》本是偽書,所引《外傳》更不知為何書,是不足為據的。玩味詞意,這首詞絕不是作者與趙明誠分別時所寫,而是作於遠離後。
詞的起句「紅藕香殘玉簟秋」,領起全篇。清詞評家梁紹壬稱此句「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間煙火氣」(《兩般秋雨盦隨筆》),或讚賞其「精秀特絕」(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它的上半句「紅藕香殘」寫戶外之景,下半句「玉簟秋」寫室內之物,對清秋季節起了點染作用,說明這是「已涼天氣未寒時」(韓偓〈已涼〉)。全句設色清麗,意象蘊藉,不僅刻畫出四周景色,而且烘托出詞人情懷。花開花落,既是自然界現象,也是悲歡離合的人事象徵;枕席生涼,既是肌膚間觸覺,也是淒涼獨處的內心感受。這一兼寫戶內外景物而景物中又暗寓情意的起句,一開頭就顯示了這首詞的環境氣氛和它的感情色彩。
上闋共六句,接下來的五句順序寫詞人從晝到夜一天內所作之事、所觸之景、所生之情。前兩句「輕解羅裳,獨上蘭舟」,寫的是白晝在水面泛舟之事。羅裳即羅裙,因裙之尺寸稍長於裙內之褲,解羅裙,以便輕裝登舟。於此亦見詞人在清寂無人處的率性任情。「獨上」二字暗示詞人處境,暗逗離情。下面「雲中誰寄錦書來」一句,則明寫別後的懸念。接以「雁字回時,月滿西樓」兩句,構成一種目斷神迷的意境。按順序,應是月滿時,上西樓,望雲中,見回雁,而思及誰寄錦書來。「誰」字自然是暗指趙明誠。但是明月自滿,人卻未圓;雁字空回,錦書無有,所以有「誰寄」之嘆。說「誰寄」,又可知是無人寄也。迴文織錦、雁足傳書,詩詞中濫熟故典。易安在這裡無意於用典,不過拈取現成詞藻寫入句中,習用故不覺耳。可以想見,詞人因惦念遊子行蹤,盼望錦書到達,遂從遙望雲空引出雁足傳書的遐想。而這一望斷天涯、神馳象外的情思和遐想,不分白日或月夜,也無論在舟上或樓中,都是縈繞於詞人心頭的。
詞的換頭「花自飄零水自流」一句,承上啟下,詞意不斷。它既是即景,又兼比興。其所展示的花落水流之景,是遙遙與上闋「紅藕香殘」、「獨上蘭舟」兩句相拍合的;而其所象喻的人生、年華、愛情、離別,則給人以「無可奈何花落去」(晏殊〈浣溪沙〉)之感,以及「水流無限似儂愁」(劉禹錫〈竹枝詞九首〉其二)之恨。詞的下闋就從這一句自然過渡到後面的五句,轉為純抒情懷、直吐胸臆的獨白。
「一種相思,兩處閒愁」二句,在寫自己的相思之苦、閒愁之深的同時,由己身推想到對方,深知這種相思與閒愁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方面的,以見兩心之相印。這兩句也是上闋「雲中」句的補充和引申,說明儘管天長水遠,錦書未來,而兩地相思之情初無二致,足證雙方情愛之篤與彼此信任之深。前人作品中也時有寫兩地相思的句子,如羅鄴的〈雁二首〉其二「江南江北多離別,忍報年年兩地愁」,韓偓的〈青春〉詩「櫻桃花謝梨花發,腸斷青春兩處愁」。這兩句詞可能即自這些詩句化出,而一經熔鑄、裁剪為兩個句式整齊、詞意鮮明的四字句,就取得脫胎換骨、點鐵成金的效果。這兩句既是分列的,又是合一的。合起來看,從「一種相思」到「兩處閒愁」,是兩情的分合與深化。其分合,表明此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深化,則訴說此情已由「思」而化為「愁」。下句「此情無計可消除」,緊接這兩句。正因人已分在兩處,心已籠罩深愁,此情就當然難以排遣,而是「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了。
這首詞的結拍三句,是歷來為人所稱道的名句。清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指出,這三句從范仲淹〈御街行〉「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脫胎而來,而明人俞彥〈長相思〉「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一絲」兩句,又是善於盜用李清照的詞句。這說明,詩詞創作雖忌模擬,但可以點化前人語句,使之呈現新貌,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成功的點化總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僅變化原句,而且高過原句。李清照的這一點化,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王士禛也認為范句雖為李句所自出,而李句「特工」。兩相對比,范句比較平實板直,不能收醒人眼目的藝術效果;李句則別出巧思,以「才下眉頭,卻上心頭」這樣兩句來代替「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的平鋪直敘,給人以眼目一新之感。這裡,「眉頭」與「心頭」相對應,「才下」與「卻上」成起伏,語句結構既十分工整,表現手法也十分巧妙,因而就在藝術上有更大的吸引力。當然,句離不開篇,這兩個四字句只是整首詞的一部分,並非一枝獨秀。它有賴於全篇的烘托,特別因與前面另兩個同樣工巧的四字句「一種相思,兩處閒愁」前後襯映,而相得益彰。同時,篇也離不開句,全篇正因這些醒人眼目的句子而振起。明李廷機的《草堂詩餘評林》稱此詞「語意飄逸,令人省目」,讀者之所以特別易於為它所吸引,其原因在此。(陳邦炎)
〈少年遊〉 周邦彥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關於這首詞有一則本事:「道君(宋徽宗)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遊〉云。」(張端義《貴耳集》卷下)其事確有與否一向有人懷疑(如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王國維辨其必無。無論創作緣起如何,文學作品畢竟不同於生活情事的照搬。就這首詞而論,詞中人物便只是一對秋夜相會的情人罷了。詞屬雙調,意分三層,主要從女方著筆。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一層。寫情人雙雙共進時新果品,單刀直入,引讀者進入情境。「刀」為削果用具,「鹽」為進食調料,本是極尋常的生活日用品。而并州產的刀剪特別鋒利(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吳地產的鹽品質特別好(李白〈梁園吟〉:「吳鹽如花皎白雪」),「并刀」、「吳鹽」借用詩語,點出其物之精,便不尋常。而「如水」、「勝雪」的比喻,使人如見刀的閃亮、鹽的晶瑩。二句造型俱美,而對偶天成,表現出鑄辭的精警。緊接一句「纖手破新橙」,則前二句便有著落,絕不虛設。這一句只有一個纖手破橙的特寫畫面,沒有直接寫人或別的情事,但「潛臺詞」十分豐富:誰是主人,誰是客人,誰招待誰等等,讀者已能會心。這對於下片一番慰留情事,已具情節的開端。手是纖纖的玉手,初得之新橙,與如水并刀、勝雪吳鹽,組成一幅色澤美妙的圖畫。「破」字清脆,運用尤佳,與清絕之環境極和諧。三句純是物象,卻能傳達一種愛戀與溫情,味在品果之外。
「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又一層。先交代閨房環境,用了「錦幄」、「獸煙」(獸形香爐中透出的煙)等華豔字面,夾在上下比較淡永清新的詞句中,顯得分外溫馨動人。「初溫」則室不過暖,「不斷」則香時可聞,既不過又無不及,恰寫出環境之宜人。接著寫對坐聽她吹笙。寫吹「笙」卻並無對樂曲的描述,甚至連吹也沒有寫到,只寫到「調笙」而已。此情此境,卻令人大有「未成曲調先有情」(白居易〈琵琶行〉)之感。「相對」二字又包含多少不可言傳的情意。此笙是女方特為愉悅男方而奏,不說自明。此中樂,亦樂在音樂之外。
上片兩層創造了一個溫暖馨香的環境,醞足了依戀無限之情,為下片寫分別難捨作好鋪墊。上片寫到「錦幄初溫」是入夜情事,下片卻寫到「三更」半夜,過片處有一跳躍,中間省略了許多情事。「低聲問」一句直貫篇末。誰問?未明點,讀者從問者聲口不難會意是那位女子。為何問?也未明說,讀者從「向誰行宿」的問話自知是男子的告辭引起。寫來空靈含蓄。挽留的意思全用「問」話出之,更有味。只說夜深(「城上已三更」)、路難(「馬滑霜濃」)、「直是少人行」,只說「不如休去」,卻不直道「休去」,表情措語,分寸掌握極好。「言馬言他人,而纏綿偎依之情自見,若稍涉牽裾,鄙矣。」(清沈謙《填詞雜說》)這幾句不僅妙在畢肖聲口,使讀者如見其人;還同時刻畫出外邊寒風凜冽、夜深霜濃的情境,與室內的環境形成對照。則挽留者的柔情與欲行者的猶豫,都在不言之中。詞結束在「問」上,結束在期待的神情上,意味尤長。恰如毛先舒所說:「後闋絕不作了語,只以『低聲問』三字貫徹到底,蘊藉嫋娜。無限情景,都自纖手破橙人口中說出,更不必別著一語。意思幽微,篇章奇妙,真神品也。」(清王又華《古今詞論》引)
詞中所寫的男女之情,意態纏綿,恰到好處,可謂「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戰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不沾半點惡俗氣味;又能語工意新,「香匳泛話,吐棄殆盡」(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六),的確堪稱「本色佳製」。(周嘯天)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這首詞,據舊題元人伊世珍作的《瑯嬛記》引《外傳》云:「易安結縭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但如王學初在《李清照集校註》中所指出:「清照適趙明誠時,兩家俱在東京,明誠正為太學生,無負笈遠遊事。此則所云,顯非事實。」何況《瑯嬛記》本是偽書,所引《外傳》更不知為何書,是不足為據的。玩味詞意,這首詞絕不是作者與趙明誠分別時所寫,而是作於遠離後。
詞的起句「紅藕香殘玉簟秋」,領起全篇。清詞評家梁紹壬稱此句「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間煙火氣」(《兩般秋雨盦隨筆》),或讚賞其「精秀特絕」(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它的上半句「紅藕香殘」寫戶外之景,下半句「玉簟秋」寫室內之物,對清秋季節起了點染作用,說明這是「已涼天氣未寒時」(韓偓〈已涼〉)。全句設色清麗,意象蘊藉,不僅刻畫出四周景色,而且烘托出詞人情懷。花開花落,既是自然界現象,也是悲歡離合的人事象徵;枕席生涼,既是肌膚間觸覺,也是淒涼獨處的內心感受。這一兼寫戶內外景物而景物中又暗寓情意的起句,一開頭就顯示了這首詞的環境氣氛和它的感情色彩。
上闋共六句,接下來的五句順序寫詞人從晝到夜一天內所作之事、所觸之景、所生之情。前兩句「輕解羅裳,獨上蘭舟」,寫的是白晝在水面泛舟之事。羅裳即羅裙,因裙之尺寸稍長於裙內之褲,解羅裙,以便輕裝登舟。於此亦見詞人在清寂無人處的率性任情。「獨上」二字暗示詞人處境,暗逗離情。下面「雲中誰寄錦書來」一句,則明寫別後的懸念。接以「雁字回時,月滿西樓」兩句,構成一種目斷神迷的意境。按順序,應是月滿時,上西樓,望雲中,見回雁,而思及誰寄錦書來。「誰」字自然是暗指趙明誠。但是明月自滿,人卻未圓;雁字空回,錦書無有,所以有「誰寄」之嘆。說「誰寄」,又可知是無人寄也。迴文織錦、雁足傳書,詩詞中濫熟故典。易安在這裡無意於用典,不過拈取現成詞藻寫入句中,習用故不覺耳。可以想見,詞人因惦念遊子行蹤,盼望錦書到達,遂從遙望雲空引出雁足傳書的遐想。而這一望斷天涯、神馳象外的情思和遐想,不分白日或月夜,也無論在舟上或樓中,都是縈繞於詞人心頭的。
詞的換頭「花自飄零水自流」一句,承上啟下,詞意不斷。它既是即景,又兼比興。其所展示的花落水流之景,是遙遙與上闋「紅藕香殘」、「獨上蘭舟」兩句相拍合的;而其所象喻的人生、年華、愛情、離別,則給人以「無可奈何花落去」(晏殊〈浣溪沙〉)之感,以及「水流無限似儂愁」(劉禹錫〈竹枝詞九首〉其二)之恨。詞的下闋就從這一句自然過渡到後面的五句,轉為純抒情懷、直吐胸臆的獨白。
「一種相思,兩處閒愁」二句,在寫自己的相思之苦、閒愁之深的同時,由己身推想到對方,深知這種相思與閒愁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方面的,以見兩心之相印。這兩句也是上闋「雲中」句的補充和引申,說明儘管天長水遠,錦書未來,而兩地相思之情初無二致,足證雙方情愛之篤與彼此信任之深。前人作品中也時有寫兩地相思的句子,如羅鄴的〈雁二首〉其二「江南江北多離別,忍報年年兩地愁」,韓偓的〈青春〉詩「櫻桃花謝梨花發,腸斷青春兩處愁」。這兩句詞可能即自這些詩句化出,而一經熔鑄、裁剪為兩個句式整齊、詞意鮮明的四字句,就取得脫胎換骨、點鐵成金的效果。這兩句既是分列的,又是合一的。合起來看,從「一種相思」到「兩處閒愁」,是兩情的分合與深化。其分合,表明此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深化,則訴說此情已由「思」而化為「愁」。下句「此情無計可消除」,緊接這兩句。正因人已分在兩處,心已籠罩深愁,此情就當然難以排遣,而是「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了。
這首詞的結拍三句,是歷來為人所稱道的名句。清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指出,這三句從范仲淹〈御街行〉「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脫胎而來,而明人俞彥〈長相思〉「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一絲」兩句,又是善於盜用李清照的詞句。這說明,詩詞創作雖忌模擬,但可以點化前人語句,使之呈現新貌,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成功的點化總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僅變化原句,而且高過原句。李清照的這一點化,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王士禛也認為范句雖為李句所自出,而李句「特工」。兩相對比,范句比較平實板直,不能收醒人眼目的藝術效果;李句則別出巧思,以「才下眉頭,卻上心頭」這樣兩句來代替「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的平鋪直敘,給人以眼目一新之感。這裡,「眉頭」與「心頭」相對應,「才下」與「卻上」成起伏,語句結構既十分工整,表現手法也十分巧妙,因而就在藝術上有更大的吸引力。當然,句離不開篇,這兩個四字句只是整首詞的一部分,並非一枝獨秀。它有賴於全篇的烘托,特別因與前面另兩個同樣工巧的四字句「一種相思,兩處閒愁」前後襯映,而相得益彰。同時,篇也離不開句,全篇正因這些醒人眼目的句子而振起。明李廷機的《草堂詩餘評林》稱此詞「語意飄逸,令人省目」,讀者之所以特別易於為它所吸引,其原因在此。(陳邦炎)
〈少年遊〉 周邦彥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關於這首詞有一則本事:「道君(宋徽宗)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遊〉云。」(張端義《貴耳集》卷下)其事確有與否一向有人懷疑(如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王國維辨其必無。無論創作緣起如何,文學作品畢竟不同於生活情事的照搬。就這首詞而論,詞中人物便只是一對秋夜相會的情人罷了。詞屬雙調,意分三層,主要從女方著筆。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一層。寫情人雙雙共進時新果品,單刀直入,引讀者進入情境。「刀」為削果用具,「鹽」為進食調料,本是極尋常的生活日用品。而并州產的刀剪特別鋒利(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吳地產的鹽品質特別好(李白〈梁園吟〉:「吳鹽如花皎白雪」),「并刀」、「吳鹽」借用詩語,點出其物之精,便不尋常。而「如水」、「勝雪」的比喻,使人如見刀的閃亮、鹽的晶瑩。二句造型俱美,而對偶天成,表現出鑄辭的精警。緊接一句「纖手破新橙」,則前二句便有著落,絕不虛設。這一句只有一個纖手破橙的特寫畫面,沒有直接寫人或別的情事,但「潛臺詞」十分豐富:誰是主人,誰是客人,誰招待誰等等,讀者已能會心。這對於下片一番慰留情事,已具情節的開端。手是纖纖的玉手,初得之新橙,與如水并刀、勝雪吳鹽,組成一幅色澤美妙的圖畫。「破」字清脆,運用尤佳,與清絕之環境極和諧。三句純是物象,卻能傳達一種愛戀與溫情,味在品果之外。
「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又一層。先交代閨房環境,用了「錦幄」、「獸煙」(獸形香爐中透出的煙)等華豔字面,夾在上下比較淡永清新的詞句中,顯得分外溫馨動人。「初溫」則室不過暖,「不斷」則香時可聞,既不過又無不及,恰寫出環境之宜人。接著寫對坐聽她吹笙。寫吹「笙」卻並無對樂曲的描述,甚至連吹也沒有寫到,只寫到「調笙」而已。此情此境,卻令人大有「未成曲調先有情」(白居易〈琵琶行〉)之感。「相對」二字又包含多少不可言傳的情意。此笙是女方特為愉悅男方而奏,不說自明。此中樂,亦樂在音樂之外。
上片兩層創造了一個溫暖馨香的環境,醞足了依戀無限之情,為下片寫分別難捨作好鋪墊。上片寫到「錦幄初溫」是入夜情事,下片卻寫到「三更」半夜,過片處有一跳躍,中間省略了許多情事。「低聲問」一句直貫篇末。誰問?未明點,讀者從問者聲口不難會意是那位女子。為何問?也未明說,讀者從「向誰行宿」的問話自知是男子的告辭引起。寫來空靈含蓄。挽留的意思全用「問」話出之,更有味。只說夜深(「城上已三更」)、路難(「馬滑霜濃」)、「直是少人行」,只說「不如休去」,卻不直道「休去」,表情措語,分寸掌握極好。「言馬言他人,而纏綿偎依之情自見,若稍涉牽裾,鄙矣。」(清沈謙《填詞雜說》)這幾句不僅妙在畢肖聲口,使讀者如見其人;還同時刻畫出外邊寒風凜冽、夜深霜濃的情境,與室內的環境形成對照。則挽留者的柔情與欲行者的猶豫,都在不言之中。詞結束在「問」上,結束在期待的神情上,意味尤長。恰如毛先舒所說:「後闋絕不作了語,只以『低聲問』三字貫徹到底,蘊藉嫋娜。無限情景,都自纖手破橙人口中說出,更不必別著一語。意思幽微,篇章奇妙,真神品也。」(清王又華《古今詞論》引)
詞中所寫的男女之情,意態纏綿,恰到好處,可謂「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戰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不沾半點惡俗氣味;又能語工意新,「香匳泛話,吐棄殆盡」(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六),的確堪稱「本色佳製」。(周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