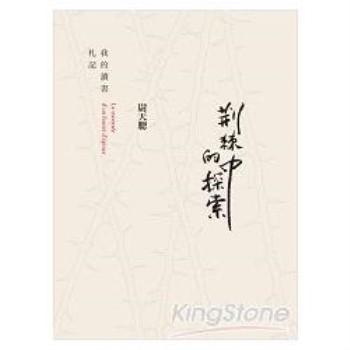在迷惘的年代!
一
歲末整理舊物,無意中重讀了老友鄭秀陶的舊作〈在一九五九的末端〉。一邊讀著,一些往事便又止不住地浮現出來。這篇作品發表在一九六○年四月號我主編的《筆匯》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刊出之後,立即受到軍方政工系統《復興崗》週報政治性的指控。往事雖不如煙,現在再談那些膚淺無聊之事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一想起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那段日子,卻仍然有揮之不去的感觸。那個可以被視為屬於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當年的那群朋友,有的已經離開人世,剩下來的也大都步入人生的晚年。秀陶大學畢業後,求職無著,就去越南一家公司任職,越戰後以難民身分去了美國,一直在一家老人院工作。幾年前曾返台一次。談起往事,也只是相互調侃一陣而已。有人說:時間可以化解一切,其實有一些事雖然看似過眼雲煙,但偶一思念卻總也別有一番情味,一時間難以化解開去。於是再次翻閱秀陶的舊作便又有了一次拋卻不掉的回想。一段回顧,也就成了一段歷史。
秀陶那首詩是這樣的:
在一九五九的末端,塵埃散漫
在歷史如賣麵茶的哨子那樣響著
我插在褲袋裡的手躍躍欲試,我仍插著
到處響著呼吼,無聲地,超頻率地
起自久未運動的生殖器的那樣地
起自一文不名的空口袋的那樣地
在一九五九的末端集聚了三百六十五日的不適
蹺板的這頭低了
於是有生命哭著,哭著自母體內強拉了出來
有生命在街上流著,咬著手指,嚷著proko_ev的音樂
仍然只是感覺,在那裡拼湊著、撥弄著,七巧板樣
或者也抬頭看看天色,看看不像什麼的雲彩
或者也散散步,在無旗的桿下
或者什麼地︙︙
塵埃散漫,該忘的都忘了
餓了就吃
在一九五九的末端
倦了就睡,或者不那麼倦
這些類似艾略特(T. S. 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的愴然和無奈,今天讓比我們年輕三○到四○歲的一代讀起來,或許會不覺得怎樣,但是就我們這一群從那一年代走過來的人說,重讀一次,仍然會引發出某些難以言宣的漠然。前些日子,在與朋友談話時,相互之間想要找一個確切的字句解答我們走過的這一段歲月是怎樣的時代。講來講去,結果仍然是難以為言。多少時候我也私下如此自問,得到的仍然是一片混雜。勉強去說,不過是隨著際遇的不同,一直在不斷地摸索而已。從懂得去觀察、思考自己的世界開始,便一直是那樣捉摸不定;有時是那麼幼稚、天真,聽得中意的便信以為真,興奮激昂,自以為懂得很多道理;有時是一廂情願,執著盲從,偶遇挫敗也會頹喪失意。如此一次又一次,就成了自己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是無法用樂觀或悲觀來形容的,只覺得一次又一次的累積,便讓人在其中感受到某種自發的力量。而每一次的矛盾、衝突,經過掙扎和折磨,也讓人覺得有了又一次新的成長。我曾經說過:在當代的詩人中,我最喜歡方思的作品,他的那首〈給〉,就一直讓我覺得那是我對已往人生的感受:
倘若每一思念,每一渴望,
每一充盈苦難的心跳都是存在,
那麼,多少次短暫而永恆的經驗,
我已活過,
多少次的死亡,多少次的重生。
你是遠赴天邊的西風,
我是那鷹追趕希望,
你是智慧,
我是以有涯逐無涯的凡人,
擲滿懷信仰的一生於真理的等待。
有人問我:「你對生活意義的思考,是不是受到文學的啟發?」我自己覺得並不完全如此,但也不能說沒有關係。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抗戰結束不久,兵荒馬亂,一切沒上軌道,我因為聽人說書,就生吞活剝地讀了《隋唐演義》、《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說岳》、《七俠五義》一類的章回小說,完全是趣味性的滿足,就連夏丏尊翻譯的《愛的教育》,雖然接近現實,也只是在其中感受到校園倫理的溫暖而已;因為那時在我們家鄉小縣城裡,學校還時興罰跪;根本談不上啟發。直到一九四九年,經過一段流亡的生活,到了台灣,在台北的師院附中就讀,初中二年級的導師是史惟亮先生,他教音樂,鼓勵同學唸課外書,每週的導師課,都要同學輪流作讀書報告。輪到我的時候,不曉得什麼機緣,竟然把圖書館的一部舊書《易卜生集》借來,老老實實地把它讀完。那本書是潘家洵翻譯的,書中胡適所寫的〈易卜生主義〉讀了以後,讓我在觀看世間的事物時,有了自己的思緒。
情況是這樣的:
很小以來,由於受到傳統的正規教養,一直對世間的事物,只作正面的思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至於循規蹈矩就成了一條必然追循的道路。但是,在易卜生的作品裡,所見到的卻是家庭間的虛偽、社會上的假仁假義。於是他的《娜拉》、《傀儡家庭》、《社會棟樑》、《國民公敵》都帶給我很大的撞擊。書中附錄中有一段胡適的解說,讓我一直記得,他說: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汙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這些話是在正規教育中聽不到的,於是就很感動,而《國民公敵》中司鐸門醫生力抗社會惡勢力的那段自勉的話:「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往往是最孤立的!」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由此讓我想到人的尊嚴的問題。
後來的思路發展也與史老師有關。史老師住在學校的單身宿舍裡,我們常去跟他聊天。他有一本從大陸帶來的舊書《貝多芬傳》,是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R. Rolland)的作品,從他的談話裡,我們漸漸認識到音樂和藝術的真正價值,而且也知道了羅曼羅蘭,以及他的那部《約翰‧克利斯多夫》。正好圖書館裡存有舊書,於是就輪流借來閱讀。在這之前,好友送我一部美國小說家德萊塞(T. Dreiser)的《天才夢》,是鍾憲民譯的,我懷著夢幻的企望想在這部作品裡尋找著浪漫的天才生活,結果所見到的卻是一片極庸俗的,讓人窒息的現實。讓人一片沮喪。
那時剛從流亡的困苦生活中安定下來,茫然之中,極其需要得到鼓勵。羅曼羅蘭就適時地成為我們的引導。由於得到鼓舞,有些同學就把書中的一些話當作國文課本那樣背誦,直到今天,我還能一句不錯地背得出來,而且作文課時不斷地模擬他的句法,感到自傲。像下面的句子,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我們周圍的空氣多麼沉重。老大的歐羅巴在重濁與腐敗的氣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質主義鎮壓著思想,阻撓著政府與個人的行動。社會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類喘不過氣來。——打開窗子罷!讓自由的空氣重新進來。」「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這些話,當時雖然未能有著實質的了解,聽起來却很有鼓舞的作用,但也只是興奮而已,並沒有開始作深度的思索。直到高中時,因為一位生物老師的啟發,才漸漸學習去推想一些現象後所蘊藏的問題。
有一次老師講達爾文,說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我不知為什麼說出「那多可怕!」老師在下次上課時,就拿了一本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給我看。對我說:「這本書是修正達爾文的,認為互助才是生命的本質。」他知道我讀過巴金的小說,就告訴我:「巴金是李蒂甘的筆名,他信仰無政府主義,景仰兩個人,一個叫巴枯寧,一個叫克魯泡特金。巴金的筆名就是由此而起的。」因為這個機緣,後來我就想盡辦法找到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和《麵包與自由》來看。讀著,讀著,就出現了一種嚮往,覺得自己長大了。——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是真的長大,而是某一種夢的追尋。
但是,受到這種影響,在高中畢業,特別進入大學以後,便開始覺得對人生有了某種企望。其實仍然只是吸取營養的階段而已;由是精神開始有著飢餓的感覺。在制式教育讓人找不到方向和出路之時,我的很多朋友便由此走進了宗教的世界。而我則沒有規律地搜集各種似懂非懂的書刊來讀,以彌補內心的空虛。這些累積,在不知不覺之間也有某種力量孕發出來,促使自己向一個自己不甚了解的世界去追尋、探索。那時上世紀剛要進入六○年代。
二
那時韓戰已經結束,在美國防衛條約的保護下,台灣已經進入一個偏安粗定的時代,但由於連年戰亂和顛簸流離遺留下來的沉壓還沒有完全散去,大多數的人,幾乎都依然活在倦怠和無奈之中。雖然國際上的陰霾和島內現實的窒悶仍會不時地讓人憂心,卻很難再有甚麼事會使人激動起來;往事與舊夢雖然仍然也會帶給人少許猶疑,經過時間的沖洗,卻已漸行漸遠,大都成了過去。接著下去的便是得過且過,使得疲憊和慵懶普遍成為流行。回想起來,便止不住想起當日的幾行詩。這些詩,當時讀了並不覺得怎樣,過後一想,倒覺得非常貼合現實。其中兩句是黃用寫的:
我已安然於被統治下的和平,
因我熟知那種肯定。
另兩句出自唐文標之手:
逐水草而居,牛羊逐水草而居。
且安心地隨眾人逃荒吧!
這就是台灣當時的景況。在連年的騷亂與惶恐之後,不僅從外地逃亡來的人,難以再承受過多的勞累,即連久住本地的居民,生活的形態也一一成了類似逐水草而居的牛羊。每天只能數著日子打發時間,所謂希望,也只具有柴米油鹽等的形而下的意義,只要災難沒有落在自己肩上,就已算是幸福的日子。沒有怨懟,也沒有興奮,一切都處於無用的等待中。但是,人總是要自己肯定的,年輕的族群為了要填補內心的空白,便慣於用由外地舶來的語言宣示自己的存在:「我們是失落的一代!」—— 一副猶然自得的樣子。
這是一個喘息的時代。經濟開始復甦,整個社會漸漸由窒息走向疏解。為了迎接新的現
實,當局便透過各種管道引導大家去讀一本書,這本書的內容現在不必再去講它;僅就書名《風雨中的寧靜》,就可讓人想見它的用意所在,也一語道盡了當時現實的封閉狀態。由於一切仍在風雨之中,這寧靜也不時地會使人感到漠然和懶散,覺得天下的事似乎都跟自己不生關係。這是歷經滄桑後的無助;面對眼前的一切,只能木然地看著,即使有任何意見也不願意表達出來。那時我住在還是鄉下的中和,在這樣的處境中有一些日常所見的印象,至今還留在我的心上,揮之不去。
五十多年前的台北是非常樸素的,經過一段時期的不安,樸素得有些單調,它被包圍在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之間,重慶南路和衡陽路一帶便於焉成了市的中心。從台北火車站走出去,到了廈門街、水源路一帶,感覺上便已到了邊疆。隔著新店溪往中和一望,便覺得那裡就是塞外。那時候,跨越新店溪的中正橋還叫做川端橋,橋面太窄,車輛只能單向通行,於是橋兩端的警衛便不停地揮舞著紅、綠旗,維持著兩岸的交通。
在橋的南端,靠近中和的河灘,有一片地方,那就是人人皆知的馬場町。隔不了幾天,就有一些被稱為「政治犯」的人在天剛亮之前,被押往那裡處決。
那時候,中和還沒有把其中一半劃為永和。從廈門街一過橋,接連著的便是一片開闊的土地。由於人煙稀少,大家都會挨著次序叫出其間的主要地名:頂溪、溪洲、公路村、保健站、枋寮。而枋寮便是鄉公所的所在地,那裡有兩條舊的街道,可以算作這地區的中心。由於當時還沒有自來水,經常可以見到挑水的人在路上走過。這裡每天有七、八班公路局的車子開往台北。為了避免遲到,學生大多趕搭頭兩班車子上學。車子上了橋,就經常看到不遠的河床上排列著一些屍體。有一次竟然有十幾個之多。死的是什麼人,到了傍晚放學回家的時候就知道了。火車站的布告欄大張的告示上已經寫得非常清楚;每一個名字之上都用紅筆畫上粗大的「V」號。面對這樣的告示,起初還讓人心驚,日子一久,便也視為平常,不以為意了。
而再往橋的北端,也就是靠近廈門街、水源路一帶,有一片與河堤相接的河床地,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被搭建成幾排相聯的茶棚,起先是外省人約會、尋找親友、打探消息、尋找工作的所在,後來便成為公眾活動的場所。泡上一大杯茶就可以待上一天。幾乎每一個座位上展示出來的都是茫然、無助的臉色。日子久了,就有一些小販穿梭著,販賣小吃。也有人在黃昏以後,在那裡講說相聲,其中的吳兆南與魏龍豪直到晚近大家還記得他們的風采。在早些年,有人在報上發表文章,把當時這一帶的地方比喻為東晉初渡時的「新亭」,幾年過去,這裡卻已成為小市民廉價的娛樂場所了。如此不久,一個可以名之為安閒的時代,也就隨之推展開來。
那時人們的一切幾乎都是與外界隔絕的。我們隨著被交代下來的語言把敵對的一方名為「鐵幕」,事實上我們也或多或少地沉淪於類似的四顧茫(盲)然之中。而且在國際的熱戰冷戰交互作用下,因著政治需求而與外來的資訊切割開來。那不僅只是與現實的隔絕,同時也是與歷史的隔絕。其情況借用前輩詩人馮至的話來說,那真是:「像整個的生命都嵌在/一個框子裡,在框子外/沒有人生,也沒有世界。」在這樣處境下,一些在夾縫中難得的舶來的文化訊息便成為讓人激動的事物,傳播開來被生吞活剝地成為思想運作的媒介。
接著下去,隨著美國在各方面的介入,和留學政策的開放,一些國際間的文化消息,便零零碎碎地開啟了台灣原來封閉的門戶,而緩和局面下的短期寧靜,也使得文藝界的活動跟著鬆動起來。各家報紙開始競相刊登著武俠小說;李費蒙(牛哥)《賭國仇城》一類的作品也接續在市面上出現,瓊瑤也漸漸成為人們注意的人物。雖然如此,卻仍然讓人在紛擾中覺得欠缺些甚麼。世事混亂,瞬息萬變,而我們只能霧裡看花,不但不知何去何從,而且對自己的認識也是一片模糊。瓊瑤一本小說叫做《煙雨濛濛》,我們正是在濛濛中去認識四邊的一切。當時流行一首叫〈花非花〉的藝術歌曲,詞意來自白居易的作品,唱起來非常合乎當時的心情: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雖然唱起來頗為陶醉,但過後不久,也就有了無限的惆悵。在這樣的惆悵中,有些人便經常背誦著陳子昂〈感遇詩〉那一類的作品來填補內心的昂奮:
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
亭上誰家子,哀哀明月樓。
自言幽燕客,結髮事遠遊。
赤丸殺公吏,白刃解私仇。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
故鄉三千里,遼水復悠悠。
每憤胡兵入,常為漢國羞。
何如七十戰,白首未封侯。
那時,在經過一九四九年前後的一連串的大離亂之後,前一時期那種被稱為「革命」的浪潮已經消褪,在餘波的盪漾中,那種傳承自歷史教育對於現實的關心,卻仍然像潛伏在土壤中的種籽那樣,蠢蠢欲動。那時候,包括我們一些朋友在內的、剛要或已經從學院中走出來的一群,雖然處在大動亂的餘燼之中,感到四顧茫然,卻也因為如此,生命中總也有著某些蓄勢待發的衝動,像化學課本上所說的「初生態的氧」那樣,東衝西撞地想要在重重禁忌中探索出一條自己走下去的道路。與其說那是每個人自己心中的未來,不如說那就是潛伏在他們心中的夢,和捉摸不定的理想。那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對於一個更高、更醇靜的世界的追尋;就像他們青少年時代陶醉在初戀的純真裡那樣,不知天高地厚,心甘情願,生死以之地要把整個生命的一切交託出去。於是讀著任何充滿理想色彩的文字,唱著前代人傳承下來的歌曲,竟不知其所以然地熱血沸騰起來。在這樣的胸懷下,一些不安於現狀的人在避開政治的討論之外,便想著要去突破當前的困境,申述自己的願望,於是,一些不起眼的小刊物如《現代詩》、《筆匯》、《文學雜誌》、《現代文學》、《劇場》、《文學季刊》等,經由各自的努力,便在當時被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土地上,掙扎著冒出頭來。而與此同時,便也有一些新興的藝術團體(如「五月畫會」、「東方畫會」、「現代版畫會」等)一個又一個地,帶有草莽的性格,嘗試著去探尋自己的道路。這樣的刊物和團體,雖然受制於當時國際上熱戰、冷戰的現實,很多時候免不了要以美國流行的文化景象作為學習的階梯,而且也難以避免地感染著大戰後所滋生的茫然和無奈,把它們借用過來發抒自己的苦悶。例如,在我們所辦的《筆匯》第一期上,便經由介紹美國小說家湯瑪斯‧吳爾芙(Thomas Wolfel,1900 -1938)的時候,透過他作品中的語言,宣示了自己的處境和心願:
我們失落了,我們是赤裸的。我們是孤獨的。無邊無際而殘酷無比的天空籠罩著我們。我們永遠被逐來趕去,我們沒有家。每個人都是這樣孤獨與恐怖,如何能找到快樂與真實呢?這裡有個「門」,這個門開向真理,揭示世界的祕密。找到這個「門」,就可以走向溫暖與安全的「家」,不復有苦痛、恐怖與孤寂了。
三
就這樣,美國方面所傳來的一些訊息便也對我們產生了不少的影響。
在一九四九年的大變局下,美國曾發表一份對中國的白皮書,聲明國共兩黨都無法獲得他們的同情,面對中國,他要支持國共兩黨之外的中國人。於是當時就有「第三勢力」的形勢出現,很多海外的華人都去了香港,形成香港的文化熱潮。這熱潮中除了一些政治人物,還有中國自發的知識分子(如錢穆、唐君毅等人,和逃到香港的難民如李輝英、趙滋蕃等),在作著文化的反省,而最多的一批是美國駐香港的新聞處支持的那一群,像林以亮(宋淇)、吳魯芹等人。由於美國新聞處負有對亞洲華人的文化宣傳的重任,所以他們辦了一些出版社和報刊,如祖國週刊、友聯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大學生活雜誌、學生週刊,甚至還有陳伯莊等人的學術季刊,和馬朗等人介紹現代主義的《文藝新潮》。
這些對台灣也產生很大的影響,開啟了一個美國式的西化時代。青年中開始流行著「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潮,就是如此產生的。以至於名哲學家方東美先生感慨著:「台灣沒有獨立的大學,只有留美補習班。」
那時座落在台北市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與香港的美國新聞處幾乎就是一家人。他們很少談政治,但在文化上卻也產生很大的作用。它們出版的《美國文學批評選集》、《美國散文選集》、《美國哲學選集》、《美國詩選》和大批美國當代的小說翻譯,都是水準以上的作品。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也是受美國新聞處授意先用英文寫出再譯成中文出版的。
而在文學方面還經由林以亮、夏志清、夏濟安那些人,把美國新批評派的理論介紹了過來,讓人能夠從政治的控制中超越出來。在哲學上,經陳伯莊、殷海光等人的介紹,也使得邏輯實證論、行為科學一類的思想方式進入學術界。不管人們如何評論當時美國的對華政策,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那便是藉著這一機緣讓港台二地興起了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風潮。
為甚麼那時會有這樣的爭論呢?
不要忘了,近代的中國政黨,不管是執政的還是在野的,其所採用的治理方式都是集權主義的。再加上民國以來的「槍桿子出政權」的傳統,便使得社會的一切措施一直都是在黨治的漩渦裡打轉,特別是在一九四九以後,由於國共兩方彼此所存的戒心,這種集權主義更加隨之膨脹起來,成為極權主義。相對於此,那個時候很多不甘於這情況的刊物,便都以「自由」、「民主」命名:《自由人》、《自由世紀》、《自由中國》、《民主評論》,便是為人所知的幾個。
那時,極大多數的人是不敢涉及現實政治的,但是卻會努力經由不同的管道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和願望,以期突破舊有的、因襲的枷鎖,擴大對事物的真實認識。
舉例來說:
像在《美國文學批評選》中,有一篇張愛玲翻譯的《海明威論》,其中有一段文字就讓人對於人類的歷史中所謂的「神聖」有了新的反省。這段文字是這樣的:
「神聖」、「光榮」、「犧牲」、「白白犧牲」,這些字眼永遠使我窘迫。這些辭句使我們久已聽慣見慣,有時候站在雨中,站得太遠幾乎聽不見,只有大聲喊出的幾個字可以聽到;也曾經聽到這些,在告白上——張貼佈告的人隨手黏貼在別的告白上的告白——而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任何神聖的東西,而光榮的事物也並不光榮。而犧牲也像芝加哥的屠場,假若屠場僅只把肉埋葬起來,不作他用。許許多多字眼都是不堪入耳,結果只有地名是莊嚴的。……具體的村莊的名字、道路的號碼、河流的名字、部隊的番號、日期。抽象的字句如同「光榮」、「毅力」,或者「神聖」,相形之下都是穢褻的。
這種對於原有的「權威」的否定,雖然一時之間讓人覺得帶有虛無主義的惘然,但對於長久習於「因襲」、「服從」、「遵循」的國民惰性和麻木來說,也是一種啟發。道理很簡單,雖然近代的一些革命者常以「群眾眼睛是雪亮的」漂亮話來激動群眾,事實上在現實中卻仍然「換湯不換藥」地執行各式各樣的「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那樣的一言堂。使人一步一步地走向愚昧,便於他們的統治。就因為如此,多元性的思考也就必然會為人帶來一次新的覺醒。所以,上世紀六○年代的西化風潮,即使是翻譯作品,也會多層次地增強人們的思考維度。譬如劉大任、邱剛健翻譯貝克特的(S. Beckott)的《等待果陀》,經由《劇場》雜誌主持的公演,便讓很多人產生相濡以沫的同情和回應。為什麼會如此呢?那時候,世界一片窒息,誰也不知道明天會是甚麼樣子。在窘困之中,大家就只好莫名其妙地活在等待中。在對這種情況不知何以解說時,就稱之為「每天活在不知等待著什麼的等待中」,盼望某種奇蹟出現。由於這樣的心情,一位不熟悉的貝克特就一時成了自己的朋友。那是一個迷茫的時代,面對世事的乖張與無常,一時便很難找到甚麼確切的道理可以解答心中的疑難,於是便很自然地感受到存在的荒謬性。由是便也與西方近代的一些思想與作品有了很大的會通,像我
們前面引用的海明威的那段話,不久就被瘂弦融進了他的那首〈深淵〉裡。
去看,去假裝發愁,去聞時間的腐味
我們再也懶於知道,我們是誰。
工作,散步,向壞人致敬,微笑和不朽。
他們是握緊格言的人!
這是日子的顏面;所有的瘡口呻吟,裙子下藏著病菌。
都會,天秤,紙的月亮,電桿木的言語,
(今天的告示貼在昨天的告示上)
冷血的太陽不時發著顫
在兩個夜夾著的
蒼白的深淵之間。
而就像這種情況一樣,很多人便經由各種舶來的管道,在卡夫卡(Kafka)、喬依思(J.
Joyce)、湯瑪斯曼(Thomas Mann)、里爾克(Rilke)、卡繆(A.Camus)、沙特(J. P.Sartre)那些人的作品裡取火,得到了新的慰藉。經由這種影響所產生的作品,與很多三十年代前輩的作品相比起來,無論在語言的運用上,還是心靈感受的程度上都有者很大的差異。最明顯的一點,便是經由個人的感受和反省(而不是依照別人給予的認識),真誠地去思考真正的人性,由是而增強認識事物的能力。記得劉大任有一篇小說〈刀之祭〉,寫一個剛下部隊的低級軍官,第一次奉命去處決犯人;而呈現出來的這場血的洗禮,不僅是對被處決者的懲罰,更是對執刑者徹骨的煎熬。而就在這一段日子裡,真正身為憲兵的商禽,也在一首名為〈鴿子〉的詩裡,申述了類似的告白。他由鴿子的自由飛翔,想到自己的手已經不屬於自己;別人命令你殺人,即使不願意,你也只好去殺。如此便警覺到有一天自己也會面臨這樣被殺的命運。我現在仍然記得當年他唸這首詩時所流露的無可奈何:「……工作過仍要工作,殺戮過終也要被殺戮的,無辜的手啊,現在,我將你們高舉,我是多麼想——如同放掉一對傷癒的鳥雀一樣——將你們從我雙臂釋放啊!」這種在極權治理下所產生的人格分裂的悲哀,比起前人所說的「長恨此身非我有」,不是更具有了深一層的意義嗎?正是因為如此,在那一階段出現的一些作家,便努力著跨越前輩那樣固定的意識形態和僵化的寫實主義,而各自不同地經由作品,不受官方的約束,真實地展現自己獨自的心靈;並由這種內在世界的探尋,來反省自己的處境。這是一群新創作群(如陳映真、叢甦、白先勇、七等生、黃春明、王禎和、瘂弦、劉國松、莊詰、蕭勤、夏陽等人)開始出現的時代。像陳映真早期在〈我的弟弟康雄〉中嘶喊著「我求魚得蛇,我求食得石」的絕望、叢甦在〈盲獵〉中所呈現的在追尋中的茫然,以及一切前衛畫家所展現的風格,大都是與前輩作家有所不同的。大致說來,有人認為上世紀六○—七○年代台港二地的文學藝術的特質就是現代主義的出現,其情況就是如此的。這不能不說是在禁錮中的一股精神上的突破和解放。
一
歲末整理舊物,無意中重讀了老友鄭秀陶的舊作〈在一九五九的末端〉。一邊讀著,一些往事便又止不住地浮現出來。這篇作品發表在一九六○年四月號我主編的《筆匯》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刊出之後,立即受到軍方政工系統《復興崗》週報政治性的指控。往事雖不如煙,現在再談那些膚淺無聊之事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一想起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那段日子,卻仍然有揮之不去的感觸。那個可以被視為屬於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當年的那群朋友,有的已經離開人世,剩下來的也大都步入人生的晚年。秀陶大學畢業後,求職無著,就去越南一家公司任職,越戰後以難民身分去了美國,一直在一家老人院工作。幾年前曾返台一次。談起往事,也只是相互調侃一陣而已。有人說:時間可以化解一切,其實有一些事雖然看似過眼雲煙,但偶一思念卻總也別有一番情味,一時間難以化解開去。於是再次翻閱秀陶的舊作便又有了一次拋卻不掉的回想。一段回顧,也就成了一段歷史。
秀陶那首詩是這樣的:
在一九五九的末端,塵埃散漫
在歷史如賣麵茶的哨子那樣響著
我插在褲袋裡的手躍躍欲試,我仍插著
到處響著呼吼,無聲地,超頻率地
起自久未運動的生殖器的那樣地
起自一文不名的空口袋的那樣地
在一九五九的末端集聚了三百六十五日的不適
蹺板的這頭低了
於是有生命哭著,哭著自母體內強拉了出來
有生命在街上流著,咬著手指,嚷著proko_ev的音樂
仍然只是感覺,在那裡拼湊著、撥弄著,七巧板樣
或者也抬頭看看天色,看看不像什麼的雲彩
或者也散散步,在無旗的桿下
或者什麼地︙︙
塵埃散漫,該忘的都忘了
餓了就吃
在一九五九的末端
倦了就睡,或者不那麼倦
這些類似艾略特(T. S. 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的愴然和無奈,今天讓比我們年輕三○到四○歲的一代讀起來,或許會不覺得怎樣,但是就我們這一群從那一年代走過來的人說,重讀一次,仍然會引發出某些難以言宣的漠然。前些日子,在與朋友談話時,相互之間想要找一個確切的字句解答我們走過的這一段歲月是怎樣的時代。講來講去,結果仍然是難以為言。多少時候我也私下如此自問,得到的仍然是一片混雜。勉強去說,不過是隨著際遇的不同,一直在不斷地摸索而已。從懂得去觀察、思考自己的世界開始,便一直是那樣捉摸不定;有時是那麼幼稚、天真,聽得中意的便信以為真,興奮激昂,自以為懂得很多道理;有時是一廂情願,執著盲從,偶遇挫敗也會頹喪失意。如此一次又一次,就成了自己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是無法用樂觀或悲觀來形容的,只覺得一次又一次的累積,便讓人在其中感受到某種自發的力量。而每一次的矛盾、衝突,經過掙扎和折磨,也讓人覺得有了又一次新的成長。我曾經說過:在當代的詩人中,我最喜歡方思的作品,他的那首〈給〉,就一直讓我覺得那是我對已往人生的感受:
倘若每一思念,每一渴望,
每一充盈苦難的心跳都是存在,
那麼,多少次短暫而永恆的經驗,
我已活過,
多少次的死亡,多少次的重生。
你是遠赴天邊的西風,
我是那鷹追趕希望,
你是智慧,
我是以有涯逐無涯的凡人,
擲滿懷信仰的一生於真理的等待。
有人問我:「你對生活意義的思考,是不是受到文學的啟發?」我自己覺得並不完全如此,但也不能說沒有關係。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抗戰結束不久,兵荒馬亂,一切沒上軌道,我因為聽人說書,就生吞活剝地讀了《隋唐演義》、《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說岳》、《七俠五義》一類的章回小說,完全是趣味性的滿足,就連夏丏尊翻譯的《愛的教育》,雖然接近現實,也只是在其中感受到校園倫理的溫暖而已;因為那時在我們家鄉小縣城裡,學校還時興罰跪;根本談不上啟發。直到一九四九年,經過一段流亡的生活,到了台灣,在台北的師院附中就讀,初中二年級的導師是史惟亮先生,他教音樂,鼓勵同學唸課外書,每週的導師課,都要同學輪流作讀書報告。輪到我的時候,不曉得什麼機緣,竟然把圖書館的一部舊書《易卜生集》借來,老老實實地把它讀完。那本書是潘家洵翻譯的,書中胡適所寫的〈易卜生主義〉讀了以後,讓我在觀看世間的事物時,有了自己的思緒。
情況是這樣的:
很小以來,由於受到傳統的正規教養,一直對世間的事物,只作正面的思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至於循規蹈矩就成了一條必然追循的道路。但是,在易卜生的作品裡,所見到的卻是家庭間的虛偽、社會上的假仁假義。於是他的《娜拉》、《傀儡家庭》、《社會棟樑》、《國民公敵》都帶給我很大的撞擊。書中附錄中有一段胡適的解說,讓我一直記得,他說: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汙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這些話是在正規教育中聽不到的,於是就很感動,而《國民公敵》中司鐸門醫生力抗社會惡勢力的那段自勉的話:「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往往是最孤立的!」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由此讓我想到人的尊嚴的問題。
後來的思路發展也與史老師有關。史老師住在學校的單身宿舍裡,我們常去跟他聊天。他有一本從大陸帶來的舊書《貝多芬傳》,是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R. Rolland)的作品,從他的談話裡,我們漸漸認識到音樂和藝術的真正價值,而且也知道了羅曼羅蘭,以及他的那部《約翰‧克利斯多夫》。正好圖書館裡存有舊書,於是就輪流借來閱讀。在這之前,好友送我一部美國小說家德萊塞(T. Dreiser)的《天才夢》,是鍾憲民譯的,我懷著夢幻的企望想在這部作品裡尋找著浪漫的天才生活,結果所見到的卻是一片極庸俗的,讓人窒息的現實。讓人一片沮喪。
那時剛從流亡的困苦生活中安定下來,茫然之中,極其需要得到鼓勵。羅曼羅蘭就適時地成為我們的引導。由於得到鼓舞,有些同學就把書中的一些話當作國文課本那樣背誦,直到今天,我還能一句不錯地背得出來,而且作文課時不斷地模擬他的句法,感到自傲。像下面的句子,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我們周圍的空氣多麼沉重。老大的歐羅巴在重濁與腐敗的氣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質主義鎮壓著思想,阻撓著政府與個人的行動。社會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類喘不過氣來。——打開窗子罷!讓自由的空氣重新進來。」「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這些話,當時雖然未能有著實質的了解,聽起來却很有鼓舞的作用,但也只是興奮而已,並沒有開始作深度的思索。直到高中時,因為一位生物老師的啟發,才漸漸學習去推想一些現象後所蘊藏的問題。
有一次老師講達爾文,說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我不知為什麼說出「那多可怕!」老師在下次上課時,就拿了一本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給我看。對我說:「這本書是修正達爾文的,認為互助才是生命的本質。」他知道我讀過巴金的小說,就告訴我:「巴金是李蒂甘的筆名,他信仰無政府主義,景仰兩個人,一個叫巴枯寧,一個叫克魯泡特金。巴金的筆名就是由此而起的。」因為這個機緣,後來我就想盡辦法找到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和《麵包與自由》來看。讀著,讀著,就出現了一種嚮往,覺得自己長大了。——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是真的長大,而是某一種夢的追尋。
但是,受到這種影響,在高中畢業,特別進入大學以後,便開始覺得對人生有了某種企望。其實仍然只是吸取營養的階段而已;由是精神開始有著飢餓的感覺。在制式教育讓人找不到方向和出路之時,我的很多朋友便由此走進了宗教的世界。而我則沒有規律地搜集各種似懂非懂的書刊來讀,以彌補內心的空虛。這些累積,在不知不覺之間也有某種力量孕發出來,促使自己向一個自己不甚了解的世界去追尋、探索。那時上世紀剛要進入六○年代。
二
那時韓戰已經結束,在美國防衛條約的保護下,台灣已經進入一個偏安粗定的時代,但由於連年戰亂和顛簸流離遺留下來的沉壓還沒有完全散去,大多數的人,幾乎都依然活在倦怠和無奈之中。雖然國際上的陰霾和島內現實的窒悶仍會不時地讓人憂心,卻很難再有甚麼事會使人激動起來;往事與舊夢雖然仍然也會帶給人少許猶疑,經過時間的沖洗,卻已漸行漸遠,大都成了過去。接著下去的便是得過且過,使得疲憊和慵懶普遍成為流行。回想起來,便止不住想起當日的幾行詩。這些詩,當時讀了並不覺得怎樣,過後一想,倒覺得非常貼合現實。其中兩句是黃用寫的:
我已安然於被統治下的和平,
因我熟知那種肯定。
另兩句出自唐文標之手:
逐水草而居,牛羊逐水草而居。
且安心地隨眾人逃荒吧!
這就是台灣當時的景況。在連年的騷亂與惶恐之後,不僅從外地逃亡來的人,難以再承受過多的勞累,即連久住本地的居民,生活的形態也一一成了類似逐水草而居的牛羊。每天只能數著日子打發時間,所謂希望,也只具有柴米油鹽等的形而下的意義,只要災難沒有落在自己肩上,就已算是幸福的日子。沒有怨懟,也沒有興奮,一切都處於無用的等待中。但是,人總是要自己肯定的,年輕的族群為了要填補內心的空白,便慣於用由外地舶來的語言宣示自己的存在:「我們是失落的一代!」—— 一副猶然自得的樣子。
這是一個喘息的時代。經濟開始復甦,整個社會漸漸由窒息走向疏解。為了迎接新的現
實,當局便透過各種管道引導大家去讀一本書,這本書的內容現在不必再去講它;僅就書名《風雨中的寧靜》,就可讓人想見它的用意所在,也一語道盡了當時現實的封閉狀態。由於一切仍在風雨之中,這寧靜也不時地會使人感到漠然和懶散,覺得天下的事似乎都跟自己不生關係。這是歷經滄桑後的無助;面對眼前的一切,只能木然地看著,即使有任何意見也不願意表達出來。那時我住在還是鄉下的中和,在這樣的處境中有一些日常所見的印象,至今還留在我的心上,揮之不去。
五十多年前的台北是非常樸素的,經過一段時期的不安,樸素得有些單調,它被包圍在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之間,重慶南路和衡陽路一帶便於焉成了市的中心。從台北火車站走出去,到了廈門街、水源路一帶,感覺上便已到了邊疆。隔著新店溪往中和一望,便覺得那裡就是塞外。那時候,跨越新店溪的中正橋還叫做川端橋,橋面太窄,車輛只能單向通行,於是橋兩端的警衛便不停地揮舞著紅、綠旗,維持著兩岸的交通。
在橋的南端,靠近中和的河灘,有一片地方,那就是人人皆知的馬場町。隔不了幾天,就有一些被稱為「政治犯」的人在天剛亮之前,被押往那裡處決。
那時候,中和還沒有把其中一半劃為永和。從廈門街一過橋,接連著的便是一片開闊的土地。由於人煙稀少,大家都會挨著次序叫出其間的主要地名:頂溪、溪洲、公路村、保健站、枋寮。而枋寮便是鄉公所的所在地,那裡有兩條舊的街道,可以算作這地區的中心。由於當時還沒有自來水,經常可以見到挑水的人在路上走過。這裡每天有七、八班公路局的車子開往台北。為了避免遲到,學生大多趕搭頭兩班車子上學。車子上了橋,就經常看到不遠的河床上排列著一些屍體。有一次竟然有十幾個之多。死的是什麼人,到了傍晚放學回家的時候就知道了。火車站的布告欄大張的告示上已經寫得非常清楚;每一個名字之上都用紅筆畫上粗大的「V」號。面對這樣的告示,起初還讓人心驚,日子一久,便也視為平常,不以為意了。
而再往橋的北端,也就是靠近廈門街、水源路一帶,有一片與河堤相接的河床地,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被搭建成幾排相聯的茶棚,起先是外省人約會、尋找親友、打探消息、尋找工作的所在,後來便成為公眾活動的場所。泡上一大杯茶就可以待上一天。幾乎每一個座位上展示出來的都是茫然、無助的臉色。日子久了,就有一些小販穿梭著,販賣小吃。也有人在黃昏以後,在那裡講說相聲,其中的吳兆南與魏龍豪直到晚近大家還記得他們的風采。在早些年,有人在報上發表文章,把當時這一帶的地方比喻為東晉初渡時的「新亭」,幾年過去,這裡卻已成為小市民廉價的娛樂場所了。如此不久,一個可以名之為安閒的時代,也就隨之推展開來。
那時人們的一切幾乎都是與外界隔絕的。我們隨著被交代下來的語言把敵對的一方名為「鐵幕」,事實上我們也或多或少地沉淪於類似的四顧茫(盲)然之中。而且在國際的熱戰冷戰交互作用下,因著政治需求而與外來的資訊切割開來。那不僅只是與現實的隔絕,同時也是與歷史的隔絕。其情況借用前輩詩人馮至的話來說,那真是:「像整個的生命都嵌在/一個框子裡,在框子外/沒有人生,也沒有世界。」在這樣處境下,一些在夾縫中難得的舶來的文化訊息便成為讓人激動的事物,傳播開來被生吞活剝地成為思想運作的媒介。
接著下去,隨著美國在各方面的介入,和留學政策的開放,一些國際間的文化消息,便零零碎碎地開啟了台灣原來封閉的門戶,而緩和局面下的短期寧靜,也使得文藝界的活動跟著鬆動起來。各家報紙開始競相刊登著武俠小說;李費蒙(牛哥)《賭國仇城》一類的作品也接續在市面上出現,瓊瑤也漸漸成為人們注意的人物。雖然如此,卻仍然讓人在紛擾中覺得欠缺些甚麼。世事混亂,瞬息萬變,而我們只能霧裡看花,不但不知何去何從,而且對自己的認識也是一片模糊。瓊瑤一本小說叫做《煙雨濛濛》,我們正是在濛濛中去認識四邊的一切。當時流行一首叫〈花非花〉的藝術歌曲,詞意來自白居易的作品,唱起來非常合乎當時的心情: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雖然唱起來頗為陶醉,但過後不久,也就有了無限的惆悵。在這樣的惆悵中,有些人便經常背誦著陳子昂〈感遇詩〉那一類的作品來填補內心的昂奮:
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
亭上誰家子,哀哀明月樓。
自言幽燕客,結髮事遠遊。
赤丸殺公吏,白刃解私仇。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
故鄉三千里,遼水復悠悠。
每憤胡兵入,常為漢國羞。
何如七十戰,白首未封侯。
那時,在經過一九四九年前後的一連串的大離亂之後,前一時期那種被稱為「革命」的浪潮已經消褪,在餘波的盪漾中,那種傳承自歷史教育對於現實的關心,卻仍然像潛伏在土壤中的種籽那樣,蠢蠢欲動。那時候,包括我們一些朋友在內的、剛要或已經從學院中走出來的一群,雖然處在大動亂的餘燼之中,感到四顧茫然,卻也因為如此,生命中總也有著某些蓄勢待發的衝動,像化學課本上所說的「初生態的氧」那樣,東衝西撞地想要在重重禁忌中探索出一條自己走下去的道路。與其說那是每個人自己心中的未來,不如說那就是潛伏在他們心中的夢,和捉摸不定的理想。那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對於一個更高、更醇靜的世界的追尋;就像他們青少年時代陶醉在初戀的純真裡那樣,不知天高地厚,心甘情願,生死以之地要把整個生命的一切交託出去。於是讀著任何充滿理想色彩的文字,唱著前代人傳承下來的歌曲,竟不知其所以然地熱血沸騰起來。在這樣的胸懷下,一些不安於現狀的人在避開政治的討論之外,便想著要去突破當前的困境,申述自己的願望,於是,一些不起眼的小刊物如《現代詩》、《筆匯》、《文學雜誌》、《現代文學》、《劇場》、《文學季刊》等,經由各自的努力,便在當時被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土地上,掙扎著冒出頭來。而與此同時,便也有一些新興的藝術團體(如「五月畫會」、「東方畫會」、「現代版畫會」等)一個又一個地,帶有草莽的性格,嘗試著去探尋自己的道路。這樣的刊物和團體,雖然受制於當時國際上熱戰、冷戰的現實,很多時候免不了要以美國流行的文化景象作為學習的階梯,而且也難以避免地感染著大戰後所滋生的茫然和無奈,把它們借用過來發抒自己的苦悶。例如,在我們所辦的《筆匯》第一期上,便經由介紹美國小說家湯瑪斯‧吳爾芙(Thomas Wolfel,1900 -1938)的時候,透過他作品中的語言,宣示了自己的處境和心願:
我們失落了,我們是赤裸的。我們是孤獨的。無邊無際而殘酷無比的天空籠罩著我們。我們永遠被逐來趕去,我們沒有家。每個人都是這樣孤獨與恐怖,如何能找到快樂與真實呢?這裡有個「門」,這個門開向真理,揭示世界的祕密。找到這個「門」,就可以走向溫暖與安全的「家」,不復有苦痛、恐怖與孤寂了。
三
就這樣,美國方面所傳來的一些訊息便也對我們產生了不少的影響。
在一九四九年的大變局下,美國曾發表一份對中國的白皮書,聲明國共兩黨都無法獲得他們的同情,面對中國,他要支持國共兩黨之外的中國人。於是當時就有「第三勢力」的形勢出現,很多海外的華人都去了香港,形成香港的文化熱潮。這熱潮中除了一些政治人物,還有中國自發的知識分子(如錢穆、唐君毅等人,和逃到香港的難民如李輝英、趙滋蕃等),在作著文化的反省,而最多的一批是美國駐香港的新聞處支持的那一群,像林以亮(宋淇)、吳魯芹等人。由於美國新聞處負有對亞洲華人的文化宣傳的重任,所以他們辦了一些出版社和報刊,如祖國週刊、友聯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大學生活雜誌、學生週刊,甚至還有陳伯莊等人的學術季刊,和馬朗等人介紹現代主義的《文藝新潮》。
這些對台灣也產生很大的影響,開啟了一個美國式的西化時代。青年中開始流行著「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潮,就是如此產生的。以至於名哲學家方東美先生感慨著:「台灣沒有獨立的大學,只有留美補習班。」
那時座落在台北市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與香港的美國新聞處幾乎就是一家人。他們很少談政治,但在文化上卻也產生很大的作用。它們出版的《美國文學批評選集》、《美國散文選集》、《美國哲學選集》、《美國詩選》和大批美國當代的小說翻譯,都是水準以上的作品。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也是受美國新聞處授意先用英文寫出再譯成中文出版的。
而在文學方面還經由林以亮、夏志清、夏濟安那些人,把美國新批評派的理論介紹了過來,讓人能夠從政治的控制中超越出來。在哲學上,經陳伯莊、殷海光等人的介紹,也使得邏輯實證論、行為科學一類的思想方式進入學術界。不管人們如何評論當時美國的對華政策,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那便是藉著這一機緣讓港台二地興起了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風潮。
為甚麼那時會有這樣的爭論呢?
不要忘了,近代的中國政黨,不管是執政的還是在野的,其所採用的治理方式都是集權主義的。再加上民國以來的「槍桿子出政權」的傳統,便使得社會的一切措施一直都是在黨治的漩渦裡打轉,特別是在一九四九以後,由於國共兩方彼此所存的戒心,這種集權主義更加隨之膨脹起來,成為極權主義。相對於此,那個時候很多不甘於這情況的刊物,便都以「自由」、「民主」命名:《自由人》、《自由世紀》、《自由中國》、《民主評論》,便是為人所知的幾個。
那時,極大多數的人是不敢涉及現實政治的,但是卻會努力經由不同的管道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和願望,以期突破舊有的、因襲的枷鎖,擴大對事物的真實認識。
舉例來說:
像在《美國文學批評選》中,有一篇張愛玲翻譯的《海明威論》,其中有一段文字就讓人對於人類的歷史中所謂的「神聖」有了新的反省。這段文字是這樣的:
「神聖」、「光榮」、「犧牲」、「白白犧牲」,這些字眼永遠使我窘迫。這些辭句使我們久已聽慣見慣,有時候站在雨中,站得太遠幾乎聽不見,只有大聲喊出的幾個字可以聽到;也曾經聽到這些,在告白上——張貼佈告的人隨手黏貼在別的告白上的告白——而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任何神聖的東西,而光榮的事物也並不光榮。而犧牲也像芝加哥的屠場,假若屠場僅只把肉埋葬起來,不作他用。許許多多字眼都是不堪入耳,結果只有地名是莊嚴的。……具體的村莊的名字、道路的號碼、河流的名字、部隊的番號、日期。抽象的字句如同「光榮」、「毅力」,或者「神聖」,相形之下都是穢褻的。
這種對於原有的「權威」的否定,雖然一時之間讓人覺得帶有虛無主義的惘然,但對於長久習於「因襲」、「服從」、「遵循」的國民惰性和麻木來說,也是一種啟發。道理很簡單,雖然近代的一些革命者常以「群眾眼睛是雪亮的」漂亮話來激動群眾,事實上在現實中卻仍然「換湯不換藥」地執行各式各樣的「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那樣的一言堂。使人一步一步地走向愚昧,便於他們的統治。就因為如此,多元性的思考也就必然會為人帶來一次新的覺醒。所以,上世紀六○年代的西化風潮,即使是翻譯作品,也會多層次地增強人們的思考維度。譬如劉大任、邱剛健翻譯貝克特的(S. Beckott)的《等待果陀》,經由《劇場》雜誌主持的公演,便讓很多人產生相濡以沫的同情和回應。為什麼會如此呢?那時候,世界一片窒息,誰也不知道明天會是甚麼樣子。在窘困之中,大家就只好莫名其妙地活在等待中。在對這種情況不知何以解說時,就稱之為「每天活在不知等待著什麼的等待中」,盼望某種奇蹟出現。由於這樣的心情,一位不熟悉的貝克特就一時成了自己的朋友。那是一個迷茫的時代,面對世事的乖張與無常,一時便很難找到甚麼確切的道理可以解答心中的疑難,於是便很自然地感受到存在的荒謬性。由是便也與西方近代的一些思想與作品有了很大的會通,像我
們前面引用的海明威的那段話,不久就被瘂弦融進了他的那首〈深淵〉裡。
去看,去假裝發愁,去聞時間的腐味
我們再也懶於知道,我們是誰。
工作,散步,向壞人致敬,微笑和不朽。
他們是握緊格言的人!
這是日子的顏面;所有的瘡口呻吟,裙子下藏著病菌。
都會,天秤,紙的月亮,電桿木的言語,
(今天的告示貼在昨天的告示上)
冷血的太陽不時發著顫
在兩個夜夾著的
蒼白的深淵之間。
而就像這種情況一樣,很多人便經由各種舶來的管道,在卡夫卡(Kafka)、喬依思(J.
Joyce)、湯瑪斯曼(Thomas Mann)、里爾克(Rilke)、卡繆(A.Camus)、沙特(J. P.Sartre)那些人的作品裡取火,得到了新的慰藉。經由這種影響所產生的作品,與很多三十年代前輩的作品相比起來,無論在語言的運用上,還是心靈感受的程度上都有者很大的差異。最明顯的一點,便是經由個人的感受和反省(而不是依照別人給予的認識),真誠地去思考真正的人性,由是而增強認識事物的能力。記得劉大任有一篇小說〈刀之祭〉,寫一個剛下部隊的低級軍官,第一次奉命去處決犯人;而呈現出來的這場血的洗禮,不僅是對被處決者的懲罰,更是對執刑者徹骨的煎熬。而就在這一段日子裡,真正身為憲兵的商禽,也在一首名為〈鴿子〉的詩裡,申述了類似的告白。他由鴿子的自由飛翔,想到自己的手已經不屬於自己;別人命令你殺人,即使不願意,你也只好去殺。如此便警覺到有一天自己也會面臨這樣被殺的命運。我現在仍然記得當年他唸這首詩時所流露的無可奈何:「……工作過仍要工作,殺戮過終也要被殺戮的,無辜的手啊,現在,我將你們高舉,我是多麼想——如同放掉一對傷癒的鳥雀一樣——將你們從我雙臂釋放啊!」這種在極權治理下所產生的人格分裂的悲哀,比起前人所說的「長恨此身非我有」,不是更具有了深一層的意義嗎?正是因為如此,在那一階段出現的一些作家,便努力著跨越前輩那樣固定的意識形態和僵化的寫實主義,而各自不同地經由作品,不受官方的約束,真實地展現自己獨自的心靈;並由這種內在世界的探尋,來反省自己的處境。這是一群新創作群(如陳映真、叢甦、白先勇、七等生、黃春明、王禎和、瘂弦、劉國松、莊詰、蕭勤、夏陽等人)開始出現的時代。像陳映真早期在〈我的弟弟康雄〉中嘶喊著「我求魚得蛇,我求食得石」的絕望、叢甦在〈盲獵〉中所呈現的在追尋中的茫然,以及一切前衛畫家所展現的風格,大都是與前輩作家有所不同的。大致說來,有人認為上世紀六○—七○年代台港二地的文學藝術的特質就是現代主義的出現,其情況就是如此的。這不能不說是在禁錮中的一股精神上的突破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