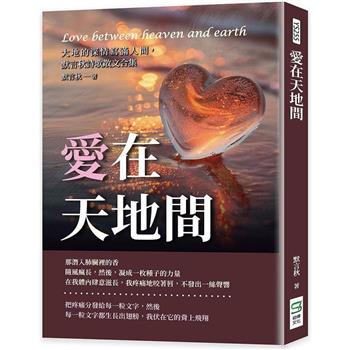人間有味是清歡
初夏,小滿剛過,接連兩天陰雨。雨後空氣清新,晚上一個人在家,決定下樓去走走。
小區草坪上,兩個稚童在奔跑嬉戲。我駐足觀看,因互不相識,且喚他們大童、小童吧。大童在玩一種類似「飛碟」的玩具,路燈下我看不真切。只見他手一拉一揚,飛出一物,然後落地,小童歡呼雀躍,撿拾落地的「飛碟」。
「姐姐,你來玩嗎?」小童跳著跑到我跟前。
背後是路燈,我逆光而站,小童看不清我的容貌,自然看不出我的年齡,一聲姐姐,打破所有隔膜,彷彿是童年夥伴的呼喚。
「好啊!」我欣然答應,抬腳加入他們。
「你幾歲了?」我問小童。
「我三歲!」
哦,三歲,多麼小啊!
「你呢?」我問大童。
「我上三年級了!九歲!」
哦,九歲的童年!
「讓我試試吧!」我伸出雙手,大童慷慨地將玩具遞給我。我這才看清楚,玩具很簡單,一根約20公分長、形狀似螺絲的塑膠棒,一個類似螺絲帽的彈力器,一隻「飛碟」。
「你教我吧!」
大童爽快答應,邊說邊示範:先用左手握住塑膠棒的底端,然後套上螺絲帽樣的彈力器,再插上飛碟。舉起來,右手用力將彈力器向上拉,飛碟就飛出去了!
我照著樣子嘗試,第一次飛碟畫出一個弧形,落在近處的草坪。大童一邊撿起,一邊強調:拉出去的時候要快!越快飛得越高!
好!我再試試。
左手握住塑膠棒底端,右手捏住彈力器,雙臂抬起,心裡默唸:「快!用力!拉!」「嗖!」果然,飛碟彈出一道直線射向天空,夜幕中,竟然不見了蹤影……我們抬頭傻等,片刻後,小童「咯咯咯」地笑著:「在這裡,在這裡!」原來飛碟像長了眼睛,居然落在了小童的腳邊。他將飛碟舉過頭頂,像一個凱旋的英勇小戰士飛奔而來!
哈!飛碟在和我們捉迷藏呢!
我感激地把玩具還給大童,揮手告別,他倆依然在昏黃的燈光下玩耍嬉戲。
原以為快樂是他們的,此刻,回頭看著他們奔跑的身影,內心竟是滿滿的喜悅和幸福呢!
謝謝寶貝,在這個夜晚,將一份童真和快樂傳給我。
前行,過道兩邊是小區的老人在晚練,統一節拍,擊掌拍腿。其實每天晚上這個時間,我在樓上都可以聽到清脆的擊掌節奏,卻不喧鬧。老人的那份沉澱即使在運動中也傳遞著安寧。
也許是受了小童的感染,我加入他們的行列,站在一位奶奶身邊,互相微笑點頭算是問候。鍛鍊已接近尾聲,我跟著節奏,雙臂伸展,抬頭閉眼,舒展的身體像此刻舒展的心。
天上沒有星星,心頭竟有繁星閃爍……安詳如老人,安詳如我心。
告別老人,繼續前行。路燈下,一位少年在練習跳繩,父親在旁邊幫助數數:「55、56、57、58、59……」一盞路燈,一對父子,與我無關,我卻留戀地回望,內心無限歡喜幸福。
人間有味是清歡,如今天這個夜晚。此心安處是吾鄉,城市裡的家園,是菩提,是一顆柔軟心。
換一種姿態見到更美的風景
做一個眺望者,是我一貫的姿態。而今天在一片寧靜裡,我更願做一個仰望者。
因為眺望的誘惑,我必須揮灑汗水,盯著腳尖,心無旁騖地奮力登高。只有登高者曉得「一覽眾山小」是眼睛所見,「高處不勝寒」是心靈寫照。
九月,我踏進這片陌生的天地。隆冬又將至,我會不會像候鳥一樣遷徙?我想改變一種飛翔的姿勢,也許能看到更美的風景。
每天早上騎車帶兒子去上學,迎著東方,仰望一輪紅日在遠遠的地平線上徐徐升起,蒼宇如此遼闊,此刻和天地如此親近。有時,還會欣賞到飛機劃過的痕跡,白白的,長長的,懸在天際,如飄逸的絲帶。天空為背景,紅日為襯托,我和兒子都會仰起脖子,讚嘆這片絢麗。「媽媽,你看!真美!」兒子的話千真萬確。仰望天空,會欣賞到另一種別樣的景緻。
上下班的路上,閃爍的霓虹,寬闊的道路,我必經的那片明淨的湖。偶爾聽得飛鳥輕鳴,每次我都會用目光去追尋,希望能看到飛鳥的身影。有時鳥兒也會停在枝頭,梳一梳羽毛,朝我歪頭瞅瞅。我叫不出鳥的名字,卻感覺到無比親切。只要看到鳥兒的雀躍,心裡便會湧出莫名的喜悅。以一種平等的姿態去感受,內心便多了一份祥和快樂。
天鵝湖岸,是我和愛人帶孩子一起散步的地方。一直夢想擁有一片海,而今天這片澄澈的湖讓我安靜下來。春和景明,波光瀲灩,水面攢動著無數的光,如剪碎的金片,密密匝匝地灑在水面上,輕柔的風吹過,盈盈翩舞。
滿天星斗的夜晚,湖邊更靜了,偶見三三兩兩的行人。放眼四周,燈光多於星斗,極目更遠處,燈光和星光輝映。牽著愛人溫暖的手,看著兒子蹦跳引路的身影,停下來,指向燈火更深處,告訴愛人和兒子,遠望是憧憬,眼前是觸手可及的幸福。
換一種姿態,擁有真實與幸福。紀伯倫說:
天堂就在那
在那扇門後
在隔壁的房裡
但是我把鑰匙丟了
也許我只是把它放錯了地方
天堂其實就在手邊,就在你抬眼之處。願芸芸眾生,能活在屬於自己的人間天堂,熟悉的地方見到更美的風景。
誰念西風獨自涼
捧讀〈納蘭詞〉,被他的詞情縈繞,越發相信,納蘭的詞心與生俱來。上蒼悲憫,讓一顆早逝凡塵的星子,用另一種方式永存人世。
「家家爭唱〈飲水詞〉,納蘭心事幾人知?」他生在鐘鳴鼎食之家,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為何納蘭容若的詞裡,流淌的卻是排遣不去的惆悵與憂傷?在光陰的河流上,他淡漠春花,獨賞秋涼;他相忘繁華,貪戀清雅;他摒棄權貴,靜享禪緣硯香。
摘一粒星子掛在柳梢,憑欄,眺望人間蒼茫。
佇立在光陰的岸頭,溯流打撈三百多年前的一段青梅舊事。
情感路,傷心途。
他與青梅表妹十年的情愫心照不宣,彼此深知,隻字未提。「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鬟心隻鳳翹。待將低喚,直為凝情恐人見。欲訴幽懷,轉過回闌叩玉釵。」所有心緒,他寄於詞中,誰解?字字成曲,吟於窗外飛絮聽。
他與青梅表妹的相逢應在七歲那一年。她被一輛馬車帶到納蘭府,人生只是如初見,相見一眼兩無猜。在懵懂天真的無憂光陰裡,在受人仰慕的納蘭府,兩人相伴長大。一個是纖塵不染,梨花帶雨,一個是俊朗優雅,清逸絕俗。人間的煙火飄縈不出童話,有情人無法踰越現實的鴻溝。父親納蘭明珠,位高權重的肱股之臣,母親覺羅氏,親王之女,他們怎會答應有著尊貴身分、受人仰視的納蘭府的長子迎娶一朵卑微的青梅?一個自小父母雙亡的可憐女,怎麼會端坐在牡丹爭豔的富貴門?
無法掙脫宿命的手,表妹被納蘭容若的父母送進了宮。十年清夢,還沒來得及開啟,就被掩上重重的門,冰封在永遠無法躍出的河底。
納蘭的傷,從此始,世間能夠醫治他的藥,唯有詞。
清秋冷月,追昔前塵,心事交於誰?那段刻入骨卻未開啟的愛,如三月被東風吹落的一樹潔白的梨花,片片殘章;如六月被夜雨打溼的一池聖潔的清荷,朵朵淒涼。再纏綿繽紛的枝頭,怎奈花期不慈悲,聲聲催逼,散入流水,隨波去……溫暖而殘忍,絕美而又痛徹心腑。挑燈展卷,涼涼清輝筆墨中。
「彤雲久絕飛瓊字,人在誰邊?人在誰邊?今夜玉清眠不眠?香銷被冷殘燈滅,靜數秋天。靜數秋天,又誤心期到下弦。」
「撥燈書盡紅箋也,依舊無聊。玉漏迢迢,夢裡寒花隔玉簫。幾竿修竹三更雨,葉葉蕭蕭。分付秋潮,莫誤雙魚到謝橋。」
兩首〈採桑子〉,相思遙寄月明中。一段未曾開啟的情,隨西風逝雲外,傷痕藏心頭,憑詞哀悼,冷月之下,幾點黃花滿地秋。
從此,納蘭容若心湖的某個潔淨溫暖處,長著一顆叫青梅的硃砂痣。
人不知生在權貴之家的他為何憂傷,他是詞人,有屬於自己的天宇,他可以端坐在自己的雲間,俯視蒼生。然而,行走在凡塵,掙扎不出被人間煙火灼傷的痛,徹悟,又何如?
後來康熙賜婚,納蘭娶了兩廣總督盧興祖之女為妻──一個安靜嫻雅、柔情似水、痴心戀他的女子。上蒼待納蘭不薄,他亦無法抗拒眼前這個清雅、溫柔、嬌媚的妻。然她亦知,他的心底永駐一個如梨花的女子。「軟風吹遍窗紗,心期便隔天涯。從此傷春傷別,黃昏只對梨花。」
痴情而善解人意的盧氏,依然用純粹高潔的愛溫暖著納蘭。納蘭也收藏起表妹,要好好善待眼前純美的妻。然世事難料,千帆過盡,流水依然潺潺去。三年相愛相牽的手,卻抵不過宿命之手的輕輕一招,盧氏在產下她和納蘭的嬰孩後,靜靜死在這個她願意把生命相交的愛人的懷裡,臉上是無悔無憂安靜的微笑。至死,她只把溫暖與微笑留給他。
納蘭,上蒼用右手給了他歡喜,左手又給了他更深的傷痕。她用溫暖為他縫補好的心,又被寒冰劃開。「淚咽卻無聲,只向從前悔薄情。憑仗丹青重省識,盈盈,一片傷心畫不成。」他想給她更多更深的愛,她應該擁有的愛。
然飛鶴去,夕陽沉,殘霜一地葉飄零。青衫溼遍,喚不回。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他本該縱馬放歌在天涯,帶著「身向榆關那畔行」的蕭蕭豪邁和男兒的凌雲壯志。然歲月的風塵沾上他的衣襟,蘸沉香,成詞闋。
「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納蘭攜詞,行走在他的憂傷裡。捧讀〈納蘭詞〉,我必信上蒼賦予納蘭與生俱來的詞心,也必信生命賜予納蘭纏繞繁華與淒涼的歷程,讓他的詞心、詞情在凡塵裡站立成一朵絕美而永不凋零的仙葩。
初夏,小滿剛過,接連兩天陰雨。雨後空氣清新,晚上一個人在家,決定下樓去走走。
小區草坪上,兩個稚童在奔跑嬉戲。我駐足觀看,因互不相識,且喚他們大童、小童吧。大童在玩一種類似「飛碟」的玩具,路燈下我看不真切。只見他手一拉一揚,飛出一物,然後落地,小童歡呼雀躍,撿拾落地的「飛碟」。
「姐姐,你來玩嗎?」小童跳著跑到我跟前。
背後是路燈,我逆光而站,小童看不清我的容貌,自然看不出我的年齡,一聲姐姐,打破所有隔膜,彷彿是童年夥伴的呼喚。
「好啊!」我欣然答應,抬腳加入他們。
「你幾歲了?」我問小童。
「我三歲!」
哦,三歲,多麼小啊!
「你呢?」我問大童。
「我上三年級了!九歲!」
哦,九歲的童年!
「讓我試試吧!」我伸出雙手,大童慷慨地將玩具遞給我。我這才看清楚,玩具很簡單,一根約20公分長、形狀似螺絲的塑膠棒,一個類似螺絲帽的彈力器,一隻「飛碟」。
「你教我吧!」
大童爽快答應,邊說邊示範:先用左手握住塑膠棒的底端,然後套上螺絲帽樣的彈力器,再插上飛碟。舉起來,右手用力將彈力器向上拉,飛碟就飛出去了!
我照著樣子嘗試,第一次飛碟畫出一個弧形,落在近處的草坪。大童一邊撿起,一邊強調:拉出去的時候要快!越快飛得越高!
好!我再試試。
左手握住塑膠棒底端,右手捏住彈力器,雙臂抬起,心裡默唸:「快!用力!拉!」「嗖!」果然,飛碟彈出一道直線射向天空,夜幕中,竟然不見了蹤影……我們抬頭傻等,片刻後,小童「咯咯咯」地笑著:「在這裡,在這裡!」原來飛碟像長了眼睛,居然落在了小童的腳邊。他將飛碟舉過頭頂,像一個凱旋的英勇小戰士飛奔而來!
哈!飛碟在和我們捉迷藏呢!
我感激地把玩具還給大童,揮手告別,他倆依然在昏黃的燈光下玩耍嬉戲。
原以為快樂是他們的,此刻,回頭看著他們奔跑的身影,內心竟是滿滿的喜悅和幸福呢!
謝謝寶貝,在這個夜晚,將一份童真和快樂傳給我。
前行,過道兩邊是小區的老人在晚練,統一節拍,擊掌拍腿。其實每天晚上這個時間,我在樓上都可以聽到清脆的擊掌節奏,卻不喧鬧。老人的那份沉澱即使在運動中也傳遞著安寧。
也許是受了小童的感染,我加入他們的行列,站在一位奶奶身邊,互相微笑點頭算是問候。鍛鍊已接近尾聲,我跟著節奏,雙臂伸展,抬頭閉眼,舒展的身體像此刻舒展的心。
天上沒有星星,心頭竟有繁星閃爍……安詳如老人,安詳如我心。
告別老人,繼續前行。路燈下,一位少年在練習跳繩,父親在旁邊幫助數數:「55、56、57、58、59……」一盞路燈,一對父子,與我無關,我卻留戀地回望,內心無限歡喜幸福。
人間有味是清歡,如今天這個夜晚。此心安處是吾鄉,城市裡的家園,是菩提,是一顆柔軟心。
換一種姿態見到更美的風景
做一個眺望者,是我一貫的姿態。而今天在一片寧靜裡,我更願做一個仰望者。
因為眺望的誘惑,我必須揮灑汗水,盯著腳尖,心無旁騖地奮力登高。只有登高者曉得「一覽眾山小」是眼睛所見,「高處不勝寒」是心靈寫照。
九月,我踏進這片陌生的天地。隆冬又將至,我會不會像候鳥一樣遷徙?我想改變一種飛翔的姿勢,也許能看到更美的風景。
每天早上騎車帶兒子去上學,迎著東方,仰望一輪紅日在遠遠的地平線上徐徐升起,蒼宇如此遼闊,此刻和天地如此親近。有時,還會欣賞到飛機劃過的痕跡,白白的,長長的,懸在天際,如飄逸的絲帶。天空為背景,紅日為襯托,我和兒子都會仰起脖子,讚嘆這片絢麗。「媽媽,你看!真美!」兒子的話千真萬確。仰望天空,會欣賞到另一種別樣的景緻。
上下班的路上,閃爍的霓虹,寬闊的道路,我必經的那片明淨的湖。偶爾聽得飛鳥輕鳴,每次我都會用目光去追尋,希望能看到飛鳥的身影。有時鳥兒也會停在枝頭,梳一梳羽毛,朝我歪頭瞅瞅。我叫不出鳥的名字,卻感覺到無比親切。只要看到鳥兒的雀躍,心裡便會湧出莫名的喜悅。以一種平等的姿態去感受,內心便多了一份祥和快樂。
天鵝湖岸,是我和愛人帶孩子一起散步的地方。一直夢想擁有一片海,而今天這片澄澈的湖讓我安靜下來。春和景明,波光瀲灩,水面攢動著無數的光,如剪碎的金片,密密匝匝地灑在水面上,輕柔的風吹過,盈盈翩舞。
滿天星斗的夜晚,湖邊更靜了,偶見三三兩兩的行人。放眼四周,燈光多於星斗,極目更遠處,燈光和星光輝映。牽著愛人溫暖的手,看著兒子蹦跳引路的身影,停下來,指向燈火更深處,告訴愛人和兒子,遠望是憧憬,眼前是觸手可及的幸福。
換一種姿態,擁有真實與幸福。紀伯倫說:
天堂就在那
在那扇門後
在隔壁的房裡
但是我把鑰匙丟了
也許我只是把它放錯了地方
天堂其實就在手邊,就在你抬眼之處。願芸芸眾生,能活在屬於自己的人間天堂,熟悉的地方見到更美的風景。
誰念西風獨自涼
捧讀〈納蘭詞〉,被他的詞情縈繞,越發相信,納蘭的詞心與生俱來。上蒼悲憫,讓一顆早逝凡塵的星子,用另一種方式永存人世。
「家家爭唱〈飲水詞〉,納蘭心事幾人知?」他生在鐘鳴鼎食之家,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為何納蘭容若的詞裡,流淌的卻是排遣不去的惆悵與憂傷?在光陰的河流上,他淡漠春花,獨賞秋涼;他相忘繁華,貪戀清雅;他摒棄權貴,靜享禪緣硯香。
摘一粒星子掛在柳梢,憑欄,眺望人間蒼茫。
佇立在光陰的岸頭,溯流打撈三百多年前的一段青梅舊事。
情感路,傷心途。
他與青梅表妹十年的情愫心照不宣,彼此深知,隻字未提。「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鬟心隻鳳翹。待將低喚,直為凝情恐人見。欲訴幽懷,轉過回闌叩玉釵。」所有心緒,他寄於詞中,誰解?字字成曲,吟於窗外飛絮聽。
他與青梅表妹的相逢應在七歲那一年。她被一輛馬車帶到納蘭府,人生只是如初見,相見一眼兩無猜。在懵懂天真的無憂光陰裡,在受人仰慕的納蘭府,兩人相伴長大。一個是纖塵不染,梨花帶雨,一個是俊朗優雅,清逸絕俗。人間的煙火飄縈不出童話,有情人無法踰越現實的鴻溝。父親納蘭明珠,位高權重的肱股之臣,母親覺羅氏,親王之女,他們怎會答應有著尊貴身分、受人仰視的納蘭府的長子迎娶一朵卑微的青梅?一個自小父母雙亡的可憐女,怎麼會端坐在牡丹爭豔的富貴門?
無法掙脫宿命的手,表妹被納蘭容若的父母送進了宮。十年清夢,還沒來得及開啟,就被掩上重重的門,冰封在永遠無法躍出的河底。
納蘭的傷,從此始,世間能夠醫治他的藥,唯有詞。
清秋冷月,追昔前塵,心事交於誰?那段刻入骨卻未開啟的愛,如三月被東風吹落的一樹潔白的梨花,片片殘章;如六月被夜雨打溼的一池聖潔的清荷,朵朵淒涼。再纏綿繽紛的枝頭,怎奈花期不慈悲,聲聲催逼,散入流水,隨波去……溫暖而殘忍,絕美而又痛徹心腑。挑燈展卷,涼涼清輝筆墨中。
「彤雲久絕飛瓊字,人在誰邊?人在誰邊?今夜玉清眠不眠?香銷被冷殘燈滅,靜數秋天。靜數秋天,又誤心期到下弦。」
「撥燈書盡紅箋也,依舊無聊。玉漏迢迢,夢裡寒花隔玉簫。幾竿修竹三更雨,葉葉蕭蕭。分付秋潮,莫誤雙魚到謝橋。」
兩首〈採桑子〉,相思遙寄月明中。一段未曾開啟的情,隨西風逝雲外,傷痕藏心頭,憑詞哀悼,冷月之下,幾點黃花滿地秋。
從此,納蘭容若心湖的某個潔淨溫暖處,長著一顆叫青梅的硃砂痣。
人不知生在權貴之家的他為何憂傷,他是詞人,有屬於自己的天宇,他可以端坐在自己的雲間,俯視蒼生。然而,行走在凡塵,掙扎不出被人間煙火灼傷的痛,徹悟,又何如?
後來康熙賜婚,納蘭娶了兩廣總督盧興祖之女為妻──一個安靜嫻雅、柔情似水、痴心戀他的女子。上蒼待納蘭不薄,他亦無法抗拒眼前這個清雅、溫柔、嬌媚的妻。然她亦知,他的心底永駐一個如梨花的女子。「軟風吹遍窗紗,心期便隔天涯。從此傷春傷別,黃昏只對梨花。」
痴情而善解人意的盧氏,依然用純粹高潔的愛溫暖著納蘭。納蘭也收藏起表妹,要好好善待眼前純美的妻。然世事難料,千帆過盡,流水依然潺潺去。三年相愛相牽的手,卻抵不過宿命之手的輕輕一招,盧氏在產下她和納蘭的嬰孩後,靜靜死在這個她願意把生命相交的愛人的懷裡,臉上是無悔無憂安靜的微笑。至死,她只把溫暖與微笑留給他。
納蘭,上蒼用右手給了他歡喜,左手又給了他更深的傷痕。她用溫暖為他縫補好的心,又被寒冰劃開。「淚咽卻無聲,只向從前悔薄情。憑仗丹青重省識,盈盈,一片傷心畫不成。」他想給她更多更深的愛,她應該擁有的愛。
然飛鶴去,夕陽沉,殘霜一地葉飄零。青衫溼遍,喚不回。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他本該縱馬放歌在天涯,帶著「身向榆關那畔行」的蕭蕭豪邁和男兒的凌雲壯志。然歲月的風塵沾上他的衣襟,蘸沉香,成詞闋。
「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納蘭攜詞,行走在他的憂傷裡。捧讀〈納蘭詞〉,我必信上蒼賦予納蘭與生俱來的詞心,也必信生命賜予納蘭纏繞繁華與淒涼的歷程,讓他的詞心、詞情在凡塵裡站立成一朵絕美而永不凋零的仙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