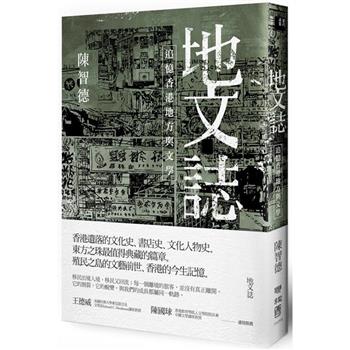白光熄滅九龍城
燈光與碎片
啟德機場跑道燈光徹夜明亮,像堅固的星座,為夜間升降的飛機提示路徑。我們以為星座總比我們持久,但這晚看來那麼虛弱。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凌晨降臨,跑道燈光倏然熄滅,市民不禁叫喚,短暫漆黑後,燈光突然再亮起,市民雀躍起哄,但它只閃爍了幾下,然後真正熄滅,結束比我們年長的光,歷史裡的離合、笑靨淚痕,奔向了冷卻宇宙。
再沒有飛機掠過九龍城的低空,再沒有頻繁的震耳巨響,我們反而不習慣,但知早晚會戀上這新的寧靜。因鄰近機場的建屋高度限制,大半世紀以來,整片九龍城社區維持低矮樓房外觀,在這晚,我們也預見它早晚撤換作新的高樓。
承認新舊輪替是必然,我們不敢否定新事,卻總忐忑於「發展」二字;只有九龍城一面淡然,看慣變幻。但九龍城也在我們不察覺的時候回首前塵,追憶城寨渡頭往返的清廷官吏、城寨門前腳戴枷鎖的罪犯、宋皇臺前痛惜文化失落的前清遺民、被日軍夷為平地的啟德濱。
時流洗淨鉛華,九龍城只暗自追懷,不肯在人前話舊,我們都理解,它藏著半島最幽隱的歷史記號,歷劫時代遺下依稀可辨的痕跡:宋皇臺、九龍城寨、啟德濱、啟德機場,面目全非,但未完全逝去。至若我輩在飛機巨響下的唐樓中的蹦跳嬉鬧、烙印腦際的笑靨淚影,待得雙燕歸來,也未必願意記起。
直至我們翻開紙頁,滿眼不滅跡印,盡是前人的文字。
目前所見,最具古風的九龍城風景,莫如侶倫筆下的記述。一九三○年與友人組織島上社,創辦文學雜誌《島上》的侶倫,二○年代末居於九龍城,位於近海的啟德濱外圍,他為居所命名「向水屋」,並邀得徐悲鴻題字,書橫幅掛於壁上。侶倫於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散文集《無名草》,有一篇文章〈故居〉,為戰前九龍城留下世外桃園式的記錄:
我的住居是一列新建樓房的一間四層樓上,沿住屋外有一個寬廣的,鋪了花磚子的迴廊式的陽臺,……可以看見由高聳的獅子山下面伸展過來的一塊巨幅的風景畫:一簇簇蒼翠的樹木和一片灰色的屋頂─是一世紀來不輕易變動的古風的殘留。隱蔽在灰色之中的,是村落,工場,醬園,尼庵,廟宇,園地和人家。一個小丘橫在那裡,小丘的中部,像腰帶似地鑲著古舊卻還完整的九龍城的城牆。
這是目前為止我所讀到的,戰前從啟德濱外圍望向九龍城寨風景地貌的最完整紀錄。這優美散文同時是記錄九龍城地貌的重要文獻,《無名草》一九五三年曾再版一次,早已絕版,之後未有再版,讀到的人恐怕不多,侶倫後來在寫於一九七七年的文章〈向水屋追懷〉中,引用了部分〈故居〉的內容,但不及原文詳細。
侶倫文中所指的「新建樓房」,是指建於一九二○年代的啟德濱住宅。一九一○年代,由何啟與區德等多人創辦的啟德營業有限公司,主持填海建屋計畫,新建成的社區稱為啟德濱。啟德公司的填海計畫,未竟全工就倒閉,政府接收後在填海區興建機場,命名為「啟德」。二戰期間,日軍攻占香港後,為擴建機場拆去九龍城寨城牆,宋皇臺、啟德濱社區亦被夷平。
侶倫在《向水屋筆語》一書,多處談及九龍城,其中〈故人之思〉記錄了葉靈鳳一九二九年偕郭林鳳在香港短暫居住的日子,侶倫安排他們租住在九龍城:
那是座落「宋皇臺」旁邊一間房子的第二層樓。從那「走馬騎樓」向外望,正面是鯉魚門,右面是香港,左面是一條向前伸展的海堤;景色很美。尤其是晚上,海上的漁船燈火在澄明的水面溜來溜去,下面傳來潮水拍岸的有節奏的聲音。在海闊天空之中,人彷彿置身超然物外境界。
因為「向水屋」之名以及葉靈鳳短住九龍城,一時傳遍香港文壇,《伴侶》雜誌編輯張稚廬送給侶倫一首舊詩寫道:「半島爭看一俊才,宋皇臺下寫沉哀。不知十里衙前道,幾見翩翩靈鳳來。」前兩句寫侶倫,後兩句寫葉靈鳳。寫侶倫時提及宋皇臺,只就其居處位置而言,侶倫是早期香港新文學拓荒者之一,創辦新文學社團和刊物,宋皇臺與侶倫其人其文無多大關係,它另有迥異於新文藝取向的象徵意義。
宋皇臺本九龍城以南海濱山坡上一塊大石,南宋末年,宋帝昰與宋帝昺被元朝軍隊追逼,在文天祥、陸秀夫等人護送下逃至九龍城一帶,短暫停駐再繼續逃亡。後人紀念其事,於相傳宋帝曾登臨之大石刻「宋王臺」三字,旁邊另有「清嘉慶丁卯重修」七字,為保護古蹟,香港政府於一八九九年通過「保存宋王臺勝蹟條例」,其後修茸鄰近地方,闢為公園。日治時期,大石被炸,裂為數塊,刻字部分竟奇蹟倖存,戰後港府擴建啟德機場,於大石原址興建機場客運大樓,石刻部分切割成長方形,移送機場附近空地,闢作「宋皇臺公園」。
二十世紀初,辛亥革命後,前清文人避居香港,有感山河變易,香港「雖信美而非吾土」,文人將家國與身世之悲寄託於宋皇臺,藉雅集相互唱酬。一九一七年,蘇澤東輯錄前清探花陳伯陶等人所著宋皇臺詩詞,編為《宋臺秋唱》。宋皇臺向為香港最著名古蹟,文人懷古之餘,亦追溯九龍古事,如陳伯陶〈宋皇臺懷古並序〉:
九龍,古官富場地,明初置巡司,嘉慶間,總督百齡築砦,改名九龍。道光間復改官富巡司為九龍巡司,而官富場之名遂隱。
前清文人追懷失去的時光,以歷史抗衡殖民地的無根,不意間為香港敘述了遺民角度的歷史。宋皇臺也不只是前清文人吟詠對象,抗日戰爭期間,南來香港避亂的文人,也有許多藉宋皇臺抒發時局憂患,如陳居霖〈雨訪宋皇臺偕雪瑛三首錄二〉其一云:「抱得春愁海樣深,江山如晦忍重臨。崖門極目蒼波冷,空憶當年帝璽沉。」正將時代憂患與個人飄零之悲合而為一。二十世紀初,香港仍有許多與宋皇臺相關的古蹟,如二王殿村、侯王廟、國母梳妝石等,同為前清文人避港必訪之地。二王殿位於二王殿村內,即《新安縣志》中的二黃店村,位於今日的馬頭圍區,陳伯陶〈宋行宮遺瓦歌並序〉記云:「官富場宋皇臺之東有村名二王殿,景炎行宮舊基也,新安縣志稱土人因其址建北帝廟即此,今廟後石礎猶存。其地耕人往往得古瓦,色赭黝,堅如石,雖稍麤朴,然頗經久。」序後有詩,抒其獲得古殿遺瓦的感慨:「凄涼故國哭杜鵑,零落舊巢悲海燕。手揩此瓦重摩挲,惆悵遺基淚如霰。」
宋皇臺、二王殿村與古殿遺瓦為前清遺民共同吟詠之對象,吳道鎔亦有詩云:
寒林擁日到虞淵,戎馬艱難瘴海邊。七百年來陵谷變,二王村尚鳥啼煙(二王村)。敷天左袒語非虛,直到窮邊有帝居。破碎河山瓦全少,千秋一片重璠璵(宋行宮瓦)。
吳道鎔與陳伯陶、張學華等合稱「嶺南九老」,皆前清遺民,辛亥革命後避居香港。陳伯陶手執古瓦而垂淚,吳道鎔視瓦片如古玉,不僅視為古物,實為難以重整的文化中國碎片,其懷古、歷史意識與離散海外之悲,已糾結難分。
蛻變的軌跡
戰後侶倫從回港,舊居已隨啟德濱湮滅,侶倫仍居九龍城,住在獅子石道,其後一再搬遷,徐悲鴻題字的橫幅「向水屋」仍掛屋中。原來日軍攻占香港前夕,侶倫把橫幅從鏡架取出,摺疊後夾進書中,藏於塞滿舊書的箱子裡,待戰後回港,箱子仍在,那橫幅也成了劫後倖存的珍寶。
侶倫筆下的啟德濱,遠望可見一片村落,工場,醬園,尼庵,廟宇;於我來說,可說是一個「史前」的九龍城,它引發歷史想像,但不涉個人回憶。一九九五年,當讀到郭麗容小說〈城市慢慢的遠去〉,我知道,我終於找到屬於我這年代的九龍城書寫。
在龍崗道的郵局,還有代人寫信的攤子。雜貨店仍然是六、七○年代模式,穿著白背心的老闆坐在櫃面,無線電播出南音。
其實香港還有許多地區,如上環、土瓜灣、西灣河等,保存六、七○年代或更早的模樣,直至我們的青年時代為止。不同年代都有屬於那年代的新事,我們許多年後才了解,除了新事物,舊物的延續也是一種時代產物和集體記認:
當赤鱲角新機場啟用後,九龍城將會重新發展。那時由香港島望去九龍城區,據說會像紐約曼赫頓。在矗矗的摩天大廈之間,玻璃幕牆與陽光閃爍。「天地良心,我愛你就是因為我愛你。」這些句子將沒處停留。
郭麗容的小說教我追思前事,九龍城的獅子石道、侯王道、福佬村道、南角道,都是我小時常去的地方。在油麻地乘坐三號巴士,或在旺角上海街登上十三號巴士前赴九龍城,是小時除了上學以外最熟悉的路途,車窗外的風景多年如一,我默認著如何沿巴士駛過的路徑,步行往返兩地。媽媽經營的兩家店鋪、姑婆經營的時裝店、姨婆開設的裁縫店都位於九龍城,是祖母輩、父輩與親戚們最常聚會的地方,尤當「作牙」時節。
九龍城總給我破舊、熱鬧,具人情味而嘈雜的感覺,麻雀牌聲混和飛機間歇經過的聲音,在幽僻的冷巷,傳來收音機播送的鬼故事。不過最恐怖的,莫如給父親帶到九龍城寨的簡陋牙醫診所脫牙,只為著老牙醫是他的朋友。經驗豐富但沒有專業認可資格的老牙醫,沒使用任何麻醉藥物,以簡陋工具把未完全鬆脫的乳齒用力拔出,我每次都發出比我小時所能承受的痛苦更尖銳的呼聲。
追隨哥哥、眾位表姐和表哥,攀上高聳而狹窄的木樓梯,我像一隻流竄的蟑螂。有時在梯間與拿著空漱口盅到大牌檔買白粥的大人打個照面,我側身讓過,梯間響徹我喜聽的木屐躂躂之聲。屋內大人在搓麻將,小孩在走廊玩,黑白電視傳來真的槍聲,教我們知道遠方有戰爭,我特別記得大人物逝世和有人被審判的新聞畫面,大人們有的切齒憤慨,有的低聲惋嘆。傍晚過後,收音機播送鬼故事,再傳來一首又一首粵曲,鑼鼓喧天,女聲婉轉,夾雜眾人不息的爭鬧,我不知應該掩耳,還是學習。
偌大的屋內,除大廳以外,以木板、衣櫃分割出許多小房間,我走進其中一所昏暗無窗的房間,書桌上一盞小燈,照出一個寫字的青年,也照出香煙裊裊,但照不亮身旁凌亂的書刊和紙頁。某天,那人遞給我一疊廢棄稿紙,在鋼筆增刪塗改的暗藍色墨水字跡間,我記著一些寫著「高爾基」、「契可夫」這樣奇怪組合的字詞。
後來媽媽結束九龍城的店鋪,祖母過世,很少再往九龍城,直至八○年代中,香港移民潮澎湃,啟德機場成了同學間最後話別之所,那幾年間,我們熟悉機場甚於圖書館。那時並不知道,移民的人若干年後又舉家回流,但同學間已很難碰面,友誼早晚褪色,九七問題卻帶來過早的斷裂。一九九○年我赴臺灣升讀大學,又幾度往返機場,到我畢業之時,機場準備遷往大嶼山,大片連接大嶼山之北的人工島嶼工程方興未艾。
一九九七年暑假,我到臺灣探望隔別三年的同學,最後一次從啟德機場登上飛機,回程時最後一次越過九龍城的低空降落。機場繁忙如昔,轉換航班資訊的告示板仍發出熟悉的「躂躂躂躂」聲響。啟德機場即將關閉,我已作好離別的準備,那知它的消失並不像一次爆炸。
九龍城的蛻變早於一九九四年拆卸九龍城寨已發其端,啟德機場的關閉,只是這蛻變之另一端。對城外人來說,城寨像個大迷宮,除了建築格局因素,城寨也儲存了前代香港的歷史、英占香港後種種烙印人心的陰暗記憶,董啟章《繁勝錄》中之一節,正寫出城寨如同迷宮的深意:「有人說走進寨城的人沒有一個能走出來,因為寨城會奪走人的記憶,令人不願意再離開。」城寨關乎我城的陰暗記憶,拆掉它是攻克陰暗記憶的最簡單卻又帶點暴虐的方法,在城寨低空掠過的飛機,也許提供另一種超越的可能,《繁勝錄》的敘事者走進城寨最後抵達出口,正遇見這種超越:「降落的飛機又在低空掠過,我掩著耳,抬頭望向那一隙天空,卻甚麼也沒看見,只感到四周好像陰暗了一下。」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凌晨,最後一班客機降落,啟德機場結束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任務,經過一段搬遷日子後,原來的客運大樓被分割為許多不同部分重新開放,分租給各種不同機構,作許多不同用途。二○○三年四月,「沙士」陰霾籠罩的日子,我重回沒有飛機升降的啟德機場客運大樓,穿梭於人跡杳杳的不同區間,記下種種不由自主的割裂。每感它的割裂,它的蛻變,與我們的成長都屬同一軌跡。
燈光與碎片
啟德機場跑道燈光徹夜明亮,像堅固的星座,為夜間升降的飛機提示路徑。我們以為星座總比我們持久,但這晚看來那麼虛弱。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凌晨降臨,跑道燈光倏然熄滅,市民不禁叫喚,短暫漆黑後,燈光突然再亮起,市民雀躍起哄,但它只閃爍了幾下,然後真正熄滅,結束比我們年長的光,歷史裡的離合、笑靨淚痕,奔向了冷卻宇宙。
再沒有飛機掠過九龍城的低空,再沒有頻繁的震耳巨響,我們反而不習慣,但知早晚會戀上這新的寧靜。因鄰近機場的建屋高度限制,大半世紀以來,整片九龍城社區維持低矮樓房外觀,在這晚,我們也預見它早晚撤換作新的高樓。
承認新舊輪替是必然,我們不敢否定新事,卻總忐忑於「發展」二字;只有九龍城一面淡然,看慣變幻。但九龍城也在我們不察覺的時候回首前塵,追憶城寨渡頭往返的清廷官吏、城寨門前腳戴枷鎖的罪犯、宋皇臺前痛惜文化失落的前清遺民、被日軍夷為平地的啟德濱。
時流洗淨鉛華,九龍城只暗自追懷,不肯在人前話舊,我們都理解,它藏著半島最幽隱的歷史記號,歷劫時代遺下依稀可辨的痕跡:宋皇臺、九龍城寨、啟德濱、啟德機場,面目全非,但未完全逝去。至若我輩在飛機巨響下的唐樓中的蹦跳嬉鬧、烙印腦際的笑靨淚影,待得雙燕歸來,也未必願意記起。
直至我們翻開紙頁,滿眼不滅跡印,盡是前人的文字。
目前所見,最具古風的九龍城風景,莫如侶倫筆下的記述。一九三○年與友人組織島上社,創辦文學雜誌《島上》的侶倫,二○年代末居於九龍城,位於近海的啟德濱外圍,他為居所命名「向水屋」,並邀得徐悲鴻題字,書橫幅掛於壁上。侶倫於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散文集《無名草》,有一篇文章〈故居〉,為戰前九龍城留下世外桃園式的記錄:
我的住居是一列新建樓房的一間四層樓上,沿住屋外有一個寬廣的,鋪了花磚子的迴廊式的陽臺,……可以看見由高聳的獅子山下面伸展過來的一塊巨幅的風景畫:一簇簇蒼翠的樹木和一片灰色的屋頂─是一世紀來不輕易變動的古風的殘留。隱蔽在灰色之中的,是村落,工場,醬園,尼庵,廟宇,園地和人家。一個小丘橫在那裡,小丘的中部,像腰帶似地鑲著古舊卻還完整的九龍城的城牆。
這是目前為止我所讀到的,戰前從啟德濱外圍望向九龍城寨風景地貌的最完整紀錄。這優美散文同時是記錄九龍城地貌的重要文獻,《無名草》一九五三年曾再版一次,早已絕版,之後未有再版,讀到的人恐怕不多,侶倫後來在寫於一九七七年的文章〈向水屋追懷〉中,引用了部分〈故居〉的內容,但不及原文詳細。
侶倫文中所指的「新建樓房」,是指建於一九二○年代的啟德濱住宅。一九一○年代,由何啟與區德等多人創辦的啟德營業有限公司,主持填海建屋計畫,新建成的社區稱為啟德濱。啟德公司的填海計畫,未竟全工就倒閉,政府接收後在填海區興建機場,命名為「啟德」。二戰期間,日軍攻占香港後,為擴建機場拆去九龍城寨城牆,宋皇臺、啟德濱社區亦被夷平。
侶倫在《向水屋筆語》一書,多處談及九龍城,其中〈故人之思〉記錄了葉靈鳳一九二九年偕郭林鳳在香港短暫居住的日子,侶倫安排他們租住在九龍城:
那是座落「宋皇臺」旁邊一間房子的第二層樓。從那「走馬騎樓」向外望,正面是鯉魚門,右面是香港,左面是一條向前伸展的海堤;景色很美。尤其是晚上,海上的漁船燈火在澄明的水面溜來溜去,下面傳來潮水拍岸的有節奏的聲音。在海闊天空之中,人彷彿置身超然物外境界。
因為「向水屋」之名以及葉靈鳳短住九龍城,一時傳遍香港文壇,《伴侶》雜誌編輯張稚廬送給侶倫一首舊詩寫道:「半島爭看一俊才,宋皇臺下寫沉哀。不知十里衙前道,幾見翩翩靈鳳來。」前兩句寫侶倫,後兩句寫葉靈鳳。寫侶倫時提及宋皇臺,只就其居處位置而言,侶倫是早期香港新文學拓荒者之一,創辦新文學社團和刊物,宋皇臺與侶倫其人其文無多大關係,它另有迥異於新文藝取向的象徵意義。
宋皇臺本九龍城以南海濱山坡上一塊大石,南宋末年,宋帝昰與宋帝昺被元朝軍隊追逼,在文天祥、陸秀夫等人護送下逃至九龍城一帶,短暫停駐再繼續逃亡。後人紀念其事,於相傳宋帝曾登臨之大石刻「宋王臺」三字,旁邊另有「清嘉慶丁卯重修」七字,為保護古蹟,香港政府於一八九九年通過「保存宋王臺勝蹟條例」,其後修茸鄰近地方,闢為公園。日治時期,大石被炸,裂為數塊,刻字部分竟奇蹟倖存,戰後港府擴建啟德機場,於大石原址興建機場客運大樓,石刻部分切割成長方形,移送機場附近空地,闢作「宋皇臺公園」。
二十世紀初,辛亥革命後,前清文人避居香港,有感山河變易,香港「雖信美而非吾土」,文人將家國與身世之悲寄託於宋皇臺,藉雅集相互唱酬。一九一七年,蘇澤東輯錄前清探花陳伯陶等人所著宋皇臺詩詞,編為《宋臺秋唱》。宋皇臺向為香港最著名古蹟,文人懷古之餘,亦追溯九龍古事,如陳伯陶〈宋皇臺懷古並序〉:
九龍,古官富場地,明初置巡司,嘉慶間,總督百齡築砦,改名九龍。道光間復改官富巡司為九龍巡司,而官富場之名遂隱。
前清文人追懷失去的時光,以歷史抗衡殖民地的無根,不意間為香港敘述了遺民角度的歷史。宋皇臺也不只是前清文人吟詠對象,抗日戰爭期間,南來香港避亂的文人,也有許多藉宋皇臺抒發時局憂患,如陳居霖〈雨訪宋皇臺偕雪瑛三首錄二〉其一云:「抱得春愁海樣深,江山如晦忍重臨。崖門極目蒼波冷,空憶當年帝璽沉。」正將時代憂患與個人飄零之悲合而為一。二十世紀初,香港仍有許多與宋皇臺相關的古蹟,如二王殿村、侯王廟、國母梳妝石等,同為前清文人避港必訪之地。二王殿位於二王殿村內,即《新安縣志》中的二黃店村,位於今日的馬頭圍區,陳伯陶〈宋行宮遺瓦歌並序〉記云:「官富場宋皇臺之東有村名二王殿,景炎行宮舊基也,新安縣志稱土人因其址建北帝廟即此,今廟後石礎猶存。其地耕人往往得古瓦,色赭黝,堅如石,雖稍麤朴,然頗經久。」序後有詩,抒其獲得古殿遺瓦的感慨:「凄涼故國哭杜鵑,零落舊巢悲海燕。手揩此瓦重摩挲,惆悵遺基淚如霰。」
宋皇臺、二王殿村與古殿遺瓦為前清遺民共同吟詠之對象,吳道鎔亦有詩云:
寒林擁日到虞淵,戎馬艱難瘴海邊。七百年來陵谷變,二王村尚鳥啼煙(二王村)。敷天左袒語非虛,直到窮邊有帝居。破碎河山瓦全少,千秋一片重璠璵(宋行宮瓦)。
吳道鎔與陳伯陶、張學華等合稱「嶺南九老」,皆前清遺民,辛亥革命後避居香港。陳伯陶手執古瓦而垂淚,吳道鎔視瓦片如古玉,不僅視為古物,實為難以重整的文化中國碎片,其懷古、歷史意識與離散海外之悲,已糾結難分。
蛻變的軌跡
戰後侶倫從回港,舊居已隨啟德濱湮滅,侶倫仍居九龍城,住在獅子石道,其後一再搬遷,徐悲鴻題字的橫幅「向水屋」仍掛屋中。原來日軍攻占香港前夕,侶倫把橫幅從鏡架取出,摺疊後夾進書中,藏於塞滿舊書的箱子裡,待戰後回港,箱子仍在,那橫幅也成了劫後倖存的珍寶。
侶倫筆下的啟德濱,遠望可見一片村落,工場,醬園,尼庵,廟宇;於我來說,可說是一個「史前」的九龍城,它引發歷史想像,但不涉個人回憶。一九九五年,當讀到郭麗容小說〈城市慢慢的遠去〉,我知道,我終於找到屬於我這年代的九龍城書寫。
在龍崗道的郵局,還有代人寫信的攤子。雜貨店仍然是六、七○年代模式,穿著白背心的老闆坐在櫃面,無線電播出南音。
其實香港還有許多地區,如上環、土瓜灣、西灣河等,保存六、七○年代或更早的模樣,直至我們的青年時代為止。不同年代都有屬於那年代的新事,我們許多年後才了解,除了新事物,舊物的延續也是一種時代產物和集體記認:
當赤鱲角新機場啟用後,九龍城將會重新發展。那時由香港島望去九龍城區,據說會像紐約曼赫頓。在矗矗的摩天大廈之間,玻璃幕牆與陽光閃爍。「天地良心,我愛你就是因為我愛你。」這些句子將沒處停留。
郭麗容的小說教我追思前事,九龍城的獅子石道、侯王道、福佬村道、南角道,都是我小時常去的地方。在油麻地乘坐三號巴士,或在旺角上海街登上十三號巴士前赴九龍城,是小時除了上學以外最熟悉的路途,車窗外的風景多年如一,我默認著如何沿巴士駛過的路徑,步行往返兩地。媽媽經營的兩家店鋪、姑婆經營的時裝店、姨婆開設的裁縫店都位於九龍城,是祖母輩、父輩與親戚們最常聚會的地方,尤當「作牙」時節。
九龍城總給我破舊、熱鬧,具人情味而嘈雜的感覺,麻雀牌聲混和飛機間歇經過的聲音,在幽僻的冷巷,傳來收音機播送的鬼故事。不過最恐怖的,莫如給父親帶到九龍城寨的簡陋牙醫診所脫牙,只為著老牙醫是他的朋友。經驗豐富但沒有專業認可資格的老牙醫,沒使用任何麻醉藥物,以簡陋工具把未完全鬆脫的乳齒用力拔出,我每次都發出比我小時所能承受的痛苦更尖銳的呼聲。
追隨哥哥、眾位表姐和表哥,攀上高聳而狹窄的木樓梯,我像一隻流竄的蟑螂。有時在梯間與拿著空漱口盅到大牌檔買白粥的大人打個照面,我側身讓過,梯間響徹我喜聽的木屐躂躂之聲。屋內大人在搓麻將,小孩在走廊玩,黑白電視傳來真的槍聲,教我們知道遠方有戰爭,我特別記得大人物逝世和有人被審判的新聞畫面,大人們有的切齒憤慨,有的低聲惋嘆。傍晚過後,收音機播送鬼故事,再傳來一首又一首粵曲,鑼鼓喧天,女聲婉轉,夾雜眾人不息的爭鬧,我不知應該掩耳,還是學習。
偌大的屋內,除大廳以外,以木板、衣櫃分割出許多小房間,我走進其中一所昏暗無窗的房間,書桌上一盞小燈,照出一個寫字的青年,也照出香煙裊裊,但照不亮身旁凌亂的書刊和紙頁。某天,那人遞給我一疊廢棄稿紙,在鋼筆增刪塗改的暗藍色墨水字跡間,我記著一些寫著「高爾基」、「契可夫」這樣奇怪組合的字詞。
後來媽媽結束九龍城的店鋪,祖母過世,很少再往九龍城,直至八○年代中,香港移民潮澎湃,啟德機場成了同學間最後話別之所,那幾年間,我們熟悉機場甚於圖書館。那時並不知道,移民的人若干年後又舉家回流,但同學間已很難碰面,友誼早晚褪色,九七問題卻帶來過早的斷裂。一九九○年我赴臺灣升讀大學,又幾度往返機場,到我畢業之時,機場準備遷往大嶼山,大片連接大嶼山之北的人工島嶼工程方興未艾。
一九九七年暑假,我到臺灣探望隔別三年的同學,最後一次從啟德機場登上飛機,回程時最後一次越過九龍城的低空降落。機場繁忙如昔,轉換航班資訊的告示板仍發出熟悉的「躂躂躂躂」聲響。啟德機場即將關閉,我已作好離別的準備,那知它的消失並不像一次爆炸。
九龍城的蛻變早於一九九四年拆卸九龍城寨已發其端,啟德機場的關閉,只是這蛻變之另一端。對城外人來說,城寨像個大迷宮,除了建築格局因素,城寨也儲存了前代香港的歷史、英占香港後種種烙印人心的陰暗記憶,董啟章《繁勝錄》中之一節,正寫出城寨如同迷宮的深意:「有人說走進寨城的人沒有一個能走出來,因為寨城會奪走人的記憶,令人不願意再離開。」城寨關乎我城的陰暗記憶,拆掉它是攻克陰暗記憶的最簡單卻又帶點暴虐的方法,在城寨低空掠過的飛機,也許提供另一種超越的可能,《繁勝錄》的敘事者走進城寨最後抵達出口,正遇見這種超越:「降落的飛機又在低空掠過,我掩著耳,抬頭望向那一隙天空,卻甚麼也沒看見,只感到四周好像陰暗了一下。」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凌晨,最後一班客機降落,啟德機場結束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任務,經過一段搬遷日子後,原來的客運大樓被分割為許多不同部分重新開放,分租給各種不同機構,作許多不同用途。二○○三年四月,「沙士」陰霾籠罩的日子,我重回沒有飛機升降的啟德機場客運大樓,穿梭於人跡杳杳的不同區間,記下種種不由自主的割裂。每感它的割裂,它的蛻變,與我們的成長都屬同一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