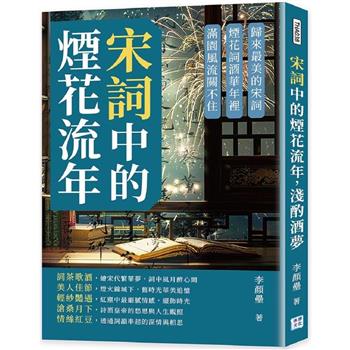詞酒流年裡,風月共醉
酒後的蘇東坡,一個人,一匹馬,在春天的夜裡閒逛,腳下是淺淺流動的溪水,月亮旁有著幾絲微雲。「緩步困春醪,春融臉上桃」(〈菩薩蠻〉),走累了想要小憩,他下馬躺在芳草上,思索起一闋新詞;
晏殊呢,喝了一小杯美酒後說:醉了,睡覺去!「綠酒初嘗人易醉,一枕小窗濃睡」(〈清平樂〉),一枕濃睡醒來,已是夕陽西下,不知他在夢中是否想好了如何表達醉意?
酒與宋詞,是剪不斷的情緒,注定連在一起。
燈紅酒綠、處處笙歌,怎能無酒?就連老夫子司馬光也不免要作一闋〈西江月〉抒發一下:「寶髻鬆鬆挽就,鉛華淡淡妝成。輕煙翠霧籠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
平時一本正經的儒家大師,歡樂聚會上也多喝了幾杯,喝了酒惝恍飄忽,也覺得跳舞的姑娘色藝可愛,而牽起情思:
此夕幾年無此晴,碧天萬里月徐行。
官壚賣酒傾千斛,市裡行歌徹五更。
潼酪獨烹僧缽美,琉璃閒照佛龕明。
頹然坐睡君無笑,寶馬香車事隔生。
這就是宋代的社會生活:生活穩定,處處有酒,即便是窮鄉僻壤,三里五里,都必有酒旗招搖,人們對酒的需求不斷增加;農業生產力提高,糧食產量豐厚,國庫糧食收入的三分之一,都拿來釀酒,酒坊十里內瀰漫酒香,迷醉多少詞人。
從陸游這首〈丁未上元月色達曉如晝予齋居屬貳車領客〉的詩中可看出,當時人們的日常飲食、交際宴請、饋禮酬答,都離不開酒,造酒、賣酒也是國庫的重要收入來源。
「官壚賣酒傾千斛」,除了賣官酒,當時還讓官伎們當壚賣酒——這事兒王安石變法時做得最勤快,他命令把酒肆建到城門口,讓一群濃妝豔抹的美女在前頭歌舞,有老百姓出城,就上來拋媚眼、拉拉扯扯:賣酒了、賣酒了……
其實不用如此煽情,人們也趨之若鶩。「不向尊前同一醉」(〈破陣子〉)、「相看莫惜尊前醉」(〈鵲踏枝〉)、「一曲新詞酒一杯」(〈浣溪沙〉)。那麼多人喝酒,怎麼會沒有喝酒高手?唐代李白被譽為「醉仙」,白居易自稱「醉尹」,連皮日休也獲得「醉士」的雅號;那麼在飲酒成風的宋代裡練就出來飲酒大師,應不比唐人遜色。
宋代飲酒的第一號名家,應該是以詩酒豪放自詡的石延年。他的詩,風格奇峭深美,比如〈寄尹師魯〉:「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換桃李。雁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裡。眉比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汝如洗。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他喝酒的方式也十分怪異:披頭散髮,赤腳戴枷而飲,叫做「囚飲」;坐於枝頭上飲酒,叫做「巢飲」;用槁草捆紮於身,伸頸而飲,飲後復縮進草束之中,叫做「鱉飲」,不免狂放得有些病態。
石延年的酒興與酒量,更是人人甘拜下風。他在海州任通判時,另一位飲酒能手劉潛專程來訪,石通判又回訪劉潛的船。兩人對飲,從白天喝到半夜;眼看酒罈快要見底,一時又難上岸買酒,便在船上尋了一斗醋,摻入酒裡喝。第二天一早,酒與醋全都喝光,仍沒有分出勝負,只好相約再戰。
後來兩人到東京城的王家酒店對飲,一整天只喝酒不說話,天黑後兩人也都沒有醉意,相揖而去。最後誰贏了,史書沒記載,我們只須知道這妙趣橫生的故事就好了。
喝酒怎會沒有行酒令?對於宋人而言,他們不但在飲酒中尋求歡樂和刺激,還往往將自己對酒的見識,透過行酒令表述出來,而後再由行酒令發展到「小詞」、「散曲」等。這是一種文人交往、酬酢的小雅文化,即由「鬥酒」到「鬥才」,鬥出了一種生活情調,是俗態中的風雅。
大文豪歐陽脩與友人飲酒行令,要求每人作的兩句詩必須觸犯刑律。其中一人說:「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另一人說:「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輪到歐陽脩,他慢條斯理地說:「酒黏衫袖重,花壓帽檐偏。」眾人一聽,大惑不解,問他為何詩中沒有犯罪內容,他說:「喝酒都喝成這樣,再嚴重的刑律都能犯下了!」眾人遂相視大笑。
如此,推杯換盞間填寫的詩詞,怎能不帶著酒味?你看,那詞牌本身就沾染著酒水:〈醉梅花〉、〈調笑令〉、〈天仙子〉、〈水調歌頭〉、〈荷葉杯〉、〈醉公子〉……
黃菊枝頭生曉寒,人生莫放酒杯乾。風前橫笛斜吹雨,醉裡簪花倒著冠。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盡清歡。黃花白髮相牽挽,付與時人冷眼看。
從這一闋〈醉梅花〉,看看詞人黃庭堅喝成了什麼樣子!不但酒杯不離手,一口氣喝醉,還帶著菊花滿城奔跑,那是怎樣的場景?文人士大夫飲酒作樂,司空見慣,而女子飲酒在當時也是常有之事;愛喝酒的歐陽脩還記敘了這樣一個故事:
花底忽聞敲兩槳,逡巡女伴來尋訪。酒盞旋將荷葉當,蓮舟蕩,時時盞裡生紅浪。
花氣酒香清廝釀,花腮酒面紅相向。醉倚綠陰眠一餉,驚起望,船頭擱沙灘上。
採蓮的人兒盪舟嬉戲,興致濃時,摘下荷葉當酒盞酣暢一飲,船兒一搖晃,酒盞也跟著晃動;酒氣荷香共芬芳,花面人面相映紅,酒足人自醉,那就需要小憩片刻;待到醒來一看,自己的小舟已擱淺在沙灘上了。採蓮女的歲月靜好,還驚起了女詞人李清照的「一灘鷗鷺」,她的〈如夢令〉,也是在「沉醉不知歸路」的狀態下揮毫完成。
李清照酒後之作不比任何一個男詞人差,不信,讓宋代的男女詞人都聚到一起飲酒,醉後比試一番。而詞人都拋棄成見,只是喝一場酒、賦一闋詞,這也定是歷史塵埃中最美的場景之一。
龍焙今年絕品,溢出多少風流
元朝的張可久在散曲〈人月圓·山中書事〉中,後半首寫到:「數間茅舍,藏書萬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釀酒,春水煎茶。」真是太令人嚮往了。山中何所有?有茶書詩酒、松雲泉石,靜如太古的歲月;三月有煙光草色、落花啼鳥,春睡既足,就汲泉採花、煎茶釀酒,簡直是神仙生活。
但事實上,常年做下級官吏的張可久恐怕無法享受這種生活,他述說的是一種願望;不過他的願望宋人達到了,寫這支小令也許是在羨慕宋朝吧。
唐朝出了「茶聖」陸羽,中國茶文化已在當時達到鼎盛,似乎已經被文人們品得不能再講究了:水的沸騰度、湯花的綿厚度,都有很多訣竅,繁複的工序讓人眼花撩亂;但其實,到了崇尚雅意的宋人這裡,茶的講究才真正開始。
宋朝繁華,製茶工藝大有提升,宋太祖趙匡胤嗜飲茶,在宮廷中設立茶事機關,宮廷用茶有了分級,茶儀成為禮制,賜茶已成皇帝籠絡大臣、眷懷親族,甚至向國外使節示好的重要手段,文官集團中出現了「湯社」等專業品茶社團;至於民間,茶文化更是生機盎然,有人遷徙搬家,鄰里要「獻茶」,有客來,要敬「元寶茶」,訂婚時要「下茶」,結婚時要「定茶」,同房時要「合茶」,親友聚會更離不開茶會,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都飄浮著茶的清香。
單說採茶的講究,就勝唐朝一籌:採茶的人須五更天上山採摘,醞釀著春的氣息,讓人薰陶其中;而太陽出來前即要收工,因未受過日照的嫩芽最為滋潤,集天地靈氣之精華——就是這樣的新茶,在宋代社會備受追捧。
而在眾多的採茶工序後,煎茶更是技高一籌:
龍焙今年絕品,谷簾自古珍泉。
雪芽雙井散神仙。苗裔來從北苑。
湯發雲腴釅白,盞浮花乳輕圓。
人間誰敢更爭妍。鬥取紅窗粉面。
蘇東坡無疑是性情中人,也是喝茶的高手,他用陳年的雪水煎茶,煎至合宜的程度後,再沖入盛放茶膏的茶盞,等著雪白的泡沫高高浮起;而面對此等令人期待的情境,詞人自然是難以形容的欣喜。
細細品味,此樂何極?
想來,有閒才能品茶,而在舉國都閒的情景下,生活慢起來,慢到什麼都不再重要、不再去理會了。國都亡掉了,即使遷至臨安,茶樓依然甚多,人們約會相聚,大多邀於茶樓。與北宋相比,南宋社會各階層飲茶風氣更盛,將宋代的茶文化推向極致,南北飲茶文化的交流,使臨安城中酒肆、茶坊遍布坊巷,而以此為中心發展出茶肆文化。
當然,茶的品位與茶肆都有分級:皇帝、大臣、文人雅士,士卒、平民,都有屬於自己的場所,聊以點綴生活。
飲茶風氣的普及,將宋代的茶文化推展到藝術化的高級階段。兩宋以茶為主題的詩作屢見不鮮,其中描寫飲茶勝境的佳句更是層出不窮,如范仲淹的「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泠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和章岷從事鬥茶歌〉);林和靖的「潏潏藥泉來石竇,霏霏茶靄出松梢」、「閣掩茶煙晚,廊回雪溜清」(〈湖山小隱二首〉);陸游的「青雲腴開鬥茗,翠罌玉液取寒泉」(〈晨雨〉);范成大的「煩將煉火炊香飯,更引長泉煮鬥茶」(〈題張氏新亭〉)等等。泡茶時,湯水蒸騰的氤氳之氣,齒頰留下的茶香,以及茶湯沁入肺腑的溫馨感受,給宋人帶來了充分的愉悅。
不但品味生活,還要作為娛樂玩出花樣,比如行茶令。浙江樂清人王十朋在《梅溪文集》中說道:「予歸,與諸友講茶令,每會茶指一物為題,各舉故事,不通則罰。」所舉故事,都要與茶有關,答錯則輸;輸者只許聞茶香,眼睜睜看著別人飲茶。宋代濟南女詞人李清照,常與其丈夫——著名的金石學家趙明誠行茶令,而十有八九都是趙明誠敗北。
宋人飲茶,甚至還能出魔術,這就有了分茶——往茶碗裡沖水的同時,用調茶工具撥弄,使茶湯表面的泡沫幻化成鳥獸蟲魚、花草、流雲等圖案: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
蒸水老禪弄泉手,隆興元春新玉爪。
二者相遭兔甌面,怪怪奇奇真善幻。
紛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萬變。
銀瓶首下仍尻高,注湯作字勢嫖姚。
楊萬里的這首〈澹庵坐上觀顯上人分茶〉寫得神乎其神,在這場茶藝表演中,細膩的末茶與水相遇,在黑釉的兔毫盞上幻化出千奇百怪的畫面,如紛雪行太空,又如泉影落寒江;有時像淡雅疏朗的丹青,或勁疾灑脫的草書。到如此境界,這位分茶者顯然是位老手。
山東人王千秋流寓金陵時,曾參與過幾次富貴人家的茶宴,填出了一闋更為形象的〈風流子〉:
夜久燭花暗,仙翁醉、豐頰縷紅霞。正三行鈿袖,一聲金縷,卷茵停舞,側火分茶。笑盈盈,濺湯溫翠碗,折印啟緗紗。玉筍緩搖,雲頭初起,竹龍停戰,雨腳微斜。
清風生兩腋,塵埃盡,留白雪、長黃芽。解使芝眉長秀,潘鬢休華。想竹宮異日,袞衣寒夜,小團分賜,新樣金花。還記玉麟春色,曾在仙家。
富貴人家的夜宴,酒闌歌舞歇,正是分茶時,主持分茶的還是位美女;她技藝高超,笑語盈盈,不慌不忙,纖如玉筍的手下,起落間有雲起龍飛之妙。這樣的茶湯,喝下去後真是清風生兩腋,簡直能讓人永保青春。那如此精絕的小團茶,又從哪裡來?自然是皇上御賜的;而這茶樹的種子,是仙人家裡的。這場浩大的分茶情境,反映著宋代人心目中的極品人生:既富且貴,青春長駐,紅袖添香,還要閒適風雅。
既然說到:茶葉是皇帝御賜的。那麼分茶中真正的絕頂高手,自然要數當時的皇帝——宋徽宗趙佶。他的寵臣蔡京在〈延福宮曲宴記〉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宣和二年(公元一一二零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於延福宮……上命近侍限茶具,親自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盞面,如疏星朗月。顧諸臣曰:『此自布茶。飲畢皆頓首謝。』」徽宗親自分茶讓群臣觀賞,日月星辰都在茶盞中展現,似乎是一位印象派大師的傑作,這也許稱得上是分茶的最高境界吧。
宋朝人就是這樣,在回味無窮的品茶中,度過了數個春秋,風華了一個朝代,對於現代人快速的生活節奏來說,學習宋人品茶,倒是一種調節的好方法——那就用青瓷沖一盞香茶,在茶香與瓷香交融間,且當一回宋代人吧。
一壺好茶,就可解萬霎憂愁,心情也頓時開朗許多。
酒後的蘇東坡,一個人,一匹馬,在春天的夜裡閒逛,腳下是淺淺流動的溪水,月亮旁有著幾絲微雲。「緩步困春醪,春融臉上桃」(〈菩薩蠻〉),走累了想要小憩,他下馬躺在芳草上,思索起一闋新詞;
晏殊呢,喝了一小杯美酒後說:醉了,睡覺去!「綠酒初嘗人易醉,一枕小窗濃睡」(〈清平樂〉),一枕濃睡醒來,已是夕陽西下,不知他在夢中是否想好了如何表達醉意?
酒與宋詞,是剪不斷的情緒,注定連在一起。
燈紅酒綠、處處笙歌,怎能無酒?就連老夫子司馬光也不免要作一闋〈西江月〉抒發一下:「寶髻鬆鬆挽就,鉛華淡淡妝成。輕煙翠霧籠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
平時一本正經的儒家大師,歡樂聚會上也多喝了幾杯,喝了酒惝恍飄忽,也覺得跳舞的姑娘色藝可愛,而牽起情思:
此夕幾年無此晴,碧天萬里月徐行。
官壚賣酒傾千斛,市裡行歌徹五更。
潼酪獨烹僧缽美,琉璃閒照佛龕明。
頹然坐睡君無笑,寶馬香車事隔生。
這就是宋代的社會生活:生活穩定,處處有酒,即便是窮鄉僻壤,三里五里,都必有酒旗招搖,人們對酒的需求不斷增加;農業生產力提高,糧食產量豐厚,國庫糧食收入的三分之一,都拿來釀酒,酒坊十里內瀰漫酒香,迷醉多少詞人。
從陸游這首〈丁未上元月色達曉如晝予齋居屬貳車領客〉的詩中可看出,當時人們的日常飲食、交際宴請、饋禮酬答,都離不開酒,造酒、賣酒也是國庫的重要收入來源。
「官壚賣酒傾千斛」,除了賣官酒,當時還讓官伎們當壚賣酒——這事兒王安石變法時做得最勤快,他命令把酒肆建到城門口,讓一群濃妝豔抹的美女在前頭歌舞,有老百姓出城,就上來拋媚眼、拉拉扯扯:賣酒了、賣酒了……
其實不用如此煽情,人們也趨之若鶩。「不向尊前同一醉」(〈破陣子〉)、「相看莫惜尊前醉」(〈鵲踏枝〉)、「一曲新詞酒一杯」(〈浣溪沙〉)。那麼多人喝酒,怎麼會沒有喝酒高手?唐代李白被譽為「醉仙」,白居易自稱「醉尹」,連皮日休也獲得「醉士」的雅號;那麼在飲酒成風的宋代裡練就出來飲酒大師,應不比唐人遜色。
宋代飲酒的第一號名家,應該是以詩酒豪放自詡的石延年。他的詩,風格奇峭深美,比如〈寄尹師魯〉:「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換桃李。雁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裡。眉比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汝如洗。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他喝酒的方式也十分怪異:披頭散髮,赤腳戴枷而飲,叫做「囚飲」;坐於枝頭上飲酒,叫做「巢飲」;用槁草捆紮於身,伸頸而飲,飲後復縮進草束之中,叫做「鱉飲」,不免狂放得有些病態。
石延年的酒興與酒量,更是人人甘拜下風。他在海州任通判時,另一位飲酒能手劉潛專程來訪,石通判又回訪劉潛的船。兩人對飲,從白天喝到半夜;眼看酒罈快要見底,一時又難上岸買酒,便在船上尋了一斗醋,摻入酒裡喝。第二天一早,酒與醋全都喝光,仍沒有分出勝負,只好相約再戰。
後來兩人到東京城的王家酒店對飲,一整天只喝酒不說話,天黑後兩人也都沒有醉意,相揖而去。最後誰贏了,史書沒記載,我們只須知道這妙趣橫生的故事就好了。
喝酒怎會沒有行酒令?對於宋人而言,他們不但在飲酒中尋求歡樂和刺激,還往往將自己對酒的見識,透過行酒令表述出來,而後再由行酒令發展到「小詞」、「散曲」等。這是一種文人交往、酬酢的小雅文化,即由「鬥酒」到「鬥才」,鬥出了一種生活情調,是俗態中的風雅。
大文豪歐陽脩與友人飲酒行令,要求每人作的兩句詩必須觸犯刑律。其中一人說:「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另一人說:「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輪到歐陽脩,他慢條斯理地說:「酒黏衫袖重,花壓帽檐偏。」眾人一聽,大惑不解,問他為何詩中沒有犯罪內容,他說:「喝酒都喝成這樣,再嚴重的刑律都能犯下了!」眾人遂相視大笑。
如此,推杯換盞間填寫的詩詞,怎能不帶著酒味?你看,那詞牌本身就沾染著酒水:〈醉梅花〉、〈調笑令〉、〈天仙子〉、〈水調歌頭〉、〈荷葉杯〉、〈醉公子〉……
黃菊枝頭生曉寒,人生莫放酒杯乾。風前橫笛斜吹雨,醉裡簪花倒著冠。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盡清歡。黃花白髮相牽挽,付與時人冷眼看。
從這一闋〈醉梅花〉,看看詞人黃庭堅喝成了什麼樣子!不但酒杯不離手,一口氣喝醉,還帶著菊花滿城奔跑,那是怎樣的場景?文人士大夫飲酒作樂,司空見慣,而女子飲酒在當時也是常有之事;愛喝酒的歐陽脩還記敘了這樣一個故事:
花底忽聞敲兩槳,逡巡女伴來尋訪。酒盞旋將荷葉當,蓮舟蕩,時時盞裡生紅浪。
花氣酒香清廝釀,花腮酒面紅相向。醉倚綠陰眠一餉,驚起望,船頭擱沙灘上。
採蓮的人兒盪舟嬉戲,興致濃時,摘下荷葉當酒盞酣暢一飲,船兒一搖晃,酒盞也跟著晃動;酒氣荷香共芬芳,花面人面相映紅,酒足人自醉,那就需要小憩片刻;待到醒來一看,自己的小舟已擱淺在沙灘上了。採蓮女的歲月靜好,還驚起了女詞人李清照的「一灘鷗鷺」,她的〈如夢令〉,也是在「沉醉不知歸路」的狀態下揮毫完成。
李清照酒後之作不比任何一個男詞人差,不信,讓宋代的男女詞人都聚到一起飲酒,醉後比試一番。而詞人都拋棄成見,只是喝一場酒、賦一闋詞,這也定是歷史塵埃中最美的場景之一。
龍焙今年絕品,溢出多少風流
元朝的張可久在散曲〈人月圓·山中書事〉中,後半首寫到:「數間茅舍,藏書萬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釀酒,春水煎茶。」真是太令人嚮往了。山中何所有?有茶書詩酒、松雲泉石,靜如太古的歲月;三月有煙光草色、落花啼鳥,春睡既足,就汲泉採花、煎茶釀酒,簡直是神仙生活。
但事實上,常年做下級官吏的張可久恐怕無法享受這種生活,他述說的是一種願望;不過他的願望宋人達到了,寫這支小令也許是在羨慕宋朝吧。
唐朝出了「茶聖」陸羽,中國茶文化已在當時達到鼎盛,似乎已經被文人們品得不能再講究了:水的沸騰度、湯花的綿厚度,都有很多訣竅,繁複的工序讓人眼花撩亂;但其實,到了崇尚雅意的宋人這裡,茶的講究才真正開始。
宋朝繁華,製茶工藝大有提升,宋太祖趙匡胤嗜飲茶,在宮廷中設立茶事機關,宮廷用茶有了分級,茶儀成為禮制,賜茶已成皇帝籠絡大臣、眷懷親族,甚至向國外使節示好的重要手段,文官集團中出現了「湯社」等專業品茶社團;至於民間,茶文化更是生機盎然,有人遷徙搬家,鄰里要「獻茶」,有客來,要敬「元寶茶」,訂婚時要「下茶」,結婚時要「定茶」,同房時要「合茶」,親友聚會更離不開茶會,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都飄浮著茶的清香。
單說採茶的講究,就勝唐朝一籌:採茶的人須五更天上山採摘,醞釀著春的氣息,讓人薰陶其中;而太陽出來前即要收工,因未受過日照的嫩芽最為滋潤,集天地靈氣之精華——就是這樣的新茶,在宋代社會備受追捧。
而在眾多的採茶工序後,煎茶更是技高一籌:
龍焙今年絕品,谷簾自古珍泉。
雪芽雙井散神仙。苗裔來從北苑。
湯發雲腴釅白,盞浮花乳輕圓。
人間誰敢更爭妍。鬥取紅窗粉面。
蘇東坡無疑是性情中人,也是喝茶的高手,他用陳年的雪水煎茶,煎至合宜的程度後,再沖入盛放茶膏的茶盞,等著雪白的泡沫高高浮起;而面對此等令人期待的情境,詞人自然是難以形容的欣喜。
細細品味,此樂何極?
想來,有閒才能品茶,而在舉國都閒的情景下,生活慢起來,慢到什麼都不再重要、不再去理會了。國都亡掉了,即使遷至臨安,茶樓依然甚多,人們約會相聚,大多邀於茶樓。與北宋相比,南宋社會各階層飲茶風氣更盛,將宋代的茶文化推向極致,南北飲茶文化的交流,使臨安城中酒肆、茶坊遍布坊巷,而以此為中心發展出茶肆文化。
當然,茶的品位與茶肆都有分級:皇帝、大臣、文人雅士,士卒、平民,都有屬於自己的場所,聊以點綴生活。
飲茶風氣的普及,將宋代的茶文化推展到藝術化的高級階段。兩宋以茶為主題的詩作屢見不鮮,其中描寫飲茶勝境的佳句更是層出不窮,如范仲淹的「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泠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和章岷從事鬥茶歌〉);林和靖的「潏潏藥泉來石竇,霏霏茶靄出松梢」、「閣掩茶煙晚,廊回雪溜清」(〈湖山小隱二首〉);陸游的「青雲腴開鬥茗,翠罌玉液取寒泉」(〈晨雨〉);范成大的「煩將煉火炊香飯,更引長泉煮鬥茶」(〈題張氏新亭〉)等等。泡茶時,湯水蒸騰的氤氳之氣,齒頰留下的茶香,以及茶湯沁入肺腑的溫馨感受,給宋人帶來了充分的愉悅。
不但品味生活,還要作為娛樂玩出花樣,比如行茶令。浙江樂清人王十朋在《梅溪文集》中說道:「予歸,與諸友講茶令,每會茶指一物為題,各舉故事,不通則罰。」所舉故事,都要與茶有關,答錯則輸;輸者只許聞茶香,眼睜睜看著別人飲茶。宋代濟南女詞人李清照,常與其丈夫——著名的金石學家趙明誠行茶令,而十有八九都是趙明誠敗北。
宋人飲茶,甚至還能出魔術,這就有了分茶——往茶碗裡沖水的同時,用調茶工具撥弄,使茶湯表面的泡沫幻化成鳥獸蟲魚、花草、流雲等圖案: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
蒸水老禪弄泉手,隆興元春新玉爪。
二者相遭兔甌面,怪怪奇奇真善幻。
紛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萬變。
銀瓶首下仍尻高,注湯作字勢嫖姚。
楊萬里的這首〈澹庵坐上觀顯上人分茶〉寫得神乎其神,在這場茶藝表演中,細膩的末茶與水相遇,在黑釉的兔毫盞上幻化出千奇百怪的畫面,如紛雪行太空,又如泉影落寒江;有時像淡雅疏朗的丹青,或勁疾灑脫的草書。到如此境界,這位分茶者顯然是位老手。
山東人王千秋流寓金陵時,曾參與過幾次富貴人家的茶宴,填出了一闋更為形象的〈風流子〉:
夜久燭花暗,仙翁醉、豐頰縷紅霞。正三行鈿袖,一聲金縷,卷茵停舞,側火分茶。笑盈盈,濺湯溫翠碗,折印啟緗紗。玉筍緩搖,雲頭初起,竹龍停戰,雨腳微斜。
清風生兩腋,塵埃盡,留白雪、長黃芽。解使芝眉長秀,潘鬢休華。想竹宮異日,袞衣寒夜,小團分賜,新樣金花。還記玉麟春色,曾在仙家。
富貴人家的夜宴,酒闌歌舞歇,正是分茶時,主持分茶的還是位美女;她技藝高超,笑語盈盈,不慌不忙,纖如玉筍的手下,起落間有雲起龍飛之妙。這樣的茶湯,喝下去後真是清風生兩腋,簡直能讓人永保青春。那如此精絕的小團茶,又從哪裡來?自然是皇上御賜的;而這茶樹的種子,是仙人家裡的。這場浩大的分茶情境,反映著宋代人心目中的極品人生:既富且貴,青春長駐,紅袖添香,還要閒適風雅。
既然說到:茶葉是皇帝御賜的。那麼分茶中真正的絕頂高手,自然要數當時的皇帝——宋徽宗趙佶。他的寵臣蔡京在〈延福宮曲宴記〉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宣和二年(公元一一二零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於延福宮……上命近侍限茶具,親自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盞面,如疏星朗月。顧諸臣曰:『此自布茶。飲畢皆頓首謝。』」徽宗親自分茶讓群臣觀賞,日月星辰都在茶盞中展現,似乎是一位印象派大師的傑作,這也許稱得上是分茶的最高境界吧。
宋朝人就是這樣,在回味無窮的品茶中,度過了數個春秋,風華了一個朝代,對於現代人快速的生活節奏來說,學習宋人品茶,倒是一種調節的好方法——那就用青瓷沖一盞香茶,在茶香與瓷香交融間,且當一回宋代人吧。
一壺好茶,就可解萬霎憂愁,心情也頓時開朗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