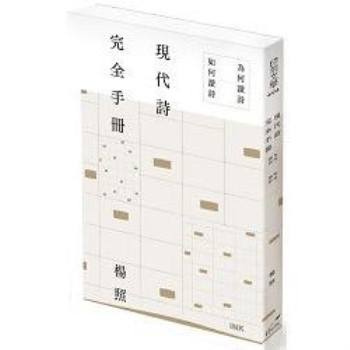當時正年輕
「……當時正年輕,真的是年輕,日間再累,一覺睡過來,又是一條好漢。還記得當年隊上有小倆口結婚,大家鬧就鬧到半夜,第二天天還沒亮,新媳婦就跑到場上獨自大聲控訴新郎倌一夜搞了她八回,不知道是得意呢還是憤恨。隊上的人都在屋裡笑,新郎倌還不是天亮後扛個鋤頭上山,有說有笑地挖了一天的地?這就叫年輕。
「年輕氣盛,年輕自然氣盛,元氣足。元氣是,不足就狂,年輕的時候狂起來還算好看,二十五歲以後再狂,沒人理了。孔子晚年有狂的時候,但他處的時代年輕。」
這是阿城說的,最近讀到的。讓我想起許多年前讀過福婁拜的《情感教育》,整本小說最後一段故事。
Frederic遇到了老朋友Deslauriers,回憶當年在學校的時光。記起來有一個地方,大家稱之為「土耳其女人那裡」,其實那個女人名字叫Eoraide Turc,可是以訛傳訛,很多人真的以為她是個信奉回教的土耳其人,結果給她開的妓院平添幾分異國情調的吸引力。
福婁拜如此描述那個地方:身著白色長袍,頰上塗著胭脂,戴著長耳環的女孩們,有行人經過時,她們習慣輕敲窗櫺,到了晚上她們就站在門階上以低啞的聲音輕唱。
年輕的Frederic和Deslauriers去燙了髮,繞進貴婦人的花園裡偷摘了花,轉啊轉,轉進了「土耳其女人那裡」。Frederic要將花獻給那裡的女人,然而天熱、害怕、加上罪惡感、加上從來沒有一次看到那麼多可供他挑選的女人,種種因素使得他面色青白,一句話都講不出來。於是成群的妓女鬨然大笑,Frederic嚇得落荒而逃,因為錢都在Frederic身上,Deslauriers也只好跟著跑出來。他們其實什麼都沒做,可是有人看見他們跑出來的身影,於是他們上妓院的事在地方連傳了三年還沒平息。
想起這些,最後Frederic說:「那是我們一生最快樂的時刻。」整本小說結束在Deslauriers原原本本地複誦 Frederic說的:「那是我們一生最快樂的時刻。」
我是在高中畢業那年讀《情感教育》的,就是你現在的年紀。好幾年,一群妓女輕敲窗櫺、低聲唱歌的形象環繞在我腦海裡。於是我們幾個人去了一趟華西街,刻意故作鎮定地走過暗巷,最後忍不住拔腿狂奔、落荒而逃。可是我們的落荒而逃中,絕對沒有Frederic他們感受的那種快樂,我們是被完全不在預期中的醜陋給嚇跑的。非但沒有白袍沒有低啞的歌聲,而且正因為帶著對白袍與低啞歌聲的憧憬,使得那街上的景物與聲響,更讓人難以忍受。去過華西街之後沒幾天,我們出發去中部遊玩。先去了溪頭,但是只待了一晚,就離開了,覺得溪頭找不到真正好玩的。我們晃啊晃,在幾個城鎮閒晃了好幾天,晃到了大甲。在喝鮮美的蚵仔湯時,老闆告訴我們不遠的大安有個海水浴場,而且大甲最好最當令的就是西瓜。於是那個晚上,我們半夜出發,一人手上捧著一顆西瓜,散步夜遊到大安海邊。
我已經不記得到底那條路有多遠了,只記得走到時已經精疲力盡,走到了才發現海水浴場晚上根本不開放的,而且連我們這樣鑽進鑽出多少火車站、遊樂場,翻過多少次學校圍牆的人都找不到缺口可以突破。我們只好百無聊賴地坐在唯一有燈的地方──派出所的門口,把西瓜敲開來吃。唯一看得到的景色,除了那個一樣百無聊賴,而且拒絕和我們分享西瓜的警員之外,只有天空中奇幻的海雲。
我們對著海雲聊天。聊到天快亮了才拖著步伐走向大安火車站。等火車的時候,我們累得眼睛都睜不開了,突然間H用近乎夢囈的聲音叫我,說:「看,我看到天空上有一句詩。一句奇怪的詩。」我奮力張眼,竟然真的在太陽即將升起的黎明天色裡,感應到了一句詩,一句我知道卻無法說出來寫下來的詩。像個小小的、無從解釋也無需解釋的神蹟。年輕的神蹟。
那是我們一生最快樂的時刻,因為有詩而年輕氣壯的時刻。
詩的不可解,不可解的詩
在海灘陷落月暈昇起之前
我已經思索過了樹與淚與真理
在如垂淚般降著暴雨的森林
在痛哭後失神空洞的
無可辯白命運裡……
這是十八歲那年夏天,度過一個疲憊不眠的夜,我一抬頭在清晨遠空雲彩上看到的四句詩。不可能的經驗,然而無法忘懷。
那時候,我已經寫過許多詩了。我已經明白自己不是個天才型的詩人,我偷偷最喜歡的故事是李賀的苦吟:騎著驢子在街衢間不停地遊晃,有了一兩句詩的靈感就匆匆地寫下來丟進行囊裡。我總覺得李賀之所以需要驢子需要街道,正因為沒有那種天啟般的聲音在腦中響起,告訴他多到讓他的手他的筆來不及抄記的眾多詩篇,或許短小靈巧到只有一句,或許龐大巨帙至千行。天才詩人應該都是這樣的。李賀聽不見那個聲音,所以必須看到行人看到市招看到楊柳或沙塵暴,才有辦法想出詩句來。就像我聽不見那個聲音,我只能不斷讀書、讀別人寫過的詩,從中間裁剪、焠煉出自己的句子。我也曾經想假裝自己幸運到聽見那個超越的聲音,假裝即席洋洋灑灑一首其實是前晚苦吟背下來的詩,然而很快就洞悉了其中的無聊與無妄。畢竟除了自己以外,還能去假裝給誰看呢?
然而那天清晨,在一個疲憊不眠的夜之後,我真的看到那四句遙遠浮顯在天空上的詩。當然是幻影,當然是不眠與疲憊製造的幻影,可是它們看起來如此真實。那不只是抽象的字句,有著一筆一畫明確的形狀。更不可解的,那字體看起來遠比十八歲的我寫出來的幼稚,有一種掙扎勉強的笨拙,笨拙到讓我覺得不好意思逼視,卻又在醜陋中傳遞一份新鮮與興奮。
那個字體,不只是詩句,一直纏擾著我。在從大甲走海線回台北的火車上,我幾度幾乎入睡,守在夢與醒間的門關上的,竟然就是這字體。似我又非我的字體讓我一再醒來。
我彷彿回到更早更多年前,最初與字相遭遇,學習駕御字、掌握字的童稚心境裡,一種自己以為已經完全遺忘失落了的狀態。「在那個時代,……字母一個接一個被寫出,要不是歪歪扭扭駝著背,就是自命不凡地表現優美。在那個時代,拼寫是一場戲劇性事件,是我們的教養在一個詞內進行的戲劇性事件。」這是多年以後,我在Gaston Bachelard的《夢想的詩學》裡讀來的一段話。是了,就是那樣戲劇性時期的印記。
那四行詩本身也是不可解的。迥異於我自己有意識創作的其他詩句,我完全不明瞭這四句詩的來龍去脈。我不知道這詩是怎樣發想的,更不清楚各行次序安排與意象間的彼此關聯。
可是我又很清楚,這絕對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人的詩。只能是我的。它有那麼清楚的財產印記。那種句式、那種組構樹與淚與真理的三角關係,一個自然物件、一個人體動作加一個抽象名詞並列的方式,是十八歲的我所慣用的。還有並列之後繼而將它們兩兩結合迴旋成句的展開,也是十八歲的我所慣用的。更重要的,我在這四句詩裡立即讀到只能在自己體內感應的熟悉。明明是我的,卻對我展示著不可能。這是最大的神祕、最大的謎。讓你不能走開不能掉頭不顧的謎與神祕。我在那瞬間,領悟到了現在正在苦惱著試圖要讀詩的你的最大問題的答案。如果詩是難解、不可解的,要如何評判詩的好壞?我們讀不懂的詩,就是壞詩嗎?讀不懂我們憑什麼評斷那是壞詩?可是倒過來,難道寫出讓人不解不能解的詩,人家就不能指責那是首壞詩了嗎?
我當時的領悟是,詩或許不可解,然而好詩必須提供豐富的暗示,讓你覺得在眼底撩亂的不可解中,藏著可解的路徑。好詩引誘著你從不可解中努力尋求可解,它讓你就是不能走開不能掉頭不顧它的神祕與謎。它誘惑著人去找不可解中的可解。你進入詩,於是詩也進入了你。
詩是公開的隱藏
契訶夫(Anton Chekhov)寫過一篇題名為〈吻〉的小說,小說裡描寫一團俄國士兵在行軍中經過一座小城。晚上團裡十九名軍官都受邀到城裡一位退役將領家中喝茶,其中有一位年輕、害羞、極度缺乏自信的軍官叫Ryabovitch是故事的主角。
在聚會過程中,賓客們開始跳起舞來,Ryabovitch覺得很不自在,因為他一輩子從來沒有跳過舞,一輩子從來沒有過用手抱住女人的腰的經驗。為了避免這種因身體動作拙劣帶來的尷尬,他跟其他幾個人去了彈子房,可是到了那裡他還是不自在,因為他也不會打撞球,老是擋到路礙著人家。沒辦法,他只好再回大家跳舞的大廳去。
就在這過程中,Ryabovitch顯然記錯路轉錯了彎,闖進了一間小房間裡。在黑暗中,突然有一個年輕女孩衝了過來,口中唸著:「終於等到了!」,在Ryabovitch右頰靠近鬍子的部位吻了一下。那女孩立刻察覺到自己親錯人了,來的並不是她苦候幽會的對象,尖叫一聲逃開了。頂多只有幾秒鐘,只有一個輕輕的吻。
這樣幾秒鐘,卻對Ryabovitch產生不可思議的變化。契訶夫形容他剛剛被女孩帶香氣的雙臂短暫環繞的脖子似乎塗上了神聖的油膏,右頰被吻的部位則是一片冰涼,「一股新奇的感覺湧滿了他整個人,而且愈來愈奇怪……他忘記了自己有著……『毫不起眼的外表』……」
第二天,離開小城前行的路上,Ryabovitch依舊被包圍在那個吻的神祕力量裡。到了晚上,他終於忍不住了,把他的奇遇講給同伴們聽。他講得很仔細,畢竟這幾秒鐘的事已經在他腦中迴旋了幾百次幾千次。然而讓他自己驚訝、繼而難過的是,不管他說得再怎麼仔細,他的「豔遇」一下子就說完了。沒了。講不下去了。他原本還以為自己話匣子一開能夠一直滔滔不絕地講到第二天早上哩。
更讓他驚訝、更讓他難過的是,他的同伴竟然沒有被感動,也沒表現出多大的興趣。人家轉而去聽真正更「香豔」的故事,怎樣在火車上和陌生女子做愛的故事。
我們每個人都曾是那個驚訝、難過、失望的Ryabo-vitch。或者說我們一生中總會經歷過好幾次Ryabovitch 的這種困窘。我們自己覺得天大地大,自己在心裡迴旋過千百次的最快樂最悲痛最甜美最壯麗最哀傷最淒清的經驗,我們覺得自己的神經系統都不足以承擔的巨大撼動,忍不住想要講給別人聽,然而一開口,一切就變質了。我們找不到適當的語言、對的方法來訴說,來傳達那種快樂悲痛甜美壯麗哀傷與淒清的程度。
從一個意義上看,正是在這種困窘環境裡,才有了文學的需求。Ryabovitch無法轉述、傳達的感受,我們藉著契訶夫的小說之筆領略到了。當場親自聽Ryabovitch講故事聽得索然無味的俄軍士兵們不能懂得的「靈光」(epi-phany),契訶夫小說的讀者卻在百年之後、千里之遠懂得了,這是小說的魔力。把不能說、說不清楚的來龍去脈,以全新的角度洞悉了講得透徹明白,這是小說家的當行本事。
不過別忘了,在這種困窘狀況裡,文學還提供了另一種工具,那就是詩。如果說小說是要讓Ryabovitch感受的吻,成為眾人都能感受的共同啟示,那詩就是讓我們可以選擇將那吻保留在神祕的光暈裡。小說訴說,詩卻隱藏。詩的隱藏不是不說,讓吻只留在Ryabovitch腦中,詩是一種公開的隱藏,一種帶點惡意的挑逗,詩告訴人家,我這裡藏著特別的東西,我是這樣藏那樣藏,藏來藏去後你勉強可以看到這一角那一角的暗示,或模糊輪廓的外形,然而真正的是什麼,我死也不會講明。
Ryabovitch的苦惱失望,來自於他沒有契訶夫那麼熟練的本事訴說,卻又沒有學過詩人的公開隱藏的技巧。
也許有一天,可以找到這樣一首詩
沒有哪一首詩是「唯一的詩」,對我而言。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開始詩的尋旅,正是因為生活當中有太多訊息與感覺,無法用一般的方式記錄、存留。詩具有一種特殊的,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形式意義,只有當其他形式都無效都無能為力時,我們才乞靈於詩。當然這是我的偏見,無可救藥的偏見。在我眼中看去,各種不同的記錄文類排成一列,一種文類後面放著另一種文類,固定的次序固定的功能限制。直接、淺白的日常語言、一般報導無法捕捉的,我們才訴諸於文學語言、訴諸於探索思想與感覺的散文。散文也不足以提供所需的意義工具時,我們只好向虛構的小說求救,希望藉不同的、變幻的敘述聲音給自己更大的空間。如果連小說都無能為力時呢?幸好我們還有詩。
詩最不同的地方,就在它不直接訴說。詩用不訴說來訴說,所以才能夠保留住那些一旦被訴說就破壞了的經驗與心情。用不存在來表達存在,有時是最能接近存在底層最迂迴卻又唯一的弔詭路徑。與詩最接近的,是寓言,卡夫卡寫的那種寓言;在一個荒涼、莫名的早晨,不知為了什麼匆忙趕路向道旁警察詢問時間,那樣似夢非夢的寓言。與詩最接近的,是一種質疑理性的哲學,莊子寫的那種哲學;夢了蝴蝶又醒了,醒了卻又不確定其實是蝴蝶夢成了人的哲學。
作為一種文類形式,詩介於存在與不存在間,還有另一個理由。真正具體以字句與字句、行與行整齊連綴的詩篇,遠遠少於我們日日夜夜尋覓著,理應存在的想像的詩。這又是只會發生在詩身上的奇異失落。日子過著過著,我們不會覺得這裡少了一篇散文、少了一篇小說;可是時時刻刻我會感到內在的某種虛空與飢渴,覺得在這裡,面對這樣東西、這個人、這份感動或恐懼、這道閃逝的光芒,應該有一首詩、或一句詩,應該有的。
這就是為什麼對我而言,詩不是既成的作品的羅列,而是不間斷不停歇的追索。上窮碧落下黃泉,念茲在茲地要找到最最適切於鑲嵌在這個時空定點上的詩。
所以詩沒有唯一的。沒有任何一首已經寫完的詩,可以應付如此龐大的虛空與飢渴。你問我,有沒有哪一首詩在我生命中是唯一的,我只能誠實地回答沒有。因為我始終活在詩所製造,或說詩所逗引出來的龐大虛空與飢渴中,永遠無法饜足。
甚至害怕饜足。
大水災剛過的日子,去海邊走了一趟。除了怵目驚心的道路坍方、黃泥暴露的景象之外,看到最多的,就是一堆堆沖上岸來的流木。關於大雨所造成傷害,那殘破那危險甚至那人與大自然相處上的反省,我知道該如何形容如何描述如何論理如何留存教訓。可是那些顯然都歷經奇異的山水過程的流木,就讓我感到強大的詩的召喚。該有首詩,至少有句詩,彰示流木與我們之間的關係。什麼樣的詩,我不知道。我知道不會是洛夫的〈漂木〉,不是:
……這塊木頭
已非今日之是
亦非昨日之非
極其簡單的一根
行將腐朽的木頭,曾夜夜
攬鏡自照
做著棟樑之夢的
追逐年輪而終於迷失於時間之外
的木頭
這樣的詩句。
也許會比較接近村上春樹寫的〈有熨斗的風景〉,裡面講的「自由的火」吧。流木燒起來的火,和瓦斯爐的火、打火機的火、一般的營火不一樣,而是一種在自由場所裡燒起來的形狀自由的火,因為自由,所以可以顯映看火的人的心情。
從流木燒的火,回推設想流木的自由。這樣也許可以有一首符合我在海邊的心情的詩吧。我如是想著,如是尋找著。或許有一天可以找到。當然也有可能永遠找不到這樣一首詩。
「……當時正年輕,真的是年輕,日間再累,一覺睡過來,又是一條好漢。還記得當年隊上有小倆口結婚,大家鬧就鬧到半夜,第二天天還沒亮,新媳婦就跑到場上獨自大聲控訴新郎倌一夜搞了她八回,不知道是得意呢還是憤恨。隊上的人都在屋裡笑,新郎倌還不是天亮後扛個鋤頭上山,有說有笑地挖了一天的地?這就叫年輕。
「年輕氣盛,年輕自然氣盛,元氣足。元氣是,不足就狂,年輕的時候狂起來還算好看,二十五歲以後再狂,沒人理了。孔子晚年有狂的時候,但他處的時代年輕。」
這是阿城說的,最近讀到的。讓我想起許多年前讀過福婁拜的《情感教育》,整本小說最後一段故事。
Frederic遇到了老朋友Deslauriers,回憶當年在學校的時光。記起來有一個地方,大家稱之為「土耳其女人那裡」,其實那個女人名字叫Eoraide Turc,可是以訛傳訛,很多人真的以為她是個信奉回教的土耳其人,結果給她開的妓院平添幾分異國情調的吸引力。
福婁拜如此描述那個地方:身著白色長袍,頰上塗著胭脂,戴著長耳環的女孩們,有行人經過時,她們習慣輕敲窗櫺,到了晚上她們就站在門階上以低啞的聲音輕唱。
年輕的Frederic和Deslauriers去燙了髮,繞進貴婦人的花園裡偷摘了花,轉啊轉,轉進了「土耳其女人那裡」。Frederic要將花獻給那裡的女人,然而天熱、害怕、加上罪惡感、加上從來沒有一次看到那麼多可供他挑選的女人,種種因素使得他面色青白,一句話都講不出來。於是成群的妓女鬨然大笑,Frederic嚇得落荒而逃,因為錢都在Frederic身上,Deslauriers也只好跟著跑出來。他們其實什麼都沒做,可是有人看見他們跑出來的身影,於是他們上妓院的事在地方連傳了三年還沒平息。
想起這些,最後Frederic說:「那是我們一生最快樂的時刻。」整本小說結束在Deslauriers原原本本地複誦 Frederic說的:「那是我們一生最快樂的時刻。」
我是在高中畢業那年讀《情感教育》的,就是你現在的年紀。好幾年,一群妓女輕敲窗櫺、低聲唱歌的形象環繞在我腦海裡。於是我們幾個人去了一趟華西街,刻意故作鎮定地走過暗巷,最後忍不住拔腿狂奔、落荒而逃。可是我們的落荒而逃中,絕對沒有Frederic他們感受的那種快樂,我們是被完全不在預期中的醜陋給嚇跑的。非但沒有白袍沒有低啞的歌聲,而且正因為帶著對白袍與低啞歌聲的憧憬,使得那街上的景物與聲響,更讓人難以忍受。去過華西街之後沒幾天,我們出發去中部遊玩。先去了溪頭,但是只待了一晚,就離開了,覺得溪頭找不到真正好玩的。我們晃啊晃,在幾個城鎮閒晃了好幾天,晃到了大甲。在喝鮮美的蚵仔湯時,老闆告訴我們不遠的大安有個海水浴場,而且大甲最好最當令的就是西瓜。於是那個晚上,我們半夜出發,一人手上捧著一顆西瓜,散步夜遊到大安海邊。
我已經不記得到底那條路有多遠了,只記得走到時已經精疲力盡,走到了才發現海水浴場晚上根本不開放的,而且連我們這樣鑽進鑽出多少火車站、遊樂場,翻過多少次學校圍牆的人都找不到缺口可以突破。我們只好百無聊賴地坐在唯一有燈的地方──派出所的門口,把西瓜敲開來吃。唯一看得到的景色,除了那個一樣百無聊賴,而且拒絕和我們分享西瓜的警員之外,只有天空中奇幻的海雲。
我們對著海雲聊天。聊到天快亮了才拖著步伐走向大安火車站。等火車的時候,我們累得眼睛都睜不開了,突然間H用近乎夢囈的聲音叫我,說:「看,我看到天空上有一句詩。一句奇怪的詩。」我奮力張眼,竟然真的在太陽即將升起的黎明天色裡,感應到了一句詩,一句我知道卻無法說出來寫下來的詩。像個小小的、無從解釋也無需解釋的神蹟。年輕的神蹟。
那是我們一生最快樂的時刻,因為有詩而年輕氣壯的時刻。
詩的不可解,不可解的詩
在海灘陷落月暈昇起之前
我已經思索過了樹與淚與真理
在如垂淚般降著暴雨的森林
在痛哭後失神空洞的
無可辯白命運裡……
這是十八歲那年夏天,度過一個疲憊不眠的夜,我一抬頭在清晨遠空雲彩上看到的四句詩。不可能的經驗,然而無法忘懷。
那時候,我已經寫過許多詩了。我已經明白自己不是個天才型的詩人,我偷偷最喜歡的故事是李賀的苦吟:騎著驢子在街衢間不停地遊晃,有了一兩句詩的靈感就匆匆地寫下來丟進行囊裡。我總覺得李賀之所以需要驢子需要街道,正因為沒有那種天啟般的聲音在腦中響起,告訴他多到讓他的手他的筆來不及抄記的眾多詩篇,或許短小靈巧到只有一句,或許龐大巨帙至千行。天才詩人應該都是這樣的。李賀聽不見那個聲音,所以必須看到行人看到市招看到楊柳或沙塵暴,才有辦法想出詩句來。就像我聽不見那個聲音,我只能不斷讀書、讀別人寫過的詩,從中間裁剪、焠煉出自己的句子。我也曾經想假裝自己幸運到聽見那個超越的聲音,假裝即席洋洋灑灑一首其實是前晚苦吟背下來的詩,然而很快就洞悉了其中的無聊與無妄。畢竟除了自己以外,還能去假裝給誰看呢?
然而那天清晨,在一個疲憊不眠的夜之後,我真的看到那四句遙遠浮顯在天空上的詩。當然是幻影,當然是不眠與疲憊製造的幻影,可是它們看起來如此真實。那不只是抽象的字句,有著一筆一畫明確的形狀。更不可解的,那字體看起來遠比十八歲的我寫出來的幼稚,有一種掙扎勉強的笨拙,笨拙到讓我覺得不好意思逼視,卻又在醜陋中傳遞一份新鮮與興奮。
那個字體,不只是詩句,一直纏擾著我。在從大甲走海線回台北的火車上,我幾度幾乎入睡,守在夢與醒間的門關上的,竟然就是這字體。似我又非我的字體讓我一再醒來。
我彷彿回到更早更多年前,最初與字相遭遇,學習駕御字、掌握字的童稚心境裡,一種自己以為已經完全遺忘失落了的狀態。「在那個時代,……字母一個接一個被寫出,要不是歪歪扭扭駝著背,就是自命不凡地表現優美。在那個時代,拼寫是一場戲劇性事件,是我們的教養在一個詞內進行的戲劇性事件。」這是多年以後,我在Gaston Bachelard的《夢想的詩學》裡讀來的一段話。是了,就是那樣戲劇性時期的印記。
那四行詩本身也是不可解的。迥異於我自己有意識創作的其他詩句,我完全不明瞭這四句詩的來龍去脈。我不知道這詩是怎樣發想的,更不清楚各行次序安排與意象間的彼此關聯。
可是我又很清楚,這絕對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人的詩。只能是我的。它有那麼清楚的財產印記。那種句式、那種組構樹與淚與真理的三角關係,一個自然物件、一個人體動作加一個抽象名詞並列的方式,是十八歲的我所慣用的。還有並列之後繼而將它們兩兩結合迴旋成句的展開,也是十八歲的我所慣用的。更重要的,我在這四句詩裡立即讀到只能在自己體內感應的熟悉。明明是我的,卻對我展示著不可能。這是最大的神祕、最大的謎。讓你不能走開不能掉頭不顧的謎與神祕。我在那瞬間,領悟到了現在正在苦惱著試圖要讀詩的你的最大問題的答案。如果詩是難解、不可解的,要如何評判詩的好壞?我們讀不懂的詩,就是壞詩嗎?讀不懂我們憑什麼評斷那是壞詩?可是倒過來,難道寫出讓人不解不能解的詩,人家就不能指責那是首壞詩了嗎?
我當時的領悟是,詩或許不可解,然而好詩必須提供豐富的暗示,讓你覺得在眼底撩亂的不可解中,藏著可解的路徑。好詩引誘著你從不可解中努力尋求可解,它讓你就是不能走開不能掉頭不顧它的神祕與謎。它誘惑著人去找不可解中的可解。你進入詩,於是詩也進入了你。
詩是公開的隱藏
契訶夫(Anton Chekhov)寫過一篇題名為〈吻〉的小說,小說裡描寫一團俄國士兵在行軍中經過一座小城。晚上團裡十九名軍官都受邀到城裡一位退役將領家中喝茶,其中有一位年輕、害羞、極度缺乏自信的軍官叫Ryabovitch是故事的主角。
在聚會過程中,賓客們開始跳起舞來,Ryabovitch覺得很不自在,因為他一輩子從來沒有跳過舞,一輩子從來沒有過用手抱住女人的腰的經驗。為了避免這種因身體動作拙劣帶來的尷尬,他跟其他幾個人去了彈子房,可是到了那裡他還是不自在,因為他也不會打撞球,老是擋到路礙著人家。沒辦法,他只好再回大家跳舞的大廳去。
就在這過程中,Ryabovitch顯然記錯路轉錯了彎,闖進了一間小房間裡。在黑暗中,突然有一個年輕女孩衝了過來,口中唸著:「終於等到了!」,在Ryabovitch右頰靠近鬍子的部位吻了一下。那女孩立刻察覺到自己親錯人了,來的並不是她苦候幽會的對象,尖叫一聲逃開了。頂多只有幾秒鐘,只有一個輕輕的吻。
這樣幾秒鐘,卻對Ryabovitch產生不可思議的變化。契訶夫形容他剛剛被女孩帶香氣的雙臂短暫環繞的脖子似乎塗上了神聖的油膏,右頰被吻的部位則是一片冰涼,「一股新奇的感覺湧滿了他整個人,而且愈來愈奇怪……他忘記了自己有著……『毫不起眼的外表』……」
第二天,離開小城前行的路上,Ryabovitch依舊被包圍在那個吻的神祕力量裡。到了晚上,他終於忍不住了,把他的奇遇講給同伴們聽。他講得很仔細,畢竟這幾秒鐘的事已經在他腦中迴旋了幾百次幾千次。然而讓他自己驚訝、繼而難過的是,不管他說得再怎麼仔細,他的「豔遇」一下子就說完了。沒了。講不下去了。他原本還以為自己話匣子一開能夠一直滔滔不絕地講到第二天早上哩。
更讓他驚訝、更讓他難過的是,他的同伴竟然沒有被感動,也沒表現出多大的興趣。人家轉而去聽真正更「香豔」的故事,怎樣在火車上和陌生女子做愛的故事。
我們每個人都曾是那個驚訝、難過、失望的Ryabo-vitch。或者說我們一生中總會經歷過好幾次Ryabovitch 的這種困窘。我們自己覺得天大地大,自己在心裡迴旋過千百次的最快樂最悲痛最甜美最壯麗最哀傷最淒清的經驗,我們覺得自己的神經系統都不足以承擔的巨大撼動,忍不住想要講給別人聽,然而一開口,一切就變質了。我們找不到適當的語言、對的方法來訴說,來傳達那種快樂悲痛甜美壯麗哀傷與淒清的程度。
從一個意義上看,正是在這種困窘環境裡,才有了文學的需求。Ryabovitch無法轉述、傳達的感受,我們藉著契訶夫的小說之筆領略到了。當場親自聽Ryabovitch講故事聽得索然無味的俄軍士兵們不能懂得的「靈光」(epi-phany),契訶夫小說的讀者卻在百年之後、千里之遠懂得了,這是小說的魔力。把不能說、說不清楚的來龍去脈,以全新的角度洞悉了講得透徹明白,這是小說家的當行本事。
不過別忘了,在這種困窘狀況裡,文學還提供了另一種工具,那就是詩。如果說小說是要讓Ryabovitch感受的吻,成為眾人都能感受的共同啟示,那詩就是讓我們可以選擇將那吻保留在神祕的光暈裡。小說訴說,詩卻隱藏。詩的隱藏不是不說,讓吻只留在Ryabovitch腦中,詩是一種公開的隱藏,一種帶點惡意的挑逗,詩告訴人家,我這裡藏著特別的東西,我是這樣藏那樣藏,藏來藏去後你勉強可以看到這一角那一角的暗示,或模糊輪廓的外形,然而真正的是什麼,我死也不會講明。
Ryabovitch的苦惱失望,來自於他沒有契訶夫那麼熟練的本事訴說,卻又沒有學過詩人的公開隱藏的技巧。
也許有一天,可以找到這樣一首詩
沒有哪一首詩是「唯一的詩」,對我而言。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開始詩的尋旅,正是因為生活當中有太多訊息與感覺,無法用一般的方式記錄、存留。詩具有一種特殊的,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形式意義,只有當其他形式都無效都無能為力時,我們才乞靈於詩。當然這是我的偏見,無可救藥的偏見。在我眼中看去,各種不同的記錄文類排成一列,一種文類後面放著另一種文類,固定的次序固定的功能限制。直接、淺白的日常語言、一般報導無法捕捉的,我們才訴諸於文學語言、訴諸於探索思想與感覺的散文。散文也不足以提供所需的意義工具時,我們只好向虛構的小說求救,希望藉不同的、變幻的敘述聲音給自己更大的空間。如果連小說都無能為力時呢?幸好我們還有詩。
詩最不同的地方,就在它不直接訴說。詩用不訴說來訴說,所以才能夠保留住那些一旦被訴說就破壞了的經驗與心情。用不存在來表達存在,有時是最能接近存在底層最迂迴卻又唯一的弔詭路徑。與詩最接近的,是寓言,卡夫卡寫的那種寓言;在一個荒涼、莫名的早晨,不知為了什麼匆忙趕路向道旁警察詢問時間,那樣似夢非夢的寓言。與詩最接近的,是一種質疑理性的哲學,莊子寫的那種哲學;夢了蝴蝶又醒了,醒了卻又不確定其實是蝴蝶夢成了人的哲學。
作為一種文類形式,詩介於存在與不存在間,還有另一個理由。真正具體以字句與字句、行與行整齊連綴的詩篇,遠遠少於我們日日夜夜尋覓著,理應存在的想像的詩。這又是只會發生在詩身上的奇異失落。日子過著過著,我們不會覺得這裡少了一篇散文、少了一篇小說;可是時時刻刻我會感到內在的某種虛空與飢渴,覺得在這裡,面對這樣東西、這個人、這份感動或恐懼、這道閃逝的光芒,應該有一首詩、或一句詩,應該有的。
這就是為什麼對我而言,詩不是既成的作品的羅列,而是不間斷不停歇的追索。上窮碧落下黃泉,念茲在茲地要找到最最適切於鑲嵌在這個時空定點上的詩。
所以詩沒有唯一的。沒有任何一首已經寫完的詩,可以應付如此龐大的虛空與飢渴。你問我,有沒有哪一首詩在我生命中是唯一的,我只能誠實地回答沒有。因為我始終活在詩所製造,或說詩所逗引出來的龐大虛空與飢渴中,永遠無法饜足。
甚至害怕饜足。
大水災剛過的日子,去海邊走了一趟。除了怵目驚心的道路坍方、黃泥暴露的景象之外,看到最多的,就是一堆堆沖上岸來的流木。關於大雨所造成傷害,那殘破那危險甚至那人與大自然相處上的反省,我知道該如何形容如何描述如何論理如何留存教訓。可是那些顯然都歷經奇異的山水過程的流木,就讓我感到強大的詩的召喚。該有首詩,至少有句詩,彰示流木與我們之間的關係。什麼樣的詩,我不知道。我知道不會是洛夫的〈漂木〉,不是:
……這塊木頭
已非今日之是
亦非昨日之非
極其簡單的一根
行將腐朽的木頭,曾夜夜
攬鏡自照
做著棟樑之夢的
追逐年輪而終於迷失於時間之外
的木頭
這樣的詩句。
也許會比較接近村上春樹寫的〈有熨斗的風景〉,裡面講的「自由的火」吧。流木燒起來的火,和瓦斯爐的火、打火機的火、一般的營火不一樣,而是一種在自由場所裡燒起來的形狀自由的火,因為自由,所以可以顯映看火的人的心情。
從流木燒的火,回推設想流木的自由。這樣也許可以有一首符合我在海邊的心情的詩吧。我如是想著,如是尋找著。或許有一天可以找到。當然也有可能永遠找不到這樣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