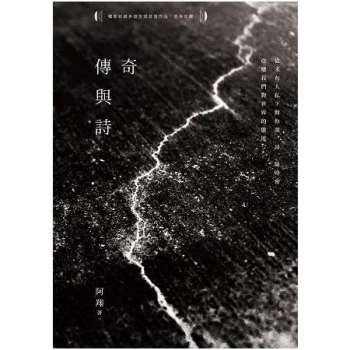▍自序
這是我第一本在臺灣出版的詩集,心情不僅僅誠惶誠恐,更多的是欣喜、悲哀交織,一時無言以表。
重新打量這部回歸繁體字的詩歌,幾乎感到陌生,但又有一種久違的親近感湧上來,畢竟離開太久了。或許我可以這麼想,我寫下的詩,通過繁體字脫胎換骨將獲得嬰兒般地新生。
我是詩人,在大陸被貼上太多的標籤:70後,旅人,自由職業者,啤酒主義者,民刊收藏家,戲劇人,攝影發燒友……,但我終究是一個隱密的詩人,或者說是一個矛盾的詩人。一方面,在有限的詩歌圈,我這個身分是公開的,可以說一覽無遺;另一方面,在詩歌圈之外的現實中,我卻刻意隱瞞了這個身分,就像靈魂在人群中不輕易外露出來,我把自己視為芸芸眾生的一員,低調而平穩地生活。這樣說並不是強調詩人的分裂,而是說,詩歌是一種自我的修遠。
我不喜歡追憶什麼,但有必要說一下,在我小的時候,因發高燒而誤打鏈黴素(streptomycin),損害了聽覺神經,從而影響了我說話表達的能力。至今我有著兩耳不同程度的弱聽,戴上助聽器也是無濟於事,因為我聽到的「聲音」遠遠大過了「語音」。所以,我與世界的溝通,只能依靠筆和紙,通過一筆一劃,幾乎不必思考什麼,而能把詩性的東西完整表達出來;但是我開口一說話,往往要費半天勁兒,一邊思考一邊努力想說清晰點,結果顯得結結巴巴、含糊不清,雖然聽眾們用鼓勵的眼光看著我,甚至給予掌聲,但我不可避免湧起一陣挫敗感。
唯有沉默給予我內心的強大,給予我慰藉。或者說,不說話,才是一個人的完整。通過寫作,詩歌在靈魂的黑暗處發出隱約的光亮,哪怕是一閃而逝,這時候我顯得敏銳無比。在時間的消逝中,寫作仍然是「日日新」的修遠,即使掌握詩藝的祕密,它依然是永恆的祕密。就好像木匠掌握了技藝,但是再好的技藝,如果不是用於自己的創造,它最多按圖索驥重複前人的經驗。最困難的恰恰就是對經驗的超越。這是由內向外的伸展,一個世界的自足性、豐富及不可捉摸的神祕,在我身外,然而卻是與我內在地相關的。
我曾經說過,在浮躁而焦慮的時代,為倖存的詩寫作而不迴避自己的病情和現實的黑暗,詩歌才能完整地暴露缺陷。至今在我看來,這句話仍然有效,無不時刻提醒著我,不要掩飾什麼,詩人畢竟被驅趕於理想國之外。烏托邦是一個隱喻,寫作也是一個隱喻。
正值這部詩集出版,但願能得到一點點回音。在此我向世界深深地鞠躬,表達我的羞愧和謝意。
這是我第一本在臺灣出版的詩集,心情不僅僅誠惶誠恐,更多的是欣喜、悲哀交織,一時無言以表。
重新打量這部回歸繁體字的詩歌,幾乎感到陌生,但又有一種久違的親近感湧上來,畢竟離開太久了。或許我可以這麼想,我寫下的詩,通過繁體字脫胎換骨將獲得嬰兒般地新生。
我是詩人,在大陸被貼上太多的標籤:70後,旅人,自由職業者,啤酒主義者,民刊收藏家,戲劇人,攝影發燒友……,但我終究是一個隱密的詩人,或者說是一個矛盾的詩人。一方面,在有限的詩歌圈,我這個身分是公開的,可以說一覽無遺;另一方面,在詩歌圈之外的現實中,我卻刻意隱瞞了這個身分,就像靈魂在人群中不輕易外露出來,我把自己視為芸芸眾生的一員,低調而平穩地生活。這樣說並不是強調詩人的分裂,而是說,詩歌是一種自我的修遠。
我不喜歡追憶什麼,但有必要說一下,在我小的時候,因發高燒而誤打鏈黴素(streptomycin),損害了聽覺神經,從而影響了我說話表達的能力。至今我有著兩耳不同程度的弱聽,戴上助聽器也是無濟於事,因為我聽到的「聲音」遠遠大過了「語音」。所以,我與世界的溝通,只能依靠筆和紙,通過一筆一劃,幾乎不必思考什麼,而能把詩性的東西完整表達出來;但是我開口一說話,往往要費半天勁兒,一邊思考一邊努力想說清晰點,結果顯得結結巴巴、含糊不清,雖然聽眾們用鼓勵的眼光看著我,甚至給予掌聲,但我不可避免湧起一陣挫敗感。
唯有沉默給予我內心的強大,給予我慰藉。或者說,不說話,才是一個人的完整。通過寫作,詩歌在靈魂的黑暗處發出隱約的光亮,哪怕是一閃而逝,這時候我顯得敏銳無比。在時間的消逝中,寫作仍然是「日日新」的修遠,即使掌握詩藝的祕密,它依然是永恆的祕密。就好像木匠掌握了技藝,但是再好的技藝,如果不是用於自己的創造,它最多按圖索驥重複前人的經驗。最困難的恰恰就是對經驗的超越。這是由內向外的伸展,一個世界的自足性、豐富及不可捉摸的神祕,在我身外,然而卻是與我內在地相關的。
我曾經說過,在浮躁而焦慮的時代,為倖存的詩寫作而不迴避自己的病情和現實的黑暗,詩歌才能完整地暴露缺陷。至今在我看來,這句話仍然有效,無不時刻提醒著我,不要掩飾什麼,詩人畢竟被驅趕於理想國之外。烏托邦是一個隱喻,寫作也是一個隱喻。
正值這部詩集出版,但願能得到一點點回音。在此我向世界深深地鞠躬,表達我的羞愧和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