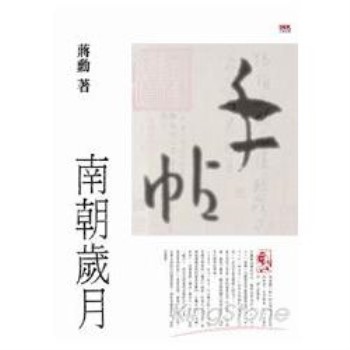第一輯 平復帖/選文一篇
1 火箸畫灰──《平復帖》種種
【我一方面閱讀諸家不同說法,但是晨起靜坐,還是與《平復帖》素面相見。細看那一張殘紙上墨痕斑剝,禿筆,沒有婉轉纖細的牽絲出鋒,沒有東晉王羲之書法的華麗秀美、飄逸神俊的璀璨光彩。但是《平復帖》頑強勁歛,有一種生命在劇痛中的糾纏扭曲,線條像廢棄鏽蝕的堡壘的鐵絲網,都是蒼苦荒涼的記憶。】
《平復帖》大概是這幾年在古文物領域被討論得最多的一件作品。
《平復帖》唐代就收入內府,宋代被定為是西晉陸機的真跡。北宋大書法家米芾曾經看過,用「火箸畫灰」四個字形容《平復帖》禿筆賊豪線條的蒼勁枯澀之美。宋徽宗有朱書題簽,「晉平原內史陸機士衡平復帖》,題簽下有雙龍小璽,四角有「政和」「宣龢」的押印。
《平復帖》在元代的收藏經過不十分清楚。明清時代曾經韓世能、韓逢禧父子、安儀周、梁清標等人收藏,綾邊隔水上都有收藏印記。董其昌在韓世能家看過,也留下跋尾的題識。
乾隆年間收入內府,後賜給皇十一子成親王永瑆。清末再轉入恭王府,流傳到溥心畬手上,隔水上也有「溥心畬鑑定書畫珍藏印」。溥心畬為了籌親人喪葬費,轉手賣給張伯駒,一九五六年,張伯駒把《平復帖》捐出,收藏於北京故宮。
啟功先生釋文
──── 一千年來定為陸機作品的《平復帖》似又重新需要釐清真正的作者,
或重新定位為晉代某一佚名文人的手跡了?
《平復帖》是漢代章草向晉代今草過渡的字體,古奧難懂,加上年久斑剝,字跡漫漶,很不容易辨認。啟功先生在六○年代釋讀了《平復帖》,雖然還有不同的看法,但目前已成為流傳最廣泛的釋文:
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以為慶。
《平復帖》開頭一段釋讀比較沒有歧異。大概是說:「彥先」身體衰弱生病,恐怕很難痊癒。初得病時,沒有想到會並到這麼嚴重。
「彥先」是信上提到的一個人,自宋以來,也因為這兩個字,引出了陸機與《平復帖》的關係,因為陸機有好朋友名叫「彥先」。
麻煩的是,陸機親近的朋友中有兩個都叫「彥先」,一個是顧榮,顧彥先;另一個是賀循,賀彥先,都是同樣出身吳國士族,又同時與陸機在西晉作官的朋友。
其實繼續探索下去,陸機的朋友中可能還不只兩個「彥先」。徐邦達先生就認為「平復帖」裡的「彥先」是另一個叫「全彥先」的人。這一點早在《昭明文選.李善注》裡就已經提到。文選裡有陸機陸雲兄弟為「彥先」寫的〈贈婦詩〉,〈李善注〉指出這個「彥先」不是顧榮顧彥先,而是全彥先。
三個「彥先」使探索《平復帖》的線索更為複雜,各家說法不一,一時沒有定論,這幾年隨著《平復帖》二○○三年在北京展出,二○○五年在上海展出,討論的人更多。有人根本否定《平復帖》是陸機所書,大概也以為依據信裡「彥先」兩個字,斷定《平復帖》是陸機真跡,而「彥先」此人是哪一個「彥先」還不清楚,寧可存疑。
但是各派說法都同意《平復帖》是西晉人墨書真跡,的確比王羲之傳世摹本更具斷代上的重要性。《平復帖》還是穩坐「墨皇」「帖祖」的位置。
啟功先生對《平復帖》的釋讀目前是最廣泛被接受的。他解讀的「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因為彥先病重,身體衰弱,正與《晉書.賀循傳》裡描述的「賀彥先」的身體多病衰弱相似,也自然會使人把彥先定為賀循。
但是《平復帖》裡的「彥先」,依據這麼一點點聯繫,就斷為「賀循」,當然還會使很多人迷惑。而因此連接上陸機,也一定會讓更多人對《平復帖》的真相繼續討論下去。二○○六年五月的《中國書法》期刊甚至有人提出──晉代讀書人為表示「榮耀祖先」,不少人都取名「彥先」,「彥先」是晉代文人非常普遍的名字。如果此說成立,《平復帖》上的「彥先」就不一定是顧榮或賀循,因此也不一定是陸機的朋友,一千年來定為陸機作品的《平復帖》又重新需要釐清真正的作者,或重新定位為晉代某一佚名文人的手跡了。
「佚名」書畫
────作為西晉人的墨跡是目前比較確定的結論,至少有了時代的斷代意義。
中國的書畫收藏一直習慣把作品歸類在名家之下。唐宋以前不落款的書畫,陸續被冠上名家的名字。許多幅山水冠上了「范寬」、「郭熙」;許多幅馬,被冠上了「韓幹」;許多幅仕女被冠上了「張萱」、「周昉」。當然,許多「帖」,就冠上了「王羲之」、「王獻之」。
沒有名家名字,似乎就失去了價值,使書畫的討論陷入盲點。連博物館的收藏都不能還原「不知名」、「佚名」「摹本」的標識,其實使大眾一開始就誤認了風格,書畫的鑑賞可能就越走越遠離真相。
許多人知道長期題簽標誌為王獻之的名作《中秋帖》,其實是宋代米芾的臨摹本,大家也習以為常把宋米芾的書法風格混淆成王獻之,相差六百年的美學書風也因此越來越難以釐清。
《平復帖》是不是陸機的作品尚在爭論中,但是作為西晉人的墨跡是比較確定的結論,至少有了時代的斷代意義。
右軍之前,元常之後
明代大鑑賞家董其昌在《平復帖》的跋裡說:「右軍以前,元常以後,為此數行,為希代寶。」「右軍」是王羲之,東晉大書法家;「元常」是鍾繇,是三國魏的大書法家。董其昌的斷代很清楚,認為在三國和東晉之間,就這麼幾行字跡,代表了西晉書風,讚美為「希世之寶」。
其實以近代更精準的說法來看,不僅鍾繇的名作《宣示表》不是三國原作,連王羲之傳世墨蹟也都是唐以後的臨摹,要瞭解晉人墨跡原作的書風,《平復帖》就顯得加倍珍貴了。
讀帖
────「帖」中原始字句的曖昧迷離、若即若離,構成讀「帖」時奇特的一種魅惑力量。
一整個夏天我在案上擺著《平復帖》,每天讀「帖」數次。
讀「帖」不是臨摹。「臨」「摹」都是為了書法的目的,把前人名家的字跡拿來做學習對象。
我喜歡讀「帖」一方面是因為書法,另一方面是可能是因為「文體」。
「帖」大多是魏晉文人的書信。在三國時,鍾繇的《宣示表》《薦季直表》大多還有「文告」「奏章」的意義。
《平復帖》以下,「帖」越來越界定成為一種文人間往來的書信。王羲之的《姨母帖》是信,《喪亂帖》是信,寥寥廿八個字的《快雪時晴帖》也是信,十五個字的《奉橘帖》更是送橘子給朋友附帶的一則短訊便條。
這些書信便條,因為書法之美,流傳了下來,成為後世臨摹寫字的「帖」。然而,「帖」顯然也成為一種「文體」。
書信是有書寫對象的,也並不預期被其他人閱讀,也不預期被公開。因此「帖」的文體保有一定的私密性與隨意性。
王羲之的「帖」常常重複出現「奈何奈何」的慨歎,重複出現「不次」這種突然因為情緒波動哽咽停住的「斷章」文體。在《古文觀止》一類正經八百的文類裡看不到「帖」這麼「私密」、「隨性」卻又極為貼近「真實」「率性」的文體。
「帖」是魏晉文人沒有修飾過的生活日記細節,「帖」不是正襟危坐裝腔作勢的朝堂告令,文人從「文以載道」解脫出來,給最親密的朋友寫自己最深的私密心事,因此,書法隨意,文體也隨意。
因為書信的「私密性」,「帖」的文字也常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我們如果看他人簡訊,常常無法判斷那幾行字傳達的意思,每個字都懂,但談的事情卻不一定能掌握。
《平復帖》當然有同樣的文體限制。
「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以為慶。」啟功的釋文到這裡都沒有爭議,但是下面一句──「承使唯男」,繆關富先生的釋讀是「年既至男」,王振坤先生再修正釋讀為「年及至男」。
三種不同的解讀,不僅是因為草書字體的難懂,不只是因為年代久遠的殘破,也顯然牽涉到大家對「彥先」這個人的生平資料所知太少。
「承使唯男」,啟功的解釋是「彥先」雖然病重,還好有兒子繼承陪伴。
「年及至男」則是認為「彥先」還在壯年,應該可以無大礙。
因為對於「彥先」這個人始終沒又真正結論,這兩句解讀的歧異一時也很難有即刻定論。
《平復帖》一開始提到的「彥先」就有了爭議,後面提到的「吳子楊往」就爭議更大。
啟功認為陸機非常欣賞「楊往」,「威儀詳跱,舉動成觀,自軀體之美也。」繆關富先生的釋讀剛好相反,認為陸機要殺楊往。
文字的釋讀,變成依據「帖」上隻字片語,彌補擴大歷史空白,有點像丹.布朗用一點蛛絲馬跡敷衍出一部《達文西密碼》小說,《平復帖》近年的討論爭論越來越大,也像一部推理小說。
「帖」中原始字句的曖昧迷離、若即若離,構成讀「帖」時奇特的一種魅惑力量。
禿筆賊毫,火箸畫灰
────死灰上的線條,卻都帶著火燙的鐵箸的溫度,
《平復帖》把死亡的沉寂幻滅與燃燒的燙熱火焰一起寫進了書法。
我一方面閱讀諸家不同說法,但是晨起靜坐,還是與《平復帖》素面相見。細看那一張殘紙上墨痕斑剝,禿筆,沒有婉轉纖細的牽絲出鋒,沒有東晉王羲之書法的華麗秀美、飄逸神俊的璀璨光彩。但是《平復帖》頑強勁歛,有一種生命在劇痛中的糾纏扭曲,線條像廢棄鏽蝕的堡壘的鐵絲網,都是蒼苦荒涼的記第二輯 萬歲通天帖/選文一篇
萬歲通天(一):姨母帖 初月帖
「姨母」的死亡,祖墳的被刨挖,簡短的書信背後是慘絕人寰的時代悲劇──不斷有哀禍傳來,悲哀、摧毀、身體被切割一樣地痛,不能承擔的痛,──王羲之用「摧剝」、「摧絕」、「痛貫心肝」、「切割」「慘塞」這些具象又絕對的字眼形容自己對生命的傷痛,重複用「奈何、奈何」訴說心裡的虛無幻滅。
大家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歡王羲之的作品,唐太宗的年代距離王羲之已經有三百年。寫在紙或絹帛上的墨跡,不容易保存,當時能夠看到的王羲之的真跡也已經不多。唐太宗傾全力蒐求,把搜求到的王羲之真跡收藏在內府,又命令當時的書法名家臨摹王羲之的帖,因此流傳至今,許多博物館收藏的王羲之的字大都是「唐摹本」。
王羲之的帖由書法名家「臨」、「摹」。「臨」是看著真跡臨寫;「摹」是把紙蒙在真跡上用淡墨細線勾出輪廓再加以填墨,也叫「雙勾填墨」,或「響拓」。
「摹本」的忠實度很高,輪廓逼真,但是墨色變化與筆勢流動感就不一定能傳達出韻味。
「臨本」是大書法家臨寫,書法家有自己個性,也一定會在臨寫中不知不覺帶入自己書寫風格,會失去王羲之真跡風貌。以《蘭亭序》來說,歐陽詢、褚遂良的「臨本」多少都會流露出唐代書風,北京故宮被認為是唐弘文館搨書人馮承素所摹的「神龍本」就可能更忠實形似於原作。
唐武則天萬歲通天二年(六九七年),當朝宰相山東瑯琊的王方慶獻出他十一代祖王導,十代祖王羲之、王薈,九代祖王獻之、王徽之、王珣,一直到他曾祖父王褒,王家一門二十八人的墨跡珍本十卷給武則天。
武則天當時剛頒布了十三個新體漢字,例如「國」寫作「圀」,表示擁有「八方」,王方慶呈現給武則天的《萬歲通天帖》卷末的「上柱圀」「開圀男」都用了新體字。
在唐太宗搜羅盡王氏法帖之後,武則天能得到這十卷書法真品,當然喜出望外。她為此特別在武成殿召集群臣,出示書法真跡,並且命中書令崔融作《寶章集》,記錄這件大事。
武則天雖然如此喜愛這件作品,卻沒有以帝王的權威將書法佔為已有,她命朝廷善書者以雙勾填墨法複製摹本,收藏於內府。把王方慶進呈的原件加以裝裱錦褙,重新賜還給王家,並囑咐王方慶──這是祖先手跡,後代子孫應當善加守護珍藏。
武則天這種作法與唐太宗千方百計要佔有《蘭亭序》的「蕭翼賺蘭亭」故事,心胸大為不同。竇泉因此為這件事作有〈述書賦〉,讚美武氏「順天矜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顧兼金」。
收在內府的這十卷摹本歷經朝代變革,幾度經過大火災劫,到清末只剩一卷,保留了王羲之的《姨母帖》、王徽之的《新月帖》,王薈的《癤腫帖》,王獻之的《廿九帖》,王志的《一日無申帖》等書帖,目前收藏在遼寧博物館,稱為《萬歲通天帖》,一般都認為是瞭解王羲之一門書法最接近真跡風格的唐摹本。
姨母帖──哀痛摧剝
────活在一個生命一無價值的戰亂年代,無論活著的人,或死去的屍骸,都一樣被蹂躪踐踏。
現存的《萬歲通天帖》第一帖就是王羲之的《姨母帖》,──「羲之頓首,頃遘姨母哀,哀痛摧剝,情不自勝。奈何奈何。因反慘塞,不次。王羲之頓首頓首」很簡短的 一封信,扣除掉前後姓名敬語,總共只有十幾個字。──剛剛得知姨母死去的消息,非常哀痛,彷彿被摧毀剝裂的痛。無法承擔的痛苦,無可奈何啊!悲慘哽咽,不說了──王羲之的帖,對親人喪亡有痛苦,有感傷,有無可奈何的虛無悵惘。
如果姨母是自然的死亡,不知道他會不會用到「哀痛摧剝」這麼重的字眼。我有時把《姨母帖》與流傳到日本的《喪亂帖》以及《頻有哀禍帖》一起對讀,發現王羲之的帖呈現了一個遷徙流離的家族在戰亂裡對生命巨大的幻滅無常之感。
《喪亂帖》講到的是北方家鄉祖墳被刨挖,──「喪亂之極,先墓再離荼毒。追惟酷甚,號慕摧絕,痛貫心肝,痛當奈何,奈何!」天下戰亂,生命價值淪喪衰亡到極點,祖先墳墓再一次被毀壞蹂躪。想到如此殘酷至極的事,痛哭嚎叫、摧毀絕望,痛到心肝彷彿被貫穿,但是,這麼痛,又能如何,無可奈何啊!──王羲之活在一個生命一無價值的戰亂年代,無論活著的人,或死去的屍骸,都一樣被蹂躪踐踏。
「姨母」的死亡,祖墳的被刨挖,簡短的書信背後是慘絕人寰的時代悲劇。一連串災難悲劇的事件,正是《頻有哀禍帖》裡書寫的「頻有哀禍,悲摧切割,不能自勝」,──不斷有哀禍傳來,悲哀、摧毀、身體被切割一樣地痛,不能承擔的痛,──王羲之用「摧剝」、「摧絕」、「痛貫心肝」、「切割」「慘塞」這些具象又絕對的字眼形容自己對生命的傷痛,重複用「奈何、奈何」訴說心裡的虛無幻滅。童年從山東瑯琊流亡到南方,王羲之的「帖」透露著戰亂流離年代沉重又無力的一聲聲嘆息。
儒家的教養訓練要求節制情感,喜怒哀樂不能隨意宣洩,即使宣洩,也必須合於節制規則。因此傳統古文典範不常出現「痛貫心肝」這樣直接而具體的的句子,王羲之《喪亂帖》裡的「痛貫心肝」卻使我想起江蕙〈酒後的心聲〉裡的「痛入心肝」,民間俚曲或許保留了更多「帖」裡鮮活的人性空間。
初月──卿佳不?
────人生矯情,但到了憂患,最本質的關心往往也只是一兩句平凡簡單的問候。
《萬歲通天帖》的第二帖是王羲之草書書寫的一封信,開頭是「初月」二字,因此被稱為《初月帖》。
初月十二日,山陰羲之報。
近欲遣此書,濟行無人,不辨遣信。
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書。雖遠為慰,過囑,卿佳不?
吾諸患,殊劣殊劣。
方陟道憂悴,力不具。羲之報。
──正月十二日,王羲之在浙江山陰回信。
這封信寫好,要託人帶去。卻沒有人來往,信送不出去。
昨天才到山陰,收到你上個月十六日的信。
離別這麼遠,收到信,覺得安慰。太過牽掛了。
你好嗎?
我太多憂患,真不好!真不好!
行旅道中,憂愁,心力交瘁。不寫了。羲之報告。
王羲之的「帖」如果不是只看書法,可能是非常貼近生活的文體。簡潔、乾淨、直接,與一般古文的修飾造詞大不相同。
寫信時的王羲之也與寫《蘭亭序》時的王羲之大不相同。
《蘭亭序》是完整的文章體例,有敘事,有寫景,有對人生現象的哲學議論。《蘭亭序》可以看見作者對文字詞彙結構的鋪排,有一定的章法,遣詞造句講究,也有思維上的邏輯連貫。
王羲之的「帖」常常是回覆朋友的來信,像《初月帖》就很明顯。
因為是回信,兩個人之間對話的空間,很像今日簡訊往來,不但簡潔,也往往只在兩人之間可以理解。
《初月帖》裡的「過囑」只會在回信中出現。對方很關心王羲之,來信一定囑咐叮嚀了很多事,諸如「保重身體」「路上小心安全」等等,王羲之回信才會有「過囑」──太讓對方牽掛了。覺得不安、感謝,覺得讓別人操心,因此有「過囑」兩個字。
我喜歡「帖」的文體裡這些簡單的敬語,文字簡單,沒有太多意思,卻人情厚重。在戰亂流離的年代,能夠說的也往往只是「卿佳不?」這樣一句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問候。「卿佳不?」「卿佳否?」在今日的簡訊中變成「你好嗎?」仍然可能是最動人的句子。
「卿佳不?」使我想起小津安二郎的經典名作《早安》,人生矯情,但到了憂患,最本質的關心往往也只是一兩句平凡簡單的問候。
「吾諸患,殊劣!殊劣!」王羲之的「帖」也從來不遵守儒家的「勵志」典範。在親人不斷死亡,故鄉祖墳遭塗炭的諸多患難中,王羲之慨歎「奈何!奈何」;或著慨歎「殊劣!殊劣」,都不是虛偽的「勵志」,而是直接書寫真實的自己的心境。
「殊劣」不常在古文出現,「劣」在現代漢字中也還用,如「惡劣」。「劣」是「不好」,是「壞」。「殊劣」似乎是心情「太糟糕了!」
我讀《初月》,卻看「劣」很久,原來「劣」也只是「少力」,──無力感、疲倦,提不起勁,像「帖」的結尾常常是「力不次」「力不具」,大戰亂裡流離的聲音,生命信仰瓦解崩潰的聲音,沒有任何可以依恃的年代,一封信裡的「過囑」或「卿佳不?」大概是唯一可以傳遞的信仰吧。
「諸患」「憂悴」筆法裡都是墨痕牽絲,連綿不斷,如淚閃爍。
第三輯 十七帖/選文兩篇
1 周撫
王羲之給周撫的信多是草書,有漢代章草的意味,二人書體自有默契。優美灑脫自在的書法,談的內容都是家常平凡小事,一問一答,十分親切,書風文體都有韻味。入秋以來,每日細讀一帖,如讀秋光。
《十七帖》在宋代刊刻時,收有二十八件王羲之的信。其中包括《遠宦帖》在內,大多是寫給當時在四川做益州刺史的周撫的,算一算,超過二十封信。
《十七帖》第一帖是──「十七日先書,郗司馬未去,即日得足下書為慰。先書已具,示復數字。」這就是王羲之寫給周撫的短信,──十七日王羲之已經寫了信給周撫,託他的妻舅郗曇帶去,郗曇還沒出發,王羲之又收到周撫的信,可見他們書信往來很頻繁。因為王羲之前一封信已經一一回答了周撫的問題,因此這一封信只寫了簡短的幾個字。這封信開頭有「十七」兩個字,因此被稱為《十七帖》,成為王羲之摹刻法帖名稱的來源。
《十七帖》唐代摹刻時並沒有那麼多件,我懷疑有可能是唐太宗完整蒐集到當時留在蜀地的一批王羲之寫給周撫的信。南北朝三百年,中原戰亂,四川相對是比較安定的,王羲之的信帖也可能在周撫家族手上保留得比較齊全。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的《十七帖》後來增補加入了六帖,合成了總共二十八件的王羲之《十七帖》。
周撫在四川做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官,王羲之對沒有去過的蜀地很有興趣,充滿好奇。《十七帖》中有好幾封信是詢問周撫關於四川的山川景物文化產業等等。
《成都城池帖》問的是成都城門城牆是不是秦代古蹟──「往在都,見諸葛顯,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為爾否?信具示。為欲廣異聞。」王羲之聽說遠在四川的成都還保留了秦代的城池建築,他對這麼古老有歷史的建築很是嚮往,特別問周撫是不是真的,很想增廣異聞。
對於蜀地的文化人物歷史的嚮往還表現在《十七帖》的《嚴君平帖》中──「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不?」很短的一封信,問起漢代蜀地一些歷史名人,很想知道他們在四川還有沒有後代。
另外一封《漢時帖》問的是四川漢代的「講堂」──「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因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王羲之對四川漢代留下來的講堂很好奇,想知道是漢代哪一位皇帝設立的。又聽說講堂裡有三皇五帝以來帝王聖賢畫像,畫得很精妙,因此問周撫:有沒有人能臨摹,畫下來,寄給他看。
蜀地的文化歷史常在王羲之嚮往中,蜀地的山川自然之奇也讓他心馳,《蜀都帖》裡談到他看了周撫對蜀地山水的描述,覺得比揚雄〈蜀都賦〉、左思〈三都賦〉都還詳盡。因此與周撫約定要一遊蜀地,「登汶嶺、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只是構想,還沒有行動,已經心魂飛馳到四川了。
王羲之對四川特有的「鹽井、火井」也充滿興趣,《鹽井帖》中問周撫──「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具示!」看來王羲之並不是只讀死書的書呆子,他問周撫有沒有親眼看到自然氣燃燒的鹽井、火井,要周撫詳細告訴他真實情況,很有實證的精神。
周撫也常寄送蜀地的特別物產給王羲之,有一次寄的是卭竹手杖,王羲之回信致謝──「去夏,得足下致卭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王羲之把四川土產卭竹手杖分給年紀大的老者,也讓大家知道周撫遠方捎來的好意。周撫送卭竹杖的事王羲之還在另一封信中提到,──「周益州送此卭竹杖,卿尊長或須今送。」這是他為了分送竹杖寫的短簡了。
王羲之給周撫的信多是草書,有漢代章草的意味,二人書體自有默契。優美灑脫自在的書法,談的內容都是家常平凡小事,一問一答,十分親切,反覆閱讀,書風文體都有韻味。入秋以來,每日細讀一帖,如讀秋光。
2 旃罽帖
因為這秋季的風,因為風行走在河面上一波一波光的足跡。因為潮來潮去。我看《旃罽帖》,好像秋日晴空一絲流雲,可牽可掛,可捲舒可伸展,也可以散到無影無蹤,只是我自己記憶裡的一點執著。
《旃罽帖》在《十七帖》和後來刊刻的《淳化閣帖》裡都有,──「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周撫送來了四川土產「旃罽」、「胡桃」、兩種「藥」,王羲之收到禮物,回覆周撫的一封信。
「旃罽」、是一種赤紅色的毛毯,「罽」這個字《紅樓夢》裡用得很多,家裡擺設常常鋪「罽」,像是戲劇舞台上用地紅毯,也鋪在床榻椅子上,用以保暖或裝飾。周撫在四川,他送王羲之的「旃罽」應該是四川土產。或許是羊毛或氂牛毛的材料。
跟紅毛毯一起送來的還有胡桃,和兩種藥。因為蜀地特殊的地形,山裡有不少特殊植物、礦物,好像至今漢藥藥材也還以蜀地或藏地出產為優。
信的第二段講到四川宜賓產的「戎鹽」。「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戎鹽」常見漢藥典籍,《本草綱目》裡也稱「胡鹽」、「青鹽」,可以瀉血熱,通便。
「戎鹽」是含氯化鈉的礦物,結晶體。它是漢藥,卻也是古代道家煉丹的材料,《抱朴子》和《酉陽雜俎》談道家煉丹都談到「戎鹽」。因此王羲之在《旃罽帖》信裡談到的「服食」不是在談治病的「藥」,這裡的「服食」更接近今天青年們說的「嗑藥」。魏晉文人都有服食藥物習慣,《世說新語》裡的「五石散」是當時常見藥物,以白、紫兩種石英,加上硫黃、石脂、鐘乳,配製成「散」,服食以後,全身發熱,產生不同感覺。
王羲之特別提道「戎鹽」與「服食」的關係,顯然周撫來信中也談到最近「服食」「戎鹽」製丹藥的經驗。
周撫把「戎鹽」從四川帶進中原,好像把大麻從荷蘭帶進台灣,只是當年似乎沒有海關禁止,「戎鹽」也沒有被當作「毒品」沒收或犯罪。
王羲之最後還因為服食「戎鹽」談起他與妻舅郗愔所得感覺意見上的不一樣。
「方回(郗愔)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郗愔是郗鑒的兒子,也是東晉豪門望族。郗鑒找女婿,找到「袒腹東床」的王羲之,這是大家都熟知的「東床快婿」的故事。郗王兩家還不只這一次聯姻,王羲之的小兒子王獻之後來又娶了郗曇的女兒郗道茂,可見兩家數代交情之深,郗曇、郗愔兄弟就常在王羲之的帖中出現,連「服食」藥物都彼此交換心得。
郗愔也愛服食丹藥,卻與王羲之感覺不一樣。王羲之覺得遺憾,只好用大家常用的「知我者希(稀)」來調侃自己。「服食」藥物本來是追求非常個人細緻的官能探險,王羲之也不會執著要求郗愔一定要有與他一樣的反應。
周撫從四川來了,帶了禮物送給王羲之。王羲之卻沒有見到他,「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我喜歡這封信的結尾,八個字,卻是如此灑脫的魏晉人的風度。生命中有無法如願的事,有悵惘,有遺憾,但是,收到禮物,寫一封信回覆,雖然見不到面,卻可以「以當一笑」。如此雲淡風輕,沒有粘黏。船過,自然水都無痕。喜悅或憂傷,也只是我們自己牽掛多事。
因為這秋季的風,因為風行走在河面上一波一波光的足跡。因為潮來潮去,鷺鷥在河岸渡步覓食,招潮蟹驚慌四處奔逃流竄。我看《旃罽帖》,好像秋日晴空一絲流雲,可牽可掛,可捲舒可伸展,也可以散到無影無蹤,只是我自己記憶裡的一點執著。
《十七帖》裡還有一封向周撫提到「藥草」的信,就叫《藥草帖》──「彼所須此藥草,可示,當致。」──你需要這裡的藥,寫下來,我幫你找。只有十個字的一封短信,簡直像藥物密碼。
29
手帖───────跋
散步時,常常看到地上落花。黃紫的色彩對比,花瓣迷離的筋脈,都如常鮮豔,但已經凋落了;它的美,不容有長久記憶。有時候看王羲之的手帖,會無端想起初到南方的他,看到的是什麼樣的花?
四月底,覺得花季都過了,其實不然。走在河岸邊,黃槿的花開得正盛。
朋友中認識黃槿的不多。小時後家住在河邊,在未經整理的河灘爛泥地常有密聚的黃槿。樹幹不挺拔,枝莖扭曲錯亂,結成木癭疙瘩,像古人批評的朽木。很難拿來做家具棟樑,卻使人想起莊子說的「無用」之材,因為「無用」才逃過人們的砍伐吧。
黃槿卻不是完全無用,黃槿巴掌大、橢圓、近似心形的葉子,台灣民間常採來襯墊糯米粿。紅的龜粿,襯著黃槿的綠葉是童年鮮明的記憶。
小時候在河灘玩耍,在密密的黃槿樹叢裡鑽來鑽去,常常會看到一隻死貓的屍體,懸掛在不高的黃槿樹枝上,腐爛了,嗡聚著一群蒼蠅,發著惡臭。
黃槿,姿態低矮虬曲,有點卑微猥瑣,生長在骯髒的爛泥灘,懸掛著動物腐臭屍體,這樣的樹木,好像很少人注意到它也開著美麗的花。
然而,黃槿的花的確是美麗的。
黃槿花式嬌嫩黃色,小茶杯那麼大小,五瓣裂萼。花蒂處圈成筒狀,上端順時鐘向外翻轉。形狀優美,像一盞清初官窯的鵝黃細瓷茶鍾。特別是映照著陽光,花瓣透明成黃金色,花瓣一絲一絲的筋脈細紋,整齊潔淨,清晰可見,使人想起女子藏在腰間的細絲絹帕。
黃槿花最美的地方是蕊心深處一抹深艷的紫色。包圍在一片嫩黃色間,那濃艷的紫使人觸目心驚。一支強壯的雄蕊從墨紫深處直伸出來,顫顫巍巍,全心綻放,透露生命在春天肆無所忌憚的繁殖欲望。
黃槿是頑強的植物,耐風,耐乾旱,耐鹹鹼,因
1 火箸畫灰──《平復帖》種種
【我一方面閱讀諸家不同說法,但是晨起靜坐,還是與《平復帖》素面相見。細看那一張殘紙上墨痕斑剝,禿筆,沒有婉轉纖細的牽絲出鋒,沒有東晉王羲之書法的華麗秀美、飄逸神俊的璀璨光彩。但是《平復帖》頑強勁歛,有一種生命在劇痛中的糾纏扭曲,線條像廢棄鏽蝕的堡壘的鐵絲網,都是蒼苦荒涼的記憶。】
《平復帖》大概是這幾年在古文物領域被討論得最多的一件作品。
《平復帖》唐代就收入內府,宋代被定為是西晉陸機的真跡。北宋大書法家米芾曾經看過,用「火箸畫灰」四個字形容《平復帖》禿筆賊豪線條的蒼勁枯澀之美。宋徽宗有朱書題簽,「晉平原內史陸機士衡平復帖》,題簽下有雙龍小璽,四角有「政和」「宣龢」的押印。
《平復帖》在元代的收藏經過不十分清楚。明清時代曾經韓世能、韓逢禧父子、安儀周、梁清標等人收藏,綾邊隔水上都有收藏印記。董其昌在韓世能家看過,也留下跋尾的題識。
乾隆年間收入內府,後賜給皇十一子成親王永瑆。清末再轉入恭王府,流傳到溥心畬手上,隔水上也有「溥心畬鑑定書畫珍藏印」。溥心畬為了籌親人喪葬費,轉手賣給張伯駒,一九五六年,張伯駒把《平復帖》捐出,收藏於北京故宮。
啟功先生釋文
──── 一千年來定為陸機作品的《平復帖》似又重新需要釐清真正的作者,
或重新定位為晉代某一佚名文人的手跡了?
《平復帖》是漢代章草向晉代今草過渡的字體,古奧難懂,加上年久斑剝,字跡漫漶,很不容易辨認。啟功先生在六○年代釋讀了《平復帖》,雖然還有不同的看法,但目前已成為流傳最廣泛的釋文:
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以為慶。
《平復帖》開頭一段釋讀比較沒有歧異。大概是說:「彥先」身體衰弱生病,恐怕很難痊癒。初得病時,沒有想到會並到這麼嚴重。
「彥先」是信上提到的一個人,自宋以來,也因為這兩個字,引出了陸機與《平復帖》的關係,因為陸機有好朋友名叫「彥先」。
麻煩的是,陸機親近的朋友中有兩個都叫「彥先」,一個是顧榮,顧彥先;另一個是賀循,賀彥先,都是同樣出身吳國士族,又同時與陸機在西晉作官的朋友。
其實繼續探索下去,陸機的朋友中可能還不只兩個「彥先」。徐邦達先生就認為「平復帖」裡的「彥先」是另一個叫「全彥先」的人。這一點早在《昭明文選.李善注》裡就已經提到。文選裡有陸機陸雲兄弟為「彥先」寫的〈贈婦詩〉,〈李善注〉指出這個「彥先」不是顧榮顧彥先,而是全彥先。
三個「彥先」使探索《平復帖》的線索更為複雜,各家說法不一,一時沒有定論,這幾年隨著《平復帖》二○○三年在北京展出,二○○五年在上海展出,討論的人更多。有人根本否定《平復帖》是陸機所書,大概也以為依據信裡「彥先」兩個字,斷定《平復帖》是陸機真跡,而「彥先」此人是哪一個「彥先」還不清楚,寧可存疑。
但是各派說法都同意《平復帖》是西晉人墨書真跡,的確比王羲之傳世摹本更具斷代上的重要性。《平復帖》還是穩坐「墨皇」「帖祖」的位置。
啟功先生對《平復帖》的釋讀目前是最廣泛被接受的。他解讀的「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因為彥先病重,身體衰弱,正與《晉書.賀循傳》裡描述的「賀彥先」的身體多病衰弱相似,也自然會使人把彥先定為賀循。
但是《平復帖》裡的「彥先」,依據這麼一點點聯繫,就斷為「賀循」,當然還會使很多人迷惑。而因此連接上陸機,也一定會讓更多人對《平復帖》的真相繼續討論下去。二○○六年五月的《中國書法》期刊甚至有人提出──晉代讀書人為表示「榮耀祖先」,不少人都取名「彥先」,「彥先」是晉代文人非常普遍的名字。如果此說成立,《平復帖》上的「彥先」就不一定是顧榮或賀循,因此也不一定是陸機的朋友,一千年來定為陸機作品的《平復帖》又重新需要釐清真正的作者,或重新定位為晉代某一佚名文人的手跡了。
「佚名」書畫
────作為西晉人的墨跡是目前比較確定的結論,至少有了時代的斷代意義。
中國的書畫收藏一直習慣把作品歸類在名家之下。唐宋以前不落款的書畫,陸續被冠上名家的名字。許多幅山水冠上了「范寬」、「郭熙」;許多幅馬,被冠上了「韓幹」;許多幅仕女被冠上了「張萱」、「周昉」。當然,許多「帖」,就冠上了「王羲之」、「王獻之」。
沒有名家名字,似乎就失去了價值,使書畫的討論陷入盲點。連博物館的收藏都不能還原「不知名」、「佚名」「摹本」的標識,其實使大眾一開始就誤認了風格,書畫的鑑賞可能就越走越遠離真相。
許多人知道長期題簽標誌為王獻之的名作《中秋帖》,其實是宋代米芾的臨摹本,大家也習以為常把宋米芾的書法風格混淆成王獻之,相差六百年的美學書風也因此越來越難以釐清。
《平復帖》是不是陸機的作品尚在爭論中,但是作為西晉人的墨跡是比較確定的結論,至少有了時代的斷代意義。
右軍之前,元常之後
明代大鑑賞家董其昌在《平復帖》的跋裡說:「右軍以前,元常以後,為此數行,為希代寶。」「右軍」是王羲之,東晉大書法家;「元常」是鍾繇,是三國魏的大書法家。董其昌的斷代很清楚,認為在三國和東晉之間,就這麼幾行字跡,代表了西晉書風,讚美為「希世之寶」。
其實以近代更精準的說法來看,不僅鍾繇的名作《宣示表》不是三國原作,連王羲之傳世墨蹟也都是唐以後的臨摹,要瞭解晉人墨跡原作的書風,《平復帖》就顯得加倍珍貴了。
讀帖
────「帖」中原始字句的曖昧迷離、若即若離,構成讀「帖」時奇特的一種魅惑力量。
一整個夏天我在案上擺著《平復帖》,每天讀「帖」數次。
讀「帖」不是臨摹。「臨」「摹」都是為了書法的目的,把前人名家的字跡拿來做學習對象。
我喜歡讀「帖」一方面是因為書法,另一方面是可能是因為「文體」。
「帖」大多是魏晉文人的書信。在三國時,鍾繇的《宣示表》《薦季直表》大多還有「文告」「奏章」的意義。
《平復帖》以下,「帖」越來越界定成為一種文人間往來的書信。王羲之的《姨母帖》是信,《喪亂帖》是信,寥寥廿八個字的《快雪時晴帖》也是信,十五個字的《奉橘帖》更是送橘子給朋友附帶的一則短訊便條。
這些書信便條,因為書法之美,流傳了下來,成為後世臨摹寫字的「帖」。然而,「帖」顯然也成為一種「文體」。
書信是有書寫對象的,也並不預期被其他人閱讀,也不預期被公開。因此「帖」的文體保有一定的私密性與隨意性。
王羲之的「帖」常常重複出現「奈何奈何」的慨歎,重複出現「不次」這種突然因為情緒波動哽咽停住的「斷章」文體。在《古文觀止》一類正經八百的文類裡看不到「帖」這麼「私密」、「隨性」卻又極為貼近「真實」「率性」的文體。
「帖」是魏晉文人沒有修飾過的生活日記細節,「帖」不是正襟危坐裝腔作勢的朝堂告令,文人從「文以載道」解脫出來,給最親密的朋友寫自己最深的私密心事,因此,書法隨意,文體也隨意。
因為書信的「私密性」,「帖」的文字也常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我們如果看他人簡訊,常常無法判斷那幾行字傳達的意思,每個字都懂,但談的事情卻不一定能掌握。
《平復帖》當然有同樣的文體限制。
「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以為慶。」啟功的釋文到這裡都沒有爭議,但是下面一句──「承使唯男」,繆關富先生的釋讀是「年既至男」,王振坤先生再修正釋讀為「年及至男」。
三種不同的解讀,不僅是因為草書字體的難懂,不只是因為年代久遠的殘破,也顯然牽涉到大家對「彥先」這個人的生平資料所知太少。
「承使唯男」,啟功的解釋是「彥先」雖然病重,還好有兒子繼承陪伴。
「年及至男」則是認為「彥先」還在壯年,應該可以無大礙。
因為對於「彥先」這個人始終沒又真正結論,這兩句解讀的歧異一時也很難有即刻定論。
《平復帖》一開始提到的「彥先」就有了爭議,後面提到的「吳子楊往」就爭議更大。
啟功認為陸機非常欣賞「楊往」,「威儀詳跱,舉動成觀,自軀體之美也。」繆關富先生的釋讀剛好相反,認為陸機要殺楊往。
文字的釋讀,變成依據「帖」上隻字片語,彌補擴大歷史空白,有點像丹.布朗用一點蛛絲馬跡敷衍出一部《達文西密碼》小說,《平復帖》近年的討論爭論越來越大,也像一部推理小說。
「帖」中原始字句的曖昧迷離、若即若離,構成讀「帖」時奇特的一種魅惑力量。
禿筆賊毫,火箸畫灰
────死灰上的線條,卻都帶著火燙的鐵箸的溫度,
《平復帖》把死亡的沉寂幻滅與燃燒的燙熱火焰一起寫進了書法。
我一方面閱讀諸家不同說法,但是晨起靜坐,還是與《平復帖》素面相見。細看那一張殘紙上墨痕斑剝,禿筆,沒有婉轉纖細的牽絲出鋒,沒有東晉王羲之書法的華麗秀美、飄逸神俊的璀璨光彩。但是《平復帖》頑強勁歛,有一種生命在劇痛中的糾纏扭曲,線條像廢棄鏽蝕的堡壘的鐵絲網,都是蒼苦荒涼的記第二輯 萬歲通天帖/選文一篇
萬歲通天(一):姨母帖 初月帖
「姨母」的死亡,祖墳的被刨挖,簡短的書信背後是慘絕人寰的時代悲劇──不斷有哀禍傳來,悲哀、摧毀、身體被切割一樣地痛,不能承擔的痛,──王羲之用「摧剝」、「摧絕」、「痛貫心肝」、「切割」「慘塞」這些具象又絕對的字眼形容自己對生命的傷痛,重複用「奈何、奈何」訴說心裡的虛無幻滅。
大家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歡王羲之的作品,唐太宗的年代距離王羲之已經有三百年。寫在紙或絹帛上的墨跡,不容易保存,當時能夠看到的王羲之的真跡也已經不多。唐太宗傾全力蒐求,把搜求到的王羲之真跡收藏在內府,又命令當時的書法名家臨摹王羲之的帖,因此流傳至今,許多博物館收藏的王羲之的字大都是「唐摹本」。
王羲之的帖由書法名家「臨」、「摹」。「臨」是看著真跡臨寫;「摹」是把紙蒙在真跡上用淡墨細線勾出輪廓再加以填墨,也叫「雙勾填墨」,或「響拓」。
「摹本」的忠實度很高,輪廓逼真,但是墨色變化與筆勢流動感就不一定能傳達出韻味。
「臨本」是大書法家臨寫,書法家有自己個性,也一定會在臨寫中不知不覺帶入自己書寫風格,會失去王羲之真跡風貌。以《蘭亭序》來說,歐陽詢、褚遂良的「臨本」多少都會流露出唐代書風,北京故宮被認為是唐弘文館搨書人馮承素所摹的「神龍本」就可能更忠實形似於原作。
唐武則天萬歲通天二年(六九七年),當朝宰相山東瑯琊的王方慶獻出他十一代祖王導,十代祖王羲之、王薈,九代祖王獻之、王徽之、王珣,一直到他曾祖父王褒,王家一門二十八人的墨跡珍本十卷給武則天。
武則天當時剛頒布了十三個新體漢字,例如「國」寫作「圀」,表示擁有「八方」,王方慶呈現給武則天的《萬歲通天帖》卷末的「上柱圀」「開圀男」都用了新體字。
在唐太宗搜羅盡王氏法帖之後,武則天能得到這十卷書法真品,當然喜出望外。她為此特別在武成殿召集群臣,出示書法真跡,並且命中書令崔融作《寶章集》,記錄這件大事。
武則天雖然如此喜愛這件作品,卻沒有以帝王的權威將書法佔為已有,她命朝廷善書者以雙勾填墨法複製摹本,收藏於內府。把王方慶進呈的原件加以裝裱錦褙,重新賜還給王家,並囑咐王方慶──這是祖先手跡,後代子孫應當善加守護珍藏。
武則天這種作法與唐太宗千方百計要佔有《蘭亭序》的「蕭翼賺蘭亭」故事,心胸大為不同。竇泉因此為這件事作有〈述書賦〉,讚美武氏「順天矜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顧兼金」。
收在內府的這十卷摹本歷經朝代變革,幾度經過大火災劫,到清末只剩一卷,保留了王羲之的《姨母帖》、王徽之的《新月帖》,王薈的《癤腫帖》,王獻之的《廿九帖》,王志的《一日無申帖》等書帖,目前收藏在遼寧博物館,稱為《萬歲通天帖》,一般都認為是瞭解王羲之一門書法最接近真跡風格的唐摹本。
姨母帖──哀痛摧剝
────活在一個生命一無價值的戰亂年代,無論活著的人,或死去的屍骸,都一樣被蹂躪踐踏。
現存的《萬歲通天帖》第一帖就是王羲之的《姨母帖》,──「羲之頓首,頃遘姨母哀,哀痛摧剝,情不自勝。奈何奈何。因反慘塞,不次。王羲之頓首頓首」很簡短的 一封信,扣除掉前後姓名敬語,總共只有十幾個字。──剛剛得知姨母死去的消息,非常哀痛,彷彿被摧毀剝裂的痛。無法承擔的痛苦,無可奈何啊!悲慘哽咽,不說了──王羲之的帖,對親人喪亡有痛苦,有感傷,有無可奈何的虛無悵惘。
如果姨母是自然的死亡,不知道他會不會用到「哀痛摧剝」這麼重的字眼。我有時把《姨母帖》與流傳到日本的《喪亂帖》以及《頻有哀禍帖》一起對讀,發現王羲之的帖呈現了一個遷徙流離的家族在戰亂裡對生命巨大的幻滅無常之感。
《喪亂帖》講到的是北方家鄉祖墳被刨挖,──「喪亂之極,先墓再離荼毒。追惟酷甚,號慕摧絕,痛貫心肝,痛當奈何,奈何!」天下戰亂,生命價值淪喪衰亡到極點,祖先墳墓再一次被毀壞蹂躪。想到如此殘酷至極的事,痛哭嚎叫、摧毀絕望,痛到心肝彷彿被貫穿,但是,這麼痛,又能如何,無可奈何啊!──王羲之活在一個生命一無價值的戰亂年代,無論活著的人,或死去的屍骸,都一樣被蹂躪踐踏。
「姨母」的死亡,祖墳的被刨挖,簡短的書信背後是慘絕人寰的時代悲劇。一連串災難悲劇的事件,正是《頻有哀禍帖》裡書寫的「頻有哀禍,悲摧切割,不能自勝」,──不斷有哀禍傳來,悲哀、摧毀、身體被切割一樣地痛,不能承擔的痛,──王羲之用「摧剝」、「摧絕」、「痛貫心肝」、「切割」「慘塞」這些具象又絕對的字眼形容自己對生命的傷痛,重複用「奈何、奈何」訴說心裡的虛無幻滅。童年從山東瑯琊流亡到南方,王羲之的「帖」透露著戰亂流離年代沉重又無力的一聲聲嘆息。
儒家的教養訓練要求節制情感,喜怒哀樂不能隨意宣洩,即使宣洩,也必須合於節制規則。因此傳統古文典範不常出現「痛貫心肝」這樣直接而具體的的句子,王羲之《喪亂帖》裡的「痛貫心肝」卻使我想起江蕙〈酒後的心聲〉裡的「痛入心肝」,民間俚曲或許保留了更多「帖」裡鮮活的人性空間。
初月──卿佳不?
────人生矯情,但到了憂患,最本質的關心往往也只是一兩句平凡簡單的問候。
《萬歲通天帖》的第二帖是王羲之草書書寫的一封信,開頭是「初月」二字,因此被稱為《初月帖》。
初月十二日,山陰羲之報。
近欲遣此書,濟行無人,不辨遣信。
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書。雖遠為慰,過囑,卿佳不?
吾諸患,殊劣殊劣。
方陟道憂悴,力不具。羲之報。
──正月十二日,王羲之在浙江山陰回信。
這封信寫好,要託人帶去。卻沒有人來往,信送不出去。
昨天才到山陰,收到你上個月十六日的信。
離別這麼遠,收到信,覺得安慰。太過牽掛了。
你好嗎?
我太多憂患,真不好!真不好!
行旅道中,憂愁,心力交瘁。不寫了。羲之報告。
王羲之的「帖」如果不是只看書法,可能是非常貼近生活的文體。簡潔、乾淨、直接,與一般古文的修飾造詞大不相同。
寫信時的王羲之也與寫《蘭亭序》時的王羲之大不相同。
《蘭亭序》是完整的文章體例,有敘事,有寫景,有對人生現象的哲學議論。《蘭亭序》可以看見作者對文字詞彙結構的鋪排,有一定的章法,遣詞造句講究,也有思維上的邏輯連貫。
王羲之的「帖」常常是回覆朋友的來信,像《初月帖》就很明顯。
因為是回信,兩個人之間對話的空間,很像今日簡訊往來,不但簡潔,也往往只在兩人之間可以理解。
《初月帖》裡的「過囑」只會在回信中出現。對方很關心王羲之,來信一定囑咐叮嚀了很多事,諸如「保重身體」「路上小心安全」等等,王羲之回信才會有「過囑」──太讓對方牽掛了。覺得不安、感謝,覺得讓別人操心,因此有「過囑」兩個字。
我喜歡「帖」的文體裡這些簡單的敬語,文字簡單,沒有太多意思,卻人情厚重。在戰亂流離的年代,能夠說的也往往只是「卿佳不?」這樣一句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問候。「卿佳不?」「卿佳否?」在今日的簡訊中變成「你好嗎?」仍然可能是最動人的句子。
「卿佳不?」使我想起小津安二郎的經典名作《早安》,人生矯情,但到了憂患,最本質的關心往往也只是一兩句平凡簡單的問候。
「吾諸患,殊劣!殊劣!」王羲之的「帖」也從來不遵守儒家的「勵志」典範。在親人不斷死亡,故鄉祖墳遭塗炭的諸多患難中,王羲之慨歎「奈何!奈何」;或著慨歎「殊劣!殊劣」,都不是虛偽的「勵志」,而是直接書寫真實的自己的心境。
「殊劣」不常在古文出現,「劣」在現代漢字中也還用,如「惡劣」。「劣」是「不好」,是「壞」。「殊劣」似乎是心情「太糟糕了!」
我讀《初月》,卻看「劣」很久,原來「劣」也只是「少力」,──無力感、疲倦,提不起勁,像「帖」的結尾常常是「力不次」「力不具」,大戰亂裡流離的聲音,生命信仰瓦解崩潰的聲音,沒有任何可以依恃的年代,一封信裡的「過囑」或「卿佳不?」大概是唯一可以傳遞的信仰吧。
「諸患」「憂悴」筆法裡都是墨痕牽絲,連綿不斷,如淚閃爍。
第三輯 十七帖/選文兩篇
1 周撫
王羲之給周撫的信多是草書,有漢代章草的意味,二人書體自有默契。優美灑脫自在的書法,談的內容都是家常平凡小事,一問一答,十分親切,書風文體都有韻味。入秋以來,每日細讀一帖,如讀秋光。
《十七帖》在宋代刊刻時,收有二十八件王羲之的信。其中包括《遠宦帖》在內,大多是寫給當時在四川做益州刺史的周撫的,算一算,超過二十封信。
《十七帖》第一帖是──「十七日先書,郗司馬未去,即日得足下書為慰。先書已具,示復數字。」這就是王羲之寫給周撫的短信,──十七日王羲之已經寫了信給周撫,託他的妻舅郗曇帶去,郗曇還沒出發,王羲之又收到周撫的信,可見他們書信往來很頻繁。因為王羲之前一封信已經一一回答了周撫的問題,因此這一封信只寫了簡短的幾個字。這封信開頭有「十七」兩個字,因此被稱為《十七帖》,成為王羲之摹刻法帖名稱的來源。
《十七帖》唐代摹刻時並沒有那麼多件,我懷疑有可能是唐太宗完整蒐集到當時留在蜀地的一批王羲之寫給周撫的信。南北朝三百年,中原戰亂,四川相對是比較安定的,王羲之的信帖也可能在周撫家族手上保留得比較齊全。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的《十七帖》後來增補加入了六帖,合成了總共二十八件的王羲之《十七帖》。
周撫在四川做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官,王羲之對沒有去過的蜀地很有興趣,充滿好奇。《十七帖》中有好幾封信是詢問周撫關於四川的山川景物文化產業等等。
《成都城池帖》問的是成都城門城牆是不是秦代古蹟──「往在都,見諸葛顯,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為爾否?信具示。為欲廣異聞。」王羲之聽說遠在四川的成都還保留了秦代的城池建築,他對這麼古老有歷史的建築很是嚮往,特別問周撫是不是真的,很想增廣異聞。
對於蜀地的文化人物歷史的嚮往還表現在《十七帖》的《嚴君平帖》中──「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不?」很短的一封信,問起漢代蜀地一些歷史名人,很想知道他們在四川還有沒有後代。
另外一封《漢時帖》問的是四川漢代的「講堂」──「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因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王羲之對四川漢代留下來的講堂很好奇,想知道是漢代哪一位皇帝設立的。又聽說講堂裡有三皇五帝以來帝王聖賢畫像,畫得很精妙,因此問周撫:有沒有人能臨摹,畫下來,寄給他看。
蜀地的文化歷史常在王羲之嚮往中,蜀地的山川自然之奇也讓他心馳,《蜀都帖》裡談到他看了周撫對蜀地山水的描述,覺得比揚雄〈蜀都賦〉、左思〈三都賦〉都還詳盡。因此與周撫約定要一遊蜀地,「登汶嶺、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只是構想,還沒有行動,已經心魂飛馳到四川了。
王羲之對四川特有的「鹽井、火井」也充滿興趣,《鹽井帖》中問周撫──「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具示!」看來王羲之並不是只讀死書的書呆子,他問周撫有沒有親眼看到自然氣燃燒的鹽井、火井,要周撫詳細告訴他真實情況,很有實證的精神。
周撫也常寄送蜀地的特別物產給王羲之,有一次寄的是卭竹手杖,王羲之回信致謝──「去夏,得足下致卭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王羲之把四川土產卭竹手杖分給年紀大的老者,也讓大家知道周撫遠方捎來的好意。周撫送卭竹杖的事王羲之還在另一封信中提到,──「周益州送此卭竹杖,卿尊長或須今送。」這是他為了分送竹杖寫的短簡了。
王羲之給周撫的信多是草書,有漢代章草的意味,二人書體自有默契。優美灑脫自在的書法,談的內容都是家常平凡小事,一問一答,十分親切,反覆閱讀,書風文體都有韻味。入秋以來,每日細讀一帖,如讀秋光。
2 旃罽帖
因為這秋季的風,因為風行走在河面上一波一波光的足跡。因為潮來潮去。我看《旃罽帖》,好像秋日晴空一絲流雲,可牽可掛,可捲舒可伸展,也可以散到無影無蹤,只是我自己記憶裡的一點執著。
《旃罽帖》在《十七帖》和後來刊刻的《淳化閣帖》裡都有,──「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周撫送來了四川土產「旃罽」、「胡桃」、兩種「藥」,王羲之收到禮物,回覆周撫的一封信。
「旃罽」、是一種赤紅色的毛毯,「罽」這個字《紅樓夢》裡用得很多,家裡擺設常常鋪「罽」,像是戲劇舞台上用地紅毯,也鋪在床榻椅子上,用以保暖或裝飾。周撫在四川,他送王羲之的「旃罽」應該是四川土產。或許是羊毛或氂牛毛的材料。
跟紅毛毯一起送來的還有胡桃,和兩種藥。因為蜀地特殊的地形,山裡有不少特殊植物、礦物,好像至今漢藥藥材也還以蜀地或藏地出產為優。
信的第二段講到四川宜賓產的「戎鹽」。「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戎鹽」常見漢藥典籍,《本草綱目》裡也稱「胡鹽」、「青鹽」,可以瀉血熱,通便。
「戎鹽」是含氯化鈉的礦物,結晶體。它是漢藥,卻也是古代道家煉丹的材料,《抱朴子》和《酉陽雜俎》談道家煉丹都談到「戎鹽」。因此王羲之在《旃罽帖》信裡談到的「服食」不是在談治病的「藥」,這裡的「服食」更接近今天青年們說的「嗑藥」。魏晉文人都有服食藥物習慣,《世說新語》裡的「五石散」是當時常見藥物,以白、紫兩種石英,加上硫黃、石脂、鐘乳,配製成「散」,服食以後,全身發熱,產生不同感覺。
王羲之特別提道「戎鹽」與「服食」的關係,顯然周撫來信中也談到最近「服食」「戎鹽」製丹藥的經驗。
周撫把「戎鹽」從四川帶進中原,好像把大麻從荷蘭帶進台灣,只是當年似乎沒有海關禁止,「戎鹽」也沒有被當作「毒品」沒收或犯罪。
王羲之最後還因為服食「戎鹽」談起他與妻舅郗愔所得感覺意見上的不一樣。
「方回(郗愔)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郗愔是郗鑒的兒子,也是東晉豪門望族。郗鑒找女婿,找到「袒腹東床」的王羲之,這是大家都熟知的「東床快婿」的故事。郗王兩家還不只這一次聯姻,王羲之的小兒子王獻之後來又娶了郗曇的女兒郗道茂,可見兩家數代交情之深,郗曇、郗愔兄弟就常在王羲之的帖中出現,連「服食」藥物都彼此交換心得。
郗愔也愛服食丹藥,卻與王羲之感覺不一樣。王羲之覺得遺憾,只好用大家常用的「知我者希(稀)」來調侃自己。「服食」藥物本來是追求非常個人細緻的官能探險,王羲之也不會執著要求郗愔一定要有與他一樣的反應。
周撫從四川來了,帶了禮物送給王羲之。王羲之卻沒有見到他,「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我喜歡這封信的結尾,八個字,卻是如此灑脫的魏晉人的風度。生命中有無法如願的事,有悵惘,有遺憾,但是,收到禮物,寫一封信回覆,雖然見不到面,卻可以「以當一笑」。如此雲淡風輕,沒有粘黏。船過,自然水都無痕。喜悅或憂傷,也只是我們自己牽掛多事。
因為這秋季的風,因為風行走在河面上一波一波光的足跡。因為潮來潮去,鷺鷥在河岸渡步覓食,招潮蟹驚慌四處奔逃流竄。我看《旃罽帖》,好像秋日晴空一絲流雲,可牽可掛,可捲舒可伸展,也可以散到無影無蹤,只是我自己記憶裡的一點執著。
《十七帖》裡還有一封向周撫提到「藥草」的信,就叫《藥草帖》──「彼所須此藥草,可示,當致。」──你需要這裡的藥,寫下來,我幫你找。只有十個字的一封短信,簡直像藥物密碼。
29
手帖───────跋
散步時,常常看到地上落花。黃紫的色彩對比,花瓣迷離的筋脈,都如常鮮豔,但已經凋落了;它的美,不容有長久記憶。有時候看王羲之的手帖,會無端想起初到南方的他,看到的是什麼樣的花?
四月底,覺得花季都過了,其實不然。走在河岸邊,黃槿的花開得正盛。
朋友中認識黃槿的不多。小時後家住在河邊,在未經整理的河灘爛泥地常有密聚的黃槿。樹幹不挺拔,枝莖扭曲錯亂,結成木癭疙瘩,像古人批評的朽木。很難拿來做家具棟樑,卻使人想起莊子說的「無用」之材,因為「無用」才逃過人們的砍伐吧。
黃槿卻不是完全無用,黃槿巴掌大、橢圓、近似心形的葉子,台灣民間常採來襯墊糯米粿。紅的龜粿,襯著黃槿的綠葉是童年鮮明的記憶。
小時候在河灘玩耍,在密密的黃槿樹叢裡鑽來鑽去,常常會看到一隻死貓的屍體,懸掛在不高的黃槿樹枝上,腐爛了,嗡聚著一群蒼蠅,發著惡臭。
黃槿,姿態低矮虬曲,有點卑微猥瑣,生長在骯髒的爛泥灘,懸掛著動物腐臭屍體,這樣的樹木,好像很少人注意到它也開著美麗的花。
然而,黃槿的花的確是美麗的。
黃槿花式嬌嫩黃色,小茶杯那麼大小,五瓣裂萼。花蒂處圈成筒狀,上端順時鐘向外翻轉。形狀優美,像一盞清初官窯的鵝黃細瓷茶鍾。特別是映照著陽光,花瓣透明成黃金色,花瓣一絲一絲的筋脈細紋,整齊潔淨,清晰可見,使人想起女子藏在腰間的細絲絹帕。
黃槿花最美的地方是蕊心深處一抹深艷的紫色。包圍在一片嫩黃色間,那濃艷的紫使人觸目心驚。一支強壯的雄蕊從墨紫深處直伸出來,顫顫巍巍,全心綻放,透露生命在春天肆無所忌憚的繁殖欲望。
黃槿是頑強的植物,耐風,耐乾旱,耐鹹鹼,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