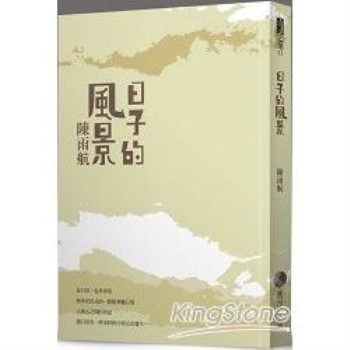輯一
長崎蛋糕
有一種日式蛋糕叫做カステラ(Castilla,卡斯提拉),它是由麵粉、雞蛋和砂糖等蒸烤出來的。通常是蛋黃色的大方塊狀,然後再分切成小塊。我們一般稱為長崎蛋糕、蜂蜜蛋糕或者長崎蜂蜜蛋糕。
其實更早的時候就有這種蛋糕了。我記得在早期糖果糕餅的禮盒裏,常見到小塊的這種蛋糕,烤得微焦的上皮還有抽象鬱金香圖案的拉花。長崎蛋糕在台灣的普及大致在一九六○年代以後。典型的這種蛋糕店舖裏只專賣這一種蛋糕,他們在店面玻璃櫃裏擺上多層的大塊蛋糕,店內櫃檯後面的架上還疊有許多金色紙盒,這些紙盒長度約為二十七點五公分,高度約六點五公分,寬度則從七、八公分到二十幾公分不等,依顧客的需要,切成相對應的寬度裝盒出售。以我最近常去的一家這種蛋糕店來說,他們分成五種尺寸零售。
這些店也像其他類型的中西點糕餅店一樣,接受大量的訂單,有一陣子訂婚、彌月滿多人使用的,但現在西點糕餅禮盒包裝越來越講究的時代,相對樸素的長崎蛋糕大概比較少人使用了吧。
我喜歡長崎蛋糕的理由之一,是它的質地紮實(但還在鬆軟的範圍之內),另外就是有一點點濕潤感。通常買回來開封即食,要是放到第二天,我就會收進冰箱,以保持好的咬口。
早期某一、二品牌不知是被併購了呢,還是擴充成全國發行的大品牌綜合西點公司,長崎蛋糕於是成了量產品。它們通常的保存日期長得多,因而以玻璃紙袋或塑膠袋密封,裡面還放一包乾燥劑。雖然我並不排斥,但它比較鬆,也沒有一般蛋糕常有的濕潤度。我是覺得它遠不如傳統店舖製作的新鮮好吃。可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內人就與我持相反的論調,這也是我在購買時要稍微躊躇一下(也只有一下)的原因。
從小就知道這種蛋糕叫卡斯提拉,四個音節,未嘗細究。知道這名字怎麼來的則是得自補習班的地理老師。這位老師上課兩手空空,在黑板畫起地圖來極詳細。有一天上到西班牙,他畫了伊比利半島,又劃分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接著是西班牙的細部。提到卡斯提爾高原時,他頓了一頓,說:有一種蛋糕叫卡斯提拉,就是從這裡來的……那當兒,用現在的話說,我知道的這一種小小的蛋糕就和廣大的世界接軌了。
卡斯提拉其實就是西班牙前身卡斯提爾王國的人們吃的主食,十六世紀日本室町幕府末期由葡萄牙人傳到長崎,然後流行開來。這是我們這裏卡斯提拉店會說「長崎本舖」、「長崎蛋糕」的緣由吧。台北市西寧南路有一家卡斯提拉店,名字叫「南蠻堂」,也充滿了長崎意涵。
日本人稱的「南蠻」是指西洋人,因為是從南方來的。雖然指涉不一樣,但顯然其名詞和位置視角與中國是一致的。日本有所謂「南蠻料理」,顧名思義是早期西洋料理發展而成的。加拿大作家威爾.弗格森在他名為《日本,搭個便車吧》(馬可孛羅出版)的書裡,對肆無忌憚地使用「南蠻」這樣帶歧視性的名詞加以撻伐,他說,相應於「南蠻料理」,我們西洋人是不是應該用「日本鬼子料理」來反擊呢。
回到卡斯提拉蛋糕。這類蛋糕店還常常用「長生本舖」、「長壽堂」、「加壽蛋糕」等等店招或形容詞,有時還用上南極仙翁的圖案,似乎暗示著常吃這種蛋糕會長壽。我不知道是什麼緣由或怎樣形成的,但我從不相信,哪有這麼好的事,不就是一塊蛋糕嗎?
職人一席話(長崎蛋糕2)
購食長崎蛋糕,本屬很平凡的一件事,但是這類蛋糕店並非到處可見。於我而言,有幾年間的光陰,一個星期會經過專做長崎蛋糕的店舖一次,也不會每次都買。這件事固然不像購買吐司麵包那樣日常,但也並不特別到需要再三思量。或者僅能說是日常再加一點期待的特意吧,或許可以稱之為「庶民式的一點點華麗心情」。
顯然南蠻堂的老闆並不只是這麼想。
幾年前寒冷的一個傍晚,我走進南蠻堂,像往常一樣買了一小盒蛋糕,轉身要走。
「這個蛋糕最好放兩天再吃喔。」坐在裏面的一位四十幾歲的漢子突然站起來向我發話。自從一年半前開始駐足這家蛋糕店以來,切蛋糕裝盒給我的十有九次是一位老先生或老太太,對眼前這個漢子沒甚麼印象。
「我連續兩星期看到你進來我們的店,所以想告訴你蛋糕比較好吃的方法。」
真湊巧,從來不會這麼高頻率地購買的啊,唯一的一次就被發現了。
「可是,我記得第一次買蛋糕時問過你們這蛋糕可以放幾天,你們的回答是四天,然後就得收到冰箱裏。」
「那是因為夏天。」他說:「像現在冬天,放個兩天以上,讓它水分均勻,蛋糕上面覆蓋的那層薄紙濕了的時候,會比較好吃。你應該試試梅雨季節的蛋糕,那是一年之中最好吃的時候……」
老闆說了許多有關長崎蛋糕的事情,於我而言,都很新鮮。然而我特別感到深刻的是他嚴肅而認真的表情,兩道微蹙的眉頭更加深了他的這個印象。從蛋糕的做法到一個專業師傅的養成;從不放添加物食品的分辨到食物的自然法則。他專注和投入的神態,不禁使我聯想起過去一位朋友說起資本主義經濟、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棒球指擦球時的神情,兩者一無軒輊。
除了蛋糕風味的良窳之外,老闆也提及了其他的吃法。譬如說,切薄片,塗上奶油,「那才叫奶油蛋糕哩」;或者切薄片夾水果成為水果蛋糕。還有,「如果你願意一試的話,可以等到蛋糕發黴,然後把發黴的外皮剝去,那簡直好吃到……」
後面這種吃法聞所未聞,但也不會太令我吃驚,不是有人還喜歡特意吃發黴的起司嗎﹖
我有沒有接受蛋糕店老闆的建議呢?沒有。我喜歡吃比較純粹不加奶油起司的蛋糕,這是我之所以獨鍾長崎蛋糕的原因。
甚至於連老闆一再叮嚀的「放個兩天以上」的建議,我都未加理會。那麼一小盒蛋糕,在買回家當晚和第二天分幾次就吃完了,哪能等「兩天以上」呢?我能做到的大概只有等待梅雨季節「一年中最佳的風味」吧。
但是,老闆那席話以後,有點甚麼不一樣了,說不上來。我切蛋糕的速度慢了些,切得比較整齊,而品嘗的動作也緩了下來。
也就只有這樣而已。倘若把吃蛋糕這件事變得太鄭重其事,那就失去了生活上的愜意。如同我前此說過的,不就是一塊蛋糕嗎?
肥前屋二三事
1
我喜歡到「肥前屋」吃鰻魚飯。很多人也都有與我相同的喜好,所以我們得常常排隊。
有時候想起來,這件事還滿誇張的,幾乎每次去都要排一下隊,差別只是快一點慢一點而已。有時候隊伍從門口排到十幾公尺外,快接近天津街了,那樣估計沒有五十分鐘或一小時輪不到,通常我會望望然而去。吃頓飯要排隊,總覺得沒有十分必要……肥前屋已是例外了,但也要適可而止吧。
為什麼肥前屋?沒別的,因為那裏的食物新鮮好吃又便宜。
以鰻魚飯來說,那幾乎是每一個客人必點的。微甜、多汁,烤得恰到好處(有時看起來焦一點,但好像味道也沒有差別),附一小碟淺漬蔬菜、一碗味噌湯,每客一百四十元。如果要多一些鰻魚和飯,那就叫一份大的,二百四十元。
這十年來,我常光顧這家店,因為喜歡吃日本料理的緣故。日本料理,我哪懂得個中三昧?不管你是在台灣或是在日本,講究起來,就要考量它的代價了。(哪一種料理不是這樣?)因此,庶民式的料理店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肥前屋營業時間是中午十一點半到兩點半,下午五點半到九點。通常我若是不能早些去,就寧可晚些,中午一點以後人就少了,很快就補了位,有時甚至隨到隨點。那時候外面沒有長龍,心裏也就沒有壓力,反而能從容享用食物。
雖然店家供應不少菜色,但我幾乎不太點別的,首選還是鰻魚飯。如果兩個人以上,或者心情上想奢侈一些,再點一盤生魚片吧,最常見的是紅魽和鮭魚還有別的什麼,一人份一百八十元。可以接受的價錢,而且新鮮,咬口恰到好處。
因為人多擁擠,那裡真的只能專心品嘗美食,然後起身走人。一個朋友的朋友在長安西路當代美術館對面巷子裏開了一間名叫「波西米亞人」的咖啡店,離開肥前屋後,安步當車到那兒喝杯咖啡,才是聊天談事的好地方。有很長一段時間,那是我公私約會的固定行程。
2
有一個傍晚,我跟兩位朋友約了在肥前屋吃飯然後去聽一場音樂會。到了那裡一看,肥前屋前大排長龍,若是執意要吃,絕對來不及趕上音樂會,只好另謀他圖。我們於是在附近找到了一家也是以鰻魚飯見長的「京都屋」,京都屋生意也不錯,但不必排隊,雖然價位比肥前屋略高一點,可座位雅致些,比較像在餐廳吃飯,那兒的鰻魚飯有三款,招牌的海鮮沙拉也都不錯,值得一試。那以後我就有了兩種選擇。
像這樣熱門的店,我會努力避開周末前去。但有一個周末到附近有一點事,結束之後,一時興起,就約了幾個人前去。到肥前屋一看,長龍;轉到京都屋,外面擠滿了人,店員分發號碼牌時,告訴我半個小時後一定有。我們到附近巷弄轉了轉,三十分鐘後回來,又等了十分鐘,還是輪不到。我問滿頭大汗的店員,到底要等多久,他算了算告訴我,我們是第九順位,還有得等呢?只好怏怏然而去。
我的結論是肥前屋的客人習慣速戰速決,那裡的氣氛使然。京都屋的客人是期望慢慢享受一頓餐食,調子完全不一樣。如果要排隊,應該選擇肥前屋。
3
據說肥前屋的老闆來自日本。我想應該就是九州的長崎吧,「肥前」是日本古國名,大致就是現在的長崎、佐賀兩縣一帶。我曾經在店裏看到一個布帘還是什麼的,下款寫的也就是長崎的某某工商協會之類。
九○年代初,肥前屋就是這個模樣了,生意好、排隊、以鰻魚飯知名……
記憶裏,更早的時候我就去過一次肥前屋,地點也是附近,但風格完全不同。
那是八○年代初的一個中午,影評人張昌彥先生帶我去的。很普通的一個日式食堂,桌子少,客人不多,空間適當,記得在一個角落裏還有一方和式座位,得脫鞋上去。
張先生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電影研究所,是少數從日本學電影回國的學者,任教於文化大學影劇系的他,論文是有關日本電影裏家族這樣的主題,那意味著以小津安二郎和山田洋次的作品為主,他是我認識的朋友中唯一一位看過小津全部作品的人。
我們各點了一客秋刀魚定食,吃飯的時候,張先生告訴我一段初到日本讀書時的趣事。
他跟研究所同學一起吃飯時,同學告訴他,在日本吃秋刀魚的正確方法是所有的部分都要吃進肚子,包括魚骨在內……
這當然是玩笑。
吃完飯,我看到張先生盤子裏一付剔得十分乾淨的秋刀魚魚骨。
(後記:這是九年多前寫的,近年去得少了,一年一回吧。這一兩年,鰻魚價格高騰,肥前屋小份的鰻魚飯已漲至二百五十元一客矣。)
輯三
尋找小津
1
高聳的大廈、櫛比鱗次的房屋、擁擠的交通、喧囂的市聲、行色匆匆的人群……這是德國電影導演文.溫德斯(Wim Wenders)一九八五年作品《尋找小津》(Tokyo-Ga)開頭時的一些片段。
熱愛他的前輩小津安二郎(一九○三~一九六三)的溫德斯,當然感覺到了八○年代中葉的東京,與他從小津電影中感受到的安謐寧靜的影像是多麼的不同。畢竟那是四、五○年代以及六○年代初期的東京,畢竟那是小津獨特的世界。
當然,溫德斯還是找到了一些小津的世界。在影片進行的稍後,溫德斯拍了一些小津電影裡的經典過場鏡頭。是T字形的東京後街巷弄,行人從遠處巷口的一邊入鏡,然後消失在另一邊,背景響著聽起來熟悉的西洋音樂……
之後,就是關於厚田雄春(一九○四~一九九二)的訪談了。厚田雄春是小津電影的長期夥伴,擔任攝影指導。
厚田提到小津曾告訴他:要做看門狗,就做大戶人家的看門狗吧……。有幾次,面對鏡頭的厚田感傷落淚。
這是我能記得的關於《尋找小津》的梗概,畢竟,從金馬電影展看到這部電影至今已超過二十年了。
溫德斯想必十分看重與厚田雄春的友誼,他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攝影集《一次》(Einmal, Bilder und Geschichten,中文繁體字版二○○五由田園城市文化公司出版),最前面就是一九九一年拍的厚田雄春的照片,以這本書紀念他。
2
我和朋友們熱心觀看小津的電影作品是在八○年代初,當時拜錄影帶普及之賜,能找到的小津作品大概都看了。《晚春》、《彼岸花》、《早安》、《浮草》、《秋日和》……當然還有《東京物語》和《秋刀魚之味》。有一個時期,我擁有一卷《秋刀魚之味》的錄影帶,一方面是方便,一方面是喜歡,居然看了四、五遍。
小津的電影多半聚焦於家庭生活,或是女兒出閣、子女離家,或是舊日不再、親人辭世等等……在溫馨中帶些淡淡的哀愁,有時也不乏一些幽默感(我在一本書裏讀到他早年編劇時期,常爲一些電影編寫好笑的橋段)。他的電影情節不是很富戲劇性,緩慢進行,孳生氣氛,很能使人共鳴,且在心裏感受到絲微生命中的悠遠和無奈之思。這大概是它能被許多觀眾接受且由衷欣賞的緣故吧。
3
八○年代末,我第一次到東京,當然,除了巷弄裏某些情景會勾起聯想以外,那是完全迥異於小津的電影世界。歲月流逝如斯,一個時代一個時代過去,有些東西一去不復回那是最自然不過之事。
在這一星期差旅的某一天晚上,我居然在新宿的街頭聽到十分熟悉的旋律,那正是《東京物語》和《秋刀魚之味》都出現過的〈軍艦行進曲〉。《東京物語》裡,笠智眾飾演來東京探望兒孫的老先生平山,他趁便與老友約在酒館會晤,當他們喝得酩酊,談著他們在戰爭期間失去的兒子時,背景音樂就是〈軍艦行進曲〉。在《秋刀魚之味》裏,也是笠智眾飾演的會社高級職員平山(兩部電影不同的角色用同一個姓氏),戰時是驅逐艦「朝風號」艦長,他在中學老師(東野英治郎飾)開的麵店巧遇昔日艦上的水兵(加東大介飾),水兵邀他就近到家裏坐坐,接著到附近酒館喝酒,水兵要老闆娘放〈軍艦行進曲〉,然後口裏合著旋律一面在酒館繞圈子行進,一面向昔日長官行舉手禮,最後是平山和老闆娘都跟著旋律行舉手禮……
我尋聲找到歌曲旋律的源頭,竟是一間大型的柏青哥店。我後來才得知,這首舊日帝國的榮光,俗稱〈軍艦March〉的歌曲,已成為柏青哥店振奮精神的主打曲子。
4
小津電影也不是Ogisan輩的專利。
前些年認識的一位年輕作家,同時也是影像工作者的李志薔,他也很喜歡小津的電影。我偶然在他的新聞台上讀到他的一篇散文〈秋刀魚之味〉(後來他自己改拍成電視電影《秋宜的婚事》),是將他對家人的情感和觀看小津電影的回憶等交織書寫,氛圍滿小津的,心靈物景交融,文字很是動人。
物語家族
二○一三年四月,在電影院看了小津安二郎的經典作《東京物語》和山田洋次向小津致敬的《東京家族》。
《東京物語》大約是三十年前家用錄影帶剛開始流行沒幾年時看的,雖然隔了這麼多年,但中間讀過中譯劇本和電影分鏡本,因此內容還算熟悉。能在大銀幕上觀賞小津作品,是難得的機緣。
《東京物語》和《東京家族》用相對溫馨的劇情表達了「家庭崩毀」的主題。家庭崩毀由來已久,當社會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社會時就已發生,老家衰微,新家成長,而時光綿延向前。因此,電影裏的家庭崩毀不是一個控訴式的命題,而是一個哀傷的歌謠吧。
相隔六十年,社會有了更新的變化,也反應在新拍的《東京家族》電影裏。蒼井優的紀子角色雖然不能如原節子飾演的紀子那般完美,但放諸今日的標準,也是眾裏難尋的了。一個人的孤獨生活如今已更為普遍,從而《東京家族》的悲劇感也就略微淡化。橋爪功飾演的平山周吉看來就是比笠智眾更具生命力,失去了伴侶,他還可以繼續在園子裏工作,在榻榻米上剪腳指甲(真是神來一鏡),鄉村人情在,還有一犬相伴,呼應了當今家庭的現象:子女會離家,寵物不會。
一九五三年的《東京物語》距大戰結束未久,平山周吉跟兩位朋友在小酒館裏相互訴說著子女的事,幾個老人說起他們在戰爭裏失去的孩子,你兩個,我一個……結論是:即使他們今天還活著,也不會聽從父親的意思。《東京家族》的時代是三一一日本東北大地震之後的當代,電影裏有著「這國家到底要把我們帶到哪裏去」的批判之外,老輩對兒女依然不滿,但這個不滿在最後有了改變。從《東京物語》裏「復活」的二兒子平山昌二(妻夫木聰飾),是父親眼裏的浪子,總擔心他不務正業,未來如何是好,可最終做父親的明白,不管兒女選擇甚麼,只要努力以赴,他們總會走出自己的路子,因而結局對年輕人的未來也有更好的祝福。
看來山田洋次對家庭的現狀有較樂觀的看法。
瀨戶內海小鎮
一遊文學作品、歷史書籍提到的地點,或者電影拍攝的場景,可能是許多文藝青年喜歡做的事。我沒那麼上癮,一來世界那麼寬廣我無法經常旅行,二來閱讀世界無限大而吾生也有涯。能夠去,我們就到現場看看;如果不是那麼方便,也可以做別的選擇。
幾年前,到日本岡山、廣島一帶旅行,安排停泊點時,我選擇在尾道住一天,看看小津安二郎《東京物語》裏起始和結尾的那個瀨戶內海小鎮。
旅遊書上介紹了一些景點,譬如說乘纜車上去的千光寺和那裏的公園、文學小徑等等。但我們時間有限,大多放棄了,先拜訪淨土寺再說。
有著錯落宏偉的建築,淨土寺幅員廣闊,但在前庭尋找電影裏的場景並不太難。略一瀏覽,大概看得出約在山門以及圍牆邊的參道。老伴過世的早晨,平山老先生在那裏不知眺望著甚麼,然後向尋來的兒媳也或者是自言自語:「看來今天又是個熱天吶。」半世紀過去,變化不算大,特別是尚未有其他訪寺客人到來的早晨,有著近似悵然的清寂。倒是外面的天地變化多些,從參道往外望去,雖然眼底的山陽本線鐵道,幾排屋脊簷瓦後方的瀨戶內海水道,以及水道過去的向島,大體可以附比電影的影像,但視線左上方橫空斜過去的尾道大橋整個改變了眼前的景觀。水道上來往的船隻並不巨大,引擎顯然改善許多,沒聽見電影裏反襯寂寥的渡船馬達碰碰之聲。
下了淨土寺,步行不多久,來到尾道電影資料館。資料館不算大,較受人矚目的是小津的角落,有更多《東京物語》在當地取景之處的照片,這些大多是空景,最有趣的是淨土寺只有平山和其兒媳那場清寂之戲,從另一邊拍的照片呈現出笠智眾和原節子兩位演員的後面是一大群看拍電影的民眾。我們也在放映室看了幾十分鐘特別製作的小津紀錄影帶。
關於小津的《東京物語》,這樣也就夠了。難得的是到了這樣頗具風情的小鎮,感受到它獨特的氣息。有機會要找大林宣彥的電影來看,因為他是尾道出生成長的導演啊。於尾道,小津只是過客,大林宣彥的「尾道三部作」和「新尾道三部作」等以故鄉為背景的作品當是值得一探。
長崎蛋糕
有一種日式蛋糕叫做カステラ(Castilla,卡斯提拉),它是由麵粉、雞蛋和砂糖等蒸烤出來的。通常是蛋黃色的大方塊狀,然後再分切成小塊。我們一般稱為長崎蛋糕、蜂蜜蛋糕或者長崎蜂蜜蛋糕。
其實更早的時候就有這種蛋糕了。我記得在早期糖果糕餅的禮盒裏,常見到小塊的這種蛋糕,烤得微焦的上皮還有抽象鬱金香圖案的拉花。長崎蛋糕在台灣的普及大致在一九六○年代以後。典型的這種蛋糕店舖裏只專賣這一種蛋糕,他們在店面玻璃櫃裏擺上多層的大塊蛋糕,店內櫃檯後面的架上還疊有許多金色紙盒,這些紙盒長度約為二十七點五公分,高度約六點五公分,寬度則從七、八公分到二十幾公分不等,依顧客的需要,切成相對應的寬度裝盒出售。以我最近常去的一家這種蛋糕店來說,他們分成五種尺寸零售。
這些店也像其他類型的中西點糕餅店一樣,接受大量的訂單,有一陣子訂婚、彌月滿多人使用的,但現在西點糕餅禮盒包裝越來越講究的時代,相對樸素的長崎蛋糕大概比較少人使用了吧。
我喜歡長崎蛋糕的理由之一,是它的質地紮實(但還在鬆軟的範圍之內),另外就是有一點點濕潤感。通常買回來開封即食,要是放到第二天,我就會收進冰箱,以保持好的咬口。
早期某一、二品牌不知是被併購了呢,還是擴充成全國發行的大品牌綜合西點公司,長崎蛋糕於是成了量產品。它們通常的保存日期長得多,因而以玻璃紙袋或塑膠袋密封,裡面還放一包乾燥劑。雖然我並不排斥,但它比較鬆,也沒有一般蛋糕常有的濕潤度。我是覺得它遠不如傳統店舖製作的新鮮好吃。可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內人就與我持相反的論調,這也是我在購買時要稍微躊躇一下(也只有一下)的原因。
從小就知道這種蛋糕叫卡斯提拉,四個音節,未嘗細究。知道這名字怎麼來的則是得自補習班的地理老師。這位老師上課兩手空空,在黑板畫起地圖來極詳細。有一天上到西班牙,他畫了伊比利半島,又劃分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接著是西班牙的細部。提到卡斯提爾高原時,他頓了一頓,說:有一種蛋糕叫卡斯提拉,就是從這裡來的……那當兒,用現在的話說,我知道的這一種小小的蛋糕就和廣大的世界接軌了。
卡斯提拉其實就是西班牙前身卡斯提爾王國的人們吃的主食,十六世紀日本室町幕府末期由葡萄牙人傳到長崎,然後流行開來。這是我們這裏卡斯提拉店會說「長崎本舖」、「長崎蛋糕」的緣由吧。台北市西寧南路有一家卡斯提拉店,名字叫「南蠻堂」,也充滿了長崎意涵。
日本人稱的「南蠻」是指西洋人,因為是從南方來的。雖然指涉不一樣,但顯然其名詞和位置視角與中國是一致的。日本有所謂「南蠻料理」,顧名思義是早期西洋料理發展而成的。加拿大作家威爾.弗格森在他名為《日本,搭個便車吧》(馬可孛羅出版)的書裡,對肆無忌憚地使用「南蠻」這樣帶歧視性的名詞加以撻伐,他說,相應於「南蠻料理」,我們西洋人是不是應該用「日本鬼子料理」來反擊呢。
回到卡斯提拉蛋糕。這類蛋糕店還常常用「長生本舖」、「長壽堂」、「加壽蛋糕」等等店招或形容詞,有時還用上南極仙翁的圖案,似乎暗示著常吃這種蛋糕會長壽。我不知道是什麼緣由或怎樣形成的,但我從不相信,哪有這麼好的事,不就是一塊蛋糕嗎?
職人一席話(長崎蛋糕2)
購食長崎蛋糕,本屬很平凡的一件事,但是這類蛋糕店並非到處可見。於我而言,有幾年間的光陰,一個星期會經過專做長崎蛋糕的店舖一次,也不會每次都買。這件事固然不像購買吐司麵包那樣日常,但也並不特別到需要再三思量。或者僅能說是日常再加一點期待的特意吧,或許可以稱之為「庶民式的一點點華麗心情」。
顯然南蠻堂的老闆並不只是這麼想。
幾年前寒冷的一個傍晚,我走進南蠻堂,像往常一樣買了一小盒蛋糕,轉身要走。
「這個蛋糕最好放兩天再吃喔。」坐在裏面的一位四十幾歲的漢子突然站起來向我發話。自從一年半前開始駐足這家蛋糕店以來,切蛋糕裝盒給我的十有九次是一位老先生或老太太,對眼前這個漢子沒甚麼印象。
「我連續兩星期看到你進來我們的店,所以想告訴你蛋糕比較好吃的方法。」
真湊巧,從來不會這麼高頻率地購買的啊,唯一的一次就被發現了。
「可是,我記得第一次買蛋糕時問過你們這蛋糕可以放幾天,你們的回答是四天,然後就得收到冰箱裏。」
「那是因為夏天。」他說:「像現在冬天,放個兩天以上,讓它水分均勻,蛋糕上面覆蓋的那層薄紙濕了的時候,會比較好吃。你應該試試梅雨季節的蛋糕,那是一年之中最好吃的時候……」
老闆說了許多有關長崎蛋糕的事情,於我而言,都很新鮮。然而我特別感到深刻的是他嚴肅而認真的表情,兩道微蹙的眉頭更加深了他的這個印象。從蛋糕的做法到一個專業師傅的養成;從不放添加物食品的分辨到食物的自然法則。他專注和投入的神態,不禁使我聯想起過去一位朋友說起資本主義經濟、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棒球指擦球時的神情,兩者一無軒輊。
除了蛋糕風味的良窳之外,老闆也提及了其他的吃法。譬如說,切薄片,塗上奶油,「那才叫奶油蛋糕哩」;或者切薄片夾水果成為水果蛋糕。還有,「如果你願意一試的話,可以等到蛋糕發黴,然後把發黴的外皮剝去,那簡直好吃到……」
後面這種吃法聞所未聞,但也不會太令我吃驚,不是有人還喜歡特意吃發黴的起司嗎﹖
我有沒有接受蛋糕店老闆的建議呢?沒有。我喜歡吃比較純粹不加奶油起司的蛋糕,這是我之所以獨鍾長崎蛋糕的原因。
甚至於連老闆一再叮嚀的「放個兩天以上」的建議,我都未加理會。那麼一小盒蛋糕,在買回家當晚和第二天分幾次就吃完了,哪能等「兩天以上」呢?我能做到的大概只有等待梅雨季節「一年中最佳的風味」吧。
但是,老闆那席話以後,有點甚麼不一樣了,說不上來。我切蛋糕的速度慢了些,切得比較整齊,而品嘗的動作也緩了下來。
也就只有這樣而已。倘若把吃蛋糕這件事變得太鄭重其事,那就失去了生活上的愜意。如同我前此說過的,不就是一塊蛋糕嗎?
肥前屋二三事
1
我喜歡到「肥前屋」吃鰻魚飯。很多人也都有與我相同的喜好,所以我們得常常排隊。
有時候想起來,這件事還滿誇張的,幾乎每次去都要排一下隊,差別只是快一點慢一點而已。有時候隊伍從門口排到十幾公尺外,快接近天津街了,那樣估計沒有五十分鐘或一小時輪不到,通常我會望望然而去。吃頓飯要排隊,總覺得沒有十分必要……肥前屋已是例外了,但也要適可而止吧。
為什麼肥前屋?沒別的,因為那裏的食物新鮮好吃又便宜。
以鰻魚飯來說,那幾乎是每一個客人必點的。微甜、多汁,烤得恰到好處(有時看起來焦一點,但好像味道也沒有差別),附一小碟淺漬蔬菜、一碗味噌湯,每客一百四十元。如果要多一些鰻魚和飯,那就叫一份大的,二百四十元。
這十年來,我常光顧這家店,因為喜歡吃日本料理的緣故。日本料理,我哪懂得個中三昧?不管你是在台灣或是在日本,講究起來,就要考量它的代價了。(哪一種料理不是這樣?)因此,庶民式的料理店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肥前屋營業時間是中午十一點半到兩點半,下午五點半到九點。通常我若是不能早些去,就寧可晚些,中午一點以後人就少了,很快就補了位,有時甚至隨到隨點。那時候外面沒有長龍,心裏也就沒有壓力,反而能從容享用食物。
雖然店家供應不少菜色,但我幾乎不太點別的,首選還是鰻魚飯。如果兩個人以上,或者心情上想奢侈一些,再點一盤生魚片吧,最常見的是紅魽和鮭魚還有別的什麼,一人份一百八十元。可以接受的價錢,而且新鮮,咬口恰到好處。
因為人多擁擠,那裡真的只能專心品嘗美食,然後起身走人。一個朋友的朋友在長安西路當代美術館對面巷子裏開了一間名叫「波西米亞人」的咖啡店,離開肥前屋後,安步當車到那兒喝杯咖啡,才是聊天談事的好地方。有很長一段時間,那是我公私約會的固定行程。
2
有一個傍晚,我跟兩位朋友約了在肥前屋吃飯然後去聽一場音樂會。到了那裡一看,肥前屋前大排長龍,若是執意要吃,絕對來不及趕上音樂會,只好另謀他圖。我們於是在附近找到了一家也是以鰻魚飯見長的「京都屋」,京都屋生意也不錯,但不必排隊,雖然價位比肥前屋略高一點,可座位雅致些,比較像在餐廳吃飯,那兒的鰻魚飯有三款,招牌的海鮮沙拉也都不錯,值得一試。那以後我就有了兩種選擇。
像這樣熱門的店,我會努力避開周末前去。但有一個周末到附近有一點事,結束之後,一時興起,就約了幾個人前去。到肥前屋一看,長龍;轉到京都屋,外面擠滿了人,店員分發號碼牌時,告訴我半個小時後一定有。我們到附近巷弄轉了轉,三十分鐘後回來,又等了十分鐘,還是輪不到。我問滿頭大汗的店員,到底要等多久,他算了算告訴我,我們是第九順位,還有得等呢?只好怏怏然而去。
我的結論是肥前屋的客人習慣速戰速決,那裡的氣氛使然。京都屋的客人是期望慢慢享受一頓餐食,調子完全不一樣。如果要排隊,應該選擇肥前屋。
3
據說肥前屋的老闆來自日本。我想應該就是九州的長崎吧,「肥前」是日本古國名,大致就是現在的長崎、佐賀兩縣一帶。我曾經在店裏看到一個布帘還是什麼的,下款寫的也就是長崎的某某工商協會之類。
九○年代初,肥前屋就是這個模樣了,生意好、排隊、以鰻魚飯知名……
記憶裏,更早的時候我就去過一次肥前屋,地點也是附近,但風格完全不同。
那是八○年代初的一個中午,影評人張昌彥先生帶我去的。很普通的一個日式食堂,桌子少,客人不多,空間適當,記得在一個角落裏還有一方和式座位,得脫鞋上去。
張先生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電影研究所,是少數從日本學電影回國的學者,任教於文化大學影劇系的他,論文是有關日本電影裏家族這樣的主題,那意味著以小津安二郎和山田洋次的作品為主,他是我認識的朋友中唯一一位看過小津全部作品的人。
我們各點了一客秋刀魚定食,吃飯的時候,張先生告訴我一段初到日本讀書時的趣事。
他跟研究所同學一起吃飯時,同學告訴他,在日本吃秋刀魚的正確方法是所有的部分都要吃進肚子,包括魚骨在內……
這當然是玩笑。
吃完飯,我看到張先生盤子裏一付剔得十分乾淨的秋刀魚魚骨。
(後記:這是九年多前寫的,近年去得少了,一年一回吧。這一兩年,鰻魚價格高騰,肥前屋小份的鰻魚飯已漲至二百五十元一客矣。)
輯三
尋找小津
1
高聳的大廈、櫛比鱗次的房屋、擁擠的交通、喧囂的市聲、行色匆匆的人群……這是德國電影導演文.溫德斯(Wim Wenders)一九八五年作品《尋找小津》(Tokyo-Ga)開頭時的一些片段。
熱愛他的前輩小津安二郎(一九○三~一九六三)的溫德斯,當然感覺到了八○年代中葉的東京,與他從小津電影中感受到的安謐寧靜的影像是多麼的不同。畢竟那是四、五○年代以及六○年代初期的東京,畢竟那是小津獨特的世界。
當然,溫德斯還是找到了一些小津的世界。在影片進行的稍後,溫德斯拍了一些小津電影裡的經典過場鏡頭。是T字形的東京後街巷弄,行人從遠處巷口的一邊入鏡,然後消失在另一邊,背景響著聽起來熟悉的西洋音樂……
之後,就是關於厚田雄春(一九○四~一九九二)的訪談了。厚田雄春是小津電影的長期夥伴,擔任攝影指導。
厚田提到小津曾告訴他:要做看門狗,就做大戶人家的看門狗吧……。有幾次,面對鏡頭的厚田感傷落淚。
這是我能記得的關於《尋找小津》的梗概,畢竟,從金馬電影展看到這部電影至今已超過二十年了。
溫德斯想必十分看重與厚田雄春的友誼,他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攝影集《一次》(Einmal, Bilder und Geschichten,中文繁體字版二○○五由田園城市文化公司出版),最前面就是一九九一年拍的厚田雄春的照片,以這本書紀念他。
2
我和朋友們熱心觀看小津的電影作品是在八○年代初,當時拜錄影帶普及之賜,能找到的小津作品大概都看了。《晚春》、《彼岸花》、《早安》、《浮草》、《秋日和》……當然還有《東京物語》和《秋刀魚之味》。有一個時期,我擁有一卷《秋刀魚之味》的錄影帶,一方面是方便,一方面是喜歡,居然看了四、五遍。
小津的電影多半聚焦於家庭生活,或是女兒出閣、子女離家,或是舊日不再、親人辭世等等……在溫馨中帶些淡淡的哀愁,有時也不乏一些幽默感(我在一本書裏讀到他早年編劇時期,常爲一些電影編寫好笑的橋段)。他的電影情節不是很富戲劇性,緩慢進行,孳生氣氛,很能使人共鳴,且在心裏感受到絲微生命中的悠遠和無奈之思。這大概是它能被許多觀眾接受且由衷欣賞的緣故吧。
3
八○年代末,我第一次到東京,當然,除了巷弄裏某些情景會勾起聯想以外,那是完全迥異於小津的電影世界。歲月流逝如斯,一個時代一個時代過去,有些東西一去不復回那是最自然不過之事。
在這一星期差旅的某一天晚上,我居然在新宿的街頭聽到十分熟悉的旋律,那正是《東京物語》和《秋刀魚之味》都出現過的〈軍艦行進曲〉。《東京物語》裡,笠智眾飾演來東京探望兒孫的老先生平山,他趁便與老友約在酒館會晤,當他們喝得酩酊,談著他們在戰爭期間失去的兒子時,背景音樂就是〈軍艦行進曲〉。在《秋刀魚之味》裏,也是笠智眾飾演的會社高級職員平山(兩部電影不同的角色用同一個姓氏),戰時是驅逐艦「朝風號」艦長,他在中學老師(東野英治郎飾)開的麵店巧遇昔日艦上的水兵(加東大介飾),水兵邀他就近到家裏坐坐,接著到附近酒館喝酒,水兵要老闆娘放〈軍艦行進曲〉,然後口裏合著旋律一面在酒館繞圈子行進,一面向昔日長官行舉手禮,最後是平山和老闆娘都跟著旋律行舉手禮……
我尋聲找到歌曲旋律的源頭,竟是一間大型的柏青哥店。我後來才得知,這首舊日帝國的榮光,俗稱〈軍艦March〉的歌曲,已成為柏青哥店振奮精神的主打曲子。
4
小津電影也不是Ogisan輩的專利。
前些年認識的一位年輕作家,同時也是影像工作者的李志薔,他也很喜歡小津的電影。我偶然在他的新聞台上讀到他的一篇散文〈秋刀魚之味〉(後來他自己改拍成電視電影《秋宜的婚事》),是將他對家人的情感和觀看小津電影的回憶等交織書寫,氛圍滿小津的,心靈物景交融,文字很是動人。
物語家族
二○一三年四月,在電影院看了小津安二郎的經典作《東京物語》和山田洋次向小津致敬的《東京家族》。
《東京物語》大約是三十年前家用錄影帶剛開始流行沒幾年時看的,雖然隔了這麼多年,但中間讀過中譯劇本和電影分鏡本,因此內容還算熟悉。能在大銀幕上觀賞小津作品,是難得的機緣。
《東京物語》和《東京家族》用相對溫馨的劇情表達了「家庭崩毀」的主題。家庭崩毀由來已久,當社會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社會時就已發生,老家衰微,新家成長,而時光綿延向前。因此,電影裏的家庭崩毀不是一個控訴式的命題,而是一個哀傷的歌謠吧。
相隔六十年,社會有了更新的變化,也反應在新拍的《東京家族》電影裏。蒼井優的紀子角色雖然不能如原節子飾演的紀子那般完美,但放諸今日的標準,也是眾裏難尋的了。一個人的孤獨生活如今已更為普遍,從而《東京家族》的悲劇感也就略微淡化。橋爪功飾演的平山周吉看來就是比笠智眾更具生命力,失去了伴侶,他還可以繼續在園子裏工作,在榻榻米上剪腳指甲(真是神來一鏡),鄉村人情在,還有一犬相伴,呼應了當今家庭的現象:子女會離家,寵物不會。
一九五三年的《東京物語》距大戰結束未久,平山周吉跟兩位朋友在小酒館裏相互訴說著子女的事,幾個老人說起他們在戰爭裏失去的孩子,你兩個,我一個……結論是:即使他們今天還活著,也不會聽從父親的意思。《東京家族》的時代是三一一日本東北大地震之後的當代,電影裏有著「這國家到底要把我們帶到哪裏去」的批判之外,老輩對兒女依然不滿,但這個不滿在最後有了改變。從《東京物語》裏「復活」的二兒子平山昌二(妻夫木聰飾),是父親眼裏的浪子,總擔心他不務正業,未來如何是好,可最終做父親的明白,不管兒女選擇甚麼,只要努力以赴,他們總會走出自己的路子,因而結局對年輕人的未來也有更好的祝福。
看來山田洋次對家庭的現狀有較樂觀的看法。
瀨戶內海小鎮
一遊文學作品、歷史書籍提到的地點,或者電影拍攝的場景,可能是許多文藝青年喜歡做的事。我沒那麼上癮,一來世界那麼寬廣我無法經常旅行,二來閱讀世界無限大而吾生也有涯。能夠去,我們就到現場看看;如果不是那麼方便,也可以做別的選擇。
幾年前,到日本岡山、廣島一帶旅行,安排停泊點時,我選擇在尾道住一天,看看小津安二郎《東京物語》裏起始和結尾的那個瀨戶內海小鎮。
旅遊書上介紹了一些景點,譬如說乘纜車上去的千光寺和那裏的公園、文學小徑等等。但我們時間有限,大多放棄了,先拜訪淨土寺再說。
有著錯落宏偉的建築,淨土寺幅員廣闊,但在前庭尋找電影裏的場景並不太難。略一瀏覽,大概看得出約在山門以及圍牆邊的參道。老伴過世的早晨,平山老先生在那裏不知眺望著甚麼,然後向尋來的兒媳也或者是自言自語:「看來今天又是個熱天吶。」半世紀過去,變化不算大,特別是尚未有其他訪寺客人到來的早晨,有著近似悵然的清寂。倒是外面的天地變化多些,從參道往外望去,雖然眼底的山陽本線鐵道,幾排屋脊簷瓦後方的瀨戶內海水道,以及水道過去的向島,大體可以附比電影的影像,但視線左上方橫空斜過去的尾道大橋整個改變了眼前的景觀。水道上來往的船隻並不巨大,引擎顯然改善許多,沒聽見電影裏反襯寂寥的渡船馬達碰碰之聲。
下了淨土寺,步行不多久,來到尾道電影資料館。資料館不算大,較受人矚目的是小津的角落,有更多《東京物語》在當地取景之處的照片,這些大多是空景,最有趣的是淨土寺只有平山和其兒媳那場清寂之戲,從另一邊拍的照片呈現出笠智眾和原節子兩位演員的後面是一大群看拍電影的民眾。我們也在放映室看了幾十分鐘特別製作的小津紀錄影帶。
關於小津的《東京物語》,這樣也就夠了。難得的是到了這樣頗具風情的小鎮,感受到它獨特的氣息。有機會要找大林宣彥的電影來看,因為他是尾道出生成長的導演啊。於尾道,小津只是過客,大林宣彥的「尾道三部作」和「新尾道三部作」等以故鄉為背景的作品當是值得一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