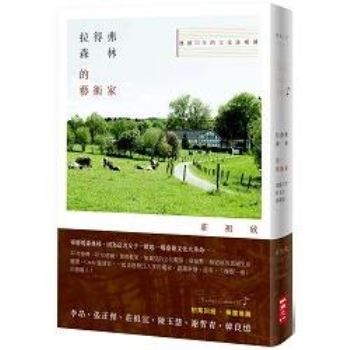◆姑娘生來愛唱歌
二十幾年前初識安德烈的時候,他說,他老爸開工廠,媽媽是家庭主婦,「那妳父母呢?」他問。
「我老爸造橋修路,我老媽啊……」,講到我老媽我總是格外得意,我說:「我媽是聲樂家、女高音,她很有名氣呢!」
「什麼?那個呀……」他居然面露難色地皺眉咽口水。
「怎麼啦?」我說:「你知道的嘛,唱古典歌劇的,茶花女、費加洛婚禮……那些,我也很愛唱的,你聽,啊~啊~(我信口捻來兩句「魔笛」夜之后的詠嘆調過門,自認聽起來還蠻以假亂真的)」,「我知道,我知道,」然後結結巴巴地,「只是,我老爸說的啦,不是我哦,他每次一聽到電視上或收音機裡女高音演唱,就撫著面頰說:『轉臺轉臺,別聽這種令人牙痛的鬼叫歌聲!』所以,我承認有點受老爸觀點影響啦!」
怎麼「有藝術水準」的德國人會有這種想法呢?德國是巴哈、蕭邦、貝多芬的故鄉,不是人人都愛欣賞歌劇和古典聲樂嗎?我承認,有些強調皇家水準的古典「學院派」唱起女高音的詠嘆調來真的讓人敬而遠之,一想到得正經危坐地聽她雙手握拳摀著小腹,滿臉痛苦地從丹田中逼出驚人的高音時,牙痛也許真的難免。但是,真正的聲樂訓練是任何一種歌唱技巧的基礎功,至於該怎麼表達,實在是見仁見智。我敢說,親臨過我母親演唱會的觀眾,肯定都會大點其頭地說:趣味、享受、意猶未盡。不但喜歡,而且會上癮!
這種意猶未盡的趣味和享受,我暗中思忖,接下來首要任務就是要引導安德烈和他的父母去欣賞,別的不敢說,但是起碼保證他們越聽牙齒會越健康!
學唱歌、登臺,從小舞臺到大舞臺十幾年來,如今幾乎每個月都會有大小的演唱會邀約。山丘小鎮的教會、合唱團、管風琴師辦的大小活動、義演工藝團體、華人文化團體,都喜歡找我去高歌數曲、軋一角。元月份教會辦的募款活動後來結算,除掉租場地、燈光、音響的開支,想不到我們小地方竟募到了三千多歐元的款項,承辦人後來跟我大大致謝,說觀眾幾乎都是衝著Cindy的歌聲慕名而來的。聽得我真是輕飄飄。但是,歌唱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把原來受到父親誤導、一聽到女高音歌聲就牙痛的另一半,訓練成為我的頭號歌迷,現在他還是我帶的「福爾摩沙合唱團」裡的中堅男低音,每回練完唱,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他總要跟我說:「好好玩,好好玩!唱歌這麼好玩怎麼以前我都不知道?」
其實小時候並沒打算走唱歌這條路的。媽媽在家教學生,她對學生的諄諄教誨我每天總要聽個好幾遍,聽著聽著就潛移默化,學生在鋼琴房內練唱發聲「啊~啊~」,我邊做功課也邊「啊~啊~」,媽媽注重訓練學生的姿勢臺風,常叫學生要對著鏡子唱,所以我把功課撇一邊,也去對著鏡子唱,唱著唱著竟發現,我還真像媽媽!我心血來潮跑去跟媽媽說:「看,我會學妳唱歌!」媽媽先是發愣,之後大笑,說:「這孩子去考聲樂系,一定沒問題!」可是,不知為何,後來考大學根本沒往這方面去動腦筋。而這點「學媽媽」的模仿功夫只成了家中宴客、茶餘飯後的餘興節目,客人撫掌大笑後,也常說,Cindy不往聲樂方面發展太可惜了!
我記得我的波蘭籍聲樂教授雅格娜曾告訴我她學習聲樂的故事。她的母親是一九五○、六○年代波蘭的首席著名女高音,有「華沙的黃鶯」之美譽,父親也是當時小有名氣的鋼琴家兼作曲家,但是她年紀輕有自己的主張,選擇和父母走完全不同的路,大學裡她主修了「日本文學」。我聽得出神,一九六○年代的波蘭和日本有什麼關係呢?等不及問:「然後呢?」她說,「然後,我的聲音破谷而出,這聲音,是上帝給你的禮物,壓抑不住的,它會自己找到路子,就是要唱出來,而且會被聽到!So-desそです」所以,她的聲音破谷而出,不但走了這條路,還當了聲樂教授。
我的聲音是否也是自己找到了路子?其實也說不清楚,我只知道,在這個無聲無息的森林小鎮裡,沒有卡拉OK,沒有一票「歌友」,真悶!唱歌,不能說是「認真努力的朝目標前進」,其實目標是什麼,當時也不太清楚;只是不可自拔地。非。唱。不。可!一唱,精神就來了,我家狗狗、鳥兒都跟著唱,卡通裡寂寞公主和森林中小動物合唱的畫面,果然成真!
這一切還得感激繪畫。二十七歲時在美術學院已修了好幾年的課,終於在拉得弗森林小鎮開第一次的個展,特別請母親來德國,以她的歌聲為我的畫展揭開序幕。無巧無不巧,韓國籍男高音Jael Jul Lim也被朋友拉來看畫,聽到我母親的歌聲,驚為天人,推崇不已。一個禮拜之後,他打電話給我,說,雖然只看了我的畫,沒聽過我唱歌,但是猜想,虎母無犬女,願不願意拜他為師?不不,不是只為了要收學生賺錢,是這樣的,他正與室內樂團、山丘音樂學校籌辦明年的音樂節,計劃將「魔笛」的部分場景搬上舞臺,問我是否有興趣共相盛舉,出一臂之力?比如說,從事舞臺佈景繪畫?我大喜過望,好像收到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說實在話,我想唱歌想瘋了!而從事舞臺佈景設計也是極度令人興奮的差事。向來山丘森林小鎮把我和繁華世界隔絕,除了安安靜靜地畫畫,還真沒什麼人跟我講話,這下竟然有如此「盛舉」邀請我加入,怎麼能不開心呢?
後來,在那次的音樂節裡我擔任了魔笛公主帕米娜的角色,總彩排的時候兒子剛滿一歲八個月,看到妖人「薩拉斯妥」居然要綁架公主媽媽,樂團鑼鼓笙簫地製造危險音效,嚇得他大哭大叫,衝到臺前非要媽媽抱。這件軼事,至今還為當時的共事人津津樂道呢,只是我家十四歲的酷哥兒怎麼也不承認當年他竟會那麼不酷。
後來韓國老師回了韓國。我求地利之便,便與小鎮和我年齡相仿的女中音繼續上課。唱歌本身無比快樂,但是年輕的女中音老師常跟我強調,她是正規大學音樂系畢業,而我是半路出家的業餘歌者,怎麼也別想達到她的「專業」歌唱素質。學習聲樂至此,我從未想過專業不專業這回事,不知為何,聽了她的專業忠告卻經不住任性,我非得唱出什麼東西來!專業是什麼?若歌唱只剩下呼吸、技巧和文憑,是否就是專業大歌唱家了?
I want to be MORE!但是森林原野廣稠無際,我怨有志難伸……
魔笛演出四年之後,我家老二也長到了兩歲,才在一次小鎮演出中場休息中認識了Wuppertal來的鋼琴家Rempel女士,Rempel特別驚訝我並沒在大學受過正式聲樂訓練,她說,我的聲音,只在這兒小鎮唱唱,不去大城市裡找好老師學,實在可惜了。
經Rempel女士介紹,我認識了埃森符克丸音樂學院(Folkwang Musik Hochschule)的雅格娜教授(Jagna Sokorska Kwika)。雅格娜給我上了兩次課就遞給我符克丸音樂學院的報考表格,叫我從現在起就開始練習甄試曲目。我盯著表格看,腦中閃過小時候媽媽的評語、親友的期許,如今,兩個小小孩的媽,我真的還能進音樂學院走這條路嗎?我說,「可是,我的兩個孩子這麼小,我......」
「什麼?」雅格娜說,「妳才幾歲?已經兩個小孩了?」
「我……我快三十二了。」
「三十二?」雅格娜一副不可置信的樣兒,「妳們亞洲人的年齡真是謎,要我猜的話,我以為你才二十二、三呢。這樣的話,報考音樂學院就不行了,音樂學院的報考年齡限制是二十七。不過,我真的喜歡妳的聲音,琢磨幾年,肯定別出凡響,妳願意的話,就做我的私人學生,我提供妳參予所有活動、音樂會,甚至考試的機會,怎麼樣?」
就這樣,我跟著雅格娜學習有五年之久,孩子白天上幼稚園,我就飆車去埃森上課。雅格娜的發聲教法很不同凡響,她的教室裡總是備有腳踏車橡皮輪胎圈一條,輪胎圈的一頭套在門把上,另一頭卡在臀部下,唱到高音,身體必須略蹲並往後退一步,橡皮輪胎圈就剛好襯住下蹲的臀部,「就是那兒!」雅格娜說,「發音中樞就在下腹部,往下坐,妳就感覺到了!」有些技巧部分我苦練死練,無奈總是時好時壞,把自己弄的很沮喪,雅格娜說:「我知道妳會的,妳只是想得太多,越想越對自己沒信心。跳舞吧!唱到這兒妳就隨著旋律轉圈圈!」剛開始彆彆扭扭,可是奇怪,轉了幾次,頭有點昏,可是我居然遊刃有餘地唱出來了!
雅格娜給了我很多機會,帶我去了希臘、北德諸多城市參加研習營及演出,讓我集結了不少舞臺經驗,也和許多聲樂研究所學生及歌劇院唱將同臺演出過。有一次在Liebstadt的演唱會中,我大膽嘗試演唱中國藝術歌曲和民歌,想不到竟成為當晚高潮,壓軸的節目其實是聲樂研究所的高材生女高音演唱「羅西尼」的花腔歌劇選曲,但是節目結束後記者一窩蜂地來採訪我,事後雅格娜遞給我看當地的報紙,標題「天生下來愛唱歌的臺灣姑娘」!她說,恭喜啊Cindy,看來觀眾和記者都很喜歡妳呢!從此不知多少次,應觀眾要求,要我把「姑娘生來愛唱歌」一唱再唱。
雅格娜跟我說,想像妳的音色在哪兒,用眼睛看到它,它就在那兒!全世界都跟妳說”No“的時候,只有妳, 妳唱出來,就跟自己和全世界說:Yes!
那五年,我不但每個禮拜飆車至埃森上聲樂課,還開車去Ratingen找老師上「歌劇指導」課(Correpetition)。教歌劇指導的多明尼克老師很兇,從頭到尾眉頭皺皺,叫我拿到譜就得馬上唱,只要一唱錯,或是表達不盡他的理想,就猛敲鋼琴,大搖其頭,說「 錯錯錯全部錯!」弄得我神經緊張,越錯越多。有一次去大學上他的團體課,見他把學生一個一個叫到臺上去「詮釋」神劇選曲,然後一個一個地罵:「這種唱法?拜託,我看你還是去開計程車好了,學什麼聲樂?」害我躲到最後一排去,把頭縮在個子高的同學後面,輕聲拿出隨身攜帶的寫生簿,低頭給眉頭皺皺、肚子大大的多明尼克老師速寫畫像。後來我把那一頁肖像撕下來,貼在謝卡上,寄給老師,但是以後真的不敢去上他的課了。想不到半年後我在埃森的演唱會中,竟見他笑眯眯地坐在觀眾席裡,為我鼓掌!
還有一陣子跟來自蘇聯的鋼琴家塔曇尼雅合作,我二人共辦了三場演唱會。塔曇尼雅不會開車,她家又住得遠,光搭火車來離我家最近的車站就要一個半小時,我再開車半小時去車站接她,這麼來來回回,光是路程就得花三、四個鐘頭,但是為了練唱,而且可以以樂會友,再多的舟車勞頓都值得。塔曇尼雅特別推崇意大利鬼才女高音 Cecilia Bartoli,她把家裡蒐藏的Bartoli演唱會錄影帶全拿來借我,要我一看再看,學她的音色表情,收放自如、渾圓厚實的中低音。是的,她不斷加強我的中低音訓練,用呼吸法把腹腔、橫膈膜、肋骨全都撐開。塔曇尼雅說得對,中低音是地基,它穩固了,高音就會自然而然地優美沖天。
為了唱歌,我東奔西跑,到處找老師,每天早起來就發聲練唱,在此得特別對長年來忍受我無限制高歌的鄰居致謝。有一次演唱會結束,我的鄰居克莉絲汀特跑來後臺擁抱我,說,我以為我每天聽,已經聽得不想再聽了,想不到坐在觀眾席聽妳唱,還是感動得熱淚盈眶。
直到六年前我遇到了來自科隆的鋼琴家Rainer Schrapers,終於結束了我東奔西跑的唱歌學習生涯。Rainer每個禮拜來我家跟我合伴奏,合作至今,大小演唱會數不清有多少。默契穩定了,技巧就不自覺地融進了歌聲和感情中,所謂的「風格」就娓娓顯露出來了。
唱歌發聲,喊完了,生活中的小憂小愁也都被沖散了,更重要的,藉著唱歌我在異鄉交到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把異鄉變成了真正的故鄉!我和愛唱歌的朋友在杜塞道夫市共組了個「福爾摩沙華語合唱團」,不但教華人唱多聲部的華語歌曲,還帶愛唱中文歌的德國人也來同樂。今年七月我們在波昂國際文化節代表臺灣團體上臺演唱,節目結束後一位德國團員來跟我說,Cindy,謝謝,這真是我最好的心理治療,什麼棘手的憂鬱症全都煙消霧散了!
一年半前在教會辦的演唱會上我和男低音Ralf Feldhoff合唱「魔笛」裡的「鳥人二重唱」--「帕帕給諾」和「帕帕給娜」才剛墜入情網就吵著以後要生男還是生女,吵著吵著,還是相擁而唱:管他生男還是生女,啊!為人父母真快樂,為人父母真是會無比快樂啊!音樂會結束,Baby剛滿三個月的百啼娜跑來跟我說,雖然夜裡起來餵奶,初為人母忙得手忙腳亂,聽了妳們的「鳥人二重唱」,忽然意識到,原來我有多幸福,多快樂!
二十幾年前初識安德烈的時候,他說,他老爸開工廠,媽媽是家庭主婦,「那妳父母呢?」他問。
「我老爸造橋修路,我老媽啊……」,講到我老媽我總是格外得意,我說:「我媽是聲樂家、女高音,她很有名氣呢!」
「什麼?那個呀……」他居然面露難色地皺眉咽口水。
「怎麼啦?」我說:「你知道的嘛,唱古典歌劇的,茶花女、費加洛婚禮……那些,我也很愛唱的,你聽,啊~啊~(我信口捻來兩句「魔笛」夜之后的詠嘆調過門,自認聽起來還蠻以假亂真的)」,「我知道,我知道,」然後結結巴巴地,「只是,我老爸說的啦,不是我哦,他每次一聽到電視上或收音機裡女高音演唱,就撫著面頰說:『轉臺轉臺,別聽這種令人牙痛的鬼叫歌聲!』所以,我承認有點受老爸觀點影響啦!」
怎麼「有藝術水準」的德國人會有這種想法呢?德國是巴哈、蕭邦、貝多芬的故鄉,不是人人都愛欣賞歌劇和古典聲樂嗎?我承認,有些強調皇家水準的古典「學院派」唱起女高音的詠嘆調來真的讓人敬而遠之,一想到得正經危坐地聽她雙手握拳摀著小腹,滿臉痛苦地從丹田中逼出驚人的高音時,牙痛也許真的難免。但是,真正的聲樂訓練是任何一種歌唱技巧的基礎功,至於該怎麼表達,實在是見仁見智。我敢說,親臨過我母親演唱會的觀眾,肯定都會大點其頭地說:趣味、享受、意猶未盡。不但喜歡,而且會上癮!
這種意猶未盡的趣味和享受,我暗中思忖,接下來首要任務就是要引導安德烈和他的父母去欣賞,別的不敢說,但是起碼保證他們越聽牙齒會越健康!
學唱歌、登臺,從小舞臺到大舞臺十幾年來,如今幾乎每個月都會有大小的演唱會邀約。山丘小鎮的教會、合唱團、管風琴師辦的大小活動、義演工藝團體、華人文化團體,都喜歡找我去高歌數曲、軋一角。元月份教會辦的募款活動後來結算,除掉租場地、燈光、音響的開支,想不到我們小地方竟募到了三千多歐元的款項,承辦人後來跟我大大致謝,說觀眾幾乎都是衝著Cindy的歌聲慕名而來的。聽得我真是輕飄飄。但是,歌唱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把原來受到父親誤導、一聽到女高音歌聲就牙痛的另一半,訓練成為我的頭號歌迷,現在他還是我帶的「福爾摩沙合唱團」裡的中堅男低音,每回練完唱,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他總要跟我說:「好好玩,好好玩!唱歌這麼好玩怎麼以前我都不知道?」
其實小時候並沒打算走唱歌這條路的。媽媽在家教學生,她對學生的諄諄教誨我每天總要聽個好幾遍,聽著聽著就潛移默化,學生在鋼琴房內練唱發聲「啊~啊~」,我邊做功課也邊「啊~啊~」,媽媽注重訓練學生的姿勢臺風,常叫學生要對著鏡子唱,所以我把功課撇一邊,也去對著鏡子唱,唱著唱著竟發現,我還真像媽媽!我心血來潮跑去跟媽媽說:「看,我會學妳唱歌!」媽媽先是發愣,之後大笑,說:「這孩子去考聲樂系,一定沒問題!」可是,不知為何,後來考大學根本沒往這方面去動腦筋。而這點「學媽媽」的模仿功夫只成了家中宴客、茶餘飯後的餘興節目,客人撫掌大笑後,也常說,Cindy不往聲樂方面發展太可惜了!
我記得我的波蘭籍聲樂教授雅格娜曾告訴我她學習聲樂的故事。她的母親是一九五○、六○年代波蘭的首席著名女高音,有「華沙的黃鶯」之美譽,父親也是當時小有名氣的鋼琴家兼作曲家,但是她年紀輕有自己的主張,選擇和父母走完全不同的路,大學裡她主修了「日本文學」。我聽得出神,一九六○年代的波蘭和日本有什麼關係呢?等不及問:「然後呢?」她說,「然後,我的聲音破谷而出,這聲音,是上帝給你的禮物,壓抑不住的,它會自己找到路子,就是要唱出來,而且會被聽到!So-desそです」所以,她的聲音破谷而出,不但走了這條路,還當了聲樂教授。
我的聲音是否也是自己找到了路子?其實也說不清楚,我只知道,在這個無聲無息的森林小鎮裡,沒有卡拉OK,沒有一票「歌友」,真悶!唱歌,不能說是「認真努力的朝目標前進」,其實目標是什麼,當時也不太清楚;只是不可自拔地。非。唱。不。可!一唱,精神就來了,我家狗狗、鳥兒都跟著唱,卡通裡寂寞公主和森林中小動物合唱的畫面,果然成真!
這一切還得感激繪畫。二十七歲時在美術學院已修了好幾年的課,終於在拉得弗森林小鎮開第一次的個展,特別請母親來德國,以她的歌聲為我的畫展揭開序幕。無巧無不巧,韓國籍男高音Jael Jul Lim也被朋友拉來看畫,聽到我母親的歌聲,驚為天人,推崇不已。一個禮拜之後,他打電話給我,說,雖然只看了我的畫,沒聽過我唱歌,但是猜想,虎母無犬女,願不願意拜他為師?不不,不是只為了要收學生賺錢,是這樣的,他正與室內樂團、山丘音樂學校籌辦明年的音樂節,計劃將「魔笛」的部分場景搬上舞臺,問我是否有興趣共相盛舉,出一臂之力?比如說,從事舞臺佈景繪畫?我大喜過望,好像收到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說實在話,我想唱歌想瘋了!而從事舞臺佈景設計也是極度令人興奮的差事。向來山丘森林小鎮把我和繁華世界隔絕,除了安安靜靜地畫畫,還真沒什麼人跟我講話,這下竟然有如此「盛舉」邀請我加入,怎麼能不開心呢?
後來,在那次的音樂節裡我擔任了魔笛公主帕米娜的角色,總彩排的時候兒子剛滿一歲八個月,看到妖人「薩拉斯妥」居然要綁架公主媽媽,樂團鑼鼓笙簫地製造危險音效,嚇得他大哭大叫,衝到臺前非要媽媽抱。這件軼事,至今還為當時的共事人津津樂道呢,只是我家十四歲的酷哥兒怎麼也不承認當年他竟會那麼不酷。
後來韓國老師回了韓國。我求地利之便,便與小鎮和我年齡相仿的女中音繼續上課。唱歌本身無比快樂,但是年輕的女中音老師常跟我強調,她是正規大學音樂系畢業,而我是半路出家的業餘歌者,怎麼也別想達到她的「專業」歌唱素質。學習聲樂至此,我從未想過專業不專業這回事,不知為何,聽了她的專業忠告卻經不住任性,我非得唱出什麼東西來!專業是什麼?若歌唱只剩下呼吸、技巧和文憑,是否就是專業大歌唱家了?
I want to be MORE!但是森林原野廣稠無際,我怨有志難伸……
魔笛演出四年之後,我家老二也長到了兩歲,才在一次小鎮演出中場休息中認識了Wuppertal來的鋼琴家Rempel女士,Rempel特別驚訝我並沒在大學受過正式聲樂訓練,她說,我的聲音,只在這兒小鎮唱唱,不去大城市裡找好老師學,實在可惜了。
經Rempel女士介紹,我認識了埃森符克丸音樂學院(Folkwang Musik Hochschule)的雅格娜教授(Jagna Sokorska Kwika)。雅格娜給我上了兩次課就遞給我符克丸音樂學院的報考表格,叫我從現在起就開始練習甄試曲目。我盯著表格看,腦中閃過小時候媽媽的評語、親友的期許,如今,兩個小小孩的媽,我真的還能進音樂學院走這條路嗎?我說,「可是,我的兩個孩子這麼小,我......」
「什麼?」雅格娜說,「妳才幾歲?已經兩個小孩了?」
「我……我快三十二了。」
「三十二?」雅格娜一副不可置信的樣兒,「妳們亞洲人的年齡真是謎,要我猜的話,我以為你才二十二、三呢。這樣的話,報考音樂學院就不行了,音樂學院的報考年齡限制是二十七。不過,我真的喜歡妳的聲音,琢磨幾年,肯定別出凡響,妳願意的話,就做我的私人學生,我提供妳參予所有活動、音樂會,甚至考試的機會,怎麼樣?」
就這樣,我跟著雅格娜學習有五年之久,孩子白天上幼稚園,我就飆車去埃森上課。雅格娜的發聲教法很不同凡響,她的教室裡總是備有腳踏車橡皮輪胎圈一條,輪胎圈的一頭套在門把上,另一頭卡在臀部下,唱到高音,身體必須略蹲並往後退一步,橡皮輪胎圈就剛好襯住下蹲的臀部,「就是那兒!」雅格娜說,「發音中樞就在下腹部,往下坐,妳就感覺到了!」有些技巧部分我苦練死練,無奈總是時好時壞,把自己弄的很沮喪,雅格娜說:「我知道妳會的,妳只是想得太多,越想越對自己沒信心。跳舞吧!唱到這兒妳就隨著旋律轉圈圈!」剛開始彆彆扭扭,可是奇怪,轉了幾次,頭有點昏,可是我居然遊刃有餘地唱出來了!
雅格娜給了我很多機會,帶我去了希臘、北德諸多城市參加研習營及演出,讓我集結了不少舞臺經驗,也和許多聲樂研究所學生及歌劇院唱將同臺演出過。有一次在Liebstadt的演唱會中,我大膽嘗試演唱中國藝術歌曲和民歌,想不到竟成為當晚高潮,壓軸的節目其實是聲樂研究所的高材生女高音演唱「羅西尼」的花腔歌劇選曲,但是節目結束後記者一窩蜂地來採訪我,事後雅格娜遞給我看當地的報紙,標題「天生下來愛唱歌的臺灣姑娘」!她說,恭喜啊Cindy,看來觀眾和記者都很喜歡妳呢!從此不知多少次,應觀眾要求,要我把「姑娘生來愛唱歌」一唱再唱。
雅格娜跟我說,想像妳的音色在哪兒,用眼睛看到它,它就在那兒!全世界都跟妳說”No“的時候,只有妳, 妳唱出來,就跟自己和全世界說:Yes!
那五年,我不但每個禮拜飆車至埃森上聲樂課,還開車去Ratingen找老師上「歌劇指導」課(Correpetition)。教歌劇指導的多明尼克老師很兇,從頭到尾眉頭皺皺,叫我拿到譜就得馬上唱,只要一唱錯,或是表達不盡他的理想,就猛敲鋼琴,大搖其頭,說「 錯錯錯全部錯!」弄得我神經緊張,越錯越多。有一次去大學上他的團體課,見他把學生一個一個叫到臺上去「詮釋」神劇選曲,然後一個一個地罵:「這種唱法?拜託,我看你還是去開計程車好了,學什麼聲樂?」害我躲到最後一排去,把頭縮在個子高的同學後面,輕聲拿出隨身攜帶的寫生簿,低頭給眉頭皺皺、肚子大大的多明尼克老師速寫畫像。後來我把那一頁肖像撕下來,貼在謝卡上,寄給老師,但是以後真的不敢去上他的課了。想不到半年後我在埃森的演唱會中,竟見他笑眯眯地坐在觀眾席裡,為我鼓掌!
還有一陣子跟來自蘇聯的鋼琴家塔曇尼雅合作,我二人共辦了三場演唱會。塔曇尼雅不會開車,她家又住得遠,光搭火車來離我家最近的車站就要一個半小時,我再開車半小時去車站接她,這麼來來回回,光是路程就得花三、四個鐘頭,但是為了練唱,而且可以以樂會友,再多的舟車勞頓都值得。塔曇尼雅特別推崇意大利鬼才女高音 Cecilia Bartoli,她把家裡蒐藏的Bartoli演唱會錄影帶全拿來借我,要我一看再看,學她的音色表情,收放自如、渾圓厚實的中低音。是的,她不斷加強我的中低音訓練,用呼吸法把腹腔、橫膈膜、肋骨全都撐開。塔曇尼雅說得對,中低音是地基,它穩固了,高音就會自然而然地優美沖天。
為了唱歌,我東奔西跑,到處找老師,每天早起來就發聲練唱,在此得特別對長年來忍受我無限制高歌的鄰居致謝。有一次演唱會結束,我的鄰居克莉絲汀特跑來後臺擁抱我,說,我以為我每天聽,已經聽得不想再聽了,想不到坐在觀眾席聽妳唱,還是感動得熱淚盈眶。
直到六年前我遇到了來自科隆的鋼琴家Rainer Schrapers,終於結束了我東奔西跑的唱歌學習生涯。Rainer每個禮拜來我家跟我合伴奏,合作至今,大小演唱會數不清有多少。默契穩定了,技巧就不自覺地融進了歌聲和感情中,所謂的「風格」就娓娓顯露出來了。
唱歌發聲,喊完了,生活中的小憂小愁也都被沖散了,更重要的,藉著唱歌我在異鄉交到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把異鄉變成了真正的故鄉!我和愛唱歌的朋友在杜塞道夫市共組了個「福爾摩沙華語合唱團」,不但教華人唱多聲部的華語歌曲,還帶愛唱中文歌的德國人也來同樂。今年七月我們在波昂國際文化節代表臺灣團體上臺演唱,節目結束後一位德國團員來跟我說,Cindy,謝謝,這真是我最好的心理治療,什麼棘手的憂鬱症全都煙消霧散了!
一年半前在教會辦的演唱會上我和男低音Ralf Feldhoff合唱「魔笛」裡的「鳥人二重唱」--「帕帕給諾」和「帕帕給娜」才剛墜入情網就吵著以後要生男還是生女,吵著吵著,還是相擁而唱:管他生男還是生女,啊!為人父母真快樂,為人父母真是會無比快樂啊!音樂會結束,Baby剛滿三個月的百啼娜跑來跟我說,雖然夜裡起來餵奶,初為人母忙得手忙腳亂,聽了妳們的「鳥人二重唱」,忽然意識到,原來我有多幸福,多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