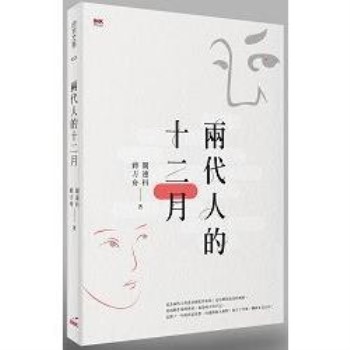一月:偏見是溝通的水流
一則閑遇
一月三日下午,從地鐵6號線換4號線去北京南站,自平安裡換乘上車後,因人多站立,便和面前一對二十幾歲的大學生(似是)、又像讀研者的戀人站在一塊兒,他們看著各自的手機,耳朵中還彼此聽著來自男方手機上一分為二、各人一個的耳塞(也許是聽音樂)。聽著看著間,他們你我望一眼,笑一下,那幸福宛若擺在鬧市的花,你們擠嚷,你們奔忙,我自安靜的開放和燦然。讓人覺得今天這中國,這世界,於他們說來,天藍水碧,風和日麗,一切都是好的和美的。
我有些嫉妒他們的年齡和屬於他們的偉大時代了。
心嫉著,車就那麼平穩嗡嗡地走。走著間,女的忽然取下自己左耳上的音樂塞,收起她的蘋果手機對著男的悄然說:
「今天我們導師又給我們講他二十多年前的光榮歷史了。」
男生些微吃驚的望著她。
女生笑一笑:「要是又有那事你會參加嗎?」
男生沉默而猶豫,好像在揣摩該怎樣去回答。
女生說:「比如說就那年那樣的事情呢?」
男生沉靜許久,笑笑搖搖頭。
女的也笑笑:「那要是畢業讓你去新疆和西藏?」
男生很堅定的搖搖頭。
女生沉靜一會再問道:「當兵呢?打仗呢?」
男生說:「我又不是傻逼。」
八○後:怯弱的一代/閻連科
世世代代,上輩人總在抱怨下輩人的不足,如同兒女總是要在父母的指責中長大樣。「八○後」與「九○後」,今天正是在這被抱怨和指責中,豁然地長大起來了,走進校園、走進社會,走進道德和口水的垃圾場。叛逆、自私、宅獨、濫情、性殤、物化,看見錢就像看見了爹;看見爹像看見了樹。大樹或小樹,壯樹或枯樹,凡此種種,人們把整個社會淪喪的污水,以愛和文化的名譽,匯在代際的龍鬚溝裡,又一桶一桶地汲將上來,大度地澆在八○、九○這兩代人的身子上,感歎他們生逢其時的物質條件,再也不需像父母那樣,把吃飽穿暖作為人生的最大之理願;像父母那樣,把對國家宏達的忠誠,化為自己跌宕的血液;將男女的牽手和胳膊肘不慎的一碰,視為觸電般的愛情與忠貞。他們有他們的世界觀、物質觀,有他們自己對人生理願的追求和偏愛。
關於世界,至於他們不光是一種地理,還是雙腳的踏行和交往,而被他們更正的世界和世界觀,不再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劃分了,而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及「貧窮非洲」的經濟區。簡言之,世界的構成,就是窮人、富人和正在走向富裕的人。就是老鼠、貓和機器人。
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昨天那遙遠廣泛的美好,就是今天的就業、車子、房子和一管口紅與一款名包的差別;是上班開車、地鐵和到辦公室後喝茶、看報與公司的無數報表及數據的差別;是入黨時舉起右手和受挫時私捏雙拳的差別;以及面對無數高官貪腐落馬如秋風落葉時,你是憂慮、喝彩還是起哄熱鬧和冷眼旁觀的差別;再或者,就是面對中國和邊鄰國家的緊張摩擦時,你是民族主義還是冷眼主義的差別。
國家,就像一款丟不掉的衣服,是把他穿在身上還是提在手裡,這對於八○的一代,有著本質的不同。
家庭、婚姻、愛情,日雜瑣碎和結婚離婚,對做小三的理解與支持,包容與不屑,性觀念的淡化與放開,凡此種種,都在這一代人的身上有著全新的詮釋和踐行。在家庭的觀念上,真正變化的不是孝道、養老、婚姻的維繫與散離,生男生女的歡樂與選擇,而是對情人、性行為和出軌的認識與態度。總之說,這一代人,和其父母是截然不同了。父母覺得衣服舊了還可以穿,「縫縫補補又三年」。而他們,覺得款式、品牌過時或將要過時就應該換一換。必須換一換。從動物園購物和到三裡屯喝咖啡,不僅是兩種生活方式,而且是兩個階層的趨向。自己買房和租房共居,不僅是富裕和貧薄的物證,而且是人生尊嚴的精神證明。這就是兩代人的存在和不同,是上一代人指責、抱怨下一代的出據和憑證,如我們今天把一切的環境惡化都指責為氣候變暖樣,由此推斷出今天霧霾的籠罩,是經濟發展之必然,明天肺癌率和死亡率的大幅提升,也是一種必然和無可逃離的中國人的宿命。然而,情況是真的這樣嗎?八○後與九○後,就真的與我們是那樣不同嗎?他們與父母、爺奶除了血脈的聯繫,其餘都草繩與剪了?還有屬於他們一代人的精神氣質,真的就是化妝品帶來的愉悅和床底歡樂後的痛楚?是今天工作、工資的苦惱和明天一對夫妻面對四個老人或六個老人的負擔?叛逆、自私、宅獨、濫情、性殤、物化,就真的是這一代的符號和特徵?能不能用一個更簡單、精準的字詞、句子去描繪這一代與上一代的差別與獨到?比如我們說老一代人只說兩個字:「革命。」說四九年後的一代也就兩個字:「理想」。說十年文革也就一個字或者兩個字:左或極左;兩個字或三個字:災難或大災難。但到了八○和九○的一代人(九○是八○的延續和發展?),我們又能怎樣去說、去判斷?
說叛逆,他們又有過怎樣驚人的屬於一代人的叛逆呢?有過如他們爺奶或老爺、老奶那樣,集體一群一群的為了革命——或共產主義,就丟掉父母、兒女,不管不顧地奔赴延安的行為嗎?說物化,他們有過對財富的貪求,像他們的父母一代樣,做公司,做股票、房產或者股東商,倒買倒賣,空手白狼,把全部的財富理想都集中在一個錢字上;對福布斯排行榜敏感到到底入不入榜,是明富還是暗富,明富了又會在福布斯榜上排第幾,落後於誰時,就不僅是財富多少之比對,而是政治、權勢、地位之比對。說他們濫情和性殤,又是誰在享受了他們的濫情和性殤?是哪一代人用怎樣的方式誘惑、引導和完成了他們的濫情和性殤?濫情和性殤,是他們自己完成的,還是由他們父母一代引誘完成的?如同一個教授在引誘他的學生時,首先要用他的學識開導一番她的女生對感情與性行為應持怎樣現代、開放的態度樣,當女生接受了導師的教導,使導師享受了她的肉體後,導師在日後的冷靜裡,又開始思考、指責她(一代人)的下流、淪喪和無底線。現在,上一代人指責八○、九○者享受物化、沒有底線時,指責一代人寧可嫁給開寶馬的「父親」,也不嫁給騎自行車的「同桌」時,是沒有考慮他們作為淪喪的導師,給八零、九零傳授了什麼的。沒有考慮八○、九○的孩子們,又從他們爸媽、爺奶那兒繼承了什麼呢。彷彿他們一代人的錯落,是天然天生的,與時俱來的,與這個原有的世界沒有關係的。不能明白,那些業已三十而立的八○一代人,你們讀了不算少的書,經過了不算少的世事和經驗,當整個社會都在指責你們這樣、那樣時,為什麼沒有人站出來言論與立說,對這個時代和你們的父輩、爺奶們辯解一些什麼呢?為什麼不可以把上一代人的衣服裸扒下來,讓他們的瘡口也展擺在世人面前呢?想到當年韓寒和批評家白燁關於八零後的寫作是不是文學的那場文憤之論戰,誰是誰非,已經不重要,但你們這一代人的朝氣和激情,在這十餘年裡去了哪兒了?
在這個被權力和金錢統治的世界裡,財富不僅被階層和特殊的人群壟斷著,而且聲音——可以發聲的一切地方,也都有權力和金錢的開關和操手,而成千上萬的八○一代和已經緊跟接上的九○們,教育不公的時候你們是沉默的;沒有就業機會的時候你們也是沉默的;就是同齡的女友跟著父輩入房同床了,你們也還依然是沉默的。而當終於可以結婚成家時,方明白結婚必須要有床位和廚衛時,雙方父母傾其所有,才在居高不下的房價中用一生的喘息,為你們的婚姻和家庭換來一處人生歇息的角落後,你們站在那角落裡,順耳聽著「啃老族」的嘲諷,面帶默認的微笑,並不怎樣覺得尷尬與委屈,也更是鮮有誰站出來大喝一聲道:
「我們為什麼變成了這樣兒?!誰把我們擠進角落變成了這樣兒?!」
上班擠不進公共汽車和地鐵,你們把身子側起來;領工資時發現就是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也沒有分文的加班費,也都無言認下了。你們把飯後留在桌上的餐巾紙,收入體內用以鼓囊本應厚實的錢包和口袋;走進醫院為一個專家號,不是頭天半夜去排隊,就是心甘情願去買倒號手們翻了兩倍、三倍的高價號。春節回家買不到或買不起飛機票和火車票,有無數八零、九零的博士、碩士、大學生,就索性春節不回家。這個世界就是一台巨大的壓榨機,榨你們爺奶的、榨你們父母的,當他們老去乾枯了,你們後續而來正年輕,青春綠旺,血液飽滿,那台機器就用更為隆隆的響聲和轉速,開始榨取著你們青春的肌理和骨髓之血液。因為你們什麼都認同,什麼都不懷疑和試問。需要選超男超女時,你們把胳膊舉了起來了,將神聖的票權投到那兒了;面對電影、電視的輕賤和娛樂,需要你們張開口袋、發出笑聲,以證明國泰民安時,你們把最爽朗、純真的笑聲和掌聲,大度豁豁地獻了出去了;需要你們在微博、微信和朋友圈裡只這樣而別那樣時,你們就只是這樣而不那樣了;你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最終就成為了最為配合榨取的一代人。把理想確定在「蘋果」的換代上,把思想確立在不存懷疑的順從上,哪怕是最需要創造性的文學與藝術,也都在配合和順從中認同和創作。於是間,社會、時代、前輩、人人,都可以說你們自私、物化、濫情、性殤了。可以說你們「沒有底線」、「無可救藥」了。
因為,說你們什麼,你們都不會反駁。
因為,需要你們怎麼,你們就會怎麼。
因為你們爺爺、奶奶那時浪漫的革命激情,在今天看來,似乎單純到可笑,可那也終歸是一種青春的激情。而這青春的激情,在你們身上不知為何就河幹濤盡了,沒有水流了。父輩們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瀕死的饑餓你們沒有過;上山下鄉高揚紅旗的熱情你們沒有過;從長安街上隊伍著手拉手的血脈臌脹你沒有過。你們似乎什麼都有,可就是沒有那種為一個民族如何如何的浪漫和激情。你們可能什麼都沒有,唯一有的是對這現實與世界取之不竭的認同感。你們在學校會懷疑同桌的一句話和一件事,而不懷疑教育之本身。到了社會上,你們懷疑自己的能力而不懷疑社會的機遇。汶川大地震中可以赴滔搶險,呈一時之壯,而事後卻兩廂遙遠,相安無事;可以為「父親是李剛」而群起提問和搜索,但也可以為比「李剛」的父親更職高權貴者的惡作而沉默。
沒有人知道你們整整一代人或兩代人為什麼會如此的順從和怯弱,也沒有人能明白你們為何甘願為了怯弱而怯弱。
社會不需要議論民主、平等和自由,你們就不談論這些了。甚至連「公民」、「憲政」這樣的字眼也幾乎從你們這一代的嘴裡消失了,哪怕是對「公民」、「憲政」的批評與批判,你們也都懶得張口去說長和道短。對這些事情的冷漠與疏離,如同小樹怕風樣,要把自己的枝葉有意張揚在避風朝陽的向面上。不需要思考現實的為什麼,只需要思考自己面對現實怎麼做。這一點在你們整整一代、兩代都來得齊整和盎然,心甘情願,任勞任怨,如同黃牛對冬季枯草的認同:既然是冬季的到來,有麥秸與荒坡的枯乾,那就完全可以不去追求自己伏耕時為主人收穫的豆料庫藏了。
實在不知道,你們為何會在如此無序混亂的社會裡,如此有序的認同和沉默。
實在不知道,你們為何會在對你們萬人所指的唾棄中,如此集體的默認和沉默。
實在不知道,在這隆隆盤旋的巨大的社會壓榨機器中,你們正成為最被壓榨的整整一代、兩代人,你們卻仍然能發出集體沉默的微笑來。
沉默源於怯弱。
怯弱而必然沉默。
……
但不要只是因為你年輕/蔣方舟
但不要只是因為你年輕
十四年前,剛剛退學的韓寒,帶著自己剛剛出版的《三重門》參加央視一個叫做「對話」的節目。
在整個節目的錄製過程中,他被當作一個犯罪嫌疑人一樣對待,主持人咄咄逼人,社科院的專家認為他只是曇花一現,還有一個紮著麻花辮的女觀眾說韓寒是「土雞」——理由是韓寒用聊天室聊天,而不是像她一樣用OICQ和ICQ。甚至,為了反襯韓寒的失敗,他身旁還坐了一個成功的垘本——考上北大的少女黃思路。
十四年後,我去參加央視一檔節目的錄製,內容是「非一般年輕人」的演講,其中大部分是九○後,○有科學家,有創業者。
演講者都朝氣蓬勃,而我很快就發現自己的位置非常尷尬,我和一群從三○後到八○後不等的老年人,坐在觀眾席中被架得很高的白凳子上,腳不著地,舉著一塊寫有自己出生年分的熒光板,帶著詭異的慈祥笑容聽這些年輕人的演講。
我們這群老年人,並不像當年「對話」節目中的專家一樣,是年輕人的評委,而是對年輕人喪心病狂的讚美者。
我們在每個演講之後發言,場景介於中學生演講比賽和「感動中國」頒獎典禮之間,每個人都生怕溢美之詞被他人搶去,因而抱著話筒無休止地進行排比句造句:「青春是一顆種子/一朵花/一棵樹/一根蠟燭……」最後聲嘶力竭地以諸如「青春無敵!做你自己!正能量!耶!」作為結束,非常地累。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某個應用軟件的CEO,九○後,非常瘦小,他抱著一個大狗熊玩偶上台,一上台就把狗熊扔到台上,說:「我覺得這個讓我抱熊的導演特別傻。」他的演講裡不無豪言壯語,例如「明年給員工派發一個億利潤」之類。而台下的大學生,則在每一次聽到「第一桶金賺了一百萬」「阿裡巴巴用千萬美金收購」這類句子時,羡慕地齊聲譁然。
他的演講,雖然充滿了明顯的誇大和對他人的不屑,可卻獲得了當天錄製最大的掌聲,以及最熱烈的溢美。
前輩們的興奮,在於終於找到了自己心目中典型的九○後,就像親眼看到外星人時,發現它就是自己想像中的銀色大頭娃娃。那個年輕的CEO符合社會對於九○後一切的想像:輕狂、自我、混不吝。
當節目播出時,他的視頻在社交網絡上風靡,配以標題諸如「九○後的話,惹怒了所有的互聯網大佬」「九○後的一番話,讓全世界都沉默了。」
當我看到播出的節目裡,所有被侮辱和輕視的中年人,都像受虐狂一樣大力地鼓掌,賣力的歡笑,我忽然想到十四年前參與韓寒節目錄製的中年人,當年臺上的那些中年專家還在麼?他們依然怒不可遏嗎?還是成了舉著寫有自己出生年份的老年人,一聽到「追逐夢想」「初生牛犢」幾個字,就在煽情的音樂中熱烈鼓掌呢?
風水輪流轉,中年人在話語權的爭奪中,成了弱勢群體。
一則閑遇
一月三日下午,從地鐵6號線換4號線去北京南站,自平安裡換乘上車後,因人多站立,便和面前一對二十幾歲的大學生(似是)、又像讀研者的戀人站在一塊兒,他們看著各自的手機,耳朵中還彼此聽著來自男方手機上一分為二、各人一個的耳塞(也許是聽音樂)。聽著看著間,他們你我望一眼,笑一下,那幸福宛若擺在鬧市的花,你們擠嚷,你們奔忙,我自安靜的開放和燦然。讓人覺得今天這中國,這世界,於他們說來,天藍水碧,風和日麗,一切都是好的和美的。
我有些嫉妒他們的年齡和屬於他們的偉大時代了。
心嫉著,車就那麼平穩嗡嗡地走。走著間,女的忽然取下自己左耳上的音樂塞,收起她的蘋果手機對著男的悄然說:
「今天我們導師又給我們講他二十多年前的光榮歷史了。」
男生些微吃驚的望著她。
女生笑一笑:「要是又有那事你會參加嗎?」
男生沉默而猶豫,好像在揣摩該怎樣去回答。
女生說:「比如說就那年那樣的事情呢?」
男生沉靜許久,笑笑搖搖頭。
女的也笑笑:「那要是畢業讓你去新疆和西藏?」
男生很堅定的搖搖頭。
女生沉靜一會再問道:「當兵呢?打仗呢?」
男生說:「我又不是傻逼。」
八○後:怯弱的一代/閻連科
世世代代,上輩人總在抱怨下輩人的不足,如同兒女總是要在父母的指責中長大樣。「八○後」與「九○後」,今天正是在這被抱怨和指責中,豁然地長大起來了,走進校園、走進社會,走進道德和口水的垃圾場。叛逆、自私、宅獨、濫情、性殤、物化,看見錢就像看見了爹;看見爹像看見了樹。大樹或小樹,壯樹或枯樹,凡此種種,人們把整個社會淪喪的污水,以愛和文化的名譽,匯在代際的龍鬚溝裡,又一桶一桶地汲將上來,大度地澆在八○、九○這兩代人的身子上,感歎他們生逢其時的物質條件,再也不需像父母那樣,把吃飽穿暖作為人生的最大之理願;像父母那樣,把對國家宏達的忠誠,化為自己跌宕的血液;將男女的牽手和胳膊肘不慎的一碰,視為觸電般的愛情與忠貞。他們有他們的世界觀、物質觀,有他們自己對人生理願的追求和偏愛。
關於世界,至於他們不光是一種地理,還是雙腳的踏行和交往,而被他們更正的世界和世界觀,不再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劃分了,而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及「貧窮非洲」的經濟區。簡言之,世界的構成,就是窮人、富人和正在走向富裕的人。就是老鼠、貓和機器人。
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昨天那遙遠廣泛的美好,就是今天的就業、車子、房子和一管口紅與一款名包的差別;是上班開車、地鐵和到辦公室後喝茶、看報與公司的無數報表及數據的差別;是入黨時舉起右手和受挫時私捏雙拳的差別;以及面對無數高官貪腐落馬如秋風落葉時,你是憂慮、喝彩還是起哄熱鬧和冷眼旁觀的差別;再或者,就是面對中國和邊鄰國家的緊張摩擦時,你是民族主義還是冷眼主義的差別。
國家,就像一款丟不掉的衣服,是把他穿在身上還是提在手裡,這對於八○的一代,有著本質的不同。
家庭、婚姻、愛情,日雜瑣碎和結婚離婚,對做小三的理解與支持,包容與不屑,性觀念的淡化與放開,凡此種種,都在這一代人的身上有著全新的詮釋和踐行。在家庭的觀念上,真正變化的不是孝道、養老、婚姻的維繫與散離,生男生女的歡樂與選擇,而是對情人、性行為和出軌的認識與態度。總之說,這一代人,和其父母是截然不同了。父母覺得衣服舊了還可以穿,「縫縫補補又三年」。而他們,覺得款式、品牌過時或將要過時就應該換一換。必須換一換。從動物園購物和到三裡屯喝咖啡,不僅是兩種生活方式,而且是兩個階層的趨向。自己買房和租房共居,不僅是富裕和貧薄的物證,而且是人生尊嚴的精神證明。這就是兩代人的存在和不同,是上一代人指責、抱怨下一代的出據和憑證,如我們今天把一切的環境惡化都指責為氣候變暖樣,由此推斷出今天霧霾的籠罩,是經濟發展之必然,明天肺癌率和死亡率的大幅提升,也是一種必然和無可逃離的中國人的宿命。然而,情況是真的這樣嗎?八○後與九○後,就真的與我們是那樣不同嗎?他們與父母、爺奶除了血脈的聯繫,其餘都草繩與剪了?還有屬於他們一代人的精神氣質,真的就是化妝品帶來的愉悅和床底歡樂後的痛楚?是今天工作、工資的苦惱和明天一對夫妻面對四個老人或六個老人的負擔?叛逆、自私、宅獨、濫情、性殤、物化,就真的是這一代的符號和特徵?能不能用一個更簡單、精準的字詞、句子去描繪這一代與上一代的差別與獨到?比如我們說老一代人只說兩個字:「革命。」說四九年後的一代也就兩個字:「理想」。說十年文革也就一個字或者兩個字:左或極左;兩個字或三個字:災難或大災難。但到了八○和九○的一代人(九○是八○的延續和發展?),我們又能怎樣去說、去判斷?
說叛逆,他們又有過怎樣驚人的屬於一代人的叛逆呢?有過如他們爺奶或老爺、老奶那樣,集體一群一群的為了革命——或共產主義,就丟掉父母、兒女,不管不顧地奔赴延安的行為嗎?說物化,他們有過對財富的貪求,像他們的父母一代樣,做公司,做股票、房產或者股東商,倒買倒賣,空手白狼,把全部的財富理想都集中在一個錢字上;對福布斯排行榜敏感到到底入不入榜,是明富還是暗富,明富了又會在福布斯榜上排第幾,落後於誰時,就不僅是財富多少之比對,而是政治、權勢、地位之比對。說他們濫情和性殤,又是誰在享受了他們的濫情和性殤?是哪一代人用怎樣的方式誘惑、引導和完成了他們的濫情和性殤?濫情和性殤,是他們自己完成的,還是由他們父母一代引誘完成的?如同一個教授在引誘他的學生時,首先要用他的學識開導一番她的女生對感情與性行為應持怎樣現代、開放的態度樣,當女生接受了導師的教導,使導師享受了她的肉體後,導師在日後的冷靜裡,又開始思考、指責她(一代人)的下流、淪喪和無底線。現在,上一代人指責八○、九○者享受物化、沒有底線時,指責一代人寧可嫁給開寶馬的「父親」,也不嫁給騎自行車的「同桌」時,是沒有考慮他們作為淪喪的導師,給八零、九零傳授了什麼的。沒有考慮八○、九○的孩子們,又從他們爸媽、爺奶那兒繼承了什麼呢。彷彿他們一代人的錯落,是天然天生的,與時俱來的,與這個原有的世界沒有關係的。不能明白,那些業已三十而立的八○一代人,你們讀了不算少的書,經過了不算少的世事和經驗,當整個社會都在指責你們這樣、那樣時,為什麼沒有人站出來言論與立說,對這個時代和你們的父輩、爺奶們辯解一些什麼呢?為什麼不可以把上一代人的衣服裸扒下來,讓他們的瘡口也展擺在世人面前呢?想到當年韓寒和批評家白燁關於八零後的寫作是不是文學的那場文憤之論戰,誰是誰非,已經不重要,但你們這一代人的朝氣和激情,在這十餘年裡去了哪兒了?
在這個被權力和金錢統治的世界裡,財富不僅被階層和特殊的人群壟斷著,而且聲音——可以發聲的一切地方,也都有權力和金錢的開關和操手,而成千上萬的八○一代和已經緊跟接上的九○們,教育不公的時候你們是沉默的;沒有就業機會的時候你們也是沉默的;就是同齡的女友跟著父輩入房同床了,你們也還依然是沉默的。而當終於可以結婚成家時,方明白結婚必須要有床位和廚衛時,雙方父母傾其所有,才在居高不下的房價中用一生的喘息,為你們的婚姻和家庭換來一處人生歇息的角落後,你們站在那角落裡,順耳聽著「啃老族」的嘲諷,面帶默認的微笑,並不怎樣覺得尷尬與委屈,也更是鮮有誰站出來大喝一聲道:
「我們為什麼變成了這樣兒?!誰把我們擠進角落變成了這樣兒?!」
上班擠不進公共汽車和地鐵,你們把身子側起來;領工資時發現就是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也沒有分文的加班費,也都無言認下了。你們把飯後留在桌上的餐巾紙,收入體內用以鼓囊本應厚實的錢包和口袋;走進醫院為一個專家號,不是頭天半夜去排隊,就是心甘情願去買倒號手們翻了兩倍、三倍的高價號。春節回家買不到或買不起飛機票和火車票,有無數八零、九零的博士、碩士、大學生,就索性春節不回家。這個世界就是一台巨大的壓榨機,榨你們爺奶的、榨你們父母的,當他們老去乾枯了,你們後續而來正年輕,青春綠旺,血液飽滿,那台機器就用更為隆隆的響聲和轉速,開始榨取著你們青春的肌理和骨髓之血液。因為你們什麼都認同,什麼都不懷疑和試問。需要選超男超女時,你們把胳膊舉了起來了,將神聖的票權投到那兒了;面對電影、電視的輕賤和娛樂,需要你們張開口袋、發出笑聲,以證明國泰民安時,你們把最爽朗、純真的笑聲和掌聲,大度豁豁地獻了出去了;需要你們在微博、微信和朋友圈裡只這樣而別那樣時,你們就只是這樣而不那樣了;你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最終就成為了最為配合榨取的一代人。把理想確定在「蘋果」的換代上,把思想確立在不存懷疑的順從上,哪怕是最需要創造性的文學與藝術,也都在配合和順從中認同和創作。於是間,社會、時代、前輩、人人,都可以說你們自私、物化、濫情、性殤了。可以說你們「沒有底線」、「無可救藥」了。
因為,說你們什麼,你們都不會反駁。
因為,需要你們怎麼,你們就會怎麼。
因為你們爺爺、奶奶那時浪漫的革命激情,在今天看來,似乎單純到可笑,可那也終歸是一種青春的激情。而這青春的激情,在你們身上不知為何就河幹濤盡了,沒有水流了。父輩們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瀕死的饑餓你們沒有過;上山下鄉高揚紅旗的熱情你們沒有過;從長安街上隊伍著手拉手的血脈臌脹你沒有過。你們似乎什麼都有,可就是沒有那種為一個民族如何如何的浪漫和激情。你們可能什麼都沒有,唯一有的是對這現實與世界取之不竭的認同感。你們在學校會懷疑同桌的一句話和一件事,而不懷疑教育之本身。到了社會上,你們懷疑自己的能力而不懷疑社會的機遇。汶川大地震中可以赴滔搶險,呈一時之壯,而事後卻兩廂遙遠,相安無事;可以為「父親是李剛」而群起提問和搜索,但也可以為比「李剛」的父親更職高權貴者的惡作而沉默。
沒有人知道你們整整一代人或兩代人為什麼會如此的順從和怯弱,也沒有人能明白你們為何甘願為了怯弱而怯弱。
社會不需要議論民主、平等和自由,你們就不談論這些了。甚至連「公民」、「憲政」這樣的字眼也幾乎從你們這一代的嘴裡消失了,哪怕是對「公民」、「憲政」的批評與批判,你們也都懶得張口去說長和道短。對這些事情的冷漠與疏離,如同小樹怕風樣,要把自己的枝葉有意張揚在避風朝陽的向面上。不需要思考現實的為什麼,只需要思考自己面對現實怎麼做。這一點在你們整整一代、兩代都來得齊整和盎然,心甘情願,任勞任怨,如同黃牛對冬季枯草的認同:既然是冬季的到來,有麥秸與荒坡的枯乾,那就完全可以不去追求自己伏耕時為主人收穫的豆料庫藏了。
實在不知道,你們為何會在如此無序混亂的社會裡,如此有序的認同和沉默。
實在不知道,你們為何會在對你們萬人所指的唾棄中,如此集體的默認和沉默。
實在不知道,在這隆隆盤旋的巨大的社會壓榨機器中,你們正成為最被壓榨的整整一代、兩代人,你們卻仍然能發出集體沉默的微笑來。
沉默源於怯弱。
怯弱而必然沉默。
……
但不要只是因為你年輕/蔣方舟
但不要只是因為你年輕
十四年前,剛剛退學的韓寒,帶著自己剛剛出版的《三重門》參加央視一個叫做「對話」的節目。
在整個節目的錄製過程中,他被當作一個犯罪嫌疑人一樣對待,主持人咄咄逼人,社科院的專家認為他只是曇花一現,還有一個紮著麻花辮的女觀眾說韓寒是「土雞」——理由是韓寒用聊天室聊天,而不是像她一樣用OICQ和ICQ。甚至,為了反襯韓寒的失敗,他身旁還坐了一個成功的垘本——考上北大的少女黃思路。
十四年後,我去參加央視一檔節目的錄製,內容是「非一般年輕人」的演講,其中大部分是九○後,○有科學家,有創業者。
演講者都朝氣蓬勃,而我很快就發現自己的位置非常尷尬,我和一群從三○後到八○後不等的老年人,坐在觀眾席中被架得很高的白凳子上,腳不著地,舉著一塊寫有自己出生年分的熒光板,帶著詭異的慈祥笑容聽這些年輕人的演講。
我們這群老年人,並不像當年「對話」節目中的專家一樣,是年輕人的評委,而是對年輕人喪心病狂的讚美者。
我們在每個演講之後發言,場景介於中學生演講比賽和「感動中國」頒獎典禮之間,每個人都生怕溢美之詞被他人搶去,因而抱著話筒無休止地進行排比句造句:「青春是一顆種子/一朵花/一棵樹/一根蠟燭……」最後聲嘶力竭地以諸如「青春無敵!做你自己!正能量!耶!」作為結束,非常地累。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某個應用軟件的CEO,九○後,非常瘦小,他抱著一個大狗熊玩偶上台,一上台就把狗熊扔到台上,說:「我覺得這個讓我抱熊的導演特別傻。」他的演講裡不無豪言壯語,例如「明年給員工派發一個億利潤」之類。而台下的大學生,則在每一次聽到「第一桶金賺了一百萬」「阿裡巴巴用千萬美金收購」這類句子時,羡慕地齊聲譁然。
他的演講,雖然充滿了明顯的誇大和對他人的不屑,可卻獲得了當天錄製最大的掌聲,以及最熱烈的溢美。
前輩們的興奮,在於終於找到了自己心目中典型的九○後,就像親眼看到外星人時,發現它就是自己想像中的銀色大頭娃娃。那個年輕的CEO符合社會對於九○後一切的想像:輕狂、自我、混不吝。
當節目播出時,他的視頻在社交網絡上風靡,配以標題諸如「九○後的話,惹怒了所有的互聯網大佬」「九○後的一番話,讓全世界都沉默了。」
當我看到播出的節目裡,所有被侮辱和輕視的中年人,都像受虐狂一樣大力地鼓掌,賣力的歡笑,我忽然想到十四年前參與韓寒節目錄製的中年人,當年臺上的那些中年專家還在麼?他們依然怒不可遏嗎?還是成了舉著寫有自己出生年份的老年人,一聽到「追逐夢想」「初生牛犢」幾個字,就在煽情的音樂中熱烈鼓掌呢?
風水輪流轉,中年人在話語權的爭奪中,成了弱勢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