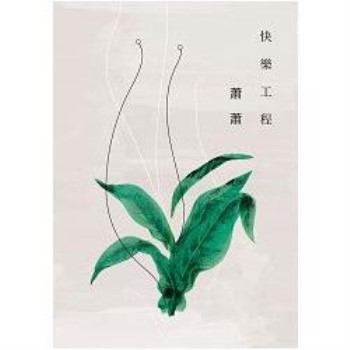斷章精彩,人生不留白
二○一一年的春天,我住在香港半山般咸道(Bonham Road)三十八號Y.W.C.A.,足足兩個月,這簡樸的旅舍屬於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乾淨、俐落,適合讀書人行旅時住個十天、八天。旅舍是香港大學替我租賃,當時我是港大駐校作家,主要的任務是四場講座,其餘的時間,我可以自由自在旅遊各地,觀察香港。
我的住居處是九樓狹長型的臨窗房,打開鎖匙房門,我擁有四個房間、四片門,在香港應該算是奢侈的吧!四間房,除了廚房之外,都有一面落地窗,隨時可以從窗玻璃看見外面形形色色、高高瘦瘦的大樓,遠觀還可以瞧見中環著名的光亮建築物,夜裡燈光轉換七彩。臥室裡一張雙人床,一條側身才可以走的通道就在床旁邊,通道另一邊就是落地窗,中間有一張小學生的書桌,我放上筆記型電腦之後,只能再放兩本書,有時累了,不打字,轉身就可以將腳擱在床鋪上,不理窗外高樓的光影,看看閒書。床鋪旁,一步遠就是衛浴間,這一步遠不是一個箭步那麼遠,但也不可小覷,剛好容下一座頂天立地的衣櫥。衛浴間五臟俱全︰一個浴缸、一個馬桶、一個洗臉臺、一個懸掛在牆壁上的置物架、一個「一個人可以轉身的地方」,晚間沐浴後,我喜歡關掉燈、拉開窗簾(這順序還不許弄錯),臨窗躺在浴缸裡,享受裸露自己、坦開心胸、人在半空中的那二十分鐘。
其實,我應該先介紹開門進來的客廳與廚房,一推開門是客廳,可以看見臨窗一張圓桌,桌面直徑不到一公尺,走一步路就可以在上面放置我買回來的蔬菜、水果、食物,真是體貼提重物的人,這是我吃飯或者看書的所在,圓桌旁就是一座小型電視機,電視機的後面、左面是兩堵厚實實的牆,後面的牆可以擋住外面的強光,有利於看電視,左面的牆上有門可以開、可以關,一開就是床鋪,算得真準,門板剛好不會擦到床沿。電視機對面當然是沙發,雙人座,香港的電視機和臺灣一個樣,喜歡和沙發相看兩不厭,都把對方當作敬亭山。緊挨著沙發,就是剛推開的門,門旁還是門,那是廚房的門,香港人應該都信仰「廚房容不下兩個女人」,至少這間廚房是依照這種信仰產生力量的,L型的石板面,剛剛好夠我燙蔬菜、下麵條、切水果,切好了,跨出廚房一步,直接送上餐桌。
我洗過手,坐近餐桌,直接把食物送上口。
剩下來的時間,臨窗,我可以優閒看路上行人匆匆。
這時我想起手中正在整理的文稿,關於西元一九三五年十月,卞之琳從自己創作的詩歌裡擷取四句,獨立成篇,命名為〈斷章〉的那首詩︰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余光中說這首詩的妙處不限於寫景與抒情,還是是一首耐人尋味的哲理妙品︰「原來世間的萬事萬物皆有關聯,真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你站在橋上看風景,另有一人卻在高處觀賞,連你也一起看了進去,成為風景的一部分,有如山水畫中的一個小人。同樣地,明月出現在你的窗口,你呢,卻出現在別人的夢中。你的窗口因為有月而美,別人的夢呢,因為你出現才有意義。」(余光中︰〈憑一張地圖〉,《詩與哲學》)
這時,我在九樓看陌生而璀璨的香港,會有誰在他的夢中念著我的璀璨或委頓呢?
余光中從這首詩看到世間萬事萬物皆有關聯,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在真實的世界裡,因為要為中學生說解這首詩,參考許多作品,閱讀過張曼儀編著的《卞之琳》(臺北:書林出版公司,一九九二),知道她還有一本《卞之琳著譯研究》(香港大學出版,一九八九),臺灣借不到,那麼輕易,我駐港大,圖書館一尋就有,後來還在餐會中跟她見了面,承她送我一本,這樣的因緣,在臺灣,想不到,到了香港,也未曾預料啊!
反觀卞之琳的一生,第一次從鄉下到上海,到商務印書館看書,買了冰心女士的《繁星》,從此開始對新詩產生興趣,誰又能料到呢?初次踏上北大,在往北京的火車上竟認識了清華的錢鍾書,那又是甚麼機緣?一九三一年初,卞之琳成為徐志摩「英詩」課程的學生,徐志摩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深深感染了他,並且將他推上了詩壇。徐志摩遭遇空難後,課堂的教授換成葉公超,葉公超又讓他沉醉於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去了。卞之琳的詩因而能出入於二十世紀三○年代「新月」與「現代」兩派之間,兼有二者之長,既能繼承古典詩傳統而不泥於古,又能借鑑西方現代詩潮而不歐化,卓然成家,直接影響四○年代九葉派詩人,也玉成了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漢園三詩人」的稱號。這些會是卞之琳生命中的必然嗎?這些必然來自於最初的一本《繁星》的偶然嗎?
卞之琳後來曾經寫過〈斷章中的斷章〉,更將這四行小詩「戲劇化」了,他這樣寫︰
淚乾了,心靜了。她已完完全全融入到「夜、光、橋」的畫面中,但她自己不曾知道。
輕輕睜開眼,她驚奇地發現不遠處一座樓房的一個陽臺上,有一張和自己同樣落寞的臉正朝向這邊。
他是在看風景,還是在看她?她不知道,也沒人知道。
……
其實,能在失意時遇到與自己冥冥中繫有一點靈犀的人,是一種最美好的慰藉,最純真的幸福。
我在高樓看風景,該怎麼想呢?關於斷章以及斷章接續成的人生。
太極圖的童心
觀察大自然時,有沒有覺得很好玩?有天就有地,有山就有水,有日就有月,呈現出對比性的存在。古代人造字,將這些具體可見的形象,從圖像轉換為線條的刻劃,這就是漢字獨有的「象形字」。
如果是抽象的意念,也常呈對比性的存在,如上與下、本與末,很早以前的「倉頡們」就以「指事字」呈現這種關係,譬如先畫一條長線代表主要的基礎物,在這條長線之上畫一橫或一豎,這就是最早的「上」;相對的,在長線之下畫一短短的線條,不論橫或直,不論簡單或多變化,那就代表「下」,這是古人的智慧。
本與末,一樣好玩,先畫一棵象形的「木」,在一豎的下方處畫一橫,那是象徵木的根本所在的「本」字;在一豎的上方處畫一長橫,那是樹梢所在的「末」字。學生曾問我:為什麼「本」字的那一橫那麼短,「末」字的那一橫卻拉得五倍長?我想,或許是因為樹根埋藏在地下,我們所能看見的極為有限,樹末的茂密葉子卻是目睹即是,一大片一大片可見的綠,蓋頂而下吧!所以漢朝的《說文解字》說:「木下曰本,木上曰末。」現代的《國語辭典》則有所延伸:本,根也,有最初的、根源、本源之意;末,頂梢也,有最後的、物體尾端、不重要、非根本的意思。捨本逐末,本末倒置,都是將本與末放在相對的位置來思考。「本」不會因為那一橫小於「末」而變得不重要,「末」也不會因為那一橫大於「本」而成為生命的根源。
每次我跟小朋友解釋「上下本末」這四個字的橫畫時,小朋友從來不會將它們當做單純的一筆短畫,總是七嘴八舌說:那是大地、那是椅子、那是蘋果,或者說:真的是樹根耶、真的是樹葉耶,他們會將這些線條自動還原為天地間的萬象,而且充滿興奮之情,孳乳,滋生,發展出更多的可能。
這種相對性的存在,除了大自然的天地山川之外,人體的結構,其實也完全符合這種柔和的對比,例如左眼、右眼,左耳、右耳,左手、右手,就是相對而又合作的關係,而且在偶數的器官中,其實又有奇數的器官作為相對性的存在,譬如兩眼之間就有一根鼻樑,兩頰之間會有一張嘴,而鼻樑裡躲藏著一組鼻孔,一張嘴其實是兩片唇的組合,兩片唇的軟會有兩排牙齒的硬相對,兩排牙齒的硬岩中間則是一頭靈活的舌。人體的這種相對性,比起大自然彷彿又多了一些變化與美感。
相對的美的存在,古代中國人所繪製的太極圖,簡易而快速地說明了這種宇宙間深奧的哲理:
陰極、陽極,是黑與白截然的對比,但在這對比中又呈現出陰極中有白點,白色的圖形裡有黑點,彷彿在說:凡事都有原則可以依循,但有原則必有例外。截然相對之時,卻未必要斷然立判。仔細看這太極圖,圖中沒有判然二分的直線,太極圖黑白二分處是柔美的曲線,黑白統合的外圍則是柔美的曲線所合成的圓。是圓,就會滾動。尤其是一頭大、一頭尖,有如蝌蚪、又像黑鯨魚與白海豚在嬉戲的兩隻動物。
有沒有發現,我說的是蝌蚪與鯨豚,我請來了極小的蝌蚪與極大的鯨豚,對比型的動物模特兒演出,仔細看右側的黑鯨魚吧(或者說是一尾黑色小蝌蚪)!是不是有一種向上騰躍的律動感?再看左側白海豚(或者說:難得一見的白蝌蚪喔),那種潛水的喜悅就從頭部的圓形造型顯露出來。如果純粹只以圖形看這太極圖,它只是陰陽相對、黑白相配的圖,如果以蝌蚪、鯨豚來想像,這圖形就讓人有嬉戲、歡悅的生之喜樂感。
聖修伯里在《小王子》裡說,他六歲時畫了一幅這樣的「第一號作品」:
然後問大人,有沒有被這幅畫嚇著了?
大人都說,誰會被一頂帽子嚇著呢?
其實這不是一頂帽子,六歲小孩畫的是大蟒蛇正在消化大象的圖畫,所以,他只好畫了「第二號作品」加以說明:
聖修伯里在《小王子》裡說,把「第一號作品」看作是帽子的人,我絕不和他談論大蟒蛇、原始森林或星星的事,我寧願把自己降到他的水準,跟他聊聊橋牌、高爾夫球、政治和領帶。
你是不是也看到太極圖裡的蝌蚪或鯨豚?如果你沒看到,下次我可能要談一點名牌、籃球、股票和錄影帶了。
坐在九樓臨窗的位置,我在想,如果有人按錯門鈴,一位陌生的香港人出現在門口,即使都用普通話吧!我們可以談些什麼?太極圖裡的陰陽、風水?恐怕也難以進入蝌蚪的腿、鯨豚的肺,難以進入我也陌生的六合彩明牌、香港人也生疏的輕裘緩帶。
那最初的天地太極,那最初的你我童心,都,去了哪裡?
二○一一年的春天,我住在香港半山般咸道(Bonham Road)三十八號Y.W.C.A.,足足兩個月,這簡樸的旅舍屬於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乾淨、俐落,適合讀書人行旅時住個十天、八天。旅舍是香港大學替我租賃,當時我是港大駐校作家,主要的任務是四場講座,其餘的時間,我可以自由自在旅遊各地,觀察香港。
我的住居處是九樓狹長型的臨窗房,打開鎖匙房門,我擁有四個房間、四片門,在香港應該算是奢侈的吧!四間房,除了廚房之外,都有一面落地窗,隨時可以從窗玻璃看見外面形形色色、高高瘦瘦的大樓,遠觀還可以瞧見中環著名的光亮建築物,夜裡燈光轉換七彩。臥室裡一張雙人床,一條側身才可以走的通道就在床旁邊,通道另一邊就是落地窗,中間有一張小學生的書桌,我放上筆記型電腦之後,只能再放兩本書,有時累了,不打字,轉身就可以將腳擱在床鋪上,不理窗外高樓的光影,看看閒書。床鋪旁,一步遠就是衛浴間,這一步遠不是一個箭步那麼遠,但也不可小覷,剛好容下一座頂天立地的衣櫥。衛浴間五臟俱全︰一個浴缸、一個馬桶、一個洗臉臺、一個懸掛在牆壁上的置物架、一個「一個人可以轉身的地方」,晚間沐浴後,我喜歡關掉燈、拉開窗簾(這順序還不許弄錯),臨窗躺在浴缸裡,享受裸露自己、坦開心胸、人在半空中的那二十分鐘。
其實,我應該先介紹開門進來的客廳與廚房,一推開門是客廳,可以看見臨窗一張圓桌,桌面直徑不到一公尺,走一步路就可以在上面放置我買回來的蔬菜、水果、食物,真是體貼提重物的人,這是我吃飯或者看書的所在,圓桌旁就是一座小型電視機,電視機的後面、左面是兩堵厚實實的牆,後面的牆可以擋住外面的強光,有利於看電視,左面的牆上有門可以開、可以關,一開就是床鋪,算得真準,門板剛好不會擦到床沿。電視機對面當然是沙發,雙人座,香港的電視機和臺灣一個樣,喜歡和沙發相看兩不厭,都把對方當作敬亭山。緊挨著沙發,就是剛推開的門,門旁還是門,那是廚房的門,香港人應該都信仰「廚房容不下兩個女人」,至少這間廚房是依照這種信仰產生力量的,L型的石板面,剛剛好夠我燙蔬菜、下麵條、切水果,切好了,跨出廚房一步,直接送上餐桌。
我洗過手,坐近餐桌,直接把食物送上口。
剩下來的時間,臨窗,我可以優閒看路上行人匆匆。
這時我想起手中正在整理的文稿,關於西元一九三五年十月,卞之琳從自己創作的詩歌裡擷取四句,獨立成篇,命名為〈斷章〉的那首詩︰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余光中說這首詩的妙處不限於寫景與抒情,還是是一首耐人尋味的哲理妙品︰「原來世間的萬事萬物皆有關聯,真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你站在橋上看風景,另有一人卻在高處觀賞,連你也一起看了進去,成為風景的一部分,有如山水畫中的一個小人。同樣地,明月出現在你的窗口,你呢,卻出現在別人的夢中。你的窗口因為有月而美,別人的夢呢,因為你出現才有意義。」(余光中︰〈憑一張地圖〉,《詩與哲學》)
這時,我在九樓看陌生而璀璨的香港,會有誰在他的夢中念著我的璀璨或委頓呢?
余光中從這首詩看到世間萬事萬物皆有關聯,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在真實的世界裡,因為要為中學生說解這首詩,參考許多作品,閱讀過張曼儀編著的《卞之琳》(臺北:書林出版公司,一九九二),知道她還有一本《卞之琳著譯研究》(香港大學出版,一九八九),臺灣借不到,那麼輕易,我駐港大,圖書館一尋就有,後來還在餐會中跟她見了面,承她送我一本,這樣的因緣,在臺灣,想不到,到了香港,也未曾預料啊!
反觀卞之琳的一生,第一次從鄉下到上海,到商務印書館看書,買了冰心女士的《繁星》,從此開始對新詩產生興趣,誰又能料到呢?初次踏上北大,在往北京的火車上竟認識了清華的錢鍾書,那又是甚麼機緣?一九三一年初,卞之琳成為徐志摩「英詩」課程的學生,徐志摩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深深感染了他,並且將他推上了詩壇。徐志摩遭遇空難後,課堂的教授換成葉公超,葉公超又讓他沉醉於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去了。卞之琳的詩因而能出入於二十世紀三○年代「新月」與「現代」兩派之間,兼有二者之長,既能繼承古典詩傳統而不泥於古,又能借鑑西方現代詩潮而不歐化,卓然成家,直接影響四○年代九葉派詩人,也玉成了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漢園三詩人」的稱號。這些會是卞之琳生命中的必然嗎?這些必然來自於最初的一本《繁星》的偶然嗎?
卞之琳後來曾經寫過〈斷章中的斷章〉,更將這四行小詩「戲劇化」了,他這樣寫︰
淚乾了,心靜了。她已完完全全融入到「夜、光、橋」的畫面中,但她自己不曾知道。
輕輕睜開眼,她驚奇地發現不遠處一座樓房的一個陽臺上,有一張和自己同樣落寞的臉正朝向這邊。
他是在看風景,還是在看她?她不知道,也沒人知道。
……
其實,能在失意時遇到與自己冥冥中繫有一點靈犀的人,是一種最美好的慰藉,最純真的幸福。
我在高樓看風景,該怎麼想呢?關於斷章以及斷章接續成的人生。
太極圖的童心
觀察大自然時,有沒有覺得很好玩?有天就有地,有山就有水,有日就有月,呈現出對比性的存在。古代人造字,將這些具體可見的形象,從圖像轉換為線條的刻劃,這就是漢字獨有的「象形字」。
如果是抽象的意念,也常呈對比性的存在,如上與下、本與末,很早以前的「倉頡們」就以「指事字」呈現這種關係,譬如先畫一條長線代表主要的基礎物,在這條長線之上畫一橫或一豎,這就是最早的「上」;相對的,在長線之下畫一短短的線條,不論橫或直,不論簡單或多變化,那就代表「下」,這是古人的智慧。
本與末,一樣好玩,先畫一棵象形的「木」,在一豎的下方處畫一橫,那是象徵木的根本所在的「本」字;在一豎的上方處畫一長橫,那是樹梢所在的「末」字。學生曾問我:為什麼「本」字的那一橫那麼短,「末」字的那一橫卻拉得五倍長?我想,或許是因為樹根埋藏在地下,我們所能看見的極為有限,樹末的茂密葉子卻是目睹即是,一大片一大片可見的綠,蓋頂而下吧!所以漢朝的《說文解字》說:「木下曰本,木上曰末。」現代的《國語辭典》則有所延伸:本,根也,有最初的、根源、本源之意;末,頂梢也,有最後的、物體尾端、不重要、非根本的意思。捨本逐末,本末倒置,都是將本與末放在相對的位置來思考。「本」不會因為那一橫小於「末」而變得不重要,「末」也不會因為那一橫大於「本」而成為生命的根源。
每次我跟小朋友解釋「上下本末」這四個字的橫畫時,小朋友從來不會將它們當做單純的一筆短畫,總是七嘴八舌說:那是大地、那是椅子、那是蘋果,或者說:真的是樹根耶、真的是樹葉耶,他們會將這些線條自動還原為天地間的萬象,而且充滿興奮之情,孳乳,滋生,發展出更多的可能。
這種相對性的存在,除了大自然的天地山川之外,人體的結構,其實也完全符合這種柔和的對比,例如左眼、右眼,左耳、右耳,左手、右手,就是相對而又合作的關係,而且在偶數的器官中,其實又有奇數的器官作為相對性的存在,譬如兩眼之間就有一根鼻樑,兩頰之間會有一張嘴,而鼻樑裡躲藏著一組鼻孔,一張嘴其實是兩片唇的組合,兩片唇的軟會有兩排牙齒的硬相對,兩排牙齒的硬岩中間則是一頭靈活的舌。人體的這種相對性,比起大自然彷彿又多了一些變化與美感。
相對的美的存在,古代中國人所繪製的太極圖,簡易而快速地說明了這種宇宙間深奧的哲理:
陰極、陽極,是黑與白截然的對比,但在這對比中又呈現出陰極中有白點,白色的圖形裡有黑點,彷彿在說:凡事都有原則可以依循,但有原則必有例外。截然相對之時,卻未必要斷然立判。仔細看這太極圖,圖中沒有判然二分的直線,太極圖黑白二分處是柔美的曲線,黑白統合的外圍則是柔美的曲線所合成的圓。是圓,就會滾動。尤其是一頭大、一頭尖,有如蝌蚪、又像黑鯨魚與白海豚在嬉戲的兩隻動物。
有沒有發現,我說的是蝌蚪與鯨豚,我請來了極小的蝌蚪與極大的鯨豚,對比型的動物模特兒演出,仔細看右側的黑鯨魚吧(或者說是一尾黑色小蝌蚪)!是不是有一種向上騰躍的律動感?再看左側白海豚(或者說:難得一見的白蝌蚪喔),那種潛水的喜悅就從頭部的圓形造型顯露出來。如果純粹只以圖形看這太極圖,它只是陰陽相對、黑白相配的圖,如果以蝌蚪、鯨豚來想像,這圖形就讓人有嬉戲、歡悅的生之喜樂感。
聖修伯里在《小王子》裡說,他六歲時畫了一幅這樣的「第一號作品」:
然後問大人,有沒有被這幅畫嚇著了?
大人都說,誰會被一頂帽子嚇著呢?
其實這不是一頂帽子,六歲小孩畫的是大蟒蛇正在消化大象的圖畫,所以,他只好畫了「第二號作品」加以說明:
聖修伯里在《小王子》裡說,把「第一號作品」看作是帽子的人,我絕不和他談論大蟒蛇、原始森林或星星的事,我寧願把自己降到他的水準,跟他聊聊橋牌、高爾夫球、政治和領帶。
你是不是也看到太極圖裡的蝌蚪或鯨豚?如果你沒看到,下次我可能要談一點名牌、籃球、股票和錄影帶了。
坐在九樓臨窗的位置,我在想,如果有人按錯門鈴,一位陌生的香港人出現在門口,即使都用普通話吧!我們可以談些什麼?太極圖裡的陰陽、風水?恐怕也難以進入蝌蚪的腿、鯨豚的肺,難以進入我也陌生的六合彩明牌、香港人也生疏的輕裘緩帶。
那最初的天地太極,那最初的你我童心,都,去了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