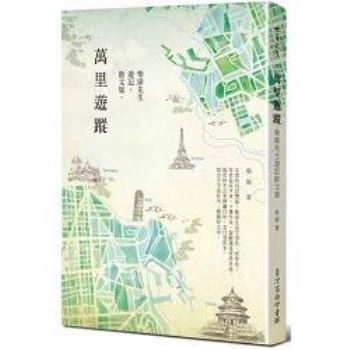重遊黃鶴樓
凡是去過武漢旅遊的人,想必去過黃鶴樓,黃鶴樓是古蹟、是名勝,更是個富於文學氣氛和神話傳說的地方。
黃鶴樓以風景優美與崔顥題詩而聞名,而崔顥更以名樓的屢建而名傳後代。且看他的題詩吧。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到底昔人誰乘黃鶴去?黃鶴樓因何而得名?有下列幾種傳說:
一、《南齊書‧州郡志下》載:「山人子安乘黃鶴過此,故名。」子安何姓,並未明書。因古代傳說中有仙人名王子喬,乘黃鶴仙去,子安遂被逕稱姓王。鄭樵《通志》首稱王子安,明清方志均循其說。
二、宋《太平寰宇記‧江南西道‧鄂州》載:「昔費文褘(筆者按:褘字左從衣,其餘同)登仙,每乘黃鶴於此樓憩駕,故名。」
三、唐代宗永泰元年(七六五)閻伯理作《黃鶴樓記》首段謂:「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筆者按:禕字左從示,其餘同)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這篇文字,現在以隸書雕刻,展貼在新建之黃鶴樓三樓大廳上,供遊客們參閱。據說為大陸所見最早寫樓記之篇章,筆者曾當場拍照,以存其真。
四、傳說有辛氏者,在原黃鵠山上賣酒,一道士常來飲之,辛氏不收酒資。道士走時,以橘皮在壁上畫一黃鶴,曰:「酒客至拍手,鶴即下壁飛舞。」辛氏遂生意興隆,因此致富。越十年,道士來,取笛鳴奏,黃鶴下壁,道士跨鶴直飛雲天,辛氏建此樓以為紀念。此道士為誰?傳說是三國時好道成仙的費禕,又說是八仙中之呂洞賓,難以查考證實。
因此,到底誰乘黃鶴而去,說來都是神話。所以崔顥的題詩中,首句即謂「昔人已乘黃鶴去」,一語概括。
再說,費禕如何成仙?《神仙傳》、《述異志》筆者一時難以找到書查考,總之都是傳說。倒是查《三國志‧蜀書‧費禕傳》謂:費禕,三國時蜀漢江夏鄳(音蒙)人,字文偉,與董允齊名。後主時為黃門侍郎,代蔣琬為尚書令,復領益州刺史,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諸葛亮〈前出師表〉謂:「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文中對費禕極為推重。〈費禕傳〉後段復謂:後主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漢壽。十六年歲首大會,因歡飲沉醉,被魏降人郭循手刃所害,諡曰敬侯,未說其有修道成仙之事。而後世在武昌還附會出若干費禕洞,說是他修鍊升仙之所,頗為荒誕離奇。
又費文褘與費禕的名字,兩者究竟誰是從示之「禕」,誰是從衣之「褘」,或兩人用字皆同,古今來混淆不清。往往一篇文章內,同一人前作禕(從示),後又作褘(從衣),各字辭典用字亦各有不同,使人莫衷一是。考其原因:或出諸手民誤植,或係抄寫錯誤,或係混淆互用,或係造字先後。因《說文》只有從衣之褘,無從示之禕,禕是後出字(從示)前人已經混用,後代的字辭典或書文,當然跟著分辨不清,即或較具權威性辭典亦復如是。
筆者經輾轉查考各種字辭典,從示之禕與從衣之褘均讀「依」,也均做「美好」解;但褘又讀揮,另有解釋。費文褘之名,如作「文采華美」解釋,禕、褘均可通用;唯人名必須統一。姓費的多出神仙,辭典有費禕、費長房,但查不出費文褘,不知費氏宗譜上能否找到?然一般書籍上,大都從衣作費文褘,茲從眾說。
至費禕之「禕」,經查《三國志‧蜀書‧費禕傳》,其正文共二十七處,注解共十三處,均係從示之禕,無從衣者。可見費禕之名當作「禕」(從示),各大字辭典應該循此統一更正為是。
現在新建之黃鶴樓公園,有「崔顥題詩圖」一景,草書浮雕,頗富文學氣息。相傳李白來此,見崔詩而擱筆,歎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而在「崔詩圖」附近,另有李白「擱筆亭」,供遊人觀賞玩味。
不過園內尚有古碑廊、詩碑廊等景觀,李白之名作,如〈送孟浩然之廣陵〉及〈題北榭碑〉均為後人所傳誦吟詠。而後者之「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常為遊客作為黃鶴樓聯語之引用。筆者最欣賞之一聯云:
「何時黃鶴歸來,且共飲金樽,繞洲渚千年芳草;
但見白雲飛去,更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黃鶴樓始建於三國孫吳黃武二年(二二三),迄今已有一千七百餘年的歷史。地址在原湖北省武昌縣西南黃鵠磯上,瀕臨長江。當年孫吳建築時,原為軍事瞭望之用,至唐代宗年間,因鄂州刺州祖庸及都團練使穆寧等治鄂時,「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宴必於是。……」(見唐閻伯理《黃鶴樓記》)漸演變為觀賞之樓,居江南三大名樓之首,素有「天下絕景」和「天下江山第一樓」之美譽。歷代文人騷客登樓吟詩作賦,謳歌黃鶴樓的壯麗景觀,留傳至今的詩詞逾千首,文賦過百篇,新舊楹聯一千四百多幅,並有多於珠璣的神話傳說,成為中華民族文學寶庫中的一顆明珠。
當時崔顥在此題詩,雖不見神話中之仙鶴,尚有黃鶴樓可以空餘。據說宋、元兩代,古黃鶴樓已不存,築在黃鵠山者乃是南樓,現在黃鶴樓公園內,仍保存有仿造的南樓一景。到了明朝,曾四次修建,兩次葺理,原樓前毀於嘉慶年間,重建後,又被張獻忠所毀。清代屢建屢毀,同治年間,重復舊觀,樓高十八丈,甚為壯麗。至清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又毀於一場大火之中;自此,黃鶴樓名存實亡,將近百年。此最後一次之大火,原樓全被焚燬,僅剩下寶銅頂一座,現存放在新建之黃鶴樓後面,列為一景,旁有碑文說明。
清光緒年間,張之洞治鄂時,在原址建了大樓一座,飛簷畫棟,高達三層,名為奧略樓。民國時雖就原址重建一西式磚樓,那都不能算是黃鶴樓的重建,一般遊客都把奧略樓,當做黃鶴樓的化身。
筆者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在武昌遊歷該樓時,那時所謂的黃鶴樓,僅存原址,仍在武昌城西臨江的黃鵠磯上。恐怕當時的黃鵠磯,因歷經江面南移,早已縮近蛇山。當時蛇山此一地帶,稱為首義公園。我們仍然把「奧略樓」當做黃鶴樓來參仰。因時逢戰亂,遊子情懷,觀賞不甚深刻;然「奧略樓」三字及「大漢陳友諒之墓」墓碑文字,仍然記憶深刻。黃鶴既被仙人騎走了,已杳不可復;然遊客及地方人士仍盼望黃鶴歸來,見於詩詞聯句中不少。中共於一九五五年興建長江大橋時,已將原黃鵠磯夷平,很多古蹟亦隨之冺滅無存。後應大眾要求,開始重建黃鶴樓。此一新樓,乃以清代圖樣為藍本,而又有所創建,樓高五層(五十一‧四公尺),黃瓦紅柱,層層飛簷,雄偉壯麗。樓頂層四面檐角,分別鑲嵌了四塊黑底餾金匾額;西為「黃鶴樓」,東為「楚天極目」,南為「南雄高拱」,北為「北斗平臨」,正是登樓攬勝所見之景象的藝術概括。
一樓正廳有「白雲黃鶴圖」,定點供遊客拍照留念。兩旁大柱上,書有原黃鵠磯上名聯:
「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恨;大江東去,波濤洗淨古今愁。」
各樓大廳正面,均鑲嵌有以黃鶴樓的神話傳說、歷史故事和楚天風光的大幅壁畫。而在層層的紅柱上,則是古今文人墨客所撰寫有關黃鶴樓的詩詞歌賦、楹聯書法,甚富文學與藝術氣氛,而又兼旅遊與觀賞之勝。當時曾抄下五樓大廳上之聯語為:
「一樓萃三楚精神,雲鶴俱空橫笛在:二水匯百川支派,古今無盡大江流。」
五樓大廳西面聯語為:
「對江樓閣參天立;全楚山河縮地來。」
除樓內有「白雲黃鶴圖」和「木刻黃鶴」外,樓外景點中,復有大幅展掛之紅花崗岩「歸鶴」浮雕,象徵群鶴飛舞,共赴歸巢圖樣;各旅遊圖說,也多以歸鶴棲息為封面;而新建之大樓前,更有兩隻「銅雕黃鶴」,棲息在龜背之上,象徵「黃鶴歸來」,也祝福遊客們像龜鶴之長壽。而在落成開放之日,民間遊藝及慶賀隊伍,從圖片中顯示,自對岸之長江大橋起,一直迤邐延伸至黃鶴樓園內,可謂盛況空前。
黃鶴既去,白雲悠悠,為了不使白雲空自飄浮,公園籌畫者,在蛇山山脊上,構建有一座白雲閣,與黃鶴樓前後輝映,高超矗立,遠望儼似一座鎮山法物。登樓四望,楚天極目,大江東去,浪下三吳,心胸為之廣闊。惟去國多年的遊子,仰視上空,眼見「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緬懷當年倚門倚閭之慈母,思子情懷,不勝傷感。「晴川歷歷漢陽樹」;再看對江的情景,以當時詩人敏慧的眼光,站在黃鶴樓上;如果在晴朗天氣,江水清明,映照著漢陽的樹木,漢水悠悠南下,長江滾滾東流,清濁分明,多麼富有詩意。就因為崔顥這句名詩,後人在龜山下面禹功磯上,建有一座晴川閣;雖然幾經興廢,現又在原址上重建。如乘船沿江上下,晴川閣的風貌,清晰可見。其風景之優美,早有「三楚勝景」的盛名;而旁邊更有一座矗立的「晴川飯店」,已成為武漢三座高大建築物之一,成為漢陽的標幟,與黃鶴樓、龜山電視塔,互相媲美。
「芳草萋萋鸚鵡洲」:鸚鵡洲在何處?一般唐詩注解有謂在今湖北省漢陽縣西南長江中;有謂在湖北省武昌縣西南大江中。經查考:古時的鸚鵡洲靠近武昌江邊,因東漢末年文士禰(姓氏讀為迷)衡在此作〈鸚鵡賦〉而得名。據《湖北通志》及《輿地記勝》等書記載:州的南端在鲇魚口,北端在黃鵠磯前。在唐、宋時期,鸚鵡洲繁華熱鬧,盛極一時,和黃鶴樓一樣是文人墨客必遊之地。該洲據說長約五華里,寬約四百公尺。後來由於長江河勢改變,江心主流由漢陽岸邊,偏向武昌岸邊,鸚鵡洲被江水沖刷,日漸縮小;到了明代末期,洲面竟被江水沖沒。後來又逐漸淤積出水,與漢陽城南陸地相連,漢陽此一地段,至今仍保留有「鸚鵡洲」之名。到了清康熙末、雍正初年,鸚鵡洲又漸沒江下,現在已無蹤跡可尋了。
崔顥,唐汴洲人,曾中過進士,少年為詩,意多浮艷,晚年忽變常體,風骨凜然。此詩純以意運,不事雕琢,流利自然,成為千古絕唱。
因為文學是苦悶的,詩人是寂莫的,由於眼前好景,而引發思鄉的情懷,對著江上的煙波,不免勾起淡淡的鄉愁。
筆者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初次遊黃鶴樓時,正值少壯之年,雖然男兒志在四方;但初次離鄉,對著浩渺蒼茫的長江,也不免有煙波江上的離愁。來臺後,離鄉四十四年,此次返鄉探親,曾兩度登臨該地,感觸自是不同。由於筆拙才窮,也難免有「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歎。中共於長江大橋完成後,據說在南岸引橋下,尚存有刻著「黃鶴樓故址」的石碑。奧略樓當然不見,許多古蹟除極少數搬離外,其餘均已泯滅。例如:湧月臺、禹碑亭、黃克強銅像、抱膝亭,及蛇山上之泡冰堂,均已不見。岳飛亭已遷至新建公園內蛇山上蛇尾部分,另立有岳飛銅像,成為公園內最後二景。聖象寶塔,俗稱白塔(武漢人稱為孔明燈)現已移至西大門牌坊前,進門後,一見就是。
我曾在入夜時分,遊覽長江大橋南岸引橋,尋覓陳友諒墓碑,果然仍在西岸下找到。雖在黑夜暗地,仍然可用鎂光燈拍照,洗出「大漢陳友諒之墓」清晰照片。前面的黃克強銅像,只剩下荒禿的墩基,因正前方是電影院,據說已被其後代移置在漢陽龜山下了。
新建的黃鶴樓公園,於西元一九八五年六月十日落成開放,占地十六‧六萬平方公尺。已從原址黃鵠磯向蛇山後移約一公里多,正建在蛇山蛇頸部分,而原黃鵠磯已被夷平成為長江大橋南岸之引橋,鸚鵡洲已沒入江中。因此,此三處古蹟,希望注解唐詩的學者及各大辭典的編者,在將來修訂時除敘明其古代史實及位置外,須再補述其變遷經過,重新予以定位,再不能以數十年前的老注解來搪塞了。
現在黃鶴樓公園,包括整個蛇山地區及兩旁山麓(蛇山,古稱黃鵠山或黃鶴山),共分三十五個景點。在歷代修建時,景點均有增添或減少,現在不足部分,據說有的將隨後補充。由西大門購票進入,即從引橋下直上,進門首見「白塔」,後為「三楚一樓」牌坊,經南軒、北軒、南亭、北亭,觀賞「黃鶴歸來」銅雕後,便直登黃鶴樓;再向蛇山後走,經「寶銅頂」、百松園,至白雲閣小憩;再經梅園、過石牌坊,經岳飛亭,而謁岳飛銅像,一路尋幽探勝,足可怡情悅性,令人流連忘返。
返時可從白雲閣南下,欣賞園內南區景觀文物,較具文學與藝術部分,環境亦較幽靜。最好從南大門購票進入,首見有「黃鶴樓公園」匾額,入內先在鵝池憩息,只見池水清悠,柳絲垂掛,迴廊曲折,荷葉田田,無論從圖片或實地觀賞,都可以引人入勝。再去瀏覽詩碑廊、古碑廊、鵝碑亭等處,讀讀古人詩句,觀賞前人書法,可滌濾塵俗,沾染文學氣氛。再上去參觀古蹟「南樓」、文苑、擱筆亭,而「崔顥題詩圖」與歸鶴浮雕。在觀賞紫竹苑與跨鶴亭後,再登臨黃鶴樓,復瀏覽蛇山前後各景點。北麓仍有可供遊憩之地,遊客在此可盤桓終日,而遊興仍濃。歸去後,美景仍留腦際,還想再度登臨。
凡是去過武漢旅遊的人,想必去過黃鶴樓,黃鶴樓是古蹟、是名勝,更是個富於文學氣氛和神話傳說的地方。
黃鶴樓以風景優美與崔顥題詩而聞名,而崔顥更以名樓的屢建而名傳後代。且看他的題詩吧。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到底昔人誰乘黃鶴去?黃鶴樓因何而得名?有下列幾種傳說:
一、《南齊書‧州郡志下》載:「山人子安乘黃鶴過此,故名。」子安何姓,並未明書。因古代傳說中有仙人名王子喬,乘黃鶴仙去,子安遂被逕稱姓王。鄭樵《通志》首稱王子安,明清方志均循其說。
二、宋《太平寰宇記‧江南西道‧鄂州》載:「昔費文褘(筆者按:褘字左從衣,其餘同)登仙,每乘黃鶴於此樓憩駕,故名。」
三、唐代宗永泰元年(七六五)閻伯理作《黃鶴樓記》首段謂:「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筆者按:禕字左從示,其餘同)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這篇文字,現在以隸書雕刻,展貼在新建之黃鶴樓三樓大廳上,供遊客們參閱。據說為大陸所見最早寫樓記之篇章,筆者曾當場拍照,以存其真。
四、傳說有辛氏者,在原黃鵠山上賣酒,一道士常來飲之,辛氏不收酒資。道士走時,以橘皮在壁上畫一黃鶴,曰:「酒客至拍手,鶴即下壁飛舞。」辛氏遂生意興隆,因此致富。越十年,道士來,取笛鳴奏,黃鶴下壁,道士跨鶴直飛雲天,辛氏建此樓以為紀念。此道士為誰?傳說是三國時好道成仙的費禕,又說是八仙中之呂洞賓,難以查考證實。
因此,到底誰乘黃鶴而去,說來都是神話。所以崔顥的題詩中,首句即謂「昔人已乘黃鶴去」,一語概括。
再說,費禕如何成仙?《神仙傳》、《述異志》筆者一時難以找到書查考,總之都是傳說。倒是查《三國志‧蜀書‧費禕傳》謂:費禕,三國時蜀漢江夏鄳(音蒙)人,字文偉,與董允齊名。後主時為黃門侍郎,代蔣琬為尚書令,復領益州刺史,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諸葛亮〈前出師表〉謂:「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文中對費禕極為推重。〈費禕傳〉後段復謂:後主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漢壽。十六年歲首大會,因歡飲沉醉,被魏降人郭循手刃所害,諡曰敬侯,未說其有修道成仙之事。而後世在武昌還附會出若干費禕洞,說是他修鍊升仙之所,頗為荒誕離奇。
又費文褘與費禕的名字,兩者究竟誰是從示之「禕」,誰是從衣之「褘」,或兩人用字皆同,古今來混淆不清。往往一篇文章內,同一人前作禕(從示),後又作褘(從衣),各字辭典用字亦各有不同,使人莫衷一是。考其原因:或出諸手民誤植,或係抄寫錯誤,或係混淆互用,或係造字先後。因《說文》只有從衣之褘,無從示之禕,禕是後出字(從示)前人已經混用,後代的字辭典或書文,當然跟著分辨不清,即或較具權威性辭典亦復如是。
筆者經輾轉查考各種字辭典,從示之禕與從衣之褘均讀「依」,也均做「美好」解;但褘又讀揮,另有解釋。費文褘之名,如作「文采華美」解釋,禕、褘均可通用;唯人名必須統一。姓費的多出神仙,辭典有費禕、費長房,但查不出費文褘,不知費氏宗譜上能否找到?然一般書籍上,大都從衣作費文褘,茲從眾說。
至費禕之「禕」,經查《三國志‧蜀書‧費禕傳》,其正文共二十七處,注解共十三處,均係從示之禕,無從衣者。可見費禕之名當作「禕」(從示),各大字辭典應該循此統一更正為是。
現在新建之黃鶴樓公園,有「崔顥題詩圖」一景,草書浮雕,頗富文學氣息。相傳李白來此,見崔詩而擱筆,歎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而在「崔詩圖」附近,另有李白「擱筆亭」,供遊人觀賞玩味。
不過園內尚有古碑廊、詩碑廊等景觀,李白之名作,如〈送孟浩然之廣陵〉及〈題北榭碑〉均為後人所傳誦吟詠。而後者之「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常為遊客作為黃鶴樓聯語之引用。筆者最欣賞之一聯云:
「何時黃鶴歸來,且共飲金樽,繞洲渚千年芳草;
但見白雲飛去,更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黃鶴樓始建於三國孫吳黃武二年(二二三),迄今已有一千七百餘年的歷史。地址在原湖北省武昌縣西南黃鵠磯上,瀕臨長江。當年孫吳建築時,原為軍事瞭望之用,至唐代宗年間,因鄂州刺州祖庸及都團練使穆寧等治鄂時,「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宴必於是。……」(見唐閻伯理《黃鶴樓記》)漸演變為觀賞之樓,居江南三大名樓之首,素有「天下絕景」和「天下江山第一樓」之美譽。歷代文人騷客登樓吟詩作賦,謳歌黃鶴樓的壯麗景觀,留傳至今的詩詞逾千首,文賦過百篇,新舊楹聯一千四百多幅,並有多於珠璣的神話傳說,成為中華民族文學寶庫中的一顆明珠。
當時崔顥在此題詩,雖不見神話中之仙鶴,尚有黃鶴樓可以空餘。據說宋、元兩代,古黃鶴樓已不存,築在黃鵠山者乃是南樓,現在黃鶴樓公園內,仍保存有仿造的南樓一景。到了明朝,曾四次修建,兩次葺理,原樓前毀於嘉慶年間,重建後,又被張獻忠所毀。清代屢建屢毀,同治年間,重復舊觀,樓高十八丈,甚為壯麗。至清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又毀於一場大火之中;自此,黃鶴樓名存實亡,將近百年。此最後一次之大火,原樓全被焚燬,僅剩下寶銅頂一座,現存放在新建之黃鶴樓後面,列為一景,旁有碑文說明。
清光緒年間,張之洞治鄂時,在原址建了大樓一座,飛簷畫棟,高達三層,名為奧略樓。民國時雖就原址重建一西式磚樓,那都不能算是黃鶴樓的重建,一般遊客都把奧略樓,當做黃鶴樓的化身。
筆者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在武昌遊歷該樓時,那時所謂的黃鶴樓,僅存原址,仍在武昌城西臨江的黃鵠磯上。恐怕當時的黃鵠磯,因歷經江面南移,早已縮近蛇山。當時蛇山此一地帶,稱為首義公園。我們仍然把「奧略樓」當做黃鶴樓來參仰。因時逢戰亂,遊子情懷,觀賞不甚深刻;然「奧略樓」三字及「大漢陳友諒之墓」墓碑文字,仍然記憶深刻。黃鶴既被仙人騎走了,已杳不可復;然遊客及地方人士仍盼望黃鶴歸來,見於詩詞聯句中不少。中共於一九五五年興建長江大橋時,已將原黃鵠磯夷平,很多古蹟亦隨之冺滅無存。後應大眾要求,開始重建黃鶴樓。此一新樓,乃以清代圖樣為藍本,而又有所創建,樓高五層(五十一‧四公尺),黃瓦紅柱,層層飛簷,雄偉壯麗。樓頂層四面檐角,分別鑲嵌了四塊黑底餾金匾額;西為「黃鶴樓」,東為「楚天極目」,南為「南雄高拱」,北為「北斗平臨」,正是登樓攬勝所見之景象的藝術概括。
一樓正廳有「白雲黃鶴圖」,定點供遊客拍照留念。兩旁大柱上,書有原黃鵠磯上名聯:
「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恨;大江東去,波濤洗淨古今愁。」
各樓大廳正面,均鑲嵌有以黃鶴樓的神話傳說、歷史故事和楚天風光的大幅壁畫。而在層層的紅柱上,則是古今文人墨客所撰寫有關黃鶴樓的詩詞歌賦、楹聯書法,甚富文學與藝術氣氛,而又兼旅遊與觀賞之勝。當時曾抄下五樓大廳上之聯語為:
「一樓萃三楚精神,雲鶴俱空橫笛在:二水匯百川支派,古今無盡大江流。」
五樓大廳西面聯語為:
「對江樓閣參天立;全楚山河縮地來。」
除樓內有「白雲黃鶴圖」和「木刻黃鶴」外,樓外景點中,復有大幅展掛之紅花崗岩「歸鶴」浮雕,象徵群鶴飛舞,共赴歸巢圖樣;各旅遊圖說,也多以歸鶴棲息為封面;而新建之大樓前,更有兩隻「銅雕黃鶴」,棲息在龜背之上,象徵「黃鶴歸來」,也祝福遊客們像龜鶴之長壽。而在落成開放之日,民間遊藝及慶賀隊伍,從圖片中顯示,自對岸之長江大橋起,一直迤邐延伸至黃鶴樓園內,可謂盛況空前。
黃鶴既去,白雲悠悠,為了不使白雲空自飄浮,公園籌畫者,在蛇山山脊上,構建有一座白雲閣,與黃鶴樓前後輝映,高超矗立,遠望儼似一座鎮山法物。登樓四望,楚天極目,大江東去,浪下三吳,心胸為之廣闊。惟去國多年的遊子,仰視上空,眼見「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緬懷當年倚門倚閭之慈母,思子情懷,不勝傷感。「晴川歷歷漢陽樹」;再看對江的情景,以當時詩人敏慧的眼光,站在黃鶴樓上;如果在晴朗天氣,江水清明,映照著漢陽的樹木,漢水悠悠南下,長江滾滾東流,清濁分明,多麼富有詩意。就因為崔顥這句名詩,後人在龜山下面禹功磯上,建有一座晴川閣;雖然幾經興廢,現又在原址上重建。如乘船沿江上下,晴川閣的風貌,清晰可見。其風景之優美,早有「三楚勝景」的盛名;而旁邊更有一座矗立的「晴川飯店」,已成為武漢三座高大建築物之一,成為漢陽的標幟,與黃鶴樓、龜山電視塔,互相媲美。
「芳草萋萋鸚鵡洲」:鸚鵡洲在何處?一般唐詩注解有謂在今湖北省漢陽縣西南長江中;有謂在湖北省武昌縣西南大江中。經查考:古時的鸚鵡洲靠近武昌江邊,因東漢末年文士禰(姓氏讀為迷)衡在此作〈鸚鵡賦〉而得名。據《湖北通志》及《輿地記勝》等書記載:州的南端在鲇魚口,北端在黃鵠磯前。在唐、宋時期,鸚鵡洲繁華熱鬧,盛極一時,和黃鶴樓一樣是文人墨客必遊之地。該洲據說長約五華里,寬約四百公尺。後來由於長江河勢改變,江心主流由漢陽岸邊,偏向武昌岸邊,鸚鵡洲被江水沖刷,日漸縮小;到了明代末期,洲面竟被江水沖沒。後來又逐漸淤積出水,與漢陽城南陸地相連,漢陽此一地段,至今仍保留有「鸚鵡洲」之名。到了清康熙末、雍正初年,鸚鵡洲又漸沒江下,現在已無蹤跡可尋了。
崔顥,唐汴洲人,曾中過進士,少年為詩,意多浮艷,晚年忽變常體,風骨凜然。此詩純以意運,不事雕琢,流利自然,成為千古絕唱。
因為文學是苦悶的,詩人是寂莫的,由於眼前好景,而引發思鄉的情懷,對著江上的煙波,不免勾起淡淡的鄉愁。
筆者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初次遊黃鶴樓時,正值少壯之年,雖然男兒志在四方;但初次離鄉,對著浩渺蒼茫的長江,也不免有煙波江上的離愁。來臺後,離鄉四十四年,此次返鄉探親,曾兩度登臨該地,感觸自是不同。由於筆拙才窮,也難免有「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歎。中共於長江大橋完成後,據說在南岸引橋下,尚存有刻著「黃鶴樓故址」的石碑。奧略樓當然不見,許多古蹟除極少數搬離外,其餘均已泯滅。例如:湧月臺、禹碑亭、黃克強銅像、抱膝亭,及蛇山上之泡冰堂,均已不見。岳飛亭已遷至新建公園內蛇山上蛇尾部分,另立有岳飛銅像,成為公園內最後二景。聖象寶塔,俗稱白塔(武漢人稱為孔明燈)現已移至西大門牌坊前,進門後,一見就是。
我曾在入夜時分,遊覽長江大橋南岸引橋,尋覓陳友諒墓碑,果然仍在西岸下找到。雖在黑夜暗地,仍然可用鎂光燈拍照,洗出「大漢陳友諒之墓」清晰照片。前面的黃克強銅像,只剩下荒禿的墩基,因正前方是電影院,據說已被其後代移置在漢陽龜山下了。
新建的黃鶴樓公園,於西元一九八五年六月十日落成開放,占地十六‧六萬平方公尺。已從原址黃鵠磯向蛇山後移約一公里多,正建在蛇山蛇頸部分,而原黃鵠磯已被夷平成為長江大橋南岸之引橋,鸚鵡洲已沒入江中。因此,此三處古蹟,希望注解唐詩的學者及各大辭典的編者,在將來修訂時除敘明其古代史實及位置外,須再補述其變遷經過,重新予以定位,再不能以數十年前的老注解來搪塞了。
現在黃鶴樓公園,包括整個蛇山地區及兩旁山麓(蛇山,古稱黃鵠山或黃鶴山),共分三十五個景點。在歷代修建時,景點均有增添或減少,現在不足部分,據說有的將隨後補充。由西大門購票進入,即從引橋下直上,進門首見「白塔」,後為「三楚一樓」牌坊,經南軒、北軒、南亭、北亭,觀賞「黃鶴歸來」銅雕後,便直登黃鶴樓;再向蛇山後走,經「寶銅頂」、百松園,至白雲閣小憩;再經梅園、過石牌坊,經岳飛亭,而謁岳飛銅像,一路尋幽探勝,足可怡情悅性,令人流連忘返。
返時可從白雲閣南下,欣賞園內南區景觀文物,較具文學與藝術部分,環境亦較幽靜。最好從南大門購票進入,首見有「黃鶴樓公園」匾額,入內先在鵝池憩息,只見池水清悠,柳絲垂掛,迴廊曲折,荷葉田田,無論從圖片或實地觀賞,都可以引人入勝。再去瀏覽詩碑廊、古碑廊、鵝碑亭等處,讀讀古人詩句,觀賞前人書法,可滌濾塵俗,沾染文學氣氛。再上去參觀古蹟「南樓」、文苑、擱筆亭,而「崔顥題詩圖」與歸鶴浮雕。在觀賞紫竹苑與跨鶴亭後,再登臨黃鶴樓,復瀏覽蛇山前後各景點。北麓仍有可供遊憩之地,遊客在此可盤桓終日,而遊興仍濃。歸去後,美景仍留腦際,還想再度登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