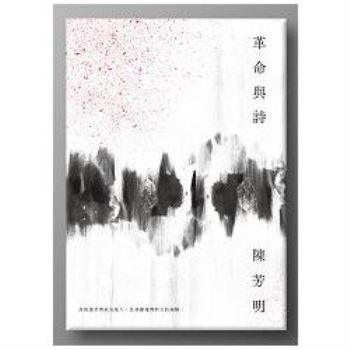詩的湖泊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阿多諾
1.
後來再也沒有回到那湖泊,回到北國針葉林圍繞的那廣大藍色水域。寧靜的湖,從天空俯望,深邃如一隻晶瑩的眼睛。如今回望時,仍然夢見那隻眼睛,不時對我凝視,對我眨眼。這時才驚覺,蜿蜒的旅路原來是以那湖泊為界,既終結了前生,也開啟了餘生。離開那湖之後,生命立刻被沖刷進入跌宕的激流,從此陰陽切割,明暗立判。
三十三歲,距離現在正好是過了半生。那年冬天的移動速度特別緩慢,已經跨年到達二月,松林傳來的寒氣依舊逼人。在嚴冬季節,樹林的顏色近乎墨綠,倒影在水面卻呈暗黑色。我那時的情緒,說有多暗,就有多暗,一如湖水的冷冷微波。寒風裡,隔著海洋,傳來美麗島事件的消息。坐在湖邊,遠望著白色水氣緩緩飄浮,終至吞噬了對岸的杉木群。在那時刻,自己的命運好像也被淹沒,完全不能辨識方向。霜氣已經消散,但整個身體竟覺得特別寒冷。彷彿被安置在冰窖裡,自己的魂魄關進一個不見出口的牢房。湖面寂寂,卻滲透著濃郁的苦澀,後半生便這樣開啟了。
如果懷抱理想的知識青年,都必須以失去自由為代價,則自己若生活在台灣,想必也會毅然介入,並且也遭到逮捕吧。在報紙上,讀著那些姓名,竟然有熟識的朋輩也在行列之中,甚至是過從密切的文學家。記憶裡,他們把生命看得很高,也把文學藝術看得更高。報導中加諸於他們的罪名,顯然已經超出所有的想像之外。不久之後,他們次第入獄,頂著「叛亂」的指控。這種政治定義,似乎也為不在現場的知識分子做好量身訂作的準備。那年的冬天是那樣遲緩,二月下旬竟來了一場暴雪。從校園高處俯望,每株杉樹覆蓋著白雪,它們都穿著白色服裝,好像準備出發到遠方參加葬禮。正是那個時刻,走出歷史系的走廊,朋友告知台灣發生一個令人髮指的血案。他描述說,林義雄住宅被兇手侵入,奪走他母親與雙胞胎女兒的性命,長女身中十餘刀。一時之間,毫不設防的心好像也被深深刺入,血液汩汩流了滿身。簡直無法承受,不禁腿軟蹲下來,全然抵禦不住廊外襲來的冷風,整個身軀幾乎是遭到棄擲。縱然沒有目睹現場慘狀,也強烈感受了人性是何等殘酷。朦朧中,似乎也看見自己躺在血泊裡,一直沉下去,沒有援手可以挽住,朝著紅色深淵不斷沉下去。穿著白色長衣的杉樹,一排一排魚貫而來,祭悼一個理想主義者之死。前生所有的夢,至此全然埋葬。
春天來時,陽光很弱,雪已經融化,綠波倒影迎接早春季節的到來。那時,台灣仍然活在審判中,命運的巨斧等待著落下。上面那神祇默然不語,靜靜俯望海島上即將開啟的美麗島大審。戰後世代的知識青年,正要跨過三十歲的界線,活生生見證了一場權力與正義的對決。有史以來,軍法審判第一次公開在新聞報導中,法官與美麗島受難人之間的對話與辯詰,彷彿給那時代的青年帶來思想上的洗禮。艾略特說,四月是最殘酷的季節,紫丁香正恣意滋長,台灣青年的四月也是極其殘酷,見證著傲慢的權力無情蔓延。隔著海洋,閱讀大審判的最後辯論,受難人說出的每一字、每一句,好像是種子那樣,一一播種在每個人的心裏。有生以來才知道,歷史閘門開啟時是多麼苦澀,從林家血案到軍法審判,無疑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跨越。從前不懂、不解的民主政治,在最短時間裏完全被催醒。
政治啟蒙的節奏是那樣迅速,遠遠超過年少以來的知識啟蒙,身陷在苦悶中,才意識到過去的文學與歷史教育是那樣無助,是那樣束手無策,對一位十二世紀中國的研究者,相當熟悉北宋、南宋的政經變化,也對當時社會生活的脈動瞭若指掌。然而面對自己的故鄉,卻忽然感到陌生異常。想到林宅的黑暗地下室裏,無辜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躺在血泊中,竟找不到絲毫合理的答案;想到高舉人權民主旗幟的政治運動者,在高牆背後,在鐵窗裏面,接受權力的凌辱,忍受時間的鞭笞,更是無法找到恰當的解釋。坐在西雅圖的書窗,舉目瞭望滿天星斗,彷彿看見自己的時代無邊無際,卻無法為自己的生命定位。書桌上疊高的宋代研究史籍,彷彿是墓碑那樣,埋葬著曾經有過的一個青春靈魂。坐在奇異的星光下,忽然看見知識的荒謬,有能力解決歷史上的困惑,卻沒有智慧處理當代的問題。在事件發生之前,每個晚上,牆壁上都投射著一個勤奮閱讀的身影,那種姿態極其謙卑,冀望著博士論文完成後,就立即返鄉。那種充滿期待與希望的身影,在事件發生後竟完全消失無蹤。西雅圖夜空的星光,倏然像淚光懸掛在窗外,憑弔著一個理想主義者之死。
焦慮、苦惱、悔恨,充塞在每個新的一天。只要思考清醒時,就有一個聲音在內心質疑著、拷問著、刑求著:龐大的知識可以找到時代出口嗎?這輩子,從未對知識追求懷有任何疑問,卻在八○年代開端,驟然產生動搖,彷彿是雪崩那樣,僅僅是些許鬆動,立即一瀉千里。生命的轉變來得太快,只是從冬季跨向春季,就已經無法認識自己。在政治上以自由主義者自命,在文學上以現代主義者自許,如今才覺悟完全不能回應海洋那邊故鄉的召喚。整個身體好像被拋棄在荒涼的土地,體內的血液如驚濤駭浪,卻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是。在找不到精神出口的時刻,只能拾起聶魯達的詩集反覆閱讀。有一天下午,偶然遇見詩中的兩行:「當你的朋友坐在監牢,你在獄外做甚麼」,像驚雷那樣擊打著心坎,不期然在心房的角落也秘密寫下這樣兩行:「當歷史關在鐵窗,你在域外做甚麼」。這樣提問時,就隱約感知未來道路已經到達一個分合的路口。
2.
美麗島大審結束,陽光回到繁花盛放的校園。騷動的思維,未嘗有一個時可靜止下來。曾經對自由主義傳統深信不疑,不僅以為必須為自己說出的每一句話,寫下的每一段字,都必須負責。而且也以為發表出來的所有語言,只要屬於誠實,就會受到尊重。年輕時閱讀《胡適文存》,深深折服於他對權力講真話的勇氣。但是,一九六○年雷震事件發生之後,似乎可以察覺自由主義有其現實上的極限。至少在台灣,威權體制的干涉,使戰後知識分子的思想出路受到阻斷。美麗島事件帶來的最大打擊,便是認清言論問政的途徑必然會遭到挫折。這種最溫和的姿態,最低調的運動,如果置放在美國的社會,似乎不可能產生絲毫波動。在出國之前,見證草根型的民主運動正在萌芽,也看見鄉土文學運動已蓄勢待發。那種活潑的空氣,是前所未有的文化氣象。如果沒有離開台灣,一九七○年代初期帶來的衝擊力量,必然會一步一步被推入政治的漩渦。對於自由的信念,隨著年歲成長,也受到美國自由社會的感染,似乎越來越堅定。遠在海外,難以準確評估台灣社會的歷史進程。鄉土文學論戰在一九七七年爆發之際,錯覺地以為一個更開放的時期即將降臨。作為書生的愚妄,莫此為甚。那時,獲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之後,找到較為從容的時間,開始提筆撰寫政論。如果要追溯自己的問政企圖,大約可以在這時窺見端倪。
敢於這樣嘗試,是因為對於宋代歷史研究漸漸感到無奈與不耐。隔海望見那麼多民主運動者含冤入獄,對於知識的效用不免發出懷疑。過去從來沒有發生如此動搖。最徬徨的時刻,亟需尋找立即的答案。就在進入五月時,許信良專程來到華盛頓大學。與他坐在可以望見湖水的校園咖啡室,漫談著台灣民主前景。他說,現在能夠努力的方向,便是在海外重建美麗島精神。對威權體制的最好答覆,就是不容批判力量停頓下來。
自己身為人權工作者,從一九七五年開始,就介入聲援第三世界政治犯的活動。加入國際特赦會以來,曾經寫信給中南美洲的強人政權,也支持過菲律賓與南韓的政治運動。能夠站在受害者的立場,表達最深沉的抗議,竟對自己故鄉的受難事件保持沉默,豈非是懦弱的退卻?五月陽光擦亮了落地窗,使湖面的反光更強烈。怔忡遠望著那藍色湖水,好像有某種意念正暗自形成。如果決定離開校園,不僅進行中的論文即將中斷,也有可能很長一段時間不能返回台灣。在南下洛杉磯前的三、四個月,內心掙扎許久。但是,想到護照被拒絕續簽時,總覺得好像走到世界的一個盡頭。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的半年,前往辦事處申請重簽,完全遭到拒絕。櫃檯後面的辦事員,以著輕蔑的語氣,鄙夷的神情說:「你被拒絕的理由,你自己知道。」在錯愕裏,生平第一次嘗到國家機器是如何欺負著國民。落寞拿著那本護照,忽然不知道國家的意義為何。回想過去的重大事跡,只記得在圖書館裏翻閱中國的《人民日報》,只記得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只記得與同學在餐廳聚會裏談論時政。如果這就被視為滔天大罪,那麼美麗島人士更是罪不可赦了。一個冤案的構築,並非是受害者具有怎樣的野心,也並非是訴諸如何的非常行動,只不過是權力在握者沒有絲毫安全感,也不過是統治者的自私與貪婪禁不起受到批判。
終於決定參加許信良籌備的《美麗島週報》,無疑是漸近中年時的關鍵決定。那時開始偏離文學,也終於離開學術。南下之旅,等於背叛了親人與朋輩的殷切期待,也背叛了十餘年苦苦追尋的詩學道路。詩與政治之間,是多麼遙遠的距離。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在一夜之間,忽然理解其中的真義。作為入世的哲學家,阿多諾對現代文化充滿批判精神。他見證了納粹在奧斯維辛的大屠殺,人間的抒情也跟著一起毀滅。在文明廢墟之上,在人體犧牲之上,如果還藉用寫詩來逃避,顯然是非常野蠻的行為。對於那時期的靈魂來說,詩忽然變得極其遙遠。
詩是什麼?那曾經是一種救贖,在青春時期無以排遣苦悶之際,詩的語言與節奏,有一定的淨化作用。在精神層面提供一把梯子,容許受困的魂魄爬到某種高度,可以看見囚牢以外的世界。詩是什麼?它的音樂性,是緊張情緒的鬆弛劑,它帶來的想像,使狹窄空間變得更加開闊,使僵化的思維轉為活潑。詩是庸俗與超俗的對決,是凌駕在政治之上的純淨藝術,使內心污穢可以得到豁免,使醜陋遭到遮蔽。時代浪潮沖刷而來,應該是醜陋的權力受到清理。如果歷史航行沒有偏離方位,則詩的方向無庸懷疑。跨過事件時,整個天地定理竟然是以顛倒的形式現形。醜陋恆居上位,權力依舊橫行。人權與正義反而受到羞辱,受到審判。如果繼續寫詩,是否間接為秩序顛倒的威權背書?詩已經失去拯救的力量,當返鄉的道路驟然切斷,當親情受到凌遲,當生命意義被嚴重扭曲,寫詩是多麼悖理。
決定離開西雅圖之前,再度驅車回到華盛頓湖。那時已經是盛夏,水色乾淨得無可置信。遠離台灣如此久遠之後,仍然斷斷續續與龍族詩社維持信息相通。從一九七○年詩社成立以來,詩是唯一的信仰。對於詩的狂熱,無論是閱讀或書寫,未嘗稍懈。學校裏的圖書館收藏中國三十年代的詩集甚豐,從七月詩派到九葉詩人的作品,都整齊放在架上。最初有意要整理失落的詩史,還特地到史丹福大學,尋找謠傳已久的詩集。那是最神聖的歲月,每首詩都進駐著一尊神,以圓熟之光,撫慰漂泊之心。
從來未曾預知,流亡的日子已經準備就緒,而且將連綿延續未來十餘年。巨大惡運之神張開巨大的網,徹底吞噬了前半生的詩學。如果要確切定義湖畔歲月,那可能是文學生命的古典時期。投入政治深淵之後,好像身驅被置放在一架龐大的縫紉機,一呎一吋慢慢遭到肢解,撕裂之後又重新縫合。離開華盛頓湖以後,也就離開寫詩的時代。如今回望那湖,才發覺每一道波紋都是詩行。
2014.1.19 木柵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阿多諾
1.
後來再也沒有回到那湖泊,回到北國針葉林圍繞的那廣大藍色水域。寧靜的湖,從天空俯望,深邃如一隻晶瑩的眼睛。如今回望時,仍然夢見那隻眼睛,不時對我凝視,對我眨眼。這時才驚覺,蜿蜒的旅路原來是以那湖泊為界,既終結了前生,也開啟了餘生。離開那湖之後,生命立刻被沖刷進入跌宕的激流,從此陰陽切割,明暗立判。
三十三歲,距離現在正好是過了半生。那年冬天的移動速度特別緩慢,已經跨年到達二月,松林傳來的寒氣依舊逼人。在嚴冬季節,樹林的顏色近乎墨綠,倒影在水面卻呈暗黑色。我那時的情緒,說有多暗,就有多暗,一如湖水的冷冷微波。寒風裡,隔著海洋,傳來美麗島事件的消息。坐在湖邊,遠望著白色水氣緩緩飄浮,終至吞噬了對岸的杉木群。在那時刻,自己的命運好像也被淹沒,完全不能辨識方向。霜氣已經消散,但整個身體竟覺得特別寒冷。彷彿被安置在冰窖裡,自己的魂魄關進一個不見出口的牢房。湖面寂寂,卻滲透著濃郁的苦澀,後半生便這樣開啟了。
如果懷抱理想的知識青年,都必須以失去自由為代價,則自己若生活在台灣,想必也會毅然介入,並且也遭到逮捕吧。在報紙上,讀著那些姓名,竟然有熟識的朋輩也在行列之中,甚至是過從密切的文學家。記憶裡,他們把生命看得很高,也把文學藝術看得更高。報導中加諸於他們的罪名,顯然已經超出所有的想像之外。不久之後,他們次第入獄,頂著「叛亂」的指控。這種政治定義,似乎也為不在現場的知識分子做好量身訂作的準備。那年的冬天是那樣遲緩,二月下旬竟來了一場暴雪。從校園高處俯望,每株杉樹覆蓋著白雪,它們都穿著白色服裝,好像準備出發到遠方參加葬禮。正是那個時刻,走出歷史系的走廊,朋友告知台灣發生一個令人髮指的血案。他描述說,林義雄住宅被兇手侵入,奪走他母親與雙胞胎女兒的性命,長女身中十餘刀。一時之間,毫不設防的心好像也被深深刺入,血液汩汩流了滿身。簡直無法承受,不禁腿軟蹲下來,全然抵禦不住廊外襲來的冷風,整個身軀幾乎是遭到棄擲。縱然沒有目睹現場慘狀,也強烈感受了人性是何等殘酷。朦朧中,似乎也看見自己躺在血泊裡,一直沉下去,沒有援手可以挽住,朝著紅色深淵不斷沉下去。穿著白色長衣的杉樹,一排一排魚貫而來,祭悼一個理想主義者之死。前生所有的夢,至此全然埋葬。
春天來時,陽光很弱,雪已經融化,綠波倒影迎接早春季節的到來。那時,台灣仍然活在審判中,命運的巨斧等待著落下。上面那神祇默然不語,靜靜俯望海島上即將開啟的美麗島大審。戰後世代的知識青年,正要跨過三十歲的界線,活生生見證了一場權力與正義的對決。有史以來,軍法審判第一次公開在新聞報導中,法官與美麗島受難人之間的對話與辯詰,彷彿給那時代的青年帶來思想上的洗禮。艾略特說,四月是最殘酷的季節,紫丁香正恣意滋長,台灣青年的四月也是極其殘酷,見證著傲慢的權力無情蔓延。隔著海洋,閱讀大審判的最後辯論,受難人說出的每一字、每一句,好像是種子那樣,一一播種在每個人的心裏。有生以來才知道,歷史閘門開啟時是多麼苦澀,從林家血案到軍法審判,無疑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跨越。從前不懂、不解的民主政治,在最短時間裏完全被催醒。
政治啟蒙的節奏是那樣迅速,遠遠超過年少以來的知識啟蒙,身陷在苦悶中,才意識到過去的文學與歷史教育是那樣無助,是那樣束手無策,對一位十二世紀中國的研究者,相當熟悉北宋、南宋的政經變化,也對當時社會生活的脈動瞭若指掌。然而面對自己的故鄉,卻忽然感到陌生異常。想到林宅的黑暗地下室裏,無辜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躺在血泊中,竟找不到絲毫合理的答案;想到高舉人權民主旗幟的政治運動者,在高牆背後,在鐵窗裏面,接受權力的凌辱,忍受時間的鞭笞,更是無法找到恰當的解釋。坐在西雅圖的書窗,舉目瞭望滿天星斗,彷彿看見自己的時代無邊無際,卻無法為自己的生命定位。書桌上疊高的宋代研究史籍,彷彿是墓碑那樣,埋葬著曾經有過的一個青春靈魂。坐在奇異的星光下,忽然看見知識的荒謬,有能力解決歷史上的困惑,卻沒有智慧處理當代的問題。在事件發生之前,每個晚上,牆壁上都投射著一個勤奮閱讀的身影,那種姿態極其謙卑,冀望著博士論文完成後,就立即返鄉。那種充滿期待與希望的身影,在事件發生後竟完全消失無蹤。西雅圖夜空的星光,倏然像淚光懸掛在窗外,憑弔著一個理想主義者之死。
焦慮、苦惱、悔恨,充塞在每個新的一天。只要思考清醒時,就有一個聲音在內心質疑著、拷問著、刑求著:龐大的知識可以找到時代出口嗎?這輩子,從未對知識追求懷有任何疑問,卻在八○年代開端,驟然產生動搖,彷彿是雪崩那樣,僅僅是些許鬆動,立即一瀉千里。生命的轉變來得太快,只是從冬季跨向春季,就已經無法認識自己。在政治上以自由主義者自命,在文學上以現代主義者自許,如今才覺悟完全不能回應海洋那邊故鄉的召喚。整個身體好像被拋棄在荒涼的土地,體內的血液如驚濤駭浪,卻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是。在找不到精神出口的時刻,只能拾起聶魯達的詩集反覆閱讀。有一天下午,偶然遇見詩中的兩行:「當你的朋友坐在監牢,你在獄外做甚麼」,像驚雷那樣擊打著心坎,不期然在心房的角落也秘密寫下這樣兩行:「當歷史關在鐵窗,你在域外做甚麼」。這樣提問時,就隱約感知未來道路已經到達一個分合的路口。
2.
美麗島大審結束,陽光回到繁花盛放的校園。騷動的思維,未嘗有一個時可靜止下來。曾經對自由主義傳統深信不疑,不僅以為必須為自己說出的每一句話,寫下的每一段字,都必須負責。而且也以為發表出來的所有語言,只要屬於誠實,就會受到尊重。年輕時閱讀《胡適文存》,深深折服於他對權力講真話的勇氣。但是,一九六○年雷震事件發生之後,似乎可以察覺自由主義有其現實上的極限。至少在台灣,威權體制的干涉,使戰後知識分子的思想出路受到阻斷。美麗島事件帶來的最大打擊,便是認清言論問政的途徑必然會遭到挫折。這種最溫和的姿態,最低調的運動,如果置放在美國的社會,似乎不可能產生絲毫波動。在出國之前,見證草根型的民主運動正在萌芽,也看見鄉土文學運動已蓄勢待發。那種活潑的空氣,是前所未有的文化氣象。如果沒有離開台灣,一九七○年代初期帶來的衝擊力量,必然會一步一步被推入政治的漩渦。對於自由的信念,隨著年歲成長,也受到美國自由社會的感染,似乎越來越堅定。遠在海外,難以準確評估台灣社會的歷史進程。鄉土文學論戰在一九七七年爆發之際,錯覺地以為一個更開放的時期即將降臨。作為書生的愚妄,莫此為甚。那時,獲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之後,找到較為從容的時間,開始提筆撰寫政論。如果要追溯自己的問政企圖,大約可以在這時窺見端倪。
敢於這樣嘗試,是因為對於宋代歷史研究漸漸感到無奈與不耐。隔海望見那麼多民主運動者含冤入獄,對於知識的效用不免發出懷疑。過去從來沒有發生如此動搖。最徬徨的時刻,亟需尋找立即的答案。就在進入五月時,許信良專程來到華盛頓大學。與他坐在可以望見湖水的校園咖啡室,漫談著台灣民主前景。他說,現在能夠努力的方向,便是在海外重建美麗島精神。對威權體制的最好答覆,就是不容批判力量停頓下來。
自己身為人權工作者,從一九七五年開始,就介入聲援第三世界政治犯的活動。加入國際特赦會以來,曾經寫信給中南美洲的強人政權,也支持過菲律賓與南韓的政治運動。能夠站在受害者的立場,表達最深沉的抗議,竟對自己故鄉的受難事件保持沉默,豈非是懦弱的退卻?五月陽光擦亮了落地窗,使湖面的反光更強烈。怔忡遠望著那藍色湖水,好像有某種意念正暗自形成。如果決定離開校園,不僅進行中的論文即將中斷,也有可能很長一段時間不能返回台灣。在南下洛杉磯前的三、四個月,內心掙扎許久。但是,想到護照被拒絕續簽時,總覺得好像走到世界的一個盡頭。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的半年,前往辦事處申請重簽,完全遭到拒絕。櫃檯後面的辦事員,以著輕蔑的語氣,鄙夷的神情說:「你被拒絕的理由,你自己知道。」在錯愕裏,生平第一次嘗到國家機器是如何欺負著國民。落寞拿著那本護照,忽然不知道國家的意義為何。回想過去的重大事跡,只記得在圖書館裏翻閱中國的《人民日報》,只記得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只記得與同學在餐廳聚會裏談論時政。如果這就被視為滔天大罪,那麼美麗島人士更是罪不可赦了。一個冤案的構築,並非是受害者具有怎樣的野心,也並非是訴諸如何的非常行動,只不過是權力在握者沒有絲毫安全感,也不過是統治者的自私與貪婪禁不起受到批判。
終於決定參加許信良籌備的《美麗島週報》,無疑是漸近中年時的關鍵決定。那時開始偏離文學,也終於離開學術。南下之旅,等於背叛了親人與朋輩的殷切期待,也背叛了十餘年苦苦追尋的詩學道路。詩與政治之間,是多麼遙遠的距離。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在一夜之間,忽然理解其中的真義。作為入世的哲學家,阿多諾對現代文化充滿批判精神。他見證了納粹在奧斯維辛的大屠殺,人間的抒情也跟著一起毀滅。在文明廢墟之上,在人體犧牲之上,如果還藉用寫詩來逃避,顯然是非常野蠻的行為。對於那時期的靈魂來說,詩忽然變得極其遙遠。
詩是什麼?那曾經是一種救贖,在青春時期無以排遣苦悶之際,詩的語言與節奏,有一定的淨化作用。在精神層面提供一把梯子,容許受困的魂魄爬到某種高度,可以看見囚牢以外的世界。詩是什麼?它的音樂性,是緊張情緒的鬆弛劑,它帶來的想像,使狹窄空間變得更加開闊,使僵化的思維轉為活潑。詩是庸俗與超俗的對決,是凌駕在政治之上的純淨藝術,使內心污穢可以得到豁免,使醜陋遭到遮蔽。時代浪潮沖刷而來,應該是醜陋的權力受到清理。如果歷史航行沒有偏離方位,則詩的方向無庸懷疑。跨過事件時,整個天地定理竟然是以顛倒的形式現形。醜陋恆居上位,權力依舊橫行。人權與正義反而受到羞辱,受到審判。如果繼續寫詩,是否間接為秩序顛倒的威權背書?詩已經失去拯救的力量,當返鄉的道路驟然切斷,當親情受到凌遲,當生命意義被嚴重扭曲,寫詩是多麼悖理。
決定離開西雅圖之前,再度驅車回到華盛頓湖。那時已經是盛夏,水色乾淨得無可置信。遠離台灣如此久遠之後,仍然斷斷續續與龍族詩社維持信息相通。從一九七○年詩社成立以來,詩是唯一的信仰。對於詩的狂熱,無論是閱讀或書寫,未嘗稍懈。學校裏的圖書館收藏中國三十年代的詩集甚豐,從七月詩派到九葉詩人的作品,都整齊放在架上。最初有意要整理失落的詩史,還特地到史丹福大學,尋找謠傳已久的詩集。那是最神聖的歲月,每首詩都進駐著一尊神,以圓熟之光,撫慰漂泊之心。
從來未曾預知,流亡的日子已經準備就緒,而且將連綿延續未來十餘年。巨大惡運之神張開巨大的網,徹底吞噬了前半生的詩學。如果要確切定義湖畔歲月,那可能是文學生命的古典時期。投入政治深淵之後,好像身驅被置放在一架龐大的縫紉機,一呎一吋慢慢遭到肢解,撕裂之後又重新縫合。離開華盛頓湖以後,也就離開寫詩的時代。如今回望那湖,才發覺每一道波紋都是詩行。
2014.1.19 木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