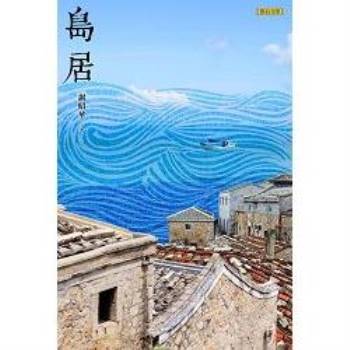悲傷色澤
二○一三這一年島嶼最為人所熟知的名詞是「藍眼淚」,就是在島嶼靠南面的海面上星羅棋佈著點點藍光,有時侵入沙灘成為令人驚喜的星沙,但大多飄浮海面,隨潮汐浮沉。它的起源莫衷一是,原先認為是渦鞭毛藻與介形蟲,而最近的研究證據顯示它應該是群集的夜光藻,一種身體會發出令人眩目螢光的海藻類。只是,牛角村的伊顯伯淡定地說:「這海面夜光早就有了呀,我伊公說,他年輕時討海就常見到了。」
這時我便覺得困惑,同一種自然景象,老漁民覺得無甚稀奇,年輕人卻為之驚豔。拜攝影技術與器材發展之賜,一群號稱「追淚族」的人潮,逐淚而居,夙夜匪懈,常於夜半離家在海岸邊苦候,調好快門與光圈,雙眼緊盯著海面,濤聲陣陣,不問世事只為淚癡狂。在清明與梅雨間令人情緒紊亂的季節,若夜半失眠外出,沿著津沙海灘、三三據點、三五據點、鐵堡、大漢據點,以至神祕如桃花源的北海坑道帶狀海岸,常不經意撞見孤獨的遊魂望著海面枯坐,身邊必然用腳架架好慢速快門相機,長時間的曝光將沁涼的夜色吸入深不可測的光圈裡,如一泉黝暗的古井,夢境滴落井底時發出清脆的回音。此時你就可聽見兩個原先陌生的遊魂對話:
「今晚淚況如何?」
「哦,似乎淚潮洶湧。」
「是嗎?」
「是呀,多麼悲傷的海!」
接著一陣沉默,如同觸動了昔日的記憶,那遍尋不著的腳底海膽刺舊傷又隱隱開始椎心刺痛。
有些追淚族日常散漫不羈,但一提起藍眼淚,雙眼便散發出星暴星系的光彩,直說可惜李安拍攝少年PI時沒來小島勘景,不然只要拍現場實景即可,完全不須借助高成本的電腦動畫師。衣食無虞的成長環境使年輕世代對自己生活土地之美充滿自信,這正是他們與上一輩相異之處。他們追淚的範圍不僅只於南竿島,更跨海至北竿、東引與東西莒諸島,旅遊指南上所敘述的跳島之旅正在他們身上應驗著。島嶼一如澎湖群島、澳洲大堡礁、愛琴海諸島一般,遊客如織;但夜間卻是諸神聚集,孤寂心靈的居所。但是伊顯伯說的並沒錯。數十年來,他每天黎明即起,喝碗溫老酒就出門。揹著漁具從牛角嶺山腳下的老石屋經蜿蜒的石板巷弄到出村港口。肩揹M16步槍在崗哨值勤的青澀充員兵睡眼惺忪地查驗了漁民證,就放他們出海作業。收纜繩上船、查看定置網、再出海佈網牽罟。對他們而言,海洋是工作的場域,體力勞動的所在,也是賺取全家溫飽的生產地。無論披星戴月,或是黎明霞光,都與日常生活融為一體。而四季變幻,日升月落,只是他們眼眸中緩緩流變的光景。近年兩岸緊張局勢和緩,對岸漁民欺人登島,或切割盜取定置漁網的情事不斷發生,常使他們數月的心血毀於一旦。對伊顯伯而言,藍眼淚是生的一部份,是三餐,是陽光,是梅雨季節的雨水,更是颱風天的風狂雨暴。
一座島一個故事,此時此地,島嶼所敘說的,是海面上數不清的深藍繁星。
聖詠
友人遠道來訪,我們驅車至島嶼西尾處一家僻靜的咖啡館小坐。島上的每一家咖啡館都靠山面海,視野寬廣。是日陽光和煦,海風習習,我們便坐在戶外咖啡座閒聊。友人拿出背包裡一本舊俄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中篇小說,說是旅途閒暇時翻閱。會想要讀這樣一位思想與個性都極端的作家作品,我不禁對眼前這位外表溫文儒雅的友人覺得好奇,猜疑他藏著的是怎樣一顆激越的心。
義大利導演費里尼也說:「生活無他,唯有無止盡的激情。」數十年軍事管理的禁令解除之時,曾經在島民平靜的心裡刮起陣陣沙塵暴。然而之後的生活激情,卻在一次次離開與返回島嶼的候船候機磨難中消耗殆盡。那年小安剛滿週歲,我們安排了假期去高雄她外公家小住。返程時大舅開車送我們到火車站,然後一路輾轉來到松山機場。無法預料的是到了航空站櫃台,卻只見航空站櫃台上貼著「天候不佳,機場關閉」八個大字,頓時進退失據。是要在航空站苦候不知何時才能開放的機場,或是再乘車轉往基隆港搭乘耗時七至八小時海上航程的台馬客輪返家,令人難以抉擇。航空站裡,候機島民與身著迷彩服的義務役軍士或坐或站,人人身旁一件件包裹行李,神色疲憊至極。前些年,國會議員修訂了離島建設條例,允許離島縣市在公民投票贊成的前提下在國際渡假村的計劃中規劃百分之五的區域開辦博奕。澎湖鄉親在正反方激烈辯論之後否決了此一公民投票案,金門原提案人也在提案兩年期滿無法成案的狀況下主動撤案。之後,輪到馬祖。
在多年盼望的機場改善計畫一再落空之後,冀望財團進駐投資,整建一座出入便捷不受天候影響機場的聲音在島嶼出現。這是多麼艱難的抉擇,許多家庭裡,因為這一爭議性極高的議題而親子交惡,姊妹反目,與兄弟鬩牆。公民投票案的宣導期間,在地民眾也自發地發起反博奕聯盟,與贊成者在公開場合與街頭巷弄激烈交鋒,也為島民上了一堂理性思辨公共議題的公民教育課程。
上午門診來了一位來自大陸的病患,基於職業的敏感與好奇,詢問了他的來處,卻意外地發現他竟是一位小學老師,昨天才與妻兒遠從江西經由福建馬尾與馬祖小三通航道來島嶼自由行。我這才驚覺,在封閉的島嶼中生活,這些年兩岸三地情勢變化的速度已超乎想像。在多年之前,我還每周一次驅車前往靖廬出診,那是安置大陸偷渡來台民眾的臨時收容所,由舊小學改建,四周圍牆上佈滿防止脫逃的鐵絲網。看完診時,年邁的天主堂修女姆姆便蹣跚而來探訪收容住民。當我驅車離開,收容所裡就會傳出陣陣聖詠的詩歌。
在死神始終旁觀的生命棋局裡,我們正與自己對弈,與歷史對弈。萬籟俱寂的夜晚,腦海裡憶起林泠的詩句:
「蒙地卡羅的夜啊/我愛的那人正烤著火/他拾來的松枝不夠燃燒,蒙地卡羅的夜/他要去了我的髮,我的脊骨……
二○一三這一年島嶼最為人所熟知的名詞是「藍眼淚」,就是在島嶼靠南面的海面上星羅棋佈著點點藍光,有時侵入沙灘成為令人驚喜的星沙,但大多飄浮海面,隨潮汐浮沉。它的起源莫衷一是,原先認為是渦鞭毛藻與介形蟲,而最近的研究證據顯示它應該是群集的夜光藻,一種身體會發出令人眩目螢光的海藻類。只是,牛角村的伊顯伯淡定地說:「這海面夜光早就有了呀,我伊公說,他年輕時討海就常見到了。」
這時我便覺得困惑,同一種自然景象,老漁民覺得無甚稀奇,年輕人卻為之驚豔。拜攝影技術與器材發展之賜,一群號稱「追淚族」的人潮,逐淚而居,夙夜匪懈,常於夜半離家在海岸邊苦候,調好快門與光圈,雙眼緊盯著海面,濤聲陣陣,不問世事只為淚癡狂。在清明與梅雨間令人情緒紊亂的季節,若夜半失眠外出,沿著津沙海灘、三三據點、三五據點、鐵堡、大漢據點,以至神祕如桃花源的北海坑道帶狀海岸,常不經意撞見孤獨的遊魂望著海面枯坐,身邊必然用腳架架好慢速快門相機,長時間的曝光將沁涼的夜色吸入深不可測的光圈裡,如一泉黝暗的古井,夢境滴落井底時發出清脆的回音。此時你就可聽見兩個原先陌生的遊魂對話:
「今晚淚況如何?」
「哦,似乎淚潮洶湧。」
「是嗎?」
「是呀,多麼悲傷的海!」
接著一陣沉默,如同觸動了昔日的記憶,那遍尋不著的腳底海膽刺舊傷又隱隱開始椎心刺痛。
有些追淚族日常散漫不羈,但一提起藍眼淚,雙眼便散發出星暴星系的光彩,直說可惜李安拍攝少年PI時沒來小島勘景,不然只要拍現場實景即可,完全不須借助高成本的電腦動畫師。衣食無虞的成長環境使年輕世代對自己生活土地之美充滿自信,這正是他們與上一輩相異之處。他們追淚的範圍不僅只於南竿島,更跨海至北竿、東引與東西莒諸島,旅遊指南上所敘述的跳島之旅正在他們身上應驗著。島嶼一如澎湖群島、澳洲大堡礁、愛琴海諸島一般,遊客如織;但夜間卻是諸神聚集,孤寂心靈的居所。但是伊顯伯說的並沒錯。數十年來,他每天黎明即起,喝碗溫老酒就出門。揹著漁具從牛角嶺山腳下的老石屋經蜿蜒的石板巷弄到出村港口。肩揹M16步槍在崗哨值勤的青澀充員兵睡眼惺忪地查驗了漁民證,就放他們出海作業。收纜繩上船、查看定置網、再出海佈網牽罟。對他們而言,海洋是工作的場域,體力勞動的所在,也是賺取全家溫飽的生產地。無論披星戴月,或是黎明霞光,都與日常生活融為一體。而四季變幻,日升月落,只是他們眼眸中緩緩流變的光景。近年兩岸緊張局勢和緩,對岸漁民欺人登島,或切割盜取定置漁網的情事不斷發生,常使他們數月的心血毀於一旦。對伊顯伯而言,藍眼淚是生的一部份,是三餐,是陽光,是梅雨季節的雨水,更是颱風天的風狂雨暴。
一座島一個故事,此時此地,島嶼所敘說的,是海面上數不清的深藍繁星。
聖詠
友人遠道來訪,我們驅車至島嶼西尾處一家僻靜的咖啡館小坐。島上的每一家咖啡館都靠山面海,視野寬廣。是日陽光和煦,海風習習,我們便坐在戶外咖啡座閒聊。友人拿出背包裡一本舊俄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中篇小說,說是旅途閒暇時翻閱。會想要讀這樣一位思想與個性都極端的作家作品,我不禁對眼前這位外表溫文儒雅的友人覺得好奇,猜疑他藏著的是怎樣一顆激越的心。
義大利導演費里尼也說:「生活無他,唯有無止盡的激情。」數十年軍事管理的禁令解除之時,曾經在島民平靜的心裡刮起陣陣沙塵暴。然而之後的生活激情,卻在一次次離開與返回島嶼的候船候機磨難中消耗殆盡。那年小安剛滿週歲,我們安排了假期去高雄她外公家小住。返程時大舅開車送我們到火車站,然後一路輾轉來到松山機場。無法預料的是到了航空站櫃台,卻只見航空站櫃台上貼著「天候不佳,機場關閉」八個大字,頓時進退失據。是要在航空站苦候不知何時才能開放的機場,或是再乘車轉往基隆港搭乘耗時七至八小時海上航程的台馬客輪返家,令人難以抉擇。航空站裡,候機島民與身著迷彩服的義務役軍士或坐或站,人人身旁一件件包裹行李,神色疲憊至極。前些年,國會議員修訂了離島建設條例,允許離島縣市在公民投票贊成的前提下在國際渡假村的計劃中規劃百分之五的區域開辦博奕。澎湖鄉親在正反方激烈辯論之後否決了此一公民投票案,金門原提案人也在提案兩年期滿無法成案的狀況下主動撤案。之後,輪到馬祖。
在多年盼望的機場改善計畫一再落空之後,冀望財團進駐投資,整建一座出入便捷不受天候影響機場的聲音在島嶼出現。這是多麼艱難的抉擇,許多家庭裡,因為這一爭議性極高的議題而親子交惡,姊妹反目,與兄弟鬩牆。公民投票案的宣導期間,在地民眾也自發地發起反博奕聯盟,與贊成者在公開場合與街頭巷弄激烈交鋒,也為島民上了一堂理性思辨公共議題的公民教育課程。
上午門診來了一位來自大陸的病患,基於職業的敏感與好奇,詢問了他的來處,卻意外地發現他竟是一位小學老師,昨天才與妻兒遠從江西經由福建馬尾與馬祖小三通航道來島嶼自由行。我這才驚覺,在封閉的島嶼中生活,這些年兩岸三地情勢變化的速度已超乎想像。在多年之前,我還每周一次驅車前往靖廬出診,那是安置大陸偷渡來台民眾的臨時收容所,由舊小學改建,四周圍牆上佈滿防止脫逃的鐵絲網。看完診時,年邁的天主堂修女姆姆便蹣跚而來探訪收容住民。當我驅車離開,收容所裡就會傳出陣陣聖詠的詩歌。
在死神始終旁觀的生命棋局裡,我們正與自己對弈,與歷史對弈。萬籟俱寂的夜晚,腦海裡憶起林泠的詩句:
「蒙地卡羅的夜啊/我愛的那人正烤著火/他拾來的松枝不夠燃燒,蒙地卡羅的夜/他要去了我的髮,我的脊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