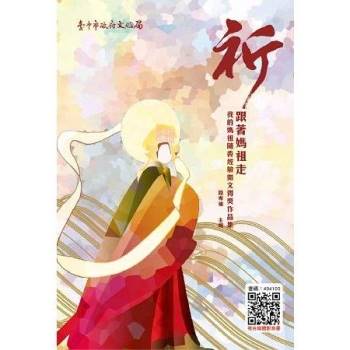祈/高于婷
記得小時候媽祖遶境時,我最怕黑白無常了。
那時甚至還不太知道黑白無常指的就是七爺八爺(1),只知道每到一個固定的時間,他們就會出現在街道上,巨大的身軀搖搖擺擺地在地上拉出一高一低晃動的影。而我不夠高,一抬頭,對上的便是對幼童來說過於猙獰的面孔。
他們一前一後地走進正在營業中的店家,過長的衣袖有頻率地揮動,我很想逃跑,卻因為出入口過於狹窄,一移動便會與其擦身而過。一時間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顫巍巍地躲在人群後,假裝所有可怕的東西都能被擋在外面,而我留在裡面,與我的恐懼一起。
約莫過了幾分鐘後,圍聚的人群散去,將我凝結的恐懼一點點抽開,所有的光都再次流瀉進來,重新把寫著勇氣的空洞填滿。
嗩吶與鑼鼓的聲音再次大聲響起,我輕皺著眉,只覺得過高的分貝使人感到不適,就像遶境時點燃一串又一串的鞭炮,不管我用手把耳朵摀得再緊再緊,都沒辦法把所有噪音通通趕走。
這是小時候的記憶,我對於民俗活動的恐懼及些許排斥。
十多年過去,我還是那個我,雖然已經不會害怕那些走進店裡的黑白無常,卻成了一個進廟不願意合掌拜拜的女孩。
很多時候我不懂,合十的掌中包裹著的祈願(2),真的能夠因為一次又一次的彎腰而成功嗎?那樣一正一反、發出清脆聲響的筊,能夠把所有事情都翻到正確的位置上嗎?
懷抱著這樣的疑問踏入大學生活,我在那裏遇到了民俗文化相關的課程,老師交雜著國、臺語的聲音,組成一個又一個臺灣的民俗活動,或大或小。
而在這之中,課堂上著墨最久的便是「媽祖進香(3)」了。
相對於其它民俗相關活動,媽祖很特別。有的不知道時間長短,有的一走便是九天八夜,始終不變的,就只有一群緊緊跟隨媽祖腳步前進的虔誠信徒們。
「你們要去看看,那些人為什麼願意走九天八夜,為什麼願意在沒有金錢交易的情況下,還發送大把大把的食物。」
老師的語氣並沒有特別激昂,但堅毅的感情卻直直打進心中。我知道自己從來就不是個虔誠的信徒,卻也還是跟上了進香的步伐,用自己的雙眼雙腳,親自見證老師希望我們所見的。北港媽祖、大甲媽祖、白沙屯媽祖,今年無論哪一個媽祖都是披著雨水在遶境的。尤其在白沙屯媽祖遶境(4)的途中,所有沿路跟隨的信徒們,也都和媽祖淋著同樣的雨前進,每個人穿上五顏六色的雨衣,成為隨香過程中最新潮的護駕團。
在大雨中,一雙雙被反覆滲濕的手不斷向外伸出,遞上食物及飲料慰勞信徒,沒走幾步就能看見一小群人停在路邊,對每個經過的人給出一瓶飲料、一顆水果、甚至是一個暖暖的肉包,口中還不忘順便為大家加油打氣。
那些不斷伸出去的手並不會因此染上任何一絲金錢的銅味,即使如此,卻還是有數不清的人在對數以萬計的陌生人付出關懷與愛心。
冰涼的雨水打在臉上、打在食物上、打在咬著包子的口中,然而每一次咀嚼到的卻又是溫熱無比的暖意。讓人分不清究竟是食物本身的溫度,還是那些遞送食物的人,心中所擁有的熱度。
他們並不會因為這樣而實質上得到些什麼,就像在廟宇中的合十拜拜後,不會因此就完成心中的願望。
但每一個「拜拜(5)」並不只是奢望能夠就此達成心中想做的事情,而是藉由深深地彎腰,增加為了目標繼續往前進的動力。就像進香當中發送難以估計數量及金錢的物資,是那些人將自己所有的虔誠灌注其中,希望每個拿到物資的信徒,都能夠有繼續前進的動力,而信徒繼續前進,為了往媽祖所在的方向,為了往自己心中期望的那個心願所在之處。
連串的鞭炮聲響起,如今除了吵雜之外,似乎也聽見了一些人們在施放鞭炮時,心中呢喃著的小小願望。如同每一次的鑼響、如同每一聲的嗩吶,在那些背後都有許多人感謝的心意,感謝媽祖曾經給予他們勇氣、讓他們不再畏懼。
白沙屯媽祖的鑾轎經過,我輕輕地將掌心貼著掌心,每一寸指節都穩穩地互相對齊併攏,閉上眼,緩緩地將誠意鎔鑄在掌中,祈願。
記得小時候媽祖遶境時,我最怕黑白無常了。
那時甚至還不太知道黑白無常指的就是七爺八爺(1),只知道每到一個固定的時間,他們就會出現在街道上,巨大的身軀搖搖擺擺地在地上拉出一高一低晃動的影。而我不夠高,一抬頭,對上的便是對幼童來說過於猙獰的面孔。
他們一前一後地走進正在營業中的店家,過長的衣袖有頻率地揮動,我很想逃跑,卻因為出入口過於狹窄,一移動便會與其擦身而過。一時間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顫巍巍地躲在人群後,假裝所有可怕的東西都能被擋在外面,而我留在裡面,與我的恐懼一起。
約莫過了幾分鐘後,圍聚的人群散去,將我凝結的恐懼一點點抽開,所有的光都再次流瀉進來,重新把寫著勇氣的空洞填滿。
嗩吶與鑼鼓的聲音再次大聲響起,我輕皺著眉,只覺得過高的分貝使人感到不適,就像遶境時點燃一串又一串的鞭炮,不管我用手把耳朵摀得再緊再緊,都沒辦法把所有噪音通通趕走。
這是小時候的記憶,我對於民俗活動的恐懼及些許排斥。
十多年過去,我還是那個我,雖然已經不會害怕那些走進店裡的黑白無常,卻成了一個進廟不願意合掌拜拜的女孩。
很多時候我不懂,合十的掌中包裹著的祈願(2),真的能夠因為一次又一次的彎腰而成功嗎?那樣一正一反、發出清脆聲響的筊,能夠把所有事情都翻到正確的位置上嗎?
懷抱著這樣的疑問踏入大學生活,我在那裏遇到了民俗文化相關的課程,老師交雜著國、臺語的聲音,組成一個又一個臺灣的民俗活動,或大或小。
而在這之中,課堂上著墨最久的便是「媽祖進香(3)」了。
相對於其它民俗相關活動,媽祖很特別。有的不知道時間長短,有的一走便是九天八夜,始終不變的,就只有一群緊緊跟隨媽祖腳步前進的虔誠信徒們。
「你們要去看看,那些人為什麼願意走九天八夜,為什麼願意在沒有金錢交易的情況下,還發送大把大把的食物。」
老師的語氣並沒有特別激昂,但堅毅的感情卻直直打進心中。我知道自己從來就不是個虔誠的信徒,卻也還是跟上了進香的步伐,用自己的雙眼雙腳,親自見證老師希望我們所見的。北港媽祖、大甲媽祖、白沙屯媽祖,今年無論哪一個媽祖都是披著雨水在遶境的。尤其在白沙屯媽祖遶境(4)的途中,所有沿路跟隨的信徒們,也都和媽祖淋著同樣的雨前進,每個人穿上五顏六色的雨衣,成為隨香過程中最新潮的護駕團。
在大雨中,一雙雙被反覆滲濕的手不斷向外伸出,遞上食物及飲料慰勞信徒,沒走幾步就能看見一小群人停在路邊,對每個經過的人給出一瓶飲料、一顆水果、甚至是一個暖暖的肉包,口中還不忘順便為大家加油打氣。
那些不斷伸出去的手並不會因此染上任何一絲金錢的銅味,即使如此,卻還是有數不清的人在對數以萬計的陌生人付出關懷與愛心。
冰涼的雨水打在臉上、打在食物上、打在咬著包子的口中,然而每一次咀嚼到的卻又是溫熱無比的暖意。讓人分不清究竟是食物本身的溫度,還是那些遞送食物的人,心中所擁有的熱度。
他們並不會因為這樣而實質上得到些什麼,就像在廟宇中的合十拜拜後,不會因此就完成心中的願望。
但每一個「拜拜(5)」並不只是奢望能夠就此達成心中想做的事情,而是藉由深深地彎腰,增加為了目標繼續往前進的動力。就像進香當中發送難以估計數量及金錢的物資,是那些人將自己所有的虔誠灌注其中,希望每個拿到物資的信徒,都能夠有繼續前進的動力,而信徒繼續前進,為了往媽祖所在的方向,為了往自己心中期望的那個心願所在之處。
連串的鞭炮聲響起,如今除了吵雜之外,似乎也聽見了一些人們在施放鞭炮時,心中呢喃著的小小願望。如同每一次的鑼響、如同每一聲的嗩吶,在那些背後都有許多人感謝的心意,感謝媽祖曾經給予他們勇氣、讓他們不再畏懼。
白沙屯媽祖的鑾轎經過,我輕輕地將掌心貼著掌心,每一寸指節都穩穩地互相對齊併攏,閉上眼,緩緩地將誠意鎔鑄在掌中,祈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