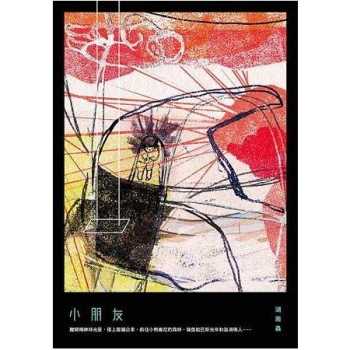神隱少女的飯糰
朋友到日本出差,好心問我要代買什麼嗎?我說:可以的話,請幫我買電影《神隱少女》中,吃了會哭出大滴眼淚的飯糰。
朋友說好。然後又補一句,希望可以買到。
那是一個我會向其傾倒許多心事的朋友,那句「好」的背後是否隱藏了某種對任性的諒解,或只是忙著收拾行李所以放棄無聊的對話,無法確定。反正是個不存在之物,用虛無回應他人實心的善意,還能收到個「不確定」,我也算很幸運了。
但,如果真有,還是很希望能買到啊。我想像它是一份奢侈的禮物,只是尚未有能力送給自己。這樣去冀望未來,是小時候每逢開學要繳學費,必會看見母親很緊張去標會的我,早就熟練的本事。
無論如何,還是被保護著跨過許多關卡,無須犯罪地長大了。其實已不記得回答朋友的當下,是否有不得不的違法念頭,掙扎著像不對時的花朵想要綻放。有時我感覺人生像兩面鏡子包夾,前後都是無止境延伸的自己,在一人獨佔的天地裡,被大量的虛無圍困。
悲傷、孤獨、害怕、惶惑,這些生命裡難以確實掌握的殘像,如骨牌一片撲倒一片,排出浪湧浮世繪。電影裡,小千一家子誤闖靈界湯屋地盤,爸媽偷吃了仙物,變成肥豬。天色暗,小千回頭朝出口奔跑,只見來時路化為汪洋,人也散了形,漸漸變得透明。不是夢,但那麼像夢,小千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以致整個人縮成一團,在世界的邊緣等待清醒——如果不是宮崎駿,這大概已足夠是個結局了。所幸湯屋主人湯婆婆的助手白龍出面相救,讓小千死纏爛打,用名字交換來一份工作,先取得暫時的身分,再來想營救爸媽的辦法……我們終於不用自行想像一個雙親被宰了吃掉的後續。
混亂的一日終於過去,小千像汪洋裡一根枯枝隨流,跟著勞動跟著睡,醒來前夢見白龍透過念力指引方向,循線前去會合,很勉強地收下白龍給的飯糰。
咬下一口,眼淚就大顆大顆地滾了出來,直至嚎啕大哭。眼淚化無形為實體,把抓不著丟不掉的感覺,整理房間似地清空。
一直很喜歡這個安排,充分展示了眼淚的神術作用,就像水庫在超量負載時趕緊洩洪(也難怪眼淚總要「潰堤」而出)。這同時也解釋了何以總有人要用「哭一哭會好過點」來規勸遭逢重大創傷的人,眼淚對著別人或許是武器,朝向自己必定是種藥品。為什麼欲哭無淚比哭天喊地更加絕望呢?就是因為連藥都沒有,只能放棄治療了。或是還不確定該不該哭,能不能哭。像我國中時一次在放學回家路上固定光臨賣燒仙草的攤子,很冷的日子,旁邊站著個約莫小學低年級生的男孩直盯著我看。問他是不是想吃?搖頭,掏出零錢給他,還是搖頭。不知哪來的靈光,我問他:「是不是迷路了?」殊不知那句話就像白龍的飯糰,讓他的雙眼瞬間水患成災。
類似的經驗我也有過。當我還是那迷路男孩的年紀時,曾經在學校遭同學推擠跌倒,狠狠撞上牆壁,鮮血從後腦勺流下來。老師帶我去保健室做簡單處置,同時通知家長來帶去醫院,整個過程,我也只是茫然,知道事情嚴重,但做不出反應。保健室的阿姨還誇我很鎮定、很乖。
但媽媽一來我就大哭了。
也可說它是一種溝通方式吧,像嬰兒在肢體和語言受限的階段,用哭來表達不滿。據說人類天生有兩種最無法忍受的聲音,睡得再沉如鎖緊全身感官,也能找到密道直搗大腦,一是蚊子飛行,二是嬰兒哭聲;前者為保護自己不被叮咬,後者為即時在孩子呼救時警醒,科學的解釋都是保護DNA存續,但人又豈只是大草原上努力從食物鏈中脫逃那樣簡單呢?
所以才很羨慕迷路男孩的眼淚,羨慕以前的自己可以對著媽媽哭泣討拍。那是多麼純真而沒有顧忌的表述啊,人長大就不能那樣哭了。無法再濫用對別人的信任,更無法信任自己。迷路男孩後來收拾好眼淚,拿著我的燒仙草站著慢慢吃,讓我陪著一起等他不知跑到哪去的姊姊。姊姊出現時他又哭了一次,看著他們,心裡有做了好事才有的那種暖。
姊弟倆牽著手回家了。小千也搭上行駛於海面的電車完成冒險,找到營救爸媽的方法,告別了湯屋。
覺得置身世界邊緣不知要往哪去的時候,偶爾我想起他們,就好像真找到了飯糰,大口大口吃下。
松崎海小朋友
看《來自紅花坂》,大概很難不想到李安的《飲食男女》或是枝裕和的《橫山家之味》,兩部真人電影都以熟練流暢簡直藝術的料理動作為序幕,那麼日常,卻像節奏踩得很不經意的舞蹈,是雀躍準備著家常盛宴之畫面,連聲音都是迷人的,爽脆的切菜聲、結實的斬骨聲、悶沉擁擠的滷肉聲、熱烈鼓噪的油炸聲……華麗更勝人生滋味,讓家中很少不開伙的我,光聽那聲音都覺得身體卡路里正快速流失。松崎海煮的早餐,則是在擦亮火柴觸動瓦斯燃起火去煮熟那泡了整夜清水的白米後,就去做其他的事當過場,比方說換過父親照片前杯子裡的水、擺正照片旁邊花瓶裡的花、到庭院裡升起那每天每天想像著死於韓戰的父親還能看見的「航行平安」國際信號旗幟(且不知道就在不遠處的海上,有艘拖船戴著一個後來以為是同父異母的男孩,也每天升起旗幟回應她)……做著這些事的同時,由手嶌葵那招牌的像沒吃飽的聲音唱的〈早餐歌〉,就像是幕後操刀手般幫她煎好了火腿和蛋、煮好了湯,只剩納豆尚未拌好醬油了。雖然都是非常簡單、好像我也做得出來的食物,搭上歌詞有各類食物狀聲和狀態形容的旋律,仍然是大豬小豬落玉盤,一直叫著「餵食時間還沒到嗎!」
當然,和家人一起吃飯的畫面也令人著迷(雖說也是有像《八月心風暴》裡那種一起吃飯絕對胃絞痛腸子打結的一家人啦……)。不知為何,總覺得使用那些老老的器具煮出來的飯一定特別好吃,比方說小時候過年陪媽媽回雲林娘家,總能吃到外婆用磚灶和大鼎做的料很實在大美味蘿蔔糕,真不是妹妹嫁人後向婆婆討教來現學現賣能比的。
長大後某年春節到台南玩「排隊一日遊」,晚上住朋友老家,看見他奶奶也是用廚房磚灶燒熱水給我們洗澡,非常意外那熱水的溫度竟可以維持好久的我,也不管是不是錯覺,從此相信這些成精的廚具都只是生錯地方,要在日本早就上《料理東西軍》了吧!
然而轉念一想,家中的大同電鍋也快有十多年歷史,在成精的路上修練多時了,即使後來我們又添購了微波爐等更新穎方便的設備,它仍然屹立不搖保有重要地位,愈發顯得無法取代,家人也不時拿它來蒸包子饅頭或肉粽,那在鍋緣衝撞著鍋蓋急忙要冒出的白色蒸氣,在寒冷的冬天簡直像幸福本身,飄出看得見的溫暖。每當聽見開關彈起的聲響,幾乎反射性就感到肚子餓,在愛的人事物面前,我們都是帕夫洛夫的制約犬。父親自從因病開始只能吃接近流質的食物後,家中的電鍋便經常備有一大碗母親幫他準備好的粥,隨時處於保溫狀態,方便他餓了就可以吃。父親成天待在家裡沒事做,總愛利用電鍋熱些有的沒的,問我們餓不餓。我搖搖頭,他便說那就放著保溫,餓了自己去吃。下班回到家,最常聽見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電鍋裡有菜,跟他說不餓,他又是同一句「餓了自己去吃」,然後每半小時從房間走出來掀開鍋蓋查看狀況,總要等到我們自動去把飯菜拿出來吃掉或放進冰箱裡,他才安安靜靜把不知原本放在哪裡自己的一碗粥放回電鍋裡,壓下開關,又慢步走回房間。
我始終記得多年前一個晚上,父親說出門買個東西,結果一去就是幾個小時沒回來。那天晚上我待在房裡一直睡不著,看書無法集中精神,音樂也不敢聽,只是把燈亮著胡亂逛一些不知所終的網站。
那時才發現,就算要出門找他,其實也完全不知道他會去哪裡呀。
耳朵一直注意著門外的動靜,不知道幾點的時候終於聽見他開門又關門的聲音,趕緊熄了燈,沉沉睡去。那感覺,就好像聽見電鍋開關彈起的聲音,一點都不華麗,但非常令人安心。
濱崎小朋友
在眾多更有個性的角色裡,濱崎大概算不上《櫻桃小丸子》裡值得一提的角色。雖然那長形的臉、鋸齒狀的牙也算頗具辨識度,偶爾也能講出令眾人額上三條線的(其實很爆笑)發言,但那畢竟是個臥虎藏龍的班級,有講話總是「噗來噗去」的豬太郎、腸胃功能差得呼吸都會肚子痛的山根、卑鄙得甚至擁有了自己主題曲〈卑鄙之歌〉的藤木、喜歡用「總而言之」亂下結論的萬年班長丸尾……很遺憾的,濱崎真的只能是配角中的配角。
事實上,在總共播出超過一千集,之後又拍了四部長篇電影的所有劇情中,真的把他放在中間位置去演出的,恐怕只有一次。那是小丸子一群人去動物園參加寫生比賽,濱崎因為吃梅子飯糰時不小心把梅汁滴在畫紙上而崩潰,不得不改畫鼻子紅紅的馴鹿,結果還誤打誤撞得了獎,連評審都騙倒了,且說整張畫表現最優的地方就是顏色用得很巧妙的馴鹿鼻子,讓畫完北極熊後發現根本只是三個黑點的小丸子,額頭上的線又更多了。但關於濱崎,我有一個更莫名的記憶。詳細的時間已忘記,只記得是某個生病請假的日子,我在房裡賴著不起床,聽見那時應該不知失業了沒的父親在客廳看卡通重播,有一幕濱崎的臉變成四根小黃瓜的畫面,父親看到大笑出聲,我在房間裡忽然覺得很溫暖,因為那正是我前天晚上看到笑出來的橋段,覺得父親竟和我有一樣的笑點啊。
那時的我,應該還是有點害怕繼父的。其實,一直都知道他對我和妹妹很好,但就仍是個不知從哪冒出來的陌生人。記得他剛成為家庭成員時,每次出門工作,我都會一直問他什麼時候回來,好像很捨不得,其實是在確認自己可以有幾天不用見到他。他每次回來都會帶禮物,我也很喜歡那些禮物,像是可以折成一隻企鵝和一隻鴨子的棉被什麼的,或是一截真正的、自己鋸一小縫的竹節存錢筒,但心裡還是忍不住想,如果只有禮物回來該有多好啊。
如今回憶此事,才知道有多傻。小孩子怎麼可能騙過大人呢?我們畢竟不是配角中的配角、不被真心注視的濱崎,演技也不渾然天成像一滴意外的梅汁轉世成馴鹿的鼻子,想來是破綻百出的作態和虛偽吧。但父親也不趕,就是慢慢來,很清楚親情是急不得的。另一個也很溫暖的記憶是《哈利波特》第四集出版時,他看新聞一直報,報不停,報不用錢,就問我:「你有看嗎?」其實那時我已經不很期待了,但就是隨口敷衍他:「有啊。」結果他就默默出門買了一本,裝在紅白塑膠袋裡掛在我房門的門把上。
很多記憶就這樣連結起來。在他數度進出醫院,且在醫院時間一次次比在家時間長的那幾年,《哈利波特》最後一集出版了,記得《蘋果日報》還做了整版上下顛倒的版面公布結局,母親轉來轉去問:「怎麼會出這種錯?」連躺在病床上的父親都忍不住好奇了:「這應該是印錯了吧……可是上面又是對的……」我只好耐心解釋何謂「防雷」,當然他們是一點都不在意也沒興趣就是了。也有些記憶單獨存在,強壯得光是想起就能將人擊倒,倒數讀秒了還是一動也不能動,徹底死絕。那是他腳受傷不是很好走路的時候,一次在家裡發脾氣,說為什麼垃圾車來了還不去倒垃圾呢?我正在看電視,且記得垃圾不多,就略微不耐地說:「不是昨天才倒過嗎?」但他正值自尊心不容挑戰的初期廢人階段,一下子就在怒火底下添了無數薪柴,氣呼呼地自己把垃圾袋綁一綁就一跛一跛地出門了。聽垃圾車唱歌的聲音是絕對來不及的,但我還是坐在沙發上冷眼看著他出門,從五樓一階一階地走下樓倒垃圾。
肯定要有報應的吧?經常想到這件事,就是我的報應。
不存在之物
任意門——
最渴望擁有任意門的時候,或許是愛上誰的時候。
當然不是為了開門就能見到想念的臉,那頂多成為神出鬼沒的跟蹤狂,結果很可能是被報警處理——所謂浪漫,永遠必須兩造同意,彷彿星座運勢冥冥中在天上閃爍信號編寫劇本,偏不讓誰和你對戲的話,就只有自己欣賞美麗的潛台詞了。只有自己,日日,在房間排練那找不到舞台演出的激情,想像的天使被想像的惡魔嘲笑、擊垮,現實再大方也給不起我要的幸福。
就算,就算擁有那樣一方蟲洞,可以把世界像紙折來折去、人身如鉛筆穿孔而過,即抵達遙遠的銀河或星雲。最大材小用的想像:假若扭開門把就到公司,不知能省下多少通勤時間,好好休息養肝?或者也不用上班了,直接開門做買賣,環遊世界跑單幫,不用機票無須託運,無疑是「一門」好生意。很熱的時候,開一道北極的風景招攬冷氣;梅雨下得人如喪屍走陰溼路,就到南國借陽光。無法把天殺的人生就地掩埋,至少可以把人身棄置到天高地遠的地方求個清淨。痛苦與救贖都自給自足,而且環保。
然而愛情,就偏要來亂。愛情很麻煩,什麼事沾到愛情都要質變,像針刺破真空包裝,密合的自私遭到破壞,紮實的闊綽摻入微塵。它是烏賊遇險時噴發墨水,只是都噴在腦子裡,對自己施展障眼法。它像病毒,侵犯身體也篡改程式碼,趁病植入諸多懷疑和自棄的迴圈,一覺醒來變成一個最善良的人。倘若擁有任意門,我會開一注獨得的樂透號碼般,去任何對方想去的地方。東京、倫敦、紐約、巴黎,世界四大城都在一日生活圈內,我們的生活圈。我會扛著門像扛著十字架,很重很重快要被壓垮,也為了誰趕時間而奔跑。我們從忠孝東路直達雪梨,從敦南誠品跨入荷蘭的天堂書店。偶爾不想遠行,就上午花蓮下午台南,晚上逛過墾丁大街,打開門,假裝我的房間就是民宿,整晚不閉戶,讓潮聲為美夢襯底,不管對方夢見誰,我都會在沙灘上巡守一整夜。
我會是一個最精明的賊,去銀行偷錢,去美術館偷雕像,去博物館偷一根恐龍的肋骨。我會布置一個房間,有白宮的沙發、青瓦台的盆栽、西斯廷禮拜堂的壁畫。我會在裡頭,很認真地祈禱……
沒有人能將我定罪,唯一能通緝我的只有我的心。全世界的風景都為我辯護,像我為誰製造無限的不在場證明。
想起上回一起吃飯,氣氛有點尷尬,我只好一直一直找話題,淘金似地挖真心話。明明知道是大忌,還是忍不住誠實了,弄得最後只剩禮貌的微笑。
儘管如此,我也沒有想逃的念頭,任由心將我逮捕歸案,伸手把門關起來。
門外的自由人都不懂,門裡就有最美的荒地。
朋友到日本出差,好心問我要代買什麼嗎?我說:可以的話,請幫我買電影《神隱少女》中,吃了會哭出大滴眼淚的飯糰。
朋友說好。然後又補一句,希望可以買到。
那是一個我會向其傾倒許多心事的朋友,那句「好」的背後是否隱藏了某種對任性的諒解,或只是忙著收拾行李所以放棄無聊的對話,無法確定。反正是個不存在之物,用虛無回應他人實心的善意,還能收到個「不確定」,我也算很幸運了。
但,如果真有,還是很希望能買到啊。我想像它是一份奢侈的禮物,只是尚未有能力送給自己。這樣去冀望未來,是小時候每逢開學要繳學費,必會看見母親很緊張去標會的我,早就熟練的本事。
無論如何,還是被保護著跨過許多關卡,無須犯罪地長大了。其實已不記得回答朋友的當下,是否有不得不的違法念頭,掙扎著像不對時的花朵想要綻放。有時我感覺人生像兩面鏡子包夾,前後都是無止境延伸的自己,在一人獨佔的天地裡,被大量的虛無圍困。
悲傷、孤獨、害怕、惶惑,這些生命裡難以確實掌握的殘像,如骨牌一片撲倒一片,排出浪湧浮世繪。電影裡,小千一家子誤闖靈界湯屋地盤,爸媽偷吃了仙物,變成肥豬。天色暗,小千回頭朝出口奔跑,只見來時路化為汪洋,人也散了形,漸漸變得透明。不是夢,但那麼像夢,小千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以致整個人縮成一團,在世界的邊緣等待清醒——如果不是宮崎駿,這大概已足夠是個結局了。所幸湯屋主人湯婆婆的助手白龍出面相救,讓小千死纏爛打,用名字交換來一份工作,先取得暫時的身分,再來想營救爸媽的辦法……我們終於不用自行想像一個雙親被宰了吃掉的後續。
混亂的一日終於過去,小千像汪洋裡一根枯枝隨流,跟著勞動跟著睡,醒來前夢見白龍透過念力指引方向,循線前去會合,很勉強地收下白龍給的飯糰。
咬下一口,眼淚就大顆大顆地滾了出來,直至嚎啕大哭。眼淚化無形為實體,把抓不著丟不掉的感覺,整理房間似地清空。
一直很喜歡這個安排,充分展示了眼淚的神術作用,就像水庫在超量負載時趕緊洩洪(也難怪眼淚總要「潰堤」而出)。這同時也解釋了何以總有人要用「哭一哭會好過點」來規勸遭逢重大創傷的人,眼淚對著別人或許是武器,朝向自己必定是種藥品。為什麼欲哭無淚比哭天喊地更加絕望呢?就是因為連藥都沒有,只能放棄治療了。或是還不確定該不該哭,能不能哭。像我國中時一次在放學回家路上固定光臨賣燒仙草的攤子,很冷的日子,旁邊站著個約莫小學低年級生的男孩直盯著我看。問他是不是想吃?搖頭,掏出零錢給他,還是搖頭。不知哪來的靈光,我問他:「是不是迷路了?」殊不知那句話就像白龍的飯糰,讓他的雙眼瞬間水患成災。
類似的經驗我也有過。當我還是那迷路男孩的年紀時,曾經在學校遭同學推擠跌倒,狠狠撞上牆壁,鮮血從後腦勺流下來。老師帶我去保健室做簡單處置,同時通知家長來帶去醫院,整個過程,我也只是茫然,知道事情嚴重,但做不出反應。保健室的阿姨還誇我很鎮定、很乖。
但媽媽一來我就大哭了。
也可說它是一種溝通方式吧,像嬰兒在肢體和語言受限的階段,用哭來表達不滿。據說人類天生有兩種最無法忍受的聲音,睡得再沉如鎖緊全身感官,也能找到密道直搗大腦,一是蚊子飛行,二是嬰兒哭聲;前者為保護自己不被叮咬,後者為即時在孩子呼救時警醒,科學的解釋都是保護DNA存續,但人又豈只是大草原上努力從食物鏈中脫逃那樣簡單呢?
所以才很羨慕迷路男孩的眼淚,羨慕以前的自己可以對著媽媽哭泣討拍。那是多麼純真而沒有顧忌的表述啊,人長大就不能那樣哭了。無法再濫用對別人的信任,更無法信任自己。迷路男孩後來收拾好眼淚,拿著我的燒仙草站著慢慢吃,讓我陪著一起等他不知跑到哪去的姊姊。姊姊出現時他又哭了一次,看著他們,心裡有做了好事才有的那種暖。
姊弟倆牽著手回家了。小千也搭上行駛於海面的電車完成冒險,找到營救爸媽的方法,告別了湯屋。
覺得置身世界邊緣不知要往哪去的時候,偶爾我想起他們,就好像真找到了飯糰,大口大口吃下。
松崎海小朋友
看《來自紅花坂》,大概很難不想到李安的《飲食男女》或是枝裕和的《橫山家之味》,兩部真人電影都以熟練流暢簡直藝術的料理動作為序幕,那麼日常,卻像節奏踩得很不經意的舞蹈,是雀躍準備著家常盛宴之畫面,連聲音都是迷人的,爽脆的切菜聲、結實的斬骨聲、悶沉擁擠的滷肉聲、熱烈鼓噪的油炸聲……華麗更勝人生滋味,讓家中很少不開伙的我,光聽那聲音都覺得身體卡路里正快速流失。松崎海煮的早餐,則是在擦亮火柴觸動瓦斯燃起火去煮熟那泡了整夜清水的白米後,就去做其他的事當過場,比方說換過父親照片前杯子裡的水、擺正照片旁邊花瓶裡的花、到庭院裡升起那每天每天想像著死於韓戰的父親還能看見的「航行平安」國際信號旗幟(且不知道就在不遠處的海上,有艘拖船戴著一個後來以為是同父異母的男孩,也每天升起旗幟回應她)……做著這些事的同時,由手嶌葵那招牌的像沒吃飽的聲音唱的〈早餐歌〉,就像是幕後操刀手般幫她煎好了火腿和蛋、煮好了湯,只剩納豆尚未拌好醬油了。雖然都是非常簡單、好像我也做得出來的食物,搭上歌詞有各類食物狀聲和狀態形容的旋律,仍然是大豬小豬落玉盤,一直叫著「餵食時間還沒到嗎!」
當然,和家人一起吃飯的畫面也令人著迷(雖說也是有像《八月心風暴》裡那種一起吃飯絕對胃絞痛腸子打結的一家人啦……)。不知為何,總覺得使用那些老老的器具煮出來的飯一定特別好吃,比方說小時候過年陪媽媽回雲林娘家,總能吃到外婆用磚灶和大鼎做的料很實在大美味蘿蔔糕,真不是妹妹嫁人後向婆婆討教來現學現賣能比的。
長大後某年春節到台南玩「排隊一日遊」,晚上住朋友老家,看見他奶奶也是用廚房磚灶燒熱水給我們洗澡,非常意外那熱水的溫度竟可以維持好久的我,也不管是不是錯覺,從此相信這些成精的廚具都只是生錯地方,要在日本早就上《料理東西軍》了吧!
然而轉念一想,家中的大同電鍋也快有十多年歷史,在成精的路上修練多時了,即使後來我們又添購了微波爐等更新穎方便的設備,它仍然屹立不搖保有重要地位,愈發顯得無法取代,家人也不時拿它來蒸包子饅頭或肉粽,那在鍋緣衝撞著鍋蓋急忙要冒出的白色蒸氣,在寒冷的冬天簡直像幸福本身,飄出看得見的溫暖。每當聽見開關彈起的聲響,幾乎反射性就感到肚子餓,在愛的人事物面前,我們都是帕夫洛夫的制約犬。父親自從因病開始只能吃接近流質的食物後,家中的電鍋便經常備有一大碗母親幫他準備好的粥,隨時處於保溫狀態,方便他餓了就可以吃。父親成天待在家裡沒事做,總愛利用電鍋熱些有的沒的,問我們餓不餓。我搖搖頭,他便說那就放著保溫,餓了自己去吃。下班回到家,最常聽見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電鍋裡有菜,跟他說不餓,他又是同一句「餓了自己去吃」,然後每半小時從房間走出來掀開鍋蓋查看狀況,總要等到我們自動去把飯菜拿出來吃掉或放進冰箱裡,他才安安靜靜把不知原本放在哪裡自己的一碗粥放回電鍋裡,壓下開關,又慢步走回房間。
我始終記得多年前一個晚上,父親說出門買個東西,結果一去就是幾個小時沒回來。那天晚上我待在房裡一直睡不著,看書無法集中精神,音樂也不敢聽,只是把燈亮著胡亂逛一些不知所終的網站。
那時才發現,就算要出門找他,其實也完全不知道他會去哪裡呀。
耳朵一直注意著門外的動靜,不知道幾點的時候終於聽見他開門又關門的聲音,趕緊熄了燈,沉沉睡去。那感覺,就好像聽見電鍋開關彈起的聲音,一點都不華麗,但非常令人安心。
濱崎小朋友
在眾多更有個性的角色裡,濱崎大概算不上《櫻桃小丸子》裡值得一提的角色。雖然那長形的臉、鋸齒狀的牙也算頗具辨識度,偶爾也能講出令眾人額上三條線的(其實很爆笑)發言,但那畢竟是個臥虎藏龍的班級,有講話總是「噗來噗去」的豬太郎、腸胃功能差得呼吸都會肚子痛的山根、卑鄙得甚至擁有了自己主題曲〈卑鄙之歌〉的藤木、喜歡用「總而言之」亂下結論的萬年班長丸尾……很遺憾的,濱崎真的只能是配角中的配角。
事實上,在總共播出超過一千集,之後又拍了四部長篇電影的所有劇情中,真的把他放在中間位置去演出的,恐怕只有一次。那是小丸子一群人去動物園參加寫生比賽,濱崎因為吃梅子飯糰時不小心把梅汁滴在畫紙上而崩潰,不得不改畫鼻子紅紅的馴鹿,結果還誤打誤撞得了獎,連評審都騙倒了,且說整張畫表現最優的地方就是顏色用得很巧妙的馴鹿鼻子,讓畫完北極熊後發現根本只是三個黑點的小丸子,額頭上的線又更多了。但關於濱崎,我有一個更莫名的記憶。詳細的時間已忘記,只記得是某個生病請假的日子,我在房裡賴著不起床,聽見那時應該不知失業了沒的父親在客廳看卡通重播,有一幕濱崎的臉變成四根小黃瓜的畫面,父親看到大笑出聲,我在房間裡忽然覺得很溫暖,因為那正是我前天晚上看到笑出來的橋段,覺得父親竟和我有一樣的笑點啊。
那時的我,應該還是有點害怕繼父的。其實,一直都知道他對我和妹妹很好,但就仍是個不知從哪冒出來的陌生人。記得他剛成為家庭成員時,每次出門工作,我都會一直問他什麼時候回來,好像很捨不得,其實是在確認自己可以有幾天不用見到他。他每次回來都會帶禮物,我也很喜歡那些禮物,像是可以折成一隻企鵝和一隻鴨子的棉被什麼的,或是一截真正的、自己鋸一小縫的竹節存錢筒,但心裡還是忍不住想,如果只有禮物回來該有多好啊。
如今回憶此事,才知道有多傻。小孩子怎麼可能騙過大人呢?我們畢竟不是配角中的配角、不被真心注視的濱崎,演技也不渾然天成像一滴意外的梅汁轉世成馴鹿的鼻子,想來是破綻百出的作態和虛偽吧。但父親也不趕,就是慢慢來,很清楚親情是急不得的。另一個也很溫暖的記憶是《哈利波特》第四集出版時,他看新聞一直報,報不停,報不用錢,就問我:「你有看嗎?」其實那時我已經不很期待了,但就是隨口敷衍他:「有啊。」結果他就默默出門買了一本,裝在紅白塑膠袋裡掛在我房門的門把上。
很多記憶就這樣連結起來。在他數度進出醫院,且在醫院時間一次次比在家時間長的那幾年,《哈利波特》最後一集出版了,記得《蘋果日報》還做了整版上下顛倒的版面公布結局,母親轉來轉去問:「怎麼會出這種錯?」連躺在病床上的父親都忍不住好奇了:「這應該是印錯了吧……可是上面又是對的……」我只好耐心解釋何謂「防雷」,當然他們是一點都不在意也沒興趣就是了。也有些記憶單獨存在,強壯得光是想起就能將人擊倒,倒數讀秒了還是一動也不能動,徹底死絕。那是他腳受傷不是很好走路的時候,一次在家裡發脾氣,說為什麼垃圾車來了還不去倒垃圾呢?我正在看電視,且記得垃圾不多,就略微不耐地說:「不是昨天才倒過嗎?」但他正值自尊心不容挑戰的初期廢人階段,一下子就在怒火底下添了無數薪柴,氣呼呼地自己把垃圾袋綁一綁就一跛一跛地出門了。聽垃圾車唱歌的聲音是絕對來不及的,但我還是坐在沙發上冷眼看著他出門,從五樓一階一階地走下樓倒垃圾。
肯定要有報應的吧?經常想到這件事,就是我的報應。
不存在之物
任意門——
最渴望擁有任意門的時候,或許是愛上誰的時候。
當然不是為了開門就能見到想念的臉,那頂多成為神出鬼沒的跟蹤狂,結果很可能是被報警處理——所謂浪漫,永遠必須兩造同意,彷彿星座運勢冥冥中在天上閃爍信號編寫劇本,偏不讓誰和你對戲的話,就只有自己欣賞美麗的潛台詞了。只有自己,日日,在房間排練那找不到舞台演出的激情,想像的天使被想像的惡魔嘲笑、擊垮,現實再大方也給不起我要的幸福。
就算,就算擁有那樣一方蟲洞,可以把世界像紙折來折去、人身如鉛筆穿孔而過,即抵達遙遠的銀河或星雲。最大材小用的想像:假若扭開門把就到公司,不知能省下多少通勤時間,好好休息養肝?或者也不用上班了,直接開門做買賣,環遊世界跑單幫,不用機票無須託運,無疑是「一門」好生意。很熱的時候,開一道北極的風景招攬冷氣;梅雨下得人如喪屍走陰溼路,就到南國借陽光。無法把天殺的人生就地掩埋,至少可以把人身棄置到天高地遠的地方求個清淨。痛苦與救贖都自給自足,而且環保。
然而愛情,就偏要來亂。愛情很麻煩,什麼事沾到愛情都要質變,像針刺破真空包裝,密合的自私遭到破壞,紮實的闊綽摻入微塵。它是烏賊遇險時噴發墨水,只是都噴在腦子裡,對自己施展障眼法。它像病毒,侵犯身體也篡改程式碼,趁病植入諸多懷疑和自棄的迴圈,一覺醒來變成一個最善良的人。倘若擁有任意門,我會開一注獨得的樂透號碼般,去任何對方想去的地方。東京、倫敦、紐約、巴黎,世界四大城都在一日生活圈內,我們的生活圈。我會扛著門像扛著十字架,很重很重快要被壓垮,也為了誰趕時間而奔跑。我們從忠孝東路直達雪梨,從敦南誠品跨入荷蘭的天堂書店。偶爾不想遠行,就上午花蓮下午台南,晚上逛過墾丁大街,打開門,假裝我的房間就是民宿,整晚不閉戶,讓潮聲為美夢襯底,不管對方夢見誰,我都會在沙灘上巡守一整夜。
我會是一個最精明的賊,去銀行偷錢,去美術館偷雕像,去博物館偷一根恐龍的肋骨。我會布置一個房間,有白宮的沙發、青瓦台的盆栽、西斯廷禮拜堂的壁畫。我會在裡頭,很認真地祈禱……
沒有人能將我定罪,唯一能通緝我的只有我的心。全世界的風景都為我辯護,像我為誰製造無限的不在場證明。
想起上回一起吃飯,氣氛有點尷尬,我只好一直一直找話題,淘金似地挖真心話。明明知道是大忌,還是忍不住誠實了,弄得最後只剩禮貌的微笑。
儘管如此,我也沒有想逃的念頭,任由心將我逮捕歸案,伸手把門關起來。
門外的自由人都不懂,門裡就有最美的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