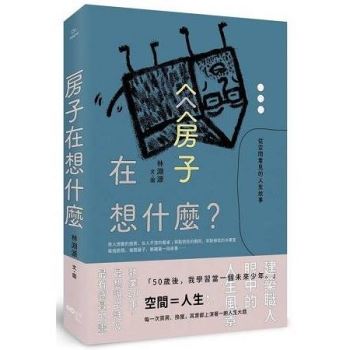男人想要的廚房
落筆之前,恐怕我得先問問:「男人到底想不想要廚房?」
這不僅是心理學的問題,可能也是生物學與進化學的問題,弄不好還會變成存在哲學的問題了。
我知道這麼說聽起來有點兒怪,何以我要小題大作。很多人以為廚房是女人的事,大部分男人是不需要管的。可是我常在想,有沒有可能是男人誤以為自己不那麼需要廚房。
得道的高僧(也是男人)說過這麼一句話:「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這句話落在男人與廚房之間就有意思了。試想如果男人不僅需要廚房,而且想要廚房比需要還多,這個世界會不會變得更可愛些,更療癒些呢!
我想說一個故事,關於一個男人與廚房的愛恨癡愁。
老友L男,外商公司的高級主管,名校畢業的管理碩士。幾年前當他還是單身時就在城市二十樓的上空擁有一戶自己的「質男部屋」。房子共20坪大的面積全部打通,一個房間與一間浴室,一個男人與一隻大狗。廚房對他而言只是牆面的一個符號,在半夜突然飢餓需要煮碗泡麵時,那符號才會發生生物學的意義。其實這位雅痞不是不愛美食,而是享用料理美饌時的L男總是在那個叫作「家」以外的「他方」,一家又一家高檔的餐廳。烹調的概念與那個男人的身體接觸僅於味蕾食道與內臟了,也難怪他會與廚房演化出那種疏離的物與物之關係。而那個房子的大小也量身訂製般的剛剛好讓1.5個人舒服居住,那個0.5代表一種非穩定交往的情感關係,其實也就是他更迭不定的女伴們。
直到40歲那一年,L男說他需要一個廚房了,因為終於遇到一個懂他的女人,男人浪蕩的靈魂與漂泊的腸胃都想要定下來了。所以他換了一間30坪的房子,一個房間一間浴室,一個餐廳與開放式廚房,跟半個不需要電視機的起居間,另外一半留給了植物與寵物。
你可以想像這個房子的幸福感多到像奶昔一般溢出來了,廚房裡日日烹調的不僅是食物,更多的是愛情。空間跟身體的關係也不再只是物理性的尺度感,更多的是感官性的親密感。對L男而言,廚房非但不再只是個符號,而且簡直從名詞變成一個充滿表情的動詞了。對於男人類來講,或許這也是一種空間認知上的演化吧!
三年後,L男離婚了。(這裡不去解釋為了甚麼原因,反正跟柴米油鹽沒關係也好像有關係。)回到獨居的他沒有再換房子,有意思的是,他把唯一的臥房拆掉,將原本的廚房延伸成為兩倍大。兩台冰箱兩座爐具,兩張島台兩盞吊燈;剩下一半的肢體動作揮舞著兩倍的兩次方的寂寞,他要讓自己睡在親密的寂寞裡。
那個懂他的女人離開以後,他似乎更加耽溺這間廚房了。就是「寂寞」這東西讓「耽溺」從嫩芽長成大樹,男人在重新單獨面對這個親密空間時開始學習從舌尖到腳趾尖跟自己好好相處,而最好的場所正是廚房,這是L男步入中年後賴以安身的存在哲學。
前陣子得知L男再婚了,某天我在臉書上收到他傳來的短訊:「哥們,我終於知道理想廚房的條件是啥了!」
「是啥?」我問
「不告訴你。」
…………………………………………………
「男人也許更想要的是廚房的主人。」
建築人
建築人的款式有許多不同路數,每種款式都有其獨到的魅力與特有的悲催。
我的朋友老徐,長得像鼎鼎大名的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就是設計了北京中央電視台總部大樓的建築大明星,庫哈斯先生有著細細長長的身材跟一身的黑衣服,老徐也是這個模樣。老徐抽菸時喜歡把香菸夾在中指與無名指之間,他說這種焚燒的儀式要安排在四支長指之間比較像壁爐烈火裡獨處的乾柴,既孤獨又快活,不曉得庫哈斯先生是否也如此。老徐長得老,三十年前就是現在的模樣了,屬於滄桑先行的建築人。聽著他在聊著對於建築的熱情與抱負時的那股苦行勁道,簡直就像是嘴裡含著快蛀光的牙在吃巧克力一般,微痛並甜著。每次見到老徐時,總會覺得眼前這位黑衣巫師好像幾個世紀沒睡似的,黑眼圈早已像年輪一般覆蓋其歷經風霜的臉頰,顯出疲累的身形卻可以直挺著軀幹談論他的作品。一串又一串如四射火光般的囈語在我眼前迸開,一下子是理性的白色,隨即又浪漫如梵谷的向日葵,然後瞬間碎裂成葛飾北齋畫裡的滔天浪花。炯炯的眼神好像要把城市裡被無聊美學漫天撒下的大網子給畫破,每次看他仰著頭直視上方擋住陽光那棟巨大樓房時的蒼白表情,就會讓我想到庫哈斯先生有一張相片,相片裡的他也仰了頭朝上方直視,但讓他直視的卻是來自屋頂缺口透進來的那道光。我猜可能是這種四十五度仰角的身體姿勢特別適合建築人,從西方的柯比意、萊特到東方的安藤忠雄與伊東豊雄都曾以這個姿勢在跟他們的光交談,那些身影被留在一張張建築史頁裡的黑白相片,各自英雄也各自不朽著。
老徐自小學習古典鋼琴,原本應該是一位在演奏台上英姿煥發的白馬王子,可自從進了那個教他要勇敢做自己的建築學院後,白馬王子就被徹底解構再從反骨裡長出一個全新的浪子。他開始喜歡有毛邊的音樂,也讓自己原本被裁剪得一絲不苟的性格長出毛邊,柔軟如一張張被隨性撕開的棉紙,也鏗鏘如落在銀盤上的鋼珠。有時流洩如瀑、有時像冰山,在他身上我見到不斷進化的流動生命,也感受到那種在探究設計可能性時,如石像一般的堅毅精神。張牙舞爪的音符在這個建築怪客的手裡,也早已超出了樂譜上那五條只能平行的直線,我總能在他的建築作品裡,聽見幽微晦澀的樂音;也在他不從眾的琴聲裡,看見不斷崩塌又不斷拔起的高塔。
十五年前老徐去了中國發展,據說是受到一股母體般的巨大召喚,他說那裡土地尺度的大美讓他有了更高的理想與情懷。眼看對岸的建築動能在這幾年蓬勃發展,早已成了國際大師仙人們比劃身手的閃亮舞台,讓我對我的石像老友抱以更深期許。多年不見的他,直到去年我到上海出差時才有機會再得聚首。這才知道堅持不離開建築領域的老徐後來熱情不減地轉進了土地的規劃與開發,現已成了城市裡的地產大亨。再次見面的那晚,他開了一瓶十萬元的紅酒與一支跟「切格瓦拉」同樣大器如砲管的雪茄,與我分享了另外一種建築人的碩大情懷。只見雪茄被夾在他一如往常的中指與無名指之間,隔著裊裊燃起的煙霧,我看到巨柴後方變胖了的「庫哈斯先生」,一時之間倒有那麼幾分「川普」的錯覺。
…………………………………………………
「當你離開你一直以為扮演得很好的那個角色時,才終於讓你自己與那個角色都活了過來,並且深愛彼此。」
落筆之前,恐怕我得先問問:「男人到底想不想要廚房?」
這不僅是心理學的問題,可能也是生物學與進化學的問題,弄不好還會變成存在哲學的問題了。
我知道這麼說聽起來有點兒怪,何以我要小題大作。很多人以為廚房是女人的事,大部分男人是不需要管的。可是我常在想,有沒有可能是男人誤以為自己不那麼需要廚房。
得道的高僧(也是男人)說過這麼一句話:「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這句話落在男人與廚房之間就有意思了。試想如果男人不僅需要廚房,而且想要廚房比需要還多,這個世界會不會變得更可愛些,更療癒些呢!
我想說一個故事,關於一個男人與廚房的愛恨癡愁。
老友L男,外商公司的高級主管,名校畢業的管理碩士。幾年前當他還是單身時就在城市二十樓的上空擁有一戶自己的「質男部屋」。房子共20坪大的面積全部打通,一個房間與一間浴室,一個男人與一隻大狗。廚房對他而言只是牆面的一個符號,在半夜突然飢餓需要煮碗泡麵時,那符號才會發生生物學的意義。其實這位雅痞不是不愛美食,而是享用料理美饌時的L男總是在那個叫作「家」以外的「他方」,一家又一家高檔的餐廳。烹調的概念與那個男人的身體接觸僅於味蕾食道與內臟了,也難怪他會與廚房演化出那種疏離的物與物之關係。而那個房子的大小也量身訂製般的剛剛好讓1.5個人舒服居住,那個0.5代表一種非穩定交往的情感關係,其實也就是他更迭不定的女伴們。
直到40歲那一年,L男說他需要一個廚房了,因為終於遇到一個懂他的女人,男人浪蕩的靈魂與漂泊的腸胃都想要定下來了。所以他換了一間30坪的房子,一個房間一間浴室,一個餐廳與開放式廚房,跟半個不需要電視機的起居間,另外一半留給了植物與寵物。
你可以想像這個房子的幸福感多到像奶昔一般溢出來了,廚房裡日日烹調的不僅是食物,更多的是愛情。空間跟身體的關係也不再只是物理性的尺度感,更多的是感官性的親密感。對L男而言,廚房非但不再只是個符號,而且簡直從名詞變成一個充滿表情的動詞了。對於男人類來講,或許這也是一種空間認知上的演化吧!
三年後,L男離婚了。(這裡不去解釋為了甚麼原因,反正跟柴米油鹽沒關係也好像有關係。)回到獨居的他沒有再換房子,有意思的是,他把唯一的臥房拆掉,將原本的廚房延伸成為兩倍大。兩台冰箱兩座爐具,兩張島台兩盞吊燈;剩下一半的肢體動作揮舞著兩倍的兩次方的寂寞,他要讓自己睡在親密的寂寞裡。
那個懂他的女人離開以後,他似乎更加耽溺這間廚房了。就是「寂寞」這東西讓「耽溺」從嫩芽長成大樹,男人在重新單獨面對這個親密空間時開始學習從舌尖到腳趾尖跟自己好好相處,而最好的場所正是廚房,這是L男步入中年後賴以安身的存在哲學。
前陣子得知L男再婚了,某天我在臉書上收到他傳來的短訊:「哥們,我終於知道理想廚房的條件是啥了!」
「是啥?」我問
「不告訴你。」
…………………………………………………
「男人也許更想要的是廚房的主人。」
建築人
建築人的款式有許多不同路數,每種款式都有其獨到的魅力與特有的悲催。
我的朋友老徐,長得像鼎鼎大名的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就是設計了北京中央電視台總部大樓的建築大明星,庫哈斯先生有著細細長長的身材跟一身的黑衣服,老徐也是這個模樣。老徐抽菸時喜歡把香菸夾在中指與無名指之間,他說這種焚燒的儀式要安排在四支長指之間比較像壁爐烈火裡獨處的乾柴,既孤獨又快活,不曉得庫哈斯先生是否也如此。老徐長得老,三十年前就是現在的模樣了,屬於滄桑先行的建築人。聽著他在聊著對於建築的熱情與抱負時的那股苦行勁道,簡直就像是嘴裡含著快蛀光的牙在吃巧克力一般,微痛並甜著。每次見到老徐時,總會覺得眼前這位黑衣巫師好像幾個世紀沒睡似的,黑眼圈早已像年輪一般覆蓋其歷經風霜的臉頰,顯出疲累的身形卻可以直挺著軀幹談論他的作品。一串又一串如四射火光般的囈語在我眼前迸開,一下子是理性的白色,隨即又浪漫如梵谷的向日葵,然後瞬間碎裂成葛飾北齋畫裡的滔天浪花。炯炯的眼神好像要把城市裡被無聊美學漫天撒下的大網子給畫破,每次看他仰著頭直視上方擋住陽光那棟巨大樓房時的蒼白表情,就會讓我想到庫哈斯先生有一張相片,相片裡的他也仰了頭朝上方直視,但讓他直視的卻是來自屋頂缺口透進來的那道光。我猜可能是這種四十五度仰角的身體姿勢特別適合建築人,從西方的柯比意、萊特到東方的安藤忠雄與伊東豊雄都曾以這個姿勢在跟他們的光交談,那些身影被留在一張張建築史頁裡的黑白相片,各自英雄也各自不朽著。
老徐自小學習古典鋼琴,原本應該是一位在演奏台上英姿煥發的白馬王子,可自從進了那個教他要勇敢做自己的建築學院後,白馬王子就被徹底解構再從反骨裡長出一個全新的浪子。他開始喜歡有毛邊的音樂,也讓自己原本被裁剪得一絲不苟的性格長出毛邊,柔軟如一張張被隨性撕開的棉紙,也鏗鏘如落在銀盤上的鋼珠。有時流洩如瀑、有時像冰山,在他身上我見到不斷進化的流動生命,也感受到那種在探究設計可能性時,如石像一般的堅毅精神。張牙舞爪的音符在這個建築怪客的手裡,也早已超出了樂譜上那五條只能平行的直線,我總能在他的建築作品裡,聽見幽微晦澀的樂音;也在他不從眾的琴聲裡,看見不斷崩塌又不斷拔起的高塔。
十五年前老徐去了中國發展,據說是受到一股母體般的巨大召喚,他說那裡土地尺度的大美讓他有了更高的理想與情懷。眼看對岸的建築動能在這幾年蓬勃發展,早已成了國際大師仙人們比劃身手的閃亮舞台,讓我對我的石像老友抱以更深期許。多年不見的他,直到去年我到上海出差時才有機會再得聚首。這才知道堅持不離開建築領域的老徐後來熱情不減地轉進了土地的規劃與開發,現已成了城市裡的地產大亨。再次見面的那晚,他開了一瓶十萬元的紅酒與一支跟「切格瓦拉」同樣大器如砲管的雪茄,與我分享了另外一種建築人的碩大情懷。只見雪茄被夾在他一如往常的中指與無名指之間,隔著裊裊燃起的煙霧,我看到巨柴後方變胖了的「庫哈斯先生」,一時之間倒有那麼幾分「川普」的錯覺。
…………………………………………………
「當你離開你一直以為扮演得很好的那個角色時,才終於讓你自己與那個角色都活了過來,並且深愛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