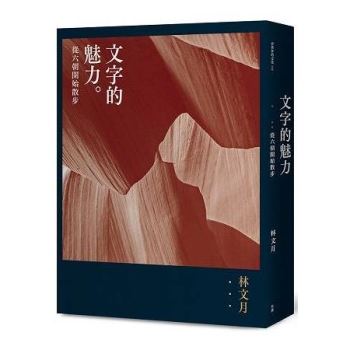【內文節選一】
記一張黑白照片──懷念莊慕陵先生
莊靈送給我一張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兩位可敬的長者。靜農師叼著煙斗坐於案前,正聚精會神作畫,些許白煙裊繞深色的衣襟邊。畫紙上三枝兩枝榦莖,依稀是梅花的構圖。旁邊站立的一位是莊慕陵先生,左手輕插腰際,右手自然地扶著桌面上畫稿的一側,指間夾著半截香菸,亦正聚精會神地俯觀畫面。眼鏡擋住了雙目的表情,但嘴角的微笑分明流露出愉悅的心情。
他們兩位都穿著深色的棉袍,背景是溫州街靜農師的書房。從偏暗的光線看來,這張照片大概拍攝於某一年的冬日午後,他們兩位的年紀大約都在七十餘歲光景;然則莊靈拍攝這張照片,許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時間飛逝!豈不令人驚心!
其實,十多年以前,我曾在靜農師的書房中看到同一張照片,十分喜歡,靜農師便將那張普通尺寸的照片贈送給我。他說:「你先拿去,我還可以跟莊靈再要一張。」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偏暗的調子。光線自右方的窗戶或檯燈照射過來,只照亮兩位長者向著光的顏面、拿個筆與夾著香煙的右手;沉暗的桌面上,除打開的半包香菸及火柴等零星小件外,一張平鋪的畫紙是聚光的中心。從畫者專注的眼神與觀者微笑的嘴角,可以感受到二人之間書畫優雅的氛圍。
靜農師與慕陵先生半世紀的友誼、正是詩文書畫優雅的交往;當然,其間也還有菸酒詼諧豪邁的另一面吧。
多年以前,我曾多次在靜農師的書房內不期然遇見慕陵先生。那間書房不過八坪大小。除兩面窗戶、一面書櫥外,屋內僅一張可供閱讀及寫字作畫的大書桌,其餘狹隘的空間裡,擺著幾張椅子和矮几。靜農師的主位永遠是桌前那張藤椅,主客可坐在他對面的另一張藤椅;而一般學生晚輩多數隨便自尋散布的各種椅子坐下。慕陵先生坐在靜農師對面的藤椅裡,他清癯的身子幾乎被藤椅的背部和扶手包圍起來,與身材魁梧的靜農師恰成有趣的對比畫面。坐於稍遠處的我,常常可以清楚地看見兩位如此的景象;也往往可以清晰地聽見他們談話的內容。慕陵先生的聲音比較輕微,一口標準的京片子,與靜農師的皖北口音、豪爽的笑聲,也形成有趣的對比,不過,他們談詩說畫間,時時語帶幽默,彼此戲謔揶揄對方,並未因小輩的我在一側而有所忌諱。他們的話題,時則有關臺北藝文界的友儕,那些人我差不多都認識;時則又忽爾回溯多年以前的大陸故舊,那些人我多數在文章裡讀過,或從靜農師的談說間聞知。而無論我認識與不認識,靜坐一旁聽兩位長輩隨興的笑談,都有如聆聽一頁頁的近代歷史或文學史,甚至彷彿如民國時代的《世說新語》一般,有趣且有益,頗令人神往!
我第一次看到慕陵先生是在民國四十五年春季。那年即將畢業的同班同學十餘人,由當時的系主任靜農師帶領,去中南部畢業旅行。當時臺大中文系的學生人數不多,師生間有極親近濃郁的感情,故而大學生舉辦畢業旅行,竟然勞駕系主任參與。畢業旅行費時幾日?旅遊過哪些地方?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只記得我們在系主任帶領之下,去訪問霧峰鄉北溝村、參觀了那時暫設在該地的故宮古物館。
我們一行人自臺北搭乘火車到臺中,再改坐公共汽車到一個簡樸的鄉村。莊慕陵先生當時為故宮古物館館長,他和二、三位工作人員站在磚造的平房門口迎接我們。在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館尚未建造以前,自大陸運轉來臺灣的故宮古器物都暫時收藏在氣候比較乾爽的中部,而由大陸護送那些古器物安然抵臺的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便也與古器物同時移居在北溝。那時珍貴的文物並未對外公開展覽,而只是小心翼翼地收藏於北溝的山洞中,由於尚未有除濕及空調的科學設備,所以定期輪流移出若干件於與山洞毗鄰的庫房內曝晾,以為維護。我們班上的同學,有幸因靜農師與館長多年的交誼,遂得藉畢業旅行參觀了一部分的國寶!
那磚造的庫房傍依山洞而蓋。四十年後的現在我仍記得那一排只糊水泥而沒有任何裝飾的簡素平房。慕陵先生引領我們進入那平凡卻意義非凡的屋中。猶記得有一間是擺設鐘鼎類古銅器。白布覆蓋著可能是極尋常的桌几,上面羅列著許多件商代、周代的名器。毛公鼎單獨放置在一方桌上,占據庫房的中央部位,既無安全措施,亦無玻璃罩蓋,幾乎伸手可觸那舉世聞名的寶物!我們輪流在那前面拍照留影;至今,學生時代的相簿中仍貼著那-方照片。慕陵先生一一為我們仔細講解每件器物的由來及特色,使我們的知識從書本文字而具體領會實物。那樣的畢業旅行,令我難以忘懷。我們已事先約略自靜晨師聞知館長如何備盡困難艱辛甚至冒險萬端地負責及時運出國寶的故事,對於眼前那位清瘦而英挺的人物,遂格外有一種欽佩之情油然興生。當年若非慕陵先生以及一些衷心愛護國家寶物的人士盡心盡力護送,今日故宮博物館中所展示及收藏的歷史珍寶將不知是怎樣一個下場?
其後,外雙溪宏偉的現代化設備博物館落成,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亦隨國寶文物北上,定居於館址附近的宿舍。又若干年,而張大千先生也從巴西歸國定居。他的「摩耶精舍」與慕陵先生的「洞天山堂」相去不過一華里,若沒有小山坡及樹木遮掩,兩家的屋頂幾可以遙相望見。靜農師的「龍坡丈室」雖距離稍遠,但老師猶且健步如飛,勤於走訪。有一段時閒,三位退休的老人家確曾有過詩酒風流,如陶公與素心友人「樂與數晨夕」的歡愉晚年的。
這張照片,應即是那段時間的某日午後,慕陵先生自外雙溪「洞天山堂」移駕來訪靜農師溫州街「龍坡丈室」,亢言談昔的吧。
悠悠二十年的時光流逝,雖然敬愛的長輩已先後作古,甚至溫州街的臺大宿舍都已經改建成為高樓公寓,我所熟悉的老舊日式木造書齋也不復存在;但是那個冬日午後,莊靈按下快門所捕捉到的這個鏡頭,卻永遠保存了人間最值得欽羨的一幕景象。
照片裡的兩位長者,都曾飽經中國近代歷史的種種憂患,他們在中年時期毅然離開家鄉,轉徙來臺灣定居,貢獻畢生精力於此地的文化教育;他們的晚年素樸而豐饒,應是無所遺憾。放大的黑白照片,無須任何注解,正說明了-切。斗室之內,知交相聚,無論奇文共賞、疑義相析或書畫展才,莫不真誠而理勝。
面對這一張照片,我看到一種永不消滅的典範,不再沉湎於傷逝的悲情,內心只覺得熙怡而感動!【內文節選二】
平安朝文學的中國語譯(節選)
我其實是專攻中國中世紀文學研究的,退休以前,一直都在臺灣大學教授中國古典文學,所以每常被人問及為何研究中國文學而翻譯日本文學?簡單言之,我是太平洋戰爭前,出生於上海的日本租界,小學五年級上學期以前,受日本語文教育,戰後,我們臺灣人的身分依法律改變為中國人,我的家庭也就離開上海遷回了「故鄉」臺灣。我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在臺北的老松國小改受中國語文教育。換言之,十二歲以前是過日本語文的生活,十二歲以後才學著使用中國語文過日子。當初在幼小的心中,我得將中國語文轉換為日本語文,或是反過來把日本語文改變成為中國語文才能生活的。當時並不知那就是「翻譯」。是的,其實在蒙蒙未解何謂「翻譯」的年少時期,我就得常常在腦中進行著翻譯了。
一九七二年日本筆會舉辦「國際筆會大會」,我出任為中華民國代表之一。依大會規定,出席者需提出與日本文化相關之論文。我以日文寫出一篇論文〈桐壺と長恨歌〉。會後將此論文自譯為中文。〈桐壺〉是日本平安時代的名著《源氏物語》的第一帖帖名。為了中國讀者的閱讀之便,遂將〈桐壺〉也譯出而附繫於論文之後,刊登於《中外文學》雜誌。相當意外的是讀者們對〈桐壺〉譯文的好感與興趣似乎更在那篇論文之上。雜誌社的編輯室接到許多讀者投書,要我繼續把《源氏物語》全部譯出。當時臺灣尚未有此書的譯本。讀者們或許並不知悉此書有多長多難翻譯;而況,自忖以我小學校五年程度的日本語文基礎,到底能否勝任此工作?當初附〈桐壺〉譯文的目的,只是為了讓讀者閱讀我論文的方便,遂將一萬字左右的〈桐壺〉原文翻譯出來,豈敢有全譯《源氏物語》的意圖?但是投書不斷,而《中外文學》的社長胡耀恆教授每每從文學院樓下的外文系辦公室走到樓上的中文系辦公室誠懇相勸,令我感動。於是,以譯事可能會中途停頓的前提條件之下,暫時答應下來。其後的生活,委實是緊張逼迫的日日。身為臺灣大学中國文學系的教授、而且是有一兒一女的家庭主婦,答應《中外文學》的同時,我在心裡暗中約制,要兼顧教師之職及為母的責任。時年四十餘歲的我,幸而體能狀況健康,家族也都了解和支持我。每月約二萬字的譯文出現在《中外文學》月刊,五年半(一九七三年四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十六期),連載遂告完成,沒有拖延一期。其後回顧,連自己也不能相信,那一段時間好似經歷一次長長的馬拉松賽跑。初時,於譯文達到三百頁左右,就出版一冊單行本。如此,在心理上比較有一種可以把握的「成就感」。全書譯完,共得五冊。
一九八二年春季,美國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舉辦國際性的《源氏物語》大會。我趁著受邀出席之便,用整個暑假的時間從事第三版的修訂工作,並且改原來的五冊本為上、下二大冊(共一三五二頁)。有趣的是,其後相較之下,世界各國翻譯此書,儘管語言相異,文字有別,只要是全譯本,文章長度卻都相近。例如中國語譯,大陸豐子愷譯為一○七三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林譯為一三二六頁(臺北洪範出版社,2000)、英譯Edward G. Sidensticker譯為一○九○頁(Alfred A. knopf, Inc, 1976)、Royall Tyler譯為一一七四頁(The Penguin Group New York, 2001)。我的譯文比豐氏譯多出三百多頁,可能是譯文之前附有種種與《源氏物語》其書相關之解釋,以及與平安時代貴族生活有關的說明文字之故。我翻譯《源氏物語》的時候,臺灣和中國大陸互相閉鎖,兩岸人民固無來往,即使信件及印刷物也都無法通郵。而且,豐子愷約是在二十世紀六○年代始譯《源氏物語》,那種取材於平安時代貴族生活的「物語」在「文化革命」之下的當地文化界,斷無被中國大陸接受的可能性。可惜在我多方採用日本現代語譯本、英國語譯本等等參考書的書房裡,獨缺中譯的《源氏物語》,此未免是遺憾之事;然而也是亦憾亦幸之事。何以?設想當時如果知悉前輩已譯成此巨著,我可能根本就不敢存有再試的念頭;而且即使再試之,一遇到猶豫存疑處,難免會賴以為參考的吧。或許,正因為伸手可及之處少了另一本《源氏物語》的中文譯書,我才不得不始終獨立思考判斷,完全依照自己的想法譯寫出來。其後得知,豐氏的譯本是在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三之間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分為上、中、下三冊發行。可惜,當時譯者已亡,故而無由目睹慶喜。至於那本譯者已故才出版的書,序文是由另一位葉渭渠氏所執筆,所以讀者也無由得知默默譯出此書的豐氏翻譯的心路歷程了。
《源氏物語》譯完後,我時常被人誤認為日本文學研究者,或在大學裡教授日本古典文學。至今,臺灣的譯界於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翻譯不可謂不多,但是對於古典文學作品的介紹卻很少,而平安朝文學的作品可說幾乎沒有。無怪乎三十餘年前,我的《源氏物語》中國語譯之出版,會引起讀者們很大的興趣和頗深的感動了。一千年以前描寫平安朝代的這本「物語」,對於中國的讀者而言,於異國情調之中,又會時時看到中國的歷史,或中國古代人物名稱之出現;甚至於讀著讀著,唐詩的一句、二句,也往往藉著「物語」裡某人說話而忽然插進來,令讀者意外感到驚奇有趣。這樣的意外和驚奇,是在我們閱讀其他的外國文學翻譯時所不可能的體驗;而其他的外國讀者在閱讀此書的翻譯時,也决不會有如此奇妙感受的。通過《源氏物語》的中文翻譯,中國讀者會感知:原來在一千年前的古代日本,有這麽多我們所不知道的世界,而其中又有些許似曾相識之處。例如打開書一看第一帖〈桐壺〉:不知是在那一朝帝王的時代,在後宮眾多女御和更衣之中,有一位身分並不十分高貴,卻格外得寵的人。那些本來自以為可以得到皇上專寵的人,對她自是不懷好感,既輕蔑、又嫉妒。至於跟她身分相若的,或者比她身分更低的人,心中更是焦慮極了。大概是日常遭人嫉恨的緣故吧,這位更衣變得憂鬱而多病,經常獨個兒悄然地返歸娘家住著,皇上看她這樣,也就更加憐愛,往往罔顧人言,做出一些教人議論的事情來。那種破格寵愛的程度,簡直連公卿和殿上人之輩都不得不側目而不敢正視呢。許多人對這件事漸漸憂慮起來,有人甚至於杞人憂天的拿唐朝變亂的不吉利的事實相比,又舉出唐玄宗因迷戀楊貴妃,險些兒亡國的例子來議論著。(林譯P.2)
《源氏物語》開頭著名的這一段文字,只要稍涉中國古典文學的人都能看到深受唐代詩人白居易名作〈長恨歌〉詩的影響。臺灣中學生的國文課本每每收入此作,許多學生甚至於能全篇朗誦而出,也不足為奇。因此,讀者在覽閱《源氏物語》的譯本時,往往會遇到既富異國情調,而又耳熟能詳,似曾相識的奇妙的喜悅。這種奇妙的喜悅,不是別的外國語譯本的讀者所能體會經驗,唯有中國讀者才會一邊領略這種奇妙的感覺,一邊被書裡所記述歷史大舞臺的變化,和一個一個人物的悲歡哀樂愛惡慾所吸引下去。
一九八七年秋季到冬季,我曾訪問旅行英國、美國和日本各地學界,會見一些學者,而决心再次投入《枕草子》的譯事。原因之一是在倫敦博物館看到Ivan Morris的英譯本《枕草子》(《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onagon》),以及日本近代學者所著各種相關論文,並且在舊書店裡買到了《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onag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和一些英文的資料。其後,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以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圖書館查閱參考書,竟好像忘了過去五年半的譯事疲憊似的,不知不覺又產生一種熱烈的情緒。回臺灣後不久,遂又一度展開了在教室裡講授中國古典文學,在家中夜深時大部分與清少納言相對,把另一位平安時代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枕草子》譯介出來。這本書在份量上遠不如《源氏物語》之長篇巨構,但翻譯之際,查閱資料最是費時耗神。在翻譯過程中,也同樣在《中外文學》雜誌每月連戴,二十二期,二年餘而譯竟。《枕草子》與《源氏物語》並稱為日本平安朝文學的「双璧」。這兩本書的作者紫式部和清少納言,後世習稱「女流作家」;而她們的書《源氏物語》及《枕草子》則又稱為「女流文學」。這樣的稱謂是由於「假名」書寫的文體始於平安朝代女性所執筆的「物語」。在日本文學史上,紫式部和清少納言,不僅是堂堂第一流的文學家,而今透過多種外國語的譯介,更已享有舉世尊重的地位。中國的讀者至今無緣得識《枕草子》與《源氏物語》,是因為我們的譯事耽誤的緣故。猶記得一九七二年冬,在京都舉行的「日本國際筆會大會」裡偶然與京都大學教授的漢學者吉川幸次郎先生相會時,吉川先生所講的話:「日本漢學界研究中國的文學,我們把《詩經》、《楚辭》……直到《水滸傳》、《紅樓夢》等等,都翻譯成為日本語文了,但是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文學卻是太過冷淡了。」至今,我還忘不了吉川先生講話時非常遺憾的表情。我們只是冷淡嗎?還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源氏物語》、《枕草子》連續從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九年,經由翻譯而介紹了兩本日本的古典文學作品以後,不知何故,臺灣的讀者們無形之中自然會對我有所期待的問:「下一本呢?」而我自己也似乎在休息一段時間後,就會思考下一本翻譯的書。在我心中,感到有必需盡一己所能的「使命感」。第三本書,我選擇了《和泉式部日記》。「看吧,她偏愛女性作家。」或許有人會這麼想。但我以紫式部、清少納言的順序譯出平安朝文學為中文,並不因為二人是女性的緣故,而是因為她們是《源氏物語》、《枕草子》這兩本重要著述的作者。其後,我選擇了和泉式部的《日記》為第三本譯著的道理,也就無需說明,是基於同樣理由,與作者的性別不相關。任何一個人都會承認《源氏物語》、《枕草子》及《和泉式部日記》為日本平安朝文學「鼎足而立」的三大巨著。這才是我唯一的考慮。
記一張黑白照片──懷念莊慕陵先生
莊靈送給我一張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兩位可敬的長者。靜農師叼著煙斗坐於案前,正聚精會神作畫,些許白煙裊繞深色的衣襟邊。畫紙上三枝兩枝榦莖,依稀是梅花的構圖。旁邊站立的一位是莊慕陵先生,左手輕插腰際,右手自然地扶著桌面上畫稿的一側,指間夾著半截香菸,亦正聚精會神地俯觀畫面。眼鏡擋住了雙目的表情,但嘴角的微笑分明流露出愉悅的心情。
他們兩位都穿著深色的棉袍,背景是溫州街靜農師的書房。從偏暗的光線看來,這張照片大概拍攝於某一年的冬日午後,他們兩位的年紀大約都在七十餘歲光景;然則莊靈拍攝這張照片,許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時間飛逝!豈不令人驚心!
其實,十多年以前,我曾在靜農師的書房中看到同一張照片,十分喜歡,靜農師便將那張普通尺寸的照片贈送給我。他說:「你先拿去,我還可以跟莊靈再要一張。」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偏暗的調子。光線自右方的窗戶或檯燈照射過來,只照亮兩位長者向著光的顏面、拿個筆與夾著香煙的右手;沉暗的桌面上,除打開的半包香菸及火柴等零星小件外,一張平鋪的畫紙是聚光的中心。從畫者專注的眼神與觀者微笑的嘴角,可以感受到二人之間書畫優雅的氛圍。
靜農師與慕陵先生半世紀的友誼、正是詩文書畫優雅的交往;當然,其間也還有菸酒詼諧豪邁的另一面吧。
多年以前,我曾多次在靜農師的書房內不期然遇見慕陵先生。那間書房不過八坪大小。除兩面窗戶、一面書櫥外,屋內僅一張可供閱讀及寫字作畫的大書桌,其餘狹隘的空間裡,擺著幾張椅子和矮几。靜農師的主位永遠是桌前那張藤椅,主客可坐在他對面的另一張藤椅;而一般學生晚輩多數隨便自尋散布的各種椅子坐下。慕陵先生坐在靜農師對面的藤椅裡,他清癯的身子幾乎被藤椅的背部和扶手包圍起來,與身材魁梧的靜農師恰成有趣的對比畫面。坐於稍遠處的我,常常可以清楚地看見兩位如此的景象;也往往可以清晰地聽見他們談話的內容。慕陵先生的聲音比較輕微,一口標準的京片子,與靜農師的皖北口音、豪爽的笑聲,也形成有趣的對比,不過,他們談詩說畫間,時時語帶幽默,彼此戲謔揶揄對方,並未因小輩的我在一側而有所忌諱。他們的話題,時則有關臺北藝文界的友儕,那些人我差不多都認識;時則又忽爾回溯多年以前的大陸故舊,那些人我多數在文章裡讀過,或從靜農師的談說間聞知。而無論我認識與不認識,靜坐一旁聽兩位長輩隨興的笑談,都有如聆聽一頁頁的近代歷史或文學史,甚至彷彿如民國時代的《世說新語》一般,有趣且有益,頗令人神往!
我第一次看到慕陵先生是在民國四十五年春季。那年即將畢業的同班同學十餘人,由當時的系主任靜農師帶領,去中南部畢業旅行。當時臺大中文系的學生人數不多,師生間有極親近濃郁的感情,故而大學生舉辦畢業旅行,竟然勞駕系主任參與。畢業旅行費時幾日?旅遊過哪些地方?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只記得我們在系主任帶領之下,去訪問霧峰鄉北溝村、參觀了那時暫設在該地的故宮古物館。
我們一行人自臺北搭乘火車到臺中,再改坐公共汽車到一個簡樸的鄉村。莊慕陵先生當時為故宮古物館館長,他和二、三位工作人員站在磚造的平房門口迎接我們。在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館尚未建造以前,自大陸運轉來臺灣的故宮古器物都暫時收藏在氣候比較乾爽的中部,而由大陸護送那些古器物安然抵臺的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便也與古器物同時移居在北溝。那時珍貴的文物並未對外公開展覽,而只是小心翼翼地收藏於北溝的山洞中,由於尚未有除濕及空調的科學設備,所以定期輪流移出若干件於與山洞毗鄰的庫房內曝晾,以為維護。我們班上的同學,有幸因靜農師與館長多年的交誼,遂得藉畢業旅行參觀了一部分的國寶!
那磚造的庫房傍依山洞而蓋。四十年後的現在我仍記得那一排只糊水泥而沒有任何裝飾的簡素平房。慕陵先生引領我們進入那平凡卻意義非凡的屋中。猶記得有一間是擺設鐘鼎類古銅器。白布覆蓋著可能是極尋常的桌几,上面羅列著許多件商代、周代的名器。毛公鼎單獨放置在一方桌上,占據庫房的中央部位,既無安全措施,亦無玻璃罩蓋,幾乎伸手可觸那舉世聞名的寶物!我們輪流在那前面拍照留影;至今,學生時代的相簿中仍貼著那-方照片。慕陵先生一一為我們仔細講解每件器物的由來及特色,使我們的知識從書本文字而具體領會實物。那樣的畢業旅行,令我難以忘懷。我們已事先約略自靜晨師聞知館長如何備盡困難艱辛甚至冒險萬端地負責及時運出國寶的故事,對於眼前那位清瘦而英挺的人物,遂格外有一種欽佩之情油然興生。當年若非慕陵先生以及一些衷心愛護國家寶物的人士盡心盡力護送,今日故宮博物館中所展示及收藏的歷史珍寶將不知是怎樣一個下場?
其後,外雙溪宏偉的現代化設備博物館落成,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亦隨國寶文物北上,定居於館址附近的宿舍。又若干年,而張大千先生也從巴西歸國定居。他的「摩耶精舍」與慕陵先生的「洞天山堂」相去不過一華里,若沒有小山坡及樹木遮掩,兩家的屋頂幾可以遙相望見。靜農師的「龍坡丈室」雖距離稍遠,但老師猶且健步如飛,勤於走訪。有一段時閒,三位退休的老人家確曾有過詩酒風流,如陶公與素心友人「樂與數晨夕」的歡愉晚年的。
這張照片,應即是那段時間的某日午後,慕陵先生自外雙溪「洞天山堂」移駕來訪靜農師溫州街「龍坡丈室」,亢言談昔的吧。
悠悠二十年的時光流逝,雖然敬愛的長輩已先後作古,甚至溫州街的臺大宿舍都已經改建成為高樓公寓,我所熟悉的老舊日式木造書齋也不復存在;但是那個冬日午後,莊靈按下快門所捕捉到的這個鏡頭,卻永遠保存了人間最值得欽羨的一幕景象。
照片裡的兩位長者,都曾飽經中國近代歷史的種種憂患,他們在中年時期毅然離開家鄉,轉徙來臺灣定居,貢獻畢生精力於此地的文化教育;他們的晚年素樸而豐饒,應是無所遺憾。放大的黑白照片,無須任何注解,正說明了-切。斗室之內,知交相聚,無論奇文共賞、疑義相析或書畫展才,莫不真誠而理勝。
面對這一張照片,我看到一種永不消滅的典範,不再沉湎於傷逝的悲情,內心只覺得熙怡而感動!【內文節選二】
平安朝文學的中國語譯(節選)
我其實是專攻中國中世紀文學研究的,退休以前,一直都在臺灣大學教授中國古典文學,所以每常被人問及為何研究中國文學而翻譯日本文學?簡單言之,我是太平洋戰爭前,出生於上海的日本租界,小學五年級上學期以前,受日本語文教育,戰後,我們臺灣人的身分依法律改變為中國人,我的家庭也就離開上海遷回了「故鄉」臺灣。我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在臺北的老松國小改受中國語文教育。換言之,十二歲以前是過日本語文的生活,十二歲以後才學著使用中國語文過日子。當初在幼小的心中,我得將中國語文轉換為日本語文,或是反過來把日本語文改變成為中國語文才能生活的。當時並不知那就是「翻譯」。是的,其實在蒙蒙未解何謂「翻譯」的年少時期,我就得常常在腦中進行著翻譯了。
一九七二年日本筆會舉辦「國際筆會大會」,我出任為中華民國代表之一。依大會規定,出席者需提出與日本文化相關之論文。我以日文寫出一篇論文〈桐壺と長恨歌〉。會後將此論文自譯為中文。〈桐壺〉是日本平安時代的名著《源氏物語》的第一帖帖名。為了中國讀者的閱讀之便,遂將〈桐壺〉也譯出而附繫於論文之後,刊登於《中外文學》雜誌。相當意外的是讀者們對〈桐壺〉譯文的好感與興趣似乎更在那篇論文之上。雜誌社的編輯室接到許多讀者投書,要我繼續把《源氏物語》全部譯出。當時臺灣尚未有此書的譯本。讀者們或許並不知悉此書有多長多難翻譯;而況,自忖以我小學校五年程度的日本語文基礎,到底能否勝任此工作?當初附〈桐壺〉譯文的目的,只是為了讓讀者閱讀我論文的方便,遂將一萬字左右的〈桐壺〉原文翻譯出來,豈敢有全譯《源氏物語》的意圖?但是投書不斷,而《中外文學》的社長胡耀恆教授每每從文學院樓下的外文系辦公室走到樓上的中文系辦公室誠懇相勸,令我感動。於是,以譯事可能會中途停頓的前提條件之下,暫時答應下來。其後的生活,委實是緊張逼迫的日日。身為臺灣大学中國文學系的教授、而且是有一兒一女的家庭主婦,答應《中外文學》的同時,我在心裡暗中約制,要兼顧教師之職及為母的責任。時年四十餘歲的我,幸而體能狀況健康,家族也都了解和支持我。每月約二萬字的譯文出現在《中外文學》月刊,五年半(一九七三年四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十六期),連載遂告完成,沒有拖延一期。其後回顧,連自己也不能相信,那一段時間好似經歷一次長長的馬拉松賽跑。初時,於譯文達到三百頁左右,就出版一冊單行本。如此,在心理上比較有一種可以把握的「成就感」。全書譯完,共得五冊。
一九八二年春季,美國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舉辦國際性的《源氏物語》大會。我趁著受邀出席之便,用整個暑假的時間從事第三版的修訂工作,並且改原來的五冊本為上、下二大冊(共一三五二頁)。有趣的是,其後相較之下,世界各國翻譯此書,儘管語言相異,文字有別,只要是全譯本,文章長度卻都相近。例如中國語譯,大陸豐子愷譯為一○七三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林譯為一三二六頁(臺北洪範出版社,2000)、英譯Edward G. Sidensticker譯為一○九○頁(Alfred A. knopf, Inc, 1976)、Royall Tyler譯為一一七四頁(The Penguin Group New York, 2001)。我的譯文比豐氏譯多出三百多頁,可能是譯文之前附有種種與《源氏物語》其書相關之解釋,以及與平安時代貴族生活有關的說明文字之故。我翻譯《源氏物語》的時候,臺灣和中國大陸互相閉鎖,兩岸人民固無來往,即使信件及印刷物也都無法通郵。而且,豐子愷約是在二十世紀六○年代始譯《源氏物語》,那種取材於平安時代貴族生活的「物語」在「文化革命」之下的當地文化界,斷無被中國大陸接受的可能性。可惜在我多方採用日本現代語譯本、英國語譯本等等參考書的書房裡,獨缺中譯的《源氏物語》,此未免是遺憾之事;然而也是亦憾亦幸之事。何以?設想當時如果知悉前輩已譯成此巨著,我可能根本就不敢存有再試的念頭;而且即使再試之,一遇到猶豫存疑處,難免會賴以為參考的吧。或許,正因為伸手可及之處少了另一本《源氏物語》的中文譯書,我才不得不始終獨立思考判斷,完全依照自己的想法譯寫出來。其後得知,豐氏的譯本是在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三之間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分為上、中、下三冊發行。可惜,當時譯者已亡,故而無由目睹慶喜。至於那本譯者已故才出版的書,序文是由另一位葉渭渠氏所執筆,所以讀者也無由得知默默譯出此書的豐氏翻譯的心路歷程了。
《源氏物語》譯完後,我時常被人誤認為日本文學研究者,或在大學裡教授日本古典文學。至今,臺灣的譯界於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翻譯不可謂不多,但是對於古典文學作品的介紹卻很少,而平安朝文學的作品可說幾乎沒有。無怪乎三十餘年前,我的《源氏物語》中國語譯之出版,會引起讀者們很大的興趣和頗深的感動了。一千年以前描寫平安朝代的這本「物語」,對於中國的讀者而言,於異國情調之中,又會時時看到中國的歷史,或中國古代人物名稱之出現;甚至於讀著讀著,唐詩的一句、二句,也往往藉著「物語」裡某人說話而忽然插進來,令讀者意外感到驚奇有趣。這樣的意外和驚奇,是在我們閱讀其他的外國文學翻譯時所不可能的體驗;而其他的外國讀者在閱讀此書的翻譯時,也决不會有如此奇妙感受的。通過《源氏物語》的中文翻譯,中國讀者會感知:原來在一千年前的古代日本,有這麽多我們所不知道的世界,而其中又有些許似曾相識之處。例如打開書一看第一帖〈桐壺〉:不知是在那一朝帝王的時代,在後宮眾多女御和更衣之中,有一位身分並不十分高貴,卻格外得寵的人。那些本來自以為可以得到皇上專寵的人,對她自是不懷好感,既輕蔑、又嫉妒。至於跟她身分相若的,或者比她身分更低的人,心中更是焦慮極了。大概是日常遭人嫉恨的緣故吧,這位更衣變得憂鬱而多病,經常獨個兒悄然地返歸娘家住著,皇上看她這樣,也就更加憐愛,往往罔顧人言,做出一些教人議論的事情來。那種破格寵愛的程度,簡直連公卿和殿上人之輩都不得不側目而不敢正視呢。許多人對這件事漸漸憂慮起來,有人甚至於杞人憂天的拿唐朝變亂的不吉利的事實相比,又舉出唐玄宗因迷戀楊貴妃,險些兒亡國的例子來議論著。(林譯P.2)
《源氏物語》開頭著名的這一段文字,只要稍涉中國古典文學的人都能看到深受唐代詩人白居易名作〈長恨歌〉詩的影響。臺灣中學生的國文課本每每收入此作,許多學生甚至於能全篇朗誦而出,也不足為奇。因此,讀者在覽閱《源氏物語》的譯本時,往往會遇到既富異國情調,而又耳熟能詳,似曾相識的奇妙的喜悅。這種奇妙的喜悅,不是別的外國語譯本的讀者所能體會經驗,唯有中國讀者才會一邊領略這種奇妙的感覺,一邊被書裡所記述歷史大舞臺的變化,和一個一個人物的悲歡哀樂愛惡慾所吸引下去。
一九八七年秋季到冬季,我曾訪問旅行英國、美國和日本各地學界,會見一些學者,而决心再次投入《枕草子》的譯事。原因之一是在倫敦博物館看到Ivan Morris的英譯本《枕草子》(《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onagon》),以及日本近代學者所著各種相關論文,並且在舊書店裡買到了《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onag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和一些英文的資料。其後,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以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圖書館查閱參考書,竟好像忘了過去五年半的譯事疲憊似的,不知不覺又產生一種熱烈的情緒。回臺灣後不久,遂又一度展開了在教室裡講授中國古典文學,在家中夜深時大部分與清少納言相對,把另一位平安時代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枕草子》譯介出來。這本書在份量上遠不如《源氏物語》之長篇巨構,但翻譯之際,查閱資料最是費時耗神。在翻譯過程中,也同樣在《中外文學》雜誌每月連戴,二十二期,二年餘而譯竟。《枕草子》與《源氏物語》並稱為日本平安朝文學的「双璧」。這兩本書的作者紫式部和清少納言,後世習稱「女流作家」;而她們的書《源氏物語》及《枕草子》則又稱為「女流文學」。這樣的稱謂是由於「假名」書寫的文體始於平安朝代女性所執筆的「物語」。在日本文學史上,紫式部和清少納言,不僅是堂堂第一流的文學家,而今透過多種外國語的譯介,更已享有舉世尊重的地位。中國的讀者至今無緣得識《枕草子》與《源氏物語》,是因為我們的譯事耽誤的緣故。猶記得一九七二年冬,在京都舉行的「日本國際筆會大會」裡偶然與京都大學教授的漢學者吉川幸次郎先生相會時,吉川先生所講的話:「日本漢學界研究中國的文學,我們把《詩經》、《楚辭》……直到《水滸傳》、《紅樓夢》等等,都翻譯成為日本語文了,但是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文學卻是太過冷淡了。」至今,我還忘不了吉川先生講話時非常遺憾的表情。我們只是冷淡嗎?還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源氏物語》、《枕草子》連續從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九年,經由翻譯而介紹了兩本日本的古典文學作品以後,不知何故,臺灣的讀者們無形之中自然會對我有所期待的問:「下一本呢?」而我自己也似乎在休息一段時間後,就會思考下一本翻譯的書。在我心中,感到有必需盡一己所能的「使命感」。第三本書,我選擇了《和泉式部日記》。「看吧,她偏愛女性作家。」或許有人會這麼想。但我以紫式部、清少納言的順序譯出平安朝文學為中文,並不因為二人是女性的緣故,而是因為她們是《源氏物語》、《枕草子》這兩本重要著述的作者。其後,我選擇了和泉式部的《日記》為第三本譯著的道理,也就無需說明,是基於同樣理由,與作者的性別不相關。任何一個人都會承認《源氏物語》、《枕草子》及《和泉式部日記》為日本平安朝文學「鼎足而立」的三大巨著。這才是我唯一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