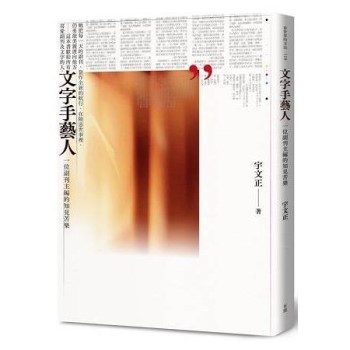催稿
自由副刊向我約一篇春節專輯的稿子,篇幅不長,趕緊寫好了交出去,比「deadline」提早一星期。梓評接到稿子回信讚美「真是太厲害了。速度又快又好看……」好不好看很難說,人家有可能是客氣,但他口吻中難掩的驚喜,我讀出來,重點是「快」。同為編輯我太理解那心情。年前跟郭強生、許悔之約一篇稿子,為「繆思的星期五──文學沙龍」朗誦會的結束而作,囑他們過完元旦假日交稿。還未收假,稿子皆已送達我的信箱。我根本來不及讀,立馬去信致謝。不拖稿已經很感動,連催都不必催,那真是聖恩浩蕩!
簡媜二十年前所寫的〈一個編輯勞工的苦水經〉,開宗明義便說,在一次非正式的口頭調查中,十位從事編輯工作的人被問到「你最想暗殺的人是誰?」,有九位痛快回答:「作家!」為什麼呢?同文裡寫到「編輯八恨」,第一恨便是「作家黃牛,沒交稿」。此恨綿綿無絕期,相信二十年後再做調查,答案還是不會變的。
或許有讀者不解,副刊不是躺著等作者投稿就得了,為什麼需要「催稿」?不,副刊並不是永遠等待作者來稿,雖然那也是一種編法,但是那太被動了。作家零星的來稿,日積月累當然也可以看出那時代創作、思想的潮流以及社會的脈動,但副刊編輯還有個任務,預先看到趨勢,看到可期待的作家,於是會有企畫性的專題,點出思潮;會有長期執行的專欄,提醒讀者留意精彩的作家,同時也鼓勵作家專注創作,人有時候需要一點壓力,更能激發潛能。副刊史上知名的專欄:聯副的「玻璃墊上」(何凡)、「寶刀集」、張作錦的「感時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長年經營的「三少四壯」都是經典例子。
當前聯副較被矚目的欄目,可能是每兩個月一位的「聯副駐版作家」,以及每周一D2版的「文學相對論」(一○五年九月起移至D4版),邀請的都是創作力正旺盛的作家。
邀約專欄或是企畫專題請作家執筆,自然都是慎選優秀、專業的作家,賦予信任,也充滿期待。而一旦需要催稿,所謂的信任或「鼓勵」就會變成「鞭策」;這「鞭子」一跑出來,便考驗著作家和編(鞭)輯之間的情誼。我是一個什麼樣的編輯呢?記得剛畢業時當記者,有回採訪吳念真先生,他說曾經有次被催稿,逼急了跑到頂樓跟編輯說:你再逼我,我就跳下去!那時一派同情:好可憐喔;要到自己做了編輯才明白,真正想跳樓的人是編輯啊!
但是大概這種「人家可能會跳樓」的心理從未從我心上除去,我始終是個婦人之仁的編輯,專業能力中最糟的一項就是催稿。截稿日到了,約定的稿子還不來,寫Email去,主旨還要不爭氣的嘻皮笑臉說:「催稿魔來了……」嚇誰呀?日前向一位女作家邀稿,她未能如期交稿,臉書上向我請求寬限。我丟一個舉手說「OK」的小貓圖案給她,順便再按一個新年快樂圖給予祝福。她愣住了,「你脾氣也太好!你應該打我屁股才是!」我回答她:「我找不到打屁股的圖案……」她回了我一個笑出眼淚的笑臉。沒辦法,一遇上我欣賞的作家,那種寵溺孩子般的母性激素便自動分泌。
當接受邀稿時,我的心會站在編輯的立場,努力早早交稿,讓人家安心;做為編輯對外邀稿時,我又情不自禁同情作家的處境,不能逼人太甚。真是蝙蝠。
於是有時預定的文章不來,先提個大綱請插畫家自行想像「配」圖;組版時還不來,先把版面空在那裡,辛苦美編,在最後一刻拿到稿子速速完成,驚險過關。即使過程萬分煎熬,但拿到的稿子讓人不枉等待,還是忍不住擊掌叫好。作家王浩威的稿子據說是出名的難催(?),有回策畫〈時代之眼──網路心理學〉專題,浩威兄的稿子遲遲不來,也難為了他,後來他人已搭上飛機,在旅次中趕出五千多字的稿子,千里傳書。雖然讓我捏一大把冷汗,但是那篇〈一個樂觀主義的心理人對未來社會的想像〉,寫得真是好,依然覺得千恩萬謝。
這到底是好的結局。但也曾策畫的系列專題,少了某一篇,便失去了某一角度的看法,催不來就是催不來,臨時找其他作家為時已晚,終於只能算了。甚至,有回合作舉辦文學獎的單位,得獎作品要出版了,預約的序始終不來,我幫忙去催,到付梓前仍無功而返,最後索性自己「下海」幫忙寫序才算了此公案──這樣的催稿本事,真的可以去跳樓啊。作家對我來說,永遠鞭長莫及!但我怎麼敢把自己這要命的弱點寫出來?以後約稿豈不門戶大開,等著開天窗?所以啊,現在企畫專題時,多半請那比我有個性得多的同事去邀稿,黑臉給他做。不然做主編幹嘛呢?
懇請不要
我很想擬一個投稿公約。編輯檯上所遇,光怪陸離,被「懇請」之事無奇不有:幫忙買書、幫忙寄書、幫忙出書、幫忙傳話、幫忙協尋、幫忙「封鎖」、打擊某人(別懷疑,真有!)……。做為編輯,其實也有不少事想懇請投稿者。
第一,懇請不要抄襲,這是天條。
第二,懇請不要一稿兩投或已刊再投。這不是常識嗎?不,網路新生代──不是讀報長大的一代,對報刊投稿的基本概念遠比老一輩稀薄。
其實現代人更須尊重這個倫理,因為網路的傳播無遠弗屆。以往,在海外地區發表過的作品,在台灣重新發表,尚可接受,畢竟讀者海角天涯,並不重疊,今則不然,只要發表過,大部分網路上都能看到,包括已在自己部落格、臉書發表的作品。(當然有些例外,是副刊主動轉載。)
不知道「網路發表」也算發表,猶可原諒,我還常收到一些投稿信,收件者有一大串,人間副刊、自由副刊各友報,甚至本報繽紛版都名列其上,是要我們幾個副刊主編群組討論由誰來刊載嗎?這種自殺式投稿倒還好,不理會便是了(除非是藝文訊息,不在此限)。糟的是我們不知道對方已經到處投,造成重稿、臨時換版,甚至本報家庭版與繽紛版重複刊登之事,不勝其擾。我遇過最誇張之事,是我剛接任主編不久,某知名出版社投來一位作家的序文。我對「序」的刊登頗感困擾,最害怕看到公關、人情序文。但有些序等於是一篇專業書評,在規畫了星期六的「周末書房」之後,這類序文理所當然可放周六書評版;有些序文其實是很好的散文,評述的不僅是書,更在寫人。那篇序便是這樣的一篇文章,但來得太急,書一個禮拜之後便要上市,聯副是預作版,我評估了一下,還是接受了。那意味著須拿下某篇已經排在版上的文章,讓美編辛苦點,也是新聞線上時有之事。惱的是,在刊出前一天,該出版社編輯打電話告訴我,那篇文章同時也給了人間副刊,對方也將刊出,要我們立即撤版。我心中不免難過,覺得對方欺我資淺,其實那位作者與聯副淵源深厚長年交好,我若打電話請作者自己選擇,稿子未必不會留聯副。但想想那編輯到底是無心之過,這一嚷嚷,小事便成了大事。終於還是默默把稿子撤下來,版再度重做。嘴上跟同事說:以後這家出版社的書概不理會!到底也只說說罷了,不能無辜遷怒作家,這點理智我還有,但初任主編時的冷暖,了然於心。現在想起,坦白說,哪家出版社我還記得,卻完全想不起那位編輯的名字了。
第三,懇請不要把「副刊」當作「訃聞」版。我在加拿大旅行時,晨間拿起旅館提供的地方小報,真讀到過整版的訃聞,覺得挺有意思。但那是旅行中,如果真住下來,會不會每天都想要讀整版的訃聞呢?
懷念逝者的悼念文、悼亡詩是文學史上重要的類型,我並沒有偏見,只要是好作品,沒有拒絕的理由。尤其悼念重要作家、文化人的文章,對讀者深具意義,聯副為此特別設有〈文學紀念冊〉欄目,此中時見令人動容之作。近讀林懷民〈思念Linda──回顧一個奮發的時代〉(105年8月19日聯副),懷念的已不只是俠女吳美雲的身姿,更是一個教人神往的年代。然而悲悼之作,要寫到雋永,有時需要時間的沉澱;多數人等不及,不是呼天搶地、便是通篇歌頌逝者,或則瑣瑣碎碎履歷表一般,還規定刊出時間,要趕告別式的、要趕百日的、要趕七七的都有。曾有某位已擱筆多年的作家,過世後遺孀投來悼念文,那作家亦得過聯合報文學獎的,我趕在告別式前刊登了;不料還有續集,夫人再投來更長的一篇,要求作家百日那天刊載。寫得愈長,愈見文筆平庸,再一查她指定的「百日」那天,恰是母親節,早有安排為世間母親而寫的親情散文。我婉拒了,對方竟「不能接受」,認為不刊登無以告慰逝者在天之靈。
拒絕這類文章須特別謹慎委婉,總覺得對方已經傷心難過,我還嫌人家文筆不好,傷口上撒鹽。而作者往往強調這對他是多麼重要,我當然明白這份情意,可惜對個人有意義,若達不到書寫的感染力,對廣大讀者便沒有太大意義。而每天都有人永別世間,設若來稿必登,副刊絕對成為訃刊。
第四,懇請不要一直改、一直改。寄出的稿件,發覺有錯字、人名、事實的錯誤,去信更正,這原是無可厚非之事,但有些作家簡直改稿成癮,投來之後,不斷置換第二個版本、第三個版本……檔案還自己編了版本1、版本2、版本3、4、5、6、7……,根本打定主意要無止境地改下去,真教人啼笑皆非。
我不明白,除非是有特殊時效的文章,或是我們預約的專欄、專題,趕在截稿日交稿,事後忍不住改稿潤飾,這能理解;若是一般的創作,並沒有人逼著交稿,何以不琢磨至滿意了再投稿?究竟在急什麼呢?對於改稿成癮的作家,我現在已知道凡是他們的文章都先放著不要去整理──反正一定會有新檔案來。麻煩的是,愛改的人,就是會「一直改、一直改」,在你組稿、美編已經排在版上之後,他又來新版本!不熟悉編輯作業的人可能疑惑,把電子檔重新丟上版不就得了?實則不然,除了抓錯別字,各方來稿所用標點、格式無奇不有,有人還習慣每寫一行要斷行一次,或是字裡行間無故到處空格;此外,半形的符號、簡繁體字、異體字的用法,民國或西元紀年、國字或阿拉伯數字都要統一,有的要做小標,拉引言、加欄名,各種編輯工夫不一而足。更麻煩的是,有的作家不僅習慣改稿,而且愈改愈長。回信告訴他,好的,會重新換上新檔,但是拜託請不要再改了,因為長度不同,版須重做。作家卻回信振振有詞:「只加了一段,所以只有那一段要重排,其他都未改。」他不知道紙本不同於電腦,一個版面可容納的字數大致是一定的,文章活生生增加了數百字,怎可能「只有那一段」要重排,不但美編必須重新設計,原來搭配的短文或是詩,也可能就此被擠掉了。還有位作家,最初來稿同意留用時是篇兩千多字的文章,作者每隔一段時間來一個新版本,等到準備上版時點開字數統計,赫然發現近四千字,簡直懷疑是詐欺了。
第五,懇請來稿時,不要告訴我你的經濟情況。最近(唉!每一陣子都會)接到這樣的信函,說本人退休/離職/離婚……後無收入,艱難度日,投稿望採用。寫得很令我心酸。但不能用的還是得退。卻使我心裡蒙上陰影:我是個沒有同情心的人!來稿時,請不要告訴我你的經濟情況。
又有一種作者,退稿後助理來電表示,詩人無法接受,問我何故退稿?我心裡圈圈叉叉。後來有別的作家告訴我:
「此人非常有錢!」
「關我什麼事?」
「他能辦許多活動。」
「我又不參加他的活動。下次讓我的助理去告訴他,我也非常有錢。」
「妳助理是誰?」
「就你啊!」
不能用的還是得退,卻使我心裡蒙上陰影:原來我是個討厭有錢人的人。
真的,來稿時,請不要告訴我你的經濟情況。第六,非十萬火急懇請不要凌晨給編輯臉書morning call。副刊編輯的職業病,視力不良、肩頸僵硬、胃痛、頭痛、坐骨神經痛、手腕關節痛(腕隧道症候群)……自從有了臉書,半夜、清晨不時有稿子來敲門,更搞得我神經衰弱。其實投稿還是使用email信箱為佳,讓編輯可以從容處理,也不會在臉書裡不小心被大量訊息淹沒、遺忘。
第七,懇請不要把副刊編輯當成24小時免費的寫作指導老師。不僅被退的稿子要求指導改進,更有人連小孩、孫子的作文都拿來請教。
第八,懇請不要一次丟來數十萬字,要編輯從中大海淘沙。噢,有的還給你一個部落格網址,要你去裡面選文章,似乎以為編輯非常缺稿。
第九,懇請不要把副刊當作職業介紹所、把編輯當成出版仲介。常有我根本不認識的人,要求我幫他推薦工作,或連一篇文章都未曾在聯副刊登過的寫作者,來信告訴我,他寫得不差,卻沒機會出版,要求我出面向出版社推薦。我並沒有那麼大的面子。
其實還有很多的「懇請」,比如懇請不要老要求編輯順便做其實一點都不「順便」的份外之事。最想說的是:懇請不要一直問、一直問!問某篇文章為什麼不用?問稿子何時刊登?問為什麼很久沒見到某某作家的文章?(天知道為什麼!)權且以此作為「第十」點結束本文吧。但是關於不斷來電逼問對編輯造成的精神恐慌,前面已寫過一篇〈電話〉,這裡就不再一直講、一直講了。
手藝人
台北市政府已禁止在殯儀館張貼輓聯,改用電子跑馬燈的形式。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這些見仁見智的爭議且不談,我感受到的是,又一種「手藝人」慢慢將會消失。專業寫輓聯者,是一種手藝人,他們必須具備基礎的國學素養,一定程度的書法能力,以及對於傳統禮儀的認知。這一行,因為從業者專業能力日漸低落,人們也不甚在乎,其實在還未被公然消滅之前,已經慢慢自行凋萎了。
副刊編輯,包括美術編輯,在我看來,也是一種手藝人;是不是「保育類」我不知道,但這門手藝,無論如何不希望在自己手裡斷絕。
有時被作家、讀者抱怨,電子板副刊文章不好找、時有誤植……,我除了儘速請求更正,忍不住對抱怨者說:「也許,這正好提醒您,重新回來看紙本副刊呢。」老王賣瓜一下吧,每當聽到作家,尤其是美學行家,例如蔣勳老師,對我說一句:「今天副刊版面真美。」那真是樂上心頭。有一回,學者林谷芳接待大陸學者時,拿出當日聯副展示,主文正是林谷芳〈真山真水〉,搭配畫家林崇漢氣勢磅礡的插畫,標題為楷書書法。大陸學者嘖嘖稱奇:「這年頭,還有人這樣子編版?」這就是手藝人的版面,也是台灣副刊引以為傲之處。
一個版面的完成,不是編輯從大批來稿中審稿、選稿,或者把稿件約來就算了事。文章份量適宜作為主文者,首先要向風格適宜的插畫家邀約插圖,如果是描述旅行、人物之作,會向作者請求提供照片,或到報社的資料庫尋找、四處向攝影家張羅。主編的腦海裡,會先有一個發表時畫面的整體想像。以〈真山真水〉為例,作者雖傳來了文中提到的富春江照片,但效果不佳,於是我把文章和照片一併傳給崇漢兄參考,讓畫家畫出他胸壑裡的「真山真水」。副刊的插畫家,不折不扣是手藝人。
今日的聯合副刊,一天整版約五千字,在組版時,三千開外的主文,通常搭配一篇千把字的短文,一首詩,再加一兩則小品文、最短篇或是文訊等等。算術差的主編如我,每天是拿著計算機組版的。也因此文章刊出的速度,除了作品本身有其「輕重緩急」,有時字數也決定了它的命運。例如長詩比短詩排隊排得久,因為要等待特別短的主文它才上得去。這些作品,經過編輯整理、加小標、抓引言或寫編按、圖說之後,編排設計是美術編輯的工作。早年聯副有自己的美編,還好幾位!現在全部歸屬美術中心,但美術中心主任對於副刊的美編有特別要求:必須先讀過文章的內容,再來排版。先領略作品的內涵,才能表現最適切的氛圍。小說、散文創作有各種風格的插畫作為主視覺;而聯副談古典文學、美學、戲劇的文章也不少,於是讀者會看到某日頭題為王德威教授的〈古典與青春〉,版面邊緣,壓著半個淡淡的京劇臉譜,那是講述國光京劇十四年的文章;張曉風教授的〈一部美如古蕃錦的《花間集》〉,版面邊緣,則裝飾著古典剪紙圖案。如果內容寫的是關於中國古典小說、書法,版面上可能會出現線裝書的襯底,或是標題上加小小的紅圈,一如古人的句讀,或是古意盎然的紅色章印。有些標題使用印刷體,有些標題請人寫書法……這些,都是「手藝人」的手筆。
我的辦公室座位後方牆上,張貼著未來七天所有組好的版面,工作中,會不時站起來,端詳每一個版面的視覺是否適切,有時移來挪去,像室內設計師,這裡補個光,那裡要留白。
美編組好的版面,交由編輯仔細校對,完成後我會再讀一次,有時再「修潤」一遍。聯副的文章名家多,很少改動,多半只訂正錯字、標點,或是事實的錯誤;繽紛版、家庭版的文章,素人為多,常有好故事,只是文字須再斟酌,編輯潤飾後,往往能清朗有神。校對、潤稿,都是手藝人的工夫。改正、清版、確認後,主編簽了名,才能夠發版、印刷。
這整個製作的程序,最初始,來自最可敬的「手藝人」,即作家(許多作家,如朱天心常以此自況),然後有編輯、插畫家或是攝影師、美術編輯、印刷工作者的通力合作,才成為第二天讀者手中的報紙副刊。請不要怪我老派、頑冥,我實在要說,不看副刊也就算了,既然讀副刊,如果不看整體版面的呈現,而只從電腦中點出一條一條的稿子,真的好可惜,好可惜!這是許多手藝人一環扣一環,把每一個版,都當作一個工藝品精雕細琢而成。這是編輯對作家、作品的心意,也是對讀者的誠意。
我知道許多作家至今仍然非常在乎在副刊的發表,不盡然是因為稿費,也不是為了宣傳,他們自己的臉書就門庭若市,他們珍惜,並且收藏這整個美感的完成。
自由副刊向我約一篇春節專輯的稿子,篇幅不長,趕緊寫好了交出去,比「deadline」提早一星期。梓評接到稿子回信讚美「真是太厲害了。速度又快又好看……」好不好看很難說,人家有可能是客氣,但他口吻中難掩的驚喜,我讀出來,重點是「快」。同為編輯我太理解那心情。年前跟郭強生、許悔之約一篇稿子,為「繆思的星期五──文學沙龍」朗誦會的結束而作,囑他們過完元旦假日交稿。還未收假,稿子皆已送達我的信箱。我根本來不及讀,立馬去信致謝。不拖稿已經很感動,連催都不必催,那真是聖恩浩蕩!
簡媜二十年前所寫的〈一個編輯勞工的苦水經〉,開宗明義便說,在一次非正式的口頭調查中,十位從事編輯工作的人被問到「你最想暗殺的人是誰?」,有九位痛快回答:「作家!」為什麼呢?同文裡寫到「編輯八恨」,第一恨便是「作家黃牛,沒交稿」。此恨綿綿無絕期,相信二十年後再做調查,答案還是不會變的。
或許有讀者不解,副刊不是躺著等作者投稿就得了,為什麼需要「催稿」?不,副刊並不是永遠等待作者來稿,雖然那也是一種編法,但是那太被動了。作家零星的來稿,日積月累當然也可以看出那時代創作、思想的潮流以及社會的脈動,但副刊編輯還有個任務,預先看到趨勢,看到可期待的作家,於是會有企畫性的專題,點出思潮;會有長期執行的專欄,提醒讀者留意精彩的作家,同時也鼓勵作家專注創作,人有時候需要一點壓力,更能激發潛能。副刊史上知名的專欄:聯副的「玻璃墊上」(何凡)、「寶刀集」、張作錦的「感時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長年經營的「三少四壯」都是經典例子。
當前聯副較被矚目的欄目,可能是每兩個月一位的「聯副駐版作家」,以及每周一D2版的「文學相對論」(一○五年九月起移至D4版),邀請的都是創作力正旺盛的作家。
邀約專欄或是企畫專題請作家執筆,自然都是慎選優秀、專業的作家,賦予信任,也充滿期待。而一旦需要催稿,所謂的信任或「鼓勵」就會變成「鞭策」;這「鞭子」一跑出來,便考驗著作家和編(鞭)輯之間的情誼。我是一個什麼樣的編輯呢?記得剛畢業時當記者,有回採訪吳念真先生,他說曾經有次被催稿,逼急了跑到頂樓跟編輯說:你再逼我,我就跳下去!那時一派同情:好可憐喔;要到自己做了編輯才明白,真正想跳樓的人是編輯啊!
但是大概這種「人家可能會跳樓」的心理從未從我心上除去,我始終是個婦人之仁的編輯,專業能力中最糟的一項就是催稿。截稿日到了,約定的稿子還不來,寫Email去,主旨還要不爭氣的嘻皮笑臉說:「催稿魔來了……」嚇誰呀?日前向一位女作家邀稿,她未能如期交稿,臉書上向我請求寬限。我丟一個舉手說「OK」的小貓圖案給她,順便再按一個新年快樂圖給予祝福。她愣住了,「你脾氣也太好!你應該打我屁股才是!」我回答她:「我找不到打屁股的圖案……」她回了我一個笑出眼淚的笑臉。沒辦法,一遇上我欣賞的作家,那種寵溺孩子般的母性激素便自動分泌。
當接受邀稿時,我的心會站在編輯的立場,努力早早交稿,讓人家安心;做為編輯對外邀稿時,我又情不自禁同情作家的處境,不能逼人太甚。真是蝙蝠。
於是有時預定的文章不來,先提個大綱請插畫家自行想像「配」圖;組版時還不來,先把版面空在那裡,辛苦美編,在最後一刻拿到稿子速速完成,驚險過關。即使過程萬分煎熬,但拿到的稿子讓人不枉等待,還是忍不住擊掌叫好。作家王浩威的稿子據說是出名的難催(?),有回策畫〈時代之眼──網路心理學〉專題,浩威兄的稿子遲遲不來,也難為了他,後來他人已搭上飛機,在旅次中趕出五千多字的稿子,千里傳書。雖然讓我捏一大把冷汗,但是那篇〈一個樂觀主義的心理人對未來社會的想像〉,寫得真是好,依然覺得千恩萬謝。
這到底是好的結局。但也曾策畫的系列專題,少了某一篇,便失去了某一角度的看法,催不來就是催不來,臨時找其他作家為時已晚,終於只能算了。甚至,有回合作舉辦文學獎的單位,得獎作品要出版了,預約的序始終不來,我幫忙去催,到付梓前仍無功而返,最後索性自己「下海」幫忙寫序才算了此公案──這樣的催稿本事,真的可以去跳樓啊。作家對我來說,永遠鞭長莫及!但我怎麼敢把自己這要命的弱點寫出來?以後約稿豈不門戶大開,等著開天窗?所以啊,現在企畫專題時,多半請那比我有個性得多的同事去邀稿,黑臉給他做。不然做主編幹嘛呢?
懇請不要
我很想擬一個投稿公約。編輯檯上所遇,光怪陸離,被「懇請」之事無奇不有:幫忙買書、幫忙寄書、幫忙出書、幫忙傳話、幫忙協尋、幫忙「封鎖」、打擊某人(別懷疑,真有!)……。做為編輯,其實也有不少事想懇請投稿者。
第一,懇請不要抄襲,這是天條。
第二,懇請不要一稿兩投或已刊再投。這不是常識嗎?不,網路新生代──不是讀報長大的一代,對報刊投稿的基本概念遠比老一輩稀薄。
其實現代人更須尊重這個倫理,因為網路的傳播無遠弗屆。以往,在海外地區發表過的作品,在台灣重新發表,尚可接受,畢竟讀者海角天涯,並不重疊,今則不然,只要發表過,大部分網路上都能看到,包括已在自己部落格、臉書發表的作品。(當然有些例外,是副刊主動轉載。)
不知道「網路發表」也算發表,猶可原諒,我還常收到一些投稿信,收件者有一大串,人間副刊、自由副刊各友報,甚至本報繽紛版都名列其上,是要我們幾個副刊主編群組討論由誰來刊載嗎?這種自殺式投稿倒還好,不理會便是了(除非是藝文訊息,不在此限)。糟的是我們不知道對方已經到處投,造成重稿、臨時換版,甚至本報家庭版與繽紛版重複刊登之事,不勝其擾。我遇過最誇張之事,是我剛接任主編不久,某知名出版社投來一位作家的序文。我對「序」的刊登頗感困擾,最害怕看到公關、人情序文。但有些序等於是一篇專業書評,在規畫了星期六的「周末書房」之後,這類序文理所當然可放周六書評版;有些序文其實是很好的散文,評述的不僅是書,更在寫人。那篇序便是這樣的一篇文章,但來得太急,書一個禮拜之後便要上市,聯副是預作版,我評估了一下,還是接受了。那意味著須拿下某篇已經排在版上的文章,讓美編辛苦點,也是新聞線上時有之事。惱的是,在刊出前一天,該出版社編輯打電話告訴我,那篇文章同時也給了人間副刊,對方也將刊出,要我們立即撤版。我心中不免難過,覺得對方欺我資淺,其實那位作者與聯副淵源深厚長年交好,我若打電話請作者自己選擇,稿子未必不會留聯副。但想想那編輯到底是無心之過,這一嚷嚷,小事便成了大事。終於還是默默把稿子撤下來,版再度重做。嘴上跟同事說:以後這家出版社的書概不理會!到底也只說說罷了,不能無辜遷怒作家,這點理智我還有,但初任主編時的冷暖,了然於心。現在想起,坦白說,哪家出版社我還記得,卻完全想不起那位編輯的名字了。
第三,懇請不要把「副刊」當作「訃聞」版。我在加拿大旅行時,晨間拿起旅館提供的地方小報,真讀到過整版的訃聞,覺得挺有意思。但那是旅行中,如果真住下來,會不會每天都想要讀整版的訃聞呢?
懷念逝者的悼念文、悼亡詩是文學史上重要的類型,我並沒有偏見,只要是好作品,沒有拒絕的理由。尤其悼念重要作家、文化人的文章,對讀者深具意義,聯副為此特別設有〈文學紀念冊〉欄目,此中時見令人動容之作。近讀林懷民〈思念Linda──回顧一個奮發的時代〉(105年8月19日聯副),懷念的已不只是俠女吳美雲的身姿,更是一個教人神往的年代。然而悲悼之作,要寫到雋永,有時需要時間的沉澱;多數人等不及,不是呼天搶地、便是通篇歌頌逝者,或則瑣瑣碎碎履歷表一般,還規定刊出時間,要趕告別式的、要趕百日的、要趕七七的都有。曾有某位已擱筆多年的作家,過世後遺孀投來悼念文,那作家亦得過聯合報文學獎的,我趕在告別式前刊登了;不料還有續集,夫人再投來更長的一篇,要求作家百日那天刊載。寫得愈長,愈見文筆平庸,再一查她指定的「百日」那天,恰是母親節,早有安排為世間母親而寫的親情散文。我婉拒了,對方竟「不能接受」,認為不刊登無以告慰逝者在天之靈。
拒絕這類文章須特別謹慎委婉,總覺得對方已經傷心難過,我還嫌人家文筆不好,傷口上撒鹽。而作者往往強調這對他是多麼重要,我當然明白這份情意,可惜對個人有意義,若達不到書寫的感染力,對廣大讀者便沒有太大意義。而每天都有人永別世間,設若來稿必登,副刊絕對成為訃刊。
第四,懇請不要一直改、一直改。寄出的稿件,發覺有錯字、人名、事實的錯誤,去信更正,這原是無可厚非之事,但有些作家簡直改稿成癮,投來之後,不斷置換第二個版本、第三個版本……檔案還自己編了版本1、版本2、版本3、4、5、6、7……,根本打定主意要無止境地改下去,真教人啼笑皆非。
我不明白,除非是有特殊時效的文章,或是我們預約的專欄、專題,趕在截稿日交稿,事後忍不住改稿潤飾,這能理解;若是一般的創作,並沒有人逼著交稿,何以不琢磨至滿意了再投稿?究竟在急什麼呢?對於改稿成癮的作家,我現在已知道凡是他們的文章都先放著不要去整理──反正一定會有新檔案來。麻煩的是,愛改的人,就是會「一直改、一直改」,在你組稿、美編已經排在版上之後,他又來新版本!不熟悉編輯作業的人可能疑惑,把電子檔重新丟上版不就得了?實則不然,除了抓錯別字,各方來稿所用標點、格式無奇不有,有人還習慣每寫一行要斷行一次,或是字裡行間無故到處空格;此外,半形的符號、簡繁體字、異體字的用法,民國或西元紀年、國字或阿拉伯數字都要統一,有的要做小標,拉引言、加欄名,各種編輯工夫不一而足。更麻煩的是,有的作家不僅習慣改稿,而且愈改愈長。回信告訴他,好的,會重新換上新檔,但是拜託請不要再改了,因為長度不同,版須重做。作家卻回信振振有詞:「只加了一段,所以只有那一段要重排,其他都未改。」他不知道紙本不同於電腦,一個版面可容納的字數大致是一定的,文章活生生增加了數百字,怎可能「只有那一段」要重排,不但美編必須重新設計,原來搭配的短文或是詩,也可能就此被擠掉了。還有位作家,最初來稿同意留用時是篇兩千多字的文章,作者每隔一段時間來一個新版本,等到準備上版時點開字數統計,赫然發現近四千字,簡直懷疑是詐欺了。
第五,懇請來稿時,不要告訴我你的經濟情況。最近(唉!每一陣子都會)接到這樣的信函,說本人退休/離職/離婚……後無收入,艱難度日,投稿望採用。寫得很令我心酸。但不能用的還是得退。卻使我心裡蒙上陰影:我是個沒有同情心的人!來稿時,請不要告訴我你的經濟情況。
又有一種作者,退稿後助理來電表示,詩人無法接受,問我何故退稿?我心裡圈圈叉叉。後來有別的作家告訴我:
「此人非常有錢!」
「關我什麼事?」
「他能辦許多活動。」
「我又不參加他的活動。下次讓我的助理去告訴他,我也非常有錢。」
「妳助理是誰?」
「就你啊!」
不能用的還是得退,卻使我心裡蒙上陰影:原來我是個討厭有錢人的人。
真的,來稿時,請不要告訴我你的經濟情況。第六,非十萬火急懇請不要凌晨給編輯臉書morning call。副刊編輯的職業病,視力不良、肩頸僵硬、胃痛、頭痛、坐骨神經痛、手腕關節痛(腕隧道症候群)……自從有了臉書,半夜、清晨不時有稿子來敲門,更搞得我神經衰弱。其實投稿還是使用email信箱為佳,讓編輯可以從容處理,也不會在臉書裡不小心被大量訊息淹沒、遺忘。
第七,懇請不要把副刊編輯當成24小時免費的寫作指導老師。不僅被退的稿子要求指導改進,更有人連小孩、孫子的作文都拿來請教。
第八,懇請不要一次丟來數十萬字,要編輯從中大海淘沙。噢,有的還給你一個部落格網址,要你去裡面選文章,似乎以為編輯非常缺稿。
第九,懇請不要把副刊當作職業介紹所、把編輯當成出版仲介。常有我根本不認識的人,要求我幫他推薦工作,或連一篇文章都未曾在聯副刊登過的寫作者,來信告訴我,他寫得不差,卻沒機會出版,要求我出面向出版社推薦。我並沒有那麼大的面子。
其實還有很多的「懇請」,比如懇請不要老要求編輯順便做其實一點都不「順便」的份外之事。最想說的是:懇請不要一直問、一直問!問某篇文章為什麼不用?問稿子何時刊登?問為什麼很久沒見到某某作家的文章?(天知道為什麼!)權且以此作為「第十」點結束本文吧。但是關於不斷來電逼問對編輯造成的精神恐慌,前面已寫過一篇〈電話〉,這裡就不再一直講、一直講了。
手藝人
台北市政府已禁止在殯儀館張貼輓聯,改用電子跑馬燈的形式。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這些見仁見智的爭議且不談,我感受到的是,又一種「手藝人」慢慢將會消失。專業寫輓聯者,是一種手藝人,他們必須具備基礎的國學素養,一定程度的書法能力,以及對於傳統禮儀的認知。這一行,因為從業者專業能力日漸低落,人們也不甚在乎,其實在還未被公然消滅之前,已經慢慢自行凋萎了。
副刊編輯,包括美術編輯,在我看來,也是一種手藝人;是不是「保育類」我不知道,但這門手藝,無論如何不希望在自己手裡斷絕。
有時被作家、讀者抱怨,電子板副刊文章不好找、時有誤植……,我除了儘速請求更正,忍不住對抱怨者說:「也許,這正好提醒您,重新回來看紙本副刊呢。」老王賣瓜一下吧,每當聽到作家,尤其是美學行家,例如蔣勳老師,對我說一句:「今天副刊版面真美。」那真是樂上心頭。有一回,學者林谷芳接待大陸學者時,拿出當日聯副展示,主文正是林谷芳〈真山真水〉,搭配畫家林崇漢氣勢磅礡的插畫,標題為楷書書法。大陸學者嘖嘖稱奇:「這年頭,還有人這樣子編版?」這就是手藝人的版面,也是台灣副刊引以為傲之處。
一個版面的完成,不是編輯從大批來稿中審稿、選稿,或者把稿件約來就算了事。文章份量適宜作為主文者,首先要向風格適宜的插畫家邀約插圖,如果是描述旅行、人物之作,會向作者請求提供照片,或到報社的資料庫尋找、四處向攝影家張羅。主編的腦海裡,會先有一個發表時畫面的整體想像。以〈真山真水〉為例,作者雖傳來了文中提到的富春江照片,但效果不佳,於是我把文章和照片一併傳給崇漢兄參考,讓畫家畫出他胸壑裡的「真山真水」。副刊的插畫家,不折不扣是手藝人。
今日的聯合副刊,一天整版約五千字,在組版時,三千開外的主文,通常搭配一篇千把字的短文,一首詩,再加一兩則小品文、最短篇或是文訊等等。算術差的主編如我,每天是拿著計算機組版的。也因此文章刊出的速度,除了作品本身有其「輕重緩急」,有時字數也決定了它的命運。例如長詩比短詩排隊排得久,因為要等待特別短的主文它才上得去。這些作品,經過編輯整理、加小標、抓引言或寫編按、圖說之後,編排設計是美術編輯的工作。早年聯副有自己的美編,還好幾位!現在全部歸屬美術中心,但美術中心主任對於副刊的美編有特別要求:必須先讀過文章的內容,再來排版。先領略作品的內涵,才能表現最適切的氛圍。小說、散文創作有各種風格的插畫作為主視覺;而聯副談古典文學、美學、戲劇的文章也不少,於是讀者會看到某日頭題為王德威教授的〈古典與青春〉,版面邊緣,壓著半個淡淡的京劇臉譜,那是講述國光京劇十四年的文章;張曉風教授的〈一部美如古蕃錦的《花間集》〉,版面邊緣,則裝飾著古典剪紙圖案。如果內容寫的是關於中國古典小說、書法,版面上可能會出現線裝書的襯底,或是標題上加小小的紅圈,一如古人的句讀,或是古意盎然的紅色章印。有些標題使用印刷體,有些標題請人寫書法……這些,都是「手藝人」的手筆。
我的辦公室座位後方牆上,張貼著未來七天所有組好的版面,工作中,會不時站起來,端詳每一個版面的視覺是否適切,有時移來挪去,像室內設計師,這裡補個光,那裡要留白。
美編組好的版面,交由編輯仔細校對,完成後我會再讀一次,有時再「修潤」一遍。聯副的文章名家多,很少改動,多半只訂正錯字、標點,或是事實的錯誤;繽紛版、家庭版的文章,素人為多,常有好故事,只是文字須再斟酌,編輯潤飾後,往往能清朗有神。校對、潤稿,都是手藝人的工夫。改正、清版、確認後,主編簽了名,才能夠發版、印刷。
這整個製作的程序,最初始,來自最可敬的「手藝人」,即作家(許多作家,如朱天心常以此自況),然後有編輯、插畫家或是攝影師、美術編輯、印刷工作者的通力合作,才成為第二天讀者手中的報紙副刊。請不要怪我老派、頑冥,我實在要說,不看副刊也就算了,既然讀副刊,如果不看整體版面的呈現,而只從電腦中點出一條一條的稿子,真的好可惜,好可惜!這是許多手藝人一環扣一環,把每一個版,都當作一個工藝品精雕細琢而成。這是編輯對作家、作品的心意,也是對讀者的誠意。
我知道許多作家至今仍然非常在乎在副刊的發表,不盡然是因為稿費,也不是為了宣傳,他們自己的臉書就門庭若市,他們珍惜,並且收藏這整個美感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