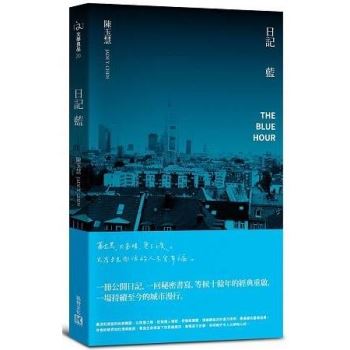Munich, Nov 1st
I
病痛已逐漸變成一個令自己避而遠之的字。偶而覺得病痛是懲罰,但為什麼?我做錯什麼?
II
善心的台灣醫生要我多祈禱,他在家無事也會為我祈禱。我也有含淚祈禱的時候,但不知向那個神,耶穌上帝?佛陀?阿拉?我幾乎都相信他們。但我沒有真的祈禱下去。我找不到話語與神溝通,神既然是全知,那麼我不必說什麼,神也必然知悉。黑格爾是對的,超越的神將人類逐出樂園後,人類不但對神,從此與自身的情感終將成為陌路。
一個德國女友說,她兒時不敢到外婆家也不敢上學,因外婆家和教室上都置掛著神殤,血淋淋的神殤像,使她晚上不停做惡夢。而我小時候在台灣的廟裡看過太多遭香火燻黑的神像,看過道士及乩童近於殘忍的做法,雖然那與神祇可能也無關,但也使我愈發離開了神。
我雖離開神,但其實很想回來靠近神。很想要對神說說話。
Munich, Nov 16th
I
走在陽光普照的市區,一條通往市場的路,或者一條通往牙醫診所的路,除了痛,我完全沒有任何可抱怨的了,走過伊薩河城門時,我突然有一個奇怪的念頭:此時就算有人在我身上刺上一刀,我也無所謂。
那是十七年前的事了,感覺上像昨天。被扯斷的珍珠項鍊一顆一顆掉在大理石地上的聲音和畫面,刀子按在皮膚上的冷感,彷彿像刺青,像一個我從來不想保留的刺青圖案。
但我終究保留下來。
II
經過市場的肉店時,德式煮肉片(Gekocht schinken)的味道迎面撲來,使我想到了孔子。
Munich, Dec 23rd
換新電腦後,打上電腦銀幕上的字變得如此碩大。文字似乎更不可信賴了。
Hong Kong, Jul 22nd
I
快速地推著手推車在香港機場的地毯上行走。
II
候機時我打電話給他,他是我丈夫。他說:我以為您已經忘記我了。
Bodensee, Jul 26th
在瑞士湖(Bodensee)邊一家餐館,在戶外坐著,桌旁的男人喜歡說話,他曾在阿爾及利亞當過兵,那是太久遠的事了,他說,你可以知道許多,但你不一定真的瞭解什麼。他強調Begreifen(瞭解)這個德文字。他還強調:還好我老得可以不必學上網。Turin, Jul 30th
I
我們開車抵達義大利,在尼采靈魂飄泊的杜林。整個城在週日中午沒有一個人。連條狗也沒有。問路時只聽到說話速度極快的婦人說了三次Subito(馬上)。
杜林的建築像西西島的巴勒摩,我和M在Lorenzo教堂裡看耶穌的裹屍布。
II
在瑞士的旅館吃早餐,中餐在義大利杜林火車站附近,而晚餐則在法國的安涅西城(Annecy)。
Verona, Oct 20th
維洛納(Verona)的圓型劇場本來有五公尺,在一次大地震後,只剩下一尺高。
站在可容納三萬人的劇場裡,想像當初維洛納的市民如何買票走入這個劇場,他們如何把獅子和老虎趕進劇場中央,讓基督徒如何赤手與猛獸博鬥,異教徒維洛納人說,「讓你們無能的神來拯救你們吧。」基督徒不斷被羅馬人譏笑懲罰,甚至處死。
現在,幾個美國德州來的婦人坐在石椅座位上照相。再照相。
遠處,劇場最高處,一個年輕人以英國口音的英文嘹亮地喊著:I’ll kill all of you(我要把你們全殺光)。他似乎在測試劇場的回音音效(果然無以倫比),那幾個美國婦人大笑起來。
Verona, Oct 21st
I
傍晚在維洛納城中心菜市場買了三隻柿子。經過一群群盛裝出來喝一杯的當地年輕人,M說,九一一事件沒給這裡帶來任何影響。他們的右派總理已經明確表示不會加入美國打擊恐怖分子的陸地行動。
II
他們的總理還說:我們西方文明比伊斯蘭文明優越。
Verona, Oct 22nd
已經十月下旬了,小雨稍歇的維洛納城裡街道轉涼,坐在露天座上吃義大利蒜油麵,這是家常菜,最簡單的食物最好吃。M說,窮人的食物最好吃。兩個情人在我們吃飯的時候,在對街站著擁吻了一餐飯的時間。Florence, Oct 24th
誰建造佛羅倫斯誰就是神。—Anatole France
法國作家史湯達爾(Stendhal)也來過這裡,他說,這個城市美得令他得了文化震撼症,後來又稱史湯達爾症候群(The Stendhal Syndrome)。
Castel del Piano, Oct 25th
亞米雅達山(Monte Amiata)是滑雪渡假區,山下是老鎮。一片片山毛櫸樹林開始光禿,沿路至山頂都是無人的褐色系度假木屋,無人、荒涼。山上平台有旅館,一個男人坐在旅館前曬太陽,他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
山頂有一尊一九三九年建的聖母像。那是墨索尼(Benito Mussolini)的極右年代,聖母像是白色大理石雕刻,表情頗詳和。聖母像四周是鐵柵欄,鐵架上結紮著來訪觀光客留下的紀念品:手帕、佛珠、項鍊、衛生紙、拍立得照片。我和M找不到任何隨身的物品,除了里拉紙鈔和鑰匙。
我什麼也沒留下。什麼也不必留下。
往山下走時,一個老人(或許也不老)成功地向我們賣出我們並不需要的蜂蜜和自製香腸。他強調,這香腸是他自己做的,說時,他還拉起他忘了拉的褲襠拉鍊。
Montalcino, Oct 25th
非平面性的鬥爭:二隻壁虎在我們住的托斯坎尼石屋牆壁上打鬥,一隻沒有尾巴,但凶悍無比,另一隻較年輕,在打鬥時不小心垂直掉落在草地上。
Montalcino, Oct 26th
他們住在十九世紀時市長住過的房子,那房子的壁爐蓋在一間小房子裡,我們一起坐在那壁爐房裡烤栗子。他提起炭疽熱時,認為是媒體協助美國政府宣傳的把戲。他說的可能也有理。他年輕時代是共產黨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毛派。年紀大了以後遷居來托斯坎尼山區,他現在有個工作:房屋仲介。他的顧客都是德國人。他說他什麼也不需要,一點紅酒一點麵包,一個女人就夠了。
不巧的是,他現在有二個女人。我們烤栗子吃時,二個女人為他爭風吃醋。那二個女人和他一起住在那棟市長的房子。他們有一個滿好的地址:2 Via Roma。羅馬街二號。
Montalcino, Oct 27th
彎往山路之前,我和M走進一家餐館。那餐館也有壁爐,女主人在聽完我們不流暢的義大利文點菜後,總是一律回答:完美(Perfecto)。Castel del Piano, Oct 30th
義大利小鎮的一家平常餐館牆上貼著二種菜單,一種給義大利人,一種給美國人。給美國人的菜單上是漢堡、熱狗和薯條。
餐館有一個穿粉紅洋裝的義大利婦人,她忙著烤披薩又忙著送菜送酒,她的丈夫是一個穿西裝及黑鞋白襪的男人,他只負責與二位來喝酒的男人說話,什麼都不管。我們不小心向他點菜,他立刻呼喚他正在廚房忙得不可開交的妻子出來。
Montepulciano, Oct 31st
我站在教堂前面的台階上,想給住在加州的P寫明信片,這裡是普契亞諾山城(Montepulciano)。這裡有股神秘力量在召喚我。跟宗教無關,比較是人類文化裡的符號及隱喻。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羅馬》(Roma)影片中,有人對別人的腦後丟番茄,而高達(Jean-Luc Godard)的電影《輕蔑》(Le Mepris)是在義大利卡皮島上拍的,我喜歡的男演員皮可利總戴著一頂帽子。我雖然喜歡高達的電影,但卻更同情於楚浮(François Truffaut)的人物。
想同時告訴P幾件事:高達是被溺愛的孩子,而楚浮則是無愛的孩子。他們長大之後成為絕然不同的人。他們也拍絕然不同的電影
而在義大利,我覺得像回到家。羅馬文化的重量並未欺壓於義大利人的現代生活之上,他們的生活不但不輕浮,還保留了古文化的氣息。義大利人可以穿著他們的名牌衣服去教堂做彌撒,回家之後發脾氣罵小孩,下午三點吃他們的義大利蒜油麵。
我要告訴P的是,我在托斯坎尼看過像朱熹形容的天光雲影,那可能也是文藝復興偉大畫家所描繪的光源。我也要告訴她,以後或者也會告訴別人,我從來沒有真的喜歡過大自然,如果有的話,是在托斯坎尼。
以及,我也要告訴他,我愛M,我真的愛他。
I
病痛已逐漸變成一個令自己避而遠之的字。偶而覺得病痛是懲罰,但為什麼?我做錯什麼?
II
善心的台灣醫生要我多祈禱,他在家無事也會為我祈禱。我也有含淚祈禱的時候,但不知向那個神,耶穌上帝?佛陀?阿拉?我幾乎都相信他們。但我沒有真的祈禱下去。我找不到話語與神溝通,神既然是全知,那麼我不必說什麼,神也必然知悉。黑格爾是對的,超越的神將人類逐出樂園後,人類不但對神,從此與自身的情感終將成為陌路。
一個德國女友說,她兒時不敢到外婆家也不敢上學,因外婆家和教室上都置掛著神殤,血淋淋的神殤像,使她晚上不停做惡夢。而我小時候在台灣的廟裡看過太多遭香火燻黑的神像,看過道士及乩童近於殘忍的做法,雖然那與神祇可能也無關,但也使我愈發離開了神。
我雖離開神,但其實很想回來靠近神。很想要對神說說話。
Munich, Nov 16th
I
走在陽光普照的市區,一條通往市場的路,或者一條通往牙醫診所的路,除了痛,我完全沒有任何可抱怨的了,走過伊薩河城門時,我突然有一個奇怪的念頭:此時就算有人在我身上刺上一刀,我也無所謂。
那是十七年前的事了,感覺上像昨天。被扯斷的珍珠項鍊一顆一顆掉在大理石地上的聲音和畫面,刀子按在皮膚上的冷感,彷彿像刺青,像一個我從來不想保留的刺青圖案。
但我終究保留下來。
II
經過市場的肉店時,德式煮肉片(Gekocht schinken)的味道迎面撲來,使我想到了孔子。
Munich, Dec 23rd
換新電腦後,打上電腦銀幕上的字變得如此碩大。文字似乎更不可信賴了。
Hong Kong, Jul 22nd
I
快速地推著手推車在香港機場的地毯上行走。
II
候機時我打電話給他,他是我丈夫。他說:我以為您已經忘記我了。
Bodensee, Jul 26th
在瑞士湖(Bodensee)邊一家餐館,在戶外坐著,桌旁的男人喜歡說話,他曾在阿爾及利亞當過兵,那是太久遠的事了,他說,你可以知道許多,但你不一定真的瞭解什麼。他強調Begreifen(瞭解)這個德文字。他還強調:還好我老得可以不必學上網。Turin, Jul 30th
I
我們開車抵達義大利,在尼采靈魂飄泊的杜林。整個城在週日中午沒有一個人。連條狗也沒有。問路時只聽到說話速度極快的婦人說了三次Subito(馬上)。
杜林的建築像西西島的巴勒摩,我和M在Lorenzo教堂裡看耶穌的裹屍布。
II
在瑞士的旅館吃早餐,中餐在義大利杜林火車站附近,而晚餐則在法國的安涅西城(Annecy)。
Verona, Oct 20th
維洛納(Verona)的圓型劇場本來有五公尺,在一次大地震後,只剩下一尺高。
站在可容納三萬人的劇場裡,想像當初維洛納的市民如何買票走入這個劇場,他們如何把獅子和老虎趕進劇場中央,讓基督徒如何赤手與猛獸博鬥,異教徒維洛納人說,「讓你們無能的神來拯救你們吧。」基督徒不斷被羅馬人譏笑懲罰,甚至處死。
現在,幾個美國德州來的婦人坐在石椅座位上照相。再照相。
遠處,劇場最高處,一個年輕人以英國口音的英文嘹亮地喊著:I’ll kill all of you(我要把你們全殺光)。他似乎在測試劇場的回音音效(果然無以倫比),那幾個美國婦人大笑起來。
Verona, Oct 21st
I
傍晚在維洛納城中心菜市場買了三隻柿子。經過一群群盛裝出來喝一杯的當地年輕人,M說,九一一事件沒給這裡帶來任何影響。他們的右派總理已經明確表示不會加入美國打擊恐怖分子的陸地行動。
II
他們的總理還說:我們西方文明比伊斯蘭文明優越。
Verona, Oct 22nd
已經十月下旬了,小雨稍歇的維洛納城裡街道轉涼,坐在露天座上吃義大利蒜油麵,這是家常菜,最簡單的食物最好吃。M說,窮人的食物最好吃。兩個情人在我們吃飯的時候,在對街站著擁吻了一餐飯的時間。Florence, Oct 24th
誰建造佛羅倫斯誰就是神。—Anatole France
法國作家史湯達爾(Stendhal)也來過這裡,他說,這個城市美得令他得了文化震撼症,後來又稱史湯達爾症候群(The Stendhal Syndrome)。
Castel del Piano, Oct 25th
亞米雅達山(Monte Amiata)是滑雪渡假區,山下是老鎮。一片片山毛櫸樹林開始光禿,沿路至山頂都是無人的褐色系度假木屋,無人、荒涼。山上平台有旅館,一個男人坐在旅館前曬太陽,他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
山頂有一尊一九三九年建的聖母像。那是墨索尼(Benito Mussolini)的極右年代,聖母像是白色大理石雕刻,表情頗詳和。聖母像四周是鐵柵欄,鐵架上結紮著來訪觀光客留下的紀念品:手帕、佛珠、項鍊、衛生紙、拍立得照片。我和M找不到任何隨身的物品,除了里拉紙鈔和鑰匙。
我什麼也沒留下。什麼也不必留下。
往山下走時,一個老人(或許也不老)成功地向我們賣出我們並不需要的蜂蜜和自製香腸。他強調,這香腸是他自己做的,說時,他還拉起他忘了拉的褲襠拉鍊。
Montalcino, Oct 25th
非平面性的鬥爭:二隻壁虎在我們住的托斯坎尼石屋牆壁上打鬥,一隻沒有尾巴,但凶悍無比,另一隻較年輕,在打鬥時不小心垂直掉落在草地上。
Montalcino, Oct 26th
他們住在十九世紀時市長住過的房子,那房子的壁爐蓋在一間小房子裡,我們一起坐在那壁爐房裡烤栗子。他提起炭疽熱時,認為是媒體協助美國政府宣傳的把戲。他說的可能也有理。他年輕時代是共產黨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毛派。年紀大了以後遷居來托斯坎尼山區,他現在有個工作:房屋仲介。他的顧客都是德國人。他說他什麼也不需要,一點紅酒一點麵包,一個女人就夠了。
不巧的是,他現在有二個女人。我們烤栗子吃時,二個女人為他爭風吃醋。那二個女人和他一起住在那棟市長的房子。他們有一個滿好的地址:2 Via Roma。羅馬街二號。
Montalcino, Oct 27th
彎往山路之前,我和M走進一家餐館。那餐館也有壁爐,女主人在聽完我們不流暢的義大利文點菜後,總是一律回答:完美(Perfecto)。Castel del Piano, Oct 30th
義大利小鎮的一家平常餐館牆上貼著二種菜單,一種給義大利人,一種給美國人。給美國人的菜單上是漢堡、熱狗和薯條。
餐館有一個穿粉紅洋裝的義大利婦人,她忙著烤披薩又忙著送菜送酒,她的丈夫是一個穿西裝及黑鞋白襪的男人,他只負責與二位來喝酒的男人說話,什麼都不管。我們不小心向他點菜,他立刻呼喚他正在廚房忙得不可開交的妻子出來。
Montepulciano, Oct 31st
我站在教堂前面的台階上,想給住在加州的P寫明信片,這裡是普契亞諾山城(Montepulciano)。這裡有股神秘力量在召喚我。跟宗教無關,比較是人類文化裡的符號及隱喻。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羅馬》(Roma)影片中,有人對別人的腦後丟番茄,而高達(Jean-Luc Godard)的電影《輕蔑》(Le Mepris)是在義大利卡皮島上拍的,我喜歡的男演員皮可利總戴著一頂帽子。我雖然喜歡高達的電影,但卻更同情於楚浮(François Truffaut)的人物。
想同時告訴P幾件事:高達是被溺愛的孩子,而楚浮則是無愛的孩子。他們長大之後成為絕然不同的人。他們也拍絕然不同的電影
而在義大利,我覺得像回到家。羅馬文化的重量並未欺壓於義大利人的現代生活之上,他們的生活不但不輕浮,還保留了古文化的氣息。義大利人可以穿著他們的名牌衣服去教堂做彌撒,回家之後發脾氣罵小孩,下午三點吃他們的義大利蒜油麵。
我要告訴P的是,我在托斯坎尼看過像朱熹形容的天光雲影,那可能也是文藝復興偉大畫家所描繪的光源。我也要告訴她,以後或者也會告訴別人,我從來沒有真的喜歡過大自然,如果有的話,是在托斯坎尼。
以及,我也要告訴他,我愛M,我真的愛他。